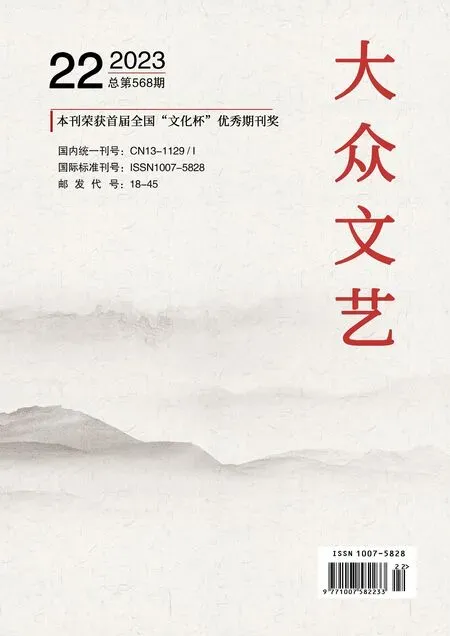论气候小说《水刀子》中的中国形象*
汤 越
(河海大学外国语学院,江苏南京 211100)
近年来,地球正持续深受人类活动印迹的烙刻,进入了以全球气候变化为核心表征的人类世时代,温室气体排放量的大幅增加给人类带来一系列的环境问题。与此同时,脱胎于科幻文学的气候小说应运而生并蓬勃发展,成为21世纪之交的一种独具特色的文学题材,明确以气候变化为主题的作品得以涌现。其中,美国新锐作家保罗·巴奇加卢皮(Paolo Bacigalupi,1972-)崭露头角,其著作畅销全球,自1999年发表第一篇文学作品以来,他一向关注气候变化的现实观照和文学想象的融合。巴奇加卢皮在大学学习期间主修东亚文化研究,毕业后曾前往中国旅居过一段时间,其作品往往带有浓郁的东方色彩,蕴含丰富的中国元素。
作为巴奇加卢皮的代表作之一,《水刀子》(The Water Knife,2015)化抽象宏大的气候变化进程为一帧帧具体可感的画面,通过生态灾难叙事构建近未来美国中西部社会,处于旱灾中的各州为抢夺水资源冲突不断,三位主人公安裘(Angel)、露西(Lucy)和玛丽亚(Maria)因科罗拉多河水源归属的最优先“水权”文件而命运相连、命途多舛。值得关注的是,小说大量描写中国,体现出作者对中国虚实交织的文学想象,乃至对中国在气候问题治理进程中扮演何种角色的思考。有鉴于此,本文借助比较文学形象学理论系统分析巴奇加卢皮在《水刀子》中塑造的多维中国形象,阐释其书写中国形象的内在动机与意义。此个案研究透过表层叙事进入形象背后,既对深入西方世界的中国认知层面具有借鉴意义,又对中国形象的丰富和完善提供一定的启示作用。
一、形象表征:中国书写的两种面向
本质上,形象具有多义性。它“是在文学化,同时也是社会化的过程中得到地对异国认识的总和”[1]。比较文学形象学主要研究的是某国文学对他国国家形象的塑造。国家形象是主体对客体的主观认知与评判的产物,可以分为三部分:“客观存在的‘源像’”“自己所构建的自塑形象”和“国外传播形成的他塑形象”[2],内嵌着真实和幻想于一体的复杂且丰富的意蕴。巴奇加卢皮笔下的中国形象褒贬兼具,在小说《水刀子》中展现出截然不同的两副面孔,以及美化和丑化并存的情感趋向。
一方面,小说中有关中国的正面叙事格外突出,塑造了实力强大的中国形象。在《水刀子》中,巴奇加卢皮将中国视为拯救气候末日图景的典范,为美国西南部城市提供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缓解水资源短缺问题的基础设施,积极帮助他们进行气候治理,通过太阳能计划资助、兴建“泰阳特区”“柏树特区”等环境舒适的生态特区和抗灾建筑,建造大型垂直农场,并与红十字会联手合赠亲善水泵,使富人等精英阶层在沙暴肆虐、水源匮乏的加利福尼亚州和内华达州幸免于难。在玛丽亚父亲眼里,中国人十分擅长造屋,“很会办大事”。玛丽亚的朋友图米也称赞中国人不浪费东西,他们将生态建筑周围公厕留下的残余物变成肥料,为特区的绿色植物增添营养。小说中的中国人还具备极强的决策力和洞察力,“比断背般的美国更能抗压”,能够借助动物预言未来灾难,并果断采取应对措施。凯斯认为中国人很懂得平衡利益,“非常会处理麻烦事”。
再者,中国被勾勒成令无数美国人梦寐以求的国度,成为气候难民向往的人间天堂。作者借玛丽亚及其父亲的视角传达了人们对中国的憧憬。玛丽亚父亲的梦想是有能力克服逃离凤凰城路途中的艰难困阻,远渡重洋到达重庆或昆明,在“中国人的蓄水池”——湄公河或长江上游的水坝工作。玛丽亚拼命地学习中文,用中国人到处派发的一次性平板电脑奋力学习,她有时会梦见自己一家正坐在赶赴中国的船上,一路划向她心中的“应许之地”。另外,人民币成为与美元并行的世界货币,甚至更受人青睐。“泰阳特区”的附近居民皆认识人民币的模样,工人们所领取的工资全是纸质人民币,商贩们为商品标价也都使用了人民币和美元的双货币形式,例如玛利亚在卖水时就吆喝,“2美元一壶,1块人民币一杯。”不仅如此,相较之美元,人们更倾向于接受人民币。小说中露西递给酒保一张50美元钞票却惨遭嫌弃,“女酒保望着钞票,好像见到狗屎一样”,向露西询问是否有人民币更换。
另一方面,《水刀子》中对中国的描述不仅凸显对中国的“仰视”态度,还滋生了“俯视”态度,关于中国的负面叙事在小说中亦有所体现。巴奇加卢皮在小说中描绘了西方对中国人的刻板印象,透露出对中国的偏见与曲解。在露西的朋友杰米看来,中国人经常戏弄美国人,他们总是“被中国人耍得团团转”。露西在一桩枪击案现场看见有中国人遇害时,其朋友提莫的第一反应是“这下糟了,中国人不喜欢枪战波及他们”[3](302)。从中可以窥见,巴奇加卢皮设想着中国凭借卓越的核心技术和高超的制造水平进军美国市场,趁机牟取私利的形象。同时,自私自利、冷酷无情的消极标签也被作者贴附在了中国人身上,对中国救济者的形象添加污点,进行污名化处理。
无疑,《水刀子》动态多维地生产出中国形象的双重叠加姿态,相背而行的形象均是对中国作为“他者”存在的想象。巴奇加卢皮采用“矛盾与并行”的艺术手法进行中国书写与一体两面的文学幻想,从表面上看,正负两面的形象具有难以调和的矛盾性。然则,从深层视之,两种形象是辩证地相互关联的。小说中西方看待中国的两种态度的界限并非泾渭分明、贯穿始终的,两者有着一致的同构意图。
二、潜在动因:中国叙事的双重根由
究其原因,小说中他者的中国形象建构同作者个人的文化体悟与特殊感受紧密相连,凝聚了作者“亲历性”的个人生活体验和思考。整体而言,作为态度主体,巴奇加卢皮对中国的个体认知是积极的,这基于现实中国的国际影响力和地位的提升,与中国的海外国民日益增多,文化输出能力日渐增强密切相关。值得注意的是,气候变化是超越地方性的全球现象,是全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任何人、任何国家都无法独善其身。《水刀子》作为气候小说,通过构筑非单一化的中国形象来揭示全球气候变化的“超级物”特性,从更广阔的视域表现气候问题的巨大时空尺度。除此之外,西方对中国的情感与对气候变化在诸多方面有相似之处,即对气候危机的忌惮、焦虑和反思等复杂情绪同样体现在文本世界中作者对中国形象的创造。
然而,虽然小说中的中国形象是作者主观叙事的结果,负荷着巴奇加卢皮的“想象和欲望投射,但并非纯粹的个人行为”[4]。根据形象学的观点,一切形象的设定皆以乌托邦或意识形态为逻辑起点。无论对中国或褒或贬的看法,其实质都是对异族他者的“社会集体想象”,它建立在乌托邦和意识形态“两极间的张力上”[5],将中国形象置于西方话语谱系中加以形塑。作者对中国形象的正面与负面叙事是一种“社会集体想象物”,分别对应着这两极之间。法国学者让-马克·莫哈指出,用离心的、符合一个作者(或一个群体)对相异性独特看法的话语塑造出的异国形象是乌托邦的;按照社会模式、完全使用本社会话语重塑出的异国形象则是意识形态的[6]。此外,作者对中国的主体想象存在一定程度的局限和偏颇之处,由此可见,对中国叙事的深层缘由进行内在、本质的研究,以及对小说中中国形象的判断与甄别至关重要。
“乌托邦”源自托马斯·莫尔创作的《乌托邦》,表示“一种理想的但并不存在的政治及社会生活方式”[7],囊括“美好”“理想”抑或“缥缈”“虚幻”的内涵。《水刀子》将无形的未来气候风险有形化,社会动荡、环境恶化、灾难四伏等问题愈加严重。值此背景,作者将“救世”愿望寄托在大洋彼岸的中国,擘画中国引领全球解决气候灾难的蓝图,使中国成为以玛丽亚为代表的美国各州民众仰慕的对象,把中国实力当作自我赶超的目标,树立“美好中国”的别国形象,借此更有效地自我勉励与鞭笞。但是,“乌托邦”式的中国形象“冒着将他者理想化的危险”[8],趁机推诿、转嫁本国的环境责任,用形而上的借口和美丽托词夸大、强化中国义务与责任,看似称赞中国担当,实则乘隙实施捧杀,从而使人们对中国报以过高的期望,悄然把中国纳入西方话语体系之中。
在《水刀子》中,作者鲜明地呈现中国形象的意识形态化趋势。“意识形态”背后蕴藏着“复杂的社会关系结构与主体认同活动”[9]。小说中对中国人的描述充溢着贬低和歪解,使西方视野中的刻板化中国形象跃然纸上,映射出作者对中国形象的凝视和抹黑行为,体现了巴奇加卢皮遵循西方主流社会中的种族歧视意识形态的逻辑,“离引发出形象制作过程的原始认知相去甚远”[10]。中国形象“意识形态”化是西方帝国话语渗透文本叙事的再现,旨在言说、肯定自我,以便筑牢西方对中国的固有认知,更好地进行国家身份的认同。由此不难洞见,《水刀子》中的中国形象塑造,是一种庞杂的文化交流和误读现象,突显了在日益严峻的气候危机的催逼之下,以巴奇加卢皮为典型的西方作家对人类世困境的思量,通过“社会集体想象”完成对中国形象的“乌托邦”和“意识形态”书写,以至对人类世话语主导权的争夺和占有,这是作者塑造中国形象的根本意图与基本机理。
三、意义生成:中国形象的世界形塑
众所周知,文学创作是一种精神生产活动,其价值指向与终极旨趣是实现意义和思想观念的双向开掘。巴奇加卢皮为中国形象注入特殊意义,使中国形象承载多重意义,变成包孕着不同意义的符号和载体。中国形象的意义生成场域是由多方一同建构,经历了从意义探索与预设到意义诠释与解读,再到意义最终生成的阶段。总体而言,挖掘小说中的中国形象的意义生成路径和内在含义具有重要意义。
巴奇加卢皮以人类世的透镜观照中国,借用极富想象力的笔触完成了对中国形象的整体构造,文本中的中国元素也发挥其“认知、情感、意动的功能”[11]。《水刀子》首次问世于名为《高地国家新闻》的美国杂志上,显然第一批受众群体大多数是西方读者,因此小说中的中国形象既让人们对中国形成基本认识,又能使人们倚靠自身原有认知读取作者设置的意义编码,能动地进行再阐释。虽然作者在小说中创造的毁誉参半的中国形象会对西方读者产生一定的涟漪效应,但不会影响读者通过重构、承认和反抗来进行形象解码,进而突破定势思维、催生出相关意义。此外,小说中人物对中国的个人表述和情感诉说,价值评判性和指涉性明显,且多用集体名词“中国人”,而不是具体到某个个体,比如杰米和提莫对中国的描述,皆以“中国人”为人称主语,这可能存在普泛化和不够客观真实的问题,引起西方读者思考。
不可否认,书写中国形象是以更全面地理解和维护本国形象为鹄的。相应地,研究中国形象的他塑是为了更好地自塑。中国形象的自塑依赖于自我与他者的异质差异。自《水刀子》中译本出版以来,这部作品备受中国研究者和读者关注。小说中以西方价值准则为核心塑造的褒贬不一的中国形象生发持续影响力,其带来的正负反馈的两种效应对中国的国族认知、认同有所冲击,但也在很大程度上使中国学者和读者深厚关切自我价值体系,仔细判别西方语境下的中国形象,探寻平等互补的主体间关系,追求正确的形象认知新维度,以推动中国形象迈向立体、客观。中国形象的西方创作潜藏着强大的话语潜能,这也使中国形象在广袤的中国本土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助力中国气候小说家创作优秀作品,为真实的中国形象发声与正名。
作为气候小说,《水刀子》对知悉气候变化向地球生存状态施加的影响意义重大,并且小说以中国为参照和对比,其中的中国形象塑造冲破时空阈值,对探求和思考人类应对全球性气候危机可能存在的选择有着长远意义。巴奇加卢皮笔下的美国各州不但是一片干旱肆虐的末世废土景象,更是有中国参与的“杂糅开放的动态空间”[12]。作者基于全球气候变化挑战,构思了人类世共同体,这有助于提高人类对气候变化的重视,培育全球化视野,形成利益共同体,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度探讨复杂多变的气候问题。
四、结语
当代外国文学中的中国形象书写,正如雨后春笋般兴旺起来,作品中的中国形象塑造提供了一个充满学术生长力的研究支点。《水刀子》基于直接、残酷的环境报道,将事实性研究与推测性想象有机结合,摇摆于历史的灾殃和未来的忧虑间,在生态使命的感召下,作者以一个全新的创想维度书写“明日中国”形象。对此,研究作者所构想的中国形象的积极与消极面向,以及两种形象的制衡和共存关系、形塑原因与生成意义尤为重要,这益于中国形象挣脱西方话语“他者”化的樊笼,发挥塑造本国国家形象的能动性和自主性。巴奇加卢皮将中国形象深潜于文字中,他用特有的思想底蕴和艺术表达方式构建符合人类发展趋势的气候话语网络,折射出东西方国家共同找寻人类世困境出路的有力尝试。中国形象的生成是动态且不断发展的,中国作家应致力于在文学作品中传播中国声音、讲好中国故事,呈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西方应以平等尊重、包容理解的心态关注中国,彼此间博采众长、纳其精华,这样才能真正实现双方的“正面增值”,抵达“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大同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