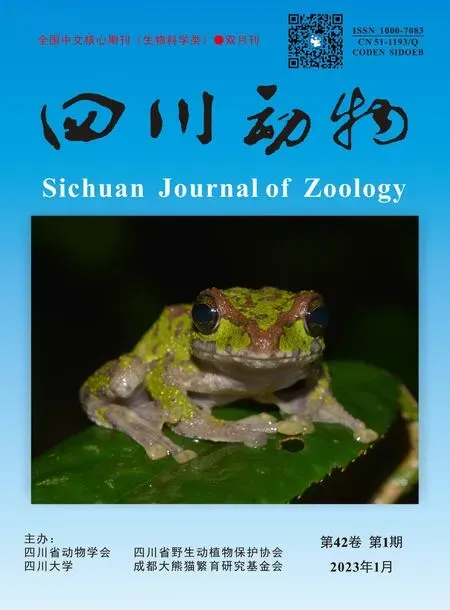广州城市绿地留鸟嵌套分布格局及其影响因素
袁倩敏 , 邓卓迪 , 梁健超, 胡慧建, 丁志锋
(1.广东省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广东省动物保护与资源利用重点实验室,广东省野生动物保护与利用公共实验室,广州510260; 2.广东海洋大学滨海农业学院,广东湛江524088)
全球城市化的规模、速度都在快速上升(Elmqvistet al.,2013),尤其是珠江三角洲的城市化更成为全球之最。城市化进程让原先自然的、连续分布的林地转变为多个间隔分布的林地斑块或城市公园(Souléet al.,1988),导致城市动物特别是鸟类种群下降甚至敏感种的灭绝(McKinney,2006;Elmqvistet al.,2013)。然而,与大量研究关注城市化对鸟类多样性分布及种群数量变化相比,有关城市鸟类群落组成结构,如嵌套格局在城市化环境下的变化规律,仍较少被关注(Tanet al.,2021)。
物种分布的嵌套性是指物种丰富度较低斑块(或岛屿)的物种是物种丰富度较高斑块(或岛屿)的物种的一个适当子集(Darlington,1957)。群落嵌套现象自20世纪50年代提出后(Darlington,1957),经过方法学的发展(Patterson & Atmar,1986)、形成机制的探讨后(Patterson & Atmar,1986;Blake,1991;Andrén,1994;Cook & Quinn,1995),已逐步成为生物地理学和保护生物学领域重要的研究主题之一(Wrightet al.,1998)。
一般来说,嵌套格局的形成与被动取样、选择性灭绝、选择性迁入、生境嵌套及人为干扰有关(Cook & Quinn,1995;Wrightet al.,1998;Fernández-Juricic,2002)。这些形成机理并非相互排斥,而是可能组合在一起共同影响生物群落的嵌套结构(Boecklen,1997)。群落嵌套性的研究不仅能够丰富和发展城市鸟类研究内容,而且能够为保护区布局和设计、SLOSS争论(是单个大的还是多个小的斑块能保护更多的物种;Ovaskainen,2002)和最小集问题(为确保区域内每个物种至少出现一次所需要的最少保护区数量;Watsonet al.,2011)提供科学依据(Matthewset al.,2015)。有关嵌套性的研究还主要集中在欧美,这限制了嵌套性在国内的潜在应用(Matthewset al.,2015;郑进凤等,2021;田路嘉等,2022)。本文对广州城市绿地留鸟嵌套分布格局及其影响因素进行研究,为丰富城市鸟类生态学研究内容,合理指导城市规划、建设和实施物种保护提供有益参考。
1 材料与方法
1.1 研究区概况
研究区位于广东省广州市(112°57′~114°3′E,22°26′~23°56′N,面积7 434.40 km2),属南亚热带季风气候区,森林覆盖率达42.14%;年均气温21.5~22.2 ℃,年均降水量1 800 mm左右,4—6月为雨季,7—9月多台风。广州市生物资源丰富,记录到鸟类251种,占广东省鸟类的45%以上(郑孜文等,2008;邹发生,叶冠锋,2016)。
选择分布于广州市9个行政区内的20个城市绿地斑块(图1)进行鸟类调查和景观参数提取。利用Fragstats 4.0计算各研究绿地的斑块面积、景观多样性、斑块密度、斑块数量和平均斑块面积指数5个景观参数(表1)。

表1 广州市主要城市绿地的景观参数Table 1 Landscape parameters of the main urban green patches in Guangzhou

图1 研究区域内的20个斑块Fig. 1 Distribution of the 20 main urban green patches in Guangzhou
1.2 鸟类调查方法
2017年9月—2019年5月,采用样线法(Bibbyet al.,2000)对每个城市绿地的鸟类进行调查。样线以足够覆盖整个样地为准,根据面积分别设置1~4条样线,在鸟类繁殖季和越冬季各调查3次。调查时匀速行进,用双筒望远镜BOSMA 8×42记录沿样线两侧各50 m范围内看到和听到的鸟类种类和数量。每次调查均在天气良好的情况下进行,时间为日出前30 min至10∶00,15∶00至日落前30 min。考虑到候鸟组成存在年际变化,本文仅分析留鸟(Fernández-Juricic,2002;González-Orejaet al.,2012;田路嘉等,2022),因留鸟终年生活在一个地区,不随季节迁徙,其嵌套分布格局及影响因素较为稳定。在进行嵌套分析前,通过基于个体的物种累积曲线对留鸟的取样充分性进行检验,该分析在EstimateS 9.1.0中进行(Colwell,2013)。
1.3 嵌套分析
鸟类的分类系统参考《中国鸟类分类与分布名录(第三版)》(郑光美,2017),获取每个绿地斑块的鸟类物种丰富度和多度,多度为多次调查中物种的最大值,建立75×20的留鸟多度×样地矩阵,使用WNODF方法分析鸟类群落嵌套格局(Almeida-Neto & Ulrich,2011)。 WNODF 是 对NODF的改进,可利用物种多度数据定量分析嵌套程度,与其他方法相比,WNODF对嵌套的计算更有优势。采用3种重采样零模型:行列固定(rc)、总数固定(aa)和总物种丰富度固定(ss),分别随机产生1 000个矩阵,对实际记录的鸟类多度矩阵×样地矩阵进行显著性检验。当P>0.05时,表明实际观测群落近似于随机群落的分布格局;当P<0.05且Z>1.96时,表明观测群落的嵌套程度显著大于随机群落,呈嵌套结构;当P<0.05且Z<-1.96时,表明观测群落的嵌套程度显著小于随机群落,呈反嵌套结构(Matthewset al.,2015)。
1.4 相关性分析
嵌套的影响因素使用Spearman秩序列相关性分析。当鸟类群落出现明显嵌套时,将WNODF计算重排后的地点嵌套序列与物种多度、绿地景观参数进行Spearman相关分析,检验各因子对嵌套结构的影响程度,该分析通过R语言Hmisc程序包中的cortest函数来计算。
1.5 随机分布模型
使用随机分布模型(Coleman,1981)检验群落嵌套格局是否与被动取样有关。在与绿地面积的模拟曲线中,若超过1/3的观测值位于预测曲线标准差范围外,则表明群落不存在随机分布,拒绝被动取样假说(Matthewset al.,2015)。
2 结果
共记录鸟类18目50科139种,其中雀形目Passeriformes最多(82种)。每个绿地斑块中的鸟类物种数在22~53种,其中有16个绿地斑块的物种数在35~53种。从居留型来看,留鸟最多(75种),占53.96%。基于留鸟个体数的物种累积曲线呈先快速上升后变为渐近线或增速放缓趋势,表明大部分绿地斑块抽样充分(图2)。

图2 基于留鸟个体数的物种累积曲线Fig. 2 Number of individuals-based accumulation curve for the species richness of resident birds
3种零模型(rc、aa和ss)的WNODF嵌套分析显示,20个绿地斑块物种多度矩阵的嵌套程度显著低于1 000个随机群落(P<0.001)且Z<-1.96,表明留鸟群落呈显著的反嵌套结构(表2)。

表2 广州城市绿地斑块中留鸟物种多度矩阵的嵌套格局分析Table 2 Nestedness analyses based on species-by-site abundance using NODF for resident birds in urban green patches of Guangzhou
随机分布模型结果显示(图3),超过1/3的绿地斑块鸟类观测值在预测曲线标准差范围外,表明广州城市绿地留鸟群落非随机分布,也意味着被动取样假说不是该区域鸟类嵌套格局的原因。

图3 广州市城市绿地斑块中留鸟物种数观测值与随机分布模型预测值对比Fig. 3 Comparison between observed and expected values under random placement model for resident birds in urban green patches of Guangzhou
Spearman秩序列相关分析结果显示(表3),物种多度、斑块面积和平均斑块面积指数与嵌套序列呈显著负相关,景观多样性与嵌套序列呈显著正相关。

表3 广州城市绿地留鸟经NODF最大化排序后的地点序列与景观参数的Spearman秩序列相关性分析Table 3 Spearman’s rank correlation between rank order of sites using NODF and landscape characteristics for resident birds in urban green patches of Guangzhou
3 讨论
本研究结果表明,广州20个城市绿地斑块的留鸟群落呈明显的反嵌套结构,表明各绿地斑块间的物种替换频繁,这与贵州花溪大学城26个破碎化林地的鸟类群落嵌套格局一致(郑进凤等,2021)。反嵌套意味着嵌套程度较弱,但嵌套度量方法的发展会改变对嵌套的判断。Matthews等(2015)综合分析97份已发表的鸟类嵌套研究论文后发现,62%的研究呈负的Z值(即表现出反嵌套格局),表明在使用NODF的算法后,反嵌套格局在群落中常见;但采用PP零模型方法后,大部分群落(74%)表现出随机分布格局,这一综合分析再次证实了嵌套度量方法的改变影响了嵌套格局的推断,只有在同一方法框架下的研究才有可比性。
广州城市绿地留鸟群落的反嵌套分布格局并非由被动取样造成,这与多数嵌套格局研究不支持被动取样假说的结论一致(Wanget al.,2011;Tanet al.,2021;田路嘉等,2022)。被动取样假说认为调查中某些物种高的多度值可能形成嵌套格局(Morrison,2013),即多度高的物种比多度低的物种更有可能在许多斑块中定殖(质量效应:Leiboldet al.,2004)。本研究也显示:物种多度与嵌套序列呈显著负相关。这看似矛盾的结果可能反映了物种多度信息难以获取或获取不充分的问题(即嵌套序列与充分的多度数据间可能不相关),这种现象也出现在Chen等(2018)和赵郁豪(2020)的研究中。
本研究中留鸟的嵌套与斑块面积、景观多样性和平均斑块面积指数呈显著相关,其中斑块面积和平均斑块面积指数均呈显著负相关,这可能表明了选择性灭绝是留鸟嵌套形成的机制之一。因为面积需求较大、生境专一性较强的物种具有较高的灭绝风险,并且会在小斑块中首先灭绝(Wanget al.,2010,2011),即选择性灭绝会出现嵌套与斑块面积显著相关的表现形式。此外,由于鸟类扩散能力较强,斑块间的间隔可能对鸟类阻隔作用不大,因此选择性迁入的作用有限(王本耀等,2012;郑进凤等,2021)。较可能的是,生境嵌套和人为干扰对反嵌套格局的形成也起着一定作用,这也体现在留鸟的嵌套序列与景观多样性呈显著正相关:即某些鸟类只在特定生境中出现,如本研究中国家重点保护野生鸟类和稀有种在流溪河国家森林公园最多,反映出生境对鸟类的选择性分布有影响;其次,城市绿地中存在相对较强的人为干扰,这对警惕性强的鸟类有明显的负面效应。总之,准确推断鸟类嵌套格局的形成机制,还需要进一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