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蓝的诗
春天的一个傍晚
就这样吧就这样
夜深了
让我唱完最后一支歌
让我再闭上眼睛想想这一切
在这个春天
在这个不长翅膀的夜晚
我采集了所有逝者的困倦
所有婴儿们未曾被污染的感觉
种植在早晨第一阵微风里
我要走过去,看看
黄昏的收获
一串串眼泪从金色花朵里滚落
而最早照进夜里的一抹阳光
有多么的虚弱啊
*1983 年
往事
在那个夜晚里有全部的往事
是你对另一个人的思念
打动了我么?
遥远的除夕之夜
你的脸隐入黑暗
你的双脚
走入另一道门
另一个夜晚的街树下
你的手指轻柔地揩去
另一张面孔上的泪水
是那茫然的力量
使你在最后的时刻
放弃了另一个花期的抉择?
那是最后一天
桌上的啤酒泛着泡沫
对面一个模糊的人影
倚墙而坐
那一夜有你全部的往事
我伏在钟声里泣不成声
亲爱的!
你怎会知道你对另一个人的
思恋
使我感动也使我
蒙羞
*1986 年
秋天的列车
秋天的列车在半夜准时通过。它载走候鸟、树叶和黄昏时
常到河边打草的老汉。
岸边光秃秃的树、羊圈的土墙和我 不走
留在风中
抱紧各自的孤独
星星看上去不太远,像铁轨旁一闪而过的小蓝灯
它们默不作声
守着生命撤走后的寂静
我不清楚秋天过后的一切
是不是都沉为忠实的矿脉
也许 我曾经和草丛中的萤火虫
一同被捉走?
是不是我冒犯了万物的法则
偷偷躲过搜索者的眼睛
在佯装的熟睡里 或者在戛然停住的亲吻中?
是不是那场庄严的告别里根本没有我
没有我想到的花开花落
而仅仅是从一只鸟里又飞出另一只鸟
轻轻拍远了翅膀 不让任何人看到
*1991 年
石人山
这座山的名字将要消逝。
是梦都会消逝。
它的被那场大雪抹去的一切
与我的整整一生有关。
话语和脸
幸福的话语和脸
而它将更久远地活着
它要痛苦地保存
我太多的遗产。
*1991 年
野葵花
野葵花到了秋天就要被砍下头颅。
打她身边走过的人会突然回来。天色已近黄昏。
她的脸 随夕阳化为金黄色的烟尘
连同整个无边无际的夏天
穿越谁?穿越荞麦花似的天边?
为忧伤所掩盖的旧事,我替谁又死了一次?
不真实的野葵花。不真实的歌声。
扎疼我胸膛的秋风的毒刺
*1992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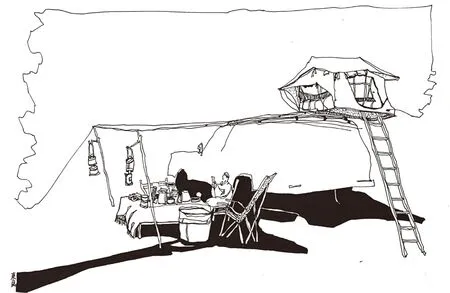
东良 《露营》
在我的村庄
在我的村庄,日子过得很快
一群鸟刚飞走
另一群又飞来
风告诉头巾:夏天就要来了。
夏天就要来了。晌午
两只鹌鹑追逐着
钻入草棵
看麦娘草在田头
守望五月孕穗的小麦
如果有谁停下来看看这些
那就是对我的疼爱
在我的村庄
烛光会为夜歌留着窗户
你可以去
因那昏暗里蔷薇的香气
因那河水
在月光下一整夜
淙潺不息
*1992 年4 月
大河村遗址
又一个大河村。
乌鸦在高高的杨树上静卧着
成群的麻雀飞过晒谷场
翅膀沾满金黄的麦芒
它们认出我。
微风还是几年前那样吹过
没有岁月之隔
我难道是又一个?
黄昏,长长的影子投向沙丘
又到了燃升炊火的时候
熟识的村民扛着铁耙
走在田埂上
牛驮着大捆的青草
像从前一样,我闪到一旁
没有岁月之隔。
只有大河村,这一动不动的
滔滔长河。
*1992 年2 月
春夜
春夜,我就要是一堆金黄的草。
在铁路旁的场院
就要是熟睡的小虫的巢。
还没有离开过,我还没有爱过。
但在茫茫平原上
列车飞快地奔驰,汽笛声声
一片片遥远的嘴唇发出
紫色的低吟 它唱着往事。
唱着路过的村庄
黑黝黝树林上空的红月亮
恍然睡去的旅人随车轮晃动
这一垄青翠的庄稼在深夜飞奔!
它向前飞逝,我就要成为
夜里写下的字。就要
被留在空荡荡的铁轨旁
触到死亡的寒冷。
还没有醒来过,我还没有呼救过。
*1992 年2 月
夏夜
那些梧桐叶!
将属于一张脸的月光偷去
但它漏下了星星
屋角蟋蟀的叫声
我爱那双拿着诗稿的手
沾满草香和湿润的夜露
我爱在麦地里迅速写下的短诗
风媒花 虫媒花
结亲和恋爱的世界上
寄到人间的情书
*1992 年6 月
写给无名的
你是没有的
你是永远不来到我记忆中的
你是没有的
而我又被谁所等待
让不安把我充满
生命中会有
无须讲话的时刻
世界上只剩下我
像大雪中坚持不落的鲜红水果
我怎样闭上眼睛梦你?
爱你?我怎样
忧伤地
朝望不见你的方向望你?
在听不到你声音的声音中倾听你?
我说不出那些话语
比泪水 更温柔的话语
你是没有的
你是永远不来到我记忆中的
你是没有的
而我又被谁所想象
被想象的虚妄取代?
生命中会有无需思想的时刻
世界上也不止有我
这期待不曾向任何人诉说。
谁是我?谁借我之口
深深地缄默?
你是永远不来到我记忆中的
你是没有的
*1992 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