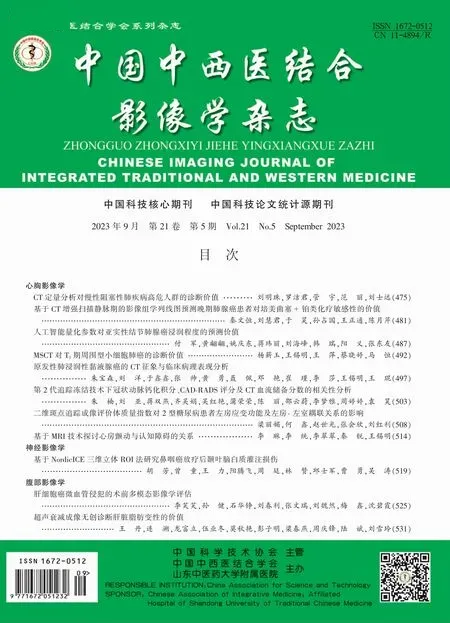基于MRI 技术探讨心房颤动与认知障碍的关系
李 琳,李 统,李翠翠,秦 锐,王锡明
山东第一医科大学附属省立医院/山东省立医院医学影像科,山东 济南250021
全球约有5 000 万人患有认知障碍,随着人口老龄化的进展,预计到2030 年,全球范围内认知障碍患者将达到7 500 万,到2050 年将达到1.35 亿[1]。尽管认知障碍的发病机制尚未完全阐明,但大量研究表明,心血管疾病及其危险因素与认知障碍存在密切联系。心房颤动(房颤)是最常见的心律失常类型之一,也是公认的脑卒中的独立危险因素[2]。在我国约有12%的缺血性卒中患者同时合并房颤,以此估算此类患者人数超过215 万[3]。研究表明,当患者存在明确卒中病史时,房颤可能会引发认知障碍[4]。但近年来,神经影像学研究发现,即使未发生卒中,房颤同样也被视为是认知障碍的独立预测因素。因此,本研究对揭示两者联系的最新文献进行总结,旨在通过分析房颤患者的影像学特征来探讨房颤引发认知障碍的可能机制,以加强临床对房颤的干预治疗,从而降低认知障碍发生的可能。
1 房颤与认知障碍简述
1.1 房颤
房颤是指心房电活动异常导致心肌运动紊乱,从而引发心脏泵血功能恶化或丧失。房颤的患病率和死亡率均较高。目前,我国45~54 岁人群中房颤的患病率为1.4%,75 岁以上人群为10.3%[5];而房颤患者的死亡风险较无房颤患者高出2 倍以上[6]。此外,房颤还会引发血栓栓塞、脑卒中、心衰等相关并发症,以及其他非特异性疾病,如认知障碍、体能下降等[7]。近年来,房颤的患病率、死亡率呈指数级增长趋势,造成了严重的公共卫生问题和经济负担。尽管当前房颤的治疗取得了一定进展,但其仍是导致脑卒中、心衰等心血管疾病的主要原因之一。
1.2 认知障碍
认知障碍是指各种原因导致的一个或多个领域客观认知功能(执行力、学习和记忆、注意力、语言、计算能力和视觉空间功能力等)异常[8],包括轻度认知障碍(mild cognitive impairment,MCI)和痴呆;MCI 是介于正常衰老和痴呆之间的一种过渡状态,既可稳定或好转,也可发展为痴呆。蒙特利尔认知评估(the Montreal Cognitive Assessment,MoCA)和简易精神状态检查(the Mini-Mental State Examination,MMSE)是最常用的认知评估工具。MoCA 在识别MCI 方面比MMSE 更具优势,这可能是由于MoCA包含的项目更复杂,但两者均受患者受教育水平的影响[9]。因此,研究人员对患者进行全面评估时应选择能够涵盖各个认知领域的评估工具,降低单一认知评估工具引起的偏倚;同时也应根据患者的自身情况设定合适的阈值,尽可能避免年龄、受教育水平等因素对研究结果的影响。
2 房颤与认知障碍的关系
认知障碍是一种多因素疾病,心血管疾病及其相关危险因素均与认知障碍密切相关。房颤是引起栓塞性卒中最常见的原因,使脑卒中风险增加了5 倍[10];而脑卒中是认知障碍的重要危险因素,房颤和认知障碍之间的关系通常被认为是缺血性脑损伤所导致认知功能逐步下降的结果。
1997 年,有研究首次描述了房颤与认知障碍之间的关系,认为房颤与MCI、阿尔茨海默病及血管性痴呆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性,其中以房颤与阿尔茨海默病的关系最强[11]。一项队列研究用调整了年龄和教育程度的MMSE 评分(<24 分)来评估MCI,发现房颤患者的MCI 患病率为14%,且与持续性房颤独立相关[12]。该评分极大减低了患者自身情况对研究结果的影响。Banerjee 等[13]发现,房颤患者在卒中前多存在认知障碍,且认知障碍与脑小血管疾病(cerebral samall vessel disease,CSVD)和神经退行性变的影像学标志物相关。此外,多项Meta 分析证实,即使是对混杂因素及卒中史进行调整后,房颤患者的认知障碍风险仍很大[8,14-15]。以上研究表明,房颤是认知障碍的独立危险因素,且与脑卒中的发生无关,这提示脑卒中仅是房颤相关脑缺血性疾病的一部分,并非是导致认知障碍的必要条件。由此推断,除脑卒中外,可能还存在其他机制诱发房颤相关认知障碍。
3 MRI 在识别房颤相关认知障碍中的作用
近年来,随着医学影像技术的发展,MRI 在颅脑结构及功能评估方面有关键性作用,越来越多的研究将MRI 应用到对房颤患者的认知功能评估中。
3.1 脑结构成像的作用
目前,房颤相关脑结构研究多采用基于体素的形态学测量方法来观察脑组织的形态结构,常用序列有T1WI、T2WI、T2-FLAIR、SWI 等。研究者基于上述序列进行后处理技术分析即可获取整体或区域性脑体积、灰质和白质体积、脑白质高信号(white matter hyperintensity,WMH)体积及微出血数量等影像学指标。
Stefansdottir 等[16]对4 000 余例房颤患者MRI 图像进行分析后发现,房颤与较低的总脑体积、灰质体积及较高的WMH 体积有关,且与疾病持续时间呈正相关,表明房颤对大脑的影响存在累积效应。但随后的一些研究结果与之相悖,如Knecht 等[17]发现无卒中房颤与海马体积缩小有关,与总脑体积及WMH体积无关。值得注意的是,该研究证实了房颤患者的学习和记忆功能受损与海马萎缩存在高度一致性,这为房颤引发的学习和记忆能力下降提供了可靠的解释依据。此外,Moazzami 等[18]通过前瞻性研究发现,在≥75 岁患者中房颤与总脑体积呈负相关,但在<75 岁患者中无统计学意义。这可能是因为总脑体积是一个相对粗略的测量值,会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如体质量、年龄等,而这些因素又不能完全以线性关系的方式起作用。近来,Nakase 等[19]通过回顾性分析发现,患有MCI 或阿尔茨海默病的房颤患者的脑室周围WMH 和深部WMH 体积明显高于窦性心律患者。这提示对伴阿尔茨海默病或MCI 的房颤患者而言,白质病变可能比脑血流损害更有诊断价值。
3.2 脑功能成像的作用
广义上讲,能够反映脑功能的MRI 技术均可称为fMRI,如BOLD、DTI、MRS 等;而狭义上fMRI 是指一种测量脑组织自发BOLD 信号的MRI 技术,包括静息态和功能态2 种模式,其可在脑解剖结构出现改变之前识别脑组织的微观变化。
一项静息态fMRI 研究首次对无卒中房颤患者的脑网络连接模式进行了分析[20],研究显示房颤患者最重要的大脑网络——默认模式网络(default mode network,DMN)出现了异常连接,连接减少的脑区主要与认知和情绪相关,且DMN 连接性降低仅限于部分腹侧脑组织区域,同时患者的部分额叶和小脑的灰质体积也出现减小趋势[21]。静息态DMN 的异常连接及部分额叶和小脑半球萎缩可能有助于解释在未发生卒中的情况下,房颤是如何通过改变脑结构和功能促使认知障碍发生的。但此研究并未进行长期随访以了解DMN 的破坏是否可作为早期指标用于预测房颤患者的认知障碍风险;且该研究采用MMSE 评估认知状态,其识别MCI 的准确性较MoCA低,不能完全反映患者的认知状态。Austin 等[22]利用DTI 观察房颤患者的白质微观结构,发现房颤患者的白质各向异性分数降低;同时灰质体积减少、微出血概率增加。白质各向异性分数降低代表白质微观结构的完整性受到破坏,这可能是CSVD 更早或更敏感的标志物之一,这一研究发现提示房颤患者在出现认知障碍之前脑微观结构可能已发生异常改变。
房颤会引起大脑结构和功能发生改变,包括局部脑体积缩小、灰质体积减少、WMH 增强及白质纤维结构异常等。尽管房颤与总脑体积之间的关系说法不一,但其他脑结构及功能的改变仍为阐释房颤与认知障碍之间的机制提供了客观证据。目前,大多研究都集中在分析房颤患者的脑结构像,而房颤相关fMRI 的研究证据有限,未来可将fMRI 作为重点研究方向,或将结构和功能成像结合起来,对房颤引起的颅脑改变情况进行更全面、综合地分析,为揭示两者之间的神经病理学机制提供更加有力的论据。
4 房颤引发认知障碍的相关机制
4.1 无症状性脑梗死
房颤导致血液在左心房内出现聚集、停滞形成血栓,血栓脱落形成的栓子随心室射血进入血液循环可引发脑栓塞,当患者无明确的卒中或短暂性脑缺血发作症状时可称为无症状性脑梗死[23]。无症状性脑梗死大多体积较小,但同样会引起脑结构或功能性破坏:一方面其可引发离梗死核心几毫米内的缺血性扩散抑制波,导致神经元损伤和脑灌注不足[24];另一方面,位于白质束内或附近的梗死可能会通过破坏周围白质纤维而影响大脑通讯网络。基于上述假设,研究发现无症状性脑梗死与临床卒中对认知功能的影响相似,且随访期间约85%的新发房颤患者出现了无症状性脑梗死,为无卒中房颤与认知障碍之间的关联提供了可靠的依据[4,25-26]。
4.2 慢性脑灌注不足
脑血管系统具有自主调节机制,在血压发生波动时仍能维持足够的灌注压。房颤引发的血液动力学紊乱会造成心输出量下降,导致脑灌注不足,这种现象在自主调节功能受损的患者中尤为明显[27]。脑灌注不足会改变血-脑脊液屏障的通透性,导致β-淀粉样蛋白(β-amyloid peptides,Aβ)清除率降低,而Aβ 沉积会继续加速血-脑脊液屏障的破坏[28];此外,低灌注会引起神经元和神经胶质细胞损伤,导致部分生物标志物被释放到细胞外,后通过静脉引流或受损的血-脑脊液屏障扩散至血液中。神经源性外泌体中的Aβ42、Tau 蛋白和生长分化因子15 等可能与房颤患者认知障碍的早期诊断有关[29-30]。因此,通过改善心输出量会缓解房颤引起的认知障碍[31]。这些发现对于房颤患者神经损伤标志物的早期检测具有重要意义,同时有助于临床医师在认知障碍的临床表现出现之前采取预防措施。
4.3 白质疾病和脑微出血
CSVD 主要指大脑皮质下结构病变,包括WMH和微出血等,这些都与脑卒中、认知障碍和血管性痴呆相关,因此CSVD 可能是不良认知表现的影像学标志物。
WMH 代表大脑出现了潜在的脑血管损伤,由于白质血管很少或无侧支血管,其易受到灌注压的影响,而房颤引起的血流动力学紊乱会加重白质对血流变化的易感性。几项纵向研究观察到房颤患者伴严重的脑室周围WMH 或WMH 的加速进展,且与脑卒中无关[32-33]。但也有研究对此持否定态度[17,34-35]。以上研究在样本量和受试者选择方面存在较大差异,亟待更加完善的研究来论证WMH 与认知障碍之间的联系。识别WMH 的进展和分布可能有助于更好地了解在房颤患者中观察到的认知障碍。
微出血与认知障碍的关联一方面体现在微出血可能破坏了具有重要意义的白质束或皮质区域,导致特定认知领域的功能障碍,如额叶的微出血与执行功能下降相关[36];另一方面,微出血可能反映了脑血管系统的整体病理状态。在Akoudad 等[37]的研究中,微出血与各个认知领域认知障碍相关,但针对腔隙和WMH 进行调整后这一关联明显减弱。这表明CSVD 对认知障碍有共同作用,它们的存在可能代表了脑损伤所发生的连续性病理学进程。最近,Mejia-Renteria 等[38]阐述了一个重要观点:心脏和大脑中的微血管功能障碍是心血管疾病患者出现认知障碍病理过程的一部分。
4.4 神经炎症反应
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房颤与炎症密切相关。房颤引起的血流动力学改变会促进血管内皮损伤或功能障碍,诱导炎症反应发生[39];另外,随着年龄增长,血-脑脊液屏障通透性增加也会启动神经炎症过程,反之,炎症也会促使心房电和结构重塑。研究显示,诸多炎症因子,如C-反应蛋白、多种白介素(interleukin,IL)及肿瘤坏死因子(tumour necrosis factor,TNF)等均与房颤相关[40-41]。而IL-2、IL-6、IL-9、IL-12 及TNF-α等又与认知障碍或阿尔茨海默病存在相关性,尤其是在记忆力和信息处理速度方面[42-43]。抗炎治疗可预防术后房颤及改善房颤患者的认知障碍和某些脑区体积损失[42,44]。由此可见,一些与房颤相关的炎症介质在认知障碍相关病理学过程中同样发挥了作用,这表明炎症反应可能是2 种疾病之间的潜在联系,打破房颤与炎症之间的恶性循环有望成为治疗房颤及预防认知障碍的关键性措施。
5 小结与展望
房颤和认知障碍均是人口老龄化的突出特征。诸多研究证据表明,房颤是认知障碍的独立危险因素,且独立于脑卒中的发生。然而,这种相关性并不一定代表着两者即存在因果关系,原因如下:①这其中可能涉及多种机制的相互作用,如无症状性脑梗死、慢性脑灌注不足、CSVD 及神经炎症反应等;②房颤患者接触到的危险因素不确定,既往研究多基于基线水平,未跟踪风险的时间变化;③许多研究方法存在局限性,包括随访时间短、样本量小等。
总之,关于房颤所致认知障碍的具体机制很复杂,亟需进一步大规模研究,尤其是前瞻性研究。同时,还应采用更加全面的认知评估方式以增加对MCI 早期诊断的敏感性。此外,迄今为止,影像学相关研究多集中在脑结构成像,缺乏关于脑功能成像的研究及评估房颤逆转是否会改善认知功能的相关研究。未来,将无创性的局部脑血流实时检测技术与不同的MRI 序列相结合,可能有助于更好地探索房颤对大脑的影响,以及阐明房颤在认知障碍发展中所起到的作用,从而为临床提供更有针对性的治疗方法,延缓房颤患者认知障碍的发生及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