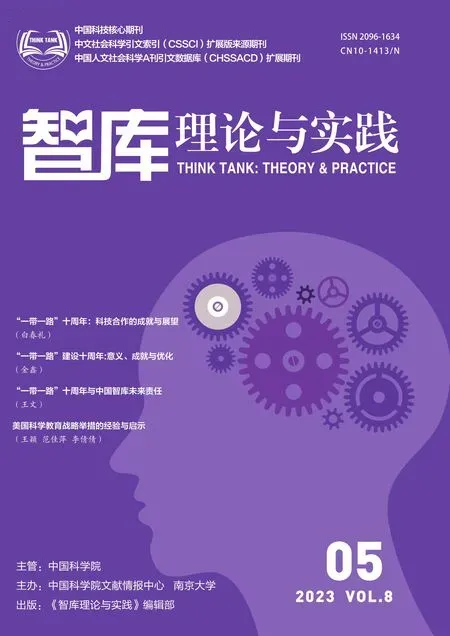智库数字公共外交:概念界定与实践发展
■ 王莉丽 谭思沩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 北京 100872
1 前言
近年来,在数字技术和全球新冠疫情的双重驱动和影响下,全球秩序、信息传播和公共外交等方面发生了巨大变革,人类社会加速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周期。智库作为知识密集型组织,通过积极的公共外交活动,在全球范围内设置政策议程、搭建多元主体交流与合作的平台及桥梁,推动全球治理的实现。数字时代的到来,不仅影响了智库的思想生产与传播策略,而且全面重构了智库公共外交的空间和模式。
本文对“智库数字公共外交”进行概念界定,分析其功能作用,并以此为框架对中、美、英3国具有代表性智库的数字公共外交实践进行探析。在此基础上,对中国智库数字公共外交的未来发展提出建议。
2 文献回顾与相关概念
当前,学术界对智库公共外交、数字公共外交均有一定的研究,“智库数字公共外交”作为一种公共外交实践也已经广泛存在。然而,鲜有研究对智库与数字公共外交这个交叉领域进行深入探讨,“智库数字公共外交”发展仍处于前学术层面。理论研究的滞后使智库数字公共外交实践发展缺乏理论规范和指导。
2.1 智库公共外交
关于智库公共外交的相关研究,国内外学界早已有之,学者们通常运用案例分析的方法从公共政策、国际关系的角度,探讨智库的功能与角色。
从公共政策角度来看,学界普遍认为智库的政策建议是国家开展公共外交、参与全球治理的思想源泉。有学者指出,智库是中国最新的政策工具,其供给的思想产品在辐射外国公众、增进西方认同、改善中国形象、增强软实力等方面发挥着比政府等官方行为体更关键的作用[1]。斯蒂芬·鲍尔(Stephen Ball)等[2]认为,智库为国家提供政策观点,在世界范围内搭建权力知识网络,开辟全球多中心治理模式。有学者指出,智库深刻影响着“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公共外交实践[3]。还有学者认为,由于智库这类非政府组织的亲民性、专业性、民主性和社会性,国际公众更容易接受其较为和善、单纯的感召[4]。智库除了充当政策产品的设计者、政党人才的提供者之外,其非政府组织的身份便于推动公共政策在国际公众范围获得更加广泛和普遍的认可[5]。
从国际关系角度来看,国内外学者结合实际案例对智库发挥功能的作用机制进行了多元探讨。朱旭峰等[6]认为,全球化、数字化、国际形势以及新冠疫情带来的变化,让世界各界行为体不能再独善其身,智库为国际事务的发展和国际关系的建构推波助澜。赵可金[7]指出,智库活动已是美国公共外交和国家安全战略的重要实施路径。王文[8]认为,智库通过公共外交手段,传播中国理念、影响国际社会、吸纳先进思想以及实现国际交流。戴安·斯通(Diane Stone)[9]指出智库专家作为知识行为体,对内,为G20(二十国集团)提供政策建议和研究服务,对外,为普通公众提供国际交流话语。智库网络提供了一种全球传播的机制,精准、快速地传递政策观点和智力成果,影响精英、公众对全球议题的关注与认知,从而塑造国际舆论的支持和理解,间接推动国际关系的走向。
2019 年,王莉丽[10]首次对“智库公共外交”进行了概念界定和理论构建。智库公共外交是指作为行为主体的智库,以高水平的政策专家和其创新的思想成果为基础,以国外智库和各界公众为目标受众,运用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大众传播等各种传播模式,以融合传播的方式,全媒介、多网络传播思想成果,开展对话与交流,影响他国公共政策和舆论。本文以“智库公共外交”的概念界定为基点,对智库数字公共外交进行理论与实践分析。
2.2 数字公共外交
目前,国内外学界有关数字公共外交的研究主要聚焦于功能与特点、传播策略与具体实践以及概念界定与理论发展三方面。
有学者指出,以微博为代表的新媒体平台,赋予网民全新的参政议政方式,拓展了公共外交的传播主体和实践渠道,互联网从单向信息传播延伸成双向互动模式[11]。还有学者认为,区别于传统公共外交,数字公共外交更为成功和优越的策略在于个性化、情感化、相关性和积极主动的信息传递及对话沟通[12]。自2020 年以来,新冠疫情给数字媒体使用、社会交往模式、国家外事活动以及全球公众生活带来了颠覆性的变化。国外学者通过实证研究发现,新冠疫情期间,由于音/视频电话、电子邮件、社交媒体等数字通信技术的使用频率大幅增加,数字接入数量和质量的差异会加剧个人间的数字不平等,进而不同国家的政治传播和数字公共外交效力也大相径庭[13]。国外研究显示,Twitter 等数字化平台是中国讨论争议性议题、回应相关指控、监测和控制国际舆论的有力工具[14]。有学者指出,数字技术赋予了智库争夺国际话语、提升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的机会[15]。
随着数字技术的蓬勃发展及其对公共外交实践的影响,公共外交概念也在不断发展演变。2005 年,简·梅利森(Jan Melissen)[16]提出了“新公共外交”的概念,作为对传播形态和国际关系变化的回应。“新公共外交”强调多面向的新媒体渠道和平台建设的重要性,以促进目标国家的公众互联、交流对话和关系建构。有学者提了“嵌入式公共外交”,突出个人节点、社会网络以及公共外交资源的有效整合[11]。尼古拉斯·卡尔(Nicholas Cull)[17]认为“公共外交2.0”以网络化传播为中心,使用在线渠道和数字平台向外国公众传播知识、培育好感,从而提升国家软实力和加强国家品牌建设。在后疫情时代背景下,有学者提出了线上的虚拟会面与线下的实地交流相结合的“融合式公共外交”,以增强线上弱联系、维护线下强关系[18]。还有学者认为,“公共外交的数字化”充分利用社交媒体的分众化、差异化、算法推荐及模因应用等优势,更加精准地触达目标受众,满足公众的情感诉求,构建互信关系,最终长期影响公众行为[19]。
在学界已有研究的基础上,本文明确提出“数字公共外交”概念,即“数字公共外交”是指多元公共外交主体运用数字传播技术和平台,与国际受众进行交流与对话,目标是关系建构与国家影响力提升。其与传统公共外交的主要区别在于更便捷的信息传播与对话互动,更注重对公众意见的尊重与反馈。
3 “智库数字公共外交”概念界定与功能作用
关于“智库数字公共外交”的研究,国内外学界普遍停留在案例分析和实践探讨层面,缺乏深入的学术分析和理论建构。亚历山大·温特(Alexander Wendt)的建构主义、杰弗里·考恩(Geoffrey Cowan)和阿米莉亚·阿瑟诺(Amelia Arsenault)提出的“独白、对话、合作”框架以及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的场域理论为研究智库数字公共外交提供了理论支撑。
亚历山大·温特的建构主义强调非物质因素,如知识、文化、观念、意识形态等,对构建国际行为体的身份和利益具有重要意义。这一观点进一步阐释了国家间互动模式的选择和公共外交的实践[20]。智库凭借权威的思想产品以及庞大的关系网络,在国际各界行为体中创造共识、传递价值,最终通过思想观念影响公众舆论,建立有利自身的身份认同。亚历山大·温特的建构主义理论为智库数字公共外交的理论与实践提供了合法性支持。
杰弗里·考恩和阿米莉亚·阿瑟诺[21]认为,公共外交主要包括独白、对话与合作3 个层次。其中,独白(monologue)是指国家或组织通过发言、演讲等单向传播的方式,向外界传递特定的观点、政策或信息。对话(dialogue)是指国家或组织与外界进行双向交流和互动,不仅包括信息的传递,还包括倾听和回应外界的观点和意见,从而促进双方之间的理解和合作。合作(collaboration)是公共外交的最高层次,是指行为体之间建立长期、高效、共赢的伙伴关系,解决共同问题、推动共同利益。杰弗里·考恩和阿米莉亚·阿瑟诺的理论虽然对公共外交的实践进行了较为清晰的理论分层,但过于简化了公共外交的复杂性和丰富性,忽略了数字技术对公共外交的颠覆性影响。
皮埃尔·布尔迪厄的场域理论认为,社会是由多个相互作用的场域组成,每个场域都具有特定的规则、参与者和权力结构,在不同的力量关系和资源分配中竞争和协商[22]。根据场域理论,有学者提出了“政策过程话语建构”模型,认为政策制定在本质上是一个话语建构的过程。社会行为主体在特定情境中为其所关注的社会现象赋予意义,形成多样政策话语并进行意义竞争。获胜者将进入政府议程,成为政策议题,最终获得制度化的地位[23]。智库作为政策制定的关键一环,通过发布报告、组织会议、发起活动等形式,向政府和公众传递有指向性的话语。
基于已有研究,结合智库与数字公共外交实践发展,本文对“智库数字公共外交”进行概念界定与理论构建:“智库数字公共外交”是指智库作为积极的行为主体,依托数字技术提供的信息传播渠道与平台,打破时空限制,以国际舆论界多元公众为目标受众,进行倾听、对话与关系构建。其功能角色是提供创新思想、设置政策议程、影响国际舆论、推进共有观念的形成和全球治理的实现。狭义上讲,“智库数字公共外交”的内容样态主要包括数字传播与对话、虚拟公共空间与场域搭建以及积极伙伴关系构建。
第一,数字传播与对话。智库通过数字媒介发布研究报告、评论文章、音视频演讲等,充分发挥数字媒介的信息传播优势,并强化与目标受众的倾听与对话。第二,虚拟公共空间与场域搭建。借助于数字技术,智库组织各种形式的线上会议,并以此为平台核心,搭建多元社交媒体联动的虚拟公共空间与场域,为国际舆论界高度关注的紧迫性和战略性议题提供阐释、对话与辩论的平台。第三,积极伙伴关系构建。一方面,智库基于全球性议题和共同利益诉求,与其他国际行为体建立伙伴关系;另一方面,基于各自国家利益开展竞争性合作,推动构建积极长效关系。
4 智库数字公共外交的实践发展
基于上文所述的“智库数字公共外交”概念和“数字传播与对话、虚拟公共空间与场域搭建、积极伙伴关系建构”框架,本文选取了中、美、英3 国具有代表性的智库进行案例分析。其中,布鲁金斯学会常年位于全球智库排名各类榜单的第一名,是美国历史最悠久、最具影响力的智库。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是英国规模最大、世界著名的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之一,是欧洲智库的标志,其在智库的“独立性、公正性、广泛性”上具有丰厚的理论基础和广阔的全球视野[24]。全球化智库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发布的《全球智库报告2020》[25]中,跻身全球顶级智库百强榜,是首个进入世界百强的中国社会智库[26]。
4.1 数字传播与对话:对话能力普遍较弱,社交媒体传播力、影响力与内容生产强度差异明显
在数字传播与对话样态下,上述3 家智库构建了以官网为核心、以多元社交媒体为辐射网络的新媒体传播矩阵,提升了其思想传播力与对话力。研究发现:就整体而言,3 家智库基于新媒体传播矩阵的对话力普遍较弱;相比较而言,3 家智库的内容生产强度、社交媒体传播力及影响力存在显著差异。
关于智库官网的对话力,本文运用迈克尔·肯特(Michael Kent)和莫琳·泰勒(Maureen Taylor)[27]提出的对话循环、信息有用性、界面有用性、生产回访及挽留访问者五维度框架进行分析。第一,在对话循环方面,3 家智库官网均有公开的反馈机制,访问者能够轻而易举地通过首页找到相关部门的通讯方式,直接参与和回复组织的信息和活动。然而,除了通讯方式,官网缺少其他对话渠道,其实现方式较为单一且循环机制较为薄弱。第二,在信息有用性方面,3 家智库官网均提供有价值、有深度、有时效性的研究报告、评论文章、书籍、公开活动等,除基本信息之外,3 家智库积极拓展议题类别、降低信息访问门槛,以满足不同受众群体的信息需求。第三,在界面有用性方面,3 家智库官网在用户交互设计方面各有千秋。布鲁金斯学会官网的语言选择最为丰富,涵盖了英语、汉语、西班牙语和阿拉伯语,选择不同语言,会根据该语言所属文化推荐相应的研究议题和成果。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官网每项研究的检索条目下方,标有阅读、收听或观看该条内容的时长,同时将文章的关键观点用不同字号和颜色突出,以便于公众迅速注意到要点、缓解视觉疲劳。全球化智库以大面积的色块改善页面的结构和布局,弱化文字带来的负担,提升官网界面的吸引力,为用户带来更佳的信息呈现和交互体验。第四,在生产回访方面,3 家智库官网在主页设有电子邮件订阅、RSS 订阅、外链分享等服务,精准定位受众、一站式聚合信息、快速简易跳转关联网站,以提高公众回访率。其中,布鲁金斯学会更新频率远远高于其他两家智库,奠定了其庞大的公众回访基础。第五,在挽留访问者方面,3 家智库官网注重专业性和逻辑性,缺乏多元的交互机制、个性化定制的推荐功能,导致智库官网在趣味性和吸引力方面表现不佳。
关于社交媒体的对话力,中国智库在国内平台的发文量、点赞数和转发量不断增多,但是在国际性平台上,中国智库与美英智库相比仍存在较大差距。美英两家智库在社交媒体建设与运营方面具有显著优势,不仅开通了母账号,还下设更有针对性的关联子账号,壮大社交平台矩阵。例如,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在Twitter 除了母 账 号“Chatham House” 外, 还 有“Chatham House Environment and Society”“Chatham House Asia-Pacific”等关联账号,既能提升覆盖面和曝光度,也加强了专业化分工,实现了信息的多渠道传播,达到了扩大数字对话力的目的。
对于内容生产强度、社交媒体传播力及影响力,布鲁金斯学会通过官网和社交媒体平台进行了大量数字传播与对话,成功塑造了其全球智库的领军形象。相比之下,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和全球化智库由于发文量相对较少,限制了其在新媒体平台的知名度和认同度。具体而言,2022 年6 月至2023年6月,布鲁金斯学会官网共计发表研究报告、评论文章、音视频演讲等1,837 篇,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发布779 篇、全球化智库更新818 篇。社交媒体方面,以Twitter 为例:布鲁金斯学会在2010年注册账户,有44.73万粉丝,截至2023年6月,共发布109,301 条推文;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于2009 年开通账号,目前拥有27.96 万的粉丝,共计发布26,280 条推文;全球化智库于2016 年注册,在Twitter 上仅有不到1 万的粉丝,累计发表4,776 条推文。因权限设置问题,布鲁金斯学会和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未对2023 年5 月之前的数据开源,本文选取了2023 年5 月1 日到6 月1日的数据做横向比较,中、美、英3 家智库分别发表了80、348、447 条推文。布鲁金斯学会的每条推文平均浏览量超过5,000 次,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的推文平均约有3,000 次的浏览记录,而全球化智库的绝大多数推文流量仅不到500 次。
4.2 虚拟公共空间与场域搭建:美英智库显著优于中国智库
数字化时代,线上会议突破时空和距离限制,降低会议成本,拓展思想传播范围,有效促进议题知识的普及,进而形成新的群体连接和交流空间[28]。智库组织各种形式的线上会议,并以此为平台核心,搭建多元社交媒体联动的虚拟公共空间与场域,使国际行为主体深入探讨关键议题,为国际舆论界搭建政策阐释、思想对话与观点辩论的空间与平台。本文选取了2022 年5 月至2023年5 月,以上述3 家智库官网发布的会议信息为数据源进行分析。研究发现,3 家智库在虚拟公共空间与场域搭建的数量、议题、参与主体以及影响力传播方面存在较大差距。布鲁金斯学会和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表现活跃、影响力较广,而全球化智库处于劣势地位。
布鲁金斯学会举办了231 场“线上+线下”会议,会议议题综合多元,兼具国内关怀和全球视野,涵盖公共政策、全球治理、经济发展、国际关系、环境与气候变化、安全与反恐、教育与技术等领域。布鲁金斯学会以Zoom、Webex 等数字媒介构筑的会议平台为核心,同时在官网发布录像回放,并通过Twitter、YouTube 等社交媒体平台的有机协同,打造出一个丰富而多元的虚拟公共场域,有助于增强会议内容传播的时效性和可及性,加强与全球各界的联系与合作,为跨越地域和领域的交流提供了有益的空间与机制。2022 年7 月,布鲁金斯学会邀请来自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德克萨斯大学等机构的资深专家、教授等通过线上会议的方式参与“全球经济状况”论坛,探讨后疫情时代全球商品市场、供应链和金融业的前景以及经济复苏之路[29]。根据该会议内容,布鲁金斯学会在社交媒体实时同步线上会场专家们的发言要点,并鼓励公众在Twitter 引用主题关键词“#Global Economy”进行提问、讨论。2023 年5 月,布鲁金斯学会中东政策中心在Zoom 发起线上会议“中东的气候变化、粮食不安全和移民”,从粮食安全和气候变化视角,对中东地区的内部城市化和外部移民议题提出政策建议。该会议结束后,布鲁金斯学会充分发挥会议平台和社交媒体的协同效应,在Twitter 发起话题“#Middle Eastevent”,进一步扩大会议的传播范围,吸引更广泛主体的兴趣和关注,促进该议题的对话与交流[30]。
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举办了236 场线上会议。会议议题涉及国防安全、经济贸易、政治法律、科学技术、公共卫生等,凸显其研究的时效性和前瞻性。会议进行的同时,意见领袖在Twitter 等社交媒体平台带动话题流量,配合主会场混合传播,搭建起全面立体、多方参与的媒介场域,为专家和全球公众提供阐释和辩论的平台,展现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在相关领域的专业性和权威性,建立起互相信赖的组织公众关系。2023 年6 月,为应对日益不确定的全球形势,由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主办的“伦敦会议2023”在英国举行,会议邀请了英国外交联邦发展事务大臣、也门共和国总理、俄罗斯和欧亚项目研究员、国际能源署主任、伦敦国王学院教授、BBC 首席记者等参会,探讨当今世界现代多边主义的原则和优先事项,旨在通过对话、分析,促进共有观念的形成,激励盟友和对手间的合作,解决紧迫性、战略性议题,建设美好、和谐的世界。同期,官方利用Twitter 和YouTube 平台配合会议中心宣传,而网络意见领袖玛丽亚·佐尔金娜(Mariia Zolkina)等[31]则以“#CH London”为核心话题,积极参与信息传播和影响力扩散,引导公众舆论和态度。
相较于美英智库,全球化智库以线上会议为核心创造的虚拟公共空间与场域较为有限。根据官网数据,2022 年5 月至2023 年5 月,全球化智库举办的线上会议不足30 场,涉及国际政治、经济贸易、人才培养、科技创新、区域发展、气候环境等议题,并通过Zoom、腾讯会议等媒体平台为政策制定者、行业精英、专家学者、国际组织人士等创造思想交流的高地。虽然其在社交媒体矩阵的配合和宣传方面也有所努力,但因核心会场影响力有限,未能在国际舆论界构成有效的传播空间和场域。2022 年12 月,全球化智库主办的第七届中国全球智库创新年会,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邀请来自10 余个国家30 余位全球知名智库负责人和资深研究者,围绕中美关系、后疫情时代的重启与发展、国际变局中的中欧智库交流等议题开展交流对话[32]。2023 年2 月,全球化智库理事长王辉耀和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前副会长包道格(Douglas Paal)、耶鲁大学法学院蔡中曾中国中心高级研究员董云裳(Susan Thornton)通过线上会议展开交流与对话,针对日益紧张和不确定的中美关系,探讨大国维持合作前景、担负全球责任的对策和出路[33]。以上述会议为核心,全球化智库一直在Twitter、微信、微博等社交媒体平台共建话题、引导流量、协同传播。然而,由于核心会议数量较少,全球化智库社交媒体矩阵传播始终缺乏立足点,在虚拟公共空间和场域的传播力及影响力方面均落后于美英两家智库。
4.3 积极伙伴关系构建:中国智库合作形式与深度有待进一步拓展
中、美、英3 家智库利用数字技术构建和加强跨国界、跨领域、跨机构的伙伴关系,并基于国家立场和利益需求开展竞争性合作。其中,美英智库更注重联合研究关系的建构,合作形式更为丰富、内容更为深入、周期更为完整,且思想性较强。相比较而言,中国智库的伙伴关系构建形式略显单薄,缺乏可持续性。
一方面,美英智库注重基于共同利益的伙伴关系建设,运用数字技术参与全球性议题,以应对全球性挑战、实现多方共赢。自2021 年2 月起,布鲁金斯学会与欧洲政策研究中心联合发起人工智能合作项目,定期邀请来自7 个国家政府、工业界、学术界和民间社会的专家,依托大数据技术,探索人工智能监管、研发和标准化层面的国际合作机会,旨在应对人工智能带来的挑战,并促进相关政策和技术的发展[34]。2023 年6 月,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联合特许信息安全学会、网络安全情报所、科技界女性论坛等机构发起“Cyber2023”数字项目,共同建立数字媒体平台和共同体关系,围绕全球政治、经济、科技、性别和网络安全等议题探索相关治理政策[35]。
全球化智库在伙伴关系建构形式方面与美英两家智库相比存在一定差异。全球化智库以会议活动为主,而不是研究项目的形式深化合作和关系。全球化智库与来自30 多个国家的驻华大使举办了大使圆桌会议,为世界了解中国后疫情时代的经济复苏、发展规划、数字化动态和可持续发展理念提供渠道[32],促进了更加包容理解的多边关系。相较而言,美英智库基于会议活动和研究项目双重意义上的合作,更能巩固彼此间的伙伴关系的构建,凸显共同的价值观念和利益基础。
另一方面,3 家智库秉持推进共有观念、促进全球治理的目标,更倾向的模式是竞合。智库致力于在国际舆论场与其他智库展开数字空间话语权的竞争,推动符合国家利益的观点生产和传播。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高级研究员瑞恩·哈斯(Ryna Hass)[36]通过官网、社交媒体等数字渠道多次表示,中国是美国意识形态较量中的“敌人”——美国虽然将中国视作当今世界上强劲的挑战和威胁,但是也在全球生产、数字经济、信息传播领域存在积极向好、寻求合作的一面——据此从智库视角引导国际公众对中国的认知,塑造有利美国利益的舆论环境。
5 结语
当前,数字化革命深刻改变了国际政治的框架条件,也重构了世界各国的公共外交理念与模式。智库作为国家思想创新的源泉和多元公共外交的重要行为体,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面对全球智库数字公共外交的转型,中国智库由于数字化意识不足、平台受限、内容生产力滞后以及来自美欧的战略遏制与技术封锁等多维因素,在国际舆论场面临逐渐失声与缺席的困境。随着中国政治、经济、军事、科技实力的不断增强,美欧等国家对中国的质疑与遏制也将会进一步升级,中国智库亟需加强数字公共外交意识与能力,加强与世界各国的思想对话与关系构建,提升中国的软实力与国际话语权。具体而言,应加强顶层设计与战略规划,全面提升中国智库数字平台建设与内容生产力,增强智库数字传播与对话能力;充分运用数字技术举办形式与规模多样化的智库会议,增强议题设置能力和思想广度,并以此为核心,搭建多元社交媒体联动的数字化媒介场域与国际对话平台;加强智库之间的积极伙伴关系建构,打造智库数字联盟,通过多元、深入的交流对话与项目合作,提升媒介化共情,推动共有观念形成以及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
无论是“数字公共外交”还是“智库数字公共外交”,对于学界和业界而言,都是新生概念和领域,其内容和样态将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演变以及国际政治和社会文化语境的变迁而不断演进。本文仅仅是抛转引玉,还有诸多具体的议题亟待学界深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