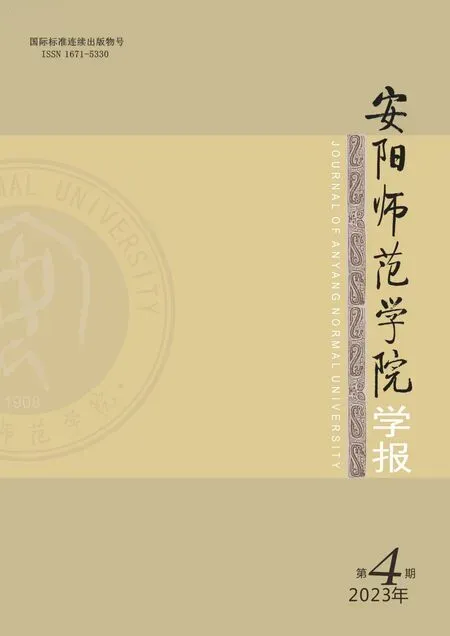唐传奇中的女侠形象及其文化意蕴
张 雨
(云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云南 昆明 650500)
豪侠是唐传奇的创作题材之一,《文言小说审美发展史》记载:“爱情、豪侠、隐逸,这三种题材向来为正史所拒绝,或处于正史的边缘,而在唐人传奇中,它们却居于中心位置。”[1](P178)唐代小说家在作品中塑造了许多侠客形象,其中,女侠形象异常出彩。唐传奇中的女侠大多诞生于中晚唐时期,结合当时的时代背景,不难发现,唐代女侠的出现与唐王朝女性意识的觉醒、佛道文化的交融、藩镇势力的崛起紧密相关。
一、女侠的历史渊源
侠是中国古代社会历史的特殊产物,在历代典籍中多有记载。女侠属于侠的范畴,早在东汉时期就被书写,如范晔《吴越春秋》中的越女。到了唐代,女侠形象尤为突出,在唐代豪侠小说中的地位不容小觑。
(一)女侠的内涵
女侠,从语言学上看,是一个偏正词组,其主体强调“侠”,“女”作为一个修饰语,表示“女性的侠客”,两者是修饰与被修饰的关系。所以,探讨女侠的内涵时,要先明白何为“侠”。
关于“侠”的渊源,最早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韩非的《五蠹》载:“儒以文乱法,侠以武乱禁。”[2](卷19,449)韩非认为侠的精神在本质上与国家法律相背离,凭借武力随心所欲,是危害社会稳定的因素。但此时对于侠的定义,却没有一种具体的解释,“以武犯禁”也只是论侠时的一种标准。先秦游侠的事迹,散见于《左传》《国语》《战国策》中,正史中司马迁《史记》中的《游侠列传》以及《汉书》中的《游侠传》是专为游侠而作,足可见最初的侠,是在史学范畴中存在。而史家对于侠客有着一套社会性的伦理评价标准,从“以武犯禁”到“其行虽不轨于正义”[3](P3182)可见,到了汉代,侠具有双重属性,一方面,“侠”的行为不受纲常制度的制约,与“盗”同类;另一方面,“侠”的精神是扶危救困,救人于危难之中。
女侠属于侠的范畴,也有双重属性。其一,其行为不受社会准则束缚。其二,行侠的目的是扶危救困,拯救自己或他人。女侠与两个群体相区分。女侠与男性侠客相对,在生理上区别于男子,心理上体现出独特的“刚柔之美”。女侠也与传统女性不同,首先,她们武艺高强,会各种剑术或道术。其次,她们有自我意识,不会依附于他人,与男子结合不是主要的生存手段,可以随意选择自己的人生道路。最后,她们有强烈的斗争意识,在面对困难时,依靠个人的力量,与他人斗争。因此,文学史上的女侠就是在作品中出现的带有自主意识和斗争精神且武艺高超的女性。
(二)小说中的女侠
唐前对女侠的书写较少,最早记载女侠的文献应是东汉赵晔《吴越春秋》中的《越女剑》:
越王又问相国范蠡曰:“孤有报复之谋,水战则乘舟,陆行则乘舆。舆、舟之利,顿于兵弩。今子为寡人谋事,莫不谬者乎?”范蠡对曰:“臣闻古之圣君莫不习战用兵,然行阵、队伍、军鼓之事,吉凶在其工。今闻越有处女出于南林,国人称善。愿王请之。立可见。”越亡乃使使者聘之,问以剑戟之术。……越王问曰:“夫剑之道则如之何?”女曰:“妾生深林之中,长于无人之野,无道不习,不达诸侯。窃好击之道,诵之不休。妾非受于人也,而忽自有之。”……越王大悦,即加女号,号曰“越女”。乃命五校之队长、高才习之以教军士。当此之时皆称越女之剑。[4](P241-242)
由此可见,越女身份神秘莫测,精通各种道术,是女侠形象的雏形。魏晋时期干宝《搜神记》中的《李寄斩蛇》记载了李寄为民除害,是智勇双全的女侠典范。此后,南朝范晔的《后汉书·列女传》中也记载了女侠赵娥为父报仇的故事。
李唐王朝在统一南北的基础上得以建立。“有唐一代,尚武任侠之风弥漫全国,唐代女子传承了前朝北方巾帼英雄的雄浑武风,她们与男子一样精通弓马骑射。”[5](P82)在尚侠之风的影响下,唐代小说家在作品中书写女侠故事,塑造了许多性格鲜明的女侠形象。这些故事主要收录载《太平广记》里。其中,较有代表性的篇目有《聂隐娘》《红线》《崔慎思》《谢小娥》等。
唐后的小说,对女侠也有所记载,如明代凌濛初的《韦十一娘》和清代蒲松龄的《女侠》等。但唐后的女侠书写大都是沿袭唐传奇的模式,艺术成就也不如唐传奇。
二、唐传奇中的女侠类型
与之前小说中的女侠相比,唐传奇中女侠数量更多,个性鲜明。根据女侠行侠目的的不同,大致可以分为复仇型女侠、报恩型女侠、仗义型女侠三类。
(一)复仇型女侠
唐人在传奇小说中塑造了大量复仇型女侠。据统计,“唐人豪侠小说女侠形象中的复仇女侠共九人,分别是谢小娥、蜀妇人、尼妙寂、贾人妻、军使女、崔慎思妾、村妇、邹仆妻、歌者妇。”[6](P20)其中,以谢小娥和崔慎思妾为代表。
唐传奇中女侠复仇的动机都是为了保护自己或亲人。谢小娥就是为父、夫复仇的典型代表。《谢小娥传》载:
小娥姓谢氏,豫章人,估客女也。生八岁丧母,嫁历阳侠士段居贞。居贞负气重义,交游豪俊。小娥父蓄巨产,隐名商贾间,常与段婿同舟货,往来江湖。时小娥年十四,始及笄,父与夫俱为盗所杀,尽掠金帛。段之弟兄,谢之生侄,与童仆辈数十悉沉于江。小娥亦伤胸折足,漂流水中,为他船所获,经夕而活。因流转乞食至上元县,依妙果寺尼净悟之室[7](卷491,4030)
由此可见,谢小娥背负了血海深仇,所以她女扮男装,依靠自己的力量为父、夫报仇。从她的行为可以看出,谢小娥是有勇有谋的女侠,她的复仇性质是正义的,符合社会伦理道德。
《崔慎思》记载的是一名女子怀有为父报仇的动机,嫁给书生为妾,伺机复仇:
二年余,崔所取给,妇人无倦色。后产一子,数月矣,时夜,崔寝,及闭户垂帷,而已半夜,忽失其妇。崔惊之,意其有奸,颇发忿怒。遂起,堂前彷徨而行。时月胧明,忽见其妇自屋而下,以白练缠身,其右手持匕首,左手携一人头。言其父昔枉为郡守所杀,入城求报,已数年矣,未得;今既克矣,不可久留,请从此辞。遂更结束其身,以灰囊盛人首携之。谓崔曰:某幸得为君妾二年,而已有一子。宅及二婢皆自致,并以奉赠,养育孩子。言讫而别,逾跨墙越舍而去。慎思惊叹未已。少顷却至,曰:适去,忘哺孩子少乳。遂入室。良久而出曰:喂儿已毕,便永去矣。慎思久之,怪不闻婴儿啼。视之,已为其所杀矣。杀其子者,以绝其念也。古之侠莫能过焉。[7](卷194,1456)
由此可见,崔慎思妾在大仇得报之后,果断地抛弃家庭,甚至还亲手杀死了自己的孩子。
透过唐传奇中女侠的复仇行为,可以看出她们依靠个人力量为血亲复仇,其胆识和精神值得肯定。另一方面,她们复仇的手段未能遵循社会的法律准则,折射出国家法律机制的不完备。实际上,复仇女侠处于艰难的生存处境,只能依靠个人力量,以快意复仇的形式来宣泄自己内心的不满。
(二)报恩型女侠
报恩型女侠受古代刺客的影响。“刺客”是中国古代社会发展过程中的特殊职业。司马迁在《史记·刺客列传》中记载了先秦时期五位刺客的事迹。《刺客列传》中的五位刺客拥有超人的胆识和非凡的能力,报答知遇之恩,不惜以身涉险行使刺杀任务。唐传奇的报恩型女侠就是继承了古代刺客游侠有恩必报的传统。
这类女侠以《聂隐娘》和《红线》中的同名主人公为代表。《聂隐娘》记载大将军魏锋之女聂隐娘十岁时被一尼姑带走,尼姑亲授其武艺,五年后隐娘学成归来。由于聂隐娘武艺非凡,因此备受陈许节度使刘昌裔赏识。为报答刘昌裔的知遇之恩,聂隐娘一心一意为刘昌裔效力。《红线》中的红线是潞州节度使薛嵩的婢女,虽然她身份卑微,但为报答其主之恩,盗窃田承嗣枕边的金盒,从而化解了一场可能爆发的战争。
唐传奇中的报恩女侠一般有两种特征。一是武艺高超,有勇有谋。《聂隐娘》中描述聂隐娘学成归家后,能够飞檐走壁,且“白日刺其人于都市,人莫能见。”[7](卷194,1457)拥有超凡的剑术。《红线》中红线在不伤人性命的前提下取到了田承嗣床头的金盒,用以震慑田承嗣,突出了她高超的武学才能。由此可观,作者在塑造报恩女侠形象时,有意渲染她们非凡的本领和过人的胆识。二是结局都是功成身退。《聂隐娘》中结尾写道:”自此无复有人见聂隐娘矣。”[7](卷194,1459)《红线》中也写道:“红线拜且泣,因伪醉离席,遂亡其所在。”[7](卷195,1462)由此可以看出,报恩女侠的行为具有非功利性,在任务完成之后选择功成身退。
这类女侠丰富了唐传奇中的女侠形象,不容忽视的是女侠所有的行为的动机都是出于报恩,但她们并未是非不分,《聂隐娘》中的陈许节度使刘昌裔、《红线》中的潞州节度使薛嵩,都有历史原型,他们代表正义的一方。作者对这类女侠隐逸的处理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她们的侠气,使她们在显与隐之间展现了侠客风范。
(三)仗义型女侠
唐代对于侠的正义性有了更高的要求,使侠的归宿走向了“义侠”。李德裕《豪侠论》载:“义非侠不立,侠非义不成。”[8](卷709,7277)在这种观念下,唐代文人在小说中塑造了惩恶扬善,仗义助人的女侠。仗义型女侠以樊夫人和荆十三娘为代表。
《樊夫人》中记载:
后至唐贞元中,湘潭有一媪,不云姓字,但称湘媪。常居止人舍,十有余载矣,常以丹篆文字救疾于闾里,莫不响应。乡人敬之,为结构华屋数间而奉媪。媪曰:“不然,但土木其宇,是所愿也。”……忽告乡人曰:“吾欲往洞庭救百余人性命,谁有心为我设船一只?一两日可同观之。”有里人张拱家富,请具舟楫,自驾而送之。……命拱之舟返湘潭,拱不忍便去。忽有道士与媪相遇曰:“樊姑尔许时何处来?”甚相慰悦。拱诘之,道士曰:“刘纲真君之妻,樊夫人也。”后人方知媪即樊夫人也。拱遂归湘潭。后媪与逍遥一时返真。[7](卷60,373-374)
可见,樊夫人在修仙得道之后心系百姓,无偿为乡民治病,凭一己之力拯救了洞庭百余人性命。她的身上兼具仁者情怀和侠者风范。
《荆十三娘》中表达女侠仗义助人的行思,更为直接具体:
唐进士赵中行,家于温州,以豪侠为事。至苏州,旅止支山禅院僧房,有一女商荆十三娘,为亡夫设大祥斋,因慕赵,遂同载归扬州。
赵以气义耗荆之财,殊不介意。其友人李正郎弟三十九爱一妓,为其父母夺与诸葛殷,李怅怅不已。时诸葛殷与吕用之幻惑太尉高骈,恣行威福,李惧祸,饮泣而已。偶话于荆娘,荆娘亦愤惋,谓李三十九郎曰:“此小事,我能为报仇。但请过江,于润州北固山,六月六日正午时待我。”李亦依之。至期,荆氏以囊盛妓,兼致妓之父母首,归于李,后与赵同入浙中,不知所止。[7](卷196,1472)
可见,荆十三娘对赵中立的义举十分钦慕,听说李郎故事之后,为李郎夺回爱妾的行为,展现了她的见义勇为、不畏权贵的性格特征。
唐传奇中的女侠“是男性气质与女性气质的二元统一体,她们勇猛果断,又并非如男人般一味用强,男性气质出现在女侠的身上弥补了女性本身的生理缺陷,提升了女性的人格价值,更展现了一种独立于男女两性的刚柔统一的人格魅力。”[9](P63)她们打破了性别的束缚,对男权文化为中心的封建社会宣泄自己的不满,实现了“侠”与“义”的高度统一,是文人内心完美理想女性在作品中的呈现。
三、女侠书写的文化意蕴
侠是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一种特殊产物,女侠亦不例外。唐传奇中的女侠形象有其特定的文化意蕴。唐人笔下的女侠形象与女性意识的觉醒、佛道文化的的影响、中晚唐的社会现实紧密相连。
(一)女性意识的觉醒
自周朝以来,受宗法观念的影响,社会的话语权都归男性,所有女性只不过是男性的附庸,没有独立意识。到了唐代,“李唐王朝的皇室出自北镇,为关陇贵族集团,是鲜卑化的汉人,其女系母统均为胡族血脉。唐代宫廷妇女在家族中地位较高,历来以果敢善断而著称。”[5](P83)受胡风胡俗的影响,儒家思想的正统地位受到挑战,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女性思想的觉醒。
唐代女性家庭地位较高,大多具有参政意识。“唐代妇女参政无论是参政者人数还是参政的范围都是其他朝代无法比拟的。参政者上至后妃、公主,下至普通劳动妇女,几乎包含了社会各个阶层的女性;参政的范围也从规谏、用人到宫廷政变乃至立废君主,甚至出现了直接当政掌权的女皇帝。”[10](P33)在这种风气的影响下,唐人笔下的女侠也参与政治生活。如聂隐娘一开始是为薛帅效力,当看到刘昌裔之后,曰:“刘仆射真神人。”[7](卷194,1458)毅然投奔了刘昌裔,表现出超出常人的政治远见。红线虽为婢女,却能协助主人处理文书,为主人守护城池,具有政治才能,并且在主人无助之际主动请缨,为其主解决问题,体现出了侠者风范。
除此之外,唐传奇中的女侠还具有鲜明的个性色彩,可以自由选择配偶。如聂隐娘选择磨镜少年作为自己的夫婿;谢小娥为父、夫报仇雪恨之后,拒绝里中豪族的求聘;荆十三娘丧夫之后,可以自由与其他男子交往,甚至可以再婚;女侠也可以选择自己的人生道路,不受他人的影响和社会的束缚。如崔慎思妾为父报仇之后,选择与家庭决裂,抛夫杀子;聂隐娘和红线在完成任务之后,都选择了归隐自然,不问世事。
在女性意识的觉醒下,唐传奇中的女侠具有参政意识,表现出敏锐的政治眼光,有明确的政治立场,她们也可以决定自己的婚姻大事,选择自己的人生道路,具有鲜明的个性特色。
(二)佛道文化的渗透
中唐时期,儒释道宗教思想共同发展,《因话录》中载:“元和以来,京城诸僧及道士,尤多大德之号。”[11](P855)其中,佛教在唐代尤为盛行,“许多文人都不可避免地受到佛教的影响。佛教对他们的思想、行为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2](P36)
佛教中轮回转世、自我救赎、行善积德的思想观念影响唐传奇小说的创作。《红线》中红线自述“前世本为男子”,因意外杀人而被转世为女子,因此红线的所思所想都是为了赎清自己前世的罪孽。小说中提到的“转世”与“赎罪”,是佛教轮回思想的反映。而她对世人的慈悲,则是佛教关爱生命、大慈大悲的真实写照。樊夫人无偿救助遭受困苦的百姓;荆十三娘在人遭受困难时,挺身而出的行为是佛教行善积德观念的体现。
到了晚唐,道教十分盛行,据载:
上好神仙术,遂起望仙台以崇朝礼。复修降真台,舂百宝屑以涂其地,瑶楹金栱,银槛玉砌,晶荧炫耀,看之不定。内设玳瑁帐、火齐床,焚龙火香,荐无忧酒。此皆他国所献也。(亡其国名。)上每斋戒沐浴,召道士赵归真已下共探希夷之理。由是室内生灵芝二株,皆如红玉。又渤海贡马脑樻、紫瓷盆。马脑樻方三尺,深色如茜所制,工巧无比,用贮神仙之书,置之帐侧。紫瓷盆容量半斛,内外通莹,其色纯紫,厚可寸余,举之则若鸿毛。上嘉其光洁,遂处于仙台秘府,以和药饵。后王才人掷玉环,误缺其半菽,上犹叹息久之。(传之于濮州刺史杨坦。)[11](P1390)
统治者对道教已经到了痴迷的程度,可见道教在唐代的地位。
道教思想也渗透到唐人小说的创作中。首先,唐传奇中女侠的装扮具有道教色彩,如红线在出发前额上的“太乙神名”是道教主神之一。其次,女侠的法术也带有道教的神秘色彩,如红线能夜行百里、穿屋过庭,聂隐娘能够飞檐走壁、化药为水。再者,女侠的内在品格也体现了道教的文化特征,如红线和聂隐娘一心为主出谋划策,排忧解难,在任务完成之后,她们选择归隐自然,表现出了对名利、生死的超越,具有道教神仙信仰回归自然、自由逍遥的特点。
由此可见,唐人笔下的女侠拥有神秘的道术,服食丹药之后可以长生不老,有些女侠还以拯救苍生为己任,是道教和佛教思想的体现。
(三)中晚唐现实的折射
唐人小说兴盛于中晚唐时期,此时的唐王朝经历了安史之乱。战乱给唐代带来的灾难是不可磨灭的,如《旧唐书·郭子仪》载:
时藩虏屡寇京畿,依蒲、陕为内地,常以重兵镇之。永泰元年五月,以子仪都统河南道节度行营,出镇河中。八月,仆固怀恩诱吐蕃、回纥、党项、羌、浑、奴刺,山贼任数、郑庭、郝德、刘开元等三十余万南下,先发数万人掠同州,期自华阴趋蓝田,以扼南路,怀恩率重兵继其后。回纥、吐蕃自泾、邠、凤翔数道寇京畿,掠奉天、醴泉。京师震恐,天子下诏亲征,命李忠臣屯东渭桥,李光进屯云阳,马璘、郝廷玉屯便桥,骆奉先、李日越屯盩屋,李抱玉屯凤翔,周智光屯同州,杜冕屯坊州,天子以禁军屯苑内。京城壮丁,并令团结。城二门塞其一。鱼朝恩括士庶私马,重兵捉城门,市民由窦穴而遁去,人情危迫。[13](卷120,3461-3462)
《新唐书·兵志》中也记载:
其军、城、镇、守捉皆有使,而道有大将一人,曰大总管,已而更曰大都督。至太宗时,行军征讨曰大总管,在其本道曰大都督。自高宗永徽以后,都督带使持节度使,始谓之节度使,然犹未以名官。景云二年,以贺拔延嗣为凉州都督、河西节度使。自此而后,接乎开元,朔方、陇右、河东、河西诸镇,皆置节度使。
及范阳节度使安禄山反,犯京师,天子之兵弱不能抗,遂陷两京。肃宗起灵武,而诸镇之兵共起诛贼。其后禄山子庆绪及史思明父子继起,中国大乱,肃宗命李光弼等讨之,号“九节度之师。[14](卷50,1329)
可见,中晚唐时期,藩镇割据严重,地方节度使拥兵自重。在这样的环境下,“唐代文人士子把生活中的所见所感通过小说写出来,像社会政治、达官贵族生活作风等方面问题,因为不便于明示,便以不现实的笔法创作出来。”[15](P26)聂隐娘和红线虽然是虚构的,但魏帅、刘昌裔、田承嗣、薛嵩都能从历史上找到原型,他们都是真实的历史人物,均为地方节度使。作者通过写他们之间的冲突,展现了安史之乱后藩镇割据的混乱现状,同时也从侧面流露出作者渴望维护社会稳定的政治理想。
经历了安史之乱后,盛唐气象已经不在,人们在黑暗、腐败的统治下求生存。处于夹缝中的唐代文人便以虚构的方式塑造女侠形象,书写女侠故事,反映了中晚唐黑暗的社会现状。
四、结语
唐人小说是中国古代文言小说的巅峰,描写了大量的豪侠故事,对女侠的描写尤为突出。唐人笔下的女侠,武艺高超,性格鲜明,敢于向以男权文化为主导的封建社会提出挑战,是文人内心理想女性人格的外化。结合中晚唐的时代背景,不难发现,唐传奇的女侠形象是女性意识觉醒和佛道文化交融下的产物,透过唐人小说中的女侠形象,也能窥视中晚唐的现实世界。
——从《刺客聂隐娘》看侯孝贤的“归去”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