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略特的诗艺之环:走向《四个四重奏》
谈炯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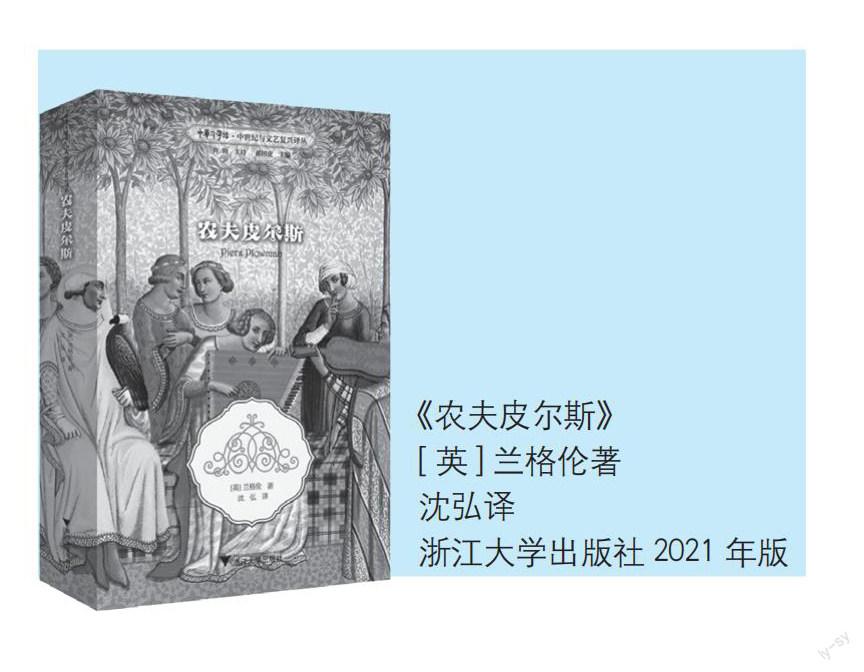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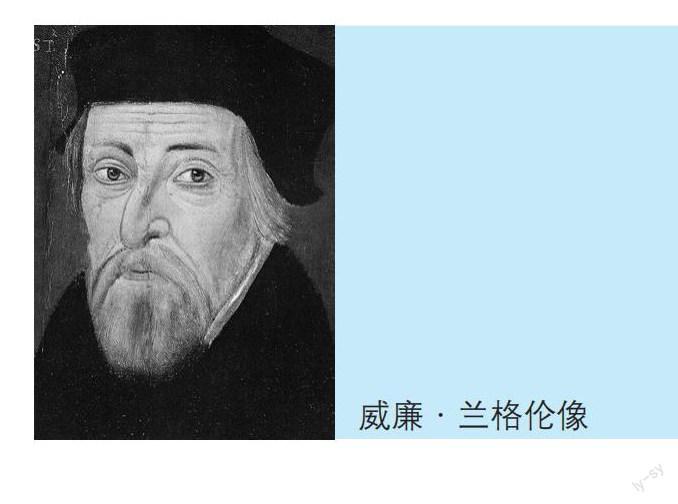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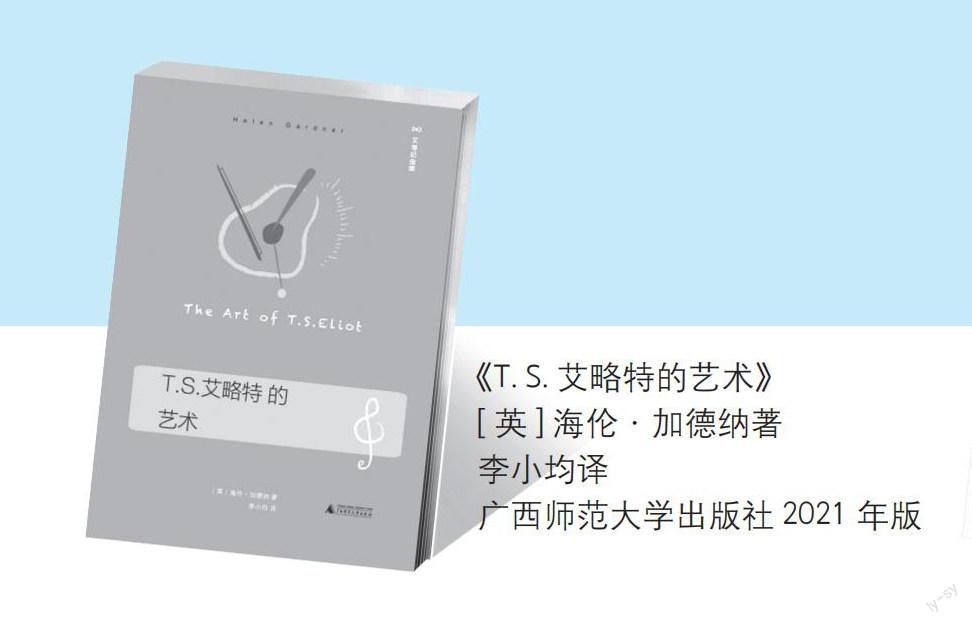
無疑,T. S. 艾略特(1888-1965)其诗其文,在英语现代诗的发展中,占据着极为关键的位置。他之于英语现代诗的重要性,在于他总是能发现一种清晰的理论公式,并将它贯彻到自己的写作中去:他的评论打碎了乔治时代失去革命性的浪漫主义绵软如肥皂泡的风格,又引入了一种崭新的、知觉化的感受力,取代慵懒而模糊的无身体的韵律。《荒原》《传统与个人才能》,客观对应物、感性的分离,他的诗歌与理论被迅速纳入经典化的过程,并造成现代文学评价标准的板块漂移:由于玄学派板块的挤压,邓恩从枯燥、抽象的诗歌盆地隆起为难度等级极高的山峰,雪莱、弥尔顿却经历着一次次地震,成为一种需要被克服的痼疾。而关于艾略特的诗歌与理论的论述,又仿佛形成了新的、伸出文学大陆的“半岛”,逐渐有了自己的水系、地势与气候。在艾略特的第二故乡英国,他的受欢迎程度仅次于莎士比亚。
同时代性的书写
英国文学评论家海伦·加德纳(Helen Gardner,1908-1986)所著《T. S. 艾略特的艺术》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对艾略特诗歌的即时观察。该书初版于一九四九年,其渊源则是作者于一九四二年写作的《艾略特最近的诗歌》一文。不同于大多数此类著作,加德纳是以《四个四重奏》为论述中心的。
评论同时代的文本是大概最适用于新批评的方法,把文本当成一种完善的晶状结构,而不借助外部的历史、社会与传记材料来稀释它的文学性。此书出版时,距离艾略特完成最后一首四重奏《小吉丁》不过七年(其余三首,《燃毁的诺顿》1935年,《东库克》1940年,《干塞尔维其斯》1941年)。《四个四重奏》所书写的内容,还没有彻底地熔铸成某种公共经验,它依然把那些个人性的书写附在词的羽翼下,它所提及的事物依然是当下的,所以既鲜活,又常被忽视。人们倾向于认为当代的文本是松软的、浸过水又沾上现实尘埃的海绵拖把,只有当它被闲置已久,现实的尘埃逐渐让它变硬、难以使用时,读者与评论家们才愿意反复地挤压文本的海绵柱,以恢复它在历史中原本的柔韧与自然。但同时代的作品之所以能够产生一种深刻的“同时代性”,正是因为它完全是“不合时宜的”。读者常常会把同时代性理解为书写新闻事件,这些看似合时宜的作品,就像报纸上寻常的新闻摄影,是将信息压缩在图像的连接、断裂与皱褶中的,而图像本身却并没有从其中流溢出来。我们只是在读,把图像读成另一种文字,但我们的眼睛与耳朵并没有为它打开。诗歌不服从于一般新闻写作所要求的纯粹工具性,它要求全部知觉的介入,可以成为图像,那非文字的图像。在艾略特那里,诗歌在文字成为非文字的地方成立。
例如他在《小吉丁》中写到德军对英国的轰炸,便是把历史事件上升为关于本质经验的沉思。他的升华没有让诗丧失具体性,当他将德国轰炸机比作“黑色的鸽子吐着闪亮的舌头”“俯冲的鸽子以白炽的/恐惧之焰划破天空”,他并没有取消这一事件的复杂性;相反,他勾勒出它令我们恐惧的地方,即在绝对恶的笼罩下,人类之言说的艰难。轰炸机作为“现代圣灵”,是那种技术力量的象征。与之对应的,在《干塞尔维其斯》中,密苏里河成了“强壮的、棕色的神”,不论圣灵还是神,它们都有超出于人性之上的权能。但人正是因为自信于可以把控机器非人性的破坏力,才会崇拜作为绝对的进步神话之具象化的机器。圣灵可以与人相切磋,它落到你的肩膀上,是这样的一个时刻:你感到自己强烈地与世界联系在一起,就像电路板上一个小小的电路,因为共同的电的通过而震颤,你看到太阳的第一束光,啄破了地平线,你的皮肤上有露水的味道。但我们的现代圣灵绝非如此,一旦它与你发生联系,你必须伏卧于地如一条被晒干的蚯蚓。
艾略特用鸽子象征圣灵,这个意象第一次出现在《小吉丁》的第八十到一百五十一行。这一大段诗歌模仿了但丁的《神曲》,无论形式上还是内容上。诗句以三行作为一个单位向前缓步推进,空袭过后,黎明之前,诗人在巡逻路上走着,他遇到了逝去诗人(主要指叶芝与乔纳森·斯威夫特)的鬼魂,那些大师教导他“既然我们的关注是言语,言语逼迫我们/使部落的方言纯净”,而在灾异之中,灰烬之下,保持语言的纯净几乎成为一种英雄主义。加德纳认为,在《四个四重奏》中,艾略特成功地抵制了把这首长诗写成自传的诱惑。他为英语发明了真正的颂诗,英语读者无法适应品达式的精致韵律的甜腻,也无法容忍布满水密隔舱的日记体长诗,这种长诗结构松散,每一段都可以被淹没、被舍弃。颂诗对当下经验的处理不同于日记或自传:“日记可以给我们进步感和成长感,但没有内含于开始之中的终结感,而是必然的成长感;日记有叙事的兴趣,却没有情节带来的深层次愉悦。”每一段日记都是攀着海藻、装载着货品的水密隔舱,它沉入我们海水一般苦涩的日常,在其中迟缓而犹疑地移动。日记依照一个给定的航线行走,这航线像珍珠项链一样把一个个终点串在一起,因为它随时可以停下,所以在这条线上,每个点都是将来时的终点,这样的书写也无所谓颂诗需要的严谨结构了。
身体的语言
或许我们可以想象一位活在十四世纪的艾略特。他必定要在一个乡村小教堂,用结结巴巴的羽毛笔蘸上失聪的黑色,一丝不苟地勾勒那些坚固如罗马柱的花体字。那个世界被同一种语言、同一种知识型联结在一起。我们所设想的这个不为人知的神父艾略特,可以用诗人艾略特的几句即兴诗来描述:“遇到艾略特多不愉快!/他的容貌是一副教士气派,/他的额角这样肃穆严峻,/他的嘴巴这样一本正经”。如果神父艾略特为了缓解一下抄经的疲倦,或许想要反刍自己的经院哲学作些诗的话,他会发现拉丁语是一件称手的工具,而他所使用的词语与象征早已尽善尽美,仿佛一张严谨的密码表,可以将思想转写为图像与韵律。他也不必考虑读者,因为所有能读懂拉丁文的读者都欣然接受这一套语言系统。
但正如诗人艾略诗在《宗教和文学》一文中论述的,对于现代读者,宗教诗歌是次要的:“宗教诗人并不是用宗教精神来处理全部诗歌题材的一位诗人,而是只处理全部诗歌题材中一个有局限性的部分的一位诗人:这位诗人排除了人们通常认为是人类特性的一些主要激情,因此也就承认了他对这些激情的无知。”艾略特不相信在剥离其使用价值后,文字可以单独获得价值。当然,他并不认为我们不能纯粹欣赏一部科学或哲学著作的文风,但对语言欣赏的滥用会磨损我们对这些经典作品真正力量的感受。如果钦定本《圣经》仅仅被当成英语散文作品,它就不足以构成一个独立的象征系统,且对英国文学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钦定本《圣经》就像金矿,有的人找到了矿脉,于是成为经典的一部分,有的人觅得一身灰尘,让语言也布满了灰尘。但这一切悲喜剧的源头都在于这文本被当成了金矿,当成神的话语本身。现代文学的语言危机就在于—依艾略特之见—当《圣经》被当成文学讨论后,就像我们把金矿当成了一座布满了钻孔的白蚁巢,那些金子,那些神圣的光辉消逝了,其文学影响也就此终结。
作为宗教信徒和保守主义者的艾略特,显然不欣赏现代文学批评分食《圣经》的倒影的尝试。一九二七年,艾略特加入英国国教,并入了英国籍。三年后他发表的《灰星期三》便因为宗教体验的进入而体现出与包括《荒原》在内的前期诗歌在风格上的差异。加德纳注意到,艾略特前期诗歌晦涩、浓缩,紧绷如锻炼过度的肌肉。《灰星期三》却有着咒语一样的节奏,围绕着个别诗句不停打转。艾略特的前期诗歌习惯于编织嗅觉与味觉体验。与视觉不同,嗅觉与味觉较少被诗人们注意到。因为相比视觉,嗅觉与味觉更加切近身体,它们有着绵密的连续感与厚度,仿佛充盈于我们血液的一种气息。视觉可以直接榨出意义,纳入思维的过程,嗅觉与味觉除了表征它们自己以外,并不与形而上直接相关。当我们说“森林”,我们看到的是一派浓稠得无法进入的绿色,听到的是风拨动牙刷软毛的铮铮,是摇落的水珠与落叶,是鸟从齿轮般咬合在一起的阴影中冲出,这幅景象可以轻易地上升为象征:在人生的森林中我们总是迷惘。但当我们以嗅觉与味觉的方式去感受一片“森林”,我们闻到松林与露珠的清香,落叶发酵后的臭味,我们想象着我们如何咀嚼森林中淡蓝色的氧气。这样的感觉几乎完全服从外在环境,我们的知性难以为嗅觉与味觉披挂上一身意义的勋章。正因如此,艾略特前期诗歌中的嗅觉意象,完全不追求意义上的升华,他采用这些意象,旨在拓下陈腐而令人厌烦的世界的一个碎片。譬如《序曲》中的这些句子,“走廊里一股炸牛排的味儿”“早晨开始意识到/踩满锯屑的街上传来的/微微走了气的啤酒味儿”。这些嗅觉意象是人造的、庸常的,它同时关联着味觉,但也只唤起某种乏味的味觉。
《T. S. 艾略特的艺术》引述了艾略特对阿诺德“没人能否认诗人的特权是书写一个美的世界”这一言论的评价。在艾略特看来,诗人本质上的特权,不在于那个被意识形态的糖浆层层包裹的“美”,而是“能够看到美与丑的底层,在于看到厌烦,以及恐怖,以及光荣”。加德纳认为正是“厌烦、恐怖以及光荣”构成了前期艾略特与基督徒艾略特的统一性。嗅觉与味觉的意象当然不可能变成那种尖锐的恐怖,它们四处弥散,给人以温水煮青蛙的窒息感。但恐怖要求一种对生活本质的洞察,厌烦至多是恐怖所垂下的阴影。从前期诗歌到《荒原》,恐怖逐渐成为他诗中的主角,随着那个皈依时刻的到来,恐怖背后的光荣遂构成了《四个四重奏》。
诗剧与戏剧诗
艾略特在《四个四重奏》中完成了他在《灰星期三》里开启的探索。这位时刻需要为自己的晦涩辩护的诗人,想要找到一种具有普适的可理解性,可以穿透阶级隔膜发挥其效用的语言:在拉丁中世纪曾经有过这样的语言,它如同连接作者與读者的脐带,不倦地沟通彼此。海伦·加德纳将《灰星期三》与《四个四重奏》和兰格伦的《农夫皮尔斯》对比。威廉·兰格伦(William Langland,1330-1400)生活在十四世纪,生前是一名默默无闻的小牧师(甚至由于位阶较低,无法享受圣俸)。研究者认为兰格伦可能在大马尔文修道院接受了完整的神学教育。加德纳在《T. S. 艾略特的艺术》中多处提及兰格伦:尽管与乔叟相比,兰格伦沿用了旧的头韵诗形式,他的语言也没有在英语文学中留下持久的印记;从一五六一年到一八一三年,他的作品再没有重印,关于他的研究也停滞不前,但他的《农夫皮尔斯》仍是英语诗歌中最富想象力的作品之一。如果我们想象中的神父艾略特学会了写诗,他也许就会成为语言更强劲的威廉·兰格伦;如果兰格伦生活在艾略特的时代,他或许也会写出《灰星期三》那样的作品。
在《灰星期三》中,艾略特几乎完全置换了自己的意象系统:玫瑰、花园、珍珠独角兽、白色的蜥蜴取代了头发中的纸带子、阿伽门农尸体上的鸟粪。他依然热衷于用典,只不过这次集中于《圣经》与《神曲》。在这首诗中,更多时候艾略特并不停留在特定的意象上,与其让读者沉溺于对意象美学质感的咀嚼,不如让意象服从于主题,因为对于皈依者艾略特来说,这主题具有极端的重要性。不过,《灰星期三》并不是一次成功的尝试。但这对于兰格伦,则是一种惯习的手法:用《圣经》语言标示思维的路径,直接使用宗教意象表达思想。这在艾略特的时代已经失去了理解基础,而兰格伦由于被迫下沉至生活的底部—他与妻女居住在康希尔的小木屋,靠为赞助人祈祷赚取报酬—所以他的语言在他所生活的年代拥有了艾略特追求的普适性。他不像宫廷诗人,为少数几个王公贵族写作,他的读者是那些布道文的听众,其中既有小商小贩,又有马夫农民。所以《农夫皮尔斯》采用了一种混杂的语体风格,其中既有粗浅的俗词俚语,又有文雅的雄辩,既有琥珀般散发神圣光泽的诗句,又有乡野村夫们泥泞的口音。
对普适性语言的追求把艾略特导向了诗剧的创作。他的前期诗歌有戏剧诗的特点,即他会通过一些人格面具来说话,并且会有一个极为精巧的舞台背景内嵌于诗行中。譬如《杰·阿尔弗莱特·普鲁弗洛克的情歌》(以下简称《情歌》)这首名诗,虽然是以第一人称展开叙述的,但这声音非常明确地属于一个异于作者的说话人,作者与说话人保持着反讽的距离,类似于剧作家与剧中角色的距离。我们跟随普鲁弗洛克穿行于黄昏的城市中,《情歌》展开的背景,对于一首中等篇幅的诗来说,是一个非常广阔的背景:从廉价小客店到上流社会的沙龙,从黄昏到夜晚。《情歌》不仅在现实空间中展开,它还打开了一个经典与神话的空间:普鲁弗洛克将自己与《圣经》中的先知约翰、哈姆雷特王子等对照,以一种否定的方式确定自己的位置—“尽管我已经看见我的头颅(稍微有点秃了)给放在盘子里端了进来”“不!我不是哈姆雷特王子,也不想成为王子;/我是侍从大臣,一个适合给帝王公侯出游/炫耀威风的人,发一两次脾气,/向王子提点忠告;毫无疑问,是个随和的爪牙”。
但诗剧与戏剧诗的文体特质毕竟大不相同。在现代,诗歌常常被当成一种案头文学;而诗剧,它既是诗的,也是戏剧的。如果诗剧中的句子因过度的典故、修辞而板滞,就像没有盖盖子的液体胶,渗出来的过多的意义凝固住了,使得它不再可以被使用,那么它就不是戏剧的;同样,如果它没有像飞过水面的瓦片一样在观众的心灵上轻轻点上几下,那么它就不是诗的。而要打出最多的水漂,语言的瓦片就不能太厚重,同时,剧作者让语言打向我们心灵的水面时的角度以及他与水面的距离也很重要。戏剧语言需要即时让观众理解:它必须产生意义。
这里,我们应该审思一下戏剧中的意义与诗歌中的意义的差别。一个词,它连接了声音与符号,我们把声音与符号这些语言的外壳称为能指,把词所指的概念称为所指。所指与能指并非严丝合缝地一一对应,而是系于一长串永无休止的能指链条:它可以根据联想的原则无限延伸。譬如,说到“衣架”时,我们由它联想到“衣服”,由“衣服”到“洗衣机”,由“洗衣机”到“洗衣液”,由“洗衣液”到生产洗衣液的“车间”,由“车间”到“劳资关系”,由“劳资关系”到“资本论”,所以,“衣架”这个所指上不仅能挂衣服,也能挂上整个世界。不存在固定的意义,意义是我们观察能指链条时所处的位置。在一则轶事中,当有人问起艾略特他的几行诗的意思时,他把这几行诗又读了一遍。我们大概会觉得艾略特在刻意地沉默,逃避对诗的阐释,事实上,他更有可能是在提醒读者诗歌在能指层面的效用。诗歌有时会处在德里达式的“延异”中;戏剧,却要更逼近所指,它必须对观众有所表达,也对观众的回应有所期待。戏剧正是在观看与被观看中产生的一系列动作与言语的扭结。
走向《四个四重奏》
在《T. S. 艾略特的艺术》出版时的一九四九年,艾略特才刚刚开始了他的戏剧实验,完成了《斗士斯威尼》的两个片段,以及《大教堂凶杀案》和《家庭团聚》。很难从舞台的角度考虑这些戏剧,加德纳罗列了这些戏剧在技术上的缺陷:“提示部分过于笨拙,动机不足或不可信,明显依靠巧合。”但她坚持认为,这些作品是“十七世纪以降最好的英语戏剧诗”。当然这里我们主要把这些戏剧当成以对话形式写作的诗歌。
《大教堂凶杀案》中并不存在人物,存在的只是观念的器皿。这出戏剧几乎是静态的,艾略特以埃斯库罗斯早期戏剧为模板,观众看不出谋杀坎特伯雷大主教托马斯的那些骑士的心态变化。人与人之间的联系与互动造成的戏剧性让位于人与观念的联系。这出戏剧真正动人的地方在于合唱曲的运用。合唱消解了“我”的存在,只留下“我们”这样一个单一的巨大声部,它需要配合既定的音乐,用语词填充音乐的存在,随着音乐的起降而改变它的锐度与亮度。艾略特为《磐石》剧本(《磐石》由伦敦主教区下辖四十五教堂基金会委托创作,1934年5月28日至6月9日于马具匠之井剧院演出)所写的合唱词,是他第一次尝试这种言说方式。与《大教堂凶杀案》一样,这些合唱词有强烈的应制色彩,磐石的典故出自耶稣登山宝训中的磐石之喻,所以,这出剧与《大教堂凶杀案》一样,是一出宗教剧,是以舞台的形式进行布道的尝试。
一九六八年,《T. S. 艾略特的艺术》第六次重印时,海伦·加德纳介绍了艾略特创作《四个四重奏》的因缘—在接受作者访谈时,艾略特以他惯常的谦逊谈到了自己创作《燃毁的诺顿》的经过:“《燃毁的诺顿》取自《大教堂凶杀案》的‘一点儿余料’,他觉得‘浪费了太可惜’,于是就把这‘一点儿余料’和《爱丽丝漫游奇境记》的开头以及一个周日去燃毁的诺顿的一处花园闲观‘搅拌在一起’。”因为其强大的语言能量,《大教堂凶杀案》没有成为一出真正的现代诗剧,古典戏剧强调情节,现代戏剧更强调剧场的存在,艾略特的诗剧不在这两者的行列。但也正因为创作诗剧的尝试,艾略特真正地找到了一种有普适效应的语言,不再依赖神话的构型,不再要求读者谙习诸多潜文本。他直接与他的读者对话,不臣服于自传性的书写,以自传性稀释理解的难度。可以被自传性稀释的难度,本身就是可疑的,就像浓雾,当我們置身其中时,就会发现它们只是一些稀疏的水珠。《四个四重奏》本身是有难度的,它的难度不是作者刻意制造的难度,而是因为语言的鞘中,那把观念的剑有时锋利,有时锈迹斑斑,有时甚至在怀疑论中打结。
但《四个四重奏》最终完成了艾略特的诗歌创作:不仅仅在于它完全摆脱了英语诗中“英雄诗体”的强力传统,还在于它重新找回了那种充满可能性的语言—一种超越阶级的现代经验可以在这语言中栖居。与兰格伦不同,《四个四重奏》不再能依赖于一个固定的象征系统与知识、教育体系。它只能在自反性中反复提纯语言本身的存在,语言有时径直变成音乐,有时变成一种即将到来的东西:“每首诗都是一则墓志铭。”它拓下我们生命中的一部分,当拓包在石碑上敲击,我们看到那些笔画:时间的一小块碎骨,在我们的注视下成型。承载这些词语的纸,常常是过于脆薄了,它会在阳光照射下破裂,变成一地语言的皮屑。制作一张词的拓片需要耐心、柔韧与持久的练习。但我们拓印下来的词语从来不是那镂在石头上的永恒的词语本身,只是复本。就算大诗人,也仅仅是在拓印永恒,他们每个人都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一块石碑。可惜的是,更多的诗人,或者说绝大多数诗人,只是把大诗人制作的拓片拍摄下来而已。
在完成了《四个四重奏》后,沉默成了艾略特的最后一首诗。《T. S. 艾略特的艺术》再版时,加德纳也没有再往书中加入关于艾略特新作的内容。这本书呈现的那个大诗人已在《四个四重奏》中达到顶峰,而这本书同样以《四个四重奏》为讨论的起点和终点。因着这一份即时的批评,文学界得以把握艾略特诗艺的环状结构,仿佛他在《四个四重奏》开头所引述的希腊哲人赫拉克利特的名言:“上升的路与下降的路是同一条路。”我们走完了那上升的路,我们看到《四个四重奏》成为语言指环上的那颗钻石,后世的诗人一遍遍地擦亮它,回到它,乞求那纯净的语言与对语言的意识重临于我们的诗行。

———摄影大师艾略特·厄维特拍的一组情侣照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