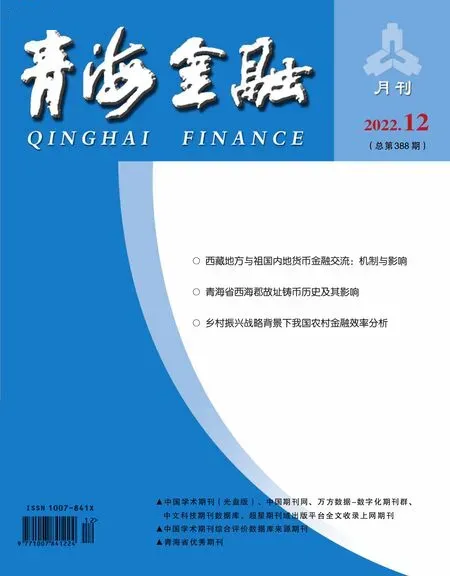西藏地方与祖国内地货币金融交流:机制与影响
■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课题组
引 言
西藏自古以来就是祖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第七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上指出:“深入开展西藏地方和祖国关系史教育”“要挖掘、整理、宣传西藏自古以来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事实,引导各族群众看到民族的走向和未来,深刻认识到中华民族是命运共同体,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从历史维度看,西藏地方和祖国内地货币金融交流十分密切,涉及经济、社会、政治等全方位的交往活动。
一、前吐蕃时期(公元633年以前):贸易发展推动了中原地区货币在西藏使用
西藏的前吐蕃时期在时间上大致对应中原地区的隋朝以前(公元618年以前),这一时期,中原地区的货币流通经历了以物易物到使用一般等价物到称量货币到金属铸币的过程,基础的信用活动开始萌芽。而西藏地方经历了以物易物到使用一般等价物再到称量货币的阶段,与中原地区金融活动的脉络基本一致,只是因长期部落战乱而未出现统一的铸币。
(一)两地货币金融交流的主要方式
前吐蕃时期,中原地区与西藏地区之间通过形式简单的贸易实现货币金融交流,中原地区陆续以贝、铜、黄金、白银、丝绸、茶叶等作为一般等价物,在与西藏的货物交换中行使货币职能。
原始部落时期(殷周时期前后),有藏民用牦牛等牲畜、青稞麦(中原称为“耒”)等与中原的农产品进行以物易物1西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编:《西藏昌都卡若遗址试掘简报》,《文物》,1978年第9期;童恩正、冷健:《西藏昌都卡若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发掘及其相关问题》,《民族研究》,1983年第1期。。春秋战国前期,西藏以贝币为主参与交换,在部分地区以与中原地区同样的铜、黄金、丝绸作为财富的象征。此后,中原地区开始进入金属铸币阶段,而在西藏出土的同一时期陪葬品中,发现了黄金制品、铜器和铁器。另外,西汉时期也有将茶作为商品通过四川向西藏交换牦牛等的记载2焦虎三、焦好雨:《茶马古道“锅庄文化”文史调查与研究辑要》,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在大致相当于中原汉晋时期,青藏高原西部和北部地区已经通过丝绸之路和中原地区建立相当程度的联系与交流3霍巍:《“高原丝绸之路”的形成、发展及其历史意义》,《社会科学家》,2017年第11期。。西藏汇入丝绸之路为西藏提供了承接中原地区与中亚、西亚的通道,大量物资包括货币通过丝绸之路流入,在这一过程中,丝绸、金银等也逐步开始在西藏地区作为一般等价物使用,对当地金融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二)两地货币金融交流的影响机制
前吐蕃时期,中原地区和西藏贸易交流主要依靠原始部落间的联系、中原古羌人部落西迁及早期民间商人的活动来实现,同时带动了货币的交流。从西藏昌都卡若遗址出土的陶器特征看,在四五千年前西藏与中原地区的原始部落间就已经存在某种交往联系。新石器时代结束到吐蕃王朝兴起前这一历史时期中,的确有来自黄河上游的若干羌人部落和由北方草原地区南下的游牧部落先后从不同方向进入西藏高原4参见《后汉书·西羌传》和《新唐书·吐蕃传》。,这些部落的长期迁徙,是中原地区和西藏开展贸易以及货币交往的重要前提。从民间商人活动看,公元6世纪左右(吐蕃囊日伦赞时期),在雅隆部出现了集市,市场繁荣,各族商人带着珍宝和特产及其他货物前来交易。这一阶段,依托集市和丝绸之路,民间商人活动成为中原地区与西藏交流的重要纽带,也是中原地区向西藏输送货币的主要途径。
(三)两地货币金融交流对西藏社会发展的影响
前吐蕃时期,中原地区和西藏货币金融交流对西藏社会发展起到了一定的积极影响,最主要的是西藏首次出现了度量衡及贸易价格的规定,西藏经济得以快速发展,商品交换日趋活跃。《贤者喜宴》中记载:“赤欧囊尊之子制造升、斗及秤以量谷物酥油,贸易双方商议互相同意的价格。而在此之前西藏地区无贸易标准一升、斗及秤。”中原地区与西藏早期商人贸易和货币交往活动,也为西藏输入了汉族文化,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西藏地区社会文化的发展,据藏文典籍《雅隆觉卧佛教史》载,“囊日颂赞时,自汉地传入历算和医药。”
二、吐蕃时期(公元633—842年):中原地区社会局势的变化对货币金融交流产生了重要影响
西藏的吐蕃时期在时间上大致对应中原地区的唐朝(公元618~907年),在这一时期,中原地区经历了实物货币退出,到金属铸币确定为主流地位的过程,信用活动有序发展,纸币、金融业开始萌芽。但“安史之乱”后,分裂割据、社会动荡,货币普遍减重、贬值,区域性通货膨胀频发,不仅造成了经济上的混乱,也对货币金融业的发展产生了负面影响。而西藏在吐蕃时期,主要使用砂金等贵金属作为货币,部分地区开始使用唐朝铜钱,“安史之乱”后,铜钱逐步被废止,改回以物易物的实物货币形态。
(一)两地货币金融交流的主要方式
吐蕃时期,依托正处于繁盛时期的丝绸之路和政治和睦,中原地区和西藏地方通过双方间的政治、经济交流促进货币金融交流。
文成公主入藏、吐蕃派遣青年至唐学习、吐蕃商人到中原地区贸易的过程中,唐朝的沙金选淘和熔炼技术逐步传入西藏,为西藏地区的砂金货币发展创造了条件。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黄金成为财富的象征,被吐蕃王室作为货币使用。大量黄金还作为贡品向唐朝进贡、缴纳和亲聘金5参见《旧唐书·吐蕃传》。。
值得注意的是,吐蕃时期,茶叶作为西藏的一种特殊的货币,连接了西藏和中原地区的贸易活动。文成公主入藏后,唐朝开办了官方互市贸易区,大力发展民间贸易,大量茶叶被输入西藏。公元712年,唐蕃会盟决定开展以丝、茶换马的互市贸易。吐蕃用黄金、铸币大量购买唐朝的丝绸、茶叶等,黄金、丝帛、茶叶直接充当了流通手段和支付手段。
(二)两地货币金融交流的影响机制
这一时期双方的贸易主要分两种方式进行:一种为朝贡贸易,由兼具政治与经济两种使命的互通使者完成;另一种为互市贸易,双方间除丝绸织物外,茶叶、马匹也成为重要交易品。吐蕃通过贸易获取大量唐朝铜钱,丝绸和茶叶作为一种货币形式被广泛交换使用。唐朝在鼎盛时期与吐蕃之间处于相对和平的历史阶段,但在“安史之乱”后,中原地区战乱割据,两地的货币金融交流开始收缩。五代十国时期的分裂动乱,基本上中断了西藏和中原地区的货币金融交流。
(三)两地货币金融交流对西藏社会发展的影响
从经济层面看,吐蕃时期,西藏与中原地区的贸易带动了农牧业、手工业和建筑业的发展,西藏各地的经济联系日益密切,商业开始蓬勃发展。随着吐蕃王朝势力的不断扩张,形成了面向南亚、中亚和东亚地区的较为稳定的交通干线和路网——高原丝绸之路6霍巍:《论青藏高原古代各族人民共同开创了“高原丝绸之路”》,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1年第2期。,大大促进了西藏生产力的发展和经济社会的进步。从政治层面看,西藏的统治阶级和农奴主在商业活动中集中了黄金、土地、茶叶等绝大多数社会财富,压榨农奴,激发了奴隶和平民的反抗和起义,是推动西藏吐蕃奴隶制的经济制度向封建农奴制的经济制度飞跃的根本动力7陈崇凯:《西藏地方经济史》,甘肃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三、大一统时期(公元842~1888年):日趋紧密的政治关系推动货币金融交流进一步深化
吐蕃王朝覆灭后,西藏开始了持续近400年的战乱分裂,此时期中原地区基本处于宋朝统治时期。随后西藏纳入元朝的管辖,元朝设立宣政院正式管理西藏。大一统时期,中原地区的货币流通体系大体经历了初期以铜钱为主,纸钞发行后因滥发导致钞法败坏,到最后货币白银化的过程。金融机构有了较大的发展,其业务从简单的银钱兑换逐步发展到存款放款再到汇款、信贷等活动。当铺、银炉进一步发展,还出现了专门从事汇兑业务的票号。同一时期,西藏以黄金、白银为主要货币,同时使用盐、酥油、青稞、茶叶等作为一般等价物,信用事业开始发展。
(一)两地货币金融交流的主要方式
1.官方朝贡和民间茶马贸易是西藏与中原地区货币金融交流的重要渠道。宋代,西藏割据势力中较为强大的唃厮啰地方政权与宋朝之间经常朝贡,马匹、黄金等输入中原地区,宋朝会回赐熟铜或者铜钱8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五七。并在西藏流通。元代,西藏纳入中央统一管辖后,官方朝贡得到进一步发展,西藏使臣入朝往往会得到元朝回赐的大量财物和货币,且允许他们沿途开市买卖,使得货币在两地之间大量流通。明代,中央政府派遣的入藏使团,每到一处都要代表朝廷“抚谕给赐”,所赐物品有绒锦、纻丝等物。这些赏赐的丝绸不仅发挥使用价值,还作为财富的代表,行使货币职能,在西藏通用。茶马贸易得到进一步的发展,茶充当了流通手段和支付手段的职能。到明代,以商人为中心的民间“私茶”贸易得到了中央政府的支持,从洪武五年(1372年)开始,明廷陆续在川陕各通番关口设置茶马司,负责茶叶和马匹买卖等相关事宜。大量的茶叶、布匹进入西藏后作为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行使货币职能9王晓燕:《明代官营茶马贸易体制的衰落及原因》,《民族研究》2001年第5期。。
2.西藏纳入中央政府管辖后,赈济和财政制度的调整对西藏的金融活动产生了直接影响。元朝政府在特定时期会对西藏的穷苦差民给予赈济,“1292年,命给乌斯藏5驿(差民)各马100,牛200,羊500,皆以银”。“1314年,西番诸驿贫乏,给钞万锭10详参《元史·成宗本纪》,卷十九、卷二十五。”。这些赈济所得成为西藏的流通货币。清代,有多次记载清朝在灾年免除西藏的货币赋税,并以直接拨付银两的方式给予西藏财政支持。
3.中央政府通过汇兑管理和军事活动维持了西藏的金融稳定。金融业务方面,清代为满足驻藏官兵饷银汇兑的金融需求,西藏及周边的金融机构开始出现。雍正至乾隆年间,打箭炉作为支持汉藏贸易金融中介的“锅庄”(职能包括担保赊销预购等),由13家发展为48家,大的“锅庄”经济年收入可达2万两以上11陈崇凯,《西藏地方经济史》,甘肃人民出版社,2008年12月版,第421页。。总体而言,西藏与川边的茶叶贸易存在逆差,这使得西藏的银砖源源不断地流向打箭炉,其中部分被铸成四川藏元,又通过与西藏的贸易或以发给驻藏官兵粮饷的身份进入西藏市场流通,在这一过程中,清廷在西藏发行自铸银币以抵制外币的金融政策得以实现。
军事活动方面,清廷通过反击廓尔喀入侵的斗争,肃清金融市场,推动藏元成为康巴地区的主要流通货币。清初,廓尔喀铸造大量掺入合金的小面值银币流入西藏,谋取暴利12。据统计,自16~18世纪200年的交易中,藏族人民蒙受了数以千万两白银的巨额经济损失。1792年,清廷击败入侵的廓尔喀军队,廓尔喀向清朝称臣,乾隆皇帝下诏禁止尼币在藏地流通。清廷还在藏地设立铸银局,严禁铸币掺假、明确重量和兑换比例,稳定币制,有效地遏制了外国经济势力的掠夺,保护了藏族人民的经济利益。
(二)两地货币金融交流的影响机制
1.大一统前期,政治、军事及经济合作是维持西藏与中原地区货币金融交流的重要保障。从政治军事层面看,宋朝先后与六谷部、唃厮啰部保持了政治军事上的合作。宋朝对六谷部视为“生户”,破例赐给大量弓箭和兵器。湟水流域新兴的唃厮啰部与宋朝始终保持着亲密关系13陈崇凯,《西藏地方经济史》,甘肃人民出版社,2008年12月版,第480页。。从经济层面看,民间的贸易形式主要是茶马互市,朝廷的主要目的还是安抚少数民族14《宋史·外国八·吐蕃传》。。这一过程中,中原商人使用铜钱和绢帛支付马价,茶马贸易成为西藏与中原地区货币金融交流的主要支柱,逐步影响了西藏市场的货币结构15《宋会要·食货》。。
2.元朝时期,西藏结束了长期分裂割据的局面,正式纳入中央政权的管辖之下,较为稳定的政治局面及完整的驿站系统,方便了商贸互通,极大地促进了西藏与中原地区的货币金融交流。从政治层面看,元朝推行帝师制度,稳固地建立起对西藏的统辖,为西藏与中原地区经济金融交流提供了安定的政治环境。此外,按照元朝的制度,在西藏划分万户,共设13个万户,以萨迦为首,形成萨迦地方政权。元朝中央先后在藏族地区设置了三个宣慰使司都元帅府,成为具有双重职能的地方军政机构,在辖区范围内同时管理民政和军务。从经济层面看,元朝在清查户口16藏族简史编写组:《藏族简史》,西藏人民出版社,第144页,2000年版。的基础上,设置完整的驿站系统,驿站设有“甲姆本”(站官),负责督办当地人民赋税差役等,驿站系统的建立使中央和西藏地方紧密地联结起来,极大地促进了西藏与中原地区货币金融交流。此外,元朝先后在定日、聂拉木等地建立了多处商贸市场,民间也出现了不少集市,如乃宁集市、加日郊集市等。
3.明朝以都司武卫制度加强对西藏地方的军政管辖,以“多封众建”的治藏政策分散教派和地方势力的权力,以“厚赏羁糜”制度在加强政治隶属关系的同时,促进西藏与中原地区间货币金融交流。17世纪初,在元明政权更替后,明朝中央对西藏地方的治理采取了三项重要措施:一是将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的都司卫所制度推行于整个涉藏藏族地区,以都司武卫行使地方的军政管理职能;二是打破元朝倚重萨迦派的格局,采取“多封众建,尚用僧徒”的封贡政策,维持西藏政治分散和教派分立的格局;三是推行“厚赏羁糜”的政策,即对于来贡的藏族僧俗官员,明廷往往给予数倍于原物的优厚赏赐。明朝中央对西藏地方的治理政策,极大地提高了西藏各地僧俗领袖遣使入贡的积极性,进一步促进了西藏与中原地区的货币金融交流。
4.清朝大力调整治藏方略,在维持西藏政治安定的前提下,以强化藏汉贸易互通、赏赐、俸禄等形式,促进了西藏与中原地区的货币金融交流。清朝时期,西藏先后经历蒙藏统治者的争权斗争、准噶尔部侵扰等,康熙帝派兵“平准安藏”。此后,为便于管理西藏,清政府着手调整西藏地方管理体制,正式废止第巴制,建立噶伦制。初期委派康济鼐、阿尔布巴和隆布鼐三人为噶伦。1728年,清廷成立驻藏大臣衙门,一直沿袭至清代末年。1751年,清廷授权七世达赖喇嘛管理西藏事务,并成立噶厦政府。此后,清军平定廓尔喀17廓尔喀是尼泊尔的一个山地民族,自18世纪中叶这个民族开始统治了尼泊尔。侵扰,并颁布《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乾隆皇帝下诏颁布新的货币政策,自铸银币,维护了藏族人民的经济利益。
(三)两地货币金融交流对西藏社会发展的影响
大一统时期,中原地区和西藏的货币金融交流,极大地促进了西藏私有制的发展,形成了极具特色的介于奴隶制和封建制之间的庄园制经济,特别是随着中央王朝通过西藏佛教领袖人物来加强对西藏地方管理的格局的形成及延续,促进了西藏政教合一制度的成型。
宋代,茶马互市等贸易引起的黄金等货币的流通,推动了西藏土地私有化的进程和封建庄园经济的建立。9世纪末期,出现了通过黄金货币支付进行的土地自由买卖。随着黄金成为财富贮藏手段,推动了西藏土地私有化和自由交易的发展。
元、明、清时期,西藏的封建农奴制度逐渐获得充分发展,以三大领主为核心的经济结构也完全成型。这一时期西藏与清廷其他地区的商贸往来出现了空前的繁荣局面,形成了四川省的打箭炉、云南省的大理府、甘肃省的西宁府等货币金融交流的主要地点,极大地促进了西藏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
四、半殖民地半封建时期(公元1888~1949年):维护了对西藏的货币主权与经济社会稳定
清末和民国时期,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中国政治经济社会整体处于动荡之中,国内金融市场和机构虽然发展较快,但货币、信用活动都呈现出较为复杂混乱的局面。这一时期,西藏的金融环境趋于复杂,流通的国内货币减少,但种类增多;外国银币在康藏地区流通,中外货币的竞争持续不断,金融状况趋于恶化,但中央政府(清廷和民国政府)通过贸易和金融改革,维护了对西藏的货币主权和藏汉经济金融交流,避免西藏彻底沦为列强的经济附庸和政治傀儡。
(一)两地货币金融交流的主要方式
19世纪末20世纪初,印度卢比银币在英国推动下,成为西藏地区的流通货币。1888年,英军借中印锡金领土争端入侵西藏。1890年和1893年,中英双方先后签订了不平等的《藏印条约》《藏印续约》,清政府被迫开放亚东为商埠口岸,并在5年内免征关税,亚东正式开关时,进出口货物价值还是以白银计算,三年后卢比银币逐步成为计量单位18陶思曾:《川藏游踪汇编-藏輶随记》,四川民族出版社,1985年第1版。,在外国货币入侵的背景下,中央政府在这一时期采取了多种金融措施,维护了西藏地方的金融和货币的稳定。
1.清廷铸造藏洋与印度卢比展开金融斗争,捍卫了对西藏的货币主权。张荫堂就川铸藏元和印度卢比的争夺问题,最早提出了市场贸易多少决定货币价格高低的观点,货币流通市场的争夺实际上就代表着贸易的竞争19吴丰培:《清季筹藏奏稿》第三册,国立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会编,1948年版。。为藏印贸易的巨大利润所引诱,西藏僧俗贵族与外国资本一道垄断藏印贸易,操纵西藏市场,给西藏经济社会稳定和人民生活带来了巨大影响,清廷下决心采取应对外国银币冲击的举措。一是仿照卢比银币自铸藏元20张策刚:《中国康巴地区货币史》,四川出版社巴蜀书社,2013年12月版。。1901年,打箭炉同知刘廷恕首倡“印币亡边”说,认为放任卢比银币流通将严重影响清政府对康藏的统治。1902年,打箭炉地方政府利用运藏饷银,仿照卢比银币铸造三钱二分重的“炉关锲”藏元。清政府用藏元发放边饷,得到打箭炉官兵的欢迎。1902年,“炉关锲”藏元铸造二十余万枚,次年增至八十余万枚仍供不应求。二是强力推动藏元使用。政府规定政府税收、支出均只以藏元收付,如案件诉讼费以藏元缴纳,不得使用卢比。尤其在赵尔丰武力平叛后,藏元逐渐在康藏交界地区推广,宝丰隆银号用藏元经营康藏金融业务,从根本上解决了驻藏官兵饷银的汇兑问题。同时,发行“当十铜元”作为藏元的辅币,极大地便利了当地人的零星交易。三是打击外币和假币流通。如在1910年,清政府驻藏大臣联豫查封了西藏地方官员私设的一家造币厂,阻止其质量低劣的银币扰乱市场。
2.国民政府通过对西藏沙金、羊毛、麝香等尽力收购、发放贷款、扶持川茶等方式稳定金融局势。“康藏沙金产量每年都在万两以上,且全由私商操纵”21行政院经济会议抄送康藏土产应由行政院统制沙金尽量收买之提案(1941年3月8日),国家总动员会议档案:《民国时期西藏及藏区经济开发建设档案选编》,中国藏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6-7页。,货币价值的较大波动严重影响着当地百姓的生活。1941年3月8日行政院专门召开经济会议,决定康藏沙金由政府尽量收买,逐步稳定了当地物价。1946年2月16日,蒙藏委员会在拟定加强西藏与内地金融联系事致行政院呈中决定,拟在拉萨、噶伦堡、康定、玉树、丽江等处设立中央银行分行及其办事处,发行法币及办理放款、汇兑业务,这一举措为货币流通和当地的金融稳定作出了贡献。
(二)两地货币金融交流的影响机制
1.晚清时期,受外国货币入侵影响,西藏与内地各省的货币金融交流遭到一定削弱,但清廷通过贸易及财政金融体制改革,维护了对西藏货币主权的控制及两地货币金融的交流。在经济层面,印度卢比银币曾在康藏流通数十年,数额至少在四千万以上。据估算,英国仅从铸币得到的利润就达四百万两之多22陈一石:《卢比侵淫康藏及其影响》,《中国钱币》1990年第6期。。19世纪末,随着康藏对卢比银币的依赖越来越强,当地白银大幅贬值。“卢比一元,抵换藏币(章卡)四十余枚,以至七八十枚,藏中不能制止”23吴丰培:《赵尔丰川边奏牍》,四川民族出版社,1984年版。。英国商人垄断涉藏地方金融市场,获得高额铸币收益。内地商人将茶叶贩至西藏获得卢比银币,返回内地后需将其熔为银锭或换成内地银元才能再购茶叶,大大影响了贸易效率。而英国商人利用货币之利向西藏大量出口茶叶,1905年,入藏印茶已达入藏川茶总量的一半以上24吕昭义:《英属印度与中国西南边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这些因素导致西藏与内地金融交流的基础受到削弱。
鸦片战争以后,晚清政治越加腐朽,经济越加凋敝,社会矛盾日益尖锐,而西藏历经两次英国侵藏战争,先后签订了多个不平等条约,被迫打开了藏印通商大门。西藏僧俗贵族从藏印贸易中获得了巨大利益,部分西藏贵族对清朝中央政府产生了离心倾向。晚清政府尽力捍卫对西藏的货币主权,如:中央政府或直接在西藏设立宝藏局铸币,或允准四川地方政府铸币,并采取有力措施扩大本币流通,对有效打击外币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维护了西藏与内地的金融交流。
2.民国时期,中央政府先后采用边茶贷款、整顿金融市场和推行金融政策等方式,加强西藏地区同内地各省的经济贸易关系。从政治层面看,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帝制,但西藏的封建农奴制社会并未发生实质性的改变。英国不断扩大对西藏的经济侵扰,加速了西藏经济社会的半殖民地化,特别是在英帝国主义的怂恿唆使下,少数分裂主义分子不断挑起事端,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的关系一度恶化,严重影响西藏地区与内地各省由来已久的正常经济金融交流。
从经济层面看,与内地各省的商业贸易是长期以来西藏地方经济的主要支柱之一,西藏人民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些商品,例如茶叶、粮食、盐、布匹、农具和金属器物等都来自于内地各省。但自清末始,随着帝国主义对西藏经济侵略的加深,印茶、印币大量涌入,冲击西藏市场,西藏地区与内地各省的经济交往受到了严重破坏。民国政府采取多种政策措施,加强西藏地方同内地各省的经济贸易关系。如1935年6月20日财政部长孔祥熙向行政院呈交《财政部为西藏与内地各省通商减免税事》,提出西藏与内地各省通商减免税收的有关规定,得到批准。通过中央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的共同努力,藏汉贸易与货币金融交流得到了一定的恢复和发展。
(三)两地货币金融交流对西藏社会发展的影响
半殖民地半封建时期,英印向西藏倾销日用品、低价大量掠夺西藏工业原料(出超),加之西藏自铸银币数量不足、成色低劣,一段时间内印度卢比大量入侵,据统计,1909~1920年间藏银贬值超过50%。康藏商民在货币支付上处于劣势,使茶叶等贸易受到很大负面影响。部分投资于藏印贸易的藏族贵族财富迅速增长,在西藏地方政权的影响力大增,且政治态度逐渐倾向于英国。中央政府对西藏的管理式微,对西藏与内地各省经济金融交流深度产生了负面影响。
晚清朝廷尽力迎击外币侵藏的挑战,通过自铸货币等手段,维护清王朝和藏族人民的利益。通过发行藏元、整顿币制、筹集资金,一定程度上保证了清廷巩固对康藏的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统治。1916年四川藏元停铸前,总计制造1750万枚,成为康巴地区的主要流通货币,直到1958年才停止流通。尽管未实现把卢比驱逐出西藏的预期目的,但也一定程度上加强了清廷对西藏政治上的主权控制,使开关以后的西藏没有完全沦为列强的经济附庸和政治傀儡25陈崇凯:《西藏地方经济史》,甘肃人民出版社,2008年12月版。。
值得注意的是,半殖民地半封建时期内地各省与西藏地区的金融交流也一定程度促进了西藏经济社会的发展,在西藏产生了某些资本主义萌芽,商业贸易有所发展,但由于中央政府政治上的衰弱,这种交往没有形成大的社会变革,解放前封建农奴主经济在西藏依然占据绝对优势。
五、结语
祖国内地与西藏地方自古以来就通过货物贸易和丝绸之路等途径等开展货币金融交流,历经几千年的变化与动荡从未间断。这种货币金融领域密切的交流蕴含着自身的特点与机理,对西藏地方经济社会等产生过深远的影响。藏汉民族在历史长河中交融共生,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密切关系。
跳出历史往前看,西藏地方与祖国内地货币金融交流的经济社会意义也有了更具体的表达。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到现在70多年来,党中央将国家涉藏政策措施与西藏具体区情紧密结合,实事求是地研究西藏经济金融发展的客观条件、具体困难和实际需要,采取特殊优惠的政策。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改革、开放、搞活经济方针政策指引下,西藏现代金融进入了快速发展的阶段,党中央先后召开七次西藏工作座谈会,赋予西藏一系列特殊优惠的金融政策,开启了全国支援西藏、西藏深刻融入全国市场的新一轮大交往大交流大交融。金融业主动发挥血脉特质,支持西藏实体经济、重点项目和基础设施建设、优化产业结构、脱贫攻坚等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对西藏政治稳定、经济发展和社会和谐发挥了重要作用,真正成为藏汉民族之间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桥梁。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新时代的西藏工作也呈现出新的阶段性特征。2020年,中央召开第七次西藏工作座谈会;2021年,习近平总书记亲临西藏视察并在庆祝西藏和平解放70周年纪念时书赠贺匾“建设美丽幸福西藏 共圆伟大复兴梦想”,充分彰显了西藏工作在党和国家工作全局中的重要战略地位。面对新形势新任务,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进一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持续深化西藏与区外各省市的交往交流交融,推动建立相互嵌入的金融环境,充分发挥金融力量提升发展质量,为促进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建构作出应有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