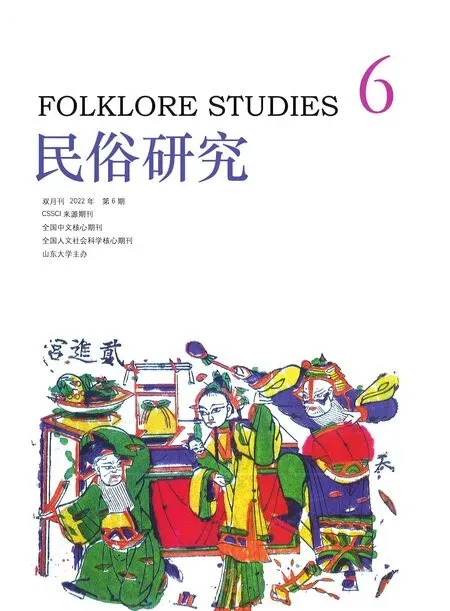在解构与重构之间:农业遗产与工业文明交互中的文化认同困境
陈加晋 卢 勇
古往今来,遗产与认同总是相关联的,因为其不仅是人类先祖在生产生活中创造与传续给后代的遗留物,更是承载族群内部成员亲缘纽带、集体记忆与情感寄托的载体。中国自古以农立国,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念兹在兹的“中华文明植根于农耕文明”(1)习近平:《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论坚持全面深化改革》,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年,第406页。,包括社稷、宗庙、家国、道义、礼法等中华文明之叙事框架无不以农耕文明为根柢。古语所云“礼莫初于宗,惟农为初有宗”(2)龚自珍:《龚自珍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49页。“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3)司马迁:《史记》卷六十二《管晏列传》,中华书局,1959年,第2132页。等,亦道尽古人视农业为文化之源的深刻认知。更重要的是,即便栉风沐雨数千载之后,中华文明的农业底色与农耕本色也从未改变。费孝通指出:“任何一个游牧民族只要进入平原,落入精耕细作的农业社会里,迟早就会服服帖帖地、主动地融入汉族之中。”(4)费孝通:《费孝通全集》(第十三卷),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42页。可以说,传统农业是形成集体表述最早、历史记忆最久远与最能代表国家与民族性认同的文化类型。遗憾的是,当农耕文明与农业文化在当代主要以“农业遗产”作为存在形式与叙事方式时,其文化认同的话语实践及相关研究却是整个中华遗产序列中最为薄弱的。王思明指出,“文化如果没有社会认同和传承就没有意义”(5)王思明:《农业文化遗产的内涵及保护中应注意把握的八组关系》,《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2期。。李畅提出,通过“社区增权”可以强化农业文化认同和参与积极性。(6)参见李畅:《后农耕时代农业文化遗产的认知与保护》,《中国园林》2018年第8期。张颖发现,农业遗产主体失位会导致遗产归属与认同关系产生断裂。(7)参见张颖:《耕读传家:论乡村振兴战略中农业遗产保护活化的文化逻辑》,《贵州社会科学》2019年第5期。徐业鑫系统阐释了农业遗产文化认同载体的记忆价值与现实困境。(8)参见徐业鑫:《文化失忆与重建:基于社会记忆视角的农业文化遗产价值挖掘与保护传承》,《中国农史》2021年第2期。此外,亦有个别学者就农业遗产文化认同进行个案分析。(9)参见屈册、张朝枝:《元阳梯田原住民的遗产认同:基于话语分析的视角》,《旅游学刊》2016年第7期。
亨廷顿在提出“文化认同”概念时,就已将其重要意义表达得十分清楚,“文化认同,尤其是对外来文化价值的认同,足以瓦解一国的政治制度”,“文化认同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是最有意义的东西”。(10)[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等译,新华出版社,2010年,第128页。国内早期的相关研究主要限于政治文化领域(11)参见麻国庆:《全球化:文化的生产与文化认同——族群、地方社会与跨国文化圈》,《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4期;周大鸣:《澳门人的来源与文化认同》,《广西民族研究》2000年第2期;刘存宽:《香港回归与文化认同》,《河北学刊》1998年第2期;董淮平:《李光耀在新加坡现代化初期的文化认同》,《求是学刊》1998年第1期。,不过很快就被引入到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讨论之中。2003年“认同感和历史感”被写入联合国《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国际公约》,其后彭兆荣、高小康等学者阐释了非遗与认同的内在关联。(12)参见彭兆荣:《人类遗产与家园生态》,《思想战线》2005年第6期;高小康:《非物质遗产与文学中的文化认同》,《文艺争鸣》2007年第3期。时至今日,学界不仅形成“非物质文化遗产空间保护的基础是广泛的文化认同”(13)季中扬:《非物质文化遗产空间保护与文化认同困境》,《江苏社会科学》2013年第5期。等基本共识,更是将文化认同视作主要议题之一。包括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内的诸多遗产类型皆从农业遗产中衍生而出(14)参见乌丙安、孙庆忠:《农业文化研究与农业文化遗产保护——乌丙安教授访谈录》,《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1期。,在农业遗产保护与话语实践远不如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情况下,农业遗产文化认同面临的问题最为突出。有鉴于此,笔者尝试将“工业文明”作为叙事背景与观照对象,探讨农业遗产与工业文明交互下文化认同困境的生成原理、演进逻辑等问题。
一、失语:工业文明解构作用下的农业遗产文化认同
布莱克曾指出,人类历史上能够同现代化运动相提并论的社会变革只有两次,一次是人类的诞生,另一次是文明的出现,而工业革命以来的全球现代化是人类第三次伟大的变革。(15)Cyril Edwin Black, Dynamics of Modernization: A Study in Comparative History.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1966.转引自孙立平:《社会现代化》,华夏出版社,1988年,第6页。在工业革命与现代文明到来之前,农业无疑是塑造人类社会的逻辑原点,乡村中的知识、技能的传承被视作最基本、最普遍的社会传承。中华农耕文明垂万年而不衰,以“天人合一”为哲学指导、“精耕细作”为基本原则、“农牧复合”为主要特征的传统农耕体系(16)参见王思明、卢勇:《中国的农业遗产研究:进展与变化》,《中国农史》2010年第1期。不仅赋予了中华文明重要特征,更是中华文明之所以绵延不断、长盛不衰的主要原因。无论是“耕读传家”的个人理想,还是“农为邦本”的治国方略,无不体现出我国古代社会对于农耕文明与农业文化的深刻认同。
作为传统区域农业经济—生态—文化—社会的复合体(17)参见闵庆文、张丹等:《中国农业文化遗产研究与保护实践的主要进展》,《资源科学》2011年第6期。,农业遗产既是农民的生产方式与生产场所,也是农民的生活方式与生活空间。前者构成了农民的立业之本,后者构成了农民的立命之根。因此,从认同主体看,首先且最重要的应是农民对于遗产,也就是其世代“生于斯、长于斯”的社会空间与物质文化体系的认同。一旦原本的生产体系被替代或者物质空间被置换,那么农业遗产就在第一时间失去了认同的物质基础与所指对象。西方的“We Are What We Eat”与中国的“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在内涵上大致相当(18)参见曾雄生:《食物的阶级性——以稻米与中国北方人的生活为例》,《中国农史》2016年第1期。,正是集体性农业生产需求与劳动场景的形成,才有地域性的农村聚落与传承性的农民职业,进而才能在诸如“面对面的社群”“地方知识体系”等空间或载体中形成特定的记忆与表述,并萌生出由农民到大众的文化认同感。试想一下,如果没有哈尼族先民在梯田上世代耕作的实践与知识积累,那么记录梯田耕作程序与技术的哈尼民歌《四季生产调》必然不会出现(19)参见邵晓飞:《论中国各民族农业文化遗产对水资源温度差异的调控成效与创新》,《中国农史》2020年第4期。,相关的民俗禁忌、仪式庆典等文化认同的符号也会失去存续的意义。
值得注意的是,工业对于农业遗产的解构恰恰从最基本的物质空间与生产体系开始。马克思指出:“工业的历史和工业的已经生成的对象性的存在,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20)[德]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57页。作为迄今为止最富活力和创造性的生产力量,工业不仅为中国增加了一项新兴产业,而且快速代替农业成为整个国家、社会的新的底层逻辑与基本法则。短短百年里,中国最普遍与最稳定的乡村社会形态迅速崩解(21)参见麻国庆:《乡村振兴中文化主体性的多重面向》,《求索》2019年第2期。,而且几乎没有村落能够置身事外,成为工业浪潮中的“飞地”。在农业生产区,农家世代选育之种转变为由生物科技创制出的良种,人力、畜力生产转变为机器生产,农家肥改为化肥;在农业生活区,民居建筑用材从木、石改换为水泥、砂浆,生活用品从竹、木、铁制变为塑料、钢制等。可以说,从农业到农村、农民,从生产到生活、生态等各个方面与要素都不同程度地被摧毁、置换或替代,乡村原本的统一性与整体性被肢解得支离破碎(22)参见李明、王思明:《多维度视角下的农业文化遗产价值构成研究,《中国农史》2015年第2期。,农业成为单纯粮食供给的“空间生产”,农民则转变成工业型农业的生产者,并失去了原本的立业基础。
对于农民来说,失去家园与精神的“立命之根”可能比失去“立业之本”所带来的伤害性更大。职业可以选择或更换,更何况农业工业化使生产规模和效率产生质变,农民食物来源与家庭收入都实现了跃升,但可惜的是,工业文明无法给予一套与之相匹配的上层建筑、思想观念、道德伦理及乡风民俗。温铁军曾判断,“中国属于典型的东亚小农经济的经济基础,如果我们超前引入现代上层建筑,其结果就是不可维持”(23)温铁军:《农村上层建筑》,红色文化网,http://www.hswh.org.cn/wzzx/llyd/sn/2013-05-02/12890.html,发表时间:2013年5月2日;浏览时间:2021年11月23日。,其原因在于:无论是广义的传统乡土社会,还是狭义的农业遗产,都不单具有物质生产和生计保障功能,还容纳了复杂而固化的文化价值、生活意义、记忆属性等内容。(24)参见卢勇:《引进与重构:全球农业文化遗产“日本佐渡岛朱鹮—稻田共生系统”的经验与启示》,《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2期。遗产地农民不仅世代“生于斯、死于斯”(25)费孝通:《乡土中国》,北京出版社,2005年,第7页。,而且在集体性聚居、劳作、互动中缔结了亲密而稳定的亲缘、地缘和业缘关系,乡村社会由此成为一个充满集体记忆的文化空间,即哈布瓦赫所说的“特定社会群体之成员共享往事的过程和结果”(26)[法]莫里斯·哈布瓦赫:《论集体记忆》,毕然、郭金华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40页。。正是基于共同的文化记忆,农业遗产空间内的个体与个体、个体与集体之间才能产生意义关联的情感纽带(27)参见王子涵:《结构与过程:集体记忆视域下民俗的能动性探源》,《民俗研究》2019年第6期。,农民得以萌生出对于集体的忠诚感、归属感与认同感。由此来看,农业遗产作为乡村社会记忆的符号特征越明显,其被工业解构后的文化认同危机就越严重。正如孙庆忠所言,“如果农民的身体跑了,但精神尚在,那么乡村就不算破败;一旦农民的魂被带走了,乡村就彻底破败了”(28)孙庆忠:《文化失忆:乡土中国的现实处境》,《中国乡村发现》2018年第2期。,当农业遗产失去了族群性表述与谱系性记忆的部分,农民就失去了区别于“他者”的身份标识和区别于“他群”的精神家园。
基于多年实地调研经验,笔者认为农业遗产被工业文明解构后的文化认同困境至少有以下四个表征:
首先,农民对自身文化自卑。当地农民面临工业文化侵入时,第一反应不是在“他者”的镜像中重新审视和确认自我,而是在巨大反差中觉出文化等级,继而降低自我身份、否定自我价值。面对外来的官员或专家,即便在当地颇具名望的族老或乡贤,也常表现得谦卑和缺乏自信。诸如在遗产申报等关乎其切身利益的遗产实践过程中,他们会主动或默认放弃遗产的阐释权和话语权,转而退化为单一的资讯或线索提供方。
其次,农民从农村土地逃离。这是最为大众所见的社会现象。据国家统计局《2020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全国农民工总量为2.856亿(29)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中华人民共和国2020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国家统计局网站,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2102/t20210227_1814154.html,发表时间:2021年2月28日;浏览时间:2022年1月3日。,换言之,我国有超过四成的农民选择离开故土。曾经令人向往的归园田居成为当地人避之的“囚笼”,农村“空巢”问题越发严重。贾平凹在《秦腔》中所问“难道棣花街上我的亲人、熟人就这么很快地要消失吗?这条老街很快就要消失吗?土地也从此要消失吗”(30)贾平凹:《秦腔》,安徽文艺出版社,2010年,第496页。,反映出我国知识分子对农村“空巢化”现象的忧虑。
再次,与农民脱离土地密切关联的是其对自身身份的抛弃。如果说农民工群体的大量出现反映了农民对于自身身份半脱离的话,那么年轻人主动阻隔代际交流(31)参见徐业鑫:《文化失忆与重建:基于社会记忆视角的农业文化遗产价值挖掘与保护传承》,《中国农史》2021年第2期。、拒绝提取记忆就是对“农民这张皮”的真正抛弃。当下,几乎已没有年轻人愿意留在乡村(哪怕是世界级农业遗产地),他们通过考学或工作彻底退出了乡村生活。得不到年轻人的认同与接续,遗产地“绵延的社区史”(32)[美]保罗·康纳顿:《社会如何记忆》,纳日碧力戈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4-14页。难以为继,遗产的叙事与传承机制很可能彻底终结在这一代人的身心之中。
最后,乡村道德秩序败坏。如果农业遗产缺失了文化认同的记忆载体,那么就会失去“对个体的约束和关系网络的控制”(33)[法]莫里斯·哈布瓦赫:《论集体记忆》,毕然、郭金华译,上海人民出版,2002年,第33页。能力,乡村社会也就不同程度地出现道德崩解和伦理失范的情况。据张灿强调查,留守农村的农民最主要的文娱活动是看电视和打牌(34)参见张灿强、龙文军:《农耕文化遗产的保护困境与传承路径》,《中国农史》2020年第4期。,其余人情淡薄、聚众赌博等现象也十分突出。在道德崩坏之下,契约关系变成农民最能接受的关系。(35)参见麻国庆:《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的表达与文化的文法》,《学术研究》2011年第5期。
当下,不少人类学、民族学家抱以一种“丧失式叙述”的口吻来回望并总结这段社会变革的事实与文化变迁的过程(36)参见[日]太田好信:《文化の客体化——観光をとおした文化とアイデンティティの創造》,《民族学研究》57巻4号,1993年,第386页。,以至于守望乡土、复建传统俨然成为了一种学术“正确”。但在历史发生之前与进行阶段,农业遗产的文化认同却一直处于“失语”状态。诚如季中扬所指,“在启蒙现代性话语体系中,乡土文化认同往往被认为是保守的、怀旧的,甚至是反现代性的”(37)季中扬:《乡土文化认同危机与现代性焦虑》,《求索》2012年第4期。,特别是自“五四运动”至20世纪90年代前的主流叙事,都将工业与农业、现代与传统、城市与乡村看作截然不同且互斥、对立的文明阵营:前者被定义为先进、精英,后者则被定义为落后、粗鄙,无论是政府还是大众都乐见甚至积极推动乡村文化的边缘化直至淘汰,并视之为时代进步的手段。尽管乡土文化的现代性问题已经发生并持续恶化,但从官方话语到大众文化叙事都被有意或无意地遮蔽(38)参见季中扬:《乡村文化与现代性》,《江苏社会科学》2012年第3期。,就连以农业遗产研究为业的学术界一度都有过争议,据李根蟠回忆:改革开放初期,有人认为“精耕细作以后不要提了”,甚至提出“单一小农经济结构是我国长期动乱贫穷的病根”(39)李根蟠:《农史学科发展与“农业遗产”概念的演进》,《中国农史》2011年第3期。,尽管之后争论平息,但足见当时整个社会对于传统农业的偏见。
总之,当农业遗产作为传统乡土社会的遗蜕被放置在与工业文明尖锐对立的宏大叙事框架中去认知并叙述的时候,那么涉及农业遗产的系列问题就会被漠视,甚至被想象成现代化进程中需要清扫的障碍,文化认同失语也就成为必然。在几乎全民都享受着工业化的福利时,似乎唯有农民在默默承担着变革中的“阵痛”,他们虽很少抱怨,甚至对于自身的文化变迁表示漠然,但依然朴素地表达着对“家园衰败”的不满。对此,方李莉感慨道:“在彻底失语的状态下,他们根本不会看得起自己的文化,更不会去珍惜自己的文化。他们所希望做的一切就是如何去挣脱这一传统文化的枷锁。”(40)方李莉:《警惕潜在的文化殖民趋势——生态博物馆理念所面临的挑战》,《民族艺术》2005年第3期。
二、失真:工业文明重构作用下的农业遗产文化认同
尽管农业遗产的文化认同失语是时代难题,但我们首先得承认,恰恰是工业与现代主义的主流化赋予了农业遗产话语的实践空间,或者更具体一点说,农业遗产的文化主体与文化认同实质上是现代性的产物。白瑞斯指出:“正是由于现代化的工业文明导致了传统日常生活方式的急遽消失和文化全球化的加剧,人们才意识到了保护文化多样性的紧迫性和必要性。”(41)白瑞斯、王霄冰:《德国文化遗产保护的政策、理念与法规》,《文化遗产》2013年第3期。同样地,只有在工业文明语境下,农业遗产方具备稀缺性与不可再生性,尤其当人们不得不面对新旧文化的冲突性选择时(42)参见赵世林、田婧:《主客位语境下的民族文化遗产保护》,《云南社会科学》2008年第1期。,文化认同才得以在与工业文明的比较中作为一种自觉的文化意识真正萌发,并随着农业遗产的不断小众化而被赋予越来越珍贵的现实意义。
事实上,我国农业遗产事业的确是沿循上述逻辑而发展至今,特别是自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工业化为国民创造了相对富足的物质条件,但工业思维指导下的石油化学型农业却不断遭遇现代性困境,传统农耕文明中的“可持续”因子因此率先得到了再发现与价值重估(43)参见李根蟠:《农史学科发展与“农业遗产”概念的演进》,《中国农史》2011年第3期。,我国从“走出传统”迈入“发现传统”阶段。到21世纪初,以联合国粮农组织“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计划的开展为标志,我国涉农遗产纷纷“经典化”(44)李倩、管宁:《文化遗产:经典化、保护经验与中国智慧——网络时代文化遗产的历史命运》,《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6期。:一大批遗产资源被认定为“全球/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从而由区域认同的农业文化共同体荣升为受国家乃至世界认可的文化典范。方兴未艾的农业遗产运动无疑破解了文化认同失语之困境,诸如伽红凯发现的兴化垛田“反迁移”现象(45)参见伽红凯、王思明:《非均衡发展:农业文化遗产地的反迁移效应》,《中国农史》2020年第1期。、任洪昌分析的福州茉莉花与茶文化系统遗产地市民在认同维度中的得分均高于外来居民(46)参见任洪昌、林贤彪等:《地方认同视角下居民对农业文化遗产认知及保护态度——以福州茉莉花与茶文化系统为例》,《生态学报》2015年第20期。,都不同程度地反映出遗产地居民认同感与文化自信的提升。但遗憾的是,这场实践活动的主导或主力一直都不是作为遗产创造者、拥有者与使用者的农民,而是政府、学者以及大众消费者。换言之,从挖掘到管理、从区域认同到国家认可等几乎所有农业遗产的过程与环节,都是由“他者”所阐释、赋权及推动的。在农民缺位与“他者凝视”之下,农业遗产必然遭遇重构、加工及改造。
就作为主导与管理者的政府而言,其部分立场与农业遗产整体利益是一致的,但其施政重点具有动态性与阶段性。从面上看,政府在过去20年里更关注的是农业遗产的“生产”“生态”,而非“生活”或“文化”价值的拓展(47)参见陈加晋、卢勇、李立:《美学发现与价值重塑:农业文化遗产的审美转向》,《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5期。。笔者在调研过程中也发现政府官员往往最为乐道的是本地农业遗产所创造的经济效益。这不仅弱化了遗产的文化属性,更容易出现引导偏差。而且,政府(尤其是中央政府)一般会从更高站位、更宏观视域和更长远利益的角度来看待农业遗产,例如在第六批“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认定工作中,农业农村部的目标导向是“传承优秀传统文化和促进乡村文化振兴”(48)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农村社会事业促进司:《第六批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发掘认定工作启动》,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网站,http://www.shsys.moa.gov.cn/gzdt/202012/t20201214_6358070.htm,发布时间:2020年12月14日;浏览时间:2021年12月15日。,这实际上与遗产地农民最为迫切的精神需求是有一定距离的。更重要的是,由于政府具备强大的权力集中与资源整合能力,因此可以根据需要随时从中遴选出代表性的部分加以宣扬和利用。(49)参见仝艳锋:《“他者”视野下乡村文化遗产的价值发掘》,《文化艺术研究》2019年第4期。
相比而言,作为遗产权威解释者的学者立场似乎更客观,但学者乃至某一学科与遗产的具体实践操作之间的关系度其实是很微弱的(50)参见卫才华:《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民俗学》,《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4期。,而且同样摆脱不了“他者”的身份。清水昭俊曾对人类学家的遗产调查活动做过总结:“他们将调查对象的社会和文化与外界对它们的影响,分别作为不同的东西加以分析性地区分。”(51)[日]清水昭俊:《永遠の未開文化と周辺民族——西欧近代人類学史点描》,《国立民族学博物館研究報告》17巻3号,1993年,第428-429页。由此出发,许多人类学家在实地调查基础上写成的民族志都会遵循这样的模式:因没有亲历过去与受外部影响,故只能在“接触后发生变化”的范畴内加以描述(52)参见刘正爱:《谁的文化,谁的认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运动中的认知困境与理性回归》,《民俗研究》2013年第1期。,并以此为基础描绘出他们“想象中认为合理”的传统社会文化图像。这难免不会引起文化的失真。
有赖于工业化叠加科技化、城市化、市场化的快速发展,大众消费群体通过输出消费力成为农业遗产体系内一支重要力量,特别是长期居住在城市空间的消费者们怀揣“乡愁”和对家园的眷恋,出于对遗产强烈的情感需求与文化认同而发起消费行为(53)参见张朝枝、朱敏敏:《文化和旅游融合:多层次关系内涵、挑战与践行路径》,《旅游学刊》2020年第3期。,这一点在集合了农商、农艺、农旅等多重效应的“遗产旅游”上体现得最为鲜明,遗产旅游也得以被民俗学家认为在本质上是一种认同性经济。(54)参见傅才武:《论文化和旅游融合的内在逻辑》,《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2期;程鹏:《旅游民俗学视野下遗产旅游民俗叙事研究》,《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4期。另一方面,旅游化又是农业遗产文化重构最严重、记忆篡改最复杂的场域。因为与政府、学者等其他“他者”群体相比,消费者对遗产地农民的影响更大。他们不仅拥有庞大的基数,而且具备消费支付及与村民频繁接触而形成的强大话语力。对此,约翰·厄里提出:“作为旅游主体的外来者与作为旅游客体的当地人之间是一种权力关系,后者则处于被前者所示范与影响的位置。”(55)[英]约翰·厄里、[丹麦]乔纳斯·拉森:《游客的凝视》,黄宛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第4-5页。在以游客口味而非农民内心所向为文化准绳的消费空间内,游客所追逐的真实体验是一种“伪真实”(56)Dean MacCannell, “Staged Authenticity: Arrangements of Social Space in Tourist Setting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ume79, Issue3, 1973, pp.589-603.,不符合地域文化的内在生产逻辑。
可见,无论是政府、学者还是大众消费者,他们对于农业遗产都有各自的立场、利益需求和价值判断,其中包含着一种强势的权力与话语关系。(57)Laurajane Smith, Uses of Heritage. Abing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6, p.11.以农业遗产为现实场域,每个“他者”群体都在相互博弈与协商中,共同影响着农业遗产文化主体的失真程度及其走向。归纳起来,其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文化叙事的精英化。农业遗产体系内大多数的叙事文本并没有正式的记载与留存,它之所以能够不断传承乃至发扬光大,主要依靠父子相传与口口相授。可以说,每一个村民都是知识的创造者与文化的传播者。然而,当下遗产文本的讲述者变成了以学者为核心的精英群体(58)参见徐业鑫:《文化失忆与重建:基于社会记忆视角的农业文化遗产价值挖掘与保护传承》,《中国农史》2021年第2期。,流传在农民群体间的生产知识与生活故事则变成呈现在程式化的书本或媒体上的文化知识。知识分子对遗产叙事的话语垄断,不仅容易造成文化传播问题,而且还会涉及文化本土化和生命力问题。因为现通行于精英群体的主流遗产叙事大多都源于西方,话语主导也在西方,这在世界级农业遗产的申报文本上体现得十分明显。此外,经村民世代创造与集体加工后的遗产叙事会呈现出极大的创造性与变异性(59)参见[英]杰克·古迪:《神话、仪式与口述》,李源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3页。,而精英创造的文化叙事缺乏这样的活力和生命力。
其次是文化内容的同质化。大多数消费者的认知与选择是零碎且浅层的,本质上处于一种“符号消费”阶段,即基于那些看似代表性实则指示性的符号来吸引其产生消费动机。(60)参见杨利慧:《遗产旅游:民俗学的视角与实践》,《民俗研究》2014年第1期。同时,受制于大众消费者庞大的群体基数特性,遗产的主体文化在扁平化的同时还趋于同质化,即在内容上完全以大众欣赏取向为主,在价值观上也呈现一种中立化趋势(61)参见麻国庆:《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的表达与文化的文法》,《学术研究》2011年第5期。,这样才能被作为最大公约数的游客认可并接受。高度扁平与同质的文化内容不仅消解了乡土文化丰富的内涵,而且脱离了原有的农业生产与乡村生活,无法反映和代表真实的遗产地社会面貌。
与之类似的是文化仪式的舞台化。文化仪式作为一种受规则支配的象征性活动往往承载着遗产地人民特殊的情感与美好的期望。保罗·康纳顿认为:基于内蕴的规则、情感与神圣感,仪式能够得以渗透到非仪式性活动中,从而“把价值与意义赋予那些操演者的全部生活”。(62)[美]保罗·康纳顿:《社会如何记忆》,纳日碧力戈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50页。对于遗产地农民来说,举行仪式是其文化建构与认同提升的重要方式;但对于游客来说,遗产地仪式所展现出的特色与生动表现力却是富有吸引力的“旅游资源”。在“游客的凝视”中,农业文化仪式被搬上舞台定期展演,村民的认同载体成了满足游客的工具(63)参见陈志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客体化与乡村振兴》,《文化遗产》2019年第3期。,丧失了思想、情感与意义的仪式退化为农民日常可有可无的“空壳”。
最后是文化审美的雅致化。农业文化遗产的审美性同样是农民集体劳动实践的产物,其审美经验原本并不是审美对象自身的独特性与艺术性,而是来自农民对审美对象的文化认同(64)参见陈加晋、卢勇、李立:《美学发现与价值重塑:农业文化遗产的审美转向》,《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5期。,所以也就不难理解乡村与城市空间之间十分迥异的美学风格,但在城市化浪潮与精英思维的冲击下,遗产文化审美自发趋向精致化,尤其表现在农产品越做越精致、民居越建越奢雅等方面。这些做法的结果是:既得不到城市群体的青睐,又失去了农民自身的认可。
概言之,当农业遗产事业在经历数十年发展而成为现代文明所缔造的权力之间的一种博弈和实践对象后,现代性权力强势介入,农民难以真正成为“发声”的主体,由此必然造成农业遗产文化认同的失真。实际上,失真本身并不意味着危机或困境,因为无论是当下还是前工业时代都不存在绝对“原真性”文化,变迁与自愈是文化的常态与规律。(65)Jonathan Friedman, Culture Identity and Global Process. London: Sage Publication, 1994, p.45.真正让人忧虑的是:在这种“他者”所操控的语境下,农业遗产从其存续的生产生活场景中“脱嵌”并表现出一种“失调性”(66)张举文:《非物质文化遗产与中国文化的自愈机制》,《民俗研究》2018年第1期。;农民“失权”后,不再具有与农业遗产建立关系的内生动力与能力。(67)参见孙九霞、周一:《遗产旅游地居民的地方认同——“碉乡”符号、记忆与空间》,《地理研究》2015年第12期。这些严重影响到农业遗产的文化记忆修复和认同构建。
三、重建农业遗产文化认同之难:谁来认同与认同什么
无论是农业遗产的文化认同失语抑或失真现象,都是工业发展与农业现代化的代价之一。(68)参见徐业鑫:《文化失忆与重建:基于社会记忆视角的农业文化遗产价值挖掘与保护传承》,《中国农史》2021年第2期。出于对工业与农业文明关系的反思与重新定位,重建或重塑文化认同似乎成为大多数学人心中的必然路径。有学者指出:“文化再生产的不可避免性,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民族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转型中必然要经历建构—解构—重构—再建构的过程。”(69)王庆贺、韩斌:《黔东南苗族“刻道”的节日化建构及其实践逻辑》,《民族论坛》2021年第3期。除去文化的内在机理,即便从已有的实践经验(如遗产旅游)也能证明,作为一种集体意识(70)参见宋峰、熊忻恺:《国家遗产·集体记忆·文化认同》,《中国园林》2012年第11期。的遗产文化认同确实是可以被构建的,不然就无法解释文化认同的“失真”现象。但是,对于从哪着手、构建什么、如何构建等问题,学界论说纷纭,莫衷一是。这也是目前农业遗产的文化议题大多停留在文本与话语阶段,而鲜有真正能操作、可落地的范式或路径的原因所在。由此来看,农业遗产的文化认同困境不仅表现在“已发生”的现实情境里,同时还表现在“难解决”的重建路径中。
首先,从发生主体即“谁来认同”来看,农业遗产的认同主体比较容易辨别和区分,政府、学者、农民及大众消费者层面,实际上也与宏观层面的农业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等保护主体(71)参见韩成艳:《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主体与保护主体之解析》,《民俗研究》2020年第3期。相一致。他们虽各自拥有不同的文化选项与认同选择,但毫无疑问,其中最重要的主体是农民。诚如马克思通过“实践”概念来表达对人作为主体的肯定,农业遗产最主要的实践主体就是农民,没有农民的生产创造与生活场景,农业遗产所代表的乡村空间就只能是一处“空壳”或“遗迹”,故重建农业遗产文化认同最为重要的尺度与标准应该是“农民认同”。对此,政府与学界皆高度认可。比如2021年10月农业农村部国际交流服务中心副主任蔺惠芳就明确指出:“遗产地保护利用要摒弃急功近利的短视心态……帮助农民真正认识到守护农业遗产的重要意义和价值,增强认同感、参与感。”(72)彭瑶:《在农业文化遗产中汲取乡村振兴的力量》,《农民日报》2021年10月10日。
增强“农民认同”的难点在于具体如何实施。农民群体虽先天拥有农业遗产最合理合法的“叙事权”,但自身不具备对之进行阐释的自知性、自觉性与自主性,加之缺乏知识、资本及组织支持,因此在现实中很难有效“发声”,更难以真正参与利益分配与话语表达。尹凯总结道:“每一个从资源到遗产的过程都不可避免地意味着物件、地方与实践在所有权、话语权、阐释权上的全面分离。”(73)尹凯:《遗产过程的两分路径:“成为遗产”和“成为遗产之后”》,《云南社会科学》2020年第1期。农业遗产在事实上已成为除农民以外的多重主体共谋共享的事业:政府借助社会赋予的公共权力成为农业遗产的政策制定者与方向引导者;学者通过知识创造与资政权力成为农业遗产的解释者与赋权者;社会大众则拥有强大资本与文化消费力。相比之下,农民似乎只是从“工业型”农业的生产者转变为“遗产型”农业的生产者。不同阶层或背景的群体表面上在合力做同一件事,但因各自立场或阵营的利益、职能和目标不同,故在遗产实践中会自然地将农业遗产的价值引到符合自己需求的方向上去(74)参见魏爱棠、彭兆荣:《遗产运动中的政治与认同》,《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5期。,比如产业和消费,甚至产生制造遗产赝品的热情(75)Uzzell, D.L.(ed.), Introduction: The Natural and Built Environment. London and New York: Belhaven Press, 1989, p.3.。霍尔指出,在涉及到“遗产故事由谁来讲”一类核心问题时,“背后是知识与权力的协商”(76)Stuart Hall, “Whose heritage? Un-settling ‘the heritage ’re-imagining the post-nation”, Third Text,vol.49, no.13, 1999, pp.3-13.,显然农民不在协商范畴之内,甚至可能不在关注范畴内,因为与“遗产地农民”相比,社会各界真正关注的其实是“遗产”。对此,有不少知识分子基于科学态度与情怀持续发声,如孙庆忠就直言不讳道:“保护不是农业农村部的保护、不是地方政府官员的保护,而是泥河沟老百姓自己的保护。”(77)孙庆忠:《并轨:扎根乡村的田野工作与促进变革的行动研究》,《民俗研究》2021年第6期。尽管如此,学者作为个体对实践与行动层面的影响有限,那些真正广泛直面农民的“多重凝视”却基于立场与利益很难将农民视作对等的主体。一些看似在遗产转化与利用方面做得较好的范例,深究起来也都不同程度地“缺乏对当地农民队伍的有效呵护”(78)顾军、苑利:《我国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存在的问题与反思》,《贵州社会科学》2021年第9期。。
提升农民的“文化自觉”似乎可以成为破局的“钥匙”。文化自觉,即费孝通所言之“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79)费孝通:《论人类学与文化自觉》,华夏出版社,2004年,第188页。,但诚如前揭,绝大多数的农民对自己的文化缺乏全面认知,因此还是得靠政府与专家学者的介入与引导。这难免再度陷入“他者”与“我者”关系的悖论中。目前来看,有少数脱蜕于民俗学或人类学的农业遗产学人通过长期驻村与乡村教育让我们看到了某种希望与可能(80)参见以孙庆忠为代表的学者工作,孙庆忠:《并轨:扎根乡村的田野工作与促进变革的行动研究》,《民俗研究》2021年第6期;《田野工作与促进生命变革的乡村研究》,《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3期;《田野工作的信念与真情》,《民俗研究》2017年第5期;《佳县泥河沟村 以农业遗产保护延续“枣缘社会”》,《世界遗产》2015年第11期。,但是这种方式往往需要一个先行的前提或并行的条件:发现并构建农民的集体记忆,也就是前述费孝通所指农民应“生活在一定文化中”。有很多学者建议或呼吁建立博物馆、村史馆、陈列馆等保存与展示文化遗产的设施或场所(81)参见张灿强、龙文军:《农耕文化遗产的保护困境与传承路径》,《中国农史》2020年第4期。,在笔者看来,这实质上是指向文化记忆场域的构建。从文化认同到集体记忆,实际是一体两面的问题,没有记忆,就没有认同,或者说没有文化记忆,文化认同就无法解释。(82)参见季中扬、高鹏程:《“非遗”保护与区域文化认同》,《文化遗产》2021年第3期。由此来看,从某种程度上说,我们又回到了原点。
其次,就认同的对象即“认同什么”而言,如果把农业遗产的集体记忆与文化认同看作“因应”“表征”及“载体”的关系,那么可以说,以遗产地集体记忆为核心的文化形态就是农业遗产领域最主要的认同对象。史密斯认为,遗产是一个与记忆行为建立密切关系的文化过程(83)Laurajane Smith, Use of Heritage. Abing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6, p.44.,但遗产话语的出现本身就意味着文化“失忆”现象的产生,而失忆的根本原因是农业文明被纳入到工业文明体系与现代叙事框架之内。一旦我们言及集体记忆与文化认同的“重塑”“复建”“复兴”等话题,某种意义上就包含着对于现代文明的抵抗和对传统的回归(84)参见王杰文:《“遗产化”与后现代生活世界——基于民俗学立场的批判与反思》,《民俗研究》2016年第4期。,因此,我们需审慎处理现代性背景下重建农业遗产文化认同的“限度”问题。
在工业化高度成熟的“后工业社会”阶段,任何涉及前工业时代的实践活动,都必须以“工业文明”这个人类社会当下最大也是最基本的事实为前提,并以符合现代性演进逻辑、融入现代发展潮流为目标,否则只能面临淘汰。农业遗产的源头是基于传统农业文明的生产实践,也就是以家庭为单位,完全或主要依靠人力畜力,并以满足自身消费需求为主的小农经济(85)参见张芳、王思明主编:《中国农业科技史》,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出版社,2011年,第342-343页。,其本身就是与工业文明相异甚至相斥的。如果我们贸然对其进行现代化改造,那么农业遗产作为“遗产”的最重要的内核事实上便不复存在。我们很难想象会有这样的场景:农业遗产地农民一边驾驶着大型收割机,一边高唱着描述传统农具意向的民歌。(86)参见卢勇、高亮月:《挖掘与传承: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兴化垛田的文化内涵探析》,《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6期。这种景象是不可能出现的。但如果我们直接以之为基础,重建集体记忆所依托的村落活动与文化环境,又容易陷入“复古”的陷阱。尽管我们已反思并意识到“现代性脱离不了各个社会的文化传统”(87)金耀基、周宪:《全球化与现代化》,《社会学研究》2003年第6期。,但传统与现代毕竟是两个文明阶段的产物,农业遗产天生具有反现代的因子。对此,苏东海不客气地指出:“古老文化所以能够传承至今,是因为他们仍生活在产生这些文化的古老环境中。一旦融入主流社会,古老文化就逐步丧失了固有的社会环境而濒临消失。”(88)苏东海:《生态博物馆的思想及中国的行动》,《国际博物馆(中文版)》2008年第Z1期。因此,我们需要进一步思考的是:如何厘清传统与现代的关系?如何对农业遗产进行适当剔除与改造?如何让农业遗产真正转型为具备“现代”属性、同时不改“传统”底色的文化形态?其中的限度问题,对于任何实践主体来说都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此外,我们在讨论“认同什么”的限度问题时依然不能忘记农民尺度,即农民是否欢迎与认可我们对于农业遗产集体认同的构想及构建过程。须知,认可并追寻现代而非传统生活,才是符合人性的正常选择甚至是更普遍的心声。假使兴化垛田能够开展大机械生产,那么当地农民必然不会采取人工播种的方式。(89)参见卢勇、王思明:《兴化垛田的历史渊源与保护传承》,《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4期。农业遗产所反映的乡村社会固然富含亲近自然的生态性与宜居舒适的生活节奏,但工业所缔造的现代文明与城市空间在整体上是一种更高维度的文明形态与生活方式,其所带来的财富、教育、医疗、交通等,都是农村无法比拟的。因此,当我们在强调农业遗产的文化记忆价值,希望保留其乡土气息与传统特色之时,某种程度上就是希望农民能永远生活在农村并世代以农为业。这是否是一种漠视了农村发展与农民追求现代生活的双标行为?我们所设立的“农业遗产保护区”,是否更隐含着视农民为“物”、违背人道尊严的色彩?(90)参见周星:《民族民间文化艺术遗产保护与基层社区》,《民族艺术》2004年第2期。王思明曾指出:“我们没有理由限制农民迁徙的自由,把农民羁留在农村;我们也没有理由自己在城市享受现代化生活设施的同时,要求农民一成不变地保留原来的生产和生活设施。”(91)王思明:《农业文化遗产的内涵及保护中应注意把握的八组关系》,《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2期。任何人都不能以“遗产”之名代替农民做出“认同什么”的选择,甚至希望他们留守在前现代的文化空间里,因为任何民族、地区的人民都有追求幸福与做出选择的权力。
四、余 论
农业遗产之所以在与工业文明交互中出现文化认同困境,从表面看源于工业文明自身强大的解构与重构能力以及人们相关认知的不断变迁,根因上还是现代工业文明语境下传统农业文明的适应性与发展性难题。在前现代社会中,农业传承是一类最普遍的社会传承,遗产地农民虽普遍认同但不自知。在现代工业大发展阶段,农业遗产的实体与记忆空间被解构得支离破碎,农民失去了文化认同的基础与对象,国人也乐见现代对传统的全面替代。随着工业文明的现代性问题及其衍生出的传统文化濒危性问题的暴露,人们开始重新发现传统并对农业遗产进行再评估,以此构建认同和寻找根魂,但在现代性权力所构筑的遗产叙事框架内,农业遗产成为“他者”,即政府、学者及大众消费者等“多重凝视”的对象,由此导致遗产所有权与话语权逐渐分离,农业遗产从原有的生产生活场景中脱嵌。农民失权后在事实上成了农业遗产的“他者”,遗产的文化主体及其认同失真危机也就不可避免。其重构与失真程度取决于知识、权力和资本等强势话语之间的协商与博弈。(92)参见潘君瑶:《遗产的社会建构:话语、叙事与记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的遗产传承与传播》,《民族学刊》2021年第4期。
在已发生或正发生的问题之外,“难以解决问题”可能是关系到未来的另一大难题。尤其在最基本的“谁来认同”与“认同什么”议题上,我们很难在现实中坚守“农民认同”这一最大尺度和“传统”“现代”之间的限度。但无论如何,这是我们在重建农业遗产文化认同之路上必须要跨越的障碍。我们相信,尽管每一个社会成员同时隶属多个范畴:个人的、家庭的、族群的、地域的、民族的、国家的……,但最具归属感的是承载着集体记忆、凝聚着大众乡愁的遗产家园。如果没有农民的创造与认同,我们任何的情感与认同都是脱离历史与现实的虚无,所以我们的基本准则必须是“农民经济上可持续,精神上愉悦,文化上感到自豪”(93)王思明:《农业文化遗产的内涵及保护中应注意把握的八组关系》,《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2期。。在农业遗产话语实践中,我们应将社会的强势“他者”(尤其是政府和学者的介入)转变成“我者”(农民)的内生动力,从而由客体化认同逐步让渡到主体性认同。(94)参见朱伟:《现代语境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表达与叙事》,《文化遗产》2021年第1期。就农业遗产文化认同的方向而言,我们不应简单将传统与现代看作两个并列的事物,而是要将后者作为一个大前提,并推动前者融入后者之中。也就是说,农业遗产不仅要积极吸收现代文明的活力因子,更要在保持乡土底色的基础上拥有现代的性质,因为在以工业文明为底层规则与基本叙事的时代,任何不与现代文明相融的事物都难以持久存续。这不仅是“城乡一体化”的应有之义,也是构筑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理论之石。
——围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