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哥战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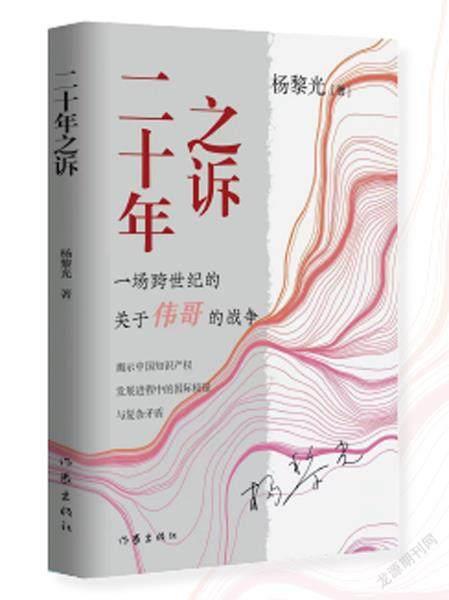
对一桩延续二十年知识产权案例的剖析

这股始自美国的蓝色风暴,第一时间如一股强劲的台风跨过太平洋,先后扫过日本和韩国,到达中国香港和台湾,直奔它的另一个重要登陆场——中国大陆。
这是一块辉瑞公司迫切想放进嘴里的巨大蛋糕。到1999年,含美国在内获得“Viagra”销售许可的国家和地区共计11个,即为辉瑞公司贡献了十多亿美元的销售额。而这11个国家和地区的人口总数,尚不及中国的三分之一。更何况拥有庞大消费人口基数的中国,还拥有无与伦比的补肾壮阳的悠久文化传统和中药温补的千年春药实践,和“Viagra”的产品属性毫无违和感。这不,在欢呼“Viagra”诞生的全球媒体多声部大合唱中,以中国大陆为主体的华文媒体的表现就像一支嘹亮的小号。
据不完全统计,仅在1998年6月至12月的半年间,中国大陆就有多达320种以上的杂志、1800多种报纸刊出800多萬文字,事无巨细地报道了“Viagra”。以电波信号为介质的电视台和电台的播出次数和时长难以统计,相信与文字报道相比也不遑多让。有人做了一个统计,光是把这多达800万字的平面媒体版面,以当时的平均广告价格折算,其价值就高达7200万元人民币。当时的一位传播领域的专家甚至断言,仅就中国大陆地区而言,辉瑞公司的“Viagra”在尚未获得市场准入、广告零投入的情况下,就至少积累了超过5亿元人民币的无形资产知名度。有意思的是,若干年后,这位专家就要修正自己的结论了。5亿元人民币的无形资产的估计当然没问题。有问题的是这价值5亿元人民币的无形资产,辉瑞公司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收货人。
一字亿金,“伟哥”两字,竟是史上最贵的拼字游戏。
这两个如今看起来普普通通的汉字,不久后就直接引发了一场旷日持久、价值以亿美元计的“伟哥”商标权争夺战,直到今天仍然烽火不熄、缠斗不止。是谁第一个创造了“伟哥”这个大名,然后被整个华人媒体圈通用的呢?这个发明权,对媒体而言,并无多少利益诉求,因此没有什么人争抢。倒是最终拥有“伟哥”商标权的广州威尔曼药业公司在日后的诉讼答辩中,有理有据地论述了他们是“伟哥”商标首创者的理由。本书对此有详细解读,此处暂且不表。
至于中文媒体圈首刊者,一般倾向认为是香港报刊,因为中国南方历来有称呼某男子为某某哥的传统,香港媒体人极有可能顺手妙合了译音和传统,习惯性地想出了这一译名,但也很有意思的是,无任何人出来认领这个称号。最后是美国的一份华文报纸《世界日报》宣称自己是始作俑者。该报于1999年2月18日以“伟哥译名追本溯源来自本报”为题,刊文揭示“伟哥”一词的来龙去脉:
辉瑞药厂“Viagra”在去年4月上旬上市以来,迅速成为有史以来最热门的新药品,中文报刊的报道至今无合适的译名。本报纽约地方版在去年4月28日见报的专题,首次以“伟哥”译名问世,马上得到群众口碑。随着联合报的中文译名的影响力,又得到了许多中文报纸的解释,“伟哥”一名又迅速在世界传开。
追溯命名的渊源,这个令辉瑞药厂痛失商机的“伟哥”,其实诞生在纽约的白石镇本报编辑部。当时,由记者撰写的稿件,本来将“Viagra”译为“痿而革”,取其实兼其意,其实已经和辉瑞想出的“威而刚”,颇有异曲同工之妙。结果稿件在编辑台上经过集思广益,由“痿而革”演变为“威尔戈”,逗趣而寓雄伟之意,再变为“伟一哥”,最后去“一”而成“伟哥”,果然见报后人人叫绝。谁知将近十个月后,竟成引起商品侵权诉讼的根源。
美国中文报纸《世界日报》的这种自我认领,既未获得媒体界的认同,也无人与其争论。因为,不要说远在万里之外的《世界日报》,就是此时此刻身处其中的中国药界,谁又能想到,一场涉及药物专利权、商标权,贯穿行政、法律诉讼,直接相关数十家中国药企,前前后后折腾数十场官司的“伟哥”大战,会在10个月后拉开帷幕,并成为中国“入世”前后,在知识产权保护领域的标志性案件。
“伟哥”,借汝之名,多少人、多少中国药企的命运因之逆流成河!刚刚兵临中国市场城下,“Viagra”这个药物明星就以“伟哥”这个中文译名为马甲,被中文媒体反复追捧,短时间内在中国家喻户晓。对此,彼时的辉瑞公司上下应该是喜忧参半的。喜的是,王师未动,声威已劲,省下了多少品牌建立、产品推广、消费者教育等上面的银子。忧的是,短时间内拿不下攻城的云梯——中国上市许可,尽人皆知却无货可售的情况下,反而可能导致走私、黑市和仿冒泛滥的局面,甚至搞得使管理部门的审批动作更加谨慎。
新加坡《联合早报》的报道指出:“中国医药管理局有关人士解释说,按照中国法规,对于进口药物,不管其在国外临床效果如何,都需要在中国重新进行全面严格的临床检测。预计北京的试验将在四五月份(1999年)完成。一份汇总全国七家医院情况的验证报告,将上报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经论证后,由政府部门最后考虑是否引进该药。”该报道还援引“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有关人士”的话表示:即使该药最终通过临床试验允许在中国上市,医药监管部门也要结合中国国情,对该药的销售范围、对象等加以限制。
《中华工商时报》的一则报道说:“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警告,私售‘Viagra’将按制售假药论处。”辉瑞公司在向媒体喊话时也显得有点小心翼翼:“Viagra”会在北京、上海的临床试验全部结束后,向中国药品监督管理局提出“一类新药当地生产”申请,有望于1999年9月在地处大连的中国辉瑞制药公司投入生产并上市。媒体和潜在的消费者们都睁大眼睛,等着看这头药界的世纪猛兽,到底何时“攻城”。谁也没有想到,就在1998年圣诞节,一个东北能人和一条飞行轨迹有点怪异的“飞龙”突然出现在城楼上,尖声高叫:
战争开始了!
“飞龙”指的是沈阳飞龙药业公司。“东北能人”,说的是公司掌舵人姜伟。成立于1987年的飞龙公司,是中国最早的保健品企业之一。在被戏称“全民喝药”的20世纪八九十年代,珠三角有“太阳神”,长三角有“娃哈哈”,大东北的代表就是这一条“飞龙”。
“一个充满了悲情诗意的企业家和他一手谱就的咏叹曲。”财经作家吴晓波在他的名作《大败局Ⅰ》中,这样概括姜伟和他的飞龙公司的盛衰起伏。在该书中,对姜伟和他的飞龙公司的败局剖析被列为第五章节。如果吴晓波是以失败样本的剖析价值来排名的话,素来好胜、自负的姜伟,恐怕不会太满意。姜伟1977年参加高考,毕业于辽宁省中医学院,曾担任辽宁省中药研究所药物研究室副主任,是不折不扣的科班“中药人”。
个性不安于平庸的姜伟于1986年下海,1990年接手飞龙公司。当时的飞龙公司,只是一家注册资本75万元、职工60多人的小工厂,主打产品叫“飞燕减肥茶”。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中国,“减肥茶”显然是一个过于细分、小众,甚至有点超前的保健品类。飞龙公司以此作为主打产品,其经营状况一望可知。姜伟接手飞龙公司后,立即于次年推出了“延生护宝液”,后经辽宁省卫生厅批准改为“延生护宝胶囊”。
这个产品,让“飞龙”一飞冲天。
“延生護宝液”的原料是雄蚕蛾、淫羊藿、红参、延胡索等中药材,据称对男女肾阳虚引起的诸症有一定疗效。中医药科班出身的姜伟,搞出这款传统中药改良型配方的保健药品并不出奇,引人注目的是他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极限轰炸”广告战术。
这里的“蓝”们主要指的是当时的“太阳神”“娃哈哈”。
这两家企业依靠成功的广告策略一跃而成为保健品市场上的带头大哥。他们的主要特色是高举高打,斥重金抢占中央电视台的黄金播出时段,实行无差别广告轰炸策略,成为产品传播的一种成功营销方式。借助于此一时期中央电视台如日中天的影响力,一批敢于赌一把的不怎么知名的品牌奇迹般地一夜之间鸡毛飞上天,最后竟催生出了世界营销史上极具中国特色的中央电视台“标王现象”。
此一流派,至今回响不绝,仍被一些所谓的营销大师和他们的甲方奉为圭臬。
而折服于毛泽东军事理论的姜伟,则从前者的“在局部战争中,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的战术思想中,融会贯通出了自己的“极限轰炸”广告投放思路。概括起来,姜伟的打法就是“集中火力,单点突破;以点带面,各个击破”。
“首战”长春,他一掷千金,密密麻麻的“延生护宝胶囊”广告,几乎包下了该市所有报纸的广告版面,随后电视、电台等媒体相继跟进。单点密集轰炸之下,半个月后长春城被顺利拿下。
以“长春歼灭战”为样板,姜伟依样画葫芦,集重兵相继攻克哈尔滨、齐齐哈尔等重点城市。
至此,整个东北市场尽入姜伟之手。
在经略华东市场时,姜伟又出妙手,先在南京、杭州、苏州等地铺货,对最大的目标——上海却“围而不攻”:在上海的报纸上大登“延生护宝胶囊”广告,却不给上海市场投放产品,活生生吊起了上海人的胃口。经此一役,飞龙公司在大上海暴得大名,顺利敲开了华东市场大门。
“一招鲜”炸出了一片天。姜伟的“极限轰炸”广告战术,在一开始的3年里取得了辉煌的成功,帮助飞龙公司刷出了一条亮丽的经营曲线:1991年初闯市场,即创下产值1200万元;1992年实现产值1.8亿元,利润6000多万元;1993年产值飙升至10亿元,利润高达2亿元。
弹指间,沈阳飞龙药业公司不仅实现了辽宁省医药行业43年来单一品种年产值超亿元的突破,并且一下子提升至10倍的高度,一跃成为该省医药行业的第一创利大户,在全国医药行业人均利税评比中荣登榜首,在全国所有外商投资企业1992年度人均利税排名中名列第二。在国有企业扎堆、效益普遍低下的东北,飞龙公司的效益可谓鹤立鸡群,成为神一般的存在。
在强劲的“飞龙冲击波”中,姜伟本人也在短时间内集齐了当时堪称顶级的诸多桂冠:全国劳动模范、中国青年联合会常委、全国杰出青年企业家、中国十大杰出青年、中国改革风云人物,等等。姜伟的广告“极限战”的战果是如此耀眼,让后来者眼前为之一亮。在飞龙公司之后崛起的“巨人”“三珠”“红桃K”等企业纷起效尤。只是他们的炒作手法更加粗暴,他们的战场——广大的农村市场——更加粗放。
产品靠“点子”、市场重营销的保健品“战国时代”悄然而至。
数年后,姜伟在反思他的失误时认为,“飞龙”的败落应该归咎于国内保健品市场的鱼龙混杂和新入品牌的乱砍滥伐。
在1995年初,全国保健品总数达到令人目瞪口呆的2.8万多种。
为从千军万马中突围,广告战术变异为吹牛大赛,什么“联合国批准”“总理感谢信”等等都敢往外喊。姜伟抱怨说:“我们是保健品开发的先驱者,一下不会玩了,什么都成了保健品,保健品成了粮食,搞保健品的成了种粮的老农,还竞争个什么劲!”然而,他好像忘了,保健品市场一度走到人神共愤的境地,他与有功焉。
一位叫徐徐的作者曾经在1997年写过一篇《飞龙之死》的文章,用不无偏激的语言质问姜伟:
用整版整版的报纸篇幅,连篇累牍地宣传一个保健品,实行轰炸式广告灌输的是谁?沈阳飞龙。把一个保健品吹成包医百病的治疗药的是谁?沈阳飞龙。把一种酒吹成有病治病、无病防病、男女老少、四季皆宜的灵丹妙药的是谁?沈阳飞龙。把充满不实之词的印刷品广告撒得到处都是的是谁?沈阳飞龙。把八字没一撇的出口贸易胡吹成‘延生护宝液’出口韩国80亿元的是谁?沈阳飞龙。在迅速地树立起一个品牌的同时,又迅速地毁掉一个品牌。飞龙如此,后来的成功者也将如此。从这个意义上说,飞龙不死,市场不容,天地难容!
在飞龙人的记忆中,1994年的秋天是最后一个丰收的秋天。此时,“延生护宝胶囊”依然在全国旺销,放眼望去,都是飞龙广而告之的“新生活的开始”。姜伟兴冲冲飞往香港。这时的飞龙公司,尽管货款被中间商大量拖欠,但账面利润仍有2亿元。
《大败局Ⅰ》对姜伟的香港之行有过描述。在香港包装上市之际,香港律师一共提出2870个问题,姜伟大半答不上来。自我感觉一向良好的姜伟意识到:“人家有一条没有直说,就是总裁不懂、集团也没有人懂国际金融运作。”
“当听说飞龙集团在香港上市有希望,我差点上了天,可在香港待了一段时间,备受煎熬,再也兴奋不起来了。”姜伟终于发现,拿着国内那套唬人的办法到了国际金融大都会的香港竟然寸步难行,“我们在做利润审计时,以为利润做得越大就越容易融资,结果人家说,上市后,利润就由不得你们定了,你报了这么多利润就要多分红,你利润掉下来就全砸锅了,香港股市很规范,做不得一点假。”最后香港人给飞龙公司下了诊断书,飞龙公司有四大隐患:没有可信的长远发展规划,没有硬碰硬的高科技产品,资产不实且资产过低,财务管理漏洞太大。
尽管如此,上市运作仍在继续。1995年3月23日,飞龙公司拿到了联交所的获准文书,但是4月18日,上市倒计时之际,姜伟突然做出了让所有人大吃一惊的决定:飞龙公司放弃上市。历经6个月,耗费1800万元,姜伟带着一套规范的财务报表和评估报告回到了沈阳。
对此惊人之举,当年姜伟的解释比较清奇:“虽然我们获得了走向国际市场的入门证,但我们发现了诸多的不足与弊病,飞龙集团虽然是国内优秀的民营企业,但离真正成为符合国际资本标准的合格企业,还不只差一星半点。我们非常渴望走向国际市场,但机会来了,又发现准备远远不足。”
但事实上,“放弃”香港上市,在姜伟的经营生涯里是一个巨大的创伤。两年后,有记者让他填写一份“姜伟性格透视”的问答表,在“最大遗憾”一栏里,他写上了“失去香港上市机会”。在若干年后,姜伟卷入轰动一时的“中科创”事件,买壳上市未果,又一次在资本市场铩羽而归。后来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夏冬的采访时,谈到了香港往事,似乎是最接近真相的心声流露。
其实姜伟的上市之梦到今天已经是第7个年头。“1994年,沈阳飞龙业绩相当好,‘延生护宝胶囊’风靡大江南北,当时就想上市,理由很简单,一可以筹钱,二可以出名。但东北这地方老国企集中,一起往资本市场里挤,我一个民营企业要拿到指标简直是天方夜谭。那时正值H股热,灵机一动就想到了香港市场,‘百富勤’的梁伯韬与我一拍即合, 1994年10月我第一次与梁伯韬在北京见面,仅仅谈了20分钟就基本搞定。”
但姜伟的灵机一动却使当时的证监会犯了大难,那时在香港上市,你姜伟一个个体户要往香港钻能行吗?在姜伟1994年11月只身闹到证监会时,接待他的时任中国证监会发行部主任高西庆有点不知所措,说要请示研究。当年12月,证监会口头通知,沈陽飞龙公司在香港上市不需要中国证监会批准,障碍扫除了。对沈阳飞龙公司能够上市而没有上市这一历史,姜伟说:“1995年初香港股市大跌,我权衡了很久,主动提出中止上市,历经6个月,耗资3000万,可我换回了一套规范的财务报表和评估报告,我认为值。”
1996年姜伟又有了新的计划,在美国“买壳上市”,通过收购一家美国上市公司,使飞龙集团跻身美国资本市场,可其中的惊险让姜伟现在都心有余悸:“当时准备收购美国一家公司70%的法人股,可按美国法律,法人股要经过批准才能变为普通股,我不仅没融到资,反而还要出大笔的美金,哪有这种赔本的买卖。在美国谈判,给我的资料全是英文,谈判也用英文,翻译又不管用,自己成了瞎子聋子,幸亏关键时刻灵感出现,才化险为夷。”
两次海外上市计划均无疾而终,不但没有融到资,反而倒贴了不少冤枉钱。但姜伟始终没有断了上市融资这个念头。他对记者诉苦:“我当然想上市:想上国内的A股,想上创业板,可我到哪里去弄这三年的财务指标,今年我已46岁,不是10多年前30多岁的姜伟了,我再也耗不起这个时间,只剩下买壳上市这一条路可走了。”
姜伟南赴香港争取上市、寻求外部资源之际,正是国内保健品市场风云突变之时。
涌向几乎没有“门禁”的保健品行业的市场热钱,不断抬高着这个行业的河床。
韭菜,已经不够割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