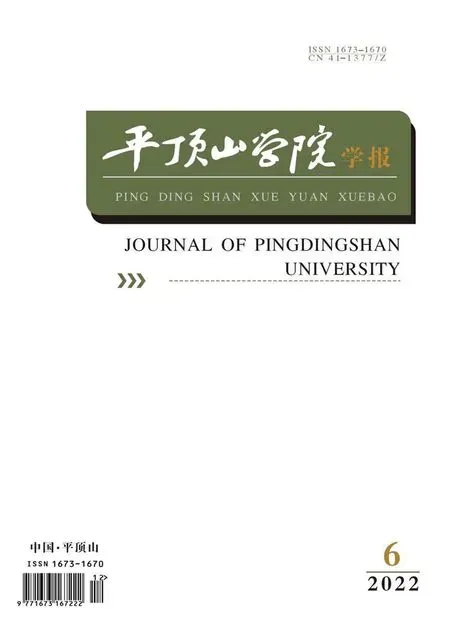“无声之乐”与“大音希声”
——论儒道音乐哲学之同异
张小雨
(文山学院 历史系,云南 文山 663099)
中华文明素有礼乐文明之别称,礼乐并举、优于政刑是其一贯的文化特色与制度特点。音乐很早便成为古代中国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特别是在先秦诸子争鸣时期,儒道法墨等学派皆不约而同地发表过其对于音乐的基本看法。而正如蒋孔阳先生所说:“先秦的哲学家,很少是从纯哲学的角度来探讨哲学问题的,他们都是从当时社会政治伦理的需要,来探讨哲学问题。”[1]当时的哲人们还没有今日“为艺术而艺术”——将艺术作为一种独立门类,承认并探讨其区别于他者价值的思想观念,而是从整个现实社会需要出发,来研究音乐与政治、道德、伦理、修养的关系,并最终建立起哲学体系。说到底,先秦诸子的音乐观念作与其哲学主张一致的,本质上是其思想理论在认识、分析音乐时的具体结果。因此,我们可将各家的音乐观念作为途径,来一窥其整个的哲学系统。其中,儒家的“无声之乐”与道家的“大音希声”两大概念文字相近,内涵却大不相同,恰好可作为我们把握两家音乐观念同异乃至理解其哲学主张的入门之径。
对此两大概念,已有研究的基本特点是:第一,将《礼记·孔子闲居》篇中记载的“无声之乐,无体之礼,无服之丧”三者联系起来,并统一到“无体之礼”中。例如刘丰先生的《“无体之礼”:先秦礼学思想的发展与转向》一文。其从儒家礼乐一体角度,研究“无声之乐”与传统礼制的关系,以及这一概念提出的思想史背景。第二,因为上博简中《民之父母》一篇存在着与《礼记·孔子闲居》《孔子家语·论礼》高度相似的部分内容,且二者均记载了此“三无”概念,故有学者致力于通过考证简文,从而论证《孔子家语》一书的真实性及《礼记·孔子闲居》篇产生的时间。例如杨朝明先生的《儒家文献与早期儒学研究》一书及廖名春、张岩的《从上博简〈民之父母〉“五至”说论〈孔子家语·论礼〉的真伪》一文等。第三,将《老子》中的“大音希声”与《庄子》中的“天籁”进行对比,着重研究道家音乐美学思想。例如李巧伟先生的《道家“天乐”论音乐美学传播思想探究》一文等。本文的特点是从音乐哲学角度,通过将这两种用字较为类似的观念进行详细对比,一窥儒道音乐哲学之同异。
一、来源
儒家的“无声之乐”一语,首先可见于《礼记·孔子闲居》。其原文为:
孔子闲居,子夏侍。子夏曰:“敢问《诗》云:‘凯弟君子,民之父母。’何如斯可谓民之父母矣?”孔子曰:“夫民之父母乎,必达于礼乐之原,以致五至而行三无,以横于天下。‘四方’有败,必先知之,此之谓‘民之父母矣’。”[2]1626
子夏曰:“‘民之父母’,既得而闻之矣,敢问何谓‘五至’?”孔子曰:“志之所至,诗亦至焉。诗之所至,礼亦至焉。礼之所至,乐亦至焉。乐之所至,哀亦至焉。哀乐相生。是故正明目而视之,不可得而见也。倾耳而听之,不可得而闻也。志气塞乎天地,此之谓‘五至’。”[2]1627
子夏曰:“‘五至’既得而闻之矣,敢问何谓‘三无’?”孔子曰:“无声之乐,无体之礼,无服之丧,此之谓‘三无’。”子夏曰:“‘三无’既得略而闻之矣,敢问何诗近之?”孔子曰:“‘夙夜其命宥密’,无声之乐也。‘威仪逮逮,不可选也’,无体之礼也。‘凡民有丧,匍匐救之’,无服之丧也。”[2]1628
《礼记正义》引郑玄注曰:“名《孔子闲居》者,善其倦而不亵,犹使一子侍,为之说《诗》。著其氏,言可法也。退燕避人曰闲居。”[2]1626这意味着《孔子闲居》篇是孔子无事休息时与学生的对话。在对话中,学生子夏请教孔子:《诗经·泂酌》一诗中曾说“凯弟君子,民之父母”,究竟何为民之父母?孔子回答说,民之父母要做到能通达礼乐本原,并以之“致五至而行三无”,最终“横于天下”。“无声之乐”便是“行三无”中的“一无”。
上述文字亦可见于《孔子家语·论礼》,原文与《礼记》大同小异。同时,《孔子家语·六本》还记载道:“孔子曰:‘无体之礼,敬也;无服之丧,哀也;无声之乐,欢也。不言而信,不动而威,不施而仁,志。夫钟之音,怒而击之则武,忧而击之则悲。其志变者,声亦随之。故志诚感之,通于金石,而况人乎?’”[3]177-178此段文字又几乎可原文见于刘向《说苑·修文》,应该是孔子在另一场合对“行三无”的进一步说明。此外,《大戴礼记·主言》还记载了孔子在另一次闲居时与弟子曾子的对话。孔子向曾子解答何谓“主言”“七教”“三至”,其中与“无声之乐”有关的是:“曾子曰:‘敢问,何谓三至?’孔子曰:‘至礼不让而天下治,至赏不费而天下之士说,至乐无声而天下之民和。明主笃行三至,故天下之君可得而知也,天下之士可得而臣也,天下之民可得而用也。’”[4]此段文字又几乎可原文见于《孔子家语·王言解》。我们通过对比这几段文字不难得知,“无声之乐”与“至乐无声”应为近义概念,是孔子提出的一种治理国家的理想方式。
关于《礼记》各篇的成书时间,虽然学术界一直众说纷纭,且历来对《孔子家语》的真实性认识也存在分歧,但我们认为,“无声之乐”一语应是对孔子本人原话的记录,是最能反映儒家乐教基本内涵的重要概念。原因有三:第一,从《孔子闲居》的文章背景来看,它是孔子在休息时向子夏传教《诗经》的记录。子夏是孔门弟子中与《诗》学较为密切者,《论语》曾多次记载子夏向孔子请教《诗经》中某些诗句的含义。《汉书·艺文志》也曾提到“有毛公之学,自谓子夏所传”[5]。这都能说明子夏最终于《诗》有大成,甚至可能是后世毛诗之始祖。而《孔子闲居》篇所载便极可能是子夏与孔子之间的一次论《诗》实录。第二,上博简中有《民之父母》篇,其内容与《孔子闲居》篇的前半部分大体相同,皆是子夏向孔子问《诗》,孔子答语中也皆有“五至三无”一语。简文整理者濮茅左先生说:“《礼记·孔子闲居》合‘民之父母’与‘三王之德’(三无私)两文为一,两文都是子夏与孔子的问答。《孔子家语·论礼》包含着《礼记》中的《仲尼燕居》孔子与子张、子贡、言游论礼,及《孔子闲居》孔子与子夏论‘民之父母’‘三无私’的内容,且所论简略。”[6]随后,濮先生还以上博简《民之父母》篇为底本,将《礼记·孔子闲居》以及《孔子家语》的《论礼》与《问玉》四篇文章进行对校,并列出其主要异文。在此统计中,除《问玉》篇外,其余三文皆有“五至三无”的记载,只不过《民之父母》篇将其写作“亡声之乐”,其实同义。杨朝明先生曾根据《民之父母》一、二简的内容,将《孔子家语》与《论礼》进行比较,提出“《礼记》的《孔子闲居》是根据《家语》改编而成,意味着上博楚简该篇和《礼记》的《孔子闲居》都本于《家语》”[7]。无独有偶,廖名春、张岩先生也在比较此三篇文章后认为,“较之《礼记·孔子闲居》篇及楚简《民之父母》篇,《孔子家语·论礼》篇所记更真实,更符合原意,说它袭自《礼记·孔子闲居》篇,显然是不能成立的”[8]。上博简被断代为战国晚期,其所记载之内容应早于此,而《孔子家语》是在孔子去世后其弟子于孔子之“家”论学交流之记载,最早应成书于战国早期。这意味着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大体上形成了一种二重证据关系,且它们能说明“五至三无”一语应是子夏或其弟子对当年孔子论《诗》原话的记录,相关文章应产生于战国初期至中期。第三,从内容来看,本文认为“达礼乐之原”“无声之乐”等说法极其接近孔子一贯的礼乐观念,应是孔子本人思想的直接体现。这在下文还将展开论述。
道家的“大音希声”一语,则见于今本《老子》的第四十一章。其原文为:
上士闻道,勤而行之;中士闻道,若存若亡;下士闻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为道。故建言有之:明道若昧,进道若退,夷道若颣。上德若谷,大白若辱,广德若不足,建德若偷,质真若渝。大方无隅,大器晚成,大音希声,大象无形。道隐无名,夫唯道善贷且成。[9]115-116
《老子》一书的具体作者及成书时间至今仍有争议,且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的各版本之间也存在一定的文字出入。此段文字亦可见于郭店楚简《老子乙》、长沙马王堆汉墓《帛书老子乙德经》两种文献。刘笑敢先生对比了郭店楚简本、马王堆帛书本、河上公注本、王弼注本、傅奕本共五种《老子》文本(1)详参刘笑敢:《老子古今:五种对勘与析评引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426—427页。,由其结论可知:虽然此五种版本存在诸多文字差异,但帛书本、王弼本、河上公本皆有“大音希声”四字。傅奕本虽写作“大音稀声”,但“稀”与“希”二字本同意通用,故可视为同一概念。郭店本原文写作“大音祗聖,天象亡坓”[10]118,前文是“大方亡禺,大器曼成”[10]118。“方”即方形,“禺”通“隅”表示角,有棱有角才可谓之方形;“器”指“器物”,“成”即做成,制作完成才可谓之器物。从原文语句来看,在此“大甲无(亡)乙”的句式中,甲、乙二者的关系为乙是甲得以产生存在的必要条件,有乙才可谓之甲。因此,“大音祗聖”中的“聖”,应写作“聲”,音必须以声的形式才能存在、被人感知。可能是因为“聲”与“聖”二字形相近,导致竹简传抄错误。“祗”也应与“无”“亡”字同义,共同组成“大甲无乙”之句式(2)孙星群先生认为楚简的“祗”字应是“耑”字的异体,“耑”又与“黹”互用,而“黹”又可作“希”。“耑”“黹”“希”三字通用,意为稀少的精美之物,所以原文就应写作“大音希声”。此可备一说。详参孙星群:《无声之乐 孤掌之声 大音希声——儒释道音乐思想思考二》,见《人民音乐》,2008年第9期,第68—69页。。否则,如果按原文强解为“大音是尊敬圣人的”,便与此句中的其他子句句式不同、意义不通,不能成文。
加之,从传世文献来看,韩非曾对《老子》做过解读。《韩非子·喻老》篇有言曰:
楚庄王莅政三年,无令发,无政为也。右司马御座而与王隐曰:“有鸟止南方之阜,三年不翅,不飞不鸣,嘿然无声,此为何名?”王曰:“三年不翅,将以长羽翼;不飞不鸣,将以观民则。虽无飞,飞必冲天;虽无鸣,鸣必惊人。子释之,不谷知之矣。”处半年,乃自听政,所废者十,所起者九,诛大臣五,举处士六,而邦大治。举兵诛齐,败之徐州,胜晋于河雍,合诸侯于宋,遂霸天下。庄王不为小害善,故有大名;不早见示,故有大功。故曰:“大器晚成,大音希声。”[11]
韩非以楚庄王“不鸣则已,一鸣惊人”的故事为例,来解释老子所提出的概念。我们暂且搁置其具体结论,而聚焦于原文中的“故曰”二字。这说明至少在韩非看到的那个《老子》文本中,此处原文是写作“大器晚成,大音希声”的。与此类似,《吕氏春秋·乐成》篇有言曰“大智不形,大器晚成,大音希声”[12],这也与《韩非子》文本相近。另,郭店楚简的断代为战国中晚期,韩非子生活于战国末期,《吕氏春秋》成书于战国晚期,三者在时间上也是相近的。
结合上述情形,我们便能得出以下结论:第一,因为有帛书本、王弼本、河上公本以及《韩非子》《吕氏春秋》五大文本为对参,《老子》此处的原文应写作“大器晚成,大音希声”。郭店楚简本应是由于字形相近而导致抄录错误。比如后文的“天象亡坓”,从竹简原文来看,“天”与“大”字形极其接近,可能亦属抄录错误。第二,虽然古今各种《老子》文本存在一定差异,但“大音希声”这一词汇基本贯穿于各大版本,是道家较为原始的重要概念。
总之,“无声之乐”极可能是孔子本人的原话,“大音希声”也产生较早,是早期道家的原始理念,二者都较为贴近儒道音乐观念及哲学思想之本义,我们将其进行联系对比,对于了解两家主张来说便显得极有代表性。
二、释义
考析概念含义,首先应从训诂入手,先对其进行语义分析与解释,再进一步阐述义理内涵。但是,词语含义千变万化,为准确解释,就离不开对其所处具体语境的考察。
《孔子闲居》篇原文已为“无声之乐”预设了两大语境。第一大语境是这样的:“无声之乐”属于“三无”之一,而“致五至”“行三无”是为“民之父母”的具体方法,此八者皆是在上者治理国家、“平均天下”[2]1305的重要途径。因此,“无声之乐”全称应是“行无声之乐”,即在国家范围内推行没有声的乐教。在儒家的语境中,声、音、乐三者有所不同。《礼记·乐记》谓:“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声相应,故生变,变成方,谓之音。比音而乐之,及干戚、羽旄,谓之乐。”[2]1251声是人在接触外物后,受其“感动”影响,内在产生变化,并将此变化以声响形式表达出来的结果。它们可能是人自身的鸣、叫、吼等,也可能是人利用他物发出来的简单声响。音是在声的基础上,通过“变成方”——将简单声响组织化、系统化,最终形成一定规律后的结果,即今天音乐的意思。乐是在音的基础上融入舞蹈,成为一种综合艺术形式,类似于今天的大型音乐舞蹈史诗。声、音、乐三者的基础是声,而声又产生于人对外部世界刺激的反应。人与动物皆会受外界刺激并做出反应,都能发出声、听见声,但动物不能演奏乐器、谱曲填词,所以仅有人能欣赏、创作、演奏音与乐。在当时,乐又被称为古乐、雅乐,有着较为明确的内涵,并非所有的“大型音乐舞蹈史诗”皆能被视为乐。其主要是指自上古黄帝以来,歌颂历代圣王道德功绩的一批特殊乐曲,即《周礼·大司乐》所载“(大司乐)以乐舞教国子舞《云门》《大卷》《大咸》《大韶》《大夏》《大濩》《大武》”[13]。此七首乐曲便是西周乐教的具体教授曲目。一方面,这些乐曲的思想主题中蕴含了上古圣王的道德、精神、实践等,所以它们对后人的道德修养具备指导作用;另一方面,这些歌曲的音阶旋律“中正和谐”,可以对人的情感发动产生影响,使其在无形中逐渐归于平和,最终从思想、情感两方面得到教化与熏陶。因此,西周统治者及后世的儒家都提倡要“以乐为教”——将雅乐作为一种教化方式来影响百姓。
可是,离开了声,如何还有音、乐及乐教呢?这便要回到原文的第二大语境:“致五至行三无”是有前提条件的,即“必达于礼乐之原”。郑玄注曰:“原,犹本也。”[2]1626“原”是本质的意思,君主必须先通达于礼乐之本,才能“致五至”“行三无”。所以,只要能将礼乐之本质彰显、实现,就可以脱离具体的礼乐形式,更不用说声。那么,礼乐之本质又是什么呢?试看前文所引《孔子家语·六本》之语,那是在说,“三无”皆有与之搭配的内在情感状态,比如“无声之乐”便代表人的欢乐之情。人内在的情感状态统一被称为志,它决定人所发出的声,志怒便有武音、志忧便有悲音。同理,礼、丧皆是如此,它们本质上来说仅是此内在志的外在形式,所以志是礼乐之“原”。庞朴先生曾解释说:“礼、丧、乐,这是人的一些社会行为。其外在表现,为体、服、声;其内在主宰,乃敬、忧、欢。此敬、忧、欢,实为人的种种情,是人心在礼、丧、乐诸情境下的跃动,是心之所之,因之亦可统称之曰志。这个志,若主宰于信、威、仁,则表现为言、动、施;若见诸金石,其声有武、悲、乐之不同。”[14]此外,《论语·阳货》篇载:“子曰:‘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朱子注曰:“敬而将之以玉帛,则为礼;和而发之以钟鼓,则为乐。遗其本而专事其末,则岂礼乐之谓哉?”[15]礼表现为一系列礼节、仪式、礼器、制度,但其根本是人内在对他人、天地的尊敬之情。乐也表现为一系列乐器及其发出的音响,还有舞蹈、唱词等,但其根本却是人内在的平和之情。它们皆可以志统之,而志又往往被理解为“心之所之”,故礼乐最终都离不开人心。礼乐本质上是对主体表达内心世界的一种合理性约束,人以礼乐的形式来表达内在之变化才不至于过分或不及,更不至于危害自身及社会。礼乐本质上皆是工具,只要能够实现“心之所之”——志能够合理正当,便可以超越工具,直接实现教化百姓之目的。因为从本质来看,所谓教化,其实就是利用一批社会行为规范来培养内心。在儒家看来,礼乐是圣人在仰观俯察后所制定出的对天地自然规律之效法。其内在含有天地的本质规定性,也是圣人这一完全进入道德至善境界之主体的全部表达,所以是最为纯粹至善的,最利于感化人们走向更高道德境界。外物对人内心的影响是激发志,志是礼乐之所以能产生的基础,而礼乐产生的根本目的便是要给主体之志提供一种规范,使其能够在符合天地给予人本质规定性的前提下进行,最终使人能成全为人。反过来,礼乐之本是基于人内在精神情感需要的,它们不是纯粹强制性的外在规范,故人对于礼乐也有一种追寻之志。建立在人内在需要之上的礼乐制度,才能拥有坚固的基础。这样看来,志也与情相通。《孔子闲居》后文又引《诗经·昊天有成命》篇“夙夜其命宥密”一语来解释“无声之乐”,郑玄注曰:“《诗》读‘其’为‘基’,声之误也。基,谋也。密,静也。言君夙夜谋为政教以安民,则民乐之,此非有钟鼓之声也。”[2]1628孔子认为周成王行“无声之乐”的方法,是夙兴夜寐地谋划如何以政教安民,百姓受其善政良教的影响逐渐具备了一种乐的情感,便能在不借助任何钟鼓之声的情况下实现“无声之乐,欢也”[3]177的结果。
综合以上对原文两大语境的把握,我们将“无声之乐”解释为:在上者欲将国家治理好、成为民之父母,就必须通达于礼乐之本质——志,了解百姓之心及其受外在影响后的发展趋势,形成一套礼乐制度来教化百姓,使其能尽量避免外在的不良影响,并合理地表达内在。百姓受到国家善政良教的影响,便能生活在和谐社会中,此时就算不借助乐教,人们也能在无形中获得一种快乐、平和之情,当然也就不再需要借助雅乐来传达、营造和谐的价值观念与社会氛围。基于此,本文非常认同王博先生所说:“‘乐之所至,哀亦至焉’的说法,其意义在于,在把礼乐秩序建立在志的基础之上后,又把它们还原到情感上去。”[16]
历史上几个重要的《礼记》注解本子,大体上也是从这一角度来理解“无声之乐”的。孔颖达说:“‘无声之乐,无体之礼,无服之丧’,此三者皆谓行之在心,外无形状,故称‘无’也。”[2]1628“今此言以‘基’为‘谋’,言早夜谋为政教于国,民得宽和宁静,民喜乐之。于是无钟鼓之声而民乐,故为‘无声之乐’也。”[2]1629孔颖达认为,此处的“无”意为无形、不可见,“三无”皆指向内在,于内心深处行之,故不可见露于外。如若君主能不辞辛劳创建善政良教,则民自然能获得宽和宁静的心态,心中喜乐自觉接受约束,便不再需要有声之乐教。与此类似,陈澔曰:“夫子以喻无声之乐者,言人君政善,则民心自然喜悦,不在于钟鼓管弦之声也。”[17]其说都与本文对“无声之乐”的解释一致。孙希旦则是联系前文的“五至”来解释“三无”,他说:“无声之乐,谓心之和而无待于声也。无体之礼,谓心之敬而无待于事也。无服之丧,谓心之至诚恻怛而无待于服也。三者存乎心,由是而之焉则为志,发焉则为《诗》,行之则为礼、为乐、为哀,而无所不至。盖五至者礼乐之实,而三无者礼乐之原也。”[18]1276在孙希旦看来,和、敬、至诚恻怛三者皆存在于心中,这是主体外在行动及表现的内在基础——志,而《诗》、礼、乐、哀等仅是人们用以表达此心志的外在形式而已。所以,善于“致五至行三无”之人,必定要超越这些形式而直达主体内在本质。志从根本来看便是人内在的行为动机、思想情感状态,而对于君主来说,其所有政教行为皆只能有一种志向——为民之父母。所以,孙希旦还说:“愚谓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既有忧民之心存于内,则必有忧民之言形于外,故《诗》亦至焉。”[18]1275“五至”“三无”的出发点是君主为民之父母的志向,有此志向,便能夙兴夜寐治理国家,将民众之疾苦视为自己必须解决之事,故言辞中自然存在忧民之语,由此形成诗歌;继而必然会采取实际行动解决此类问题,由此建立礼乐制度来治理、教化天下;人们生活在有序社会中,又得到君主教化,由此生发一种平和、快乐之情;最后百姓的情感回馈至君主,君主以其快乐为乐、以其哀愁为哀。国家治理有序、百姓获得幸福,君主之志向无形之中在天地间流行,这便是儒家理想中的安乐治世。
《老子》原文也为“大音希声”提供了两大语境。第一大语境是这样的:“故建言有之”后的语句,是对前文“上士”“中士”“下士”闻道后会产生不同表现的解释。道有着“明道若昧”等特点,所以它不易被把握,进而不同层次的人在面对道时才会有“勤而行之”“若存若亡”“大笑之”的不同表现。同时,整个第四十一章又是对第四十章“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9]113的解释。因为道自身的规律是不断向其相反方向运动,且以柔弱、虚无为用,所以它能同时包纳事物的两大对立面,使得天下万物皆可以道为根本而不可穷极。万物皆属于可见可感的有形存在,必须依赖形上的无形不可见之本体才得以产生。因为所有可见有形的具体事物皆有其限制范围,一旦为此则不可为彼,彼此之间不具备融通性与超越性。道则处于形上本体地位,不断向其相反方向发展而不限于某种有形、有限的具体情况,从而使得其能成为有形世界的最终根源。在原文中,从“明道若昧”到“质真若渝”为一组,皆是采用“甲若乙”的句式。其中甲是乙的反义词,即明对昧、进对退、夷对颣、上对谷、大对辱、广对不足等。这几组反义词的组合是为了说明道具备“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的特点,即任何一种事物发展至极点时,便进入到道的层次,随之便会呈现与之相反的特征。此“甲若乙”的句式便是在说,凡人大多认为,甲发展到极致便意味着没有乙,例如大明不能有昧,前进不能后退,平坦不能有崎岖等。但实际上,发展至极致的事物已经触碰到道的层面,进而要向其反面转化并呈现相反状态,那种“明而不昧”“进而不退”的情况不可能在现实中存在。这便与常人的想法相反,所以“下士”只能“大笑之”。从“大方无隅”到“大象无形”则为第二组,前文已有交代,它们形成“大甲无乙”的句式,甲乙之间的关系是乙是甲的必要条件,有乙才可谓之甲。它们是为了说明道具备“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的特点。原本方形、器物、音乐、形象皆是可以在形下世界中被感知到的“有”,但在其之上,还有更加本质性的“大某”存在。“大某”不表现为某种具体形式的“有”,却优于任何一种“有”。
可见,此处的“大”字很重要,它其实提供了《老子》文本的第二大语境:在《老子》中,“大”字常常代表着道。例如,第二十五章说:“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大曰逝,逝曰远,远曰反。故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域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9]65-66这意味着道是抽象本体的字,“大”是此本体的名。在古代名往往比字更正式,所以“大音希声”的 “大”不是小的反义词,而是形容此“音”已经发展至道的层次。“大音”其实便是“道音”,是音、声这类形下事物发展到极点的最终结果。
综合以上两大语境,我们将“大音希声”解释为:原本所有形下世界的音、声皆必须以声响的形式存在,才能被人听到。如果没有声响,便不可谓之是音乐。但是,从本体的角度来看,极致的音乐即最符合抽象本质赋予音乐先天规定性的最完美、最崇高的音乐,已经脱离任何一种形下声响而存在,实际是道。在此道或“大”的层面来说,真正最有价值的音乐恰恰是无声的。因为任何一种具体的音、声皆不能完美地承担道的全部内涵,它们皆是有限的。相反,所有有形音乐皆产生于无形之道。
与《礼记》相同,我们也需要将此结论与历史上重要的《老子》注本相对照。王弼《老子道德经注》曰:“听之不闻名曰希。〔大音〕,不可得闻之音也。有声则有分,有分则不宫而商矣。分则不能统众,故有声者非大音也。”[9]116“听之不闻名曰希”出自《老子》第十四章[9]35,此章也是对道这一抽象本体的描述。“大音”其实便是道,它并不表现为任何一种具体的音阶,即非宫非商。因为宫商角徵羽五者各自有其规定性,为此则不能为彼。“分则不能统众”,如若“大音”是某一种可被听闻到的音阶旋律,便会使其丧失抽象本质地位。这其实与我们的结论相通。《老子道德经河上公章句》注曰:“大方正之人,无委曲廉隅。大器之人若九鼎瑚琏,不可卒成也。大音犹雷霆,待时而动,喻当爱气希言也。大法象之人质朴无形容。”[19]河上丈人是将其与人之修为联系起来看,认为“大方”“大器”“大音”“大象”皆是形容人的修为境界。“大音”指的是一个人能沉默寡言:天地间最振聋发聩的声音便是惊雷,它需要待时而发,不能随意出现,故人也应当效法此天地间的“大音”,做到“爱气希言”,只在需要时发出最正确的言论,方能在人世间发出如同自然界里的雷声那样巨大的响动。虽然其说浑然一体,也符合《老子》“人法天”的基本观念,但本文认为这种说法忽视了此语的基本语境及文辞,距离其本义较远。此外,钱锺书先生曾认为“大音希声”近似于白居易《琵琶行》“此时无声胜有声”(3)详参钱锺书:《老子王弼注》第十四则,副标题为“大音希声”。见钱锺书:《管锥编》(补订重排本)第2册,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80页。的境界,其实不然。白居易所说的是形下世界中音乐的演奏技艺问题,而《老子》则是从形上角度来界定其一般本质。在白居易看来,琵琶女通过大弦“嘈嘈如急雨”与小弦“切切如私语”的演奏后,已经起到了“说尽心中无限事”的演奏目的,此时进入到“凝绝不通声暂歇”的下一轮情感抒发。她在吐尽心中事后,以“此时无声胜有声”的方式将“别有幽愁暗恨生”表达了出来,说明自己心中还有诸多不可利用琵琶演奏将其表现出来的情感。故以静表动是一种演奏手法及表达方式,显然与《老子》之旨迥异。
三、本质
“无声之乐”或“至乐无声”概念的本质是将人的内在情感志向放置于外在礼乐刑法之上,即此四者仅是手段与途径,它们应服务于人及人所生存的环境。礼乐刑法仅是人用以表达自身情感、进行道德修养以及维护社会秩序安定的外在途径而已。从根本上看,国君行良政善教来安顿百姓,使贤人各尽其职,则自然会实现社会和谐、人民幸福的最终目的,而可以不过多纠结于具体手段与方式。礼乐的本质并非外在的声色仪表,而只是其精神内涵。
虽然儒家强调要“以乐为教”,但乐教并非使人获得演奏、创作音乐的技能,而是要借助一批“中正和谐”的音乐帮助自身内在情感发动做到“无过无不及”,才能实现道德境界的提升。因此,在儒家的语境中,像郑卫之音那样仅看重音乐的艺术水平与娱乐价值而无过多深刻思想内涵的音乐,是不值得提倡的。声、音、乐(郑声、郑卫之音、雅乐)之间除构成要素的复杂程度不同外,根本区别在于道德内涵。《乐记》说:“凡音者,生于人心者也。乐者,通伦理者也。是故知声而不知音者,禽兽是也。知音而不知乐者,众庶是也。唯君子为能知乐。是故审声以知音,审音以知乐,审乐以知政,而治道备矣。是故不知声者,不可与言音。不知音者,不可与言乐。知乐,则几于礼矣。礼乐皆得,谓之有德。”[2]1259乐之所以能高于音、声,根本在于其能“通伦理”、像“德”。聆听雅乐并非仅是一种艺术享受,更是道德启迪。
儒家追求的最高音乐形式是同时涵盖艺术上的美与道德上的善,符合礼制规定且对人有着积极引导作用的“文质彬彬”的雅乐。在儒家看来,人之所以要接受礼乐教化,原因有二:第一,持有“性善论”的儒者认为,人具有从天那里禀赋到的先天善性,此为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属性。但在后天的形下世界中,人可能会受外在不良影响而无法将其完全实现,故需要一种由那些已经实现善性的圣人制定出来的方式引导自身,使其能复归于善良的天性。这是一种自内而外式的论述。持有“自然人性论”的儒者则认为人天性质朴,其善恶皆有待于后天的影响与熏陶。所以,必须谨慎地选择能够“感动”人内在的外在事物,要杜绝外在的不良影响,以礼乐这一善良途径引导人变为善人,才能有利于社会整体的和谐。这是一种自外而内式的展开。第二,礼乐之所以值得人们遵循,一方面是因为它们是天地运行规律的体现,即《乐记》所谓“大乐与天地同和,大礼与天地同节”[2]1267。圣人制礼作乐是以一套人世间的制度规定来仿效天地而已,根本目的是实现人对天地的遵循。礼乐的正当性完全根基于天地的本体地位,而并非对人的强制束缚。另一方面则是因为礼乐是已经达到道德纯善之圣人的“制作规划”,人们接受礼乐实际是效仿圣人之德以成全自身。
道家对此却不以为然。在老子的哲学思想中,道处于本体地位,其余的形象、声音、事物等皆是由道这一本体产生的,是道这一不可见、不可听之形上本体在形下世界的具体彰显。老子彻底否定自商周以来的形上观念,转而用道这一剥离了宗教、信仰、意识的概念作为本体,认为道自身及其产生万物的基本规律是自然无为——无目的性。因此,在道家看来,天地并不具备意识主体性,更不具备道德伦理价值(天地不仁)。礼乐制度不可能是天道运行规则带给人的道德启示,它们并不存在用以祭祀、遵守、教化的形而上价值基础。道家并不承认儒家为礼乐教化构建的形上本体依据与现实价值基础,而是认为道创生天地万物,并内在于万物之中,从中显露其特性。万物是原本无限可能之道的一个个有限已成之物,所以,所有形下之物包括礼乐在内皆只能从某一方面反映出道而不能尽得全貌。
以声来说,宫商角徵羽的本体皆是道,五者之间不存在谁为其余四者本体的关系。形上之道在还未形成、彰显为物体时,原本具备无穷多的可能性,但一旦变现为形下之物,便会具体成为其中一种而丧失其无限可能性。这一过程便是王弼所说的“分”。道之全体通过“分”而为万物,从而失去其“统众”的本体地位与能力,成为具体的形下之物。因此,人们不可能仅凭借其感官能力,通过体认形下之物便了解道,进而涵养自身,而应是由类似“涤除玄览”[9]25的方式,实现超感官、超功利的理性直觉,才能将其把握。一方面,这种“大音”是无声的,它自然而然、无为而成、朴素虚静,是没有任何后天局限性的绝对至美之乐;另一方面,“大音”其实就是道,是全部有声之乐得以产生的最终本源,所以不会沦为任何一种具体音乐。可见,在老子的观念中,声、音、乐三者的价值排序恰恰与儒家相反,乐这一人为因素最大、修饰最多的综合艺术形式恰因距离质朴之道最远而价值最低。同理,声则要优于音。同时,在声之上仍有更高者,即“大音”“希声”“无声”。这种“无声”并非指代幽冥寂静的无声安静状态,而是不表现为、彰显为、沦落为任何一种具体音响形式的声音本体状态、本来面目,其实就是道。“大音”超脱于形下世界,无法在经验世界中被直接感知,是众音之所以能产生的根本原因,人只能通过体道才能认识它。它虽然被称为“大音”,但实际却不是一种能被听见的声音,不能指望用耳朵听见它。
《庄子》则用“人籁”“地籁”“天籁”来形容音乐。“人籁”泛指一切人发出的声响及使用乐器产生的音乐;“地籁”则是一切自然界中的声响,包括生物鸣叫及风声、水声;“天籁”并不是在前二者之外还有一种声音,而是使得二者之所以能成为其自身的先天本体,即“夫吹万不同,而使其自己也”[20]26。因为“天籁”并不表现为任何一种具体声响,我们把握它的方式也不是耳听,而是“无听之以耳而听之以心,无听之以心而听之以气。听止于耳,心止于符。气也者,虚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虚。虚者,心斋也”[20]80-81。
正因为如此,王弼才会将《老子》的“无名”注解为:“物以之成,而不见其形,故隐而无名也。”[9]116物依赖道使其成为物,但人却不能直接使用其感官能力来理解道。这是因为视觉所达之形、象,听觉所达之音、声,皆是道在后天的已成之物,道自身却是“无状之状、无物之象”[9]35。道是属于感觉范围内但又有所超越的东西。故“大音之声”实际上是要表达这样一种音乐哲学观念:五声、十二律等音阶样式,其本体皆在于道。相对于道来说,它们仅能得其部分而非全体,不能真正反映道,故不能执着于此形式。主体欲实现对道之全体的感知与体认,就不能仅凭感官能力去了解形下之物,而必须直接去体认“大音”——它实则已经剥离任何一种具体音阶样式,而上探至道的层面。
可见,“大音希声”与“无声之乐”的思维模式有类似之处:它们都将声响形式置于次要地位,而分别将道体与人心视为根本。老子认为音阶乐舞不可得道之全体,故应以求道为重而忽视音乐形式本身。这也是后来庄子“得鱼而忘筌”[20]492、“得意而忘言”[20]493之意。孔子则认为音乐舞蹈应当服务于人及人所生存的社会环境,提倡要先实现人之安顿。只要能推行良政善教,使得社会和谐、人民幸福,便自然可以实现乐教之目的,而不必再求助于音乐这一形式。老子认为道是音乐之本,“大音”是无为之乐、自然之乐,道家于音乐艺术主要追求其能反映自然的真及能复归道体的善。孔子则认为人特别是人之心志、情感才是音乐的本原,“至乐”是有为之乐、人间之音,儒家于音乐艺术主要追求其思想道德的善及艺术形式的美。所以孔子才会极力赞扬《韶》乐“尽美尽善”[21]222,并能闻之后“三月不知肉味”[21]456;“大音”是形下世界所有音乐背后的那个抽象本质,“至乐”则是人为之乐,是圣君治理国家达到极致后民众幸福心情的自然流露。
儒家认为符合礼、表现道德、形式优美的音乐是最佳音乐,但道家则认为最美的音乐是符合道、表现自然的,它们其实不能在形下世界找到完全对应。由此可见,老子及后世道家不可能认同孔子及后世儒家的乐教主张。因为在他们看来,儒家所推崇的雅乐乐舞甚至包括其所批判的郑卫之音,在道这一本体面前其实并没有根本区别,二者都仅能得其一偏,执着于雅乐是不懂得“大音希声”,沉迷于郑卫之音则是“五音令人耳聋”[9]31。儒家虽然也不以音、声为本体,而是从天地本体、情感本原、道德修养等方面来论述音乐,但却认为雅乐是对此天地本体的集中展现,人必须由对此类形下事物之体认才能使得情感发而中节,继而才能逐渐走向超越并最终追寻至形上的本体世界。道家对儒家的批判并不是站在其对立面,像墨子那样直接批驳儒家乐教思想及乐舞活动产生的诸多弊端,从而试图解构之,而是从其特有的哲学本体论角度出发,通过重新界定音乐的内涵、本质、价值,从而为其找到一种区别于儒家乃至春秋诸位贤士大夫及墨家、法家之观念的独特形而上地位。因此,其相关思考显得极具哲学性,也更深刻。道家的根本主张是仁义礼智的价值观念、礼乐教化的制度安排都必须符合道的基本特征,这是对儒家乃至西周乐教的一次重构。虽然反对礼乐教化,但在老子看来,仁义、慈爱等道德仍然具备重大价值,只不过其内涵与意义并非儒家所理解的那样。
总之,儒道两家所争论的是这样一组哲学性质的根本问题:何为音乐?音乐的最高价值与最终本体何在?人应当如何认识、体会、彰显音乐的内涵及价值?我们借用孙星群先生的一句话——“有声之乐,物激人也;无声之乐,道倾心也”[22],儒道争论的便是何谓这“倾心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