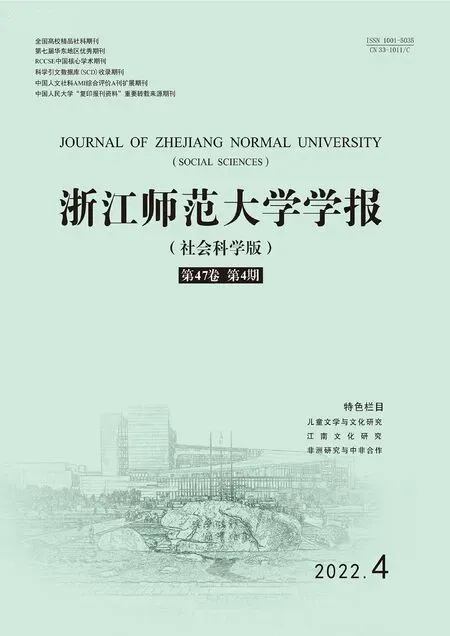战争的演绎与乡土的衍异
——《重回故乡》与《他来了么》的译介
冯 波
(安徽师范大学 文学院,安徽 芜湖 241002)
“乡土文学”研究曾一度近乎“显学”,不过论者往往将目光拘囿于本地风土民情的考察,忽略了域外乡土思潮的潜在影响。因此我们看到,虽人人言必称“乡土”,却少有人深入发掘“乡土”现代意涵发生、发展的内在情形。跨文化视角的阙如也成为当下学界“乡土文学”研究式微的本因与瓶颈所在。笔者以为,就东亚叙事中的“乡土中国”而言,乡土与国家、民族的现代意涵本就息息相关。因此,20世纪30年代前后围绕“欧战”的热议,势必延伸至个人与家国的复杂关系,这其实为中国现代知识分子重识自我提供了一个重要契机。因此,将目光聚焦于20世纪30年代“非战”小说中乡土叙事的译介,即是希冀在战争的历史语境中,以舶来的乡愁的本地化情形为路径,探析中国知识分子现代乡土意念的衍异及其现代主体性的建构过程。
一
20世纪的“一战”以及俄国的十月革命使得世界历史由近代开始转入现代。欧洲的战火虽然没有蔓延到中国,但“一战”后的巴黎和会则是点燃中国五四运动的导火索。除却政治、经济层面的影响,“一战”所带来的思想上的巨大冲击显然更为深刻。其实在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心里从来就没有彻底扫清战争的阴霾。诚如1925年茅盾在介绍法兰西战争文学时所说:“这三部在欧战发生十年后出版的小说都是写当时战争正烈的事,好像是春夜袭人的恶(噩)梦,令我们觉得几年来世界各处喊的‘战争的影子渐在人们脑子里暗淡下去了’实在有点自欺。照现在世界的情形看来,深恐上次大战的材料,尚未被文学家用完,而第二次大战又要来供给新材料了。”[1]
“一战”虽然造成了生灵涂炭,但是也开启了东西方文明、文化对话的全新时代。20世纪初梁启超的欧洲游历及其《欧游心影录》的发表,《东方杂志》早期对欧战的反思文章,乃至社会各界对欧战十年的纪念活动等,无不是此种域外战事在国人心灵的震荡与回响。但彼时国人对战争的认知与其说是恐惧毋宁称之为疑惧更为合适。譬如,早在1914年罗素就已看到:“中国人向我们学习,不像日本人是为了富国强兵,而是为了追求伦理和社会价值,追求知识上的兴趣。他们对于我们的文明也抱有怀疑的态度。他们之中有好几个人对我说,他们在1914年之前还不怎么怀疑,但‘大战’让他们觉得西方的生活方式中必定有缺陷。”[2]杜亚泉主编的《东方杂志》一系列与欧战相关的讨论,辜鸿铭在1920年出版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梁启超、张君劢等的欧洲考察及之后的《欧游心影录》,乃至学衡派的文艺主张等,就是此种“怀疑”的结果。而西方反思“一战”的名作《西方的没落》在中国的译介更是具有标志性的事件。这部被卡西尔怒斥为“恶的预言者”写的“历史的占星术”的作品[3]不仅极大地震动了欧美世界,同样也震惊了东方古国,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自晚清洋务运动始,中国一度以欧美为师的思想态势所发生的动摇与转向。
因此,当20世纪初的中国知识分子言及战争时,他们其实已然抱有否定战争、重审欧美的先入之见。尤其对于政治利益集团分赃不匀重新洗牌而引发的“一战”而言,战争的“非正义性”更强化了这种“非战”倾向。在20世纪30年代围绕着“战争文学”的理论译介也大多是从“非战”的立场予以选择的。譬如,俞荻译介了温塞尔(Sophus Keith Winther)的《写实的战争小说》,[4]董先修节译了戈斯的《战争与文学》,[5]邵荃麟介绍了意大利的殖民文学与战争文学等。[6]这些译介的相关理论文章在一致呼吁“文学”应承担起唤醒民族国家意识的重任之余,更多的是对战争本身的合法、合理性的强烈质疑。正如温塞尔在分析巴比塞和施威格的作品时所说:“在这小说之中,以及别的小说之中,只有一个真正的敌人,那就是狭隘的国家观念。”[4]“战争文学”理论的译介将“非战”的价值标准传递给本地的受众,这对20世纪30年代的文学创作有普遍的指导意义,“战争文学”作品的广泛传播也使得反思“战争”对人性的戕害与对所谓“爱国主义”的质疑走向深化。譬如巴比塞的《火线》与雷马克的《西线无战事》的译介就曾轰动一时。而这些译介的“非战”小说中,既关涉战争,又以故乡为背景的乡土小说创作更值得关注。譬如拉兹古的《战中的人》和跋佐夫的《他来了么》就很有代表性。
茅盾对国人的反躬自问某种程度上代表了中国知识分子对彼时民族国家危机的现代焦虑。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一系列事关乡土的“非战”小说的热译,其实不过是借域外战争来浇胸中块垒罢了,这是他们译介的内在动力。于是我们看到,他们对西方的、国家民族的战争反思自然对应于本地的、个人的乡土价值。国家利益集团的征伐与“乡土”独特性的不屈表达也成为20世纪30年代前后域外与本土独特的交流与反思方式。从这个方面说,战争其实为国人重估传统乡土,进而思考个体在国家民族中的身份站位提供了一个难得的历史契机。
二
文学如何演绎战争?在《重回故乡》和《他来了么》的战后还乡叙事中,预设“战场”与“故乡”极具张力的空间对峙,并通过这两个颇有意味的文化心理空间的转化来生成多义的诗意想象与价值取向是一种颇值得探究的叙事策略。一方面,战后还乡的叙事视角将“战场”与“故乡”分割开来,本应成为“战争小说”重要表现场域的“战场”却并未“在场”,而战场之外,似乎与战争关系并不紧密的“缺席”的“故乡”,反倒成为一种新的“在场”,这使得“故乡”在战争叙事中愈加鲜明突出;另一方面,战后还乡的回溯视角,又使得“非战”沿着“在场”的质疑与“缺席”的反思的双向理路走向了深入。如此一来,原本相对简单的、传统的怀乡恋旧也就变得更为复杂多义了。
《重回故乡》是匈牙利作家拉兹古《战中的人》的第六篇,其中第一篇《一个英雄的死》1921年由茅盾翻译,初刊于《小说月报》第12卷第3号。此外尚有林疑今1931年刊于《现代文学评论》的同名译本。[11]《重回故乡》最早以《复归故乡》为题同样由茅盾翻译刊载于《文学》杂志第153期,②后收入1928年开明书店译文集《雪人》。此后蒋怀青又以《重回故乡》为题译介,20世纪30年代有“复兴书局版”和“湖风书局版”各一种。③《战中的人》是拉兹古(Andreas Latzko)“非战”小说的代表,在译后记中译者茅盾援引罗曼·罗兰的话说:
《火线》(巴比塞H.Barbusse著,笔者注)是喊出将来的胁迫,但是对于现在却没有……在《战中的人》,却是审判现在,人类立在证人的箱(厢)里,对于“屠杀人者”控诉。人类么?并不定是。不过几个人,几个刚巧也是受害者,因为他们也是一个个人,所以他们的苦痛,刺到我们心里,更较群众的,为强烈……这本书的作者,拉兹古,将来就是第一排的证人,指摘一九一四年人类大耻事开演时人们的狂情妄念。[12]
在罗曼·罗兰看来,作为欧战“第一排证人”的拉兹古举证战争罪恶的突出特点即是充分展现战争给人造成的肉体与精神的痛苦,“但这并非因为拉兹古心中满记着肉体的痛苦,所以随手写出,这是因为他要使这种印象深印到别人的脑中去”。[12]个人化的身体体认显然增强了战争想象的真实度和说服力,但更为重要的是,身体成为连接“故乡”“战场”对峙空间的重要媒介,个体与故乡、国家/民族的逻辑关系的省思也得以彰显。
《重回故乡》是一个战后返乡的士兵,杀死一个以战争牟利的人的悲惨的故事。穷苦的约翰·蒲丹被统治者送上战场。战争中,蒲丹面部受伤,英俊的面孔变得丑陋不堪。他怀着痛苦与忧伤再次回到了故乡,却发现自己的主人正在发着战争横财,还霸占了自己的未婚妻。盛怒之下,蒲丹杀死了主人,他自己也被管家打死。蒲丹被战争摧残的“脸”是极具象征意义的身体书写,原本英俊的面孔因战争而变得丑陋:
他的鼻子看起来好像异色的小骰子拼补成的一个东西。他的嘴是歪的,全个的左颊好像一块臃肿的生肉,红而且交错着深色的瘢疤。唉!多么丑陋!可怕!此外他还有一长穴,深的足容一个人的手指,这长穴代替了一条颧骨。[13]3
一只眼睛失去了,带着一个破碎的颧骨,一张补缀成的脸颊,和半边的鼻子……[13]7
脸部细节的刻画强烈地传递了战争所带来的痛苦感。但是当蒲丹“贪婪地”看着故乡“叶丛间透露出的湖光”“熟识的灰土色的山脉”“教堂的尖塔”和“城堡的一角”时,他却越发强烈地感到“每抵一站,他的脸儿似乎变得丑陋些”。[13]1-2在此,因战争而导致个体与故乡关系的复杂变动得到了生动的展现。首先,个人与故乡原本亲密的血脉联系突出地表现为一种不对称的、错置的扭结。蒲丹记忆中的故乡是温暖、美丽的,他一度因自己丑陋的“脸”而深感“无颜以对”。但是当他终于回到“他热切思慕过的故土”,希冀让故乡抚平他的伤痛时,故乡却报以冷漠与嘲弄。车站守卫的妻子已经认不出这个“好像恶魔投胎”的故人,他与未婚妻马克撒的重逢也以爱人被惊吓以致逃走而告终。记忆的家园与现实故乡的强烈反差解构了个体与故乡理想化的情感期待,而身体叙事则强化了这一关系断裂的不容置疑。其次,当断裂后的个人与故乡关系转化为仇恨时,则彻底宣告了个体与故乡的决裂。昔日的爱人在发着战争横财的炮弹厂做工,并被炮弹厂的主人老林务官霸占。故乡成为援助战争的渊薮,与其说是战争戕害了这个漂亮的青年的身体,毋宁说是故乡摧残了游子的灵魂,于是,复仇的过程开始与战场厮杀的片段回忆同步展开。复仇的一瞬间,“一种冷的、坚决的宁静在他的心里慢慢地升起,仿佛在战壕里当号手给了一个放射的记号的时候”,[13]31老林务官的猎刀更“像一把枪刺”,诱使蒲丹拔刃而起刺进了“敌人”/故人的胸膛,同时也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个体之于故乡由“断裂”而至“决裂”的残酷现实不仅宣告了故乡与个体血脉关联的不可修复,也预告着在战争撕裂下个体对自我身份定位的惶惑。
第七种是利润效应。创新效益是企业追求的最终目标,如果能取得较好的利润和回报,就会形成良性循环。创新速度的提高最终能够为企业带来丰厚的利润回报。⑤
诚然,身份迷失的体验虽说与故乡的难以归宿密切相关,但更具有象征意义的还是表现在“故乡”与“战场”对个人的争夺中。“战场”所隐喻的“国家”/“民族”空间将个人与故乡的关系进一步延伸到个人与国家的辩证关系中。在战场所隐喻的国家话语内,个体之于国族的从属性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文化精神信仰的一种表现形式,这正是传统的“家国”而至“国家”的经典叙事的题中应有之义。因此,“战场”空间强势覆盖下的个人是集体性的政治期待对个体精神文化的统摄。于是我们看到,相较于“故乡”而言,“战场”大多是宏大的、鲜明的存在。然而,当离开“战场”返乡时,作为意识形态空间的“战场”与作为精神情感空间的“故乡”则成了颇有意味的对位。战时“战场”是现实,“故乡”是记忆;战后“故乡”是现实,“战场”成为记忆,战时、战后“战场”与“故乡”的虚实倒转恰恰为重识家园与故国提供了一个难得的反思空间。正如拉姆贝克所言:“回忆成为建立个人和集体身份认同的一个关键组成部分,为冲突也为认同提供表现的场所。”④“战场”的空间以记忆的方式“虚化”为一种“不在场”的“在场”。虽然人已回到故乡,但伤痛时刻提醒着战争并未远去。反之,“故乡”的空间则以现场实录的方式构成了一种“在场”的“不在场”,因为虽然人已回到故乡,但显然心还被缚在战场。而颇有意味的是,这两个虚实相间的空间由起初的撞击、撕扯,而逐渐成为一种浑然一体的存在。譬如,蒲丹复仇时已然无法分清楚“战场”与“故乡”的异同,二者似乎合二为一。“战场”毁掉了他的“左脸”,“故乡”夺走了他的真爱,当他天真地、自感羞愧“无脸见江东父老”之时,故乡却早已嫌恶这个游子的丑陋。故乡的炮弹炸毁了蒲丹的尊严,蒲丹同样用战争的方式报复了故乡的欺骗。于此,诸如混乱与平静、突进与逃遁、杀戮与拯救、亵渎与救赎等一系列的二元对立项似乎都是一体两面而已,混乱只为平静,突进也是逃遁,杀戮亦是拯救,亵渎正是救赎。而个体则在“故乡”与“战场”空间的争夺中,不断游移、漂泊无着。
拉兹古的描写是惊人的,战争对人性的戕害从肉体而深抵灵魂,故乡在战争中已然崩塌,乡愁也在崩塌中滋生了了仇恨,“战争”也因之具有了外在与内在两个象征维度。在“故乡”与“战场”双向的冷漠、欺骗、欺压乃至侮辱的共同钳制与压迫下,外在的战争质疑了个人无条件服膺于国家民族利益的理所当然,而个人内心的挣扎则痛苦地否定了个人之于故乡传统的情感关联。在个体回归故乡的失望与逃离战场的质疑中,作为人类灵魂庇护所的故乡失去了拯救的意义,作为民族国家意义张扬的战场也没有赋予个人以崇高的价值,而这一双向的失效为修正个人、故乡与国家民族关系提供了一个重要而必要的前提。
三
如果说蒲丹的“重回故乡”是一具残破的躯体的痛苦,那么“他来了么?”的诘问则是永远无法魂归故里的悲哀。这部描写1885年塞保之战的小说虽非直接反思“一战”,但其在30年代译坛的“旧事重提”仍可看作是反思“一战”的余音。因为反思“一战”引发的“非战”思潮即是对所有战争的垂注,而并不局限于“一战”本身。与《重回故乡》注重以身体演绎战争的文学想象方式类似,这部“非战”小说对战争同样有着切身的体认。从译后记看,“一八八五年塞尔维亚与保加利亚之战时,跋佐夫亲到战场去看过,他对于塞保间兄弟之争非常痛心”。[10]
从小说的叙事结构看,《他来了么》同样是一个返乡的故事。母亲采娜盼着儿子司脱音战后回家,却不知他已战死他乡,因此,司脱音的返乡只是一个永远无法实现的愿望。在《他来了么》中,跋佐夫并没有刻意展现战争的伤痕,作品强烈的无奈感和悲剧性则是通过对归乡者的“等待”来予以演绎的。在这一充满希望、但已感无望却不愿相信的执著的“等待”中,人类的善良、被压迫、被凌辱、深感无奈的痛苦感被细致而深切地传达出来。这很容易引起国人的共鸣,因为对于深植着“叶落归根”的传统生命信仰的国人而言,没有什么比“客死他乡”更可悲、可叹的了。正如钱杏邨所说:“跋佐夫非常深刻的,细致的,凄凉悲恻的描写了母亲期待儿子归来的心理,妹妹冒着大风雪去山峰上等候哥哥的情形,使人读了非常的感动。我感觉到这不是一篇散文,这简直是一首抒情诗……跋佐夫就以这样的心情,母性的慈悲的情怀,在坚决的向战争提出抗议……”[14]透过《他来了么》中的空间设置,我们同样在故乡与战场对个体的空间争夺中,循迹到个人与故乡、国家关系的微妙变动。譬如,篇末“在毕洛特附近葡萄园里,司脱音的坟上,雪已经积成了堆了”[15]便将个人与故乡、个人与国家的关系生动譬喻为生存与死亡这一极具张力的空间叙事结构。也就是说,战争使故人客死他乡,个人与故乡的纽带关系被死亡所割裂;等待故人返乡的无着则预示着战争没有带来希望,只能带来死亡,而死亡同样质疑了个人之于国家的附属关系。《他来了么》不同于《重回故乡》主动对战争的复仇,它以一种被动的、甚至是略带“消极”的方式回应着人与国家、民族之间的某种理所当然的关系,在对战争的“凝视”中,“等待”所展现的朴实、善良的人性构成了对无视人性、扭曲人性的战争的“无声反抗”。与《重回故乡》在个人与故乡、战场间建立紧密的逻辑关系略有不同,《他来了么》的“无声反抗”的被动姿态使得三者的关系显得相对松散,而作品在生死维度上对“非战”的演绎则格外突出了个人之于故乡、国家的独特、神圣的生命价值与人性尊严。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演绎战争的极富艺术性的想象并不限于文本本身。因为作为一种跨文化实践,译介本身即是“种种外来及本地体制权利协商的过程”。[16]在《他来了么》被译介的过程中,强烈的个人人性吁求也是通过此种“协商”而得以落实的。作为“保加利亚文学史上的乔失(Chaucer,一般译作‘乔叟’)”,[10]跋佐夫尖锐的批判锋芒首先得到了受众的首肯。比如,从笔者现有的文献资料看,中国文坛对跋佐夫的译介最早可追溯到1911年茅盾对其名作《轭下》的翻译,在《世界文库》“第二年革新计划”中,编者不仅肯定了跋佐夫是“保加利亚民族第一个伟大的诗人和小说家。他不仅是民族革命的歌人,他又是实际行动的革命家……《轭下》中的那个乡镇Bela cherkva就是作者的故乡的化名”,[17]虽说这同样是一个“重回故乡”的故事,《轭下》的最后一章就是作者重回故乡苏保忒(Sopot)时的印象的回忆,[10]但是编者强调的仍然是“民族革命的歌人”“实际行动的革命家”等事关国家、民族、革命等的鲜明的阶级政治倾向,而故乡则反倒被淹没于革命之中了。但在十年之后当鲁迅翻译《战争中的威尔珂(一件实事)》时,译者就已开始注意到作家在革命之余对故乡真挚的情感书写,鲁迅说:“跋佐夫不但是革命的文人,也是旧文学的轨道破坏者,也是体裁家(Stilist)……他爱他的故乡,终身记念着……他没有一刻忘却巴尔干的蔷薇园。他爱他的国民,尤痛心于勃尔格利亚和塞尔比亚的兄弟的战争,这一篇《战争中的威尔珂》,也便是这事的悲愤的叫唤。”[18]从20世纪二三十年代国内对跋佐夫的译介看,⑤译作的选择及其受众也并不局限于革命政治的范畴,而显示出对作品怀乡情感的普遍关注与认同。那么在此接受背景下,当受众面对《他来了么》这部并没有特别突出、鲜明的尖锐批判性,甚至略带被动的、无声反抗的译作时,他们在反思战争的同时,显然也更容易转向对故乡、对普通人的生存境况的观察。个人生命的价值与尊严开始在战争中得以放大,个人与故乡、国家的关系得以重理。徐调孚在《反对战争的文学》中就说:“如果我们承认文学的目的是表现人生的,那么,无论你用什么方法去表现;写实也罢,象征也罢;总是扩大人类的欢愉或悲哀的同情,总有时代的特色、社会的环境做它的背景的。文学的使命,原是要引起读者的同情与慰藉,提高读者的精神与心境呀!”[19]
正因如此,我们发现这部“非战”小说并未随着反思“一战”热度的消减而逐渐远离人们的视线。《他来了么》自20世纪20年代由茅盾译介后,在30年代得到了持续的关注,直至40年代依旧热度不减。比如,20年代茅盾在《妇女杂志》上首译《他来了么》,数年后再次将该译作收入译文集《雪人》,并由开明书店出版。在30年代,《他来了么》的译作版本甚至激增到12种,延至40年代尚有9种之多。⑥这其中除了茅盾外,孙用是另一个重要的译者,他在1942年和1945年先后两次译介该作品。
一个有趣的事实是,译者依据的译本其实鱼龙混杂,甚至有些语焉不详,但这丝毫不影响该译作的热度。从“译者附识”的夫子自道看,这些译作大多以《保加利亚文选》为原本,譬如孙用在译文篇首就予以说明:“本篇自伊凡·克勒斯塔诺夫编译的世界语本《保加利亚文选》翻译。”[20]而茅盾最早的译文则是由Stayan Christoff的英译本转译。[10]那么,《保加利亚文选》中所选译作是否就是Stayan Christoff的英译本呢?因年代久远,原先的版本已难以见到,恐怕这只能暂时成为疑案了。即便在今天,仍有译者对当年茅盾的译作难以释怀,以致张冠李戴地误以为茅盾不过是“编了一个故事”,而自己所译才是正宗。⑦而另一个颇值得玩味的是,作为一部“非战题材”的小说,《他来了么》的翻译、发表并不限于文学类期刊,甚至包括宗教刊物、英文教辅乃至国文课本。譬如,王子美所译《他在来么》就发表在《公教周刊》上,这是闽南天主公教会马守仁主教主办,由当时在鼓浪屿天主堂任传道的李蔚如编辑,1929年4月由厦门鼓浪屿天主堂在福建鼓浪屿编辑并出版的宗教刊物。提倡的是救人灵魂、不干预政治、爱主爱国的宗教观点。[21]再如,王志强、罗书肆的翻译都有中英文对照,为的就是方便外语学习。而茅盾的译作更是入选了顾颉刚、叶绍钧编的《新学制国语教科书》。⑧我们知道,无论声称要拯救人的灵魂的宗教,抑或塑造人的灵魂的教育都比其他的教化方式更注重人性与普世的价值情感。而《他来了么》也正是因为其以文学想象演绎了战争,透视了生命价值、人性尊严,所以才能够让不同的受众趋之若鹜,《他来了么》成为宗教与教育的宠儿也就不足为奇了。
20世纪30年代事关战争的“乡愁小说”的热译并非偶然,除了对弱小民族的同情外,因战争而引发的个人与民族、国家关系的重识显然对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精神文化结构更具建设意义。我们知道,中国人的家、国观念深受儒家思想影响,譬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22]就是对个人、家/故乡、国家关系的经典表述。梁启超曾说:“吾中国社会之组织,以家族为单位,不以个人为单位,所谓家齐而后国治是也。……舍家族制度外无他物,且其所以维持社会秩序之一部分者,仅赖此焉。亦可见数千年之遗传,植根深厚,而为国民向导者,不可不于此三致意也。”[23]但恰恰是战争动摇了这一超稳态的精神文化结构,一方面,战争造成的现实与精神空间的暌违,由此生发的乡愁再次将“五四”以降“救国保种”的集体性的政治吁求拉回到了个人化的、更具普遍意义的人性本身,即对人的价值与尊严的肯定与尊重;另一方面它又“逼迫”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去重审个人与家园/故乡,直至国家的关系,即如何在家、国的伦理价值框架中安放个人的理想与信仰。而时值20世纪30年代,随着对“一战”的深切反思,“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经典历史叙述显然已难以完全诠释国人对现代国家民族精神的诠释与期待,而这一省思与变迁恰是从“传统乡土”中“国”对“家”强势压迫性结构的松动开始的。生命个体内在的“陆沉之感”,不仅是内在的人性尊严被漠视的焦虑,更是外在的个人与民族、国家关系的危机,它不仅推动了现代乡土意念的衍异,同时也开始形塑现代知识分子民族国家认同的身份建构与认同。
注释:
①参见潘莱士:《禁食节》,沈雁冰译,《小说月报》1921年第7期,后收入莫尔纳:《雪人》,开明书店,1928。原作者Isaac Leib Peretz(1851—1915),通译佩雷茨,波兰籍犹太作家,是现代犹太文学的奠基人之一。
②此处存疑,未查到相关作品,只在《文学》153期的目录处有“复归故乡,玄译,但文献只有三页,未见作品”。参见拉兹古:《复归故乡》,《文学》总第153期。
③版本如下:拉兹古:《重回故乡 非战小说集》,蒋怀青译,湖风书局,1933;拉兹古:《重回故乡》,蒋怀青译,复兴书局,1936。
④保尔·安泽、米夏埃尔·拉姆贝克:《紧张的过去:关于创伤与记忆的文化文章》,转引自阿斯曼:《回忆空间:文化记忆的形式和变迁》,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第7页。
⑤20世纪二三十年代国内译介跋佐夫的作品主要有:跋佐夫《在毗伦山中》,波云译,《东方杂志》1923年第3期,“毗伦山(Pirin)”即皮林山脉,位于保加利亚西南部;跋佐夫:《失去的晚间》,胡愈之译,《小说月报》1923年第1期;跋佐夫:《草堆》,浦行帆译,《东方杂志》1929年第16期;跋佐夫:《星:东方的传说》,南池译,《新女性》1929年第5期;跋佐夫:《倔强的人》,马风(卜英梵)译,《东方杂志》1930年第7期;跋佐夫:《约佐祖父在望着》,北冈译,《小说月报》1931年第3期;跋佐夫:《残废者》,索林译,《春光》1934年第1期;跋佐夫:《乐乍老头子在看着》,梭甫译,《文学》1934年第5期;跋佐夫:《村妇》,鲁迅译,《译文》1935年终刊号;跋佐夫:《在缪丝的园里》,颐荪译,《青年界》1935年第5期。
⑥四十年代的译介情况如下:跋佐夫:《他回来了吗》,王岑译,《中国公论》1940年第5期;《他来了吗(未完待续)》,璇译,《破浪》1941年第2期;跋佐夫:《他来了吗》,孙用译,《文艺生活》1942年第6期;跋佐夫:《他来了吗(中英文对照)》(连载),长贞译,《吾友》1942年第7、8、9期;跋佐夫:《他回来了吗》,唐茜译,《文艺新哨》1942年第5期;跋佐夫:《保加利亚小说选 他回来了吗》,周国棨译,《吾友》1944年第19期;跋佐夫:《他来了吗》,孙用译,《联合周报》1945年第13期;瓦左夫:《翻译 他回来了吗?》,斤斤译,《读者》1948年第4期;Ivan Vazoff:《他回来了吗(中英文对照)》,曾海如译,《建国月刊》1948年第1期。
⑦譬如,余志和在“朝内166文学公益讲座”中称:“茅盾不是逐字逐句翻译,而是编了一个故事,我在书中把它翻译成《硬汉一去不复返》。”参见http://m.sohu.com/a/240331854_701664,但在发表于《文艺报》的署名文章中却删去了如上这句话。在其编译的《硬汉一去不复返》中却署名柳本·卡拉维洛夫,由此可见余志和谈及《他在哪儿》与《硬汉一去不复返》为同篇小说当是讹误。参见余志和编译:《保加利亚中短篇小说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余志和:《希望引起中国读者的共鸣:我译〈保加利亚中短篇小说集〉》,《文艺报》2018年7月9日第7版。
⑧参见顾颉刚、叶绍钧:《新学制国语教科书(第五册)》,胡适、王岫庐、朱经农校订,商务印书馆,19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