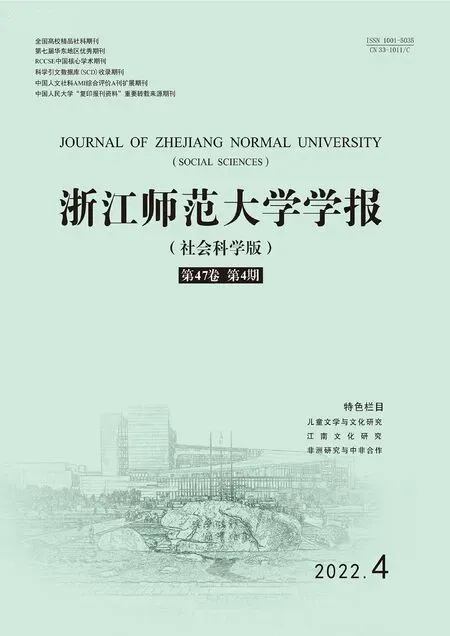论陆游题跋的追忆书写
——兼论题跋的时间指示性
王润英
(中国社会科学院 文学研究所,北京 100732)
题跋是勃兴于宋代的特殊文体,折射出其时学术文化的全面昌盛和文人士夫丰盈的精神世界,目前已吸引不少论者的眼光。在热门的北宋学术类题跋代表欧阳修和文学类题跋代表苏轼、黄庭坚之外,陆游作为南宋的题跋大家,近年来颇受关注。然而相关研究多从文本的题材内容、表述方式及其展现的文化意蕴诸方面定位陆游题跋,①尚处于描述表层。我们认为,观照陆游题跋中极具特色的追忆书写或能深入把握此论题,并藉此真正标的陆游在题跋文体上的位置,推进对长期以来讨论不足的题跋文体特性的深度感知。 陆游题跋收录于其自为编定的《渭南文集》,凡六卷258则,②约占其散文总量的四分之一,此数量放诸南宋亦相当突出。但陆游题跋最特别之处更在于其中大量的追忆书写,即借由题跋对象引出对旧事故人的怀想,有时甚至毫不顾及题跋对象,展现出对文本强烈的主体掌控。事实上,学界对陆游诗歌中频繁的回忆已有觉察和论析,③值得注意的是,进入文章世界后,虽然《渭南文集》共收录陆游创作的11种文类,但追忆书写却成规模地出现在题跋里。单从题跋相对其他文体较少体制规约而更便于主体的自由表达等易见因素去考量,显然不足以解释此种现象。那么,陆游的追忆书写与题跋文体之间究竟存在何种深层的联系?这种联系包括追忆如何进入题跋,在进入之后又怎样在文体规约下开展、结构而呈现最终的文本等,这些问题是本文讨论的重点。
一、顺应与搭载的选择:进入追忆的方式
对题跋的界定,历代诸说中最清晰者当为明代徐师曾《文体明辨序说》:“按题跋者,简编之后语也。凡经传、子史、诗文、图书之类,前有序引,后有后序,可谓尽矣。其后览者或因人之请求,或因感而有得,则复撰词以缀于末简,而总谓之题跋。”[1]这段话交待了题跋的依托对象、写作缘由和文本所处的位置。然而在离开题跋书写的历史现场后,其中最易被忽视的是,题跋并非凭空而起,它是题跋作者在观览一个具体对象或媒介物之后产生的。而后览的行为本身暗含了一种时间差,即题跋撰作并非伴随所题对象产生而进行的共时性写作。即便古人在游宴场合,可能一人或多人作书作画并预留出空白的文本位置,其他人很快在后面题跋,其中仍然存在程序的先后;而更多时候,题跋书写面向的往往是“旧时之物”。旧物仿佛信使,天然携带来自逝去光阴里的复杂信息,或者说它其实指向了旧时光。题跋既然在观览旧物后写成,便意味着题跋作者从书写之初即面临旧物带来的时间提示。但在题跋撰作实践中,它仍然只是明显的可选项,是否接收提示而进入对旧时的追忆书写,需要考虑题跋作者的主体选择。
陆游性分敏锐易感,朱熹称之具难得的“诗人风致”(《答徐载叔庚》)。[2]在其漫长人生里,历“庆元党禁”“开禧北伐”等多番国家动荡,从幼年奔窜避祸,到中年辗转远游,尤其在晚岁退居山阴后长达二十年的时光里,陆游总是以追忆的方式反复咀嚼和回味过去。正如研究者所论,他亦擅长利用深情的审美追忆,形成一种艺术思维方式行于笔下,他的诗歌晚年创作最丰,充满动人的追忆之作。[3]事实上,陆游的绝大部分题跋亦作于退居家乡之后。可以想见,当有着强烈追忆需求、惯于且长于追忆的陆游与自带旧时提示的题跋文体相遇,等于双向信号成功接通,他在题跋中随旧物提示进入追忆书写,自有不言而喻的默契。题跋作者与文体之间的奇妙契合,促使陆游笔下呈现出以往题跋文本都不曾出现的追忆书写景观。这种特出的景观不只在于陆游题跋显眼的追忆书写规模,更在于陆游撰作题跋时如何进入追忆,而后者是达成前者的关键。按照西方的理论探索,回忆特别是审美回忆应是“思的聚合”,[4]要重新开启或聚合被时光掩藏到后台的漂浮之“思”,需要媒介的召唤。陆游撰作题跋时,在旧时之物这个理想触媒下,顺应提示直接进入追忆书写,是最便捷也最常见的方式。
其中一类乃读书览画等文人日常中因感题跋。如隆兴元年(1163),32岁的陆游于镇江任上读到杲禅师所作《蒙泉铭》,跟随这篇旧铭,在题跋中忆及年少时过郑禹功处和杲禅师有过的一面之缘,继而想起自己当年在座上醉饮阔论的洒爽轻狂。(《跋杲阐师〈蒙泉铭〉》)[5]138-139又如淳熙八年(1181),陆游在山阴故庐中统得家藏旧籍《朝制要览》,故于题跋里忆起父亲陆宰晚年喜读此书,常为子弟讲论因革直至夜分的情形。(《跋〈朝制要览〉》)[5]157绍熙元年(1190)正月,陆游夜阅故书,嘉泰四年(1204)再曝此书,因此在题跋里念及南郑时的同幕好友和曾经跨马呼鹰的前线岁月。(《跋陕西印章》)[5]199
另一类则是应他人之请而题跋。如乾道七年(1171)时任夔州通判的陆游因事偶至卧龙山咸平寺,寺中长老预备将《关著作行记》刻石,故向陆游请题。陆游在题跋中遂忆起行记作者关耆孙出使硖中时震栗众人的风采和对陆游独独厚遇的情谊。(《跋〈关著作行记〉》)[5]150而嘉泰元年(1201),已是77岁的陆游收到昔日老友张维之子寄来一轴《槃涧图》求题,于是借题跋怀念与张维自福建时“朝莫相从”到张去世二十余年间书信不断的深厚交谊。(《跋〈槃涧图〉》)[5]251-252不论因感而题或是应人请题,旧籍、古画甚至老印章等这些作为题跋媒介的旧物总是将陆游的思绪情感带至幽远的昔日,他在撰作题跋时顺应提示便轻易叩开了记忆花园。
值得注意的是,虽偶有枝蔓,陆游众多顺应旧物提示而进入的追忆书写却总是指向相似或同质的方向,展现出其生命中最关切的人事和最深重的情感所系:国家恢复与亲人挚友。关于前者在陆诗中的饱和程度,正如钱锺书先生《宋诗选注》描述:“他看到一幅画马,碰见几朵鲜花,听了一声雁唳,喝了几杯酒,写几行草书,都会惹起报国仇、雪国耻的心事。”[6]同样的道理,当对国家恢复和亲人挚友的关怀浓烈至一定程度,陆游在撰作题跋时,进入追忆书写的方式就不再只是顺应媒介旧物的提示,我们甚至能从顺应中见出他有意无意地搭载媒介旧物,将追忆拐向内心牵挂的主题。
陆游曾为陈师道《后山居士诗话》作跋,文章从当时流传的“《谈丛》《诗话》皆可疑”起,前段对《诗话》来历真伪作一番论辨,后段却突然转向,不叙诗话作者陈师道,而是跳至与题跋对象不相干的陈之二子陈丰与陈登。读完全文方能明白,原来二子中的陈登曾于过江为李邺之摄局时因李降金受牵连被驱以北。(《跋〈后山居士诗话〉》)[5]165陈登不过三试不第、贫窘中因父得官的普通官吏,[5]166亦不见与陆游有过从,此跋从《后山居士诗话》绕到忆陈登,陆游所申之事无非金人入侵而致南北隔阻。又如《跋〈临汝志〉》,陆游在为这部淳熙年间编刊的地方志作跋时,全文追忆欧阳澈。欧阳澈曾于金人犯阙时上书请使金庭,建炎初再上书极诋用事大臣误国,年三十一而抗言被杀。《临汝志》非欧阳澈编撰,二者唯一的关联即后者乃临川人,在众多的临川人中独忆其人其事,足见陆游搭载《临汝志》记录主战忠臣的偏好选择。[7]23
相对于国家恢复,陆游对亲人挚友的系念较少被讨论,但从其题跋的追忆书写来看却是另一不容忽视的主题。陆游题跋多次顺应旧物提示进入追忆书写,皆转向了对亲人挚友的追念。《渭南文集》中有明确日期标注最早的一篇题跋是陆游31岁时所作《跋尹耘师书〈刘随州集〉》,彼时陆游仅追记《刘随州集》的得书经过;然而到绍熙元年(1190)再跋时,却补记手抄该集的尹耘师乃其乡里前辈,曾经“与九伯父及先君游”,通过“与游者”最后绕到亲人上。[5]136又如嘉泰二年(1202),陆游为洪兴祖之帖作跋,跟随旧帖走进回忆,却主要记自己儿时在丹阳先生门下和友人许子威亲如兄弟的美好时光,题跋末才交待洪兴祖只是许子威曾言及的一位有学行的人。(《跋洪庆善帖》)[5]259
顺应旧物提示而进入追忆书写,陆游仍会在题跋中不时拐向他最关切的方向。事实上,由于题跋内设的时间指示性,顺应提示进入追忆书写变得极为容易。基于此,题跋的这种文体特性也往往被题跋作者所利用。从陆游的题跋中可见,很多时候他并不只是被动顺应,或者顺应后再变化方向,而是主动利用题跋内设旧时提示的文体优势,不露痕迹地搭载题跋进入追忆书写,以顺利抒发和展现他的心之所系。并且,陆游有大部分题跋并非因人之请而是因感而发所作,此种情况下,甚至题跋对象也可以自主挑选。如淳熙三年(1176),刚经历了罢官风波、在失望无奈的心绪下自号“放翁”的陆游,于重阳这个特殊的日子又捧起得自蜀中的《温庭筠诗集》,此集曾为其父陆宰旧藏。(《跋〈温庭筠集〉》)[5]163显然,这是漂泊异乡又仕途受挫的陆游主动选择能与旧时发生勾连的特定载体,在题跋的追忆书写中搭载对父亲的怀念,也让内心暂有停倚。
开禧三年(1207)正月,距韩侂胄请下诏伐金已半年有余,北伐战事正吃紧,朝中仍有反对北伐的主和派,陆游连续为《周侍郎奏稿》及周侍郎《寻姊妹帖》作跋,前者忆年少时所见,和父亲往来的贤公卿们“每言及高庙盗环之寇、乾陵斧柏之忧,未尝不相与流涕哀恸。虽设食,率不下咽引去。先君归,亦不复食也”(《跋〈周侍郎奏稿〉》)。[5]307-308后者则记建炎多故时,“群盗如林,士大夫家罹祸,有尽室不知在亡者”(《跋周侍郎〈寻姊妹帖〉》)[5]309-310的悲惨情状。接连两篇跋文,陆游皆是在特殊关头选择适宜的题跋对象,以顺利展开对往事的追忆,搭载其切望彼时国势危蹙下士大夫皆能振起捍虏的焦灼和愤慨。从这个意义上看,内设旧时提示的题跋,仿佛是为陆游提供的一叶可以自由搭载的时光之舟,通过它能穿越时空与往昔再度相遇。可以说,从顺应提示到主动搭载,陆游最大限度地发挥了题跋时间指示性的文体特性,也因此得以在题跋中构建一个丰富的追忆书写世界。
二、“昔”与“今”的排布:开展追忆的技巧
无论顺应或是搭载旧物提示,作者在进入具体的题跋撰作后,如何开展追忆书写便成为关键。事实上,以旧物作为题跋对象,它一方面提示着过去,另一方面旧物本身即是连接当下与过去的线索。因此追忆书写总是存在隐形的参照原点,总是可以回落到时间的标尺上与参照原点相互观照和对话。正是在这种今昔相看中,追忆书写的意义才得以实现与彰显。换句话说,题跋中追忆书写如何开展的问题,也即是如何排布追忆书写中的“昔”与隐形的可参照的“今”之间的问题。落实到题跋撰作中,便包括在追忆书写中如何安排往昔内容的比重,往昔和隐形的参照今日之间如何产生关联,二者在怎样的空间里相互观看,“昔”与“今”如此腾挪又能助力呈现怎样的表达效果等,这些问题,并非借助以往粗简的“今昔对比”就能涵容和诠释的。
陆游题跋中的追忆书写,始终存在两个参照原点,围绕人生的“今夕”和围绕国家的“当时”。在这两个参照原点分别后退的时间标尺上,停落着陆游无比丰盛的往昔追忆。以下为方便讨论,将分别从这两组时间标尺来考察陆游题跋对追忆书写的开展。
首先是人生的时间标尺。陆游的亲人朋旧多出现在这组标尺上。开展追忆书写时,陆游往往将题跋的全部篇幅分配给往昔追忆,着意记录与其个人生命史有交集但不一定拥有声名的亲友。并且考虑到题跋“缀于末简”的位置不宜长篇大论,故常采用梗概或截取代表性侧面的方式来呈现追忆对象。前者最典型的如陆游为外兄王正夫所著《三近斋余录》作跋,以极简之笔留下对正夫的介绍:“正夫名从,元丰中书舍人震字子发之子,仕至上饶守云。”(《跋〈三近斋余录〉》)[5]289后者使用面更加广泛,如陆游在《跋世父大夫诗稿》和《先左丞〈使辽语录〉》中追忆三十八伯父陆宦,皆把握住伯父令人称奇的特点,即虽然自幼染末疾只能左手钞书但笔力清健;[5]174、314在《跋〈之罘先生稿〉》和《跋蔡肩吾所作〈蘧府君墓志铭〉》中忆及蜀中莫逆蔡迨时,又两回皆叙蔡迨在调任桂阳令途中染暴病一夕而亡、令人难以释怀的悲剧。[5]192、212把题跋的文本空间完全留让给往昔,作为参照的今日始终在题跋正文之外,处于隐形状态。如此布置,既能以尽可能多的笔墨叙述追忆对象,在书写态度上也显得更加客观,陆游仿佛静默在题跋落款里的史家,此类题跋亦具有了人物小传的意义。
如前所述,陆游的题跋多作于晚年,自淳熙五年(1178)从蜀地归山阴后,其老友故旧相继离世,高寿的他眼见故人凋零,悲痛中难免思及自身。反映到题跋中,则可见陆游在部分追忆书写中虽将主要篇幅留给往昔,但总会在最末不自觉地引入参照的今日。作于嘉泰三年(1203)的《跋范元卿舍人〈书陈公实长短句〉后》,面对陈公实郎君所出范元卿手书卷轴,陆游忆起绍兴间自己十六七岁即与陈公实等作六人游,公实还称其“小陆兄”,此种“联杖履、均茵凭”的景象尚在睫前,然六十余年间,六人中五人竟已离世,陆游在题跋中不觉写下“予年七十九”,太息弥日。[5]270如果说陈、范等人与陆游兄长同场屋,年纪稍长,那么和陆游年龄接近且多年往还不断的老友,则更使他不由地想到自身。此跋作后第二年嘉泰四年(1204),比陆游小一岁的周必大去世。陆游与周壮年时相识于高宗绍兴朝——高宗曾对陆游有知遇之恩,绍兴朝亦数次作为盛世的象征出现在陆诗中:“高皇昔中兴,风雨躬沐栉。”(《岁暮感怀以余年谅无几休日怆已迫为韵十首》其七)[8]“高帝中兴万物春,青衫曾忝缀廷绅。”(《望永思陵》)[9]“贞观开元嗟已远,为君试说绍兴初。”(《山墅》)[10]——周必大在陆游的绍兴朋旧里最晚离世,对陆游来说其离世实更有连同盛世远去之感,令他无限悲恸和失落。因此当开禧二年为《周益公诗卷》作跋,追忆起和周必大的相交过往时,陆游不免也想到自己的限期:“今益公舍我去,所不知者,相距几何时耳。”[5]306开展追忆书写时,在主要叙述往昔内容后引入参照的今日,虽然只需寥寥几笔,却使往昔与原本隐形的参照今日处于同一文本空间,一方面由于省略掉“昔”与“今”中间漫长细微的动态量变过程,将“今”“昔”两种悬殊的情态并置,能产生巨大的情感张力;另一方面也提供了“今昔互看”的视角:今日之我在追忆中回望昔日,又通过昔日的镜子重新看到今日之我,留下思绪和情感的余韵。
其次是国家的时间标尺。执着于国家恢复且频繁行之笔下,是作家陆游的重要特点。在其题跋的追忆书写中,人生时间标尺以外,围绕国家的时间标尺自难忽略。在这组标尺上,陆游总是追忆起许多前朝人物。如嘉泰四年(1204)陆游作《跋韩忠献帖》,忆北宋名臣韩琦:“方曩霄犯边时,忠献公首当御戎重任,功冠诸公。后入辅帷幄,陈谟画策,驾驭人材,镇服虏情,自曾集贤以降,皆协赞而已。”[5]276在追忆书写中主要叙往事,丝毫不引入可参照的当下,但言辞里满是对韩琦的推赞尊崇。又如嘉定二年(1209),已行至生命最后一年的陆游作《跋傅给事帖》,忆傅崧卿等绍兴初士大夫:“绍兴初,某甫成童,亲见当时士大夫相与言及国事,或裂眦嚼齿,或流涕痛哭。人人自期以杀身翊逮王室,虽丑裔方张,视之蔑如也。卒能使虏消沮退缩,自遣行人请盟。”[7]21跋文前段充满情感地描摹当时主战派的生生群像,后段悲愤指斥秦桧掠以为功,变恢复为屈辱的和戎,使志士仁人抱愤入地,将最大的文本容量留给往昔追忆,明显的褒贬态度亦贯穿全文。联系两文的撰作背景,作前文时陆游已得闻宋廷意欲北伐(《睡起已亭午终日凉甚有赋》),[11]作后文时距北伐失败逾二年,可知陆游在追忆书写中同样以往昔内容为主,不引入参照当下,却增加感情色彩和意图指向,今昔内容如此排布,就不仅是人生标尺上对亲友故旧人物小传似的着意记录,更是在借助追忆前朝人物倾吐胸臆和抱负,在围绕国家的时间标尺上唤醒历史上与其心意相通的理想符号。
国家的时间标尺上,当时之南宋是陆游始终无法放下的重石,其题跋的追忆书写在涉及相关内容时呈现出今昔内容排布上的变化。庆元改元(1195),陆游作《跋张监丞〈云庄诗集〉》:“虏覆神州七十年,东南士大夫视长淮以北,犹伧荒也。以使事往者,不复黍离、麦秀之悲。此张公为使官赋诗,忠义之气郁然,为之悲慨弥日。”[5]220全文皆叙当时南宋士大夫偏安的情状,虽只字不提往昔,但“虏覆神州七十年”一句却分明指向对宋室南渡前的追忆。类似的写法,还有《跋吕侍讲〈岁时杂记〉》。《岁时杂记》乃吕希哲记故都节物及中州风俗的一部著作,陆游跋文针对其时士大夫安于江左,难求新亭对泣者的状况,谈及此书的意义:承平无事时,对于这些人尽皆知的常识似不必记,但“自丧乱来七十年”遗老凋零后则知其不可阙,追忆的思绪自然拉回到丧乱之前。而《跋〈嵩山景迂集〉》中,陆游又借《嵩山景迂集》中一句诗因涉故都之事在当时变得难解,叹息“丧乱隔绝,南人不复知”,以此牵动对故都的追忆。显然,在追忆故国故都时,陆游注意到了时间标尺上可参照的今日,并打破常规将隐形的参照今日作为追忆书写的主体,通过“虏覆神州七十年”“丧乱隔绝”等具有时间切分意义的词句打开微妙的豁口,以引导追忆。如此排布,即便往昔在题跋文本中并不出场,也能从当下截然不同的变迁中遥想一个可能回不去的深广往事时空。
现实的情况是,在陆游的生命中,人生和国家的时间标尺实难泾渭分明。壮年时去到南郑,他曾无限接近过恢复国家的理想,此后留下半生追忆。晚年何曾预料再遇开禧北伐,却不为所用。彼时陆游为老师曾几的《曾文清公奏议稿》作跋,跋文前段追忆绍兴末金兵入塞时,年逾七旬的曾几聚族百口未尝以为忧,而忧国深重;后段转向四十七年后宋廷北伐讨金,年过八十的自己却不能上前线杀虏,愧而嗟叹:“真先生之罪人也。”[5]301原本隐形的参照今日再被引入追忆书写,与往昔处于同一文本空间相互比照并且容量相当,将陆游二度与理想擦肩而过的失落展现殆尽。人生和国家的时间标尺在陆游这里又继续平行下去,并且这两组平行线又都将走向终点。此文作后的次年即开禧三年,陆游在《跋〈刘戒之东归诗〉》中追忆起当年在南郑王炎幕中的同舍好友,从“乾道中”十四五人,到“开禧中”张季长和陆游尚存,再到“今春”独剩孑然的自己,陆游又在追忆书写里将往昔切分成多个有意味的时间单元,它们逐次掉落到时间的标尺上,将时间的紧迫感和挤压感突显出来,恢复国家的愿望随北伐失败遥遥无期,而人生之限的脚步正迫促赶来。通过“昔”与“今”的花式腾挪排布,陆游题跋中的追忆书写得到了极致化的开展。
三、暗示与明言的设置:传递追忆的结构
题跋基于一定的载体或媒介物而写成,实际上意味着媒介物始终保持着开放的姿态和结构。它对首次题跋者是敞开的,同样对二次、三次甚至跨越时空的未来题跋者皆是公平敞开的。题跋从撰作之时起即处于这种自体开放的结构当中,所以题跋作者对可能出现的未来题跋者(也是读者)很难不会有所预料。陆游题跋的追忆书写自然也属于此范畴,它联系着过去与当下,作者也已经预见到未来的存在。反映到具体的题跋撰作,则呈现为陆游在追忆书写中主动留下可以引发他人参与和回应的结构,设置暗示乃至直白的明言,向来者发出邀请,以各种方式试图使追忆书写携带的信息穿越时空一直传递。
题跋的撰作以文字与来者发生交流,实际上贯穿着文人之间默默的心灵碰撞与智力交接。要在题跋中展现开放的文本结构,呈现邀请的态度和引导的意图,相较于直白的明言,带有适当接受“障碍”的暗示能产生更好的效果。它既引发来者探索的热情,又使他们在跨越“障碍”后收获知音相接的会心体验。陆游题跋的追忆书写,为传递追忆信息,正是在文本结构的暗示设置上极尽变化。
首先是在题跋的结尾处作文章,以提问的方式向来者发出对话邀请,如此便将原有的文本结构完全打开。如《跋朱新仲舍人自作墓志》,陆游全文追忆朱翌于秦桧擅权之时持守正气竄避峤南十余载后自识其墓,在文末又设问道:“向使公谄附以苟富贵,至莫年世事一变,方忧愧内积,惟恐人道其平日事,其能慨然奋笔自叙如此乎?”[5]240答案自然是否定的,几乎不容来者产生任何质疑,但以提问的方式打开文本结构后,陆游的追忆就不再困顿于原文,还将随着引导而来的来者的认同甚至继续书写而延续和生长。此外,在《跋朱希真所书杂钞》中,追忆朱敦儒等诸贤于建炎间裔夷南牧、群盗四起时仍相与讲学之事后,陆游于跋文末问道:“吾辈生平世,安居乡里,乃欲饱而嬉,可乎?”[7]12以及《跋韩立道所藏〈兰亭序〉》里借观书帖引出对西汉丞相王商于未央庭中见单于之事的追忆,且在末尾问:“虽单于不觉自失,况余子有不汗洽股栗者哉?”[5]300个中设置有异曲同工之妙,皆以提问敞开文本结构,静候更多认同意见加入追忆。
文末设置的提问有时更会升级为无望中对未来知音的呼唤,如前引名篇《跋傅给事帖》。陆游在追忆傅崧卿等绍兴初主战派后,跋文末哀恸而问:“今观傅给事与吕尚书遗帖,死者可作,吾谁与归?”时运而往,在北伐失败、朝中主降派当道的嘉定二年,士大夫心气衰颓,实难寻得如傅崧卿等人那般的同道知己了。失望的陆游以问题的方式结束此跋,但又借提问敞开文本结构,把期待留给更遥远的未来。更为有趣的是,在《跋张魏公〈与刘察院帖〉》中,陆游还将文末设置的提问折返,直接向追忆对象发问。此文正文追忆名臣张浚并展开评论,而针对自己的此番评论,陆游在文末设想能和张浚对话:“使御史公无恙,得予此说,其将以为能知言乎?”[5]314独辟蹊径的一问,文本结构被成功打开,并且因为首先向追忆对象提问,等于获得了权威认可,而把同样的问题再抛给未来读者时,自然比通过陆游本人提问更能获得他们的信服和跟随。
其次,已有研究者注意到陆游题跋中强烈的情感表达,然而更准确的是,陆游题跋尤其是题跋中的追忆书写整体弥漫着悲伤的情感;这或许源于追忆行为本身总是关涉遗憾,[12]但从书写的角度来看,亦可见出陆游在文本结构设置方面的特点。即在题跋结束时表达传播力极强的悲伤慨叹,④“悲乎”“可悲也”“为之涕下”“太息不能自已”等词句在其跋文末尾随处可见,这些悲伤情感具有能够继续流动扩散、溢出原文的特点,方便打开文本结构,引导和触发未来读者相似的情感体验。陆游追忆书写中的悲伤慨叹,有来自国家经历丧乱剧变后的今不如昔,如《跋张监丞〈云庄诗集〉》,面对宋室南迁七十年后东南士大夫对故国的淡忘,当读到诗集中张监丞为奉使官属时所赋的数十篇诗歌,感受到久违郁勃的忠义之气,陆游难以抑制内心伤悲,“为之悲慨弥日”。又如《跋韩干马》,陆游观韩干所绘,联系当时南渡将八十年而秦兵洮马不复可见的情形,从而忆及北方沦陷的故土,“殆欲霣涕矣”。文末真挚的悲伤慨叹作为打开文本结构的情感暗示,极易引发来者的认同和反馈。国家而外,陆游跋文末尾的悲伤慨叹亦来自对他人悲惨遭际的同情或共情。如对《跋蔡肩吾所作〈蘧府君墓志铭〉》与《跋〈之罘先生稿〉》中得官不易且于就任途中暴病而亡的蔡迨,陆游分别在两篇跋文末以沉重的“每念之,未尝不流涕也”与“哀哉”表达对莫逆中道奄忽的哀恸;《跋〈三苏遗文〉》里,又对故史官周辅虽得唐安守而归、然未至家却暴卒之事叹息曰:“可悲也。”[5]179悲慨在文末戛然而止,却将情感蔓延到文本以外,召唤来者的聚集和新文本的接续。
最后,时光易逝、亲朋凋零以及理想终归于失落,是陆游题跋追忆书写中最深重的悲慨。这类涉及个人切身经历的永恒话题在历史中无数次重现,每个时空里都能找到它的影子,因此也最有可能收获读者的回音。如《跋〈京本家语〉》,《京本家语》本是陆宰从故都携来,中遭兵火与虫龁鼠伤后好不容易缀辑修复。当陆子聿于五十七年后再次装辑,陆游在这部传递了三代人的书中又见到父亲所书的题跋,且在其后续题,文末曰:“方先少保书此时,某年十四,今七十矣,不觉老泪之濡睫也。”[5]213-214将几十载时光人事的悲慨凝在泪水濡睫间,使高饱和的情感在文本结束后仍然延续。而追忆六十年间相继离世故友的《跋范元卿舍人〈书陈公实长短句〉后》,则几乎暴露了陆游这种情感引导暗示的有意设置。跋文原可在“为之太息弥日”的悲伤情绪中结束,但陆游又添加“虽然,使死而有知,吾六人者安知不复相从如绍兴间乎?会当相与挈手一笑,尚何叹?”显然已预料到读者对文末设置的情感跟随,于是将自我开解的想法也一并无保留地付予未来的知音。开禧北伐之时陆游作《跋〈曾文清公奏议稿〉》,又在终生理想无法实现的内在伤悲上,加码愧对先生厚望的自我深责,文末“真先生之罪人也”一句将志向难酬的郁恸推至顶点,打开文本结构,同时也埋下连接古今相似情感的线索。
古代绘画发展到宋代,逐渐走向尚意,重视留白,宋代绘画文本系统也因此具有极大的开放性,研究者认为这是宋代绘画题跋兴盛的重要原因。[13]事实上反之亦然,形制简约的题跋,若考虑对读者的导引,追求文本的开放,那么在文本结构上适度留白是题跋作者能够尝试的突破口。陆游题跋的追忆书写注意到此点,不限于在题跋结尾处提问和作悲伤慨叹产生情感导引,还通过设置文章结构的留白,给来者以暗示。
首先是跋文与落款之间的留白。在《跋〈秘阁续帖·张长史率意帖〉》中,陆游于正文追忆其年少时,曾在故签书枢密王伦家得见其出使时从故都带回的张旭《率意帖》,从文本意义上看属于完整的往事追忆;然而在落款中,陆游又写道“时年六十有六,距初见时四十有五年矣”。于是结合前面所读的正文,方才将作者之意连缀起来:宋廷南渡多年,自己已从少年变为老翁,而复国的理想何时才能实现?在跋文和落款间留白,等于为未来读者设置谜题,留下吸引他们去衔接和探索的部分,在此过程中题跋的文本结构即被打开。
其次是题跋正文内部的留白。《跋〈之罘先生稿〉》里,陆游于正文中记蔡迨的悲惨遭遇,文末却突然旁逸:“嘉父,犍为人,肩吾没后数年,始以进士起家。”只交待蔡迨和这位嘉父唯一的联系是,前者去世数年,后者才以进士起家,但嘉父是谁,他和蔡迨究竟有何关系,陆游为何要在此文中言及嘉父,这些信息读者读完此文后皆不可知。直到我们读《剑南诗稿》之《次韵杨嘉父先辈赠行》,中有“嘉客如晨星,俗子如春萍”句,[14]方知杨嘉父和蔡迨皆是陆游的老友,将貌似无关的二人置于同一篇题跋,意在传达易逝生命时光里朋旧散落如晓星的悲愁。
最后是跋文与跋文之间的留白。陆游78岁时曾为高宗御书作跋,文中追忆其求学云门时初次见高宗御题以及绍兴三十二年(1162)得面孝宗而蒙恩赐同进士出身一事;81岁开禧北伐前,陆游再次为此幅御书题跋,文中则记施师点得到善于用人的仁祖高宗重用却早逝的悲剧。[5]131-133前后两跋追忆毫不相干的二人之往事,需要读者两相参看,填补陆游预留的文本结构空白,方知施师点之事只是一种类比寄托,陆游所伤乃为其人生将近终点而不得用,抱负再难施展。
暗示的设置在于触发未来读者的心领神会和情感默契,文本结构通过适当的游戏障碍而敞开,使得陆游题跋的追忆更加顺利地被交接和延续。然而在非常之事上,将暗示设置运用得异常娴熟的陆游,却主动舍弃操作技术的便利。如在《跋东坡帖》中,陆游追忆汪应辰敢于忤秦桧意,不以一身祸福易其忧国之心,深受汪氏生气凛然的意气感染,针对南宋当时令人失望的士风,陆游直白地呼吁“忠臣烈士,所当取法也”,并命其子将汪所刻东坡帖再求善工坚石刻之以传天下。[5]248又如《跋〈周侍郎奏稿〉》,忆及建炎间内平群盗、外捍强虏的士大夫,陆游直接阐明作跋的意图:“某故具载之,以励士大夫。倘人人知所勉,则北平燕赵,西复关辅,实度内事也。”[5]307对未来读者如此直白的明言,在书写上并不算巧妙,但针对非常事、非常时,真挚强烈的情感总是胜于花哨的书写技术,并且依然能够超越文本结构,带给读者震撼人心的力量,传递陆游最希望留给未来的追忆。
四、题跋时间指示性的再发现
通过对陆游题跋中追忆书写的分析,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陆游在题跋一体上的贡献。首先,从进入追忆的方式上看,具有强烈追忆需求且长于审美追忆的陆游与题跋内设的时间指示性异常契合,不仅顺应媒介物的提示进入追忆书写,陆游更变被动为主动,利用题跋的此种文体优势搭载自身最关切的内容,在题跋中构建了一个规模巨大的追忆书写世界;其次,从开展追忆的技巧来看,陆游针对不同的叙述目的,在题跋的追忆书写中花式排布“昔”与“今”的文本容量和位置,以成熟的技巧在题跋中最大限度地开展追忆,增强了题跋追忆书写的表现力;最后,从传递追忆的结构上看,陆游通过暗示的设置,以及面对非常事、非常时而直白地明言,敞开题跋文本结构,助力追忆信息在不息的时光中传递延续。虽然题跋中的追忆书写由来已久,但在之前和之后的作者中,再难找出如陆游般执着追忆并在题跋中开展大规模追忆书写者;在题跋追忆书写的技术层面,陆游亦将其推到了难以超越的地步。明人毛晋曾言:“题跋一派,唯宋人当家”,[15]那么题跋的追忆书写,则有陆游当家。并且陆游在题跋追忆书写上的拓展和贡献,也代表着题跋在南宋的新发展。
陆游题跋中极富特色的追忆书写,促使我们重新回到题跋书写的历史现场,思考题跋文体与追忆书写之间的联系。于是,题跋多基于旧时之物写成而具有内设的时间指示性这一文体特性被重新发现。也正因此,我们得以真正把握陆游在题跋文体上的贡献,并明晰题跋于南宋的发展。长久以来,在题跋较少文体规约、书写相对自由的传统认识影响下,学界对题跋文体特性的讨论并不充分。作为定型和兴盛于宋代的特殊文体,随着题跋的时间指示性被阐明,题跋文体附着的宋代文化特性也得到充分揭示。比如宋人的题跋撰作为何总是走向追忆,特别是宋人强烈的主体性介入之后,宋人题跋中何以出现大量的追忆书写,这些问题便都能得到更加有效的解释。换句话说,研究宋代题跋中的追忆书写,相当于观照到宋代题跋中占比极大的一类,最具题跋作者主体色彩的一类,同时也是其中最能代表宋人气韵的一类。
再往前一步,题跋的时间指示性与追忆书写密切相关,这其实也为宋代题跋为何多作于作家晚年提供了重要的解释视角。陆游及其之前的苏轼和黄庭坚,之后的刘克庄等都呈现出这类特点。由此可知,宋代的题跋书写又可能呈现出一种“老”,它包括书写技法上的成熟老练、传达情感的深沉蕴藉和思想的锐利精当等,体现着宋人独特的思维方式和审美眼光。但与此同时,这种“老”又绝非封闭的状态。如前文所述,题跋始终处于自体开放的文本状态,而宋人题跋中的追忆书写又很好地诠释了题跋文体如何串联起往昔、当下和未来。刘东先生曾启发性地提出宋人具有“题跋意识”,[16]保持着与古人、今人和后人的对话态度。思想上内转的成熟深刻和意识态度上的开放从来就不矛盾,或者说它们恰好组成宋代题跋的核心质素,承载着宋人延续文明的自觉担当。
注释:
①例如郑砚云:《陆游题跋文研究》,硕士学位论文,陕西师范大学,2007;倪海权:《陆游文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哈尔滨师范大学,2012;朱迎平:《读〈渭南文集〉跋文札记》,《绍兴文理学院学报》2017年第6期。
②有不少研究者将《渭南文集》第二十五卷“杂书”类12篇均归入陆游题跋,我们认为这种归类有待商榷。题跋在一定的载体或媒介物上写成,而“杂书”类多为“读……后”,本质上更接近读后感,陆游在文集中的分类实际上已体现出清晰的题跋文体意识,故本文统计其题跋数量时不计入“杂书”类。
③较有代表性的如高利华:《论陆游之“诗人风致”——兼论从戎为原型的审美回忆》,《杭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1期;李文月:《论陆游诗歌的回忆书写》,硕士学位论文,山东师范大学,2019,等等。
④传播学家马歇尔·麦克卢汉在《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商务印书馆,2000,第257页)和乔纳森·芬比在《个人隐私与公开曝光》(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2,第15页)中的观点类似,二者皆认为人们对负面信息更加关注,因此负面信息往往具有更强的传播力。陆游题跋末尾的“悲慨”正是一种负面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