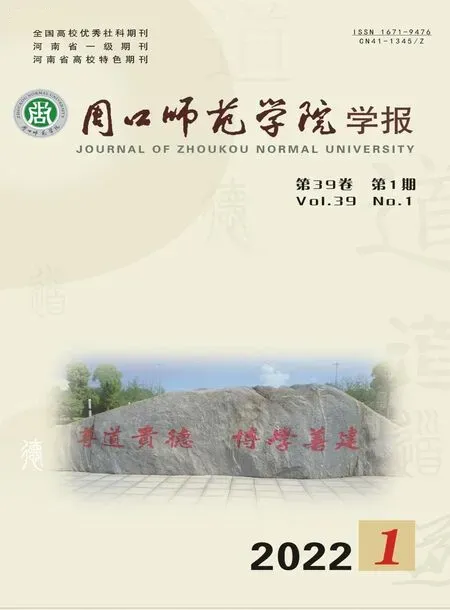面对时代的沉思
——重读段荃法的中篇小说《活宝》
冯文莉,吕东亮
(信阳师范学院 文学院,河南 信阳 464000)
段荃法是20世纪50年代崛起的国内知名的农村题材小说家,是以李凖为代表的河南农村题材小说家群体的重要一员。文学史研究专家洪子诚先生在其著作《中国当代文学史》中提及的作家不多,却将段荃法列为20世纪五六十年代农村题材小说创作的代表性作家之一,这也确认了段荃法创作的文学史意义。改革开放之后,段荃法在艰难的创作转型中开启了新的书写农民之路,小说《活宝》成为其扬弃自我的见证。
一、典型反面人物
中篇小说《活宝》是段荃法创作历程中的重要作品,作家本人也比较珍爱这部小说。1986年,段荃法在黄河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河南作家丛书”之一种的小说集,书名就是《活宝》,《活宝》也被评论界视为“作者调整中取得艺术成就最高的一篇”[1]。在《活宝》中,段荃法塑造了田火火这样一位独特而不容忽视的“活宝式”人物,迥异于作者之前塑造的一系列乐于奉献、思想先进的正面人物,如泼辣干练、以大局为重的乡村女干部凌红蝶,爱护青年、经验丰富的供销社主任王斗,爱队如家、勤劳朴实的老农王二夫妇等。田火火自私自利、好吃懒做、陈腐守旧又笑料十足,是作家立意调整之后尝试创作的典型反面人物。除了塑造人物的典型性之外,《活宝》也展现了作者以幽默笔法叙写农村生活、刻画农村人物的高超技艺。与之前作者塑造的正面人物形象相比,田火火的形象极具灵动性与趣味性,有较高的文学研究价值。大致说来,《活宝》中的田火火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官瘾十足,面子至上
田火火人生的高光时刻当属其任治保主任时期,彼时的田火火威风凛凛、官派十足。他打着干部的旗号,趴墙头,听窗角,混吃混喝;喊着“改造旧分子”的口号,强迫社员为自家挑水、换面、拉煤,占尽便宜。改革开放的春风吹来,田火火不合时宜的“主任”头衔自然不保,可他还是沉浸在做官的美梦中不愿醒来。已是平民的田火火在集市上碰到过去同为村干部的李支书,不想丢了脸面,便吹嘘自己升了村长,还信口胡诌为自己编造了许多“丰功伟绩”,唬得李支书对他敬重有加。后来,为了赌气、挣面子,田火火夸下海口要买下村民田小川价值不菲的收录机,然而豪言壮语犹在耳,却囊中羞涩无法兑现,于是他又利用李支书夫妇的信任,编造理由借走了他们为儿子结婚准备的800元钱。最终,还不上账的田火火不得不以食抵债,被搬得家中空空,成为十里八乡的笑料。以“官”为重、以民为轻,“面子至上”,是田火火身上抹不去的标签,而他之所以有着近乎“痴”的当官梦,是因为在寻常百姓心目中,“官”拥有着绝对的话语权,田火火“官职”加身,便可指挥乡亲为己做事,而乡民即便不情愿也只得顺从。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说到底还是“官贵民贱”“官为主,民为奴”的陈腐思想在作祟,田火火的“官梦”之下掩藏着段荃法对于奴性思想的批判。不只是段荃法,进入新时期以来,随着文学自觉性的推进,反思中原文化中的弊病,有意识地揭露、批判隐藏在现象之下的糟粕,成为许多河南作家创作的主题,尤其是对“奴性”思想的揭露,更是成为热门主题。不论是南丁《科长》中善于揣测领导意图的磕头虫式的王科长,还是乔典运《冷惊》中韭菜被支书老婆偷割还怕被支书报复的王老五,都蕴藏着作家对社会遗留的封建奴性人格的无情鞭挞,这在政治文明建设的今天仍然具有很强烈的现实意义。
(二)好吃懒做,陈腐守旧
田火火作为一名地地道道的农民,却丝毫没有农民阶级勤劳朴实的优良品质,反而好吃懒做,一身陋习。商品经济的春风吹遍了广袤的农村,田家寨的村民丁彩霞、田小川等都借着好政策的东风勤劳致富,盖起了楼房,日子过得红红火火。只有田火火仍旧住在破旧的茅草屋,穷得叮当响。妻子苇叶劝他想办法为家里挣点钱,他却不以为然,仍旧天真地相信不久便会“革资本主义的尾巴”“刮红色台风”,幻想着重新瓜分经济果实。他的眼光极其狭隘,又陈腐守旧,不愿接受新事物的到来,在他身上,农民由于阶级局限性而附带的某种程度的接受滞后性被放大了。无独有偶,古华在《芙蓉镇》中也塑造了王秋赦这样一位与田火火同类型的“喜剧人物”。与田火火相比,王秋赦家境更为贫寒,田火火好歹还有几间瓦房遮风挡雨,而王秋赦只能住祠堂、破庙,靠给人跑腿混饭吃,无产无业,游手好闲的生活滋养了他一身恶习:自私、懒惰、贪婪。土地改革时,田火火在田家寨,政治上是依靠对象,无论搞什么运动,都先找他扎根串连;生活上是照顾对象,啥时候发救济粮、救济款、救济物资,都少不了他的一份。而王秋赦凭借着他优质的“雇农”身份,被认定为“土改根子”,再分胜利果实时,他分得了四时衣裤、全套铺盖、两亩水田、一亩好土,还分得了本镇最气派的吊脚楼。这种不劳而获,甚至越贫穷越光荣的特殊岁月,让田、王两人的懒惰思想滋生成参天大树,他们嫉妒甚至憎恶那些靠勤劳致富的人,以吃公家的、住公家的、要公家的为荣,时刻都盼望着土改,分浮财。和田火火坚信自己革“革命果实”的一天终会到来不同,王秋赦自己都知道“分浮财”是穷开心,是不可能实现的。在1964年“四清”工作组进驻芙蓉镇时,王秋赦却主动迎合李国香公报私仇的潜在心理,举报胡玉音、谷燕山、黎满庚等,将他人的悲惨生活作为自己敛财、升官的垫脚石,将整个芙蓉镇搅得乌烟瘴气,人人自危。和王秋赦相比,田火火所为只是为了获利,之后闹的一出出喜剧,受害者往往是他自己,似乎显得更加“纯洁”一些。然而不可否认的是田火火、王秋赦,甚至《平凡的世界》中的孙玉亭都是特殊时期温床上培养出来的毒瘤,他们懒惰且麻木,看不清现实。所以,田火火在闹一出出笑话的同时将生活过得穷困潦倒,王秋赦也因接受不了现实而精神崩溃。
(三)自私自利,好高骛远
田火火无疑是自私的,利用手中的权力,为自己谋私利,丝毫没有考虑乡亲们的感受,即使是面对家人,他也是自私的。他娶苇叶进门后,万事不沾手,“夜里熬半夜,早晨不起床,家里活地里活全靠妻子、儿子张忙。每隔几天,火火还要喝几两酒,吃一顿肉,妻子攒下的几个卖鸡蛋钱,都被他这样花光了”[2]103。儿子因为家底太薄而娶不起媳妇,他也毫不担心,甚至花光了儿子外出打工挣来的辛苦钱。被苇叶催促着想法子挣钱,田火火又大言不惭地放出豪言“吾子挣大钱不图小利”[2]105,一门心思地去找那一本万利的活计。最后干啥啥不成,在闹出一个个笑话后依然不思悔改。
田火火身上既有浓厚的封建奴性思想,又保留着落后愚昧的特质,甚至还融入了小市民无赖、自私的一面。在田家寨的“舞台上”,田火火充其量只是一位蹩脚的喜剧演员,他的可笑之处在于明明是名不见经传的小配角,却偏偏浓妆艳抹妄想成为万众瞩目的主角。他的自我认知出现了偏差,本该暗淡退场的小角色迷失了自己,却仍旧攒足劲朝舞台中心靠拢,结果自然是笑料百出。作者文笔犀利,在有限的篇幅里刻画了田火火这样一位荒诞可笑又充满悲剧的小人物。
二、幽默之重塑
田火火滑稽可笑的形象之所以如此活灵活现,引人注目,与作者一贯以来的幽默文风大有关系。幽默是段荃法作品的一大特色,在幽默意识方面,段荃法立足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承袭前人“谑而不虐”的风格,又充分汲取中国民间文化的营养,为文坛注入了轻松活泼的创作理念。从《凌红蝶》《“状元”搬妻》到《活宝》,再到《天棚趣话录》,段荃法在审美意识、艺术手法、创作篇幅等方面都进行了不同程度的调整,尤其是作品中的幽默意识有了明显的重塑痕迹。值得注意的是,从《活宝》开始,这种幽默意识有了更为深刻、丰富的内涵,概括说来就是从“会心的笑”转变为“含泪的笑”。
(一)“会心的笑”——欢乐的新农村赞曲
段荃法生于农村,长于农村,早年又在农村开展工作,和农村保持着天然联系。段荃法是捕捉农村新气象的能手,敢想敢干、充满拼劲的农民们便成为他小说中的主人公,一个个鲜活的农民形象通过段荃法细腻的笔触,裹挟着时代的气息朝气蓬勃地向我们走来。
1959年作家出版社出版了段荃法的短篇小说集《凌红蝶》。《凌红蝶》的主人公凌红蝶形象高大饱满,一言一行无不透露着作者对农民和农村生活的熟悉与亲切,语言淳朴,充满独特的韵味。为了衬托凌红蝶的光辉形象,作者在描写反面人物妇女凤紫时这样写道:“迎面走来一个中年女人,长得很胖,胸扣掉了,没有缝上,露着一片红肉,宽嘴巴,扁鼻子,眼很细,猛看去,好像葫芦瓢上画了两条墨线线。”[3]巧用比喻进行辛辣的讽刺让人拍案叫绝。这种不经意间将作者好恶隐藏于字里行间的幽默写法同样延续到了《活宝》里,在田火火偷钱买病牛寻牛黄一节,作者巧妙地将买牛的钱设置成不多不少正好“二百五”,以此来隐喻田火火办了傻事,不着痕迹又笑料十足。
1963年7月,段荃法发表短篇小说《“状元”搬妻》,该小说先后被收入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新人新作选》、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河南三十年短篇小说选》、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建国以来短篇小说》中册,成为段荃法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代表性作品之一。小说着重塑造为了集体利益不惜牺牲个人利益,一心一意为集体饲养牲口的王二夫妇形象。作者借着极其质朴和生动的语言,运用大量民间俗语,讲述了王二夫妇在表彰大会上讲述饲养牲口的点点滴滴,让人记忆深刻,难以忘怀。描述王二作为劳模代表首次发言的场景时,作者这样写道:“王二背着手走上台来。他先扫了大家一眼,便拔出脖子里插的旱烟袋,慢条斯理地装上烟末,还没点火就吸起来,下边立刻发出一阵轻轻的欢快的笑声,王二清醒过来,把没点燃的烟末磕掉,又将烟袋插在脖子里说,我叫王二,说我家人口说多也算多,说少也算少,说少,只有我和老婆过日子,说多,加上我喂那四个牲口,整整有六口欢欢乐乐一大家子。”[4]一个滑稽的吸烟动作,几句“自报家门”的话语,便把模范饲养员王二热爱集体的思想、质朴风趣的性格鲜活生动地描绘了出来。并且在小说中作者借王二之口勾勒出了王二之妻,善良、乐于奉献、任劳任怨的光辉形象,突出了妇女在新时期的重要作用。这种思想在当时仍旧尊崇男性的力量美,凸显男性重要建设作用的时代背景下是非常值得肯定的。这种生活场景白描式的欢乐情景再现的写法,在《活宝》中也随处可见。
由此可见,段荃法五六十年代的作品,“注重的是故事的动人和人物性格的典型,而且注重在社会学特别是政治伦理学意义上的价值批判,一切都在革命与反动、先进与落后的斗争中展示”[5]。小说多选取的是歌颂新人新事的题材,欢乐场景中蕴含的往往是作者对农村新气象的由衷赞美,小说中的人物大多发出的是“会心的笑”。
(二)“含泪的笑”——深刻的反思意识
段荃法在《活宝》后记中写道:“我在努力调整着自己,在调整中,我坚持我认为自己应该坚持的东西,我将丢掉我认为自己应该丢掉的东西。当然,我也将继续努力借鉴和学习新的东西,以不断补充自己,丰富自己。对我来说,这种调整会是困难的,也会是较为长期的,但无论多么困难,无论时间多么长,我也将努力坚持这种调整。”[2]300进入新时期,随着文艺界的拨乱反正,思想解放运动的蓬勃发展,外国文学的大量涌入,中国文学观念得到更新。在这种思潮下,有些作家便开始有意识或者无意识的创作调整,段荃法显然是有意识的创作调整,因此他考虑问题便更加深刻。
《活宝》是段荃法在决意调整后非常出色的篇目,作者也首次尝试将中篇《活宝》和短篇《古道旁的小楼》《典型人物》组合在一起,以一组小说的形式,反映急剧变化着的农村生活,并在小说中塑造了田火火这样一位笑料百出的典型小人物。与段荃法早期热衷塑造平民式英雄人物不同,田火火形象是段荃法有意调整后创作的一个“另类”:他游手好闲,好吃懒做,愚昧落后,整天做着不切实际的当官梦,穷得叮当响却反复宣称“吾子挣大钱不图小利”,颇有些鲁迅笔下阿Q的风范。塑造这样一个反面小人物对段荃法而言是一次大胆的尝试,当然,作者的意图并不仅仅是尝试新人物形象的塑造,而是深入对人性缺陷的挖掘。20世纪80年代,“小说开始显示出与一体化时代不尽相同的追求和风貌,作为一种想象的和虚构的文体形式,逐渐剥离了单纯的政治目标关怀和强调的教化功能,对人的内心痛苦、情感要求、思想矛盾等与人性相关的问题开始在小说中得以反映和表现”[6]。《活宝》中田火火在上演一出出令人捧腹的闹剧之前,也是一位“光鲜”的人物,他对“官”有着天然的迷恋,认为一朝官职在身便可威风无比。这种浓厚的“官本位”思想在特定时期暂时占了上风,历史的车轮进入正常轨道后,这类错误思想自然应该湮没在历史的尘埃里;然而田火火却缺乏对历史敏锐的认知,仍旧沉浸在“刮红色台风”“革资本主义尾巴”这样陈腐的旧梦里,妄想着不劳而获,与社会严重脱节,从而沦为众人的笑柄。部分如田火火一般带着旧时代落后因子的小人物,为了满足一己私欲,明面上打着“为集体”“为国家”的幌子,暗地里却做着损集体利个人的事情,他们的种种自私行为阻碍了社会的进步。田火火身上既带有陈腐落后的时代因素,又夹杂着农民阶级的保守,以及城市小市民的自私,作者力透纸背,深刻剖析了田火火式小人物的人性弱点。相较于前期作品深入农民写农民、赞美农民的审美理念,段荃法此时的创作仍旧以关注农村现状为主,但又不仅仅局限于展现农村生活,他开始有意识地剖析农村存在的问题。更为可贵的是作者在创作人物时仍然能够保持客观的态度,在叙事的同时极少直接表达个人评价,这样就产生了最大限度地凸现表现对象的效果,使得小说常常是“言有尽而意无穷”。
“中篇小说《活宝》发表以后,我有意停笔,想总结一下前段创作,以求自己有新的突破。”[7]在总结《活宝》创作经验的基础上,从1987年开始,段荃法以“天棚趣话录”为总题发表短篇小说,受到评论界的高度肯定。当然在这些小说中段荃法延续了他一贯的幽默文风,《沉浮》中春妞为怀上孩子在院子里骑大白公鸡,晚上抱着两个南瓜睡觉;《洗衣女》里县招待所小职员李秀因为偶然结识了地委李部长,身份被多种揣测,在招待所的地位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作者描绘的生活中的一幕幕闹剧,让读者忍不住发笑,可笑过后又不免对这些陋习、奉承行为深感厌恶。这些小说反映了作家从审视生活到文学观念的总体性调整,由此,作家改变了以往“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的思维模式,开始放弃围绕着现实的某个社会问题来构思情节、塑造人物的创作方法,甚至不再去特别关注个别人的命运和具体事件的是非得失,而是将探测的目光投向了社会和历史的深处:那陈陈相因的社会风尚,那司空见惯的习惯势力,那千百年来奉行的道德公理。他要透过普通人的行为方式、思想方式、情感方式,去显示那些在一定程度上积淀着时代和历史本质特征的社会心态。作家超越了单狭的视角,转向审视并创造更具有普遍性的“群”的心态,笑中带泪,令人深思。
如果说“天棚趣话录”是代表段荃法晚期创作成就的杰作的话,那么《活宝》则是这一杰作的开启者。《活宝》留下了段荃法从“十七年”文学范式中转型的轨迹,这轨迹是段荃法一个人的,也是段荃法这一代人的。
三、社会历史的烙印
作家塑造田火火这样一位反面人物形象,很显然并不仅仅是为了延续幽默文风,段荃法在批判国民性的同时,还有着对社会历史的沉思。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历史性变化,农民成为助力中国经济腾飞的强有力支撑,这在历史上是了不起的大事件。艺术地、生动地反映这个伟大事件乃是我国文学的光荣任务,《活宝》之所以引人注目,就是因为它在反映这个伟大事件的深度和完整性上有着独特的闪光点。作家十分了解与熟悉变化着的农村生活,表面上看,他只是信手拈来田火火这么一个小人物,但作家诙谐幽默的笔法,成功地描画了潜伏于部分农民心灵深处的激流——他们面对新政策的迷茫与不适的精神状态及变化过程。
首先,我们必须注意的是田火火在作品中处于怎样的位置。纵观整部作品,《活宝》里的人物在农村经济改革的大背景下,实际上可以划分为两个队伍:一个是以丁彩霞、田小川为代表的勤劳致富队伍,另一个就是以田火火为代表的懒散落后队伍。他们之间的斗争较量,实际上也昭示着农村经济发展的方向。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两个对立的队伍中,田火火似乎是一个孤独存在的个体,不论是丁彩霞、田小川,还是田家寨的众村民,甚至是田火火的妻子苇叶,他们都坚定地站在勤劳致富一方,这种状况对农村经济发展来讲自然是可喜的。我们大可以嘲笑田火火的愚昧、懒散以及各种不合时宜,可我们也应该认识到,制度的改革、经济的腾飞是面向所有中国人民的。而像田火火这样的落后分子不仅仅存在于田家寨,在中国广袤的农村大地上也有着广泛的同盟军,比如《芙蓉镇》里的王秋赦,《平凡的世界》里的王满银等。王满银祖上曾做过“拔贡”,在东拉河一带颇有名望。祖父抽大烟,父亲是村前庄后有名的二流子,及至王满银出生家里光景早就一“烂包”。这样的家庭滋生了王满银好吃懒做、四处闲逛的恶习,子承父业,他俨然是一个新二流子,并因贩卖老鼠药被“劳改”。农村实行生产责任制后,他跑出去做小生意,但一没资本,二没门路,奔波多年仍旧两手空空,只赚得了满脸的皱纹、双鬓的白发。田火火、王满银们的遭遇提醒我们,不但要看到改革开放后中国农村乃至中国农民的新变化、新气象,也不能忽视少部分群众的痛苦挣扎。段荃法塑造田火火滑稽形象的成功之处就在于:一方面按照生活现实的样子,充分地写出了他作为个体农民在农村经济改革过程中曾有过怎样的不适、怀疑,甚至是自发的反对;另一方面,又从环境对人物的制约关系中充分发掘和表现了田火火那种由于生活地位和历史条件所决定的,不走新道路就只能四处碰壁的必然性,从而相当深刻和全面地昭示了生活发展的辩证法。
其次,我们也应该看到作者在田火火身上倾注的多元情感,不只是批判,还有理解和同情。人们常说,农民最讲究实际,这自然不容辩驳,但我们也不可忽视或低估理想在庄稼人生活中的重要作用,每个阶级都有着自己的实际和自己的理想,所不同的只是他们各自实现理想的路径。田火火也存在着理想——一夜暴富,并且到了“走火入魔”的地步,他挖空心思买病牛寻牛黄,在田家寨四处挖土寻宝,就是为了实现发家理想。那么农民有没有可能实现发家理想?这是不容置疑的,《活宝》中的丁彩霞、田小川就借着商品经济的春风发展副业,走个体经营的道路,从而实现了发家的理想。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这些“先富者”走的是“勤劳致富”的路子,所以田火火这种渴望不劳而获的发家理想就只能沦为空想。田火火作为贫苦农民的代表,经历了恰好成为鲜明对照的两个时代、两种生活的巨大变化——不仅是客观世界,也包括主观世界的巨大变化。在小说的开头,作者提到田火火在特殊历史时期耀武扬威、张牙舞爪的状态,再对比一下结尾,田火火穷困潦倒却迷茫不自知,仍旧不思悔改的现状:这就深刻揭示了如果个人的发展悖逆社会历史发展的潮流,那么他必然就要承担不良后果的道理。田火火作为赤贫人群,在“文革”开始前应该是每天为温饱忧心的,贫穷让他没有多余的物质积累,赤贫的身份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曾给他带来了好处,在新时期等着吃大锅饭的道路早已被堵塞,但田火火还顽固地把它看成可行的现实。反过来,丁彩霞、田小川等所走的勤劳致富的道路却被田火火所不屑,认为历史还会重来,丁彩霞、田小川会成为被革对象。田火火将现实和梦想如此颠倒是很可笑的,带有很大的喜剧成分,然而在喜剧的背后又隐藏着很深的悲剧内容:他的挣扎带有极大的盲目性,因而不可避免地遭致悲惨的命运。段荃法正是通过田火火形象的塑造,对在新时期还执拗地活在旧思想里的农民给予同情,并且站在共产主义思想的高度,含着微笑批评了他们的弱点,指出他们将带来的危险后果。田火火的种种表现,形象地揭示了“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这一著名论断的深刻意义。
田火火是段荃法立意调整后塑造的典型人物,在他身上凝聚了作家丰富的农村生活经验,熔铸了作家的幽默和诙谐,表现了作家对农民的深切理解和真挚情感,因此它不仅深刻,还丰满且坚实。正是由于田火火形象塑造的成功,《活宝》成为段荃法转型过程中不容忽视的佳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