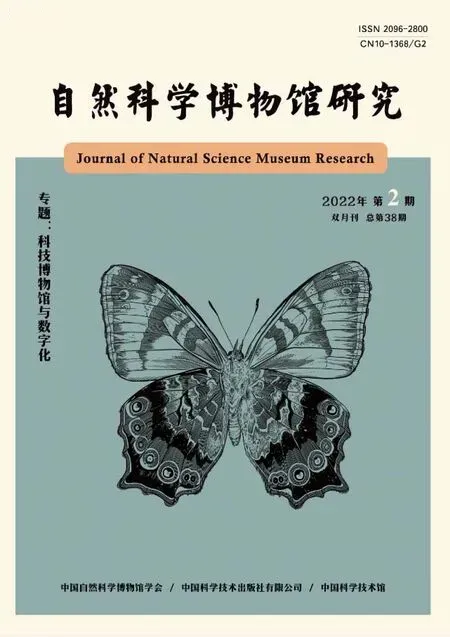近代西方人在华建立自然史博物馆类型及目的取向研究
蒋 凡
自然史类博物馆是近代西方人在华建立的博物馆中的重要类型,其中以在华大英博物馆、徐家汇博物院、上海亚洲文会博物馆以及北疆博物院最具代表性。这些自然史博物馆的诞生与当时西方自然史研究的大背景关系密切,它们并非现代意义上以知识普及为目的的博物馆,而更多地扮演了西方调查了解中国地域内自然发展史的工具,为西方的自然史标本收集和研究提供帮助。
一、 近代西方自然史研究与自然史博物馆的发展
早在文艺复兴时期,随着人文主义的发展,人们对自然世界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学者们开始尝试把化石、标本和古董收藏起来,作为研究自然界复杂事物的一种手段[1]。林奈(Carl von Linné)创立的以系统方式研究自然史的分类法推动了自然史研究的发展。1859年达尔文《物种起源》(TheOriginofSpecies)的出版推动了自然史研究的进一步发展,自然史不再是平面的、关于分类的观察和描述,而是成为立体和动态的关于自然世界发展的理性研究。从最初单纯为满足好奇的探索,直到理性有秩序的分类,再到对进化论的认识,自然史研究成为西方认识世界的重要途径。
自然史研究的发展与西方社会的需求有直接关系。“进行海外贸易、征服殖民地、获取自然资源,都迫切需要研究和了解当地的自然、资源、环境条件”[2],自然史研究伴随着海外贸易和商业扩张不断发展。由于欧洲研究材料的不足,自然史研究者将目光和触角沿着全球的贸易活动伸向尚不为欧洲所知的地方。自然史的研究成为了一种深受大众欢迎的科学和文化风尚,科学讲座、植物学研究、昆虫和化石标本的收集十分兴盛[3]。自然史研究同其他科学的一个区别,在于它“不仅是精英圈的智力追求,也是许多人参与的文化实践”[3],吸引了许多非专业研究者参与。旅行家、传教士、军官和商人通常也是自然史标本的收集者和传递者,他们中的许多人与本国著名的自然史学家保持着密切的联系,随着全球贸易的发展,形成了由研究者和采集者组成的自然史标本收集网络。这不仅促进了自然史研究的发展,而且也促进了以自然史博物馆为代表的各种收藏机构的发展。
自然史的研究与自然史博物馆关系密切。早期植物学和动物学研究者及爱好者的标本收藏形成了“早期的自然史博物馆”[4]。特别是随着西方全球殖民活动的广泛开展,自然史标本的收藏规模和范围扩大,标本储藏所成为中国的现代博物馆雏形。自18世纪开始,博物馆式的自然标本收藏机构在自然史研究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比如林奈在乌普萨拉大学建立的植物园、威廉·汉特(William Hunter)在苏格兰格拉斯哥大学建立的威廉·汉特博物馆(Hunterian Museum)等机构都是具有很大影响力的自然史博物馆。到了19世纪,地理学会、自然史学会、博物馆和植物园等众多机构发展迅速,约翰·皮克斯通(John Pickstone)用“博物馆式科学”[5]形容自然史博物馆和类似机构对自然史研究的重要性,他认为这是19世纪最重要的知识类型之一。比如,1828年在英国牛津郡成立的阿什莫尔自然史协会(Ashmolean Natural History Society)是英国最古老的自然史研究团体,他们认为“‘珍奇物品橱柜’有重要的教育价值,因此他们将打造博物馆当作了一项优先要务”[6]。在欧洲和美洲,许多国家和地方自然史博物馆就是在这个时期形成的,比如1748年成立的维也纳自然史博物馆,1793年成立的法国国家自然史博物馆和1869年成立的美国自然史博物馆等。这一时期,自然史的研究和收藏都围绕着博物馆展开,博物馆成为了自然史发展的中心地带,博物馆也成为了人们认识世界的窗口。
西方工业革命的发展、全球贸易及殖民运动的扩张,使中国不再像以前一样难以接触,西方人开始在中国港口城市建立居住地,这为西方认识中国打开了大门。西方人最早在华建立的一批自然史博物馆即基于此背景产生。随着在华自然史资料收集的规模越来越大,把所有标本不加区分地运回欧洲并不现实,在当地进行研究并直接出版研究成果成为了更好的选择。这些博物馆不仅关系到自然史研究本身,也关乎西方在华各方的利益。不论哪一方面,这些博物馆都服务于西方尝试认识中国的目的。
二、 以自然史标本收集为主的博物馆
西方人在华建立较早的几座博物馆都是自然史类型的,以澳门的在华大英博物馆(The British Museum in China)和上海的亚洲文会博物馆为例,其主要工作即为西方收集中国的自然史标本,以扩充西方的自然史收藏。
(一) 在华大英博物馆
18世纪末19世纪初,就有英国海上贸易的船员开始收集并向英国提供来自中国的自然史标本。由于当时欧洲对中国的自然环境知之甚少,这些材料非常受欢迎。与这些船员相比,在中国广东的英国东印度公司商人得益于可以接触到中国内地和中国当地人的优势,在收集中国自然史标本的活动中扮演了更为重要的角色。英国东印度公司派驻在澳门的传教士乔治·瓦切尔(George Vachell)就曾向英国剑桥哲学协会博物馆(Museum of the Cambridge Philosophical Society)寄送过“13包干草、7个蜥蜴标本、2盒昆虫、10张鸟皮、1只蝙蝠、50个地质标本、2个贝壳、8个荔枝、一盒燕窝和一个头骨”[3]等藏品。英国东印度公司在澳门的茶叶检查员约翰·里夫斯(John Reeves)也热衷于收集自然史材料,他在来中国之前就被要求收集“园艺信息和自然史标本”[1],之后他在中国建立了一个自然史藏品收集的网络,为他提供来自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的标本。
随着从澳门往欧洲寄送的自然史标本数量越来越多,这些在中国进行自然史标本收集的人们认识到,有必要成立“一个科学机构来协助他们研究自然史”[3]。到19世纪20年代末,在澳门的英国东印度公司商人开始尝试建立博物馆。据马礼逊(Robert Morrison)记载,1829年2月21日,澳门的英国东印度公司成员通过了建设博物馆的决议(一说是2月22日会议通过)[7],这次会议将待建的新博物馆命名为“在华大英博物馆”,并设立管理委员会,由馆长、秘书和司库组成;规定了会员只能是英国公民,本地居民和外国人只能担任荣誉或通讯会员[8];提名了乔治·瓦切尔为博物馆馆长,约翰·拉塞尔·里夫斯(John Russell Reeves)为秘书。
1831年的《广州杂记》(CantonMiscellany)中曾提到,在华大英博物馆是“由年轻的英国自然史爱好者建立的另一个有趣机构”[9]。当时进行国际贸易的商人和进行海外传教的牧师差不多都是业余的自然史学家。馆长瓦切尔是英国东印度公司在澳门的牧师,他自己曾提到过,他收集自然史标本就是为了获得收益[3]。博物馆的秘书里夫斯的父亲是上文提到的约翰·里夫斯,他被认为是“热心的业余自然史学家”[10],秘书里夫斯与其父亲一样具有很高的自然史收藏热情,他们都是英国在中国进行自然史标本收集的代理人。之所以建设博物馆,就是为了尽可能地为英国收集来自远东的自然史标本。
从博物馆的藏品实际情况看,由于博物馆的建设者并非专业的自然史研究者,这个博物馆看起来更像是“奇珍柜”式的博物馆,在当时的记录中也有将其认为是“珍宝阁(cabinet)”[11]的说法。在对这个博物馆的诸多描述中,很多都认为在华大英博物馆除了收藏自然史藏品外,还收藏了对于来华的西方人来说新奇且充满异国情调的“奇珍(curiosity art)”,这类收藏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满足西方人对中国的好奇而进行的收藏。从收集到的文献记录上看,在华大英博物馆的藏品可以大致分为三类:自然史标本、制成品和工艺品[11]。这些藏品无论是自然史类的标本,还是这些所谓的中国“奇珍”,在当时的西方人看来都是新奇且未知的。从这个角度看,在华大英博物馆更像是为了满足西方人的好奇而建立的收藏奇珍的仓库。
由于1834年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垄断贸易结束,在华大英博物馆随之关闭。在华大英博物馆解散后,其藏品扩充了英国的自然史标本收藏。这个博物馆的藏品曾考虑全部运送到英国亚洲学会下的加尔各答博物馆。但这个想法没能完全落实,只有148件鸟类标本、6个带蛋的鸟巢、6只哺乳动物、1只爬行动物和一些鸟类的头部与腿部等部分藏品被留在加尔各答[12]。
在华大英博物馆是一个由自然史业余者组建的小型博物馆,它以自然史类收藏为主,但也收藏能够满足西方人好奇心的其它藏品。由于其存在时间短,相关材料较少,很难说这个博物馆对中国的博物馆发展产生了多大影响。但这个博物馆对西方自然史研究做出了贡献,它最重要的功能是为英国收集自然史标本。这个博物馆解散后,它的很多藏品也被运往英国,扩充了当时英国的自然史标本收藏。从这个层面上看,它更像是由自然史爱好者建立的英国在华自然史标本收集基地。
(二) 上海亚洲文会博物馆
1874年,上海亚洲文会博物馆由英国皇家亚洲文会北中国支会(以下简称“文会”)建立。这是一座以自然史标本收藏为主的机构,它在1933年得到重建,之后成为了一座综合类博物馆。本文旨在讨论其作为自然史博物馆时期的特点。
早在1864年,文会就提出将“调查中国与周边国家有关的课题、出版期刊、建立图书馆和博物馆”[13]作为文会发展的目标。1874年上海亚洲文会博物馆建立后,自然史类标本的收藏是博物馆的主要工作。在1878年的报告中,福威乐(A. Fauvel,1877—1879年任上海亚洲文会博物馆馆长)提出亚洲文会博物馆是聚焦于自然史的博物馆而不是综合博物馆,史丹阳(Frederick W. Styan,1884—1886年任上海亚洲文会博物馆馆长)馆长曾在1884年的馆长报告中提出“不论是哺乳动物、鸟类还是爬虫类、鱼类,我们想要关于这个国家自然史的一切藏品”[14]。纵观整个上海亚洲文会博物馆发展历史,可以发现该博物馆以通过自然史标本收藏为在华西方人提供研究平台为目的的建设倾向。
当时,其负责人(馆长)的职位以“Curator”(1)从词源学的角度解释,Curator一词源自拉丁文“Cura”,意思是“照顾”。该词在人称化后,特指“照顾或总理某项实物的监护者”。为名,反映了其工作的重心在于藏品的保管,因此馆长的年报中往往以当年藏品的收集情况为主要内容。比如,在1878年的馆长报告中,福威乐提到“自1877年11月以来,已有137件鸟类标本被博物馆收藏”,同时由于博物馆来自南方的标本较少,因此希望“能在香港找到一个好的通讯员和收藏家”为博物馆提供标本,福威乐认为这将“对博物馆有很大的意义”[15];1880年博物馆收到了许多鸟类学、昆虫学标本捐赠,这扩充了博物馆的收藏,因此馆长贾森在(D.C.Jaisen,1880—1882年任上海亚洲文会博物馆馆长)认为需要对这些捐赠做出相应的感谢[16];1898年,馆长莱曼(Edmund R. Lyman,1898—1901年任上海亚洲文会博物馆馆长)提出博物馆应尽可能与在华的外国人合作以扩充收藏的想法,他希望“在接下来的一年里,让所有在中国的外国人合作,以增加博物馆的藏品。目前已经计划请他们对中国的鱼类进行分类收集。通过邀请所有外国人来经营,希望能够扩充本馆鸟类、哺乳动物和矿物的收藏数量”[17]。
收藏占据了亚洲文会博物馆的主要空间。起初博物馆的空间很小,仅将亚洲文会二楼的一个房间作为博物馆的场地。但随着藏品的不断增多,一个房间已经不能满足博物馆的需求。在1875年,柯蒂埃(Henri Cordier)就提出博物馆“希望使用文会的图书馆空间作为展览场地”[13]。1878年,时任馆长福威乐提出,随着藏品的增加,博物馆的空间需要拓展:“我们必须更新对空间的要求”[15]。直到1880年文会图书馆搬出,建立上海图书馆后,博物馆由一间变为两间。1920年的《上海指南》中这样介绍上海亚洲文会博物馆:“室凡二间。右贮兽类(如獐、猫、狼、豹、猴、野猪、刺猬等)及贝介类蛇类鱼类矿类之所在。左贮禽类(大半皆中国产)蛾蝶类鸟卵鸟巢矿苗之所”[18],可见这两个房间主要是用来存放藏品。
亚洲文会博物馆以其收藏的丰富性逐步为在华的西方人提供了研究的平台。韩伯禄(Pierre Marie Heude)、拉图许(John David Digues La Touche)和苏柯仁(Arthur de Carle Sowerby)是帮助亚洲文会博物馆进行研究的代表人物。早在博物馆成立之初的1877年,韩伯禄就被邀请参与到博物馆“鉴定和分类珍稀物种”[19]的工作中。鸟类标本是博物馆的代表性收藏,博物馆初建就征集到了鸟类115种256个标本[20]。1884—1886年,史丹阳任馆长期间将鸟类标本收藏整理得相对完善,并使其占据了博物馆收藏的主要地位,但直到亚洲鸟类专家拉图许参与到博物馆的标本整理工作中,才将馆藏的所有鸟类标本进行了专业的整理和研究[21]。直到博物馆建立40余年后的1916年,时任馆长史笪来(Arthur Stanley,1905—1921年任上海亚洲文会博物馆馆长)才提出“第一次能够在博物馆报告中宣称博物馆的所有材料都可供研究”[22]。史笪来还提到他整理藏品的目的即为了方便专家研究,“仅仅在一个标本上贴上特定名称就有其特殊的用途和重要性……这不一定是为了向公众展示,而是为了使这些藏品可以供专家使用”[23]。1922年,苏柯仁开始参与到博物馆的藏品整理工作中,当时的馆长谈维士(C.Noel Davis,1921—1927年任上海亚洲文会博物馆馆长)称“在对大量珍贵标本进行命名和分类的工作中,他的知识非常有用,其中对许多标本的认识几乎是独一无二的”[24]。
亚洲文会博物馆与在华大英博物馆最根本的区别在于组织方式的不同。在华大英博物馆更像是由几位自然史爱好者组织的西方在华自然史标本收集分支,而亚洲文会博物馆则更像西方在华精英组织的智识俱乐部。这些西方人依靠自身的影响力并通过博物馆开展更广泛的藏品收集活动,获得更丰富的标本,吸引在华的西方自然史专家参与博物馆标本的整理工作。这种类似俱乐部的形式,目的在于通过自然史标本的收藏,博物馆能够为在华的西方自然史学者提供研究的平台。
三、 以自然史研究为主的博物馆
与自然史爱好者建立的在华大英博物馆和学术团体建立的亚洲文会博物馆不同,徐家汇博物院和北疆博物院的建设者不仅有宗教背景,且都是专业的自然史研究者。韩伯禄(Pierre Marie Heude)和桑志华(Emile Licent)来华具有强烈的自然史研究动机,他们在华开展了大量的考察工作,博物馆这一机构对他们而言,除了要承担收藏其考察获得标本的作用外,更多地需要发挥研究的职能。
(一) 徐家汇博物院
徐家汇博物院是近代西方人在华建立、运营时间最久的博物馆之一,其最初由法国天主教传教士韩伯禄建设为一座自然史类博物馆,在20世纪30年代迁址后改名为震旦博物院,成为一座综合类博物馆。本文主要讨论其作为自然史博物馆阶段的情况。
韩伯禄在博物馆建立之初就旨在将其建设为自然史研究中心。《震旦博物院史略》中曾提到“该院最初的宗旨,原为著述发表,所以完全是注重在研究方面的。而主院者研究目标一定,就朝夕从事于一个部分,搜集材料,并加以研究,无复旁骛”[25]。韩伯禄来华后,将大部分精力放在了自然史标本的收集上。自1868年来,韩伯禄进行过18次大型旅行。他于1868年1月抵达上海,2月份就开始了他标本收集的旅程。直到1881年,“他在这13年间仅仅有一次简短的休息”[26]。在这期间,韩伯禄主要在中国江苏、安徽、江西和湖广等地考察。1881—1883年期间,韩伯禄将精力都放在了博物馆建设上,整理原有的材料并扩充博物馆的收藏。据《震旦杂志》记载,他的标本采集路线总长超25万千米,发现了近600种的新物种[27]。韩伯禄基于这些标本进行研究,还出版发行了自然史研究刊物《中华帝国自然史论集》(Mémoiresconcernantl‘Histoirenaturelledel’Empirechinois)。
韩伯禄不在徐家汇期间,博物馆则扮演研究室的功能。负责其日常运营的蒋其仪(Charles Rathouis)是巴黎医学院毕业的博士,他在1877年抵达中国,最初在上海天主教会工作。蒋其仪由于身体原因没有追随韩伯禄四处考察,而是在博物馆中开展自己的研究工作。蒋其仪的主要工作一方面是在徐家汇博物院进行动物学研究,另一方面帮助韩伯禄绘制标本图像以辅助其研究成果出版,其中《中华帝国自然史论集》中有许多科学插画就是他完成的。郑璧尔(Octave Piel,1935—1945年任震旦博物院院长)认为蒋其仪作为韩伯禄的助手,“他在徐家汇可以做好科研工作”,他进一步提出蒋其仪在徐家汇博物院发展的历史中“真正的位置并不在韩伯禄之后,而是在他旁边,蒋其仪配得上属于他的荣耀”[28]。徐家汇博物院的继任者对蒋其仪的高度评价,正是因为通过蒋其仪的努力才真正将徐家汇博物院标本收藏功能和自然史研究功能结合到了一起,这使徐家汇博物院能够发挥自然史标本收藏和研究中心的双重作用。韩伯禄去世后,徐家汇博物院的院长由自然史学家柏永年(Frederic Courtois,1903—1928年任徐家汇博物院院长)继任。柏永年在博物馆的工作依然是自然史研究,只是收集和研究的类型与韩伯禄不同。韩伯禄主要收集软体动物和哺乳动物标本,柏永年则将精力放在了鸟类和植物上,柏永年在1918年出版了包括1055种植物在内的植物目录, 1912—1927年间出版了5卷本《徐家汇博物院的鸟类》[28]。柏永年于1928年去世,留下了一个“收藏丰富的博物馆”[28]。虽然在柏永年去世后不久,徐家汇博物院就搬迁至震旦大学并在划归震旦大学管辖后改名为震旦博物院,但这种浓厚的自然史研究风气却一直兴盛[25]。
徐家汇博物院虽然以“博物馆”的名义建设,但并不能算是现代意义上的博物馆。曾经有研究认为该博物馆是中国最早向公众开放的公共博物馆,但其规定“入观者不取游资,持有介绍书,须要请法教士允许”[18]。参观受限,就意味着它“不能算是真正向公众开放”[29]。对韩伯禄而言,建设博物馆作为专门场所以开展自然史研究的作用,远远大于“博物馆”这一机构本身的意义。韩伯禄开展自然史研究还有宗教方面的考虑,他希望通过收藏的标本来反驳“进化论”[29],收藏于博物馆中的野猪和鹿的骨骼标本就是他用来进行相关研究的材料。后任馆长郑璧尔提到徐家汇博物院是“一个研究人员满意的研究型博物馆,这对普通好奇的人来说并不友好”[28],苏柯仁也提到徐家汇博物院“收藏仍然是研究的对象,而不是展览的对象”[30]。徐家汇博物院是自然史研究者凭借馆藏开展研究的实验室,因此有学者将徐家汇博物院称为“研究型博物馆(working museum)”[31]。
(二) 北疆博物院
北疆博物院的创建者桑志华“曾在大英博物馆和巴黎(自然史)博物馆研究过相关资料,他意识到了中国北方自然史研究的不足”[32],他在1912年时候就希望探索这一西方所知甚少的领域,在他来华前的一份计划书中曾提到,他是为了“将此地区有关动物学、植物学、地质学等方面的材料汇集起来,尽可能地整理完整的系列收藏,这不是为了建立一个公共博物馆(虽然这样的想法并不被排除),而是主要为了建立一个资料与资讯流通中心[33]”。从这个计划中可以看到,桑志华的首要目标是为西方提供中国北方的自然史研究资料。
桑志华于1914年到达中国,最初以自然史考察为主要工作。他首先在山西北部开展了考察工作,1915—1917年间,桑志华考察了山西中部和南部、北京和蒙古高原一带。在这段时间内桑志华收集了“3000~4000种植物标本、7000~8000种不同区域低等植物(蘑菇、苔藓和藻类)标本;大约800只鸟类;大约30种爬行动物……”[33]等。据称,他在12年内足迹遍布黄河流域,“约3万千米”[34]。“为保存搜集之物,博物院之设立,至为急务”[35],为收藏这些标本而建设博物馆的想法也因此产生。
1921年,桑志华准备着手建设博物馆的事宜。他以北疆博物院的名义撰写了一本指南《召告传教士及有关采集与寄送自然史标本的说明》(Appelauxmissionnairesetrenseignementspourlarécolteetl’envoid’objetsd’histoirenaturelle)[36],并分发给华北地区的教会,为北疆博物院的建设筹备自然史资料。1922年,待天津工商学院建设开始后,桑志华开始筹备北疆博物院的建设。1923年,北疆博物院的第一期建筑落成。
北疆博物院的研究特性在其建成初期的设置和工作上可见端倪。北疆博物院的法文名称被称为“Musée-Laboratoire Hoangho Paiho”,其中“Musée-Laboratoire”即“博物馆—实验室”,桑志华将北疆博物院视为博物馆和实验室的综合体。桑志华自己也提到建设北疆博物院主要是为了研究,他将其称为研究博物馆(Musée d’études)[36],它并不是为了向公众开放而建设的。1928年,博物院建成后,桑志华的考察工作再度丰富了其收藏,需要更大的收藏和研究空间,北疆博物院进行了扩建。新建成的这一部分共分三层,它虽然被桑志华称之为公共博物馆(Musée public)[36],但这三层并非全为展示服务,其“三层则暂时为博物院研究工作服务”[37]。到了1929年,北疆博物院再一步扩建了主体建筑,“新建一实验室,高两层,位于博物院之南与之成平行式……其容积较旧者扩大二倍,内计实验室三间,办公室一间,图书馆一间,大厅两间”[38]。这个建筑是“专为研究而设”的,将其收藏“皆分类别门,及各种动植物之顺序,专供有名望专门研究者研究”[39]。
北疆博物院建成后,桑志华以此为基础陆续出版了许多科研成果,其中包括《近代化石搜集》《博物院的鸟类》《集宁县的地质志》《二十年内北疆博物院典籍批评(1914—1934年)》《1928—1933年的禽鸟搜集》《山西省中部有些最新的地质》《十年来寓居和勘探黄河白河及北直隶湾地带的记述(1923—1933年)》《在中国北部、东北部和西北部(内蒙古、东北、新疆)二十年的勘探记述(1914—1933年)》《山西西南部鲜新期的长颈鹿和鹿类》《北疆博物院哺乳类·啮齿类》等等。
可见,北疆博物院在桑志华管理时期,主要承担了中国北方自然史研究中心的任务,其工作围绕着自然史考察和自然史研究展开,北疆博物院是他将这两方面工作结合到一起的基地。
四、 结论
自然史类博物馆是西方人在华博物馆活动拼图的主要部分。西方人在中国建立的在华大英博物馆、徐家汇博物院、上海亚洲文会博物馆和北疆博物院都是西方自然史研究活动在中国的延伸,根据这些博物馆建设者的需求,他们在实践中也表现出了两种不同的工作重心。
中国是西方进行全球自然史研究以构建其“秩序”的一个部分。18、19世纪是西方近代科学形成和发展时期。为了“构建一个能够准确反映自然秩序的通用分类法”[3],欧洲能够提供给西方科学研究需要的材料远不能达到这一要求,随着全球贸易和西方殖民活动的开展,从世界其他地方获取研究材料成为了西方科学研究的重要途径。在华大英博物馆、徐家汇博物院、北疆博物院和上海亚洲文会博物馆都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产生的。这些博物馆是西方自然史研究中的一环,它们是中国自然史标本的输送点、收藏所和研究室,只是在侧重点上各有不同。
上述几座博物馆最基础的职能就是向西方输送自然史标本。在华大英博物馆在当时仅负责为西方输送标本,从名称上就可以看出它具有类似西方博物馆分支机构的功能,由于当时西方人并不能在中国随意活动,在华大英博物馆在当时可以被视为中国自然史标本向西方运送的集散点。上海亚洲文会博物馆更注重对中国自然史标本的收藏,这是在华西方人学术团体组织的自然史标本收藏和研究机构,意在尽可能全面地收藏中国的自然史标本,建立“中国所有与自然史相关的学科的信息中心”,进而可以为在华的西方自然史学者提供研究资料。
徐家汇博物院和北疆博物院与前两座博物馆相比更多地承担了研究职能,这两座博物馆的负责人,不论是韩伯禄、桑志华还是徐家汇博物院的后继馆长,都将研究作为博物馆的第一工作,因而其藏品都是为了研究而收集,博物馆是他们开展考察的基地,也是开展研究的实验室。这两座博物馆虽然是天主教会创立的,但它们在华传播天主教的作用并不明显,像韩伯禄试图通过自然史标研究来反驳“进化论”一样,他们更注重通过研究的方式来完善宗教理论。戴丽娟认为北疆博物院是当时自然史研究在中国北方的“中心”[36],以此观点看,这两座博物馆构成了当时西方在中国进行自然史研究的南北两个基地。
综上所述,近代出现较早的一批由西方人建立的自然史博物馆是西方进行全球自然史研究、构建自然史科学秩序的组成部分。这些博物馆并非以现代意义上的公共博物馆为建设目的建立的,没有旨在将西方社会中的“博物馆”概念和实体作为一种理论和文化机构引入中国,没有将展示作为主要任务,也没有将中国本土视为服务对象,而是视博物馆为西方人在华开展相关活动的一种工具,以服务西方的需求为其建设的内源动力。
——军旅写生作品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