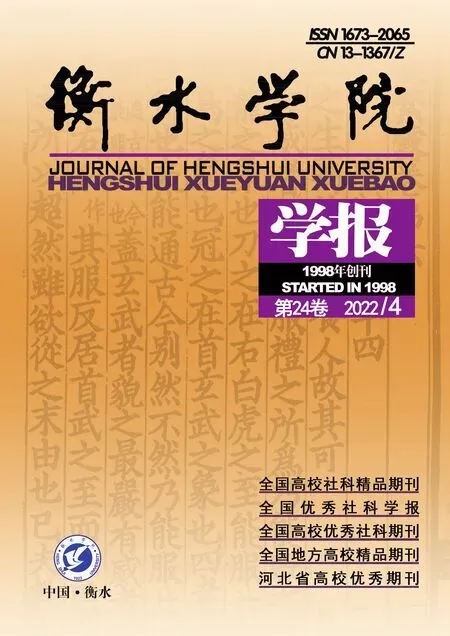庙学与文教——问津书院的教育理念与办学实践
李 永,章群琳
庙学与文教——问津书院的教育理念与办学实践
李 永1,2,章群琳3
(1.江汉大学 武汉研究院,湖北 武汉 430056;2.中南民族大学 教育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4;3.陕西师范大学 民族教育学院,陕西 西安 710062)
庙学是“庙”与“学”的结合体,既是祭祀孔子的阵地,也是开展教学活动的场所。问津书院,也称新洲孔庙,始建于西汉,因“孔子使子路问津”的典故而得名。唐朝黄州刺史杜牧在此立庙祀先圣,开兴教办学之先河,形成“庙学合一”体系。问津书院在一千多年庙学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以精深学术为依归的教育宗旨,以修身立德为主体的教育目标,以服务保障为指向的教育管理。上述教育理念与办学实践,实为古代楚黄之地庙学教育的典范,其办学治学的经验主要在于坚持立德树人的方针,培养德才兼备人才;贯彻学术自由理念,践行名师治校原则;构建和谐师生关系,实现教学相长目标;注重规约章程建设,完善教学管理制度;倡导多元主体模式,吸引民间资本办学等多个方面。
庙学;问津书院;新洲孔庙;儒学;儒家文化
汉初统治者推行尊孔崇儒政策,引发对“立学祀孔”问题的普遍关注,两汉成为庙学制初创期。自西汉淮南王刘安在孔子山修建孔庙,召集儒士著书立说以来,新洲孔庙受到地方官吏、儒生的尊崇和修护。晚唐黄州刺史杜牧改新洲孔庙为“文宣庙”,南宋黄州太守孟珙对新洲孔庙进行改建,立庙设学,作屋千间[1]。元代龙仁夫将新洲孔庙建成书院,立院讲学。明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新洲孔庙与书院学宫合建,改名“问津书院”。至明中叶问津书院发展迅猛,以陆王心学、东林学派为代表的硕儒名师纷至沓来。明末问津书院屡遭战乱侵毁,至清朝逐渐被官方掌控,成为楚黄儒生讲学会课、会考之地。民国时期,问津书院一度被改为小学、中学,新中国建立后,亦长期在此办学。20世纪末,政府将学校迁出,以保护古建筑。今天的问津书院是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是珍贵的文化遗产。
如今庙学复兴适逢新的契机。2016年国家文物局下发《关于开展文庙、书院等儒家文化遗产基本情况调查的通知》,切实加强了儒家文化遗产的保护利用工作。湖北省政府贯彻落实中央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对湖北省境内的文物保护和利用进行了部署和决策,有效改善了湖北省文庙、书院保护利用状况。2020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做出“全面复兴传统文化”的重大国策。在此背景下,开展庙学研究,有助于光扬儒家思想,延续优秀传统文化的学术正脉。问津书院在一千多年的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教育理念与管理模式,是湖北地区古代庙学教育的典范,探讨这一话题,既有助于促进儒家思想在新时代重焕生机与活力,又可为学校办学育人提供经验借鉴。
1 书院:以服务保障为指向的教育管理
两汉以后,历代统治者为推行尊孔崇儒的文教政策,多把庙学纳入正统教育体系。宋元以后,部分主祀孔子的庙宇与书院融为一体,形成“庙学合一”现象,如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茅山书院。它们都仿照官学庙制,建有主祀孔子的庙宇或殿堂,成为兴教育才又兼具祭孔功能的场所。问津书院在发展过程中,为服务师生、保障书院良好运转,逐渐形成了分工明确、制度严密、执行严格的管理体制。
1.1 山长制与董事制
南宋时期,问津书院管理体制主要包括五个方面:一是以山长或堂长负责制为代表的管理体制,二是师资管理,三是生徒管理,四是教学管理,五是经费管理[2]。书院一般设山长三至四人,由州、府官吏或地方士绅轮流担任,每届任期三年,也可连任[3]31。山长一方面是教学人员,负责书院会课会考、日常教学,另一方面也是行政人员,掌管书院春秋祭祀、经费开支等事务。山长选拔有严格的标准,既注重学识,强调科举出身,也要求其具有一定的书院管理能力和管理经验。据记载,从元初到清朝,先后担任过问津书院山长的有龙仁夫、郭庆、吴良吉、耿定向、耿定理、萧继忠、王士龙、梅元英等,他们都是当世大儒。山长制从制度层面保障了管理者的质量,为问津书院在明中叶的繁荣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受先师耿定向之托,萧继忠自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至崇祯十五年(1642年)担任书院山长,长达26年,主要做了三个方面的工作:组织募捐,扩建书院,维修院舍;学规建设;延请名儒讲学。在任期间,受东林党与阉党之争牵连,被抓捕入狱,险些丧命。待崇祯皇帝即位,东林党人得以平反,萧继忠才被释放。晚年,海内师友先后谢世,家庭迭遭兄逝儿亡之变,萧继忠仍然振作精神,支撑书院事务,可谓尽心竭力、鞠躬尽瘁。萧继忠时期是问津书院讲学之风最为兴盛之时,可与邹鲁相提并论[4]724,可见其儒学传播之盛。
明清之际,经统治者大力提倡,庙学“遍于天下”,庙学制度也日益完善。自顺治三年(1646年)问津书院改制以来的两百多年里,书院由地方士绅组成的董事会管理。董事会每届二至四人,每一届任职期限为二至四年,各成员间分工协作,共同管理书院。在这期间,担任董事会成员(也称书院管理院事)的共有202人[5],其中有多人多次出任问津书院管理院事,如操正都、操鹏等操氏五代,此外,钱履和等钱氏一门四代和梅元英等梅氏一门七代世代出任问津书院管理院事。董事会通过倡办、主持、资助书院,一方面促进了问津书院的建设,另一方面也促使问津书院的管理更加制度化、民主化。
1.2 教学管理与藏书制
宋朝实行重文和兴学政策,使得各级官学和书院获得快速发展,庙学也迎来大发展。庙学日益兴盛之时,教学管理也愈加制度化。万历年间,山长萧继忠制定了《问津书院学规》,明确讲会制度,即“每月十六日俱会于斯”,使得讲学活动规范化、制度化。清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书院管理院事邹江遐又制定《问津书院会约》,其内容比《问津书院学规》更为细致,涉及学习的诸多方式,如“优取前列之文,遍传共阅”[6]21等。在学规、会约的引导下,问津生员多勤勉好学,积极进取。
宋元时期,庙学的日常管理主要围绕课程设置、教学安排和生员考核展开。明代以前,问津书院的课程表一般为:晨读《四书》,顺序依次为《大学》《论语》《孟子》《中庸》,也可选读《五经》之类书籍;早饭后为集中讲授;午饭后自学“本经”“论策”等课程;晚上读《通鉴纲目》。明代问津书院的课程与普通官办学校不同,课程设置较为灵活,课程分为读书、习礼、诗歌三类,每天的课程分为写作、背诵、作课艺、习礼、诗歌五节[7]。书院分日、月、季会课或进行考试,并奖励膏火(即助学金)给成绩优异的贫寒之士。到清代由于受官府控制,问津书院会课除沿袭明代日、月、季会课外,每年春秋两季举行大会课,实际为科考之前的预科考试,参与者不限于本院生员[3]38。由上可知,问津书院在教学管理中尤其重视生员对儒家经典的学习,并给予适当奖励和宽松政策以激励生员勤攻苦读。
庙学一般都有“藏书阁”或“藏经楼”等设施,用来保存儒家典籍,也为教学提供资料、素材。早在明代,问津书院就设有藏书处并出版了图书。万历年间,黄冈知县林有鸣在《与康侯》(萧继忠,字康侯,康侯即萧继忠)信中说道“先师王塘南先生论学诸书贮之邺架(邺架即藏书处)……会纪一册皆先师所定”[6]8,这表明问津书院不仅设有藏书处,而且还组织儒师编写、出版图书。乾隆八年(1743年),问津书院建藏书馆,一方面为师生创造较好的教学研究条件,推动古代学术研究发展,另一方面,书院收集整理史料,编辑出版图书,极大地推动了地方文化事业的发展[8]。此外,书院也讲究书籍的典藏保管方法,规定每月打开书橱通风一到两次,每年六月或七月晒书一次,并在晾晒结束后进行清理查验。
1.3 经费管理与分院制
经费是保障庙学正常运转的重要条件。庙学一般都有稳定的学田及政府拨款作为日常办学经费,需要大修时会面向社会筹措经费。元代龙仁夫创办问津书院时,书院是民办性质,私人捐助是经费的主要来源。明中后期,书院的学田大部分来自地方士绅和书院管理人员的捐助。有时官府也会从其他款项中拨出银两来为书院购置学田,也有富户、官绅、民众购置学田再捐出,偶尔还会出现没收遭受惩戒的地方官员的田产划入书院的情况。明清时,书院田产多时曾达千余亩,全部出租佃户,收取课租。虽然不同时期问津书院经费来源有差异,但是私人捐助和官方拨款一直是其经费的主要来源。
问津书院对所属房产及田地等管理极为明细,如发现有不按章交租或侵占书院产业者,一并交官查办。例如,清乾隆十年(1745年)十月,黄冈知县邵丰緱对佃户张若愚侵占问津书院湖田一案进行审判,不仅杖打了其三十板,并且责令其偿还稞谷三石,要求其退还田亩;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华家畈有两佃农为谋取私利,擅自改动问津书院的田亩区划,书院理事将其送往官厅惩治,经官绅调解后,二人交还了侵占的田亩[3]31。此外,书院附近的林木也禁止砍伐。政府对书院田产和房产的保护,保障了办学经费,促进了办学的持续性。
中国古代书院众多,岳麓书院、东林书院、濂溪书院等虽在学术、政治等领域影响巨大,但在全国开设分院的却少之又少。明朝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问津书院于河南商城、汤池两地首创分院[9],即书院名同为“问津书院”,跨地域收取生员、授徒讲学。儒师蔡毅中在《复康侯》中言“明春仲先过汤池,然后过问津河,文才、高养邃当久脱颖”[10]23,一定程度上肯定了问津分院的办学成效。分院制扩大了问津书院办学规模,推广了问津书院教育理念和管理模式,提升了问津书院知名度和社会影响力。另外,分院还为当地培养了人才,服务于地方社会经济发展。问津书院独特的分院管理体制开创了古代书院开设分院的先河,对于促进庙学教育发展有着积极意义,是书院乃至庙学发展史上的典型代表[11]。
2 儒师:以精深学术为依归的教育宗旨
自先秦以来,儒家学说不断汲取养分进行自我更新和改造,从西汉董仲舒的“天人感应”到唐朝韩愈的“天命论”,再到宋朝的程朱理学,明中后期的陆王心学,充分显示了儒学强劲的生命力。儒学发展与儒士注重传承儒术,强调“为往圣继绝学”的精神密不可分。《问津院志》记载:“宋诸儒奋起于千三百年后,聚徒开讲,微文大义昭昭,揭日月而行江河,而后天下,后世晓然于人心天理之正。”[12]这表明问津书院儒师不仅承担着“传道授业解惑”的责任,而且肩负着正天理于人心的使命。
2.1 名师荟萃,造诣精深
庙学中供奉的古今儒师“象征着学术渊源,是学术传统的具体化”[13],激励着生员求学问道、修身立德。问津书院从小到大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广延名师的兴学策略。书院儒师邀请师门好友前来问津书院设坛讲学。比如,明代有王阳明、邹元标、耿定向、萧继忠、彭好古、顾宪成等,这些人都是当世顶尖学者。书院儒师还关心人才培养,参与书院管理。邹元标在书信《与萧康侯门下》中叮嘱萧继忠要严肃对待书院教育事业,“勿以儿戏作千古戏事”[3]249。高攀龙在《答萧康侯》信中也劝诫萧继忠要亲力亲为谋划书院发展,开拓书院教育事业。儒师参与书院讲学与管理,既有助于提高师生的整体学术水平,也有助于提升问津书院的教育质量。
书院以传承学术为旨归,重视学问研究与创新。问津书院名师云集,造诣精深,著作颇丰。龙仁夫,曾深入研究周敦颐、程颐、程颢、朱熹学说,精通经史、律历、阴阳之学,著有《周易集传》十八卷。《元史》称其见解“多发先儒之所未发”[14]9。吴澄,从年轻时校订五经,到中年采拾群言、以己意论断、条加记叙,探索朱熹研究五经未尽之意,直至晚年修成《五经纂言》,为元朝儒学的传播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萧继忠对先师耿定向的“当下本体”给予肯定,并提出了动静之说、无事之说等等。他的心性学,融合耿定向、高攀龙之学,颇为成功,实为问津书院一大成果[15]36。深厚的学术底蕴使问津书院在明中叶声播海内、名噪一时,人称可与白鹿洞、鹅湖、东林、首善诸书院媲美[3]20。
问津书院还是思想学说的策源地和传播地。宋元时期,问津书院是楚黄之地传播“廉、洛、关、闽”多学派的基地。明弘治至嘉靖年间,王阳明先后几次会讲于问津书院,吸引四方学子前来求学。此后,王阳明的弟子如邹守益、郭庆、吴良吉、耿定向、耿定理、耿定力等,均扎根问津书院传播陆王心学,使陆王心学成为当时问津书院最大门派,百年不衰。除陆王心学外,问津书院还有三大学术派别,分别是“以随处体验天理为宗”的江门学派,“以致良知为主”的姚江学派,“笃信程朱,力辟姚江之非”的东林学派[15]46。这些流派学说在问津书院兼容并存,营造出开放包容的学术氛围,既推动了书院学术研究的进步,又拓宽了生员的学术视野,激发了他们的学术潜力。
2.2 砥砺乐学,传扬儒术
先贤者以明道修德为主,先儒者以传经授业为主。历代大儒是儒学事业的开拓者,是儒学的脊梁。在他们的书信往来中尽显其严谨治学、进德修业的高尚人格魅力。儒师吴良吉年八十力学不倦,耿定向称其“屡空终身晏如也”[10]26,赞赏其甘于清贫仍刻苦研习的精神。邹元标晚年虽疾病缠身,但仍写信与好友萧继忠共勉,竭力追求“平平坦坦、朴朴实实、真真切切、濯濯皓皓”的品格[6]5。问津儒师中也不乏淡泊名利,绝意仕途,终生布衣,以讲学为己任者。如弃举子业、问道四方的盛朝衮,以授徒为业、布衣终生的谢天眷,学宗程朱、从者无数的胡居仁。儒师以砥砺乐学的精神,奉献于教育事业,体现着传扬儒术的决心。
庙学是传承儒学的载体,鲜明地传播着儒家的伦理道德观念,根据“传道”所涉及学术程度的深浅,讲学可分为学术原创性讲学、学理传播性讲学、学术普及性讲学。明代之后,问津书院讲学渐趋平民化。如《问津院志》记载,明代大学者冯从吾赴问津书院讲学,“一时缙绅学士执经问难,下至农工商贾环视窃听”[16],其讲学受众面之广,可见一斑。王阳明在剿匪历练中,深感“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故其主讲问津等书院时,利用行政权发布告渝,制订乡约,开办社学,实施乡村教化。王阳明在《社学教条》中规定,教师要“以启迪为家事,不但训饬其子弟,亦复化喻其父兄”[17]。这样一则教育了生员,二则生员可通过言行举止感化家人,使得礼让日新,风俗日美。总之,儒师把讲学与现实相结合,将圣贤学问通俗化、平民化,达到了传扬儒术、教化民众的目的。
庙学作为儒学的物质载体,不仅承载着传播儒学的学术使命,也成为弘扬王道的政治场所。问津生员刘子壮,清顺治六年(1649年)进京参加殿试,中一甲一名进士,状元及第。康熙初年湖广提学道蒋永修评价说,“他的殿试策万言,略谓二帝三王治本于道,道本于心,讲学为明心之要,修身为齐家、治国、平天下之本”[18]。可见,儒师潜移默化中已将儒家倡导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政治理想成功植根于问津生员心中。
2.3 立足讲堂,谆谆教导
庙学是培育人才的,科举是选拔人才的,在学而优则仕观念的影响下,庙学在科举取士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问津书院儒师指导生员应试科举可归纳为四要点:力求新颖,诚信考试,勤写诗文,字迹工整。第一,要求生员作答题目时另辟蹊径,力求提出新见解。因为作答之人盈千累百,唯有新意才能脱颖而出。第二,要求生员诚信考试,严禁作弊。书院会约规定生员在科举考试中“切勿徒事剽窃,微幸万一”[6]20,以告诫生员不可剽窃,不可抱有侥幸心理。第三,训练生员诗文写作能力。一是为应试科举,二是为以诗会友,加入宗派学社。第四,要求生员规范书写,字迹工整。书院会约指出,“笔笔正锋,字字法帖,小试最易制胜见长,标榜尽能出色成名”[6]21。可见,问津书院能够成为明清两代科举人才库,与儒师针对性的教学是分不开的。
问津书院儒师还十分重视教学方式的转变,注重运用历史经验教学法、誊抄传阅教学法和言行记录教学法。首先,书院学规规定每次讲会结束,生员必须就历史人物的得失各自发表观点,并与师友进行讨论、分辨,以史为鉴,从而端正自身言行举止。其次,书院要求生员互相传阅讲会中的优秀文章,传阅结束后,再选取最优等文章照原稿抄写清楚并保留原有批注,抄写四份并装订成册后由书院汇总,以供日后生员阅读学习。此外,书院讲会中的真知灼见以及学者之间的问辩,“不有记录,一飞鸟之音耳”,有鉴于此,书院安排专人记录[19]。这种做法使学术论辩情形和学术思想得以流传,从而成为生员学习的重要参考,也为后人提供了宝贵的研究资料。总之,教学方式的多样化对于指导生员自学、提高学习效率有着积极的作用。
最后,问津书院儒师对生员的求学态度十分关注,将虚心视为求学与处理师生关系的重要原则。首先,为学需要虚心,也就是要谦虚谨慎,把自己放在较低的位置,不可心浮气躁,方能有所长进。其次,对待儒师需要虚心。书院会约指出,“会文公请前辈到院,键门批阅,必有一种识见出人头地”[6]20,若有生员心中不服,对批阅结果存有异议,切勿妄加讥谈,貌受心非,不如虚心接受,日后思之,或添新见。清蒋永修在《重新问津书院碑记》中说道,与良师贤友交往,性情思虑会日益相近,但若“隔而不属,涣而不合,则心不虚之故也”[10]7。虚心求学不仅有助于精进学业,还可以拉近师生距离,达到亲师信道的效果。
3 生员:以修身立德为方向的教育目标
刑罚和教化,两者在国家治理中相辅相成。不过,儒家学者更强调教先于刑。董仲舒认为刑罚只能给人以肉体的疼痛,并不能真正触及人的内心,但教育则可以通过引发人的内心良知,凝聚人心,从而形成良好的道德氛围,使平民百姓耻于假恶丑。作为儒家德政思想的延伸,庙学践行着“以德化人”的教育理念。庙学蕴含着“庙”与“学”的教育功能,既通过立庙祀孔为莘莘学子树立进德修业的精神旗帜,又通过兴学立教指导生员掌握进德修业的具体方法。
3.1 以德为本,学以修身
俗语有云“以德为先,以学为上”。德育是学校教育中最基础、最根本的工作。两宋时期,庙学尤重生员的道德品行,并将其定为录取的重要条件。庆历四年(1044年)规定初入学者“须有到省举人二人委保”,即道德品行良好且被担保的生员才可入学。宋徽宗崇宁年间,又提出以孝、悌、睦、姻、任、恤、忠、和“八行”作为生员的道德标准。为加强道德教育,问津书院确立了“讲道论德、明体达用”的办学方针。山长耿定向也极力主张大学首明德。清蒋永修在《重新问津书院记》中也说,建立问津书院的目的是“力孝弟,明仁义”[10]6,使生员遵孝道、明仁德、守气节。
庙学作为传承儒学的主要阵地,首重生员德行之养成。问津学规六则中,放在第一位的即为德行。萧继忠提出,“吾辈即望圣学修身为第一吃紧”,他要求生员向君子看齐。书院学规规定每逢讲会,生员须商讨近日大小事宜,以供师友判别,须积极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切勿面谀而心非、意拂而耳受,要诚心听取师友规劝,真心改过向善。高攀龙在《寄康侯》信中指导萧继忠办学应“全在修身作极”[6]7。宁咸在《论知本与康侯》中言“无修无证,此既谀己又后谀人,虚浪一生”[6]5。他警醒生员唯有时刻修身,方可求真务实,做到既不谄谀他人,也不欺骗自己,才能避免生命空虚放浪。
庙学作为祀孔和教学的统一体,它所供奉的往圣先贤,不仅是道德的载体,更是学识的象征。德行和学识贯穿于问津生员修身的全过程。邹江遐订立问津会约,只以人品学问四字为归宿。宋元之际,吴澄讲学于问津书院时指出,治学必以德行为本。他曾对生员说,求学若不从道德品性出发,就只能停留于做出言语上的解释罢了。吕德芝在《问津书院记》中称赞问津生员勤勉求学、进德修业之风。他说:“吾黄之士,日得仰其温良恭俭之容,思其文行忠信之教,鼓其进德修业之气,惕其出王游衍之心,则是志于道,而谨子弟之率者,问津者也。”[20]
3.2 静坐居敬,知行合一
庙学中规定生员进德修业,不仅是对先贤先儒的认同,更是对他们所代表的儒家价值观、道德准则和践行方式的传承。问津书院提倡静坐与居敬为一体的道德修身法。明成化年间,陈献章讲学问津书院,他认为学习劳碌则没有办法洞彻真理,反对通过大量繁重阅读来增长学识,提倡在静坐中推测事物的变化始末[3]12。高攀龙着重强调人要在静中体悟出自然善性,则能停止妄念,清除邪念[6]6。张栻讲学问津书院,为学主“明理居敬”。他指出,明理(即道德认识)和居敬(即道德涵养)是道德教育的两个重要方面,两者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影响,道德涵养越深厚,道德认识则越精准,道德认识渐渐明晰,道德涵养则越高,因而两者应同时并进[14]5。
问津书院还倡导知行合一的道德修身法。自龙仁夫创建问津书院到王阳明讲学问津书院,程朱理学是问津生员学习的主要内容。王阳明来问津书院讲授心学,使院内生员耳目一新。王阳明心学思想主要是“知行合一”,即一方面强调道德意识的自觉性,要求人在内在精神上下功夫,另一方面强调道德行为的实践性,指出人要在实事上磨炼自己,做到言行一致、表里如一。可以说,“知”与“行”共同组成衡量“道”的标准。因而,问津书院不仅要求生员领悟圣贤道理,而且规定生员须将领悟到的圣贤道理付诸实践。据《续修问津院志叙》记载,问津书院师生每月一聚,“条规讲说,兢兢于实践躬行”[4]657。
知行合一道德修身法的重要表现即将立志与笃行相结合。王阳明在《送郭善甫归学》一文中言:“君子之于学也,犹农夫之于田也。”[21]他认为君子做学问就像农夫种田,立志即播种,思辨笃行就和农夫耕种灌溉、勤力劳心以求秋季丰收一样。若农夫种田仅播种而不耕作,则谷物不能成熟。因此,研究学问不光要立志,还须笃行。问津生员金德嘉,少时求学常无米为炊,但好学励行,颇有壮志,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中进士,后掌修《大清一统志》,闭门著述二十余年,为清初一大硕儒[22]。如此,果能将立志与笃行的关系迁移到学习中,方能学有所获、学有所成。
3.3 质疑求真,明体达用
为践行儒家修齐治平的教育理念,培养一大批认同并忠诚于国家和民族的儒士,庙学表征了儒家的教育理想与追求,凸显了儒家教育志向。“问津”的“津”字,意指渡口。孔子使子路去“问津”,难道仅仅是去问过河的渡口吗?问津的真正意义在于找到前进的方向,即教育的求真精神[23]。书院学规要求生员平日与师友讨论中,做到勤学不辍,养成打破砂锅问到底的学习习惯。儒师邹元标提出“人要做真人,学要明真学”[3]250。他强调生员在精进学问的过程中要脚踏实地、实事求是,以求人品学问有真长进。这些理念与信条对于引导生员坚守求真品质、立志成为有真才实学之人起到了积极作用。
求真精神需要问题意识和质疑思维,二者缺一不可。朱熹尤其强调问题意识对个人求学的重要性。他认为,读书须有疑问,能提出问题的人才能钻研到精深微妙的地方。问题意识决定求学的方向,有了问题意识,才知道从哪儿着手钻研。对于生员而言,只有当疑问渐渐扫除,达到融会贯通的程度,才称得上是学到了。其次是质疑思维。陈献章在问津书院讲学时告诫生员,在治学和求知的道路上,一旦人云亦云,只会助长自身惰性,从而丧失独立思考的能力。反之,生员要勤加思考,敢于质疑,提高辨别力。如此,生员若能具备问题意识和质疑思维,那么距离“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的境界也就不远了。
儒家一贯提倡入世理念,明体达用向来是圣贤孜孜以求的立教目标。“明体达用”即精通经义,深明道体,通晓古今,掌握治事,致用于世[24]。北宋胡瑗为贯彻明体达用教育主张,首创分斋教学法,设经义和治事二斋,治事斋分设军事、水利、治民等科,培养了一批学有专长的经世致用之才。明体达用也是问津书院的教育宗旨。书院学规规定,“凡学问,心性其体也,经济其用也……每会必将平日所斟酌兵农礼乐诸大制度一一互订”[6]3。所谓“兵农礼乐”即兵事、农业、礼仪、教育等实用之学。清光绪六年(1880年),问津生员王丕厘中进士,皇帝曰:“汝文有底有面,平时看何书?”其对曰:“日月经史兼看经世有用之书。”[3]179由此可知,在明体达用教育思想指导下,问津书院注重培养实用之才。
4 问津书院办学活动的历史借鉴
庙学自两汉初创,到魏晋南北朝形成庙学制。进入唐朝,庙学制逐步制度化、规范化,到宋元时期被普遍认同,于明清之际庙学遍布天下,至清末新学制建立,庙学分离。纵观问津书院由孔庙至庙学,由庙学至书院,由书院至学堂,到成为文化古迹,前后有两千多年历史,为社会培养了大量人才,改善并活跃了楚黄之地的学术文化氛围,为湖北尤其是鄂东地区教育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问津书院不仅使庙学所承载的历史文化和教育传统凸显于世人面前,而且为当今高校办学育人提供了诸多借鉴。
第一,坚持立德树人方针,培养德才兼备人才。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问津书院采用日常考查和期末考试的方法对生员进行德行与学业双重考察,尤其把道德品性考察放在第一位。书院里的名儒大师以身作则,躬亲践行着“服民以道德,渐民以教化”。育人成才的根本在于立德铸魂。因此,高校要秉承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积极推进课程思政建设,以形式多样的德育活动,引导学生从自身做起,加强品德修养,从知情意行着手,培养大爱大德大情怀之人。在此基础上,高校还应注重学生综合能力的培养,发展核心素养,促进道德与技艺的双修并进。
第二,贯彻学术自由理念,践行名师治校原则。问津书院名儒汇集,学派分宗,兼容并包。问津会约指出,每一种见解必有其渊源,彼此碰撞需要相互理解、包容。百余名儒学大师前来讲学,问津书院也由此文脉绵延,掀起了“开绛帐以传经,下缁帷而课读”的勤勉求学之风。此外,儒师既钻研学术,也参与管理,对于书院事业立定主宰,极力肩当,使其不落窠臼。对于当今学校尤其高等院校而言,应大力倡导教授治校,让教授群体参与制定办学方针大计,给予名师教授学术事务决策权,让教育回归本质,助推世界一流大学建设。
第三,构建和谐师生关系,实现教学相长目标。问津书院师生之间互学互助,关系融洽。儒师一方面鼓励学生各尽所长、勤勉进取;另一方面用自身文化修养去影响、感召学生,最终达到言传身教的效果。尊师爱师本是中华传统美德,但近年来,师生关系冷漠化在各高校中普遍存在,中小学师生矛盾也时常升级,这引起了人们对如何构建和谐师生关系的思考。高校中教师与学生是志同道合的伙伴,教师有自己的学术理想和教书育人的责任感,学生也有着自己的学业追求,双方若能积极沟通,互相尊重理解,有助于实现教学相长。
第四,注重规约章程建设,完善教学管理制度。不以规矩,无以成方圆。围绕“讲道论德,明体达用”的办学宗旨和教育方针,问津书院制定了基本章程,规定读书治学、进德立品、修身养性的程序和方法,希望生员志存高远、躬亲践行、德才兼备。此外,问津书院对于生员入学、肄业、考勤、考试、奖惩均从制度上订立了标准;对山长和师资的选拔也有严格的程序;教学、后勤等管理均有章可循。在管理制度的引导、鞭策下,大批生员清节自励、好学不懈。因而,高校办学同样须注重规约章程建设,从而规范师生言行举止,并内化为慎独、自律的精神,促进学校办学上层次、上水平。
第五,倡导多元主体模式,吸引民间资本办学。自明中后期开始,问津书院的学田大部分来自地方乡绅和书院管理人员的捐助,而士绅们多是曾就学于问津书院的生员。此外,书院管理也主动邀请当地富商、名宦参与并主持问津书院每年的春秋祭祀典礼等大型活动。对于当今高校而言,一方面,要重视校友会的建设,维系校友们的母校情节,利用适当时机为学校吸纳、充实办学资金;另一方面,鼓励企业家参与办学,注重发展与地方政府的关系,积极争取地方教育财政的投入,多渠道筹措教育经费,以促进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
5 结语
汉初大儒叔孙通曾言:“夫儒者难与进取,可与守成。”儒家文化是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促进国家有序发展的优质文化。“庙学合一”是儒学教育的载体,是我国古代教育的原生态。唐宋以后要求因庙设学、庙中有学,形成了“由学尊庙、因庙表学”的教育体系[25]。问津书院发展庙学教育长达一千多年,成为讲学论道、文化交流、培养人才、社会教化的场所。问津书院的教育成就,与历代学者的耕耘不辍和地方乡绅百姓的大力支持紧密相关。问津书院承载着人们对美好德行的崇敬与向往,对真理的坚定追求,对求真求善的不懈努力。如今,我们考察问津书院发展史,研究问津书院的办学与教学活动,一方面有助于充实和丰富我国儒学发展史,体现庙学研究的理论价值,另一方面也有助于传播优秀传统文化,弘扬新时代主旋律,为当今治理社会建言献策,体现庙学研究的现实价值。
[1] 皮明庥.武汉通史:秦汉至隋唐卷2[M].武汉:武汉出版社,2006:77.
[2] 邓洪波.中国书院史[M].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4:88.
[3] 李森林.江黄学府——问津书院[M].香港:香港天马图书出版社,2002.
[4] 赵所生,薛正兴.中国历代书院志•问津书院志[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5.
[5] 刘元.地方士绅与地方文化秩序建设——以湖北问津书院为中心的研究[J].兰州学刊,2013(4):57.
[6] 王会厘.问津院志:卷四[M].光绪三十二年.
[7] 汪刚.浅论问津书院的教育理念、模式及对现代教育的启示[D].武汉:华中师范大学,2014:11.
[8] 任继愈.中国藏书楼[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01:77.
[9] 新洲县志编纂委员会编.新洲县志[M].武汉:武汉出版社,1992:531.
[10] 王会厘.问津院志:卷六[M].光绪三十二年.
[11] 蔡志荣,周和义.书院与地域社会:《问津院志》的文献价值[J].兰台世界,2009(24):69.
[12] 余文祥.问津诗赋[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4:238.
[13] 广少奎.斯文在兹,教化之要——论文庙的历史沿革、功能梳辨及复兴之思[J].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7(5):129.
[14] 李森林.问津人物[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4.
[15] 谢新明,陈元生.问津史话[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4.
[16] 刘元.问津书院对湖北地方文化的影响[J].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5):49.
[17] 邓洪波.儒学诠释的平民化:明代书院讲学的新特点[J].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3):26.
[18] 邓洪波,龚抗云.中国状元殿试卷大全(下)[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6:1340.
[19] 周洪宇,申国昌.中国教育活动通史第5卷:明清[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17:304.
[20] 陈谷嘉,邓洪波.中国书院史资料(中)[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1060.
[21] 张武.问津文论[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4:194.
[22] 湖北省武穴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广济县志[M].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4:845.
[23] 高双桂.孔子河畔话问津[M].武汉:武汉出版社,2017:2.
[24] 余永德.中国教育研究文集[M].芜湖: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73.
[25] 王雷.教育文物:书写在大地上的教育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16.
Temple Academy and Education——The Educational Concepts and Practice of Wenjin Academy
LI Yong1,2, ZHANG Qunlin3
(1. Wuhan Research Institute, Jianghan University, Wuhan, Hubei 430056, China;2. College of Education, South-Central Minzu University, Wuhan, Hubei 430074, China; 3. College of Ethnic Education, Shanxi Normal University, Xi'an, Shanxi 710062, China)
Temple academy is a combination of temple and academy. It is not only a place to worship Confucius, but also a place to carry out teaching activities. Wenjin Academy, also known as Xinzhou Confucius Temple, was built in the Western Han Dynasty. It got its name from the allusion of Confucius' making Zilu ask for ferry. Du Mu, the governor of Huangzhou in the Tang Dynasty, built a temple here to worship the sages and set up a precedent for education, forming a system of integration of temple and academy. During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emple academy for more than one thousand years, Wenjin Academy has formed the educational aim based on profound learning, the educational goal based on self-cultivation and morality, and the educational management oriented by service guarantee. The above-mentioned educational ideas and practices are in fact the model of temple academy education in ancient region Chu and Huang. The experience of Wenjin Academy in running a school and studying mainly lies in the following aspects: adhering to the policy of moral education and cultivating talents with both ability and political integrity; carrying out the idea of academic freedom and practicing the principle of managing the university by famous teachers; building a harmonious relationship between teachers and students to achieve the goal of teaching and learning; paying attention to the construction of rules and regulations to improve the teaching management system; advocating the mode of multiple subjects and attracting private capital to run schools.
temple academy; Wenjin Academy; Xinzhou Confucius Temple; Confucianism; Confucian culture
10.3969/j.issn.1673-2065.2022.04.016
李 永(1982—),男,河南许昌人,副教授,教育学博士;
章群琳(1998—),女,江西九江人,在读硕士。
江汉大学武汉研究院开放性课题《武汉文庙研究:以新洲孔庙(问津书院)为中心的考察》(IWHS20182005);中南民族大学“课程思政”示范课程:《中国教育思想史》(KCSZX21018)
G529
A
1673-2065(2022)04-0082-08
2021-08-23
(责任编校:李建明 英文校对:李玉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