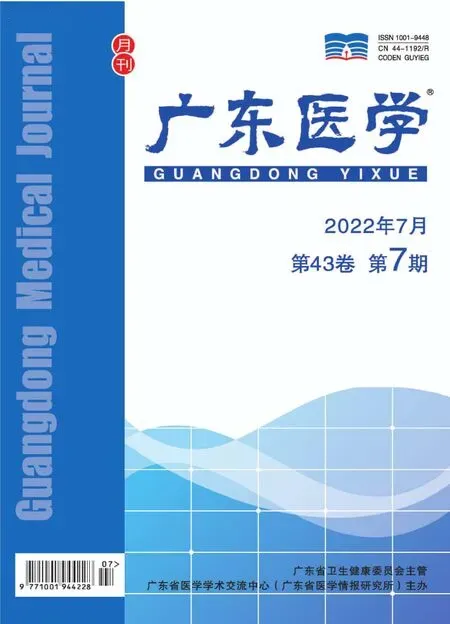免疫检查点抑制剂所致肿瘤超进展的研究进展*
廖力为, 张珑山, 席菁乐, 官键△
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 1放疗科, 2肿瘤内科(广东广州 510515)
免疫检查点抑制剂(immune checkpoint inhibitor,ICI)通过抑制肿瘤程序性细胞死亡受体-1(programmed cell death 1 gene,PD-1)、程序性死亡配体-1(programmed death ligand 1 gene,PD-L1)和细胞毒性T淋巴细胞相关蛋白-4(cytotoxic T-lymphocyte-associated protein 4,CTLA-4)等免疫检查点信号,重新激活机体抗肿瘤免疫反应识别并杀死癌细胞,是近年最有前景的肿瘤治疗方式之一[1]。美国FDA已批准7种ICI[2]:唯一的CTLA-4单抗伊匹木单抗,3种PD-1单抗:帕博利珠单抗、纳武利尤单抗和西米普利单抗,还有靶向PD-L1的阿替利珠单抗、阿维鲁单抗和德瓦鲁单抗。帕博利珠单抗、纳武利尤单抗和阿替利珠单抗已在国内获批上市,此外还有特瑞普利单抗、信迪利单抗、卡瑞利珠单抗和替雷利珠单抗4种PD-1单抗,以及抗PD-L1的度伐利尤单抗。这些药物已成功应用于黑色素瘤[3]、非小细胞肺癌[4](non small cell lung cancer,NSCLC)、头颈鳞癌[5]、肾细胞癌[6]等恶性肿瘤的治疗,能显著改善部分患者的预后,尤其对一些放化疗不敏感的肿瘤有独特疗效,同时患者经ICI治疗后体内形成的肿瘤免疫记忆能延长治疗效应[7]。然而,目前患者ICI治疗的获益率普遍不高,不同个体的治疗结局常差异巨大。ICI的治疗结局包括完全缓解、部分缓解、疾病稳定、疾病进展[8]。此外,部分肿瘤进展的患者经ICI治疗后肿瘤反而加速恶化,进展极快,该现象被称为肿瘤超进展(hyperprogression disease,HPD)[9]。HPD患者中位总生存期仅约3个月[9]。因此,接受ICI治疗的肿瘤患者同时也面临着加速肿瘤进展的风险。HPD已成为ICI临床应用中的巨大挑战,探究HPD的发生机制、预测指标对于ICI的合理临床应用至关重要。
1 HPD的定义
HPD暂无标准定义,多是通过一些临床指标进行判断,包括:肿瘤生长率(tumor growth rate,TGR)、肿瘤生长速率(tumor growth kinetics,TGK)、快速进展(fast progression,FP)、治疗失败时间(time-to-treatment failure,TTF)、肿瘤负荷、新增病灶数等。最初的HPD概念基于TGR评估[9],后来也有研究以TGK为评价指标[10]。TGR和TGK的计算都基于RECIST标准,TGR即肿瘤体积的变化率,TGK是肿瘤大小变化率,肿瘤大小用所有靶病灶直径之和表示。ICI治疗后与治疗前的TGR/TGK比值>2则达到HPD的标准,但该标准存在诸多局限[11]:首先,临床资料要求高,TGR/TGK的计算至少需要患者ICI治疗前中后3次的影像学数据。其次,肿瘤转移是肿瘤进展的重要表现,但TGR/TGK未能关注到ICI治疗后出现的非靶病灶,也无法区分肿瘤转移和普通进展。再者,影像学变化不明显的HPD也易被忽略。鉴于以上局限,新增病灶[12]、FP[13]、TTF和肿瘤负荷[14]相继被列为替代评估指标。FP的条件为:从基线到第1次评估(6周),最大径之和增加50%;或在无CT数据的情况下,患者在12周内因HPD死亡。TTF是指初次免疫治疗到评估HPD的时间,HPD的TTF应<2个月,时间跨度过长可能会将肿瘤自然进展、继发性抵抗等情况误判为HPD。另外,肿瘤负荷相比于基线期增长超过50%也被增添为HPD的判定条件之一。一般认为,在免疫治疗后2个月内,TGR/TGK增加>2,肿瘤负荷增加>50%,新增病灶>10或满足FP的肿瘤患者都可认定为发生了HPD。
HPD与进展、免疫相关不良反应(immune-related adverse event,irAE),还有假进展等概念有本质区别。HPD与进展的区别在于速率,短时间内肿瘤体积增长的程度需远超肿瘤自然恶化的情形。假进展实为炎性细胞浸润肿瘤导致的治疗初期影像学上的假性增大[15],但最终肿瘤仍会消退。所以假性进展患者一般体能状况良好,疾病症状可能缓解,而HPD患者多伴随全身情况急剧恶化。免疫相关不良反应是免疫功能激活增强后引起的皮肤、胃肠道、肝脏等器官的炎症反应,非肿瘤侵犯所致[16]。但很多时候,仅凭患者的临床表现和影像学检查难以准确鉴别这些治疗反应。因此,为了准确评估患者的治疗反应,合理临床用药与决策,需深入研究HPD的机制和预测方法。
2 HPD的相关因素和机制
HPD并不罕见,在ICI治疗的肿瘤患者中发生率约为4%~29%[17]。HPD的发生与患者特点、用药方式、临床指标变化、基因改变、肿瘤微环境等多方面因素均相关。
2.1 患者特点 HPD无明显的癌种特异性和差异性[9,18-19]。肿瘤转移的部位和数量较肿瘤性质更值得注意。一项关于晚期胃癌的研究指出肝转移瘤的发生与HPD呈正相关[20]。在NSCLC中,基线存在肝、骨转移的患者出现HPD的比例也更高[21]。一项关于多癌种的HPD患者Meta分析显示,癌转移灶多于2个或是有肝转移的患者更高发HPD[22]。年龄因素颇具争议,高龄(>65岁)[9, 23]和相对低龄[24-25]在不同研究中均被报道为HPD患者的特点[25],还有研究否认年龄与HPD有关[18, 26]。
2.2 用药方式 临床常用的ICI包括PD-1/PD-L1单抗和CTLA-4单抗两大类。使用PD-1/PD-L1单抗类药物的HPD患者的报道居多,且PD-1单抗与PD-L1单抗对HPD的诱发无明显差异,而单独使用CTLA-4单抗导致的HPD少有[27]。此外,PD-1/PD-L1单抗与CTLA-4单抗联用时发生HPD的病例也较少。这说明不同ICI诱发HPD的概率不同,而肿瘤内源性PD-1是其诱发的可能原因。PD-1最初被认为只表达于免疫细胞,但近期研究发现黑色素瘤[28]、肝癌[29]和NSCLC的部分肿瘤细胞也可表达PD-1,即内源性PD-1。其中,内源性PD-1在7种人肺癌细胞系和小鼠NSCLC细胞系M109中表达,且使用PD-1单抗或敲除PD-1可增加M109的克隆源性和存活率[30]。因此,内源性PD-1表达高的NSCLC患者使用PD-1单抗治疗反而可能促进肿瘤生长。此外,先行放疗也与HPD的发生有关[24, 31],一项关于复发或转移头颈鳞癌的回顾性研究发现所有的HPD患者均在照射区域有至少一处的局部复发[24, 31],但该现象缺乏机制解释。接受先行化疗的HPD患者也不在少数[32-33],且在化疗和靶向治疗中也有HPD的报道,但发生率远不及ICI[34-35]。
2.3 临床指标 一些与免疫和炎症相关的临床指标也有助于预测HPD。例如,ICI治疗泌尿系肿瘤后外周血淋巴细胞数增长>30%的患者发生HPD概率更低[34-35]。中性粒细胞与淋巴细胞占比(neutrophil-to-lymphocyte ratio,NLR),乳酸脱氢酶和血小板计数均与HPD发生呈正相关[34-35]。NLR和血小板/淋巴细胞比率亦是NSCLC免疫治疗的独立预后因素,二者升高提示更短的总生存期和无进展生存期,治疗应答率也更低[36]。NLR也与乳腺癌的预后呈负相关[37]。在黑色素瘤中,乳酸脱氢酶高提示预后更差[38-39]。中性粒细胞和血小板可释放TGF-β、血管内皮生长因子、IL-6、IL-8等多种趋化因子和细胞因子,促进肿瘤炎症和免疫抑制[40]。炎症同时也是HPD的可能机制之一:免疫检查点在正常机体受到感染时可阻止有害炎症因子的过度产生,因此HPD本质上可能是机体因免疫检查点受抑制而产生的一种过度炎症反应[41]。
2.4 基因标志物 随着分子生物学和基因组学的发展,寻找可靠的HPD生物标志物已经成为研究热点之一,但暂无公认、特异的HPD生物标记。其中,鼠双微粒体基因2/4(murine double minute 2/4,MDM2/MDM4)扩增和表皮生长因子受体基因(epidermal growth factor receptor,EGFR)突变是报道最多的两种基因改变[14, 42-44]。MDM2/MDM4是凋亡核心基因P53的2个主要负调控基因,MDM2/MDM4缺乏可激活P53信号,导致细胞凋亡或细胞周期阻滞[45],因此MDM2/MDM4也是潜在的肿瘤治疗靶点[46]。MDM2拮抗剂APG-115联合PD-1单抗治疗后的皮下瘤小鼠模型抗肿瘤能力明显增强,且肿瘤浸润的CD8+T细胞和M1型巨噬细胞明显增多,同时M2型巨噬细胞比例显著下调[47]。这说明MDM2/MDM4可能通过P53途径调节免疫细胞的肿瘤浸润情况,影响ICI的疗效。突变的EGFR异常激活,可通过Ras/Raf/MAPK, PI3K/AKT, PLC-PKC和 STAT等途径促进肿瘤细胞增殖[48]。另外,EGFR还能经ERK1/2/c-Jun通路上调肿瘤的PD-L1表达以促进肿瘤免疫逃逸,降低ICI疗效[49]。
ICI的重要靶点PD-1/PD-L1也与HPD密不可分。在一项多癌种研究中,基于外周血测序结果筛选出2个HPD高度相关基因[44],包括PD-L1和血管内皮细胞生长因子受体基因-2(vascular endothelial growth factor receptor 2 gene,VEGFR2)。胃癌患者的PD-L1低表达也提示HPD高风险[50]。需注意,PD-L1基线水平高的患者仍可发生HPD。一例PD-L1阳性率高达98%的患者经帕博利珠单抗治疗后发展为HPD,而患者尸检病理的PD-L1阳性率却不足10%[50]。这说明PD-L1表达水平可随治疗变化,且该变化可能与HPD相关。
其他HPD标志物的报道相对零散。例如,在一项多癌种研究中,鼠类肉瘤病毒癌基因(kirsten rat sarcoma viral oncogene,KRAS)和丝氨酸/苏氨酸激酶11基因(STK11)的突变仅在HPD患者中检出[51]。单核细胞趋化蛋白-1(monocyte chemotactic protein 1,MCP-1),白细胞抑制因子(leukocyte inhibition factor,LIF)和CD152的基线血清水平与胃肠肿瘤HPD的发生呈正相关[52]。Notch突变也在HPD患者中被报道[53-54]。
2.5 微环境 肿瘤微环境由肿瘤细胞、免疫细胞、成纤维细胞、附近的间质组织、微血管及各种细胞因子和趋化因子等构成。其中,T细胞功能障碍可能是HPD发生机制之一。HPD患者治疗前后的CD28-CD4+T淋巴细胞(CD4+Thd)计数均高于其他患者[55]。CD28是T细胞增殖活化所必需的共刺激分子,同一抗原反复刺激可产生CD28-T细胞,所以CD28-CD4+T细胞也是一种慢性炎症的标志物[11]。HPD患者在第1轮ICI治疗后全身循环衰老CD4+T细胞(circulating senescent CD4 T cells,Tsens)也迅速增殖[56]。在转移或复发的NSCLC中,HPD患者治疗前的效应或记忆T细胞(CCR7-CD45RA-T细胞)/总CD8+T细胞比例与HPD呈负相关,PD-1+CD8+T细胞中的严重耗竭T细胞占比与HPD呈正相关[19]。此外,调节T(T regulatory,Treg)细胞也参与了HPD的发生[57-58]。Treg细胞是一类起免疫抑制功能的特殊CD4+T细胞,其中效应Treg(effective T regulatory,eTreg)细胞是主要的肿瘤浸润Treg亚型。胃癌HPD患者经PD-1阻断治疗后肿瘤浸润的Ki67+eTreg明显增加,提示Treg细胞可能通过抑制免疫使肿瘤进展[57-58]。此外,HPD患者的肿瘤相关巨噬细胞浸润比其他患者丰富[59],尤其是CD163+CD33+PD-L1+类M2型巨噬细胞,且消除小鼠巨噬细胞后无类似HPD现象发生。另外,去除Fc域的纳武利尤单抗也无法诱发小鼠HPD。PD-1/PD-L1的单抗Fc域能与Fc域受体阳性的巨噬细胞结合,诱发抗体依赖的细胞介导的吞噬作用(ADCP)[60],因此PD-1单抗Fc域介导的巨噬细胞浸润可能是诱发HPD的关键。
3 HPD干预方式
HPD暂无特异性治疗药物,其防治重在于预防和早期发现。多药联用是热门的预防策略之一[61]。研究表明,PD-1/PD-L1单抗与CTLA-4联用时HPD的发生率更低[62]。靶向HPD相关异常基因的药物与ICI的联用也值得期待[61],且前文提到的动物实验中已有积极的结果报道。肿瘤导致的异常代谢环境会影响免疫细胞功能,因此ICI与代谢检查点药物联合治疗肠癌可能有助于提升疗效,同时降低HPD发生率[63]。另外,对ICI单抗药物改构修饰可去除Fc域的ADCC/ADCP功能,减少不可控的不良反应[64],也是预防HPD的策略之一,但同时也可能削减ICI的抗肿瘤疗效。进行ICI治疗的患者需动态关注影像,RECIST评估系统建议患者在经ICI治疗出现进展的4~8周后应再次行CT随访以确认是否为真性进展。并且影像学诊断有望成为早期评估的重要方式,但目前暂无成熟的免疫相关影像学标志,未来可通过人工智能、机器学习、统计学和数据库等交叉方法结合大规模影像数据进一步探索[65]。简便的液体活检有望用于HPD的预测和诊断[66]。研究发现,血浆中的游离DNA的基因组不稳定指数(genome instability number,GIN)增长>25.19单位/d时高度提示HPD[67]。还有研究通过对肿瘤组织测序分析,建立了一个用于预测和鉴别HPD患者的基因集[41]。然而,这些干预手段尚未成熟,需进一步探索、完善及验证。
4 展望
随着免疫治疗的推广应用,HPD的相关报道日益增多。HPD严重威胁肿瘤患者预后,其发生率不低,在不同癌种、不同ICI治疗的情形中均有报道,值得高度重视和研究。然而,目前相关研究以回顾性为主,其样本数量有限,纳入癌种常常混杂,且HPD定义多样,所得结论未必有很强的参考性。因此,为从宏观上更深入地了解HPD,多中心、大样本、单癌种的前瞻性研究和一个统一公认的HPD定义是必需的。
HPD与患者特点、用药方式、临床指标变化、基因改变、肿瘤微环境等多方面因素有关。肿瘤生物学特性激活和肿瘤微环境改变在HPD发生中起重要作用。当前研究集中于对HPD患者治疗前后肿瘤微环境变化现象的报道,其内在机制不明;肿瘤微环境的组分极其丰富,除T细胞及巨噬细胞外,微环境中细胞因子[68]、成纤维细胞[69]等组分都可介导产生ICI治疗抵抗,但它们与HPD的关系仍有待探究。此外,除了利用临床样本,成熟的HPD动物模型也需建立,以探究HPD发生发展的内在机制。
ICI治疗前评估和治疗中早期监测对于预防HPD至关重要。早期识别HPD的高危患者对于能否进行有效的ICI治疗非常关键,其中液体活检监测HPD基因标记物及影像学诊断是两种颇有潜力的预测手段。因此,急需寻找可靠、可早期预示HPD的生物学和影像学标志物。此外,联合用药有望预防HPD发生,但有待临床试验证实。总之,目前HPD暂无有效的预测方法及治疗手段,寻找特异的预测指标及有效的临床治疗策略是ICI治疗中亟待解决的棘手问题。
利益相关声明:所有作者共同认可文章无利益冲突。
作者贡献说明:廖力为负责论文撰写,完成相关文献资料的收集和分析;张珑山参与文献资料的分析和整理,论文校对;席菁乐指导论文写作及资料审核;官键是论文的构思者及负责人,指导论文写作。所有作者均阅读并同意最终文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