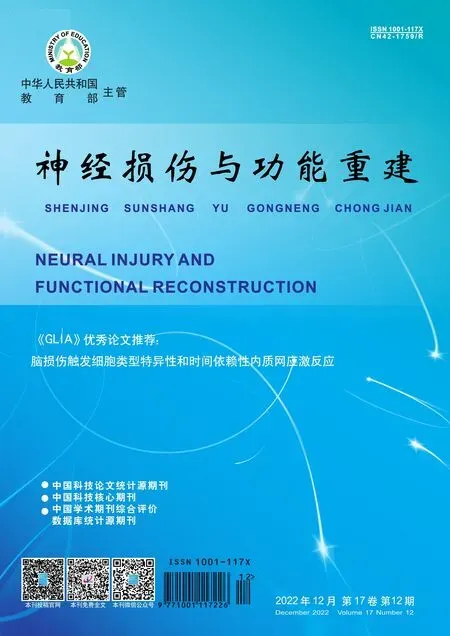血清炎性标志物在脑出血预后评估中的作用研究进展
王靖萱,陈丹阳,王佳慧,张萍,唐洲平
1 前言
脑出血(intracerebral Hemorrhage,ICH)是死亡率最高的卒中类型,1/3的患者在发病的第1个月内死亡,幸存者留有不同程度的残疾和再出血风险[1]。ICH不仅会引起原发性脑损伤,还会引起继发性脑损伤,氧化应激和炎症在损伤机制中起到重要作用。因此,尽早评估ICH的严重程度和预后有利于快速确定最佳治疗方案[2]。生物标志物在神经系统疾病的诊治和预后评估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中炎性标志物是ICH严重程度和预后评估中应用最多的生物标志物[3],现将其研究进展综述如下。
2 炎性标志物与ICH
2.1 中性粒细胞与淋巴细胞比例(neutrophil/lymphocyte ratio,NLR)
NLR增加表明中性粒细胞相关炎症反应增加,淋巴细胞介导的抗炎反应减少[4]。整体NLR越高,炎症反应越强烈[4]。Lattanzi等[5]研究发现,NLR越高,ICH患者3个月后的预后越差。Tao等[6]进一步发现,NLR水平升高可独立预测ICH后90 d的不良预后。而Sun等[7]得出了不同的观点,即高NLR水平与ICH患者的不良预后无关。由于这一争议存在,Liu等[8]进行了荟萃分析,结果发现较高的NLR是ICH患者90 d严重残疾和短期死亡率较高的预测因子,但不是住院死亡率的预测因子。此外,Yang等[9]发现,血浆纤维蛋白原(Fibrinogen)和NLR联合评分(F-NLR)要比单独NLR具有更好的预后预测效果,提示可以结合其他血清标志物,提升NLR对ICH预后的预测能力。
2.2 白细胞计数
一些研究发现,血清白细胞计数和ICH血肿扩大呈相关性,中性粒细胞计数越高,血肿扩大的风险越低,而单核细胞计数越高,风险越高[2,10],提示白细胞计数可能影响ICH预后。Agnihotri等[11]研究认为,外周血白细胞计数可作为3个月时不良功能结局的独立预测因素。然而,Yu等[13]随机对照试验结果显示,急性ICH患者白细胞计数与90 d时死亡或残疾之间没有直接联系[12]。Di Napoli等[13]研究也认为白细胞计数不是ICH死亡的独立预测因素。基于此,未来需要更多大样本量的多中心研究进一步确认。
2.3 S100钙结合蛋白A12(S100 Calcium Binding Protein A12,S100A12)
S100A12是S100钙结合蛋白家族的成员,通过与糖基化终产物受体的结合激活细胞内信号级联,诱导靶细胞中的促炎反应。循环S100A12水平已被证明与严重创伤性脑损伤患者的炎症反应、病情严重程度和短期死亡率密切相关[14]。Qian等[15]前瞻性收集了182名健康对照组和182例ICH患者症状出现后24 h内的情况,采用多变量分析评估了血清S100A12水平与30 d内ICH患者死亡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S100A12是ICH后30 d死亡的独立预测因子[15]。Qiu等[16]人的研究,进一步发现了高血清S100A12水平与美国国立卫生院脑卒中量表(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 Stroke Scale,NIHSS)评分、血肿体积、血清C反应蛋白水平、早期神经功能恶化和3个月不良预后独立相关。然而,其在ICH中的作用仍待进一步研究。
2.4 C反应蛋白(C-reactive protein,CRP)
CRP由肝脏产生,是急性炎症反应的标志。在过去10年中,对多个种族进行了大量流行病学研究,但没有发现循环CRP水平与ICH风险之间存在有意义的联系。然而,CRP似乎是一种可靠、易获得的ICH预后预测生物标志物。研究发现ICH患者血清CRP水平在入院后48~72 h显著升高,且升高程度与血肿体积有关[17]。Alexandrova等[18]对46例症状出现48 h内的ICH患者进行了研究,发现入院血清CRP水平是短期不良预后的强有力的预测因子。Diedler等[19]在包含103例ICH患者的队列中构建了多变量Logistic回归模型,结果显示,最大CRP水平是出院时和长期随访时不良结局和死亡的独立预测因素。
2.5 CD163
CD163又称M130,属于富含半胱氨酸结构域的清道夫受体超家族,由Zwadlo等于1987年发现。CD163主要定位于单核细胞/巨噬细胞表面,其功能尚不清楚。CD163可以从细胞表面脱落,在血浆和其他组织液中生成可溶性的CD163(sCD163)。Roy-O’Reilly等[20]研究发现,与短暂性脑缺血发作对照组和健康对照组相比,ICH患者血清sCD163在发病后48 h内显著升高,且较低水平的sCD163与血肿和水肿扩大相关。Xie等[21]的研究证明,发病后24 h内较高水平的血清sCD163可促进ICH患者的血肿吸收和神经功能恢复。Garton等[22]对41例ICH患者进行回顾性分析,证实了血清sCD163是ICH后3个月和12个月不良结局的独立预测因子。总的来说,现有研究样本量较小,上述结论应在更大、更多样化的ICH患者队列中进行验证。此外,需要评估慢性恢复阶段(ICH后数周至数月)的血清sCD163水平,以确定其与ICH患者预后的关系。
2.6 髓过氧化物酶(Myeloperoxidase,MPO)
MPO是一种血红素过氧化物酶,存在于髓系细胞,炎症时主要由激活的中性粒细胞分泌,发挥调节炎症反应及防御作用。血清MPO水平升高会导致氧化应激和氧化性组织损伤。在脑血管病中,MPO可破坏血管壁成分、损伤血管的完整性和功能。Phuah等[23]研究发现,MPO水平升高的遗传决定因素会增加ICH初发及复发的风险。崔海随等[24]选取了80例健康对照组和110例急性ICH患者,研究发现急性ICH患者血清MPO水平升高,与患者神经功能损伤及不良预后有关。提示可以从基因水平对ICH的预防和诊治进行更深入的研究。
2.7 半乳糖凝集素-3(Galectin-3,Gal-3)
Gal-3是凝集素的一种,广泛分布于体内,参与炎症反应。Bonsack等[25]动物实验首次证明了小鼠ICH后血肿周围脑组织中Gal-3的表达增加,提示Gal-3可能参与ICH后的脑损伤。Yan等[26]研究发现血清高Gal-3水平与ICH患者的不良预后和6个月死亡独立相关。但目前对ICH中Gal-3的研究仍然较少。
2.8 巨噬细胞迁移抑制因子(macrophage migration inhibitory factor,MIF)
MIF是一种促炎细胞因子,参与白细胞募集、炎症、免疫反应等过程[27]。一方面可参与清除病原体,在感染性疾病中发挥保护作用;另一方面,MIF作为一种免疫调节剂,可加重炎症反应导致不利作用[27]。白霜等[28]研究发现,MIF参与的信号通路可能参与了ICH后血脑屏障紧密连接的破坏,提示MIF可能对ICH后的不良结局产生影响。Lin等[29]收集120名健康对照组和120例ICH患者血清,发现血清MIF水平是6个月总生存期和不良预后的独立预测因素。然而目前关于MIF与ICH预后的研究较少,两者是否有确切关系仍需进一步探讨。
2.9 亲环素A(Cyclophilin A,CypA)
CypA是一种细胞内分子,参与调节细胞内信号转导和蛋白质折叠等过程。Nikolakopoulou等[30]动物实验发现敲除小鼠LRP1基因可导致内皮细胞CypA激活,破坏血脑屏障;抑制CypA可恢复血脑屏障的完整性,逆转和预防神经元丢失和行为缺陷,提示血清CypA水平升高可能会对大脑结构和功能产生不利影响。Chen等[31]收集了105名健康对照组和105例ICH患者入院时的血清CypA水平,发现ICH患者血清CypA水平升高,且与ICH严重程度、长期死亡率和不良预后密切相关。然而目前关于CypA在ICH中的作用及具体机制的相关研究较少,且现有研究样本量不足。
2.10 硫氧还蛋白
1964年,Laurent等首先从大肠杆菌中分离出TRX。TRX是一种广泛表达的细胞内硫醇蛋白,是抗氧化剂,被认为是氧化应激的标志,在氧化性组织损伤、炎症、感染等应激过程中被诱导产生[32]。贾耀辉等[33]对362例老年高血压ICH患者进行回顾性分析,发现血清TRX1水平与该人群预后密切相关,高水平血清TRX1是患者30 d死亡的独立危险因素,可作为该病患者死亡的预测指标。Qian等[34]进行的前瞻性观察性研究认为,血清TRX水平与ICH后NIHSS评分、血肿体积有关,是患者6个月死亡的独立预测因子。但是,TRX并非中枢神经系统所特有,目前的研究局限于血清TRX,未来可对脑脊液TRX作进一步研究,并且需要更大样本量的多中心研究。
2.11 凝溶胶蛋白(Gelsolin,pGSN)、甲壳质酶蛋白40、可溶性CD40配体
血浆型pGSN可以通过清除肌动蛋白和脂多糖等促炎信号来改善有害的炎症反应。在与组织损伤和肌动蛋白释放相关的各种疾病中,可以观察到pGSN的缺失,包括急性肝损伤、蛛网膜下腔出血、脑缺血等,且发现pGSN的降低与这些危重疾病的严重程度和预后相关。因此,pGSN被认为是急性疾病的预后标志[35-37]。Zhao等[38]回顾性研究发现,ICH患者pGSN水平明显低于健康对照组,且是6个月不良结局和死亡率的独立预测因子,但具体机制仍需要进一步探索。
甲壳质酶蛋白40是18糖基水解酶家族的一员,在炎症过程、细胞外基质重塑和纤维化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39]。甲壳质酶蛋白40也可在星形胶质细胞中表达,并可能参与急性神经炎症。Jiang等[40]研究发现甲壳质酶蛋白40与ICH的严重程度相关,是ICH后90 d不良结果和死亡率的独立预测因子。
CD40配体(CD40L)是肿瘤坏死因子家族的一员。CD40L及其可溶性对应物(sCD40L)在与细胞表面受体CD40结合时具有促血栓形成和促炎症特性。Lin等[21]研究发现,与健康对照组相比,ICH患者血清sCD40L水平较高。同时,多变量分析结果表明,sCD40L是ICH后1周/6个月死亡率、6个月不良结局和6个月总生存率的独立预测因子。
3 总结和展望
综上所述,ICH后的炎症反应可对脑组织造成损伤,给ICH患者的预后带来不利影响。血清炎性标志物检测具备有效、简便易行的特点,可作为早期对ICH进行预后评估的重要方法之一。多个炎症因子之间的联合检测可能具有更好的预后评估效果。因此,对ICH患者炎症反应的积极应对是改善患者预后的重要方法。但是,炎症因子作用的具体机制尚未完全掌握,其在ICH中到底是起到了确切病理生理作用,还是仅仅发挥了“旁观者”效应仍需进一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