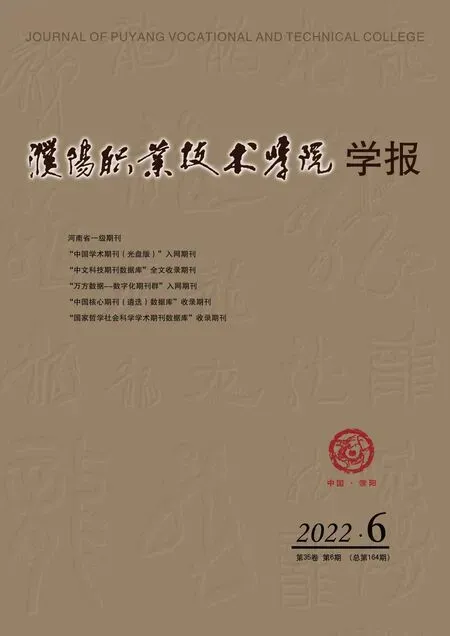中国新诗一瞥
鲁锡涛
(辽宁师范大学 文学院,辽宁 大连 116000)
从1917年2月1日《新青年》发表胡适的《白话诗八首》开始算起,新诗已经走过了一百多年的历史。自1917年以来,新诗创作涌现出一个个杰出的诗人,留下了一首首优秀的作品,但与浩如烟海的古典诗歌相比,新诗的征程才刚刚开始,如李白一样天才的伟大诗人、如杜甫一样全才的伟大诗人还没有出现一个,新诗依然深陷白话和口语化的泥沼,建构现代性的任务还没有完成。根据新诗的发展状况,本文试将新诗的发展阶段划分如下:1917年至1948年为进取时期,1949年至1977年为沉寂时期,1978年至1989年为重振时期,1990年至今为边缘时期。一百多年来,中国新诗接续中国诗歌的传统,使得中国诗歌在新的时代展现出新的风姿,不仅丰富了中华民族的诗歌园地,也以其独特的民族审美性丰富着世界诗歌宝库。
一、进取时期
新诗在现代文学“第一个十年”就形成了两种诗形。一种是自由体诗形,这是西方舶来物;另一种是格律体诗形,这是中西诗歌艺术共同作用的产物。格律体诗形以反对者的身份出现在新诗诗坛,它反对的对象是自由体诗形。随着胡适《白话诗八首》的发表,自由体诗形便进入了现代文学,呼应者众多,如周作人1919年发表的《小河》,郭沫若1920年发表的《天狗》,鲁迅1924年发表的《影的告别》。自由体诗形给中国诗坛带来了一阵阵欧风美雨,粉碎了古诗的文言文体,冲破了古诗的格律束缚,让诗人的思想可以通过诗歌自由地表达出来。胡适对新诗的看法在当时被新诗作者奉为新诗的金科玉律。如胡适认为:“近几十年来西洋诗界的革命,是语言文字和文体的解放。这一次中国文学的革命运动,也是先要求语言文字和文体的解放。新文学的语言是白话的,新文学的文体是自由的、是不拘格律的。”[1]134胡适在1920年出版的《尝试集》被读者争相抢购便是一个鲜活的证明。《尝试集》也是中国新诗的第一部白话诗集。但在“文学革命”浪潮里,以胡适、郭沫若等人为首的新诗作者并不关心他们的诗歌是否流于白话、是否缺乏审美意蕴,他们关心的是诗歌是否表达了对黑暗现实的诅咒和对光明理想的赞美,是否传递了个性解放和精神独立的思想信念。
如果说自由体新诗是从胡适和郭沫若开始的,那么格律体新诗就是从闻一多和徐志摩开始的。针对早期新诗作者因追求表达而忽视诗艺从而导致的作品内容单薄和情绪化等问题,以闻一多和徐志摩为代表的新月派从唐诗宋词中获得了启示,主张以“理性节制情感”来克服早期新诗的泛滥抒情,主张写格律体新诗来纠正早期新诗的过分自由。如闻一多提出了诗歌创作的“三美”法则,即“音乐的美(音节)、绘画的美(辞藻)并且还有建筑的美(节的匀称和句的均齐)”[2]141。徐志摩的《再别康桥》和《我不知道风是在哪一个方向吹》便是典型的格律体新诗。在20世纪20年代,以李金发、穆木天和王独清为代表的早期现代派也注意到了早期白话诗的缺点,同时也批评了格律体新诗的形式主义。这是一群深受西方诗歌影响的诗人,他们引进了象征主义,主张以隐喻、复义和暗示等艺术手法来进行诗歌创作,给中国的自由体新诗指出了新的方向。如穆木天主张:“诗的世界是潜在意识的世界。诗是要有大的暗示能。诗的世界固在平常的生活中,但在平常生活的深处,诗是要暗示出人的内生命的深秘。诗是要暗示的,诗是最忌说明的。”[3]140李金发的《弃妇》便是典型的现代派诗歌,但是早期现代派的诗歌往往使读者看不懂,使读者难以动情也拒绝沉思。
自由体新诗有其拥护者,格律体新诗也有其拥护者。民国时期,新诗涌现了一个又一个有影响力的诗派,如新月派、现代派、中国诗歌会、七月诗派、九叶诗派;新诗涌现了一个又一个杰出作家,如闻一多、戴望舒、蒲风、艾青、穆旦;新诗涌现了一首又一首代表作品,如《口供》《我底记忆》《茫茫夜》《雪落在中国的大地上》《古墙》。新诗在20世纪20年代经过郭沫若和徐志摩等诗人的创造,又经过郭沫若、闻一多、卞之琳和穆旦等诗人的改革和努力,到了20世纪40年代已形成了两大基本诗形:自由体新诗和格律体新诗,已完成了从白话语言到审美语言的转变,在题材选择、意象创造和组织建构等方面也形成了基本的审美规范,如以艾青为代表的七月诗派的诗歌和以穆旦为代表的九叶诗派的诗歌。由当时新诗的一些佳作,如戴望舒的《雨巷》、闻一多的《口供》、卞之琳的《断章》、殷夫的《一九二九的五月一日》、艾青的《大堰河——我的保姆》、穆旦的《诗八首》和冯至的《十四行集》可知,这些诗歌代表了中国新诗在民国时期的主要成就,为中国新诗的后来者指明了前进的方向。当代诗人沙克也肯定了民国新诗的影响:“当我们回望占据三分之一世纪的民国新诗,比照百年新诗的命运形势可以得出宽泛的结论,民国新诗在语言技巧、审美功能、文化构成和生命态度等方面已经完全成型,走在人类诗歌艺术的规律性轨道上。 ”[4]57
二、从沉寂到重振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新诗便进入了新中国的轨道。1949年至1956年,新中国完成了从新民主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1956年至1966年,新中国开始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1966至1976年,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探索遭遇巨大挫折。文化是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学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学的发展与社会状况息息相关。纵观1949年至1976年的新诗可以发现,新诗越来越沉默甚至失语。讨论新诗这一特殊的状态,就必然要涉及当时中国的国内外大环境。新中国刚刚成立,百废待兴,西方列强虎视眈眈,看似友善的苏联实则包藏祸心。于是,为了新生政权的稳定,国家在文化领域采取了文艺为政治服务的方针,进而发生极左偏差,对文艺管得过死,先是绿原、陈梦家和闻捷等诗人逐渐放弃了写作,到了“文化大革命”时期放弃写作的诗人就更多了。正是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下,中国新诗进取的风姿消失了。在1949年至1956年还时有政治抒情诗出现,如贺敬之的《回延安》、郭小川的《望星空》、沙白的《水乡行》;然而,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到来,新诗便步入了荒凉的冬天,只有极少数诗人还在隐秘地阅读和写作诗歌,如芒克等。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后,新中国的文艺路线从为政治服务调整为为人民服务和为社会主义服务,于是,越来越多的新诗开始涌现。影响这一时期新诗发展状况的因素不仅有政治方面的,还有文化方面的,其中最重要的是出现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西方现代文艺思想,如“第三代诗人”的诗歌。随着1978年《今天》刊物的创立,朦胧诗便进入了当代文学,朦胧诗诗人们继承和发展了中国新诗的现代传统,他们反对1949—1976年诗歌的白话和散文化倾向,将中国新诗从非诗化引到了诗化的康庄大道上。朦胧诗诗人们与他们的前辈九叶诗派一样,将诗歌的重心放在了内容的深度上面,所以他们的诗歌是审美体验和理性思维的合一,如顾城的《远和近》、舒婷的《致橡树》、北岛的《回答》。如有论者指出的:“朦胧诗在中国现当代诗歌史上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既有对中断了的20世纪中国现代诗歌的承接作用,又有影响新时期诗歌乃至整个文学发展趋势产生重大影响的价值。从广义上说,朦胧诗除了对建国三十年新诗传统的突围外,还进行了两个对接,既连接了中国的现代主义诗歌潮,又与世界现代主义诗歌接轨。”[5]9关于朦胧诗的讨论深刻影响了20世纪80年代的新诗,诗歌界掀起了一场现代诗歌热潮,比如第三代诗人的诗歌和校园诗潮,代表作品有韩东的《有关大雁塔》、海子的《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欧阳江河的《玻璃工厂》、西川的《十二只天鹅》和翟永明的《女人》等。20世纪80年代的新诗因为朦胧诗和第三代诗人的出现,呈现一个回升的状态。诗人西川作为亲历者肯定了这一时期新诗的影响力:“在80年代你要不写诗,那你简直就是一个很荒唐的人,因为全国青年都在写诗。”[6]258而诗评家唐晓渡则从学者的角度捕捉到了这一时期新诗的蓬勃姿态:“时过境迁回头看,再不怀旧的人大概都会认可,80年代是一个诗的黄金时代,也许是新诗有史以来最好的时代。”[7]77
三、边缘化时期
20世纪90年代,大众文化取代了精英文化的主流地位,精英文化被迫走向了边缘化,而新诗就是一个例子。在21世纪,大众文化凭借网络和手机等信息技术的普及和进步而更加繁荣,于是新诗便走向了更远的边缘。在我们这个诗歌的国度,新诗被边缘化是一个真实存在着的冰冷事实。正如有论者指出的:“现代新诗一方面丧失了传统的崇高地位和多元功用,另一方面它又无法和大众传媒竞争,吸引现代消费观众。两者结合,遂造成诗的边缘化。”[8]2在这里,美国华人学者奚密从国外学者的角度表达了对中国新诗边缘化的看法。
笔者认为,中国新诗被边缘化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四点。一是以世俗性、娱乐性和效益性为代表的文化产业的崛起和繁荣发展使得文化成为一种消费,人们的精神生活方式丰富多彩,比如网吧、影院和KTV星罗棋布,而文化产业正是推动大众文化盛行于世的重要力量。二是西方现代主义思潮和后现代主义思潮的涌入虽然开拓了中国诗人的视野,使得中国诗歌与世界诗歌对接,但是“消解崇高”“消解传统”和“消解审美”等诗学理念的出现也使得新诗走向了文字游戏,诗歌形式千奇百怪,诗歌内容意蕴匮乏。如“口水诗”“后非非主义诗歌”。这些“号称后新潮的诗作,不但与我们日常的感觉,我们的肉体和灵魂距离异常遥远,而且连和真正的诗歌艺术的距离也变得遥远了”[9]71。学者孙绍振看到了新诗的这一特征,认为他们在写缺乏艺术魅力的诗歌,破坏了诗歌的现代性生态。此外,21世纪之初出现的“下半身”诗歌运动,也证明了学者孙绍振眼光的预见性。三是新诗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便陷入了白话和口语化的泥沼,呈现出明显的非诗化特征。随着国家科教兴国战略的实施,中国人的文盲数量越来越少;随着贴吧、微信和知乎等网络工具的普及,文化传播变得越来越容易;又加上新诗在形式层面的不确定性,于是学生、商人、记者、飞行员、渔民、主播和演员等各色的人都拥有了进入新诗国度的门票。大量私人化诗歌和网络诗歌的出现制造了一个梦幻的和可悲的假象,好像一个只要不是文盲然的人写了一段抒情的文字,就可以说自己是诗人了。然而新诗的创作是一种独特的、审美的和艺术的文学活动,想要成为一名新诗作者是有诸多条件的。但是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新诗诗坛便泥沙俱下,如“垃圾派”诗歌、网红女诗人余秀华的诗歌。于是,“有些诗正离我们远去。它不再关心这土地和土地上面的故事,它们用似是而非的深奥掩饰浅薄和贫乏。当严肃和诚实变成遥远的事实的时候,人们对这些诗冷淡便是自然而然的”[10]45。著名文艺评论家和诗人谢冕毫不掩饰地表达了对新诗的不满。四是中国读者自幼受到的诗歌熏陶是古典诗歌而不是中国新诗,如陶渊明、李白、杜甫、王维和杜牧等诗人的作品被大量选入语文教材,高考这一重要考试还有古诗文填空和古诗文鉴赏,而中国新诗很少被选入语文教材,从而导致中国读者更喜欢的是中国古典诗歌,而不是以内容晦涩化、散文化和哲思化为特征的中国新诗。比如穆旦的《还原作用》将现代人隐喻为“污泥里的猪”,身上爬满了“跳蚤,耗子”,在“八小时工作”后想和朋友聊天却发现“通信联起了一大片荒原”。这是一首有诗意的诗歌吗?答案是否定的。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新诗虽然被边缘化了,但并不是诗人吕约宣称的“诗歌不知道自己已经死了”,新诗依然在顽强地生长:依然有众多的诗歌刊物,比如《诗刊》《扬子江》《诗林》《诗潮》《绿风》;依然有众多的诗歌活动,比如“青春诗会”“樱花诗赛”“未名诗歌奖”的接连举办;依然有众多诗人在活跃,比如北岛、吉狄马加、谭永昌、龙青、路也、王家新、黄礼孩。面对新诗被边缘化这一冰冷的现实,我们必须积极面对,去思考新诗如何走出困境,比如现代新诗是否需要具有古典诗歌的诗意?新诗现代性的迷雾能否驱散?同时,我们应该明白,新诗被边缘化只是从文学接受而言,但是关注新诗的艺术魅力的话,我们可以发现,新诗已经走在了世界诗歌的前沿,比如,北岛屡获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提名,黑丰和王家新于2019年在第六届“雅西国际诗歌节”双双获得了“罗马尼亚历史首都诗人”奖 ,叶延滨于2020年在第三届“博鳌国际诗歌节”获得了“杰出成就奖”。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无论多少,诗的读者向来很难成为一个社会的多数人”[11]520。而新诗也存在着一个“无限少数人”的群体,穆旦属于少数人,郭小川属于少数人,海子属于少数人,郑小琼属于少数人,新诗的延续正是通过一代代的少数人而完成的。
一百多年来,新诗的经历可谓曲折,经历了漫长战火的洗礼,又迎来“文化大革命”的寒潮,终于到了改革开放后的春天,却又很快走向了边缘化。宋代的王安石在《伤仲永》中讲了一个天才沦落为庸人的故事,笔者认为这可以与新诗做个类比,新诗的发展历程正好讲了一个明星沦落为路人的故事。1990年以前的新诗可谓是“其文理皆有”观众,1990年以来的新诗就“泯然众人矣”了。这并不是危言耸听,中国新诗如果再不进取,就会成为下一个方仲永。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新诗不仅与中国古典诗歌不同,也与西方白话诗歌不同;新诗是一种中国独有的诗歌体式,新诗是一种可以大有作为的现代诗歌体式,闻一多、卞之琳、穆旦和顾城等人的创作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习近平总书记 《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出:“推动文艺繁荣发展,最根本的是要创作生产出无愧于我们这个伟大民族,伟大时代的优秀作品。”[12]5然而当代新诗却缺乏关注生活和关注人民的伟大作品,这也是新诗迟迟无法引起中国读者关注的一个重要原因。参照中国古典诗歌的发展历程,我们有理由相信,一个伟大的诗人的出现可以帮助新诗走出边缘化,如柳永之于宋词;这个伟大的诗人可以收纵自如地出入自由体新诗和格律体新诗之间,他的作品充满对生命的独特体验和对诗性的无限热爱,在他的影响下,新诗将从“天上”走进人间。关于新诗的大诗人,早在民国时期就有人在呼唤,如宋淇在《论新诗的形式》里面这样说:“其实,有关新诗的问题,不管是抽象的,或具体的,原则性的,或枝节的,都可以一扫而空,只要有一个真正伟大的诗人能及时出现。”[13]2我们期待着,就在这个21世纪,中国新诗将诞生属于自己的伟大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