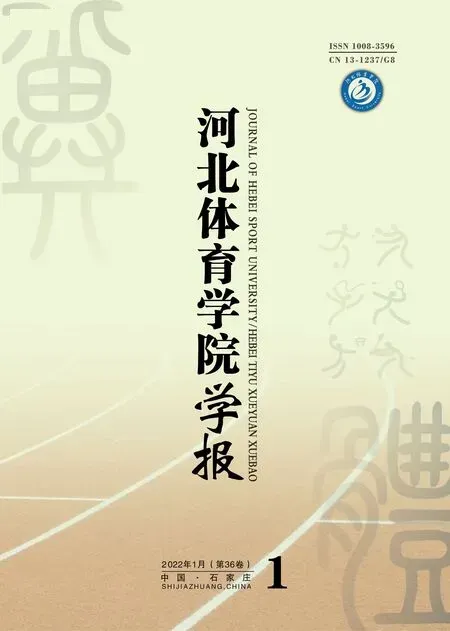镜像足球的本质
——超视距身体文化的学理定位
路云亭
(上海体育学院 传媒与艺术学院,上海 200438)
人类和很多生灵一样,有展示自己身体活性的本能,而并非有意制造一种观赏类文化,但是如足球这样的身体展示形态却给千千万万的他者带来了视觉享受。视觉媒体的出现丰富了人类的视觉感知维度,极大扩展了人类由视觉触发的想象力,因此,足球竞技的电视与网络传播具有划时代的意义。通过电视荧屏与网络视频中的精彩画面,球迷可以待在沙发上欣赏各种高水平的足球赛事。电视荧屏将自家客厅变成了赛场,足球的观赏模式得以变革。网络视频足球则进一步改革,开启了延时性、即时性、点播性的镜像服务体系,足球也由此而步入一种全新的视觉革命时代。足球的表演性内涵得以强化,足球的审美特质也因此而变异。
1 电视工业与足球实体的联姻造就的演剧形态
足球是一种自然游戏。单从个体快乐的角度看,22个人只要事先约好便可以在世界上某个场地踢一场,有没有人观看或转播,都不会对游戏者产生太大的影响。但是,足球竞赛转播对观众的影响很大,此外,场内观众与媒介观众的感受品质也不尽相同。所以,足球转播与否,直接影响到观众的收看意愿。
足球和电视的关系可以从现代足球起源国说起。“英国是最早用电视转播足球的国家,但却经历了巨大的变迁,足球界对电视的态度历经了拒绝、怀疑、试用、渴望、互利等阶段,而电视界对足球的态度是力争介入、乞求、合作、傲慢、不屑一顾、拉拢、互利。”[1]足球与电视的联姻可以看作是20世纪后半叶世界新型产业的融合典范,两者相辅相成,互相助力,合作共赢。
中国学者也关注到了电视媒介所营造出来的狂热氛围。“时光流逝到2002年的韩日6月,世界又一次陷入以电视和足球为主导要素的狂热中,与那些如今依旧富贵逼人的其他游戏不同,这次电视足球屏幕前的主角毫无例外的依然是浩浩的平民们,只要有一台可以安放电视的桌子,这个星球就无法镇静,因为足球带来呼啸和颤栗!”[2]不仅如此,足球和电视的联姻更容易制造出一种宣传效应。“电视和足球一起,在这个6月,或者是在给芸芸众生的四年一贯的生活中注入放纵的元素,或者是在暂时缓解工业化社会冰冻三尺的清规戒律……在这个狂欢的6月里,足球击败了上帝和金钱这两个工业社会永恒的主题,成为了唯一的宗教。”[2]现代媒体一度经历了纸媒一统天下的时代,虽然电影工业也曾介入足球领域,但用电影胶片来记录足球赛事,其时效性较差,难以形成新闻效应,而电视媒介的出现立刻改变了这种状况。电视媒介一度是二战后的统治性媒体形态。电视转播不仅时效性强,还有类似电影的品质优良的画面,其优势地位便立刻凸显出来。“20世纪后期,不断商业化的运动赛事也加速了另一个趋势成长,那应该是美国境内最戏剧性的一次:20世纪80年代起,运动节目移到电视的黄金时段,全国几十个电视频道,24小时都在播放比赛和相关评论。”[3]219-220即便从纯市场的角度看,足球在所有的体育项目中也是王者,而电视足球的出现,则更加巩固了其王者地位。
现代社会与媒介的合力可以重构权力秩序,足球也便在这个时候将自身的生长性权力交给了媒体世界,并在其中释放其既有威力。“一场球赛,现场最多只能有几万人观看,但是通过电视的转播,几亿人可以同时感受到足球的魅力,这无疑会带来更多的球迷,带来更多的支持,带来更大的发展。而且,媒体有制造社会流行趣味的强大力量,并在其形成过程中对人们施以潜移默化的影响。”[4]媒介与足球的联合可以缔造出诸多全新话题。任何一种新生事物都必须经过多次实验、调配、磨合才能真正产生社会效益,足球和电视的关系也有过这样的磨合期,其中最值得一说的便是电视转播的真实性问题。脱离了现场之后的足球是否具有逼真的效果?电视镜像足球替代现场足球对受众的神经系统刺激是否有副作用?失去了体验效果的足球是否还是一种真实的足球?诸如此类的问题层出不穷。
其实,电视足球的真实性问题可以从人类的感知发展史上考量。已经有人关注到了新型媒体出现后的社会风险,这种风险有认识论的元素。“后现代理论家道格拉斯认为,超真实是指真实与非真实的区别已经模糊不清,非真实超过了真实,比真实还真实。真实不再是自然的自在之物,还包括了人为生产出来的真实。”[5]26张国良认为:“大众传媒的发达使拟态环境的比重越来越大,人们认识真实世界的可能性则越来越小,因为人们通常根据媒介文本在自己头脑中描绘‘关于外部世界的图像’。”[6]时间可以消弭诸多大众性疑问。当人们接受了电视足球的鲜活镜像之后,等于认可了另外一种真实性。届时,人们完全可以在电视镜像的领域内消费自己的情感。电视时代给人们带来诸多意想不到幸福感,也降低了人们现场直击真人秀的欲求。
电视足球是视觉工业化时代的产物,其中的关键是信息传输手段。“拍摄范围、拍摄角度、特写镜头、慢动作镜头、对特殊运动员的关注、不同角度截取出的极具视觉冲击力的图片、电视解说员的解说等都超过了人们仅凭肉眼能获得的信息量。”[5]26视觉传播的时代到来后,足球一举跃出了体育的范畴,演进为一种演艺形态,并催生出新型信徒群体,足球的信仰性内涵得以强化,并很快就进化为一种令全世界球迷感奋不已的文化品类。
工业技术的进步源自人的好奇心,因为好奇心可以创造新的需求点,进而拉动消费。现代社会的专利制度一直在保护这种好奇心,借以维持现代人的价值观。质言之,一个品位高端的理性的法治社会一定是一个竭力保护知识产权的社会。现代社会充满了实验性、革命性与先锋性,并最大限度地维护社会活性的释放源头,其所针对的是一种单纯的消费市场,而非固化权威的某种指令。人的创造力几无穷尽,因此,任何一种工业技术都有阶段性的局限性,电视工业也是如此。黑白电视机的普及给足球带来了生机,彩色电视机的出现则使得足球镜像更为丰富多彩,足球传播就此展示出其更为深远的影响力和更为广阔的传输维度。足球的电视传输一度使得足球的符号变得具体而精微、细致而鲜活。“到了1958年巴西首次夺冠的瑞典世界杯,姗姗来迟的电视第一次介入到世界杯中,它以实况录像的方式,让全世界看到了以往抽象文字的方丹和科帕,让全世界不再依赖解说员口焦舌燥着急告诉他们谁是17岁的贝利——至此,在电视这个威力无比的大众传媒的极度放大下,世界杯通过荧屏也永远被改变了:不仅仅是更多的人看到简单的图像,而是让它不再是幸运儿的宠物,而成为普罗大众任意拿取的欢乐大餐,而对于这个诞生在英国煤铁和纺织劳工街区的平民游戏,因为电视而让它的平民色彩更加透彻和直接。”[2]1970年是电视足球初显威力的时段,它也构成足球传播史上的标志性事件,紧接着便是新型足球观众的精神易变。质言之,电视足球受众的出现几乎改变了世界足球传播的格局。整体而言,足球与电视的融合大体顺遂,虽然也有过一段权益纠葛的历史,但很快就达成了妥协。面对电视工业的强劲发展态势,足球不仅深植其中,还从中获得了一种看似更为强大的扩张效应。“在墨西哥第13届世界杯足球赛期间,许多越南球迷通宵达旦地观看这次大赛的电视转播。这是越南的电视网首次直播世界杯足球赛。……在越南街上,很容易辨认出谁是足球狂热分子——他们都有一双红眼睛和一个闹钟袋。墨西哥和越南两地时差是12小时,比赛期间,每日凌晨一时,河内市内万钟齐鸣,提醒球迷首场比赛马上开始。”[7]正因如此,与其说足球改变了现代人的生活方式,不如说是电视机改变了整个社会的习俗。电视转播业在很多国家都是培育新一代球迷的重要推手,其影响力可以覆盖五大洲中的绝大多数国家。电视时代足以成为一种新型的认知革命时代,它不仅代表了一种视觉享乐过程,还足以构建出一种信仰体系,电视足球已然创造出一种视觉革命,因此,人们很难设想电视消亡之后的情境。就目前的情况看,那里一定酝酿着一种值得人们萌生怀旧情怀的元素。
电视时代带来了更为直观、鲜活、充满质感的足球信息,于是,足球场外的花边新闻也改变了传输方式,得以呈现在受众面前,它们还会催生、孵化、缔造出足球的新意义。莫瑞曾言:“60年代末期,针对足球的电视栏目将重心放在特别包装过的焦点问题上,而且主要强调赛场外的活动。不论如何,媒体总是百般讨好球员。而作为新‘包装’中的人物,球员们也需要相应的报酬。观众事实上为电视体育提供了赖以存在的基础,他们对新的风气有着自己的理解,而他们所狂热奉行的胜利主义观念与其说是出于贪婪,倒不如说是对本地球队一种扭曲的忠诚心态。”[8]186-187足球缔造的社会规则失效现象还包括不顾商业法的偷窥行为。“在英国看电视,电视机税每年要缴纳128英镑(2006年),而一台普通电视机只售100英镑,很多年轻人家中置有彩色电视,为了逃税,平时只好偷偷地看,但是在世界杯足球赛期间,在这种激情的驱使下,这些偷税电视机就大量涌现……在2004年欧洲国家杯赛期间,仅在英格兰地区就有超过2.4万人,被发现在未经许可的情况下收看比赛,他们就可能被告上法庭,并处以1 000英镑的罚款。”[9]很难说偷看足球赛事的英国球迷是违法乱纪者,但从中可以看出,足球的确给一些人带来了以身试法的鼓励性能量,由此也可反证足球在现代社会中的超级影响力。
随着电视工业的全方位介入,足球的产业化规模急剧扩大,“可以认为,没有电视的普及,就不会有今天的足球产业。……这样数以千万计的电视观众和足球爱好者成为足球市场的顾客,为足球产业的形成创造了极为雄厚的购买潜力。”[10]电视足球一度具有很强的竞争力,并占据着很大的市场份额。林卫国认为:“当世界各大电视台的巨头们不惜动用数亿,甚至数十亿美元争相购买世界杯足球比赛、世界五大职业足球联赛的电视转播权的时候……足球传统意义上的内涵已经被突破,它的社会价值、经济价值和产业地位已显露无疑。现代足球作为一项新兴产业,正在成为推动一国乃至全球经济增长的一个新的增长点。”[11]电视足球的出现意味着足球的职业化水准跃入一个新阶段,职业球员所从事的职业开始成为一种成熟的职业,职业球员的劳动得到了最高限度的保障,职业球员的从业积极性也得到了极大的鼓励。从此以后,身体的潜在价值获得了更大的扩张平台,足球的演艺性新特质也得到了一种全新的阐释境遇。
2 镜像足球实现了对人类精神的再度解放
媒介技术革命的价值毋庸小觑,而技术革命的理论同样值得人们再度考量。为了扩大受众面,媒介行业本身对缔造大众偶像一直抱有热情。“体育传媒的生产过程也恰恰是一个利用符号、影像建构虚拟现实的过程。”[5]4-5高强度的媒介策划力已经将世界的本然风貌摧毁。人们看到或读到的媒介阐述很可能是一种幻象。质言之,现代人认知世界的方式一直受到媒体的左右,人类在脱离了自然感觉认知的局限之后,随即跃进媒体赋予的直觉权限的新境地。新中国的职业足球几乎和中国的电视业同步发展。正如任何国家的电视足球转播一样,中国的足球电视转播也经历过一个从大而全到小而精的过程。“当受众需要具体了解某一类体育赛事较为详细的情况时,‘裂变’就开始了。这是一个将‘大全景’推成‘近景’或‘特写’的过程,这个过程从中央电视台体育频道和继之而起的各地方台体育频道、体育板块的设置之时开始。”[12]足球电视转播节目的进步以电视技术的进步为前提,而其内在的人本动机同样无法忽视。
在虚拟环境中,人们更容易接受来自热点镜像的信息,而引导观众进入镜像世界的则是电视中呈现出来的一种不可感知的人体行为。好在人类是想象力极为强大的智慧生物,尽管人们知道电视镜像的人体行为无以真实感知,但会通过想象、联想、情感平移之类的心理活动完成对真实景象的还原工作,在完型学的意义上考量,观众可以感受到电视镜像中人物的细微情感变化,更可以感知到球场赛况的真实风貌。正因如此,镜像的非可感性特质未必会影响观众的观看热情。真实的情况也是如此,电视镜像为观众提供了海量的可视性足球资源,足球观众由此获得了超越真实感应场域的更大维度的观赏享受。
镜像传播是技术进步的产物,当技术的优势确立之后,一种新型的生活方式就会出现,足球与电视的结合就是其中的典范。“在这些动作中充满着丰富的视觉效果(所以欣赏足球不一定需要内行,或者说内行有内行的欣赏视角,外行有外行的观看视角),而到目前为止,只有电视传媒能够传达出这样的视觉效果。”[13]自现代足球出现以来,现代媒体就与其结成了各种各样的纽带关系。电视时代到来后,人类社会才第一次真正体会到了普天同庆的感觉,而足球则强化了人类社会普天同庆的内聚力。足球的超时代张力就体现在这里。电视对足球传播领域一直呈现出一种强势干预的劲头,展示出一种突变式的能量。正如莫瑞所说,“为获得某场球赛的转播权,电视台会付给足球管理机构比原来多得多的费用。从80年代早期开始,商业企业家便在最新科技的武装下,在‘以贪为善’的信条指引下,向国家对媒体的垄断发起攻击。”[8]229当时的电视媒介不仅干预到足球传播的模式,还极大地推动了受众生活方式的变革,这种强直性的精神干预现象一直影响到足球的赛制变革。
镜像足球重构了人类的生活习惯。读图时代使得文字的意义锐减,人类由此重回一种非文字力量主导的社会。“众所周知,在家看电视足球转播和球迷亲临赛场为心爱的球队和球星助威,两者的感受是根本不同的。”[14]这种差异体现在群体参与与个体独享的巨大反差层面。质言之,镜像足球与现场足球不同,仅从观赏的角度看,两者各有优长。镜像足球更多地被定义为一种对足球的间接欣赏形态。“间接观赏尤以电视、网络的作用最大,效果尤为显著,如在我国电视节目中,除现场直播和实况录像各类比赛外,每周还有足球之夜、天下足球等丰富多彩的电视足球栏目。这些都为足球比赛的欣赏提供了必要的信息储备和观赏素材。电视欣赏是当代足球欣赏中最普遍的一种方式,它能让你清晰地看到每个精彩的镜头。场上队员旁若无人的盘带、行云流水的配合、守门员不可思议的扑救、球员的每一点小小错误、裁判员的每次错漏判罚、教练员的各种表情,摄影机都能从各个不同的角度拍摄下来,导演又通过慢镜头让你去细细品味,球场的每个角度发生的精彩镜头都能让你一览无余,让你从各个不同角度尽情欣赏。”[15]间接欣赏足球还造就出一种独特的足球观众群体。他们不仅具有与现场观众不同的观赏方式,也养成不同的观球习惯,而造成此习惯的则是镜像足球独特的场域环境。足球有很强的可视性,高度大众化的形态使得它极易吸引观众的强力关注,很多人都会宽容电视足球中本真状态缺位的现象。较诸文字记述,镜像足球更富有原生态特性,于是,足球在镜像世界里恢复了其机趣的特质,并一度压制外在的理性秩序的干预,足球的镜像表述程序展示出了积极的活力。
足球始终带有一种溶解、释放、更新人的终极情感的力量。“现在越来越多的人成为电视足球现场直播的忠实观众,虽然这些观众会带着不同的心态来看待足球,关注足球,感受足球的魅力,但有一点恐怕是相同的,这就是足球场上球员的真实拼搏,丝毫没有表演的意味。”[16]其实,不同的媒介场域培育出来的观众类型差异很大,但是,观众群体对真实的身体竞技活动的渴望之情则是相通的。
这里需要在新的界标下阐释足球、媒介与戏剧的三角关系。其实,在现代传播媒介的强势压迫下,足球和戏剧的边界消失了,足球以其更具大型化、军团化、团体象征主义内涵而驰名,这些元素往往也是较为典型的戏剧性元素。镜像时代到来后,足球的戏剧性日益凸显,现已得到了广大受众的广泛认可。麦盖尔曾将看足球与看电视混为一谈,借以说明足球的观赏性价值。“当我坐在那些崭新的全坐席体育场里时,没有真正的气息,也没有真正的歌唱,我感觉好像是待在家里从电视上看球一样。”[17]质言之,镜像足球带有很丰富的现代性内涵,足球漫游到这样的地界,立即演化为一种视觉化的新型游戏,电视镜像将足球从风云多变的赛场引到温馨舒适的家庭,足球的维度、观众的期待值以及人类生活方式都得以改变。电视镜像所创造出来的舒适度、便捷度、适意度更高的足球赛事迫使更多的人不再愿意走进真实的球场,而更愿意待在沙发上领略足球竞技的风采,然而,这也有巨大的副作用,“影视观众无法像戏剧观众那样直接影响演员的表演,更无法像球迷那样直接左右球员的竞技状态。影视观众其实是‘自作多情’,单方面付出感情而得不到银幕荧屏上人物的回应,久而久之,只会增加现代人的孤独感与虚幻感。”[18]足球以镜像语汇的方式进入千家万户的客厅、卧室之后,其所能营造的大众性围聚效应锐减,镜像足球的狂欢性也被极大削弱,足球的进化之路很难被人完全掌控,它正在经历一场从户外性、参与性、场域性到室内性、静观性、内省性的转移。
质言之,电视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足球则提升了人们的思考路径。足球的介入也为电视增添了一种新鲜的身体性符号,足球与电视联袂创造出一种新型的身体时尚,足球也由此开始进入大众身体哲学的领域。不仅如此,高度发达的职业足球释放的是一种人性的绝然性元素,它强化了人性的绝对性。还将人性的诸多新细节呈现在赛场内外,在类似世界杯、欧洲杯、欧冠这样的大型足球赛事中,足球书写出来的完整教义得以呈现,镜像世界给足球插上了翅膀,这样的足球带给人的是一种更大场域的精神冲击力。
3 视觉艺术时代催生出来的新生活方式
在电视时代,电视广告对足球赚取利润而言愈加重要。足球广告在20世纪60至80年代达到高峰。“1965年,BBC第一次在周六推出联赛集锦节目:Match of the Day,为此向联赛委员会支付了5 000英镑,这笔钱被四级联赛的92个联赛俱乐部平分,每家54英镑。到了80年代,足球产业内部问题丛生,可电视足球通过转播魅力依旧巨大,转播合同金额也水涨船高。”[19]电视延伸了人的眼睛的功能,它将过去人类根本无法看到的东西通过荧屏一一呈现出来,电视足球转播就此成为一种挣钱的工具。“1987年,英国足总杯决赛时吸引了全国8 000万电视观众,尽管电视广告费高达每30秒60万英磅,破了世界纪录,但在比赛前一个月,电视台直播的广告时间就被抢购一空。这场比赛电视台总共作了25次广告插播,收得广告费1 500万英磅。”[10]德国的汽车工业与足球界的联姻堪称一种现代工业化国家的典范。“在科隆,福特汽车公司和科隆队已结盟3年。奥佩尔汽车公司多年来为作为拜仁慕尼黑队的广告伙伴而高兴。”[20]另一个足球王国巴西也一样,广告收入成为足球的一大基本资源。“1980年,巴西国家队为欧洲托柏服装制鞋公司作三年广告,穿着该公司生产的橘黄色球衣,公司每年支付巴西队500万美元。”[10]而促使足球成为商业社会新宠的主导性元素是观众的精神走向。
芭芭拉·艾伦瑞克高度评价了电视的现代功能。“文明的标准为何?也许只是规模大小的问题。狂热仪式和庆典已经发展到可以在同时间吸引几百人前来参加,在这样大小的团体中每个人都听得见现场的音乐(未经扩音器),而且一眼就能看到其他的参加者。然而所谓的文明社会,似乎就是好几千人(我们的时代则是好几百万人)被绑在一起,经济上相互依存,军事上面对同样的敌人,以及遵守同一套法律。无论是过去或现代的大型社会,要创造休戚与共的感觉,通常都要通过能让上千人观赏的大型集会;电视则可以让数百万人凝聚在一起。”[3]243意大利足球的繁荣也是借助的电视转播业务的扩大。“这一时期,足球比赛转播的收视率很高,例如1982年西班牙世界杯决赛,意大利队以2球优势击败西德队夺冠。据统计,意大利全国有3200万人收看了决赛的电视直播,这个数字在很多年内都没有任何节目能够接近。”[21]电视足球大体与现场足球保持着同样的品格,其中的明星球队跨越两界,成为收入的主要保障。“从80代中后期开始,一个地方电视体育节目开始风行,它就是《远程伦巴第》栏目。这个栏目主要针对世界上最富裕的地区伦巴第大区的两支同城球队:AC米兰队和国际米兰队。当然还有全意大利人民都宠爱有加的尤文图斯队。”[21]欧美电视业的发展大多注入了足球元素,这种联姻关系不仅缔造出一种全新的电视王国,还使得足球成为一种直观的大众消费对象。
足球赛事从一种体育项目跃进为电视节目,虽然只有一词之差,却使得足球的扩张力得以极大地提升,足球开始将全世界关注足球的人重新聚拢在一起,足球从一种小众文化变成了大众文化。镜像足球在一个偶然的时间节点打开了初始接触此类传播方式的受众的心灵世界,同时也开启了一扇带有启蒙主义意义的大门。高度发达的传媒使得很多国家的足球受众从中受益,人们簇拥在文化启蒙的大旗之下,一同享受由人类最为简单的游戏所带来的快乐。足球就此可以在一个更为庞大的群体中生根开花、舒展枝蔓,而先入为主的各种流派的镜像足球直接更换了大量新型受众的梦幻世界,电视产业再度培植起一支看球者队伍,而更为真实可感的场域足球随即演化为一种代表形而下模式的足球。
由电视传输过来的足球符号极大震慑了当代民众的精神世界,并促使他们随时偏离自己的思维航向,人们对此叹为观止。足球是西方文化的另类典范,其对非西方国家的输出具有两种动向,其一,工业性的技术性输出,表现在向第三世界国家输出电视机以及电视机生产线;其二,以电视足球节目为主导的足球文化的输出,此类文化不仅带有镜像美学的全新维度,还裹挟了大量创新性思想内涵。物质层面的电视机带有文明拓进的功能,精神层面的电视足球文化则带有现代化启蒙的效应。在文化输出的动能压力下,西方国家的电视足球节目输出带有多元性、复合性以及灌输性特质。
媒介足球在西方国家很发达,其在非西方语境中的存在状况也呈现出可人之态。且以体育媒介十分发达的香港为例。“收费的香港有线电视虽然目前只有不到一百万的收视客户,但已经逐渐具有其特色,以求得有别于其他免费电视台的竞争空间。其中最重要的是足球传播。”[22]香港虽小,但也一度是足球的发达地区,并拥有为数众多的球迷群。“有线电视目前已取得2002年世界杯的全部播映权,并同时直播/转播英国超级联赛、意大利甲组联赛、德国甲组联赛、西班牙甲组联赛、欧洲国家杯、欧洲足协杯、洲际国家杯、南美国家杯等赛事。相对而言,免费的无线电视只能转播英国超级联赛的部分赛事、亚洲足球赛事、本港足球联赛以及转播美国NBA篮球赛和美国自由摔跤大赛等。”[22]由电视工业缔造的历史已然成为一种全新的记忆。
中国的首批足球观众是在电视镜像的培育下成长起来的,其在足球启蒙阶段接受的足球信息便是1978年至1986年电视转播中的足球镜像,而那三届世界杯正是艺术足球处于世界主导力量的时期。央视前足球主播刘建宏曾回忆道:“从电视的角度来说,我们承认1978年,是中央电视台,也是中国的电视,把足球,把世界杯带到中国。但是从相对普及性来说,我觉得是1982年。为什么?因为1982年我们看的比赛多了,集锦也多了。另外我觉得,1978年的世界杯,毕竟只有半决赛和决赛,而且那个时候,中国有电视的人少啊,很少很少!”[23]电视媒介不仅传输了身体文化,还构建出一种由身体文化为原点的新思想,更会给大众带来一种全新的审美体验。黄健翔曾回忆1978年墨西哥世界杯的境况:“那个时候,78年,我记得啊直播了三场球:一个是荷兰对意大利,那场比赛里面呢有两脚惊世骇俗的远射。……阿根廷出场前,河床体育场那个看台上,扔那个蓝白纸片像雪花一样那个镜头。那一下,哎哟,这个足球怎么这么了不起呀!”[24]毋庸置疑,青春时期植入的足球符号更为牢靠,很多中国人由此成为足球的迷恋者。足球赛事具有当场性,但是,足球文化却需要一种循环阐述的能量支援。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很多足球当事人一直在讲述一些细节,宛如宫女叙旧,瞽人说书。由此可见,足球是一种感性物象,其对人的影响完全建立在大量的细枝末节之上。加莱亚诺曾说:“足球的历史精神是一段从美丽走向职责的伤感历程。”[25]从一些足球媒体人的直观描述可以看出,足球带给人的是一种有关青春、感伤、甜蜜的感情印记。
电视机在中国的普及大约在20世纪90年代末期,20世纪80年代的绝大多数中国家庭没有电视机,大家看球都依赖的是公家的电视或少数有电视的人出让性的看球机缘。这便构建出一种独特的观球现象。那一时段的中国人观看足球转播大都属于一种集体观看模式,人们很少有机会获取独享式观看镜像足球的机会。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足球观众进入到一种集体看球与独享观球的混合化阶段。进入21世纪以后,镜像足球受众开始体验个性化观球的历程。“现代社会里,卫星直播、网络传播等新技术的运用,使得大型体育赛事的报道已经进入了一个全面的视觉传播时代,电视赛事直播中以几十部摄像机深入到体育事件之中,组成了一个类似于上帝的‘万能之眼’,从而完成重大事件的超越时空的完美展现。”[5]26随着电视机的普及,无以计数的球迷已然接受了镜像足球,且已习惯于将电视足球与现场足球划上等号,甚至对后者产生了一定的排斥,完全成为一种镜像足球的受众,足球观众的新类型开始出现,可见,足球传播方式的变化引发了观众群体的异化。网络足球更加强化了镜像足球的传输能量。这里需要提及电视足球与网络足球的新型关系。质言之,在网络媒体成熟之前,电视曾经是最有影响力的传媒形态,就目前的情况看,大量的网站仍在吸纳电视足球产品,因此,人们所熟悉的网络足球也大多为电视视频的网络播放形式。电视足球在不远的将来仍旧是镜像足球的主体。
镜像时代到来后,足球无以避免地成为其中的主角。“以电视足球节目为例,它是最早实施裂变过程的。自1994年开始的中国足球联赛极大地丰富了电视荧屏,以此为突破口,一大批足球栏目脱颖而出。《足球俱乐部》《足球之夜》《足球纪事》和各种展现国际足球风貌的栏目《国际足球赛场》《足球集锦》,以及意甲、德甲、英超的赛事转播等,纷纷抢滩荧屏。”[12]电视节目的延展性能量足以催生出超越基本赛事的另一种电视形态。“以电视为主的传播媒体和足球前所未有地紧密结合在一起:足球有了表演赛,电视上有了广受欢迎的《足球之夜》《天下足球》等节目。电视和足球肩并肩,共同走向发展。”[4]电视节目有着自身的延展逻辑,电视足球也不例外。“就足球这样一个中心话题,为适应各种不同类型、不同欣赏口味、不同需求的受众,可以裂变出形态各不相同的栏目。以《足球之夜》为例,栏目创办伊始,就喊出了‘《足球之夜》,球迷每周的节日’的口号,一时间球迷受众趋之若鹜。有人统计,《足球之夜》在中等以上城市收视率超过20%,迅速成为电视体育栏目的一座重镇。”[12]足球和电视的互动关系十分紧密,两者可以轻易地达成互赢格局。随后出现的网络视频和电视荧屏并非是绝对的竞争关系。随着网络时代的到来,足球的视觉传输更为顺畅,网站点菜式服务模式的出现给大众带来了快餐一般的足球赛事,它也预示着足球的后工业时代的新景观。
镜像足球的出现一度对现场足球观众造成冲击,但是,随着受众类型的分化,镜像足球与现场足球受众开始习惯了彼此的存在。镜像足球受众和现场足球参与者各取所需,各得其乐,二者呈现出非对称性,其传播具有异质共存性,彼此相辅相成,鲜见相互干扰。但这并不意味着两者曾经的芥蒂开始消失,在足球受众类型化的语境中,两者之间失去了根本性的抵牾力。其实,镜像足球与现场足球的社会功能、审美品格、聚会机能、仪式内涵都已经不同,两者各具风貌,展示出不同的价值取向。于是,一种令人鼓舞的景象开始呈现,两者都拥有成千上万的带有信众色彩的受众群。镜像足球对现场足球的优化促进功能可见一斑。由此可见,新型传输手段的登场只能让足球受益。换言之,各种崭新的镜像足球传输手段的对抗不会有失败者,而更大的受益者只能是足球自己。
足球就是如此,它简约而直白。镜像足球凭借着一种强直性的能量而深入人心,或许快餐模式的传输会降解掉足球的部分悲剧能量,然而,镜像足球本身却可以在更为自然的语境中培育缔造出一种新型的人际关系,催生出一种新型的生活方式,并进而极大地改善球迷的心理环境。电视媒介向来具有强大的文化推介力,镜像足球直接为大众提供了更为广阔的想象空间,足球由此而转变为一种新型的生发力。
4 结语
在网络视频足球出现之前,电视足球几乎成为一种垄断性的足球传播载体。即便到了网络视频时代,电视荧屏足球还在起作用,很多网站还在购买电视足球制品。无可否认,网络视频一定会走向相对独立的一天,但是,那也是一种脱胎于电视视频的新景观。电视足球折射的是一种镜像式足球,其所培育的也是一种镜像观众,镜像观众不同于现场观众,他们更乐意静思,独享足球之美,批评足球之恶,却有可能忽略与其他球迷的共享之乐,这也是一种交际模式的新变化。当视频足球出现之时,其所带给人的是一种除却足球之外的另外的惊喜。足球不仅可以在现实生活的场域中存在,还可以在经过无数折射的荧屏中存在。世界、足球、技术的神奇性在此达成一致,共同构建出一种人世间难得一见的奇观。从镜像传输的角度看,足球并非一种预设出来的表演艺术,但是,足球是一种高尚的精神产品。电视时代使得足球的产业性得到了极大的扩张,也促成了足球产业朝大型化、国际化、越界化的方向迈进,足球由此获得了一种介于工业社会与信息社会的超然地位。足球的信息化时代给人类带来的思考空间仍然充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