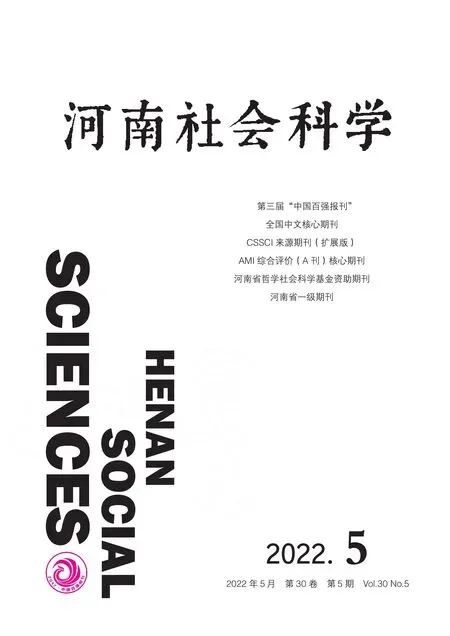迷失于颠倒的表象世界
——景观社会理论视域下的《白噪音》
郭英剑,司高丽
(中国人民大学 外国语学院,北京 100872)
法国哲学家居伊·德波于20 世纪中期创造性地提出了景观社会理论,他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已发展到视觉主导的景观阶段。在德波看来,景观并非单纯是“由大众传播技术制造的视觉欺骗”,而是“以影像为中介的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1]3。景观社会通过媒介影像的无形牵引,诱使人们从理性认知到隐性欲望均跌入景观构成的欲望世界。炫目的广告图像和标语催生着虚假消费欲望,人们的行动和思想都已被悄然掌控,日常生活变得支离破碎,渐渐沦为推动商品生产的动力与虚假欲望的载体。景观实际已发展为隐形的、非暴力的文化意识形态,温和地说服大众服从景观的奴役。
出版于1985年的《白噪音》便承载着唐·德里罗对当代资本主义景观社会的深入探析。小说由波与辐射、毒雾事件、戴乐儿闹剧三部分组成,围绕美国教授杰克一家六口的日常生活和山上学院的校园生活展开。《白噪音》作为德里罗的成名之作,展示了消费主义横行下科技发达而人们精神空虚的美国后现代社会的缩影。在这一扭曲的消费社会中,传统价值被解构,宗教信仰带来的宽慰被大大消减,人们转而通过物质消费等方式来填补内心的空虚,被媒体包围的人类在景观社会中缺失了理智,面临着死亡恐惧和精神危机。景观社会通过各种媒介,在其创造的景观时间和景观空间中通过商品麻醉消费者,使其成为商品的附属物。在毒雾事件和戴乐儿闹剧中,德里罗揭示了商品和媒介景观对人隐秘的意识形态控制。德里罗通过描写景观支配下的社会现象和个体困境,深入剖析并批判了资本主义后现代景观社会。
一、景观操纵下的生活
消费主义作为资本家压榨下层人民的新型工具,服务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资本家广泛利用生活中无处不在的广告媒介,使视觉化的图像成为人们消费的依据,从而实现资本的输出,并为大众植入消费至上的景观价值理念。对德波而言,景观并非真实存在,而是一个从现实世界中抽象出的符号,堆积在人类生活和消费过程中。在《白噪音》中,景观主要是通过消费商品和媒介影像来操纵大众心理与行为。正如小说中默里所言,美国社会的两大消费行为是看电视和超市购物,前者代表了“美国式的魔力与恐怖”,是美国人的精神消费;而后者则是美国消费社会的宗教仪式,是一种物质的消费[2]19。小说中随处可见的大型商场、超市、玻璃橱窗、商品、广告等以其令人眼花缭乱的景象、温柔的絮语诱导着消费者一同进入天堂般的购物世界。消费者自然而然地接受了这个虚幻的世界,从而被刺激消费。消费与媒介的合谋成功地将消费主体转变为异化的主体。景观理论使人们能够充分理解“消费社会的视觉文化特性之间逻辑上的联系,亦即物包围人其实就是影像包围人;消费社会本质上是一个景象社会,商品即景象”[3]。
1.符号化的商品景观
在《景观社会》的开篇引语中,德波提出了一个形象而深刻的评价:这是一个“符号胜过实物、副本胜过原本、表象胜过现实、现象胜过本质”的颠倒时代。物质消费景观造成了丰饶繁荣的假象,大众被裹挟入欲望的广阔空间,人们在此盲目消费、沉迷快感、精神消沉。在物欲横流的现代社会,占有大量物质生产成为权力的象征。
在美国后工业时代,丰富的物质产品使人们生活在商品世界中,“人们似乎是为商品而生活。小汽车、高保真音响设备、错层式房屋、以及厨房设备成了人们生活的灵魂”[4]。小说开篇德里罗就向读者展示了繁杂而炫目的商品符号景观,旅行车的车顶放置着各类物品:衣服、毛毯、文具图书、床单、小地毯、睡袋、雪橇、马鞍、木筏、音响、个人电脑、小冰箱、吹风机、烫发夹、冰球和曲棍球杆、弓和箭,还有不同品牌仍装在购物袋里的零食等[2]3。这一景观恰如德波所言,在这一世界里,商品化的过程是可见的,甚至成了所见的全部,商品构成了整个世界,亦成功地殖民化了当代社会,景观社会随之应运而生[1]14。
炫示衣食住行所用的各类商品成了学校里的重头戏,学院和商品之间的界限被彻底模糊。学生和家长把学院全然当作商品展示场所,人们被消费文化团结起来,即使被商品海洋埋葬也仍乐在其中。同时,日常生活中不常使用的物品,如雪橇板、马鞍,表明这一狂欢场景在很大程度上是社会等级和权力的符号系统之间的交流和奇观。差异性的符号消费暗示了现实生活中各人权力地位的差异。凡勃伦效应就意指这种差异性符号消费,即购买“天价”商品以获得心理满足的消费意识形态。差异性的符号消费映射着差异化的消费阶层。在景观社会中,消费不再是单纯的经济行为,而是带有社会属性、主观属性等,特别是满足过度欲望而非合理的实际需求的强化了的符号属性[5]。在商品丰富的弥散景观模式下,人们购买和消费与其说是为了物品的功能性价值,不如说是为了其符号价值。
符号消费的象征性和表征性展示了个人消费的独特品位和风格。正如杰克在商场毫不犹豫地买下大麻绳的时候说道:“我买下了五十英尺马尼拉大麻绳,为的只是放在家里,给我儿子看,讲解它产自何方,是怎样编成的。”[2]92此时这些麻绳的使用价值已被忽视,更重要的是购买麻绳在购买者身上唤起的感受和情绪,这是一种与价值体系和社会整合相异化的消费行为。伪装得友善、殷勤的商品悄然在手握控制权和无权可握的人之间划出了一条清晰可见的界限[6]。人们只有通过消费商品来证明自己的支付能力,区别自己与他人,才能获得威望和地位。
商品渐渐挣脱了指涉物的束缚,以其形象符号吸引消费者,刺激他们追求各种情感体验,快感使得形象比现实更具权威性。因此杰克会买下鲜少用到的粗绳,只因“一捆绳索看起来和摸起来是一件多么了不起的物品”。感性消费越来越占主导地位,因为消费文化使用图像、符号和符号商品来表现梦想、欲望和幻想[7]。
因此,人们的消费欲望日益膨胀,此时的消费自我“不仅是一个个体的实体,也是资本主义体制的一部分”[8]171,同时还是德波的“异化消费”(alienated consumption)的产物。在异化消费中,消费者为自己的欲望而消费。对杰克和巴比特夫妇二人来说,每次购物后,仅仅是看着熟悉的各类品牌、装得满满当当的购物袋,看着袋子上标着的质量、体积和数量,都能给他们以深深的满足感[2]21。弥散的景观伪造了个体的自由,表面上自由选择、自由消费的背后是景观的引诱和陷阱。
不只是尚在销售的货架上的商品,即使是变成没有使用价值的垃圾后商品仍对人的思维产生着巨大影响。杰克翻捡垃圾时发现一根细绳,上面打满了结和环扣,他感到自己“侦破了一个秘密,即环扣的大小之间、绳结方式(单节或双结)之间、带环扣的绳结与单独的绳结等等之间,存在复杂的关系”[2]284。一根平平无奇的绳子唤起了他如此多的深思,小小的绳结牵引着杰克的思维,甚至影响了整个人类生活,“一切都隐藏在象征之中”[2]40。但事实上,杰克并非自愿关注这些琐事,而是在后现代无深度社会影响下造成的一种条件反射——当今社会中任意事物都带有符号的烙印,除自身含义外还包含着不断变化的符号意义。
2.媒介的隐性规训
在20世纪的美国社会中,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依赖电视和广播等现代设备的信息传递功能,大众媒体扮演着宗教式的角色。唐·德里罗曾在一次电视访谈中说:“人们被各种传媒影响席卷,当媒体的刺激成了人们生活的一部分,那它也就成为小说家可以加以创作的主题。”电视、广播和其他媒介手段的现代化发展赋予人更加多元化的信息获取途径,图书报刊式的静态信息不再是主流,取而代之的是更具视觉性的信息。公众通过观赏图像资源、接收无线电信号来接收信息,日常生活可作为影视屏幕中的一种表象呈现,大众生活的可视性愈来愈强。
德波指出,“景观构成了社会上占主导地位的生活的现有模式”,其采取了新闻、广告等各种形式[9]。大众在媒介重现的充满幻象和诱惑的景观下形成了虚幻的目标导向,进而产生了欲望。因此人的存在不再基于真实需求,而是基于构成异化需求的心理需求。
正如唐·德里罗小说所示,在20 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民众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电视媒体具有重要的意识形塑功能。在德里罗看来,电视是一种非常强大的媒介,同时与其他影像媒介有所区分[2]154。电视影像对大众的独特影响源于该媒介的一些特质。首先,电视影像是不连续的,它从一个节目到另一个节目,再到一系列商业广告,并且伴随着从一个视角到另一个视角的不断转换。正如尼尔·波斯曼所说,人们看电视时所看到的是数以百万计的动态图片,持续时间短,变化大,无法产生连贯的意义[10],而这种不连续性使观众迷失方向,不知不觉成为被电视奇观操纵的傀儡[11]。弗雷德·英格利斯指出了电视屏幕的另一个固有特征,电视屏幕中的影像往往十分炫目,这种令人眼花缭乱的屏幕效果可以起到美化作用,从而激发欲望,使观众渴望他没有或不能拥有的东西,这也是电视广告如此成功的原因。此外,电视影像具有麻醉性。吉特林认为,电视将大屠杀与肥皂广告并列等同,人们的心灵被蒙蔽,意识渐趋麻痹[12]。《白噪音》中电视循环播放着灾难的场景,但这也使得大众始终与灾难本身保持距离,灾难在观众看来似乎只存在于电视屏幕之中。而在中毒事件发生后,人们即使已置身于放射物质的环境中,仍保持着观众的身份,对眼前的现实心存疑虑,焦急等待电视对此作出权威阐释。
这正体现了景观社会与专制社会的区别:景观社会所采用的统治方式更加微妙。表面上个体的自由意志并未遭受干预,实则已被隐秘操控,而这种“不干预中的隐性控制才是最深刻的奴役”[13]。这就是德波所谓的“第二自然”[1]10,也是景观社会强加的生存法则,在这个社会中,每个人都被景观的现实所包围,无从逃脱。
在影像的包围下,屏幕影像成为人们感知日常生活和世界的主要方式,现实的触觉感知功能逐渐退化。然而由大众媒体所建构的景观真实是一种被美化的表象,用于欺骗和教化民众。更重要的是,景观并非单纯是一种由媒介创造的视觉欺骗,而是已经物化了的世界观[1]3。在妻子的要求下,杰克一家每星期五都一起看电视,把此作为一种自我放纵和逃避现实的手段,集体接受电视广告的规训。广告的影响是悄无声息的,杰克在和女儿斯泰菲谈话的时候,一则推销产品的广告短歌无意识地出现在他脑海里。媒体训导人们如何享受生活,并向杰克逼真地展示了拥有某种商品将如何影响他的行为和情感,以至于杰克在观看广告以外的时空时仍无法摆脱其控制。大众在影像屏幕的视觉冲击中沉沦,其感官被悄然蛊惑。人们屈服于媒介影像,唯一的生活空间便是电视所展现的表象世界。日常生活失去了自身的神秘性,一切皆为表象存在。由于过度依赖视觉图像的引导,人对世界与自我变得越发迷茫,无法感知自身真实欲求。
二、景观统治下的主体异化
在表象化的景观社会中,大众在影像的蛊惑下失去了独立思考的能力,面临着一系列的精神危机。真实的日常生活被遮掩、替代,人们迷失在景观创造的欲望迷宫之中,无孔不入的催眠洗脑使人们日渐麻木,主体性随之失落。
1.单向度的默从
景观是一种深层的无形控制,主体的反抗和批判否定性被消解,人只能屈服默从[14]9。身处媒体建构的影像时代,真实与虚拟的界限被模糊、消除,大众在虚拟现实和真实现实间彷徨,对生活的本真感受淡化,内心世界千疮百孔,恐惧危机感无处排解,“人们作为社会主体的存在正日益被陷入一种危机的深渊”[15]。
个体在这个由各种媒体建构的景观现实社会中只追求感官刺激,不加独立思考与辨别。公众对景观的兴趣取代了对现实本真生活的渴望。个性自我在这种不干预的隐性控制下被抹去,日常生活变得同质化、重复化。同时,在媒体的影响下,人们的言说方式逐渐变为一种既定的形式。媒体重新建构了人的思想和语言,人们不再进行自我表达,而是替媒体发声,传播被媒体灌输的信息。
例如《白噪音》中斯泰菲听从收音机中的要求,坚持将水煮开[2]36。即便在梦中也在喃喃自语“Toyota Celica”这一汽车品牌名[2]169,打电话时不自觉地念出衣服上的标牌“丙烯氰纶纤维”[2]53。孩子们日常以讨论电影、汽车品牌,模仿电视里人物的说话口形为乐。发生中毒事件后,孩子们随时关注广播,不断将最新报道告知父母,并在听了收音机的描述后出现了相应的中毒症状。杰克驾车时与海因利希针对天气状况激烈地辩论起来,海因利希坚持认为被打湿的玻璃上只是硫酸或战争的灰尘,因为收音机没有播报现在正在下雨的信息。海因利希坚信人的感觉永远不可能比媒体更加正确,人们无法凭借自身体验认知日常生活。电视、广告等媒介影像以非暴力方式建构着意识形态,从而控制大众的日常生活。
人们对当前的日常生活漠不关心,只是被景观社会创造的陌生的图像世界所控制。巴比特购买麦芽加酸乳酪的习惯就是这样一种行为。尽管家中并没有人爱吃这种酸乳酪,她仍会不断购买,哪怕最后会因变质而扔掉。人们变得麻木不仁,孤独、烦闷、抑郁,“只有灾难才会吸引人们的注意力”[2]72。景观社会通过媒介传递的信息使大众产生惰性,在娱乐化呈现影像的过程中,大众对信息的接受度上升,批判意识缺失。收看电视里播放的水灾、地震、火山喷发等各种灾难新闻时,杰克感到一家人从未“如此专心致志”,大家都沉浸在记录灾祸和死难的短片中[2]70。迟钝的感知使他们渴望更猛烈的刺激,但这样短暂的感官刺激于事无补,因为“世界就是一幅无处不在的景观”,人们无从选择和反抗,只能在无意识地遵守景观生活方式的过程中巩固着景观的统治[13]。
2.时空谎言的空虚
德波指出,分离对于景观的统治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分离创造出了人们的伪意识和伪需求,是资本剥削的新手段。正是通过分离,“景观统治的实现不再主要以生产劳动为限,相反,它最擅长的,恰恰是对劳动时间之外的闲暇时间的支配和控制”[14]102。除了固有的劳动时间以外,人们的自由休息时间也被资本家用于牟利,例如杰克一家通过购物和围坐在一起看电视的方式放松,实际上却被广告宣传催眠洗脑、刺激消费,不断被榨取价值。
而从空间角度来看,传统意义上的乡村早已不复存在,只剩下城市化进程中涌现的一个个伪乡村。伪乡村中居住的农民是虚假的、非原生态的农民。事实上,无论是城市居民还是乡村农民都同样接受着媒介传递的各类信息,二者并无本质差别。如同杰克与默里所前往的农舍,虽然它具备着“一片片的草地和一个个苹果园,白色的篱笆伸展在起伏的田野上”这样的传统农舍造型,但早已失去了传统农舍的含义,它存在的唯一意义就是为人提供虚假的消遣娱乐。参观的游人们都带着相机,有的还带着各类专业设备。然而游客在此照相并非因为农舍本身的美丽,事实上,根本“没人看见农舍”,人们所见仅是写着“美国照相之最的农舍”的标示牌[2]12。景点本身如何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其代表的符号意义。
德波特别批评了城市和城镇化后的乡村,指出“城市化是真正的分离技术”[14]102,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由原始村庄中带有人情味的关系变为一种互不了解、互不关心的关系。人成为元素、成为原子,人与人之间越发疏远陌生,如同杰克一家,即使身处同幢房屋,仍能感受到一种无法排解的孤独。为了掩饰,他们又打开电视等媒体,用虚假的热闹填补精神的空虚。
三、结语
景观社会通过媒介影像刺激消费,操纵意识,混淆真实与虚幻,消解人的主体意识。杰克一家在符号化的世界里、在对媒介的依赖中迷失自我,深陷死亡的恐惧之中。景观社会的意识形态控制是隐秘的、无形的,而正是这样的隐形手段才能最大限度地麻醉和奴役大众。
詹妮弗·瓦拉在总结德里罗千禧年以后的作品时指出,这些作品缺乏富有典型英雄气质的主人公,而仅是一些“普通个体,他们在有限的、平庸的活动中前进”。虽然杰克无法阻止景观的入侵,但他也曾在影像的狂轰滥炸中追寻日常生活和真实的具身体验。他努力尝试恢复自身视觉观看、言说交流与情感体验的能力,都是为了能够发挥自身主动性,但是打破幻象的同时需要提高警惕,避免遁入新的虚幻中。人们如果选择使用暴力的方式打破虚假的幻象,就会将影像中的暴力行为带入现实中,致使大众遁入更深的迷惘中。杰克枪杀卖假药的人,是为了揭穿“戴乐尔能消除恐惧”这一谎言,打破那些蒙蔽、钝化人们直面生存危机能力的虚假幻象,让人们的生活重新回归真实。但是杰克的枪杀行为只是把影像中的暴力带入现实,在枪杀事件后,杰克的生活并未发生改变,他的心灵世界也未能获得救赎。唐·德里罗借这一场景警示大众,人们在试图打破幻象时,不可以用影像中提供的方式去报复幻象,以免遁入新的虚幻。
正如德波所言,日常生活是景观社会得以形成的重要基础,颠覆景观社会“就是要在日常生活中揭露景观的异化本质,进而摧毁景观,指引人们重回真实生存的瞬间”[13]。大众在认知到影像的虚幻性时,应该学会审视自己的生活,学会以亲身体验的方式去感知日常生活中的细微事物,捕捉“日常生活的光辉”[8]70。大众要善于发掘曾经被忽视的日常细节之美,这样才能真正走出景观的虚假幻象,获得对自我、生活最本真的感知,找回迷失的自我,消解焦虑、恐惧,心灵世界才能获得救赎。德里罗在《白噪音》中,通过揭示景观堆聚下人们的精神困境,把人们引向对后现代社会的自我审视和自我反思,重新认识景观支配下信息超载、精神破碎的自我,这一具有前瞻性和预见性的批判与剖析对于快速发展的世界极具启示性意义。
注释:
①司高丽同为本文第一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