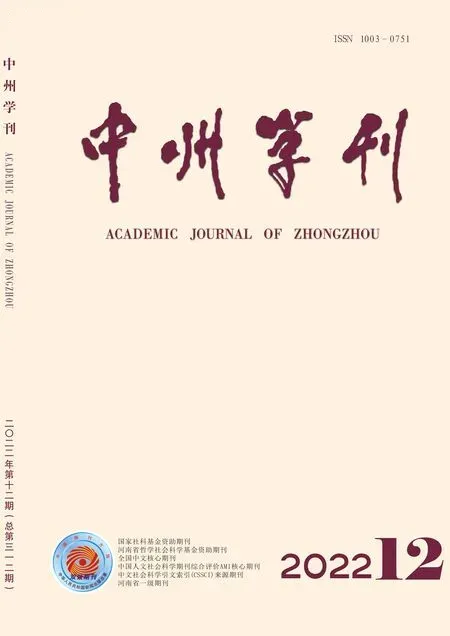周王室大夫怨刺平王与携王“二王并立”组诗考论*
——以《诗经·小雅》之《雨无正》《角弓》《小旻》《菀柳》为中心
邵 炳 军
周幽王十一年(公元前771年),西周覆亡,宗周(即西周都邑丰京与镐京,位于今陕西省西安市长安区沣水东西两岸)为犬戎所占,王室旧臣虢公翰等人拥立幽王庶子王子余臣于携邑(即今渭南市大荔县朝邑镇之“王城”)为王,史称“携王”(清华简《系年》作“惠王”)[1]。于是,携王与早已在西申(姜姓国,在今宝鸡市眉县附近,位于宗周以西)僭立为“天王”的废太子宜臼(平王),形成“二王并立”的政治格局,长达十二年(公元前771年—公元前760年)之久①。这种不同政治营垒之间的“二王并立”,是两周之际周王室内部发生的重大政治事变,更是西周与东周分界的标志性历史事件,自然会对诗歌创作产生深刻影响。其中,《诗经·小雅》中周王室大夫所创作的《雨无正》《角弓》《小旻》《菀柳》等组诗②,从不同角度艺术地再现了“二王并立”政治格局的基本状态,表达了诗人对形成这一政治格局的始作俑者——平王与携王的不满情绪,以及对携王前途命运之忧患意识。
一、《雨无正》——携王侍臣忧平王与携王兄弟相争之作
《雨无正》全诗如下:
浩浩昊天,不骏其德。降丧饥馑,斩伐四国。旻天疾威,弗虑弗图。舍彼有罪,既伏其辜。若此无罪,沦胥以铺。
周宗既灭,靡所上(止)戾。正大夫离居,莫知我勚;三事大夫,莫肯夙夜;邦君诸侯,莫肯朝夕。庶曰式臧,覆出为恶。
如何昊天,辟言不信。如彼行迈,则靡所臻。凡百君子,各敬尔身。胡不相畏?不畏于天。
戎成不退,饥成不遂。曾我暬御,憯憯日瘁。凡百君子,莫肯用讯。听言则答,谮言则退。
哀哉不能言,匪舌是出,维躬是瘁。哿矣能言,巧言如流,俾躬处休。
维曰予仕,孔棘且殆。云不可使,得罪于天子。亦云可使,怨及朋友。
谓尔迁于王都,曰予未有室家,鼠思泣血,无言不疾。昔尔出居,谁从作尔室?③
“昊天”“旻天”“天”,即“苍天”“皇天”“上帝”。唯“以体言之”者,称“苍天”;“尊而君之”者,称“皇天”;“元气广大”者,称“昊天”;“仁覆闵下”者,称“旻天”(《诗·王风·黍离》毛《传》)。足见所谓“昊天”“旻天”“苍天”“皇天”,皆为周人从不同层面对“天”的尊称。在周人眼里,天是一种有意识的人格神,更是一种至上神——上帝。因此,在西周青铜铭文中“帝”“上帝”“皇上帝”“皇天上帝”“皇天王”“昊天王”“天”等名称开始是混用的,至西周后期“天”的称谓越来越多。在称谓变化的同时,周人也逐渐改变着至上神的神性,反映了殷周两代人对宗教性质理解上的差异:从“上帝”到“天”的转变,反映了人对宇宙统一性认识的提高;至上神身份从“上帝”变成了“天”,人格性特质减少,抽象性与自然性特质增强。降及厉幽之际,宗周灭亡前后,人们对于天,不再像西周鼎盛时期那么寅畏虔恭,而是持怀疑态度,开始“怨天尤人”了。在两周之际,天国大厦的思想根基已逐渐为新思想因素所摇撼。可见,自西周初期至末期(约公元前1066年—公元前771年)近三百年间,周人的宗教情感思维本身在逐渐发生着深刻的变迁,即由“敬神畏天”向“怨天尤王”的巨大变化④。
关于“周宗”,清代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卷二十曰:“《诗》‘周宗’当为‘宗周’传写误倒。”[2]623-624我们知道,周人所表现出的宗教情感思维,自然具有一定的现实指向,即借宗天思想体现出宗周倾向,在《周颂》之《时迈》《大雅》之《思文》《荡》《文王》《大明》《思齐》以及《小雅》之《巧言》《雨无正》等作品中便是如此[3]。生产力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必然会引起人们政治思想的变化,周人的宗天思想、宗周倾向自然会使其将周王室都邑丰镐乃至西周王室之名以“宗周”来代称。在携王与平王“二王并立”初期,携王居于丰镐以东王畿之携地,平王居于丰镐以西之西申国,宗周则为戎狄所占。戎狄撤出宗周后,携王与平王为了争夺王位继承之正统,自然以夺取宗周为首要任务。《雨无正》的作者出于对幽王立谗人而废卿士、弃聘后而立内妾、御侏儒而法不昭、幸嬖女而以为后、立伯服而黜太子以致西周灭亡的积怨,自然希望居于西申的平王能够尽快自西申东迁宗周以继大统。因此,宋代范处义《诗补传》卷十八曰:“‘周宗既灭,靡所止戾’者,谓幽王既死于犬戎之祸,宗姓皆流离无有定止。曰‘既灭’,犹言靡有孑遗,甚之之辞也。”[4]
全诗共七章,诗人在首章一开篇所写的十句诗中,就展现出天命观念从周初之兴到周末之衰的演变轨迹——原来至高无上的天命观念,遭遇到痛切的失望、深刻的怀疑和激烈的否定;次章在总叙“周宗既灭”政治背景之后,便开始分叙“靡所止戾”的具体表现;第三章责王不听正言,大臣不畏天命;第四章言外患与饥馑日甚,诸臣不敢诤谏,只能独自忧伤憔悴;第五章以能言者与不能言者对比,讽刺王恶忠臣而好谗佞;第六章言出仕之危与诤谏之难;卒章言劝说出居者迁回王都而被拒[5]。不过,我们还应看到,在该诗“怨天尤王”主题中,前者为次,后者为主;“怨天”只是激烈的宣泄,“尤王”才是根本的目的。因此,明代季本《诗说解颐·正释》卷十八曰:“此平王时诗也。周室东迁,平王不能自强于政治,赖卫武公、郑武公相之,而得以立国。及二公去位既久,王至晚年,失道滋甚。正大夫离居,群臣莫肯供职,其暬御之臣独以为忧,故作此诗以责留者之怠事,去者之弃君。盖朋友规诲之辞。其忧幽深,其言切直,可以为忠矣。……此言周既东迁,群臣解体,而王心犹不知用善自惩,乃反出而为恶,威虐愈甚也。”[6]
在平王与携王“二王并立”的初期,两个王权对立的政治集团泾渭分明:站在平王一方的为申、吕、许等姜姓国及依附申国的缯国和西夷犬戎,仅仅占有从郿至宗周的渭河以北狭小地带;而站在携王一方的有以虢、芮、虞、晋、鲁、卫为首的姬姓诸侯和嬴姓秦国①,他们占据着华山以北河南、河东及河西部分土地,完全控制了宗周、骊戎通往东都雒邑(地在今河南省洛阳市王城公园一带)的交通要道。后来,由于平王改变了对敌对势力的态度,封秦襄公为诸侯并赐以岐、丰之地,又与东方的姬姓诸侯实现和解,使晋文侯、卫武公、秦襄公、郑武公转而支持平王,双方的力量对比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平王一方的实力增强,而携王一方的力量减弱。一直到平王十一年(公元前760年),携王被晋文侯所杀,“二王并立”的政治局面终告结束,平王方成一统。可见,正是这一特殊政治环境,才使得“正大夫离居”“三事大夫,莫肯夙夜。邦君诸侯,莫肯朝夕”。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诗人对“正大夫”“三事大夫”“邦君诸侯”等“靡所止戾”之怨忧情绪,是周人天命观念由尊天敬神向怨天尤人转变的具体表现,导致这一巨变的直接动因便是两周之际“二王并立”政治格局的出现。当然,“二王并立”政治格局的形成,既是西周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事情,又是引发骊山之难、导致西周覆灭的导火线。它不仅说明两周之际的王权观念已经发生重要变化,更反映了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达到了白热化程度。因此,平王自西申东迁宗周以继大统之后,“外迫戎翟之祸,内畏携王之逼”[7],其东迁雒邑是大势所趋。
二、《角弓》——周大夫刺平王与携王兄弟相残之作
《角弓》全诗如下:
骍骍角弓,翩其反矣。兄弟昏姻,无胥远矣。
尔之远矣,民胥然矣。尔之教矣,民胥效矣。
此令兄弟,绰绰有裕。不令兄弟,交相为瘉。
民之无良,相怨一方。受爵不让,至于巳(已)斯亡。
毋教猱升木,如涂涂附。君子有徽猷,小人与属。
关于“兄弟昏姻”,毛《传》缺,郑《笺》泛言“九族”“骨肉之亲”,此说不确。《小雅·沔水》毛《传》:“兄弟,同姓臣也。”《王风·葛藟》郑《笺》:“兄弟,犹言族亲也。”意皆未尽。《葛藟序》郑《笺》:“九族者,据己上至高祖,下及元孙之亲。”孔《疏》:“此古《尚书》说,郑取用之。《异义》:‘今戴礼、尚书欧阳说云:九族,乃异姓有亲属者。父族四:五属之内为一族,父女昆弟适人者与其子为一族,己女昆弟适人者与其子为一族,己之子适人与其子为一族;母族三:母之父姓为一族,母之母姓为一族,母女昆弟适人者为一族;妻族二:妻之父姓为一族,妻之母姓为一族。’”《颜氏家训》卷一《兄弟篇》:“夫有人民而后有夫妇,有夫妇而后有父子,有父子而后有兄弟:一家之亲,此三而已矣。自兹以往,至于九族,皆本于三亲焉,故于人伦为重者也,不可不笃。”[8]此化用《葛藟》,正取“人伦笃重九族”之义。从诗中“兄弟”与“昏姻”并提可知,此“族亲”,皆指父系九族;则“兄弟”,乃指同姓兄弟,即王族,亦即王室同宗族人。因此,清代段玉裁《毛诗故训传》卷六曰:“《礼·丧服》曰:‘小功以下为兄弟。’篇中言‘兄弟’者,自其亲疏言之,谓于王疏也。《丧服》曰:‘昆弟’、曰‘从父昆弟’、曰‘从祖昆弟’、曰‘族昆弟’,虽疏,必曰‘昆弟’,亲亲之辞也。此诗自称曰‘兄弟’,谓王曰‘昆’,不敢以其戚戚君而循九族之称也。”[9]同姓为兄弟(父系九族),异姓为昏姻(母系三族与妻系二族),此连类相及,皆谓兄弟。

《焦氏易林·升之需》:“商子无良,相怨一方。引斗交争,咎以自当。”[11]此化用《诗》之义。据《史记·周本纪》,周王室在恭王之后只有懿、孝二王为兄弟相及,但他们与此诗无关。故《升之需》引《诗》以“商子”代“民”,则诗中所谓“商子”者,当为“二王并立”时的幽王之废太子宜臼与庶子余臣。故“受爵不让”之“爵”,应指代王位。在诗人笔下,万民所“胥效”的兄弟,“相怨一方”,“如蛮如髦”,势不两立,正与“二王并立”时事相合:宜臼借助西申侯之力,依靠西戎之师,弑父而灭宗周,兄弟相及,互相残杀;此事不仅为万民所知晓,而且亦为万民所效仿,诸侯乃至国人自然形成了水火不容的两大政治营垒,这种状况使诗人忧之。因此,清人胡承珙《毛诗后笺》卷二十二曰:“谓王视骨肉如夷狄然,是诗人之所忧也。”[12]1180
三、《小旻》——携王大夫刺携王斗筲用事之作
《小旻》全诗如下
旻天疾威,敷于下土。谋犹回遹,何日斯沮?谋臧不从,不臧覆用。我视谋犹,亦孔之邛。

我龟既厌,不我告犹。谋夫孔多,是用不集。发言盈庭,谁敢执其咎?如匪行迈谋,是用不得于道。
哀哉为犹,匪先民是程,匪大犹是经;维迩言是听,维迩言是争。如彼筑室于道谋,是用不溃于成!
不敢暴虎,不敢冯河。人知其一,莫知其他。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

关于“不敢暴虎,不敢冯河”,毛《传》:“冯,陵也。徒涉曰冯河,徒搏曰暴虎。”《尔雅·释训》:“暴虎,徒搏也。冯河,徒涉也。”《说文·马部》:“冯,马行疾也。”段《注》:“此冯之本义也。展转他用,而冯之本义废矣。……或假为淜字,如《易》《诗》《论语》之‘冯河’,皆当作淜也。俗作凭(憑),非是。”[13]466《水部》:“淜,无舟渡河也。”段《注》:“淜,正字;冯,假借字。”[13]555《攵部》:“夌,越也。”段《注》:“今字或作淩,或作凌,而夌废矣。”[13]232清代陈奂《毛诗传疏》卷二十五:“冯、陵叠韵。……陵与夌通。”[14]4071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卷二十曰:“冯者,淜之假借。……淜通作冯,犹‘百朋’作‘百冯’也。”[2]632可见,“夌”与“陵”“淩”“凌”为古今字,故通用;“冯”与“陵”二字叠韵,皆有“涉”“渡”“越”之义,故同义;而就其“徒涉”,即“无舟渡河”之义项而言,“冯”“夌”“陵”“淩”“凌”诸字,皆为“淜”之假借字,而“淜”才为本字。
全诗共六章,首章总言当时国策邪僻不正;次章言无正确国策之危害:事前不能辨别国策之善恶,临事不能决断国策之依违;第三章言国策不定而无人敢于负责之危害;第四章言制定国策无远见,但凭浅近之言,必无成功之望;第五章言治国之贤臣难以受到重用;卒章以“暴虎”“冯河”“临渊”“履冰”反复设喻,比喻王或执政无国策,或有国策而不能掌控⑦。
由此可见,全诗以“谋犹回遹”一句为纲贯穿全篇,诗人言“国虽靡止”的原因,正是朝中无能臣,才使携王斗筲用事、治乱乏策;诗人谓即使国小民寡者,亦有才智之士,王可与之决策图功,莫使共同失败,暗含何况我王有如此广土众民之泱泱大国者。此正写当为扶持携王余臣的虢国翰死后的情景,反映了携王朝斗筲用事、治乱乏策的现实,暗示了携王终将覆亡之结局。因此,宋代王质《诗总闻》卷十二评之曰:“此诗多及‘谋’,犹当是与图事者,君子之言不用,小人之言是从。故君子为忧。”[16]
四、《菀柳》——携王侍臣怨己有功却获罪之作
《菀柳》全诗如下:
有菀者柳,不尚愒焉?上帝甚蹈,无自瘵焉。俾予靖之,后予迈焉。
有鸟高飞,亦傅于天。彼人之心,于何其臻?曷予靖之,居以凶矜!
关于“有菀者柳”,《白孔六帖》卷一百引作“有苑者柳”。“菀”,毛《传》训为“茂木”,郑《笺》从之;“苑”,《白孔六帖》卷一百训为“茂皃”,则以“菀”与“苑”字异而义同。
关于“上帝甚蹈”,毛《传》未释“上帝”,郑《笺》将“上帝”训为“幽王”,宋代朱熹《诗集传》卷十四:“上帝,指王也。蹈,当作神,言威灵可畏也。”[17]清代姚际恒《诗经通论》卷十二:“‘上帝甚蹈’,《战国策》《荀子》作‘上天甚神’。古人引《诗》类多字句错互,学者宜从本书,不必言矣;然其解释则可以依之。如以‘上帝’为‘上天’,则上帝指天也。”[18]248“上帝”本指至高无上之神明,这里则以“上帝”之地位、权势来影射周王[19]。
全诗三章,首章以“有菀者柳,不尚息焉”这一客观事象起兴,反喻朝王将有不测之祸;次章以“有菀者柳,不尚愒焉”这一客观事象起兴,亦反喻朝王将有不测之祸;卒章以“有鸟高飞,亦傅于天”这一客观事象起兴,喻不朝王亦将有不测之祸,暗示既让我治理政事,又将我置于凶险之地⑧。因此,清代姚际恒《诗经通论》卷十二评之曰:“(首章)兴也。……(次章)兴也。……(卒章)喻得淡,妙。……兴而比也。”[18]247-248

我们结合此诗的创作背景可知,诗中的“上帝”,即影射携王。因此,《菀柳》当为携王近侍之臣所作,这位近侍之臣应为有功之臣,然因故获罪后作了这首怨刺诗。
综上考论,《雨无正》为携王侍臣忧平王宜臼与携王余臣兄弟相争之作,《角弓》为周大夫刺平王与携王兄弟相残之作,《小旻》为携王大夫刺携王斗筲用事、治乱乏策之作,《菀柳》为携王侍臣怨己有功却获罪之作。此四诗从不同角度表现出诗人对造成两周之际第三次“二王并立”政治格局始作俑者——平王与携王的不满情绪,以及对携王前途命运之忧患意识。由此可见,尽管这些诗篇非一人所作,但为同一时期表达相同主旨的组诗。
注释
①具体论述参见邵炳军的文章《两周之际三次“二王并立”史实索隐》(《社会科学战线》2001年第2期)与《论周平王所奔西申之地望》(《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4期)。②关于《诗经》中保存有“组诗”的相关论述,可以参看郭晋稀《风诗蠡测》(《甘肃师范大学学报》1981年第4期)。《诗·小雅》之《雨无正》《角弓》《小旻》《菀柳》四首诗的创作年代大致在平王元年至十一年(前770—前760)之间,具体论述参见邵炳军的《〈诗·小雅·雨无正〉篇名、作者、作时探微》(《上海大学学报》2003年第2期)《〈诗·小雅·正月〉〈雨无正〉〈都人士〉〈鱼藻〉创作年代考论》(《广东社会科学》2012年第1期)与《春秋文学系年辑证》(高等教育出版社2013年版,第15—18、69—75页)。③本文所引《毛诗正义》《春秋左传正义》《尔雅注疏》,皆据中华书局2009年影印清嘉庆二十至二十一年(1815—1816)江西南昌府学刊刻阮元校勘十三经注疏本,不再逐一标注。④具体论述参见陈志信、靳无为《〈诗经〉中天(帝)的探讨》(《台州师专学报》1990年第2期)、郭杰《从〈诗经〉看周代天命观念之兴衰》(《江海学刊》1999年第2期)、罗新慧《周代天命观念的发展与兴变》(《历史研究》2012年第5期)。⑤吕,在今渭南市大荔县羌白镇、吕曲一带,东及蒲阪,非位于今南阳市西三十里吕城之吕国。许,在今渭南市大荔县东北许原一带,非位于今许昌市东三十里许城之许国。郿,在今宝鸡市眉县境,为周宣王迁申伯饯行处。事见《诗·大雅·嵩高》。芮,在今渭南市大荔县东南。虞,在今山西省运城市平陆县境。参见:《春秋地名考略》卷九、卷十二、卷十三,《春秋地理考实》卷一、卷二。⑥具体内容参见范处义《诗补传》卷二十一、严粲《诗缉》卷二十四、姚际恒《诗经通论》卷十二与陈子展《诗经直解》(复旦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816—821页)。⑦具体内容参见范处义《诗补传》卷十八、严粲《诗缉》卷二十一、季本《诗说解颐·正释》卷十九、钱澄之《田间诗学》卷七、陈子展《诗经直解》(复旦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676—680页)以及程俊英、蒋见元《诗经注析》(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588—594页)。⑧具体内容参见苏辙《诗集传》卷十三、王质《诗总闻》卷十五、梁寅《诗演义》卷十四、钱澄之《田间诗学》卷八与陈子展《诗经直解》(复旦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820—82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