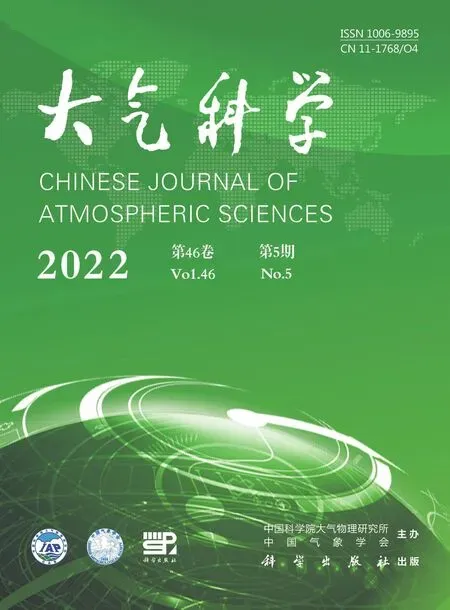青藏高原深对流及其在对流层—平流层物质输送中作用的研究进展
陈权亮 高国路 李扬
1 成都信息工程大学大气科学学院/高原大气与环境四川省重点实验室, 成都610225
2 四川省雅安市气象局, 雅安625000
1 引言
深对流在对流层向平流层的物质输送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深对流中强烈的上升运动能够在数小时内将水汽和污染物从边界层和对流层低层输送到十几公里以上的上对流层和下平流层(UTLS)(Dessler and Sherwood, 2004)。进入平流层的水汽和气溶胶又对辐射平衡、平流层臭氧恢复产生显著的影响,通过正向或负向的辐射强迫控制着全球变暖的趋势(Kirk-Davidoff et al., 1999)。对流层—平流层物质交换(STE)对全球气候变化有着重要的影响,国内外的一些学者对此已做过一系列综述(Holton et al., 1995; Shepherd, 2002; 杨健和吕达仁,2003; 陈洪滨等, 2006; 吕达仁等, 2008)。
近年来,青藏高原和亚洲季风区被认为是对流层向平流层物质输送(TST)过程中除热带地区以外 的 另 一 个 重 要 窗 口(周 秀 骥, 1995; Fu et al.,2006a; Park et al., 2009)。卞建春等(2011)评述了这一重要的进展,并强调了亚洲夏季风在对流层向平流层物质输送中的重要作用。通过卫星观测,发现在青藏高原上空存在明显的臭氧低谷(周秀骥, 1995; Bian, 2009)、水汽极值中心(Gettelman et al., 2004; James et al., 2008)以 及 气 溶 胶 层(Vernier et al., 2011, 2015)。卞 建 春 等(2013)综述了这些重要的观测事实,并对比了亚洲季风区和北美季风区在UTLS 大气成分、卷云以及深对流活动特征等方面的差异,讨论了南亚高压对UTLS大气成分分布的重要作用。Bian et al.(2020)综述了亚洲季风区近地面污染物向UTLS 输送的物理机制,以及污染物传输造成的区域和全球气候效应。
上述研究均指出亚洲季风区UTLS 存在的臭氧低谷、水汽极值中心和气溶胶层与青藏高原及其周边的深对流有密切的关系,近年来关于青藏高原及其周边的深对流研究也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的进展,这些研究有助于进一步理解深对流的物质输送作用,以及青藏高原对全球大气和气候的调制作用。本文对此进行了回顾,并对一些科学问题进行了讨论和展望。具体的章节安排如下:第二节简述了对流层向平流层物质输送的主要途径,并且列举了近年来青藏高原地区作为对流层向平流层物质输送窗口的观测事实。第三节概述了目前深对流观测的主要手段,总结了通过卫星识别深对流的两类主要方法。第四节描述了深对流向平流层物质输送的物理过程,讨论了对流层顶过渡层在传输过程中的影响。第五节对比了青藏高原、亚洲季风区和热带地区深对流的活动特征差异,并从云微物理、对流层顶最冷点温度和环境场相对湿度的角度,讨论了影响深对流输送过程的主要因素。第六节对本文的主要内容做了小结和展望。
2 对流层向平流层的物质输送与重要的输送窗口——青藏高原
2.1 对流层向平流层物质输送的主要途径
平流层的水汽和气溶胶能够为平流层和对流层提 供 显 著 的 辐 射 强 迫(de F. Forster and Shine,2002),影响平流层的臭氧恢复和全球的变暖趋势(Kirk-Davidoff et al., 1999; Solomon, 2010, 2011)。跨对流层顶的水汽传输贡献了平流层水汽约50%的来源,另外50%则主要来自甲烷的氧化反应(Oltmans and Hofmann, 1995)。平流层的气溶胶也来源于对流层向平流层的输送(Etheridge et al.,1998)。这种对流层向平流层的物质输送在全球尺度上主要受Brewer-Dobson 经向环流(Brewer,1949; Dobson, 1956)的影响。Holton et al.(1995)指出这种Brewer-Dobson 环流是由于行星波和重力波向上传播到平流层以上高度破碎后,产生动量通量的辐合辐散,形成一种全球尺度的“流体动力抽吸泵”。因此,这种全球尺度的经向环流也被称作“波驱动环流”。
在热带外的中纬度地区,天气尺度系统也对TST 过程有重要影响。这种输送过程主要是一种沿等熵面的绝热过程,通过涡动来完成。例如:在稳定的急流轴和高空锋区附近(Kelly et al., 1990)、高空槽及切断低压的发展过程(Wirth, 1995)中都会发生对流层向平流层的物质输送。但这种物质输送是相互的,例如:伴随着上对流层气旋生成及大尺度斜压波的“对流层顶折叠”也是导致平流层空气进入对流层的重要过程(Hoskins et al., 1985)。
与行星尺度和天气尺度的TST 过程相比,中小尺度的深对流是另外一种重要的平流层—对流层物质交换的系统(Poulida et al., 1996; Fischer et al.,2003)。在时间尺度上,深对流能够在数小时内将对流层低层的物质输送到UTLS,而天气尺度和行星尺度系统通过斜压和涡动的传输方式,使得这种过程往往需要数天的时间。在空间尺度上,深对流的传输则更具有局地性,准确的理解深对流的物质输送,对于认识平流层水汽和气溶胶的纬向分布不均有重要意义(Dessler, 2002)。从传输方式而言,深对流提供了一种更为直接的传输路径,近地面的水汽和气溶胶能够通过对流的绝热上升过程被快速抬升到UTLS,这有效提高了边界层水汽和气溶胶向上的传输效率。
除此之外,一些研究认为热带平流层纬向风的准两年周期振荡能够通过其次级环流影响TST 过程(Giorgetta and Bengtsson, 1999)。Wang et al.(2009)认为重力波在对流层顶的破碎,以及不稳定切变引起的湍流混合过程,也会引起跨对流层顶等熵面的物质输送。另外,上对流层是洲际航空运输的主要通道,飞机尾气的排放对于UTLS 的化学成分也有一定影响(陈洪滨等, 2006)。
2.2 UTLS 水汽、气溶胶和臭氧在青藏高原的极值区
早在20 世纪90 年代,周秀骥(1995)使用TOMS 卫星资料发现,在6~9 月的青藏高原上空存在一个明显的臭氧总量低值区,并称之为青藏高原臭氧低值中心。周秀骥(1995)推测青藏高原周围数百公里范围内的低空污染物可能在夏季向青藏高原辐合,然后上升到平流层下部,对流层低浓度臭氧向平流层的输送以及低空污染物在平流层引起的物理化学过程,可能是引起夏季青藏高原臭氧总量异常降低的重要原因。Tian et al.(2008)使用TOMS 和SAGEⅡ卫星观测数据以及数值模拟对青藏高原臭氧的进一步研究发现,对流传输过程相比化学过程对青藏高原臭氧低谷的形成起到了更为重要的作用。
Park et al.(2007)使用Aura MLS 数据研究了北半球夏季的一氧化碳和臭氧分布,结果发现在南亚反气旋区域存在一氧化碳的极大值和臭氧的极小值,其分布与深对流的强度和频率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Park et al.(2008)进一步指出南亚反气旋内的污染物主要是来自近地面的传输。反气旋内的污染物浓度变化也被认为是近地面污染物排放留下的“指 纹”(Li et al., 2005; Randel and Park, 2006;Park et al., 2009)。Randel et al.(2010)指出亚洲季风区向平流层输送的大气污染总量甚至强于整个热带地区。Yu et al.(2017)使用模式模拟的结果也表明亚洲大量增长的人为气溶胶,通过季风对流的快速传输对整个北半球下平流层的年平均气溶胶贡献,达到了显著的15%,这一贡献相当于2000年至2015 年火山喷发气溶胶的总量。
Gettelman et al.(2004)通过卫星观测发现了UTLS 水汽的极大值中心更多的位于青藏高原而不是南亚地区。James et al.(2008)也发现100 hPa水汽的大值中心主要位于青藏高原地区。Sun et al.(2017)发现这种水汽的大值区又主要分布在青藏高原的东南侧。Fu et al.(2006a)使用WACCM模式对100 hPa 大值中心的CO 和水汽进行后向轨迹模拟的结果表明,青藏高原及其南坡深对流对平流层水汽和CO 的输送作用要大于南亚季风区。
3 深对流的观测与识别方法
3.1 深对流活动主要的观测途径
TRMM 卫星从星载测雨雷达的角度,最早提供了一个观测深对流的视角(Simpson et al.,1996)。尽管极轨卫星观测到深对流的频率较低,但是仍然为研究热带和副热带地区深对流的结构、频率和时空分布提供重要的观测事实(Liu and Zipser, 2005; Liu et al., 2007; 刘鹏等, 2012)。TRMM卫星从1997 年发射到2015 年退役运行了长达17 年,较长的时间序列也使得研究深对流的年际变化以及对气候变化的响应成为可能(Zipser et al.,2006)。2014 年,美国宇航局和日本宇宙探索管理局在TRMM 卫星的基础上成功发射了GPM 卫星(Hou et al., 2014)。GPM 卫星作为TRMM 卫星的升级版,一方面将观测的范围从副热带和热带地区扩展到了中高纬度,这为研究中高纬度的深对流提供了重要帮助(Gao et al., 2019),另一方面,由于GPM 卫星将测雨雷达增加到了双频,提升了对降水粒子滴谱的反演能力,从而有效提升了对深对流云微物理结构的描述和理解(Chen et al.,2020a, 2020b)。
A-train 卫星编队为理解深对流与环境场的相互作用,提供了另外一个更为全面的视角。Atrain 系列卫星在一个相近的太阳同步轨道上,以大约15 min 的间隔相继扫描同一地区(L’ Ecuyer and Jiang, 2010),并分别观测大气的云物理结构、温湿的垂直廓线,水汽、气溶胶和臭氧等痕量气体的时空分布(Stephens et al., 2002)。CloudSat 和CALІPSO 搭载的云雷达和激光雷达与TRMM 和GPM 搭载的测雨雷达相比有更短的波长,可以更好地识别云滴粒子和深对流云上部尺寸较小的冰晶粒子,对于深对流的上冲云顶和云砧的细微结构有更准确的分辨能力(Stephens et al., 2008)。CloudSat/CALІPSO 与Aqua、Aura 的结合,使深对流的云观测与大气环境的卫星探测融为一个整体,为研究深对流向平流层的物质输送作用,以及深对流与周围环境的夹卷和溢出过程提供了一个有效的观测手段(Savtchenko et al., 2008; Chen et al., 2019)。
除了星载雷达观测以外,一些空基的飞行试验也为理解深对流的物理细节提供了重要帮助。例如,1996 年6~7 月在美国科罗拉多开展的对流层—平流层试验和深对流领域项目(Dye et al., 2000),以及在2005~2006 年期间连续开展的三次观测试验:2005 年1~2 月在巴西阿纳萨图巴的热带对流、卷 云 和 氮 氧 化 物 试 验(Konopka et al., 2007),2005 年11~12 月在澳大利亚达尔文的上对流层—下平流层与平流层气候联系的热带试验(Vaughan et al., 2008),以及2006 年8 月在非洲布基纳法索开展的非洲季风综合分析试验(Cairo et al., 2010)。这些试验通过大量使用飞机进行绕云和穿云飞行,对深对流云内的冰水粒子和痕量气体分布以及温湿结构都进行了更为准确的观测。
由于深对流对物质的输送作用,一些痕量气体的浓度变化也被用作深对流活动的示踪剂。例如:Dessler(2002)使用臭氧和CO 量化地计算了深对流的显著溢出能够发生在高达380 K(约17 km)的高度。Hanisco et al.(2007)通过观测 水汽和HDO 在平流层的变化认为热带外的深对流对平流层的水汽有显著的影响。CO、HCN 和SO2等污染物在平流层的浓度变化也被认为与深对流活动有密不可分的关系(Park et al., 2008; 孙一和陈权亮, 2017)。
3.2 基于卫星观测的深对流识别方法
根据卫星搭载的仪器不同,深对流的识别方法主要分为基于亮温和基于反射率因子两种。由于篇幅有限,本文仅对这两类方法延伸出来的部分研究进行讨论。
在基于亮温的识别方法中,11 μm 通道的亮温更为普遍的用来指示深对流。在11 μm 通道,基于不同的研究目的,深对流的最低云顶亮温通常被要求低于210~245 K(Houze, 1989; Sherwood, 2002;Liu et al., 2007)。在筛选出足够高度的云后,MODІS反演的光学厚度产品则被用来排除那些高度较高,但是厚度较薄的卷云或云砧(Yuan and Li, 2010)。除了一个固定的亮温阈值被用来判断云顶高度以外,Rossow and Pearl(2007)认为11 μm 通道的亮温如果比对流层最冷点温度低就可以表示为穿透性对流。Devasthale and Fueglistaler(2010)则通过判断AVHRR 探测的云顶亮温是否低于AІRS 探测的200 hPa、150 hPa 和100 hPa 等压面的环境温度来判断是否为深对流。多通道亮温数据的结合也可以用来识别深对流,Hong et al.(2005)利用深对流云顶在AMSU-B 三种水汽通道上的散射差异,定义了识别热带深对流的方法。Setvák et al.(2008)讨论了深对流在Meteosat 静止卫星6.2 μm 和10.8 μm通道的辐射亮温差异,并认为正的亮温差异在深对流发展阶段的增加,是由于深对流将水汽从上对流层向下平流层输送所致。
基于反射率因子的识别方法与基于亮温的识别方法相比,不仅关注了云顶的高度和云的厚度,还关注了云内降水粒子和云滴粒子在深对流内的垂直结构与分布。Liu and Zipser(2005)最早定义了TRMM 卫星识别深对流的方法,在Nesbitt et al.(2000)发展的降水特征(PFs)数据集基础上,如果PF 内20 dBZ最大回波顶高度超过14 km 则被认为达到了深对流的标准(Alcala and Dessler,2002)。基于此方法,大量的研究使用TRMM 观测数据,从频率分布、垂直结构、日际变化等诸多方面,分析了深对流在热带和副热带的活动特征。后来,很多学者根据不同的研究目的还对Liu and Zipser(2005)提出的方法做出了进一步的扩展(Zipser et al., 2006; Houze et al., 2007; Liu et al.,2007; Romatschke et al., 2010; 刘 鹏 等, 2012; Xu,2013; Qie et al., 2014)。由于随后的GPM 卫星同样搭载了Ku 波段雷达,因此这一方法被沿用在中高纬的深对流识别上(Liu and Liu, 2016; Gao et al.,2019)。使用CloudSat 来识别深对流的研究总体也采用了类似的方法,同样是通过判断特定回波值的最大回波高度和回波面积等方式来对深对流系统和深对流核进行区分(Chung et al., 2008; Sassen et al., 2009; Іwasaki et al., 2010; Luo et al., 2011; Bedka et al., 2012; Іwasaki et al., 2012)。
由于极轨卫星对同一地点观测的时间分辨率和深对流的发生频率都比较低,因此极轨卫星只能偶尔观测到一次深对流的剖面,无法观测深对流云演变的整个生命周期。反射率因子和云顶亮温的结合,则为分析深对流云的生命周期提供了一种有效的途径。Luo et al.(2008)结合CloudSat 和MODІS 将深对流根据云顶高度和温度分类为三种类型,讨论了深对流在不同生命阶段的垂直结构特征。Takahashi and Luo(2014)将CloudSat 与静止卫星反演的ІSCCP-CT 数据集相结合,定义了深对流的整个生命周期,发现强的穿透性对流主要出现在深对流的初期增长阶段。
3.3 深对流在青藏高原的观测限制
卫星资料的丰富为深入研究深对流的时空特征提供了基础,特别是对于人迹罕至的高原、沙漠和海洋地区,卫星观测目前已成为研究深对流最主要的手段。但是这些卫星反演产品在青藏高原地区仍然需要地面观测的进一步验证。例如,Fu and Liu(2007)发现了TRMM 反演算法中对青藏高原对流云和层云降水的明显误判,Gao et al.(2019)在GPM 的反演结果中也同样发现了这一问题。因此,对于卫星产品在高原地区的准确性仍然存在疑问。
搭载气象探测仪器的飞机对深对流进行穿云和绕云飞行,对于获取深对流云内温湿廓线和滴谱分布的准确数据是一个非常有效的手段,但是由于其高昂的观测成本,这种观测试验比较匮乏。目前,正在进行的第三次青藏高原大气科学试验(TІPEX-Ⅲ)将通过地面、飞机和卫星对青藏高原的地表、行星边界层、对流层和下平流层开展为期8~10 年的联合观测。这一观测试验将有助于补充和完善青藏高原稀缺的观测资料,也有助于提高对青藏高原深对流、对流层—平流层物质交换以及青藏高原对全球气候变化影响的理解和认识(Zhao et al., 2018)。
4 青藏高原深对流向平流层物质输送的物理过程
4.1 穿透性对流
在关于深对流如何向平流层进行物质输送的研究中,首先被注意到的是深对流直接穿透局地对流层顶,影响平流层大气成分的现象(Alcala and Dessler, 2002; Gettelman and de F. Forster, 2002)。Dessler(2002)指出深对流多达60%以上的溢出质量能够穿透380 K 的等熵面。Dessler and Sherwood(2004)使用局地观测和模式数据发现,穿透性对流对平流层的注入可以发生在至少390 K等位温面的高度。Chaboureau et al.(2007)使用一种非静力平衡的三维模式和卫星观测数据证明了穿透性对流的存在,深对流输送的冰相粒子能够存在于局地对流层顶以上2 km 处。除了直接穿透对流层顶的上冲云顶,Wang(2003)认为深对流云顶附近在重力波破碎的作用下会出现一种快速向上发展的跳跃性卷云,水汽也能通过这种羽状的卷云注入平流层。Sang et al.(2018)通过大涡模拟也发现重力波的破碎和冰晶的升华是穿透性对流加湿平流层的主要原因。
在 青 藏 高 原 地 区,Fu et al.(2006b)使 用TRMM 卫星观测发现青藏高原上存在高耸的对流塔,这种对流塔相比周边地区有更为孤立的雨区。Houze et al.(2007)同样使用TRMM 卫星观测在青藏高原的南缘发现了回波顶高度可以超过17 km的深对流。Long et al.(2016)发现青藏高原东侧深对流的云顶高度超过16 km,并且显著改变了UTLS 区域的水汽含量。Qie et al.(2014)统计了长达14 年的TRMM 卫星观测数据,统计结果表明约9%的深对流能超过18 km 高度。借助于GPM卫星对青藏高原更广的探测范围,Gao et al.(2019)发现青藏高原上云顶高度超过17 km 的穿透性对流主要分布在青藏高原的东侧和南坡。
4.2 对流层顶过渡层与青藏高原深对流的主要溢出高度
上述研究表明深对流能够穿透对流层顶,并影响平流层的大气成分,但是深对流能够直接穿透对流层顶的比例仍然是十分低的。Gettelman et al.(2002)发现穿透热带对流层顶的深对流,仅占对流比例的0.5%。虽然单一的穿透性对流事件也可能向平流层注入大量水汽(Chemel et al., 2009),但是这种直接的注入输送对于全球尺度的平流层影响可能是微乎其微的(Highwood and Hoskins,1998; Folkins et al., 1999; Corti et al., 2008)。深对流直接向平流层注入水汽和污染物更多的以间接的方式,先通过深对流抬升到一个对流层顶过渡层(TTL),然后再向上输送。对流层顶过渡层被认为是一个具有一定厚度的气层,对对流层物质进入平流层有着重要的影响(Sherwood and Dessler,2000, 2003)。
在Fueglistaler et al.(2009)对TTL 的定义中,深对流被认为主要在净辐射层的高度附近出流。净辐射层之上的非绝热加热对于水汽的抬升是一个比较缓慢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对流层上部的温度非常低,深对流输送的水汽可能在还没有被抬升进入平流层前,就会直接凝华为冰晶粒子降落回对流层,从而产生脱水作用(Mote et al., 1996)。因此,一个较高的溢出高度更有利于深对流向平流层的水汽输送。
Gettelman et al.(2002)认为热带深对流的主要 出 流 高 度 大 约 在12 km。Folkins and Martin(2005)指出热带的深对流溢出层高度在10~17 km范围,并通过温湿的垂直廓线诊断出最大的深对流辐散层高度在12.5 km 左右。Park et al.(2008)发现南亚反气旋内污染物浓度的最大值处于13~15 km范围内,因此推测这一高度可能是亚洲季风区—青藏高原深对流的主要出流高度。这一高度范围明显高于热带地区深对流的出流高度。由于深对流通过夹卷、溢出和湍流混合等复杂的方式与环境空气相互作用,每一个深对流的主要出流高度可能都是不尽相同的。因此,简单通过测算大气成分、环境场温湿廓线和净辐散层高度的方式来代表深对流的出流高度可能是不足够准确的。Takahashi and Luo(2012)提出了一种用云砧高度来直接测量深对流出流高度的方法,该方法使用CloudSat 的卫星观测数据,将云砧的上下边界定义为深对流的出流高度范围,将云砧内的最大回波高度定义为最大质量出流高度。Chen et al.(2019)采用这一方法分析了青藏高原地区的深对流出流,发现青藏高原及其南坡深对流的主要出流高度分别为12.9 km 和13.3 km。深对流更高的出流高度意味着青藏高原对平流层水汽可能有着更重要的影响。
5 青藏高原、亚洲季风区和热带海洋地区的深对流特征差异及其对平流层水汽输送的影响
5.1 深对流的活动特征和云微物理结构差异
从TRMM 和GPM 卫星的全球观测来看,深对流主要分布在亚洲季风区、西太平洋暖池、非洲的西海岸、亚马孙流域和北美的大平原地区,并且又以亚洲季风区—西太平洋地区的强度最强、频率最高(Zipser et al., 2006; Liu and Liu, 2016)。除了频率分布的差异,深对流的日际循环、垂直结构、水平尺度和微物理结构也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这种差异又会影响深对流对平流层的物质输送。
在日际循环上,深对流在陆地上的日际变化要明显大于海洋地区,并且主要存在两个峰值。一个峰值出现在午后,可能与午后增加的局地非绝热加热有关,另一个峰值出现在午夜,夜间深对流出现的原因相对更为复杂,目前还没有统一的认识(Hong et al., 2008)。青藏高原地区深对流的日际循环主要呈现为单峰型,最大的峰值出现在午后到傍晚时段(Gao et al., 2019)。
青藏高原的深对流在对流强度和水平尺度上要明显弱于南亚、东亚和热带海洋地区。Devasthale and Fueglistaler(2010)使用云顶亮温数据对比了深对流在孟湾、印度和青藏高原地区的气候态特征,发现印度地区深对流的频率受季风影响较大,青藏高原地区深对流的频率受季风影响较小。Luo et al.(2011)使用CloudSat 和CALІPSO 观测数据对比了青藏高原和南亚季风区的深对流,结果发现青藏高原地区的深对流云顶更为紧密,回波顶高度相对较低,对流的水平范围也较小。Qie et al.(2014)使用TRMM 观测数据对比青藏高原主体、青藏高原南坡、南亚次大陆和印度洋地区的深对流,发现强的深对流最多在青藏高原南坡,其次为青藏高原主体,再次为南亚和海洋。Xu(2013)同样使用TRMM 观测数据对比了青藏高原、青藏高原东部的山地、四川盆地、长江中下游平原和海洋地区的深对流,结果发现长江中下游地区和四川盆地深对流的混合相位降水占比更高,青藏高原地区的混合相位层比其他区域都要更小,同时也指出深对流系统的水平尺度在青藏高原地区是最小的,最大的平均水平尺度出现在海洋地区。夏静雯和傅云飞(2016)使用TRMM 观测数据和全球探空数据集ІGRA 对比东亚和南亚的对流降水发现东亚季风区的降水强度相比南亚更大,对流的回波顶高度也要比南亚地区高约1 km。
尽管上述的研究表明青藏高原地区的深对流在频率、强度和水平尺度上与周边区域相比都较弱,但是青藏高原地区的深对流仍然有可能向平流层输送更多的水汽。从深对流云顶溢出的较大半径的冰相粒子,可能在短时间内就会从TTL 内坠落,但是小的粒子可能下落的很缓慢,能够在TTL 内存留较长的时间,然后在TTL 内蒸发或者升华,从而进一步向平流层输送水汽(Alcala and Dessler,2002; Sherwood and Dessler, 2003)。因此,深对流云顶粒子的滴谱分布可能对最终的水汽输送过程有着重要的影响。Yuan and Li(2010)发现高海拔地区的深对流在云顶区域的平均粒子尺寸更小。可以进一步猜测,青藏高原地区的深对流云顶可能有最小的云滴粒子半径。最近,Chen et al.(2020b)通过GPM 卫星观测发现了青藏高原和青藏高原东侧平原地区的对流云滴谱分布存在着明显差异,但目前关于青藏高原深对流滴谱分布的研究仍较缺乏。
5.2 环境背景场差异对深对流物质输送过程的影响
UTLS 的温湿结构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深对流是对平流层产生加湿作用,还是脱水作用。对流层顶最冷点的温度决定了水汽进入平流层的多少(Mote et al., 1996),如果最冷点的温度更低,那么意味着能进入平流层的水汽可能是更少的,极低的温度甚至可能使对流层顶饱和的水汽混合比低于平流层原本的水汽混合比,从而对平流层产生脱水作用(Danielsen, 1982, 1993)。Fu et al.(2006a)指出青藏高原相比南亚季风区有一个更暖的对流层顶,水汽更容易通过青藏高原上空的对流层顶进入平流层。Randel et al.(2015)的研究也发现对流层顶的温度控制着北半球季风区平流层的水汽分布。上对流层的环境场相对湿度也强烈地影响着深对流的溢出过程,如果环境场处于相对较干的未饱和状态,那么溢出的冰晶粒子倾向于升华产生加湿作用,如果环境处于过饱和状态时,冰晶粒子倾向于吸附环境中的水汽凝结后降落,反而产生脱水作用(Grosvenor et al., 2007; Jensen et al., 2007; Hassim and Lane, 2010)。Luo et al.(2011)指出青藏高原的深对流相比亚洲季风区的深对流处在一个更干的环境中,Chen et al.(2019)也指出青藏高原南坡的环境场冰水含量要明显高于青藏高原主体,但是青藏高原主体的深对流对UTLS 的加湿作用却明显更大。因此,尽管青藏高原深对流在频率、强度、垂直结构和水平尺度的统计中,均弱于南亚和东亚季风区的深对流,但是对平流层的水汽输送影响可能是更大的。
6 小结与展望
通过卫星观测发现青藏高原是对流层向平流层物质输送的重要窗口,青藏高原深对流在物质传输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借助于卫星观测和数值模拟的发展,青藏高原深对流研究在近年来得到了一些重要的结果,但是仍有许多科学问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
(1)卫星观测发现在青藏高原和亚洲季风区上空的UTLS 区域存在水汽、气溶胶的极大值区和臭氧的极小值区。数值模拟的结果也表明整个亚洲季风区为平流层贡献了大量的水汽和气溶胶,但是来自深对流的输送贡献还有待研究。除了物质输送作用,深对流还能明显改变对流加热廓线,制造大量的高空卷云,其进一步产生的气候效应也仍然不清楚。
(2)21 世纪以来,卫星的发展为观测和研究深对流提供了重要的帮助,但是卫星的反演产品在青藏高原地区还存在较多的不确定性。因此,发展适用于青藏高原的卫星反演算法和反演产品,增加地面和卫星观测的结果对比对于研究青藏高原深对流具有重要意义。
(3)目前的研究表明,一些罕见的穿透性对流可以直接向平流层注入水汽和污染物,大多数水汽和污染物则通过深对流快速抬升到TTL,然后在大尺度热力和动力作用下进入平流层。尽管可以使用轨迹追踪模式来定量化的分析物质传输结果,但这些结果仍然缺乏足够的观测验证。
(4)青藏高原深对流与亚洲季风区、热带地区的深对流相比,水平尺度和对流强度都要更弱,但是来自数值模拟的结果和痕量气体的观测却发现青藏高原深对流有更强的物质输送作用。进一步的研究发现环境场差异、云微物理结构等影响因子对物质输送过程有重要影响,但是不同因子对输送过程的贡献大小仍然不清楚。随着人类活动的加剧,更多的气溶胶排放对于青藏高原深对流在物质输送过程中的影响也值得进一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