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念群:真正要了解中国历史的走势,要更重视那些看起来比较“虚”的部分
徐鹏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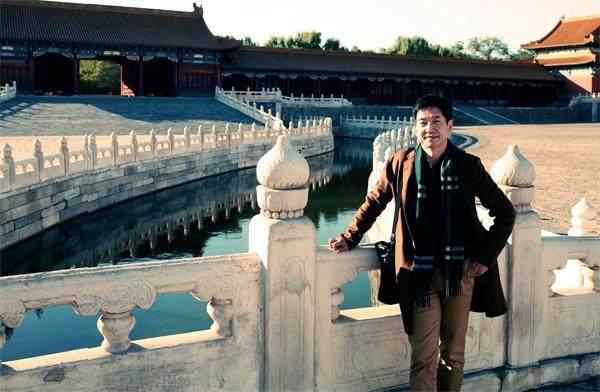
楊念群。图/受访者提供
在一些学界同仁的称呼中,杨念群有时会被唤作“杨公子“。
这一雅号源于其名望显赫的家世。他的父亲是石化领域的知名专家,母亲是北大地理学教授;祖父杨公庶是留德的化学博士,曾跟随张治中参与过国共和谈,祖母乐曼雍是同仁堂乐氏家族的三小姐;外公吴鲁强是麻省理工的化学博士,外婆梁思庄是著名图书馆学家。倘若把家族的范围再扩大一点,写出《创业史》的柳青是他的大姑丈,钱锺书和杨绛的外甥女是他的大伯母,梁思成、林徽因是他的舅公舅婆……当然族谱中最闪耀的两个名字,无疑还是他的曾祖杨度和曾外祖梁启超。
其实,作为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的杨念群自己从没在意过这件事。他反而有意与先人拉开距离。不过,家族基因有时还是会在他身上流露出些许痕迹。他自幼不缺书读,不仅祖父有藏书,周围的邻居都是大学者,每家的书房都是他的阅览室。在漫无边际的阅读中,他不知不觉地培养起了对文史的嗜好。而在治学路径的自我构建上,杨念群的“野心”更是颇有杨、梁的气魄。他想展现出一个全景式的中国历史,贯通性地理解这片土地和这个民族的前世今生、悲喜命运。
以往二十年,大家都在谈论西方社会科学方法对中国研究的支配性作用,以及社会科学如何本土化的问题。但我认为,社会科学方法既然来自西方,就很难在中国本土化。如果要摆脱学界“言必称希腊”的困境,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在中国历史内部重新发现一些传统遗留下来的概念,加以重新解读,借此机会激活其中所隐藏的价值,才能正确评估这些概念在当代的意义。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需要反思近些年“概念史”兴起的意义。概念史方法给我的启发是,能不能在中国经典文本中发掘一些本来习以为常的概念,把它放在历史脉络里重新解释。比如“大一统”,一般人可能仅仅把它的内涵单纯理解为疆域广大、人口众多,但实际上这是传统政治表述体系中最关键的概念,与许多其他概念密切相关,不能割裂开来单独理解。在传统语境中,“大一统”是沿着政权合法性这个叙述脉络一路延伸下来、被反复定义的,集中讨论的是古代王朝何以能够维持下去这个核心问题,同时又涉及一个王朝政治体制如何整体运转的问题,蕴藏着更深层次的复杂历史观念,绝非维系疆域大小这么简单。
中国古代强调历史处于不断循环之中,受近代西方思想影响,我们总是批判这种循环论是一种保守落后的思维方式,却没有认真反思为什么中国人会这样思考问题。其实古人讲循环,不是简单地主张回到过去,而是希望以历史经验为根据,寻找突破现实困境的路径。
另外,这本书还出于对史学界研究现状的思考。1990年代以来,史学界掀起了一股追求“眼光向下”的热潮,突出底层民众生活与价值观的重要性。社会史倡导下的乡村基层研究迅速成为主流,原本在历史研究版图中占优势地位的政治史反而被边缘化了。
因此,我更关心上层政治思维的形成过程。我试图重建一种“眼光向上”的视角。梁启超当年倡导“新史学”,号召我们要把眼光聚集在民众身上。我觉得后来的研究者对任公这段话有一些误解,好像完全从民众的视角出发去观察历史就足够了。实际情况可能恰恰相反,因为历史上本身就没有多少“民众”的声音被记录下来,甚至“民众”作为一个历史研究对象的合理性,我觉得都值得怀疑。因为传统中国的民众是在整体王权体系下被定位的,自宋明以来,民众就被要求挂靠在“家庭—国家—天下”这个脉络里确立自己的身份,一旦脱离这个脉络,“民众”的角色就变得完全没有意义。历史记载里的“民众”往往是受各种政治力量控制和支配的一个追随者,“民众”具有“主体性”是近代西方思想启蒙的结果。所以我们观察古代中国,不能仅仅从民众的角度去理解历史的发展走向和性质,而是应该回到上层制度和执行者的层面去理解中国政治的运作逻辑。
当然可归于“何为中国”这个话题范围之内,但在具体内容上并不限于对“中国”问题的讨论,而是想尽量有所区别。
我一直认为,“中国”这个概念可以作为一个重要的问题出发点。但历史上“中国”内涵不断发生变动,不太容易清晰地加以界定。我们现在把它当作一个讨论对象,常常是建立在“中国”已经成为现代民族国家的基础之上的,然后再从此往前推导,好像古人也在热衷于频繁使用这个概念。其实对“中国”的使用,历朝历代均不相同。
比如宋明士人使用“中国”的频率相对高一些,因为有利于和辽金元这些非华夏族群做对比,彰显汉人文化的优势。但清朝相对就不太喜欢用。
近些年学界也兴起了“从周边看中国”的热潮,主张从邻近国家和东亚视角描述定位“中国”。这个角度确实有它的价值和贡献,但我感到困惑的是,只从外部看“中国”,并不意味着能取代对中国内部核心历史的认识。因此,我还是主张从内部视角去观察“中国”观念的演变,但不应局限于对“中国”本身的理解,而是应该把“中国”和其他概念关联起来进行考察。
第一,中国历史传统自古就特别强调礼仪秩序的核心规范作用,每个人都是这个完整秩序的组成部分,“个人”必须融入一个统一的组织框架里才能受到保护,获得某种安全感,“个人”价值只有源自集体行为的逻辑才能展现出价值,这就为“大一统”观念提供了一个基本制度前提。第二,中国古代王朝通过对疆域的扩张和维护,建立起了对世界的想象。“大一统”就是为这个想象如何落地为实践过程而设计的一套观念,包括理论与行动两个层次的表述和实实在在的操作程序。当然,除了“大一统”外,其他概念可能也在发挥着各自的作用。比如“天下”也是被频繁使用的一个概念,但它更像是一个理想设计方案,或者接近一个哲学理念,至于到底怎么落实,始终众说纷纭,语焉不详。第三,古代“大一统”观从形式上具有开疆拓土的征服气象,清朝的“大一统”观及其实践又创造出了“多民族共同体”的新面相,完全区别于以往王朝对民族关系的认识。当近代中国面临外来侵略时,“大一统”观很容易与现代民族主义结合在一起,成为抵御外侮的思想来源和动力。
我理解你说的“母题”的意思是,當观察某个对象时始终会指向一个中心目标。现在受社会科学方法影响比较多的研究者,我觉得心目中反而缺乏一个原来传统意义上的“母题”。因为现代社会科学崇尚“专门化”训练,特别讲究“规范性”,对历史的观察都带有专题研究的倾向。这样做的好处是对历史某个特殊的横剖面挖掘得更深,对历史认知的点和面覆盖得较为广泛。缺点是纵向的贯通联系不够,对历史的整体性认识反而模糊了。
如果说有什么“母题”的话,那就是我更关注中国历史上政治运行的特征,总是尝试把各种历史现象放到一个政治脉络里面去思考。说得更直接一点,我始终关心的是中国人是怎么成为“政治动物”的。
中国人自古就好讲政治,甚至史书都是为了表达某种政治意图而撰写,一切社会或文化现象也都围绕政治过程展开。即使我们做社会史文化史研究,也要考虑其背后的政治目的到底是什么,而不能把它们切割开来单独观察。目前的历史研究总是人为地划分出“政治史”“经济史”“社会史”“文化史”等类别,明显是受到社会科学专门化训练的影响,其实古人不是这么观察历史的,中国古人基本上把历史现象一律当作一种广义的“政治”行为。至少“政治”作为“母题”,具有聚拢其他“主题”的典范作用。表现方式也是有“实”有“虚”,“实”的方面指的是那些具体采取的行动,“虚”的方面是一些隐喻式的表达。
真正要了解中国历史的走势,不能把什么都看得太实,应该发挥想象力,更重视那些看起来比较“虚”的部分。从某种角度说,历史是人的主观性表现,如果都做成考据那种太实的东西,也许只能揭示历史的表层现象,却展现不出深层结构。研究历史可以运用不同方法,从各个角度多向展开,但要想确定一个“母题”,就必须适当拉长时间,目光不能总是盯着一个点或一个时期,而是要寻找不同时段的历史如何连贯创造出的一个或数个主题,然后提供一个合理解释。对历史贯通性的理解是把握研究“母题”的一个基本要求。
我的个人经历很简单,从小出生长大的活动范围基本上就局限在中关村一带,从本科一直念到博士,然后当老师到现在三十多年了,职业生涯没出过大学校门,缺乏1950年代出生的那批学者所拥有的惊心动魄引以为豪的复杂经验。
我觉得个人阅历对治学路径是有影响的,它会塑造你的人生观和治学风格,但又不是决定性的。人生经验某种意义上是双刃剑,有些人凭借丰富和痛苦的阅历增加了治学的想象力,另一些人却受此羁绊变得城府很深、精于世故,恰恰限制了激情和想象力的发挥。尤其是以文史为职业的学者确实容易被打上个人经验的烙印,比如有些作家就太依赖自己积攒的生活体验去从事写作,而真正伟大的作品恰恰是超越个人阅历的产物。
我基本上是一个书斋里成长的学者,所以就需要更多地跃出有限经历的限制。如何结合自身经验,充分发挥历史想象力始终是我面临的最重要课题。重新回到“政治史”研究就是基于个人经历做出的选择。
我们这代学者没有“上山下乡”的复杂阅历,没有上一代学者反思当代历史的经验资本,但是基本上全程经历了“文革”后期到改革开放这段历史时期,尽管生活上没有出现多大的波澜,但毕竟是历史大变局过程的亲历者。我们那时候一度特别狂妄,觉得只要通过个人努力就足以改变世界。我们这代人的身上还有一种以天下为己任的浪漫幻觉和历史担当意识。因为我们那个时代确实觉得可以改变世界,在行动上也保持着某种冲动和野性。比我们晚一代的年轻人吸收现代社会科学知识显然比我们更加规范、视野更加开阔、方法也更加严谨,治学容易选择更加专门化的路径。
中国知识分子研究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常常把事实跟理想混淆起来,很容易流于“情怀党”式的表态。比如,中国历史上的确出现过士人阶层“以道抗势”的局面,我觉得这完全是一个被理想化的个别情况。王安石与宋神宗的相处也许比较接近这个状态,可那是一个非常短暂的时期,具有极大偶然性。这种偶然性特别容易受某个历史人物性格和情绪的支配,根本无法转化为制度化的选择。历史上帝王与士人的相处更多是一种合谋关系,那么“道统”在大多数情况下一定服从于政统的控制。也许在“政统”的安排之下有一些缝隙和空间可以发挥,但总体来说对抗能力非常有限。
我们理想上可能期待着中国历史上始终保留着一个以“道统”制衡“政统”的思想传统,但是我个人认为根本不存在这个东西。我这里采取的是相对平实地看待历史现象的态度,与个人立场无关,历史的残酷性不可能单靠抒发情怀和理想就能消解。我当然希望能够从历史上更多寻找到注重个人尊严和自由的系统记录,但作为研究者,我们的任务是要把一个比较接近事实的真相告诉大家,据此更便于了解我们自身的生存状态和处境。这就意味着一位历史研究者的内心必须要承担理想与现实撕裂的痛苦。
我们首先要培养一种历史感,辨析历史上哪些因素是基因里面的东西,那些属于能够变更的制度安排,能改造就改造,能挣脱就挣脱。至于挣脱到什么样的程度,有时确实受时势的制约太大。首先让生活变得更加清醒、更加理性,培养自己兼容并包的气质和多元性的选择态度。我们改变不了历史,但可以改变个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