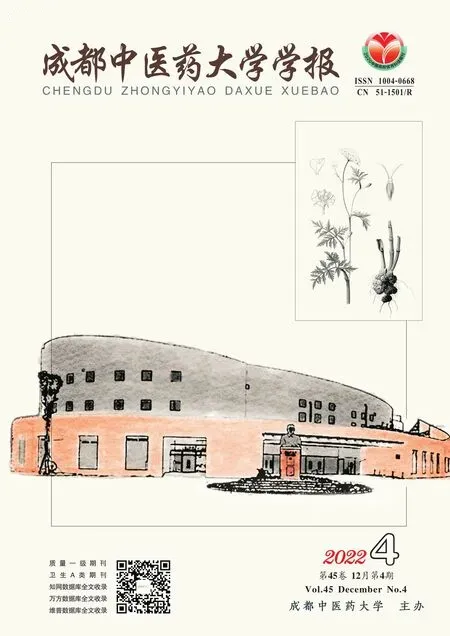谢文教授辨治冠状动脉慢血流心绞痛经验总结
聂谦,葛文君,唐小茗,武子键,黄爱玲,谢文▲
(1.成都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心血管科,四川 成都 610072;2.自贡市中医医院 心内科,四川 自贡 643010;3.郫都区中医医院 心内科,四川 成都 611730)
谢文教授,四川省名中医,四川省中医药管理局学术与技术带头人,成都中医药大学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成都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心血管科主任医师,从事心血管疾病临床、教学及科研工作30余年,擅长运用中西结合的方法以及中医辨证论治的思路,治疗各种类型的心绞痛、心力衰竭以及各种心脏疾病,重视心脏康复治疗,具有丰富的临床经验。
冠状动脉慢血流(Coronary Slow Flow,CSF)所引发的心绞痛,目前临床将其归于冠状动脉微血管障碍类疾病,属于非阻塞性冠状动脉疾的范畴[1]。其发生还可能与炎症反应、内皮功能受损、缺血再灌注损伤、冠状动脉痉挛等密切相关[2]。CSF的诊断标准为:冠状动脉造影未发现冠脉的狭窄,但造影剂充盈时间(TIMI帧数计数)明显延长[3]。现有研究发现,CSF患者核素显像出现心肌灌注缺损,心肌声学造影存在血流速度减慢、心肌灌注延迟,给予常规抗心绞痛药物症状不易缓解,主要心血管不良事件(MACCE)显著增加[4]。西医的代表药物为尼可地尔,但此药可能发生黏膜溃疡的不良反应[5]。应用基于辨证论治的个体化治疗CSF,取得较满意的疗效[6]。笔者长期师从于谢文教授学习应用中医中药治疗心血管疾病,现将谢文教授对于CSF胸痹辨治经验介绍如下。
1 引经据典,参悟CSF心绞痛病因病机
谢文教授查阅相关的古今文献后,指出在中医学中尚无CSF心绞痛的病名,但与之类似的病症,在古代的医籍中已有记载,其中尤以张仲景的《金匮要略》对类似病机的阐述最为详尽,为现今对CSF的辨治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素问·脏气法时论》中有记载:“心病者,胸中痛,胁支满,胁下痛,膺背肩甲间痛,两臂内痛。”记载了本病相类的症状。隋朝巢元方在《诸病源候论》中记载 :“胸痹之候,胸中愊愊如满。”《素问·举痛论》指出:“经脉流行不止……客于脉中则气不通,故卒然而痛”,“脉泣则血虚,血虚则痛”,指出了痛证与经脉不通、经脉不荣的关联。而明代李中梓在《医宗必读·心腹诸痛》中写道“近世治痛有以诸痛属实……”首次明确提出“痛则不通、通则不痛”的理念。而在传统医学中,“通”除了指气血运行的通畅,亦包括气血运行脉络的通畅,所以“通”也代表经络通畅。同样《黄帝内经·灵枢》记载“经脉者,所以能决死生、处百病、调虚实,不可不通”,指出经脉的通畅与否,是诊治百病、调理虚实、运行气血、决定生死的关键。
基于对中医经典理论的理解和引申,谢文教授思考后指出:根据CSF所引发的临床主要症状,当属广义的“胸痹心痛”的范畴[7]。《金匮要略》所记载的“阳微阴弦”,阐述了胸痹的病因病机,“阳微”即是指上焦的阳气羸弱、阳气虚衰或阳气不足,“阴弦”则是指下焦湿气沉着、阴寒过甚,或上焦阳虚,则必有心悸动,温煦不力,心不主血,更加阴寒凝滞血脉,定有瘀血产生[8];而现今CSF患者常“心阳亏虚,心气不足”,以“寒凝、痰饮、血瘀”为有形之实邪;心气亏虚,痰浊、血瘀闭阻,导致胸阳不展,下焦阴寒炽盛,上焦阳气虚微,本虚而标实,说明CSF病机关键时:胸中邪气痹阻经脉,血脉经络运行不利,最终发为本病。谢文教授认为,CSF心绞痛的发病机制与“阳微阴弦”理论不谋而合,其本质为本虚标实之证,首当从气血进行辨治。在临床实践中,谢文教授也观察到CSF患者多有吸烟、饮酒史,且合并高血压病、房颤、高脂血症等综合危险因素,主要临床表现包括乏力、气短、胸闷、胸痛等;此外,CSF导致的胸痹心痛的诸多症状,与劳力性心绞痛所导致的胸痹心痛具有明显的区别:CSF患者的胸痹心痛具有“三不明显”的特点:劳力诱发不明显,休息后缓解不明显,服药后疗效亦不明显。因此,谢文教授将CSF引发的心绞痛称为“慢血流胸痹(CSF胸痹)”。
2 审证求因,倡“气虚血瘀”为CSF心绞痛核心病机
对于CSF胸痹,谢文教授以“阳微阴弦”为理论基础,进一步阐述了CSF心绞痛的核心病机为本虚标实,气虚血瘀而阻滞心脉,CSF患者舌象主要为舌体偏胖,颜色紫黯,舌边可见齿痕,苔白腻,而脉滑者、脉沉细者均可得见。目前发现,CSF胸痹患者的病位在心,涉及脾、肾;中医实性证素主要包括瘀血、痰浊(饮)、气滞、热蕴;虚性证素主要包括气虚、阴虚、阳虚;其内在关联为气虚则运血无力故血瘀,血瘀进一步阻滞气机可兼气滞,气虚严重者则为阳虚,阳虚失温可见寒凝等证;因此,偏痰热患者可见脉滑,而偏寒湿者可见脉沉细;除此之外,阴虚易生内热,“血受热则煎熬血块”,因此血液煎灼,更伤津液,加重血瘀,可造成阴虚之象[9-11]。
谢文教授通过上述思考,并结合临床实践后,对CSF胸痹患者的核心病机进行了总结:“虚”是心、脾、肾三者虚衰,最终导致的心失濡养,故“不荣而痛”;“实”则是瘀血、痰饮等邪气,痹阻于心脉,使心之络脉痹阻,故“不通而痛”;虚实夹杂,病邪壅滞,最终发为胸痹心痛。其中,在所有的实证淫邪中,以“痰、瘀”二邪最为常见。谢文教授进一步指出,心脉的生理特性以血脉通常为本,健壮的心气推动血液正常循经运行;但对于CSF胸痹患者而言,心脉失其通畅与内因的“虚”和外界的“实”密切相关:在心气不足的基础上,气血运行失调,血脉通行不畅,则出现气虚血瘀等证候,心失濡养而发痹痛;加之四川盆地其独特的地理特征,自然环境中潮气重而湿度大,“天气之印象,反应于人体”,四川地区湿气重浊,湿性黏滞,湿邪日久缠绵遏阻气机升降,更易使胸阳痹阻,心气受遏,加重瘀血阻滞,病邪纠缠于脉络,血流推动不畅且运行更加阻滞,因此较易发生CSF胸痹。
谢文教授发现就,CSF胸痹的辨证而言,其证型较为繁多,病机虚实夹杂,辨证难度较大,需要通过证症合一,仔细辨别,方能准确辨明病机,从而指导治疗。鉴于此难度,谢文教授对CSF胸痹的一般辨证规律做了尝试性的总结:在虚证中,本病临证多表现为气虚、阳虚以及阴虚;实证中,可见到气滞证、痰浊阻滞证、血瘀证及三种证型夹杂的气滞痰阻血瘀证;但是在虚实夹杂的证型中,目前只观察到了气虚血瘀证,兼有痰阻[12],其中气虚血瘀和痰浊痹阻证是较为常见的证型,两者之间通过脉象可以帮助进行鉴别。
3 用“益气活血”法,创“益心通痹”方
《素问·举痛论》有云:“寒气客于脉外则脉寒……故卒然而痛,得炅则痛立止。”炅即热也,即选用温性、热性的药物或疗法,行气活血以治疗诸般痛证。《灵枢》中记载:“心病者,宜食麦、羊肉、杏、薤。”提出了通过食物来调理和治疗心系病证,其中薤白,其性辛温,具有通畅经脉,散寒导滞的功效。汉代张仲景不仅提出了胸痹的病机,同时在《金匮要略·胸痹心痛短气病脉证并治》中记载“胸痹心中痞……枳实薤白桂枝汤主之;人参汤亦主之”,提出了益气和温通经脉的治法。唐代孙思邈的《备急千金要方》记载,丹参配伍川芎具有活血化瘀,养血止痛的功效,用于治疗胸背腹痛等疾病,提出了“活血养血”的治疗“痛症”的理念。宋代方书中治疗心痛的记载非常丰富,活血化瘀被日益广泛地应用于胸痹心痛地治疗。其中《太平惠民和剂局方》中还记载了黄芪具有补气、生血、生津的作用,用于气血虚衰的治疗上,可使“气血津液生化有源头,气弱血虚诸症自愈”。明代医家进一步拓宽了胸痹的诊疗思路,并肯定了活血化瘀法的作用:王肯堂不仅对胸痹心痛和胃痛做出了鉴别,也推崇将大剂量活血化瘀用于胸痹心痛的治疗,张景岳创八纲辨证用于胸痹心痛诊疗,并肯定了“气血当同分同调”的治疗理念。清朝时期,以王清任的《医林改错》为活血化瘀法奠定了扎实了理论基础;而唐容川的《血证论》认为瘀血留于体内日久就会产生其他变证,为防他变当以“消瘀”为治法;同时,血虚对机体造成的耗损状态不能得到有效纠正,亦可引起其他病症,故当补虚以扶正固本;因此在“治血四法”中,消瘀为第二法,补虚为第四法。
在结合古今医家对胸痹的认识和现今临床对CSF胸痹的观察总结,谢文教授认为“气虚血瘀”是其核心病机,并提出了“益气活血法”为治疗本病的根本大法,传承了“温、散、通、补”的思想。
基于“益气活血法”,谢文教授针对CSF胸痹核心病机对用药组方进行了思考,参考《金匮要略》之“瓜蒌薤白半夏汤”、《证治准绳》之“失笑散”、《医林改错》之“血府逐瘀汤”等古代医家经典方剂及治疗理念,结合科室多年以来治疗胸痹心痛的临床经验,选择“益心通痹汤”对CSF胸痹进行治疗。全方由“黄芪、丹参、川芎、薤白”四药组成[13]。方解如下。
黄芪味甘,性微温;归脾、肺经。具补气固表、利尿、强心、降压、抗菌、改善毛细血管阻力、止汗和类性激素的功效,用于治疗气虚内伤、表虚自汗、浮肿、炎症及高血压等。黄芪乃甘温之品,善补肺脾气。中国最早的《神农本草经》把黄耆列为“上品”,述“黄芪疗疮补虚”;《名医别录》谓本品能“逐五脏间恶血”,用于冠心病胸痹心痛时;同时黄芪补虚益气之功显著,使得气旺则助心行血,发挥活血的功效。《药性歌诀》云:“黄耆入药,为强壮剂,具有益正气,壮脾胃,排脓止痛,活血医危的功效。”
丹参,性苦,微寒;活血祛瘀、凉血消痈之效显著。具有活血祛瘀,通经止痛,清心除烦,凉血消痈之功效。用于胸痹心痛,脘腹胁痛,症瘕积聚,热痹疼痛,心烦不眠等病。《本经逢原》述:“丹参治心腹邪气,肠鸣幽幽如走水等疾,皆瘀血内滞而化为水之候。止烦满益气者,瘀积去而烦满愈,正气复也”。用于胸痹心痛病,达活血化瘀止痛之效。《本草纲目》记录丹参可活血,通心包络。《神农本草经》记载丹参可逐心腹邪气,寒热积聚,破症除瘕,止烦满,并可益气。《名医别录》记载丹参可养血,去心腹痼疾结气,除风邪留热。久服利人。
因此,黄芪与丹参合用,共为君药,起益气活血、化瘀止痛之功效显著。
川芎,性温,味辛;乃“血中之气药”,活血行气之力强,常用于活血行气,祛风止痛,川芎辛温香燥,走而不守,既能行散,上行可达巅顶;又入血分,下行可达血海。活血祛瘀作用广泛,适宜瘀血阻滞各种病症;可治头风头痛、风湿痹痛等症。昔人谓川芎为血中之气药,殆言其寓辛散、解郁、通达、止痛等功能。《日华子本草》谓其:“治一切风,一切气,一切劳损,一切血,补五劳,壮筋骨,调众脉,破症结宿血,养新血……及排脓消瘀血。”可广泛用于血瘀气滞所致的胸、胁、腹诸痛证。
薤白,辛、温、苦之品,归心、肺、胃、大肠经,无毒,具理气、宽胸、通阳、散结的功效,用于胸痹心痛、脘腹痞痛不舒等疾病的治疗。中医长期用于治疗胸闷刺痛、泻痢后重、肺气喘急等疾病。《本草求真》:薤,味辛则散,散则能使在上寒滞立消;味苦则降,降则能使在下寒滞立下;气温则散,散则能使在中寒滞立除;体滑则通,通则能使久痼寒滞立解,阐述了薤白的辛温作用。《内经》记载:“心病宜食薤”,即体现了薤白通阳散结,行气导滞的功效。《金贵要略》中半夏汤记载:瓜蒌、半夏、枳实等配伍可治疗痰阻滞、胸阳不振所到胸痹证。
川芎与薤白合用,共为臣药,增强了行气活血、通阳导滞之效。
益心通痹合剂由黄芪、丹参、川芎、薤白等四味药组成,方中重用黄芪补气益气,养血活血,兼能化痰;丹参活血养血、凉血化瘀;川芎行气活血、祛风止痛;薤白宽胸理气、通阳散结,针对“胸痹”之“阳微阴弦”,使“离照当空,则阴霾自开”,故四药同用,共同发挥益气补虚、活血通脉,兼化痰排浊的功效,更具有补虚和治病两大特点。
此外,现代药理学研究表明,丹参可以增加血液中内源性一氧化氮的浓度,能够有效改善血管的舒缩效应,还可以增加血管内径,改善冠脉微小循环状态[14]。黄芪提取物可明显改善大鼠心肌梗死后的血液流变学指标、胶原纤维构成比例和组织病变。川芎的主要化学成分川芎嗪、香兰素、大黄酚等,可显著拮抗血管收缩作用,还可降低细胞内电位,使细胞兴奋性明显下降,舒张血管平滑肌[15]。薤白对纤维蛋白溶解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同时还能降低血脂、动脉内脂质斑块[16]等。
4 典型案例
患者胡某,女,74岁,于2018-07-10就诊。主诉胸闷胸痛1月余,诊见胸部闷痛,时而如针刺,痛处固定,动则神疲乏力、气短、汗出,心悸、少气懒言,舌质黯,苔薄白,脉弱浮滑。收治入院,冠脉造影诊断为CSF,中医诊断为胸痹心痛病,气虚血瘀证。谢文教授以益气活血为治法,投以方药益心通痹合剂(成都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院内制剂,生产批号:CZJ120011,规格100 mL/瓶),共8剂,1剂/d,30 mL/次,早中晚分三次口服。2018-07-18二诊:患者语气较前清晰、明朗,精神可,诉服药后胸部闷痛明显缓解,劳累后稍感胸闷,无针刺痛发作,余气短、汗出、心悸等症状均消失,舌质红润,苔薄白,脉稍弱。考虑患者气虚血瘀逐症虽显著缓解,再投以原方6剂,1剂/d,30 mL/次,早中晚分三次口服,以巩固疗效。此后随诊患者未再发作胸闷症状。
按语:慢血流本证属虚中夹实,以气虚与血瘀证候同时并见为特点。本例患者因年老体弱,导致脏腑气机衰减,气虚推动无力,血行不畅而瘀滞,心脉瘀阻,故见胸部闷痛,有如针刺切痛处固定等血瘀之表现,而心悸、气短、汗出、神疲乏力、动则尤甚皆为气虚之证,故其辨证为气虚血瘀。曹仁伯在《继志堂医案》中提出:“胸痛彻背,是名胸痹……此痛不唯痰浊,且有瘀血,交阻膈间。”而在现今中医临床上,随着老龄人口的增加,因年老体弱,心气虚衰,推动无力,血脉瘀阻,发为胸痹心痛者日益增多,其病机多为气虚血瘀,且发病后病势缠绵,需在祛邪后加以固本,故二诊时,患者仍感病情缠绵,时有发作,此时再予益心通痹合剂6剂加以固本。本证在老年病中具有重要意义:老年患者多有元气亏虚,脏腑虚衰,而气虚血瘀证较多见于心气不足,运血无力所致;此外,老年人群中气虚和气滞、可与血瘀并存,三者相互影响。因此,益气活血兼以行气祛痰,是根本的对症之法。益心通痹合剂服用更加方便,增加患者依从性,最终达到改善中医之CSF胸痹的效果。
5 小结
随着冠脉造影检查的普及,CSF心绞痛成为了临床的常见病症之一,这也给当代中医学带来了巨大的挑战与机遇。因为本病为多种因素共同致病,西医治疗面临较大的局限性和困难。谢文教授通过对经典条文的理解,总结其主要病因病机,并结合临床实践,对CSF胸痹深入思考,采用“益气活血法”对本病进行治疗。在临床实践中,谢文教授把握住本病“虚实夹杂”的特点,在治法上权衡利弊,扶正驱邪同用,遵循“理法方药”的临床思想,建立了完整的临证组方逻辑,体现了中医辨证论治的整体观和个体化的特点的优势,取得了良好的疗效,为CSF的临床诊疗提供了体现中医药诊疗优势的方案。谢文教授根植于临床,勤于思考,必然将继续深入研究“益气活血法“的起效机制和作用原理,以期为患者带来更多的临床获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