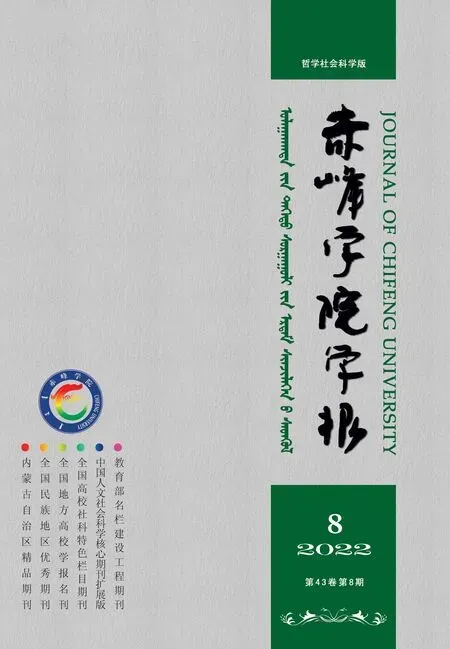北方民族对中华法律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以契丹、女真、蒙古为例
宋 卿,孙 孟
(吉林大学 文学院中国史系,吉林 长春 130012)
中华法律文化伴随中华文明与中华法系的发展而发展,凝结着中华民族的认同并具有高度持续性,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具有深厚的根基。历史上,少数民族与汉族共同发展并丰富了灿烂的中华法律文化。10—14世纪北方民族兴起,契丹、女真、蒙古纷纷走上政治舞台,建立了强大的辽、金、元政权。辽金元时期的律法承唐宋之制,吸收大量中原法律思想,同时保留了本民族的特色,契丹、女真、蒙古对中华法律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在客观上促进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目前学界已展开契丹、女真、蒙古对中华法律文化传承与发展的相关研究,徐晓光《辽西夏金元北方少数民族政权法制对中国法律文化的贡献》认为辽夏金元在法典编纂形式与法典内容结构体系方面有所创新,为中华法文化的发展注入新因质[1]。唐自斌《论宋辽金元时期的法制融合》指出宋辽金元时期的法制融合具有继承性与落后性并存的特点[2]。李玉君《文化认同视阈下的辽代立法与司法实践》考察了辽法中的儒家观念,认为辽代法律汉化具有必然性[3]。姜宇《法律儒家化与金朝法制演变》分析了儒家法律文化对金代各个时期法律政策及《泰和律义》的影响,指出金朝特色法律文化是对中华法律文化的补充[4]。学界已有相关研究多侧重于对辽金元法律中蕴含的儒家观念进行考察,对本文的展开裨益良多。本文拟在学界已有研究基础上,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视阈下,从契丹、女真、蒙古对中华传统法制思想与法律内容的吸收与创新等方面,考察北方民族对中华法律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从律法层面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些许启示。
一、契丹、女真、蒙古的法律发展
契丹、女真、蒙古均系发源于“化外之地”的北方民族,在建立政权前处于漫长的氏族社会与部落联盟时期,不成文、不规范、民族特色浓厚的习惯法发挥了重要作用。辽、金、元政权建立,统治者逐渐意识到法律的重要性及其与中原法律发展的差距,开始效法中原,创立并发展本朝法制。契丹、女真、蒙古的法律发展进程都经历了由习惯法向成文法过渡的阶段,律法中既折射出习惯法的影子,也凝结着中原法律精华。
契丹是中国北方古老的游牧民族,唐末中原混战之际发展壮大,至916年,耶律阿保机建国称帝,以契丹贵族为核心的辽王朝揭开了统治的序幕。辽立国之初尚无法典,处罚决断无规范可依,具有较强的随意性,及至“诸弟之乱”爆发,为耶律阿保机敲响警钟,始“权宜立法”[5]。《辽史·刑志》载:“亲王从逆,不磬诸甸人,或投高崖杀之;淫乱不轨者,五车轘杀之;逆父母者视此;讪詈犯上者,以熟铁锥摏其口杀之”[6],“权宜立法”尚不成熟,从内容来看主要针对谋逆、淫乱、不孝、以下犯上等行为,且刑罚方式残酷严苛。此后,契丹开始走向有法可依的轨道。神册六年(公元921年),耶律阿保机平定诸夷,“乃诏大臣定治契丹及诸夷之法,汉人则断以律令,仍置钟院以达民冤”[7],契丹诸夷与汉人并行二法,在法律上体现出辽朝“因俗而治”的二元分治色彩。“治契丹及诸夷之法”[8]成为辽代成文法典的开端,但此法尚不完备,诸多内容缺漏,决断时仍存在法律没有明确规定而临时判罚的现象,如辽穆宗应历十二年(公元962年),“国舅帐郎君萧延之奴海里强陵拽剌秃里年未及之女,以法无文,加之宫刑,仍付秃里以为奴。因著为令。”[9]穆宗残酷暴虐,滥用酷刑,其后即位的景宗、圣宗吸取教训,施行“宽严相济,用刑详慎”的治法纲要,复置钟院,更定旧法。圣宗时,“先是,契丹及汉人相殴致死,其法轻重不均,至是一等科之。统和十二年(公元994年),诏契丹人犯十恶,亦断以律”[10],法律的定例与施行呈现出契丹与汉人一贯视之、二法交融的倾向。在景宗与圣宗的铺垫下,辽兴宗于重熙五年(公元1036年)纂修太祖以来的法令,参唐律颁行《新定条制》。重熙《新定条制》共547条,着重对刑制作出规定,包括死刑、流刑、杖刑及三等徒刑[11]。有辽一代最后一次对法典的补充纂修,为辽道宗清宁六年(公元1060年)更定的《咸雍条制》,“凡合于《律令》者,具载之。其不合者,别存之”[12],重编至千余条,后又进行两次续编。然而法令出现了繁冗的弊病,致“典者不能遍习,愚民莫知所避,犯法者众,吏得因缘为奸”[13],由是大安五年(公元1089年)《咸雍条制》宣告废止,复用重熙旧法。辽朝末年,社会秩序混乱,盗叛频仍,天祚帝荒暴,重新启用法典中早已被废止的辽初酷刑,辽代法律体系陷入混乱,逐渐失效,直至辽亡。
女真发源于白山黑水间,部族早期通行习惯法,“法制简易,无轻重贵贱之别,刑、赎并行”[14]。1115年,女真人在完颜阿骨打的带领下兴兵反辽,建立了雄踞一方的金王朝。金建国之初无成文法,仍沿用习惯法的基本内容。太宗天会年间,在承继太祖“无变旧风之训”[15]的基础上,稍用辽、宋之法。至熙宗朝,“以本朝旧制,兼采隋、唐之制,参辽、宋之法,类以成书”[16],颁行金代第一部成文法典———《皇统新制》,金代系统化成文法的发展步入正轨。正隆年间,海陵制定《续降制书》,与《皇统新制》并行[17]。世宗即位后,“以正隆之乱,盗贼公行,兵甲未息,一时制旨多从时宜”,将这些临时性法规整理成《军前权宜条理》[18]。大定五年(公元1165年),续修《军前权宜条理》。大定十九年(公元1179年)诏明法者共同校订《皇统新制》《续降制书》及大定《军前权宜条理》、续行《军前权宜条理》,颁行《大定重修制条》,凡1190条,共12篇[19]。及至章宗朝,金代法律发展达到顶峰,泰和元年(公元1201年)以唐律为蓝本再成新律,颁行金代最后一部法典《泰和律义》。《金史》评《泰和律义》“实《唐律》也”,包含名例、卫禁、职制、户婚、厩库、擅兴、贼盗、斗讼、诈伪、杂律、捕亡和断狱十二律[20],金代法律走向完备。
13世纪初,蒙古兴起于漠北草原。蒙古政权建立前,“约孙”广泛通行。“约孙”在蒙古语中有“规矩”“道理”之义,也就是汉语中所谓的“习惯法”,以蒙古先民在早期社会生产实践中所形成的自然禁忌、民族信仰、生产习俗等作为社会成员共同遵守的行为习惯和道德准则。1206年,成吉思汗建立大蒙古国,随后开始了对各个部落的统一与西征,为凝聚战斗力、保障政权的稳定,成吉思汗发布系列“札撒”和命令。“札撒”即汉语“法令”之意,据志费尼《世界征服者史》,成吉思汗逝世前,曾召集众子订立遗嘱,不准违反其法令,窝阔台及其兄弟遵照圣训,立下文书[21]。窝阔台即位后,将成吉思汗的“札撒”和律令汇编为《大札撒》,作为不可违背、不可逾越的最高法律权威,并采取“因俗而治”的策略,在征服的汉人地区沿用金代《泰和律》。蒙古政权辖域广大,至忽必烈建立元朝,《大札撒》的内容已无法满足统治需要,逐渐成为藏于金柜的权力象征。《泰和律》也于至元八年(公元1271年)禁行,元朝的立法活动提上议事日程。元世祖“简除繁苛,始定新律”,至元二十八年(公元1291年)以何荣祖辑公规、治民、御盗、理财等十事为一书,颁行《至元新格》[22]。至元仁宗嗣位,以儒治国,“又以格例条画有关于风纪者,类集成书,号曰《风宪宏纲》”[23],针对纲纪、吏治问题订立监察法规。元英宗时,将至治二年(公元1322年)以前的元朝法令分类汇编,编纂《大元圣政国朝典章》,至治三年(公元1323年)又以《至元新格》和《风宪宏纲》为参考,以诏制、条格、断例为纲,颁行《大元通制》[24]。《大元圣政国朝典章》和《大元通制》反映了元代政治、经济、社会生产生活等各个方面的法律法规,是元代历史上不可或缺的重要法典。元顺帝即位后,于至正六年(公元1346年)颁行了元代最后一部法典———《至正条格》。然而顺帝后期荒淫怠政,宠幸佞臣,政权动荡,导致国家内忧外患严重,元朝的统治走向尾声,《至正条格》并没有发挥预期的效力。
二、契丹、女真、蒙古律法对中原法律文化的传承
契丹、女真、蒙古在建立政权后,法律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这种变化的背后反映的是民族自树意识的兴起。随着政权日益稳固,北方民族不再拘泥于传统的“华夷之辨”,自视“中国”的观念逐渐强烈。为佐证“正统”的合法性,辽金元统治者积极吸收中原传统文化,在法律建制上亦充分体现。辽金元律法无论在法制思想上,亦或法典内容上都充分体现了对中原法律文化的传承。
首先,法制思想的传承。中原法律文化中的“礼法合一,德刑相济”“法自君出,皇权至上”“忠君孝亲”等思想为辽金元法律所继承。
其一,辽金元的法律折射出中原法律文化中“礼法合一,德刑相济”的思想。“礼法合一,德刑相济”是中国古代传统的法制思想,主张将宗法伦理、道德教化与君权统治、刑罚措施相结合,以礼入法,德政为主,明德慎罚。《礼记·乐记》载:“礼、乐、刑、政,其极一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25],足见“礼”在本质上体现出“法”的特点,礼法、德政、刑罚殊途同归。西汉时,“礼法合一,德刑相济”的思想正式形成,大儒董仲舒认为天有阳阴,故治有德刑,德为阳,刑为阴,因此德主刑辅,不可偏废。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将“引礼入法,德刑并用”上升为“大一统”国家最高的法律意志,为此后历代王朝承继并发展,成为中原法律文化的独特内涵。
辽代法律的发展中,用刑详慎的观念逐渐深入。重熙元年(公元1032年),诏“职事官公罪听赎,私罪各从本法;子弟及家人受赇,不知情者,止坐犯人”[26],罪只论及犯人,不再牵涉无辜不知情者。“时有群牧人窃易官印以马与人者,法当死”,兴宗认为“一马杀二人,不亦甚乎”?遂“以减死论”[27]。女真政权在立法与执法的过程中也显现宽罚慎刑的原则,更加重视教化的作用。如盗窃劫掠的判罚,依金国旧法,杀人或盗劫者,击脑处死,并罚没家产,发配家人为奴[28]。天会七年(公元1129年)更定新规,“诏凡窃盗,但得物徒三年,十贯以上徒五年,刺字充下军,三十贯以上徒终身,仍以赃满尽命刺字于面,五十贯以上死,征偿如旧制”[29]。至大定十五年(1175年),世宗诏有司:“朕惟人命至重,而在制窃盗赃至五十贯者处死,自今可令至八十贯者处死”[30]。对盗窃者的处罚从直接处死到定量判罚,死刑标准从盗五十贯宽至八十贯,体现了量刑从宽思想的发展。世宗更是宽罚慎刑与教化的积极推动者,史载,“河中府张锦自言复父仇,法当死”,世宗认为张锦为父报仇且投案自首,可称其为烈士,遂“以减死论”[31]。对于职官贪赃,世宗谓宰臣:“职官始犯赃罪,容有过误。至于再犯,是无改过之心。自今再犯不以赃数多寡,并除名”[32],可见世宗容许初犯赃罪的职官反思己过,自我纠正,以行教化,但宽罚和教化并不代表纵容,如若再犯,则以除名论。元代法律中也折射出儒家礼法思想的影子,元法倡导审慎用刑,且多禁酷刑,“盖古者以墨、劓、剕、宫、大辟为五刑,后世除肉刑,乃以笞、杖、徒、流、死备五刑之数。元因之,更用轻典,盖亦仁矣”[33]。蒙古统治者重视人命,认为行刑不宜仓促,当详细审问申辩后再断罪。世祖忽必烈曾语臣下:“人命至重,今后非详谳者勿辄杀人”[34],并言:“朕治天下,重惜人命。凡有罪者必令面对再四,果实也,而后罪之”[35],可见慎刑的观念已然渗透于元代的法律思想中。
其二,辽金元律法中还蕴含着中原法律文化中“法自君出,皇权至上”的思想。维护皇权统治,保证君主的绝对权威是中国古代王朝统治的根本。董仲舒以“王者唯天之施,施其时而成之,法其命如循之诸人,法其数而以起事,治其道而以出法,治其志而归之仁”[36],论证君王的言行代表“天”的意志,赋予“法自君出”必然性。部落联盟时期的契丹、女真、蒙古,民主议事会发挥着重要作用。在王朝建立初期,这种军事民主制传统得以延续,如契丹的贵族大会、女真的国论勃极烈制度及蒙古的忽里勒台大会,重大法令的通过需经集体商议后定夺。皇帝也受法律的约束,《三朝北盟会编》引赵子砥《燕云录》,“金国置库收积财货,誓约,惟发兵用之。至是国主吴乞买私用过度,谙版告于粘罕,请国主违誓约之罪。于是群臣扶下殿,庭杖二十毕,群臣复扶上殿,谙版、粘罕以下谢罪,继时过盏”[37],此时议事会的权力依然凌驾于君主之上,皇帝犯错也要断罪受罚。随着政权的不断发展,君主专制进一步强化,辽金元王朝开始渗透中原法律观念中“权尊于法,皇权至上”的意识,君主对法律的制定和修改享有绝对的权威,皇帝诏令的效力基本等同于法律,某些敕令的内容直接纳入法律条例中。在维护皇权方面,法律严惩企图颠覆皇权统治,危害国家政权的谋逆大不敬行为。辽金元以“谋反”“乱言”而伏诛的事例众多,《元史·刑志》对各类谋逆不敬情形的处罚进行了详细的记载,如“诸乱言犯上者处死,仍没其家”[38],“诸谋反已有反状,为首及同情者凌迟处死,为从者处死,知情不首者减为从一等流远,并没入其家。其相须连坐者,各以其罪罪之”[39],触动皇权的行为处罚最为严厉,多以极刑。
其三,中原法制思想中“忠君孝亲”的观念亦为辽金元律法因袭,代代传承。辽代帝王是“孝亲”观的践行者,厉行教化,法律作为统治阶级意志的反映,自然也蕴含了浓厚的“忠孝”思想。辽兴宗戒喻族人:“国家三父房最为贵族,凡天下风化之所自出,不孝不义,虽小不可为”[40]。辽圣宗诏令“民间有父母在,别籍异居者,听邻里觉察,坐之。有孝于父母,三世同居者,旌其门闾”[41]。辽法严惩不孝之举,纵是皇族,亦不容赦,道宗时,“皇族十公悖母,伏诛”[42]。金代律法中也包含着重视忠孝的相关规定,如泰和五年(公元1205年),章宗敕尚书省:“祖父母、父母无人侍养,而子孙远游至经岁者,甚伤风化,虽旧有徒二年之罪,似涉太轻。其考前律,再议以闻”[43],章宗认为子孙远游不奉养父母的处罚过轻,应当再议,将儒家“孝”文化上升到法律层面。元代强调“重孝”,元法禁止虐待父母,重视赡养老人。《元史·刑志》载:“诸殴伤祖父母、父母者,处死”[44],“诸为人子孙,或因贫困,或信巫觋说诱,发掘祖宗坟墓,盗其财物,卖其茔地者,验轻重断罪”[45],殴打、弑杀父母,盗挖祖坟等不孝行为均要断罪处刑。晋州达鲁花赤捏克伯家在解州,因思慕妻子假称老母病亡,得奔丧假后往解州住月余,“不顾老母之养,却携妻子同来任所”,后被“断罪罢职”[46]。
此外,中原律法中还蕴含着丰富的伦理道德精神,此精神在北方民族律法中亦得以传承。以婚嫁为例,中原王朝的婚嫁程序严格,不符合儒家伦理道德的接续婚受到社会舆论的强烈谴责,并按律处罚。汉代规定:“男不自专娶,女不自专嫁,必由父母”[47],子女无权自行缔结婚姻。《唐律疏议》载:“诸尝为袒免亲之妻,而嫁娶者,各杖一百;缌麻及舅甥妻,徒一年;小功以上,以奸论。妾,各减二等。并离之”[48],唐代依据血缘关系的亲疏对接续婚施以不同程度的惩罚。女真旧俗存在接续婚,婚嫁要求亦较为随意,“富者则以牛马为币,贫者则女年及笄,行歌于途。其歌也,乃自叙家世、妇工、容色,以申求侣之意,听者有未娶欲纳之者,即携而归之,后方具礼偕女来家,以告父母”[49]。至金中后期,婚嫁要求逐渐严格,并上升至法律层面,禁止男女私奔行为,婚嫁不依礼节亦要受到处罚。世宗时规定,“以渤海旧俗男女婚娶多不以礼,必先攘窃以奔,诏禁绝之,犯者以奸论”[50]。泰和律中对接续婚亦进行了限制,“侄儿娶讫婶母,即是欺亲尊长为婚,同奸法,各离”[51],中原法律文化中的婚嫁伦理思想在金朝法律制度中充分体现。
其次,从法律内容来看,辽金元律法中的罪名、刑罚、适用原则及体例等方面都闪烁着中原王朝法律文化的痕迹,契丹、女真及蒙古等北方民族统治阶层对中原传统法律文化的认同可见一斑。
其一,“五刑”“十恶”“八议”的沿用。辽初重用康默记、韩知古等汉臣,中原法律文化和法律内容逐渐渗透于辽代的法制建设中,契丹法律伴随着政权的发展日益规范,刑罚也逐渐体系化。隋朝时以“笞、杖、徒、流、死”为五刑,唐宋沿袭之。辽制“刑之凡有四:曰死,曰流,曰徒,曰杖”[52],继承了中原“五刑”体系的主要内容。中原王朝统治者例危及君主专制统治秩序、严重破坏伦理纲常关系的十项重罪为“十恶”,十恶之罪不为常赦所原。《唐律疏议》云:“五刑之中,十恶尤切,亏损名教,毁裂冠冕”[53],更是将其标至篇首,以为训诫。统和十二年(公元994年),辽圣宗下诏“契丹人犯十恶者依汉律”[54],“十恶”为契丹统治者援引。金代也以“十恶”为大罪,并明令禁止犯“十恶”大罪的人应试科举。而针对贵族阶级的特权,中原法律中有“八议”之法,权贵只要不犯“十恶”大罪,量刑可由皇帝裁决,减轻惩罚。辽“亦有八议、八纵之法”[55],耶律乙辛偷卖禁物出境,送有司议罪,论法当处死,同党耶律燕哥以“当入八议”奏上,乙辛得以减免死罪,改以铁骨朵击打,囚禁来州[56]。元代直接继承了中原法律中的“五刑”“十恶”与“八议”,并以专条的形式明确载于法中,如“笞刑:七下,十七,二十七,三十七,四十七,五十七”[57],“谋大逆:谓谋毁宗庙、山陵及宫阙”[58],“议贵:谓职事官三品以上,散官二品以上,及爵一品者”[59]。除此之外,《元史·刑志》还将中原文化中的“五服”内容体现在量刑中:“诸亲属相盗,谓本服缌麻以上亲,及大功以上共为婚姻之家,犯盗止坐其罪,并不在刺字、倍赃、再犯之限。其别居尊长于卑幼家窃盗,若强盗及卑幼于尊长家行窃盗者,缌麻小功减凡人一等,大功减二等,期亲减三等,强盗者准凡盗论,杀伤者各依故杀伤法”[60]。对于亲属盗窃,元代以“五服”所确定的血缘关系的亲疏远近为标准,进行差别化的断罪量刑,充分体现了中原传统法律中的“准五服以制罪”原则。
其二,法律篇目体例的沿用。金朝自太宗、熙宗时,就已稍用隋唐之制、辽宋之法。章宗朝颁行了《泰和律义》,作为金代最具代表性、凝结最高成就的法典,《泰和律》共分为十二篇:“一曰《名例》,二日《卫禁》,三曰《职制》,四曰《户婚》,五曰《厩库》,六曰《擅兴》,七曰《贼盗》,八曰《斗讼》,九曰《诈伪》,十曰《杂律》,十一曰《捕亡》,十二曰《断狱》。实《唐律》也”[61],足见金代法律编纂体系对中原法制仿效程度之高。元代法律体例也借鉴了中原法律文本的体例编排形式,英宗至治三年(公元1323年)颁行的较为完备的法典《大元通制》,纲之有三:“一曰诏制,二曰条格,三曰断例”[62]。通过比对研究,目前学界多认为,“条格”即相当于中原法典中的“令”,“断例”相当于中原法典中“律”的部分[63]。继《大元通制》后颁行的《至正条格》,其断例部分包括卫禁、职制、户婚、厩库、擅兴、贼盗、斗讼、诈伪、杂律、捕亡、断狱11门,除缺少唐、金律的第一门“名例”外,其余篇目、次序皆与唐律和金律完全相同[64]。
三、契丹、女真、蒙古律法对中原法律文化的发展
作为北方少数民族的契丹、女真、蒙古,其法律的发展完善并非单一的复制中原法律制度,而是在择优吸收借鉴的同时,根据民族特色与王朝的实际情况进行变通和创新。辽金元的律法丰富了中华法律的内涵,也为此后的王朝所承继,并随之共同融入中华法系,拓展了广义概念上的中华法律文化,铸就了灿烂的中华法律文明。
首先,在法律内容的构成上,契丹、女真、蒙古的律法是多元结合的产物。北方民族统治者突破了法制建设的文化藩篱,吸收中原法律制度,但也结合本朝实际,融汇民族习惯,法律制度中蕴含着诸多变更和创新内容。
其一,“五刑”与“八议”的发展。辽代刑罚框架基本与“五刑”相似,在具体刑制上有所不同,死刑方式除绞杀、斩杀外,还包括凌迟等。凌迟非辽首创,但正式入律则始于辽。唐律中徒刑的最高期限为三年,而辽制“徒刑一曰终身,二曰五年,三曰一年半。终身者决五百,其次递减百”[65],显见辽律中已存在有期徒刑与无期徒刑之分,这些都为此后的明清王朝直接承继。
金世宗曾与宰臣针对后族犯罪的情况进行商讨,其中论及“八议”的应用。史载:
“时后族有犯罪者,尚书省引‘八议’奏,上曰:‘法者,公天下持平之器,若亲者犯而从减,是使之恃此而横恣也。昔汉文诛薄昭,有足取者。前二十年时,后族济州节度使乌林达钞兀尝犯大辟,朕未尝宥。今乃宥之,是开后世轻重出入之门也。’宰臣曰:‘古所以议亲,尊天子,别庶人也。’上曰:‘外家自异于宗室,汉外戚权太重,至移国祚,朕所以不令诸王、公主有权也。夫有功于国,议勋可也。至若议贤,既曰贤矣,肯犯法乎。脱或缘坐,则固当减请也。’二十六年,遂奏定太子妃大功以上亲、及与皇家无服者、及贤而犯私罪者,皆不入议”[66]。
金世宗吸取汉代外戚祸乱朝政的教训,认为后族犯罪不应随意使用“八议”之法宽恕,并依五服制明确划定了后族不入“八议”的范围,且对“议贤”的情况也进行了限制。可见金代统治者虽引用“八议”,却并非是对其标准的完全复刻,在实际的应用中更考虑到了维护法律公平性与政权稳定性的问题,这无疑是一种进步。自金代始,“八议”的标准愈加严格,明清专制程度空前加强,严从司法,“八议”特权陨落。
其二,畜牧法与海外贸易法的发展与丰富。受北方游牧民族习惯的影响,元代格外重视畜牧业的发展,保护畜牧业的律令条例明显多于中原王朝。文宗尝“申禁天下私杀马牛”[67];《元史·刑志》载:“诸每岁,自十二月至来岁正月,杀母羊者,禁之”[68];“诸宴会,虽达官,杀马为礼者,禁之。其有老病不任鞍勒者,亦必与众验而后杀之”[69],对禁杀日期、牲畜类别等做出具体规定,私自宰杀牛马甚至要处以杖刑。禁止滥杀牲畜,保护了牧业繁殖的正常进行,在法律层面上约束牧者的行为,加强对畜牧工作的重视。明代也对畜牧业予以重视,并立法进行保护,《大明会典》中以三卷内容对畜牧生产管理做出明令规定,包括畜产的检验,偷盗牛马的处罚等众多内容[70]。
元代社会经济繁荣发展,海外贸易也空前发达。为对海外贸易进行有效的管理、增加官方收入、扩大影响力,元政府建立七大市舶司作为专门管理机构,并于至元三十年(公元1293年)颁行《市舶则法》,详细规定了抽税具体规则、公凭公验申报、海商管理办法及违禁进出口货物、市舶官员违法失职行为处罚等二十三条内容[71]。至元《市舶则法》以宋代的市舶法令为基础,宋代虽具有较多的海外贸易法令,却始终未能形成体系,且现已失传,元代市舶法章程详细,在中国古代海外贸易法中占据重要地位,对海关官员的贪腐行为进行整治,从根本上促进海外贸易清廉有序的运行,为后世提供了借鉴经验[72]。
其次,在法典体例上,就历史记载而言,辽金两朝未有法典原文保留,元代律法保存相对全面,《大元圣政国朝典章》《大元通制》等为详细考证元代法律样貌提供了文本支撑。元代法典的编纂彰显出独特的个性:
其一,颁布大量断例作为量刑的依据。元法在形式上不同于唐宋之法,以条格和断例为主体,条格是规定典章制度的非刑事性政令法规,断例是刑事法律的总称[73]。断例又有“断案事例”和“断案通例”之分,前者即判例之意,审判机构对具体案件审理的记载可作为同类案件审理的援引依据;后者即在断案过程中形成的,以“律”的体例所辑编的成文法规定[74]。元代的断例划分标准明确,附于各篇名之下,补充、细化了刑事法律的具体内容,成为中国古代判例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明清法律产生重要影响。元代以条格和断例代替唐宋法典中的律和令,明清时期虽恢复了传统的法典形态,法律体系却与唐宋有所分别,“例”在法律中的重要性明显突出,清代将“例”的编订作为一项重要立法活动,且也存在个体案例按律的形式编为通例的情况,显然是受到元代“断例”的影响。更有学者认为明清形成以条例、则例、事例为主的例的体系是对元代法律体系“例化”的延续和升华,因将元代称为明清“典例法律体系”形成之前夜[75]。
其二,元代律法的文书体与中原律法刻板的文言文体不同,采用硬译公牍文体,将蒙古语与汉语的用语规范、词法属性结合,语言自由,语法新奇。如《大元圣政国朝典章》中关于省部纪纲的记载:“在外行省、宣慰司、路府州县,凡合行的公事不得推调,依这条例里交干办行呵,其间有不用心厮推调的,从上整治呵,怎生”[76]?奏旨、圣旨中,包含诸多如“呵”“怎生”等口头化词汇,不拘泥于复杂的形式,随意性较强,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后世白话语言的发展。
结语
2014年,在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我国古代法制蕴含着十分丰富的智慧和资源,中华法系在世界几大法系中独树一帜。要注意研究我国古代法制传统和成败得失,挖掘和传承中华法律文化精华,汲取营养、择善而用”[77],高度强调了中华法律文化的研究价值。契丹、女真、蒙古的法律发展史,是少数民族法律文化的丰富创新史,也是北方少数民族法律文化与中原法律文化的交融史。辽金元统治者虚怀若谷,以开阔的胸襟,审慎独道的考量,有选择性地吸收、借鉴中原法律文化,同时结合现实情况和民族特点,在法律建设中融入民族法制因素,进行变革与创新,有效地调节了社会关系,稳定了社会发展。
作为中华法律发展史上的重要一环,辽金元的律法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辽朝将凌迟入律,明清均有保留;金代曾以法的形式倡导“从本语”“兴骑射”,金世宗委派猛安谋克教习骑射,不亲力亲为者一律处罚[78],清王朝也将“国语骑射”与法律结合,以行赏罚,康熙帝下令:“满洲以骑射为本,学习骑射,原不妨碍读书。考试举人、进士,亦令骑射,倘将不堪者取中,监箭官及中式人,一并从重治罪”[79],应试者骑射不合格要处以重罪;元代“断例”在清朝编纂的《大清律例》中仍可窥其身影。辽金元承继唐宋之法,明清亦对辽金元的律法进行吸收借鉴,各民族不断为中华法系增添新因质,最终共同融入中华法律体系,铸就了中华法律文明。中华法律文化一脉相承,北方民族在中华法律文明的形成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促进了律法层面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发展与凝聚。近代日本和美国学者提出的“异民族统治中国史”“征服王朝论”研究是与中国历史发展趋势完全相悖的,灿烂的中华法律文化是少数民族和汉族共同创造的,“多元”的诸民族法律文化在历史的演进中交融、汇聚而成“一体”的中华法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