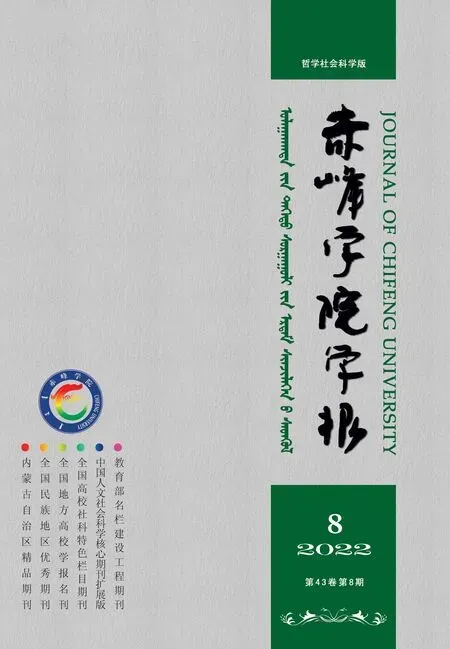北朝炎黄祖先记忆与“中华”认同
陈 鹏,蒋晓斐
(吉林大学 文学院,吉林 长春 130012)
十六国北朝时期,匈奴、鲜卑、羯、氐、羌等边疆民族先后涌入中原,建立政权。这些边疆民族在建立政权后,往往将黄帝、炎帝等华夏上古帝王追溯为本族祖先,以推动本族“华夏化”和确立本族政权的正统性、合法性。通过祖源、族源塑造,边疆民族逐渐形成炎黄祖先记忆。就此而言,十六国北朝是炎帝、黄帝成为中华民族“共祖”的重要时期,也是各民族在炎黄祖先记忆下凝聚共同“中华”认同的关键阶段。近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中明确提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1]。炎黄祖先记忆作为“中华民族共同性的生动表现”[2],无疑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历史基础和文化符号,颇有考察之必要。著名历史学家吕思勉早就注意到十六国北朝边疆民族攀附炎黄、效法华夏之现象[3];何德章指出北族人“伪托中原名族,冒引华夏名人为先祖”,最初出于政治宣传,后渐认同于华夏[4];张军认为北族族源攀附旨在构建政权合法性,并服务于政权“汉化”[5];杨懿、王瀚尧提出北魏在国家意识形态领域形成黄帝系谱与鲜卑正宗两种话语诉求[6];李凭指出黄帝形象经北朝各族尊奉为祖先,被放大为各族人文初祖[7];温拓提出宇文氏通过编纂先世传说,完备自身法统[8];苏航则指出宇文氏在北魏时本祖黄帝,至西魏改祖炎帝,旨在配合西魏改制[9]。上述研究丰富了我们对北朝诸族祖述炎黄现象的认识,但主要针对的是北朝君主或皇族的祖源、族源认识,而较少涉及皇族之外的其他“虏姓”家族,①未能充分展现北朝炎黄祖先记忆于“中华”认同演进之重要性。本文拟在前贤研究基础上,进一步考察北朝虏姓家族的祖先记忆,揭示炎帝、黄帝是如何在这一时期成为各族“共祖”和凝聚“中华”认同的。
一、北魏虏姓祖述炎黄与“中华”认同
北魏虏姓家族以黄帝为祖先,最典型案例即北魏皇族拓跋氏。《魏书·序纪》曰:
昔黄帝有子二十五人,或内列诸华,或外分荒服。昌意少子,受封北土,国有大鲜卑山,因以为号。其后世为君长……黄帝以土德王,北俗谓土为托,谓后为跋,故以为氏。其裔始均,入仕尧世,逐女魃于弱水之北,民赖其勤,帝舜嘉之,命为田祖。爰历三代,以及秦汉,獯鬻、猃狁、山戎、匈奴之属,累代残暴,作害中州,而始均之裔,不交南夏,是以载籍无闻焉[10]。
《魏书·序纪》记叙拓跋鲜卑早期历史,很可能源自拓跋氏的民族史诗或口传歌谣[11],即《序纪》所言“世事远近,人相传授,如史官之纪录焉”[12]。然拓跋氏自居“黄帝—昌意—始均”后裔,是否是拓跋鲜卑口耳相传的历史记忆呢?
黄帝、昌邑、始均,皆见于中原或华夏古史系统。《史记·五帝本纪》提到黄帝与嫘祖生二子,“其二曰昌意,降居若水”[13];《山海经·大荒西经》曰:“有北狄之国。黄帝之孙曰始均,始均生北狄。”[14]姚大力即提出《魏书·序纪》之说,展现出“将拓跋部的先世史‘嫁接’到中原古史的言说框架内的强烈倾向”,是拓跋鲜卑“汉化”的表现,并推断是北魏初年崔宏的建议[15]。《魏书·礼志》称北魏天兴元年,道武帝拓跋珪“诏有司定行次,正服色。群臣奏以国家继黄帝之后,宜为土德”[16]。对此,《资治通鉴》称拓跋珪“用崔宏议,自谓黄帝之后,以土德王”[17]。据此,姚大力推断拓跋氏“自谓黄帝之后”系采自崔宏建议,是合乎情理的。盖北魏立国,拓跋氏出于确立自身统治的合法性、正统性的需要,企图将本族传统融入中原历史中;而汉人士大夫崔宏等,则有意引导北魏统治者接受华夏文化,“用夏变夷”。
不过,道武帝接受崔宏等汉臣建议,很可能也受到拓跋鲜卑早先传统影响。早在两晋之际,拓跋鲜卑联盟首领猗迤(桓帝)去世,汉人卫操曾“立碑于大邗城南,以颂功德”[18]。此碑在孝文帝初发掘出土,文字得以保存,碑文伊始即曰:“魏,轩辕之苗裔。”[19]对于此碑,清人钱大昕指出碑文中“魏”国号和“桓穆二帝”谥号皆为后世追改,并推测“魏”字原作“拓跋鲜卑”[20]。但拓跋鲜卑为“轩辕之苗裔”,很可能是碑文原文,未见充分的否定证据。两晋时期,拓跋鲜卑承认晋朝的宗主地位,而中原士人很可能有意识地将之纳入华夏历史叙述传统,视之为“轩辕之苗裔”。这是对司马迁《史记》将四裔视作黄帝子孙的继承。汉人卫操等进入拓跋鲜卑,有意宣扬这一历史叙述传统。这是将拓跋鲜卑族源、祖源纳入华夏历史的初步尝试,成为日后道武帝接受拓跋氏为“黄帝之后”的基础。另外,《魏书·序纪》称“黄帝以土德王,北俗谓土为托,谓后为跋,故以为氏”,亦非全无依据。罗新指出“拓跋”一词,由修饰性名号“拓”(tog)+官号“跋”(beg)构成,作为鲜卑语即领土之君的意思[21]。拓跋氏号称“黄帝之后”,实际是中原古史、五德终始说与拓跋鲜卑固有文化结合的产物。
北魏前期,除将拓跋氏黄帝后裔身份与王朝德运(土德)联系起来外,似尚未特别强调拓跋氏黄帝后裔的族群性质。盖北魏前期立都平城,拓跋鲜卑“汉化”程度有限。不过,拓跋氏既然声称为“黄帝之后”,北魏又承续历朝正统,当已萌发“中华”认同。至孝文帝迁洛和“汉化”改革,以皇族拓跋氏(元氏)为首的拓跋鲜卑诸部族、诸家族祖述炎黄之现象渐多。
太和十七年(493年),孝文帝迁洛之际,在《迁都洛阳大赦诏》中称:“惟我大魏,萌资胤于帝轩,悬命创于幽都。”[22]“帝轩”即轩辕黄帝,正是孝文帝承认拓跋氏为黄帝后裔的表现。值得注意的是,迁都之际,鲜卑贵族丘目陵(穆)罴反对迁都,以“黄帝都涿鹿”为由,提出“古昔圣王不必悉居中原”。而孝文帝答道:“黄帝以天下未定,居于涿鹿,既定之后,亦迁于河南。”[23]二者皆以黄帝立都故事来论证是否应迁都,可见北魏君臣对黄帝故事颇为了解,而黄帝故事影响到北魏现实政治。《迁都大赦诏》也指出北方已定,北魏当从拓跋氏起源之“幽都”迁于“中原”,所谓“预卜还中京,垂美无穷”[24]。这正是借鉴了黄帝迁都故事,也透露出孝文帝的“中华”认同。
北魏迁洛后,推行“汉化”改革。太和十九年(495年),孝文帝“诏迁洛之民,死葬河南,不得还北。于是代人南迁者,悉为河南洛阳人”[25]。太和二十年(496年),又诏迁洛代人虏姓改用汉姓[26],诏书曰:
北人谓土为拓,后为跋。魏之先出于黄帝,以土德王,故为拓跋氏。夫土者,黄中之色,万物之元也,宜改姓元氏。诸功臣旧族自代来者,姓或重复,皆改之[27]。
可见,孝文帝改皇族拓跋氏为元氏,源自认同“魏之先出于黄帝”。在改虏姓为汉姓的同时,孝文帝还仿效汉人士族评定代人姓族等级[28],推动虏姓家族“汉化”和“士族化”。
历经“汉化”改革,北魏皇族拓跋氏(元氏)为黄帝后裔,被北魏宗室广泛接受。北魏元氏宗室墓志,即充分展现元氏对黄帝后裔身份的承认。就笔者目及,最早以黄帝为拓跋氏先祖的北魏宗室墓志,为永平元年(508年)十一月《元详墓志》。志主元详为“献文帝之第七子,孝文皇帝之季弟”,志文有云“纂乾席圣,启源轩皇”[29],正是将“轩皇”(轩辕黄帝)视作拓跋氏先祖的表现。再如《元淑墓志》,志主元淑为“昭成皇帝(什翼健)曾孙,常山康王(拓跋素)第廿五之宠子”,志文称“赫矣元极,显自黄基”[30],亦将拓跋氏追溯至黄帝;《元灵曜墓志》,志主元灵曜为“恭宗景穆皇帝之曾孙”,志文称“邈矣鸿源,道迈皇轩”[31],“皇轩”亦指黄帝轩辕氏。
正如学人所论,墓志记叙祖源,反映了“志主或其后人心理上的认可”[32]。上引北魏宗室墓志,即充分展现了自孝文帝迁洛和改制以来,黄帝祖先得到北魏宗室共同认同。不过,我们也注意到个别特例。建义元年(528年)《元顺墓志》,志主元顺为“恭宗景穆皇帝之曾孙”。志文有云:“苻玄鸟之嘉膺,契丹陵之圣绪。”[33]“丹陵”为古史传说中帝尧的诞生地,②此处似以元氏(拓跋氏)为帝尧后裔,与一般认识不同。不过,帝尧亦为黄帝后裔,这也算间接承认元氏为黄帝后裔。黄帝祖先记忆确立,是北魏鲜卑“汉化”的结果,也意味拓跋氏“中华”认同的形成。
除元氏(拓跋氏)外,北魏其他虏姓家族,亦渐将黄帝或炎帝等视作自家祖先。孝文帝改虏姓为汉姓,以朝廷权威改变了代人(鲜卑)家族昔日“以部落为号,因以为氏”传统[34],令代人姓氏在形式上与汉人趋同,趋于“汉化”。代人虏姓家族“汉化”后,亦效法汉人士大夫将姓源追溯到黄帝、炎帝等上古帝王的做法,重塑自家祖先记忆。这一情况,在北朝墓志中亦可找到例证。
北魏《叔孙协墓志》曰:“其先轩辕皇帝之裔胄。”[35]叔孙协系出拓跋鲜卑“帝之十族”之一的叔孙氏。所谓“帝之十族”,指拓跋宗室(皇族)加上献帝邻兄弟七人后裔(纥骨、普、拔拔、达奚、伊娄、丘敦、侯亥七氏)、献帝邻叔父之胤乙旃氏(叔孙氏)和疏属车焜氏(车氏),因本出帝族,在北魏政治和礼仪上具有特殊地位[36]。志文称叔孙氏“其先轩辕皇帝之裔胄”,盖“帝之十族”同源,故与拓跋氏一样以黄帝为先祖。再如《长孙忻墓志》曰:“其先盖轩辕之苗。”[37]长孙氏,即由“帝之十族”之拔拔氏改汉姓而来。更典型的例子,来自达奚氏成员墓志。正始四年(507年)《奚智墓志》称奚氏“始与大魏同先,仆脍可汗之后裔”[38]。而正光四年(523年)奚智子《奚真墓志》却称“其先盖肇傒轩辕,作蕃幽都”[39]。前者强调达奚氏(奚氏)与拓跋氏(元氏)同源,皆威帝侩(即仆脍可汗,献帝邻之父)后裔;而后者强调奚氏为轩辕黄帝后裔。正如何德章所论,“这无疑反映出两代人文化心态上的变化”[40],表明迁洛之后“帝之十族”渐接受黄帝祖先和认同“中华”。
除“帝之十族”外,其他代人家族也同样存在祖述黄帝的现象。《于纂墓志》曰:“轩辕降灵,寿丘祏绪。”[41]《和邃墓志》曰:“其先轩皇之苗裔……因食所采,故世居玄朔。”[42]《侯愔墓志》曰:“其先盖黄帝之苗裔,冠冕连衡,缨貂累袭。”[43]《陆绍墓志》曰:“其先盖轩辕之裔胄。”[44]于纂、陆绍出自北魏虏姓最高等级的贵族“勋臣八姓”之万纽于氏(于氏)和步六孤氏(陆氏),和邃系出鲜卑素和氏(和氏),侯愔系出鲜卑胡古口引氏(侯氏)。③可见,至北魏后期,虏姓家族不乏以黄帝为祖先。
北魏虏姓家族,还将祖先追溯为其他华夏上古帝王。永安二年(529年)《尔朱绍墓志》曰:“其先出自周王虢叔之后,因为郭氏,封居秀容,酋望之胤,遂为尔朱。”[45]同时下葬的《尔朱袭墓志》也有同样表述[46]。尔朱氏为契胡人,或谓之即“羯胡”[47]。当时,尔朱氏家族将自家认定为周虢叔(文王弟)之后。再如北魏末《王真保墓志》称“实轩辕之裔,后稷之胄”[48]。④王真保是匈奴休屠人[49],不仅将祖先追溯至黄帝,更明确为“后稷(周之先祖)之胄”。
要言之,自孝文帝迁洛以来,受改汉姓等“汉化”改制影响,不仅北魏宗室强化了黄帝祖先记忆,“帝之十族”和其他鲜卑、契胡、匈奴等虏姓诸族,亦以确立黄帝子孙自居。而这正是他们“中华”认同确立的重要表现。
二、北周虏姓祖述炎黄与“中华”认同
北魏孝文帝迁洛,促使迁洛代人“汉化”,但留居代地和镇戍北镇的虏姓诸族,仍呈现出鲜卑文化色彩。即如陈寅恪所论,“自宣武以后,洛阳之汉化愈深”,“其同时之代北六镇保守胡化亦愈固”,二者冲突,终造成六镇之乱[50]。北魏渐分裂为东魏北齐和西魏北周。东魏北齐与西魏北周,统治阶层核心皆为六镇豪强,鲜卑文化色彩极强。
不过,北魏虏姓诸族祖述炎黄,并形成“中华”认同,却并未消亡。东魏北齐虏姓家族,往往因袭北魏传统。首先,元氏(拓跋氏)延续了北魏皇族以黄帝为祖先的做法。例如东魏武定二年(544年)《元湛墓志》曰:“寿丘若水,开原发系。”[51]“寿丘”“若水”,皆用黄帝相关典故。其次,其他鲜卑贵族,亦不乏祖述炎黄。东魏《于彧墓志》曰:“其氏族权舆,灵峰创构,盖开庆绪于西陵,发洪源于姬水。”[52]北齐《尉孃孃墓志》曰:“发颛顼之遐源,资有夏之苗裔,开基命爵,世酋漠表。”[53]《穆子宁墓志》曰:“盖有熊氏(即黄帝)之苗裔。”[54]于彧、尉孃孃、穆子宁,分别系出鲜卑“勋臣八姓”之万纽于氏、尉迟氏和丘目陵氏。最后,其他北族也同样如此。柔然人《闾详墓志》曰:“苗裔轩皇,繁伦代北。”[55]契胡人《尔朱元静墓志》曰:“其先盖夏后氏之苗裔。”[56]乞伏鲜卑人《乞伏保达墓志》曰:“其先盖夏禹之苗裔。”[57]匈奴人《独孤誉墓志》曰:“其先出自夏后氏淳维之后,南单于之苗裔。”[58]可见,东魏北齐北族,颇多以华夏上古帝王为祖先。
较诸东魏北齐,西魏北周的虏姓家族则呈现出新面貌。北周皇族宇文氏,系出宇文鲜卑,建立政权后,在祖源记忆塑造上颇下功夫。《周书·文帝纪上》曰:
其先出自炎帝神农氏,为黄帝所灭,子孙遁居朔野。有葛乌菟者,雄武多算略,鲜卑慕之,奉以为主。遂总十二部落,世为大人。其后曰普回,因狩得玉玺三纽,有文曰“皇帝玺”。普回心异之,以为天授。其俗谓天曰宇,谓君曰文,因号宇文国,并以为氏焉[59]。
北周宇文氏与北魏拓跋氏不同,自称炎帝神农氏后裔。除《周书·文帝纪》外,《孝闵帝纪》载孝闵帝元年(557年)正月壬寅诏曰:“予本自神农,其于二丘,宜作厥主。”[60]所谓“二丘”,指圆丘和方丘,为天子祭祀天地之处。北周皇帝自居神农之后,故二丘祭祀配以神农氏。《隋书·礼仪志》即称北周“圆丘则以其先炎帝神农氏配昊天上帝于其上”[61]。
对比《周书·文帝纪》载宇文氏起源与《魏书·序纪》载拓跋氏起源,不难发现二者叙述结构颇为相近,皆由“祖先渊源+世为北方诸部大人(君长)+姓氏由来”构成[62]。问题在于,十六国至北魏,北族政权之皇族多号称为黄帝后裔。例如慕容氏号称有熊氏(黄帝)后裔,北魏拓跋氏自居黄帝、昌意子孙。宇文氏为何自居炎帝神农氏后裔,而非黄帝呢?
事实上,宇文氏在北魏时期即溯源于黄帝。北魏孝昌二年(526年)《宇文善墓志》曰:“笃彼厥初,轩黄是系。”[63]同年《宇文延墓志》曰:“轩辕之苗裔,宇文大单于之后”,铭云“资元少典,启祚熊区”[64]。苏航指出:“至迟在北魏末年,宇文氏确已借单于而夤缘于黄帝了。”[65]北魏宇文氏祖述黄帝,很可能是对诸多鲜卑虏姓祖述黄帝潮流的顺应。至北齐与北周对峙,北齐宇文氏仍延续了这种做法。北齐天保七年(556年)叙述祖源称“披山之帝,疏彼长源”[66]。《史记·五帝本纪》曰:“天下有不顺者,黄帝从而征之,平者去之,披山通道,未尝宁居。”[67]“披山之帝”,正指黄帝。而且,宇文氏祖述黄帝,在华夏古史系统上,还有史可依。《魏书·宇文福传》《北史·匈奴宇文莫槐传》皆称宇文氏“其先南单于之远属”[68]。这一观点得到不少后世学人认同[69]。《史记·匈奴列传》称:“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维。”[70]据此,宇文氏当为夏后氏后裔,甚至溯源至黄帝。⑤西魏北周宇文氏,改变祖源,显然另有目的。
宇文氏祖述炎帝,《元和姓纂》曰:“鲜卑俗呼天子为‘宇文’,因号宇文氏。或云以远系炎帝神农有尝草之功,俗呼草为‘俟汾’,音转为‘宇文’。”[71]“宇文”即“俟汾”,鲜卑语义为“草”一说,得到周一良、姚薇元等学者认可[72]。宇文氏自居炎帝后裔,似当源自“宇文”鲜卑语义。然正如苏航指出:“然‘宇文’义‘草’,北魏已然,彼时既不废祖黄,西魏又何必改炎?”[73]近年,温拓和苏航,先后就宇文氏这一问题提出新说。二者皆认为宇文氏祖述炎帝,有着浓重的现实诉求,但具体又有所不同。温拓认为宇文氏自居炎帝后裔,旨在为魏周禅代服务。《史记·五帝本纪》称黄帝“代神农氏”成为天子[74],那么,黄帝后裔西魏拓跋氏(元帝)将帝位交还给炎帝后裔宇文氏,亦“具有法统合理性的”[75]。苏航则主张宇文氏改祖炎帝,是“西魏的周制改革中的重要一环”。在宇文泰的设计下,西魏君主拓跋氏与执政宇文氏好比西周之姬、姜二姓;拓跋氏与姬氏源于黄帝,宇文氏则当与姜姓一般源于炎帝[76]。二说为认识宇文氏祖述炎帝提供了新的见解,尤其苏氏之说颇有启发。西魏北周赐复虏姓,恢复拓跋鲜卑之“三十六国、九十九姓”,形成“以拓跋氏为中心”的“官族”[77],而作为“官族”之首的宇文氏,确实与西周之姜姓类似。宇文氏改祖炎帝,很可能与西魏政治格局中君相关系有关。无论如何,西魏北周宇文氏,确实自居炎帝后裔,并服务现实政治。
除宇文氏外,其他虏姓家族也存在祖述炎黄现象。北周《尉迟运墓志》曰:“公讳运,字乌戈拔,河南洛阳人。轩辕诞圣,则垂衣服冕;昌意秉恴,则降居藏用。”[78]尉迟运为西魏北周外戚大臣尉迟纲之子、尉迟迥之侄。《周书·尉迟迥传》曰:“其先,魏之别种,号尉迟部,因而姓焉。”[79]北朝尉迟氏,为北魏鲜卑“勋臣八姓”之一或于阗王族,而于阗尉迟氏可能亦源自鲜卑[80]。尉迟迥家族号称“魏之别种”,当属鲜卑。《尉迟云墓志》将轩辕(黄帝)和昌意追溯为尉迟氏祖先,当系自居“魏之别种”,接受了拓跋氏祖述黄帝、昌意的做法。再如《是云偘墓志》曰:“公讳偘,字宝国,其先出自轩辕,受氏于有魏太武皇帝,折侯真是云尚书,即君之十二世祖也。”[81]是云氏,见于《魏书·官氏志》,北魏太和中改为“是氏”,似为拓跋鲜卑联盟诸部,然李鸿宾推论是云偘家族出自高车[82]。《是云偘墓志》称“其先出自轩辕”,倘是云氏出自高车,则“鲜卑化”之高车家族也接受了拓跋氏、宇文氏祖述炎黄的做法。
北周代人虏姓家族,继承了北魏以来的趋势,以炎黄为祖先。然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往往仍使用虏姓,而未如北魏般改用汉姓。而且,宇文氏等虏姓家族也保留鲜卑身份,上引《周书·文帝纪》即称宇文氏曾长期作为鲜卑十二部落大人。这意味着炎帝、黄帝等华夏上古帝王已跨越虏汉界限,至少被汉人和鲜卑人共同认可为祖先。除鲜卑或“鲜卑化”人群外,入华粟特人也祖述黄帝。北周《安伽墓志》称:“其先黄帝之苗裔,分族因居命氏。”[83]安伽为入华粟特聚落首领,出自中亚布哈拉之安国,墓葬具有显著中亚粟特文化特点[84]。荣新江指出《安伽墓志》书写,应是“全部交给了汉地的文人”[85];而《安伽墓志》将粟特人安伽称作“黄帝之苗裔”,“是撰写《墓志》的汉人按照汉人墓志的习惯来写的,即所有的人都是黄帝的子孙”[86]。但这毕竟展现出时人将入华粟特人也视作黄帝后裔,可见炎黄作为各族共祖的范围扩大。
在各虏姓家族祖述炎黄的同时,西魏北周出现了一场看似为“汉化”逆流的赐复虏姓改革,即赐与胡汉诸将勋臣虏姓和恢复北魏迁洛代人虏姓。西魏大统十五年(549年),“初诏诸代人太和中改姓者,并令复旧”[87]。西魏恭帝元年(554年),又诏“以诸将功高者为三十六国后,次功者为九十九姓后,所统军人,亦改从其姓”[88]。例如西魏八柱国之李虎家族(李唐先世)改姓大野氏,十二大将军之杨忠家族(杨隋先世)改姓普六茹氏。
经过赐复虏姓,各家族在形式上表现出“鲜卑化”面貌。这与上述西魏北周炎黄祖先记忆,似呈现相反趋势。但事实上,赐与虏姓者亦以炎黄为祖先。比如北周李纶,赐姓徒河氏,然《徒河(李)纶墓志》曰:“系本高阳,祖于柱史”,铭词称“系自颛顼,源流伯阳”[89]。帝颛顼高阳氏为黄帝之孙,柱史(伯阳)即李耳(老子)。这正是对李姓家族先世的描述,《新唐书·宗室世系表》即称“李氏出自嬴姓”,为颛顼之后,至周代有李耳(字伯阳)[90]。显然,李纶家族虽被赐姓徒河氏,但并未遗忘李氏姓源。再如北周韦瓘,系出京兆韦氏,为韦敻子、韦孝宽侄[91],赐姓宇文氏。《宇文(韦)瓘墓志》曰:“若乃电影含星,轩辕所以诞圣;蜺光绕月,颛顼于是降灵”[92],将祖先追溯至轩辕、颛顼。据《新唐书·宰相世系表》,韦氏正为“颛顼孙大彭”之后[93]。上文指出,而韦氏赐姓宇文氏,却仍以黄帝、颛顼为祖先,而未像北周皇室般以炎帝为祖先,可见亦未抛弃原本的祖先记忆。
不过,也有家族在赐虏姓后,似放弃原先的祖先记忆。例如北周王云,“朔州人”,本姓王氏,被赐姓若干氏[94]。⑥《若干(王)云墓志》记叙族源曰:“崇基盘峻,灵源攸远,轩顼之余,涣乎史册。”[95]轩顼,即轩辕、颛顼,然王氏一般认为出自虞(妫姓)、商(子姓)或周(姬姓)之后裔[96],可上溯之黄帝、帝喾,而未见系出颛顼者。《若干云墓志》祖述轩辕、颛顼,很可能是对拓跋氏以黄帝、昌意为祖先的因袭或效法。这意味着汉人被赐虏姓后,可能改祖所赐虏姓之祖先,但他们同样追溯至炎黄。
西魏北周虏姓家族和获赐虏姓的家族,在日常政治和社会活动中皆使用虏姓,但在祖先记忆上皆以炎帝或黄帝为祖。前者通过祖述炎黄实现“中华”认同,而后者借助祖先记忆保存了本姓祖源。二者交织在一起,共同塑造了炎帝、黄帝作为西魏北周胡汉人群的共祖形象。显然,虏姓的使用,并未成为时人祖述炎黄和认同“中华”的阻碍。相反,通过赐复虏姓,关中的鲜卑、汉人、氐羌等各族得到了整合,形成陈寅恪所言“关陇集团”[97]。关中各族皆使用“虏姓”,又认同“中华”。这促使以炎黄为共祖的“中华”认同初具各族共同体意识。
三、北朝炎黄二帝“华夷共祖”地位的确立
北朝以皇族拓跋氏、宇文氏为首虏姓家族,将黄帝、炎帝追溯为先祖,推动他们形成“中华”认同。当然,这是一个随着时间发展不断深化的过程。北魏前期,拓跋氏自居“黄帝之后”,主要是将黄帝后裔身份与北魏历运土德联系在一起,尚未有意识地强调黄帝后裔与“中华”认同的联系。至孝文帝迁都洛阳,拓跋鲜卑走向“汉化”,“中华”意识也随之强化。以拓跋氏(元氏)为首的虏姓诸族,不仅改用汉姓、更籍河南,祖述炎黄的现象也渐增多,最终形成了虏姓诸族对黄帝后裔身份的共同心理认同,并延续至后世。至西魏北周,在赐复虏姓政策之下,胡汉人群恢复或被赐虏姓,在姓氏形式上呈现出“鲜卑化”面貌。但无论是代人虏姓家族还是接受赐姓者,仍将炎帝、黄帝等华夏上古帝王认作是自家祖先。在这种情形下,炎黄二帝实已跨越了虏汉界限,被不同民族共尊为先祖,意味着炎黄祖先记忆步入新的历史阶段。
黄帝、炎帝,作为华夏人群共同接受的祖先,至晚可追溯至东周初年。《国语·周语下》载周灵王太子晋即称夏、杞、郐、申、吕、齐、许等国“皆黄、炎之后也”[98]。近年,李锐指出东周初年周平王及其史官编制出“炎黄古史系统”,“很快被各诸侯国、王公贵族认同”,而“这一古史系统,综合了各种材料,通过黄帝、炎帝,兼及其子孙臣属,乃至诸蛮夷中愿意或被迫称臣服事诸夏的人之先祖,使他们成为当时华夏诸国之祖”[99]。换言之,在“炎黄古史系统”下,华夏诸侯国和趋于“华夏化”的蛮夷,都被视作炎黄子孙。显然,炎帝、黄帝为华夏祖先,并不仅就血缘上而言,更是从文化上来讲的。正如学人指出:“普遍意义上的炎黄子孙,是一个周礼指导下的文化构建,来源很早,是文化意义上的称谓。”[100]炎黄二帝,伊始即为华夏之“人文先祖”。
至太史公撰《史记》,开篇即为《五帝本纪》,将历史从黄帝写起。顾颉刚曾提出汉武帝独尊儒术促使“黄帝竟成为历史”[101]。但这恐怕是误解,司马迁的做法,当是对东周以降“炎黄古史系统”的继承。而司马迁的创新,在于将周边民族也正式纳入“炎黄古史系统”下。例如《越王句践世家》称:“越王句践,其先禹之苗裔,而夏后帝少康之庶子也。”[102]《匈奴列传》称:“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维。”[103]赵永春、刘月指,“司马迁将少数民族说成是炎黄子孙”,较前人更为详细、系统,“构建起了华夏汉族和少数民族都是‘炎黄子孙’的‘华夷一家’的一源论思想体系”[104]。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史记·秦本纪》称秦之先祖费昌“子孙或在中国,或在夷狄”[105],《楚世家》称楚之先祖穴熊之后“或在中国,或在蛮夷”[106],《魏世家》称魏之先祖毕公高后裔“或在中国,或在夷狄”[107],无疑是《魏书·序纪》“黄帝有子二十五人,或内列诸华,或外分荒服”之模板。
东周“炎黄古史系统”,可谓炎黄祖先记忆的第一阶段,将炎黄祖先限定为华夏和“华夏化”人群内。《史记》炎黄体系,则是炎黄祖先记忆的第二阶段,炎黄已成为华夏和周边民族之共祖。但这尚仅是汉人士大夫站在中原王朝的立场对周边民族的认识,例如汉朝匈奴恐怕未必认同自己是“夏后氏之苗裔”。然至十六国时期,炎黄祖先记忆发展到第三阶段,上述情况发生了转变。进入中原的周边民族,“先后卷入到逐步认同华夏文明及其历史传统的潮流中”,“自己追溯祖先时,多溯至炎、黄”[108]。匈奴刘渊即采用了《史记·匈奴列传》之说,承认“先夏后氏之苗裔曰淳维,世居北狄”[109]。前燕鲜卑慕容氏谓“其先有熊氏之(即黄帝)苗裔,世居北夷”[110],或追溯至高辛氏(帝喾)少子厌越[111];后秦羌人姚氏自称“其先有虞氏之苗裔,昔夏禹封舜少子于西戎,世为羌长”[112];后凉氐人吕氏“追尊吕望为始祖”[113];赫连勃勃“自以匈奴夏后氏之苗裔也,国称大夏”[114]。
十六国君主确立的祖先记载,至北朝得到了继承。北魏《吕达墓志》《吕通墓志》,皆出自后凉氐人吕氏[115],墓志称他们“盖神农之苗裔”,太公(吕望)之子孙[116];北齐《吕祥墓志》曰:“炎帝之苗裔,凉王光之六世孙”[117];东魏《慕容鉴墓志》称:“帝轩辕之遐胄”[118];北齐《赫连子悦墓志》叙述祖源称:“自文命(即夏禹)开大帝之基,淳维作引弓之长”[119]。上文提到乞伏鲜卑人《乞伏保达墓志》称“其先盖夏禹之苗裔”,可能也是十六国西秦已确立的。
北魏拓跋氏祖述黄帝,与上述十六国君主可谓同出一辙。就此来讲,北魏炎黄祖先记忆,是第三阶段之延续。在这一阶段,北族祖述炎黄,一来出于塑造正统性、合法性等现实政治需求,二来源自进入中原后渐趋“汉化”之文化诉求。罗新指出十六国北朝祖先追溯,“有否历史和文化的依据,尚待考证”,但当时“民族冲突、汇流、熔冶与化合进入到一个关键的时刻,这样的同源意识,无疑为历史绕过险滩提供了极宝贵的心理平台”[120]。
在十六国北魏各北族君主的祖源叙述中,炎帝、黄帝等上古帝王,子孙“或内列诸华,或外分荒服”。他们形成了一种华夷共享的黄帝子孙历史叙述模式———炎黄子孙中一支,迁居边地,走向“蛮夷化”,后又进入或返回中原,重新“华夏化”。在这种模式下,迁徙成为选择族属的重要原因。当然,北魏除皇族拓跋氏外,其他北方诸族也不乏祖述黄帝现象,较诸十六国时期,接受炎黄祖先的范围扩大了许多。这为炎帝、黄帝日后确立“华夷共祖”地位奠定了基础。北齐魏收撰《魏书·序纪》,即上承司马迁,“将黄帝的形象弘扬推广”,成为北朝胡汉诸族祖先,“放大成为人文初祖的形象”[121]。在上述模式下,北方诸族接受炎黄子孙身份,往往与“汉化”相表里,甚至渐脱离昔日民族认同。这意味着十六国北魏之炎黄祖先记忆,为华夏或“华夏化”夷狄所享有,认同炎黄子孙身份者一般走向“汉化”。正如陈寅恪指出,北朝时期胡汉之别,不在于种族,而在于文化[122]。“汉化”的北方民族君主或贵族,在文化上已是汉人。就此而言,十六国北魏的炎黄祖先记忆,尚未真正成为华夏与夷狄共享。
西魏北周,炎黄祖先记忆则又发展至一个新阶段,即未汉化之虏姓家族亦祖述炎黄,炎帝、黄帝真正意义上成为“华夷共祖”。西魏北周恢复虏姓,显示出来自以武川镇为主的北镇鲜卑和鲜卑化人群的“鲜卑”认同,在文化上是对孝文帝迁洛以降“汉化”的逆反。然而,以宇文氏为代表的鲜卑家族,祖述炎黄;被赐与虏姓(鲜卑姓氏)的汉人、氐羌诸族,亦祖述炎黄。炎黄祖先,已不再仅被华夏族和“华夏化”人群所认同,也不仅是为了追求正统性、合法性而做出的“功利性”认同,而被关陇地区鲜卑、汉人、氐羌、高车甚至是来自中亚的粟特人共同接受。炎帝、黄帝作为关陇地区“华夷共祖”正式确立。
四、结语
近代以来,“炎黄子孙”已成为“中国人”“中华民族”的代名词。然而,一些学者提出“炎黄子孙”是近代国家、民族建构的产物,是一种“想象的共同体”或“被发明的传统”。这种观点虽部分呈现了近代中华民族走向“自觉的民族”的一面,但并不符合古代中国的历史实际,“炎黄子孙”实为中国历史上各民族、各族群不断重构和扩充的文化认同[123]。自东周至北朝,炎黄祖先记忆即经历四个阶段:东周时期,炎帝、黄帝成为诸夏尊奉之祖先,是为第一阶段;西汉司马迁撰《史记》,以汉人史家之立场,将炎帝、黄帝描述为华夏和周边族群之祖先,开启炎黄祖先记忆的第二阶段;十六国至北魏,北族君主和贵族,伴随着“汉化”,亦祖述炎黄,将炎黄二帝作为华夏和“华夏化”夷狄祖先,是为第三阶段;西魏北周,关中鲜卑、鲜卑化人群、汉人、氐羌,皆祖述炎黄,但同时保存本族认同,炎黄二帝“华夷共祖”地位最终确立,是为第四阶段。
隋唐以降,炎黄二帝“华夷共祖”地位得到延续和扩展。首先,北朝以来进入中原的鲜卑、高车诸族,维持炎黄子孙身份认同。例如唐代《贺拔亮墓志》称:“在昔轩丘诞圣,弱水降贤。庆远灵长,龙光承祀。世号大人,奄荒朔代。”[124]贺拔氏系出鲜卑或高车,但墓志追溯族源至黄帝(轩丘)。开元三年(715年)《元温墓志》曰:“昔黄帝有子廿五人,或内列诸华,或外蕃荒服。昌意少子受封北土,分国镇摄,纳聘西陵,立号鲜山,降居弱水,后迁广汉,徙邑幽都。”[125]这更是遵循了《魏书·序记》之说。其次,唐代北方民族,不乏接受炎黄祖先的。比如突厥王族阿史那氏,在草原活动之际,存在狼祖传说的族源、祖源故事,但进入中原后,渐确立起炎黄子孙身份。《元和姓纂》记叙突厥阿史那起源:“夏后氏后,居涓兜牟山,北人呼为突厥窟历。魏晋十代为君长。后属蠕蠕,阿史那最为首领。”[126]最后,北朝炎黄祖先记忆模式,影响深远。辽代契丹人即受鲜卑影响,自称“炎黄子孙”,而且也不否认汉人也是“炎黄子孙”,认为契丹人和汉人都是“炎黄子孙”,都是“中华一体”中成员[127]。
近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提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是先人们留给我们的丰厚遗产,也是我国发展的巨大优势”,“我们辽阔的疆域是各民族共同开拓的”,“我们悠久的历史是各民族共同书写的”,“我们灿烂的文化是各民族共同创造的”,“我们伟大的精神是各民族共同培育的”[128]。炎帝、黄帝作为中华民族共祖,同样是历史上各民族共同确立的。而北朝正是炎黄祖先由“华夏先祖”到“华夷共祖”发展的关键时期,并影响到后来突厥、契丹诸族。这令“中华”认同成为超越华夷各族之上的高层次认同,推动了历史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自觉和发展。
注 释:
①“虏姓”家族,指北朝以鲜卑为主的北方诸族家族.
②皇甫谧《帝王世纪》曰:“母曰庆都,孕十四月而生尧于丹陵,名曰放勋。”参见(晋)皇甫谧撰,陆吉点校.帝王世纪(卷2)五帝[M].济南:齐鲁书社,2010:12.
③侯愔族属稍复杂,他号称“燕州上谷人”,但据墓志,其愔曾祖曾任“代郡太守”,代郡作为拓跋氏根本之地,任太守者一般出自代人虏姓。虏姓侯氏往往攀附上谷侯氏,最典型者为北魏侯刚家族。参见罗新,叶炜.新出魏晋南北朝墓志疏证[M].北京:中华书局,2016:224.
④《王真保墓志》文末署为“大赵神平二年岁次己酉十一月戊寅朔十三日庚寅记”。“大赵神平”当为北魏永安三年(530年)王庆云政权年号。参见陈仲安.王真保墓志考释[A].武汉大学中国三至九世纪研究所编.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1辑)[C].1979:12-15.
⑤《史记》卷2《夏本纪》曰:“禹者,黄帝之玄孙而帝颛顼之孙也。”参见(汉)司马迁.史记(卷二)夏本纪[M].北京:中华书局,2013:63.
⑥若干云,贠安志等认为本姓王氏,但也有学者不赞同。参见贠安志编.中国北周珍贵文物———北周墓葬发掘报告[M].西安: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1993:73.墓志称“涿郡王尊、平陵公仲,即公之先也”,盖指西汉涿郡王尊、平陵王嘉(字公仲)。此虽显系伪冒,但可推知志主本姓王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