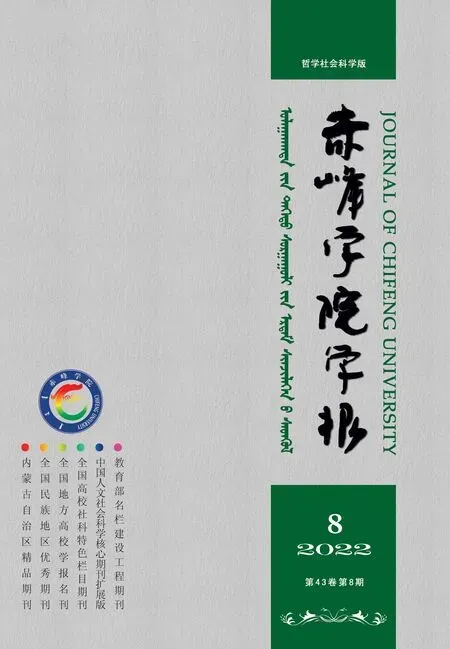中国古代北方民族政权共同体意识研究
杨 军,徐 琦
(吉林大学 文学院,吉林 长春 130012)
关于中华民族共同体思想的研究可以追溯至梁启超,其在《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中提出中华民族是由多元结合而来的一个大民族[1]。傅斯年进一步阐明该思想,1935年其发表《中华民族是整个的》一文,强调在大一统思想与大一统政治推动下,“我们中华民族,说一种话,写一种字,据同一的文化,行同一伦理,俨然是一个家族”[2]。之后傅斯年又对该理论进行补充,在强调整体的前提下,承认在中华民族中也存在各分民族[3]。顾颉刚在1939年发表《中华民族是一个》一文,引发激烈的学术争论,同时也促进相关概念清晰化[4]。张博泉具体考察中华民族发展历程,将其分为前天下一体、天下一体、前中华一体、中华一体等四个阶段,重点研究北方民族政权与中华一体的关系,及北方民族政权在中华民族形成过程中的贡献[5]。上述研究主要是论证中华民族的整体性,对于北方民族如何参与构建中华民族则较少涉及。故本文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对我国古代北方民族政权共同体意识演变发展过程及其参与构建中华民族过程进行系统考察。
一、一体二元:秦汉时期
先秦时期已对“天下”有较为清晰的解释,《礼·曲礼下》记载“君天下,曰天子”[6],郑玄注“天下,谓外及四海也”[7],《尔雅·释地》中将四海解释为“九夷、八狄、七戎、六蛮”[8],可知天下这一概念由中国与四海构成,中国为海内华夏,四海为边境四夷。包括华夏与四夷的“天下”也被认为是一个共同体,如子夏提出“四海之内,皆兄弟也”[9],荀子则更为明确地提出“天下一家”主张,提出“四海之内若一家,通达之属莫不从服”[10]。可见“天下一家”“天下一体”思想在先秦时期已经出现。
秦汉建立起统一多民族国家以后,“天下一家”“天下一体”思想逐渐被认同。贾谊提出“凡天子者,天下之首,何也?上也。蛮夷者,天下之足,何也?下也”[11],彭丰文据此认为,贾谊将天子与蛮夷比作身体的首、足以区分尊卑,但仍将二者放置于同一个整体当中,体现了贾谊夷夏一体、天下一家的观念[12]。司马迁《史记》体现出华夏与四夷同祖同源的思想,将四夷祖先追溯为黄帝后裔,从而将四夷与华夏都置于同一个以黄帝为始祖的血缘世系之中。如果说上述观念仍属于一家之言,那么西汉中期盐铁会议中士大夫与民间文人关于“天下一体”的讨论则可以代表当时儒家知识分子的共识。虽然双方关于如何解决边境问题看法不一,但都将包含夷夏在内的“天下”视为一个整体,大夫一方提出“故王者之于天下,犹一室之中也”[13],文学一方也认为“今九州同域,天下一统”[14]。可见代表官方的士大夫与代表民间知识分子的文学都认同“天下一体”观念。
汉朝统治集团也将“天下一体”观念运用于处理其与匈奴的关系中,并在此过程中促进了匈奴共同体意识的觉醒。匈奴统治集团的共同体意识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关于匈奴帝国内部共同体的构建,二是包括匈奴与汉在内的共同体的构建。
冒顿单于在给汉文帝的国书中提到,“定楼兰、乌孙、呼揭及其旁二十六国,皆以为匈奴。诸引弓之民,并为一家”[15]。楼兰、乌孙等“国”“并为一家”,可见其存在高于“国”的共同体观念。而匈奴统治西域,即是将其合并诸“国”为一体的政治观念付诸实践。匈奴采取定期朝会、和亲、设置僮仆都尉、征收赋税、纳质、驻兵屯田、遣使监国、匈奴诸王驻牧西域等措施管理西域[16],表明匈奴在不断推动共同体理念成为现实。而这一切的目的是“皆以为匈奴”,即打造包含多民族多国的匈奴草原帝国共同体。
汉文帝给单于的国书中说“汉与匈奴约为兄弟”[17],而在韩昌、张猛与呼韩邪单于签订的盟约中提到“自今以来,汉与匈奴合为一家”[18],汉与匈奴约为兄弟,构成了“一家”,汉匈双方都认可这样一个共同体,从中可见匈奴统治集团的共同体意识。值得注意的是,汉匈共同认可该共同体中存在汉匈“二元”。在汉文帝给匈奴单于的国书中提到“先帝制:长城以北,引弓之国,受命单于;长城以内,冠带之室,朕亦制之”[19],汉朝方面认可匈奴是“一体”中的一元。在王莽干涉匈奴内部事务时,匈奴单于反驳:“孝宣、孝元皇帝哀怜,为作约束,自长城以南天子有之,长城以北单于有之”[20]。可见匈奴方面也同样认同自身是“一体”中的一元。
基于上述可知,虽然“天下一体”概念是汉朝人的一种政治理念,但在与匈奴交往过程中,汉朝人运用“天下一体”观念处理汉匈关系,使得匈奴在此过程中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共同体理念也逐渐植根于匈奴统治者心中。在“一体二元”形式之下,双方通过战争、和亲、互市等方式,增加民族互动频率,推动民族融合。
二、一体多元:魏晋南北朝时期
魏晋南北朝时期,匈奴、鲜卑、羯、氐、羌等北方少数民族南下,先后在汉地建立以北方民族为统治民族、汉族为主体民族的多民族政权,北方民族地位发生变化,其共同体意识也发生了变化。出身氐族的前秦皇帝苻坚提出“方将混六合以一家”[21],北魏太尉长孙嵩及议郎博士等二百七十九人在讨论吐谷浑问题时提到“四海咸泰,天下一家”[22],可见北方民族政权已经明确提出“一体”意识,并在构建与巩固多民族共同体方面做出新实践。
其一,继承与发展儒学。匈奴刘渊“幼好学,师事上党崔游,习毛诗、京氏易、马氏尚书,尤好春秋左氏传、孙吴兵法,略皆诵之”[23]。鲜卑慕容皝“雅好文籍,勤于讲授,学徒甚盛,至千余人”[24]。正是由于许多少数民族统治者有着较高儒学素养,他们也致力于兴办儒学教育,前赵刘曜设立太学、小学,选取13岁至25岁的一千五百人入学学习;前燕慕容皝“立东庠于旧宫,以行乡射之礼,每月临观,考试优劣”[25],可见其对于儒学教育的重视;后秦姚兴时,太学已有数万人的规模。北方民族统治者尊崇儒学,重用汉族士大夫,使儒学在北方得以存续和发展,北方民族与汉族有了共同的思想基础。
其二,运用天命观证明“正统”。随着北方少数民族统治的多民族政权的建立,北方民族的民族意识发生变化,开始对传统华夷观发出质疑,否定以华夷作为能否为帝王的标准,运用天命观确立新标准。刘渊提出“夫帝王岂有常哉,大禹出于西戎,文王生于东夷,顾惟德所授耳”[26]。慕容廆在安抚降将高瞻时说:“君中州大族,冠冕之余,宜痛心疾首,枕戈待旦,奈何以华夷之异,有怀介然。且大禹出于西羌,文王生于东夷,但问志略何如耳,岂以殊俗不可降心乎”[27]。北方民族统治者打破了以往戎狄不可作天子的狭隘民族观,进一步破除夷夏之别。
另外,采用“五德始终说”以及编造符瑞也是北方民族统治者塑造自身正统形象的重要方式。五德始终说是北方少数民族政权进入华夏历史序列的重要方式,前赵开国君主刘渊自称“汉氏之甥,约为兄弟,兄亡弟绍,不亦可乎?”[28]以延续汉朝的名义为其建立的少数民族政权争取合法性。刘曜在称帝后改变了刘渊延续汉朝、排斥魏晋的做法,确立前赵承晋为水德,石勒也以后赵为水德。前燕建立后则“承石季龙水为木德”[29],承认后赵的正统性。从此,“胡族政权纳入到华夏历史序列中,就成为既成事实,是历史而不再仅仅是现实政治,这为北方胡族政权的华夏化,奠定了合法性方面的基础”[30]。
其三,构建北方民族与华夏族的同祖同源。司马迁《史记》构建“以黄帝为远祖的世系相寻、血缘相通的五帝系统”[31],并将此系统与政权合法性挂钩。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北方民族从中得到启发,为证明自身正统性,攀附黄帝世系,重新构建自身的族源传说。《十六国春秋》中记载,刘渊“新兴匈奴人,冒顿之后也,先夏后氏之苗裔曰淳维”[32]。《晋书》中记载,慕容鲜卑“其先有熊氏之苗裔,世居北夷,邑于紫蒙之野,号曰东胡”[33],《十六国春秋》则记载,“昔高辛氏游于海滨,留少子厌越以君北夷,邑于紫濛之野,世居辽左,号曰东胡”[34]。尽管《晋书》将慕容鲜卑记为黄帝苗裔,《十六国春秋》将其记为帝喾后裔,但从本质上而言都将慕容鲜卑纳入了黄帝世系之中,拓跋鲜卑则是昌意少子的后裔,昌意即黄帝之子。《晋书·符洪载记》提到,建立前秦的氐族“其先盖有扈之苗裔,世为西戎酋长”[35],建立后秦的羌族亦自称为有虞氏之苗裔。由上述可知,匈奴、鲜卑、氐、羌等北方民族构建了与华夏族同祖同源的始祖神话,将本民族纳入黄帝世系之中,以证明夷夏同为黄帝后裔,北方民族与汉族有了共同的心理认同。
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民族在明确提出“天下一体”的前提下,通过继承与发展儒学、运用天命说塑造正统形象、构建华夷同祖同源等方式,推动华夷之别的消除,进一步加强民族认同,为此后“天下一家”的实现奠定了共同的思想基础以及共同的心理认同。
三、天下一家:从隋唐到辽金
唐朝统治者在“华夏一家”的基础上,否定“先华夏而后夷狄”的民族不平等观念,强调华夷平等,唐太宗明确提到:“夷狄亦人耳,其情与中夏不殊。人主患德泽不加,不必猜忌异类。盖德泽冾,则四夷可使如一家”[36],后又强调“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37],否定以往“贵中华,贱戎狄”的民族思想,承认夷狄与华夏为平等子民。正是由于隋唐统治者这种更为开放进步的民族思想,使得“天下一家”的政治理想成为现实。贞观四年,“四夷君长诣阙,请帝为天可汗。帝曰:‘我为大唐天子,又下行可汗事乎?’群臣及四夷皆称万岁。是后以玺书赐西北君长皆称天可汗”[38]。唐太宗既是华夏之主也是夷狄之君,华夏与夷狄构成一个共同体。由契丹与女真等北方民族为统治民族的辽金则继承与发展了唐代“天下一家”的格局。隋唐至辽金时期,北方民族不仅承认自身为该民族共同体中的一部分,还积极参与其建设,推动该共同体的发展与繁荣,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北方民族的民族思想发生变化。至隋唐时期,北方民族祖源追溯不再刻意追溯至黄帝世系,如记载突厥“盖古匈奴北部也”[39],契丹“本东胡种,其先为匈奴所破,保鲜卑山”[40]。由此可以看到,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民族统治者塑造“华夷同祖同源”的成功,“华夷同祖同源”已经成为华夷各民族的共识,北方民族在这一共识之下直述祖源,恰恰反映出北方民族承认自己与华夏民族处于一个共同体中,同为这个民族共同体中的一部分,已经不再需要攀附祖源来加以证明。
至辽金时期,构建该民族共同体的主导者由汉族转为契丹与女真,契丹与女真都认同存在超越各自政权的多民族共同体即中国。一方面,辽金明确自称为中国,完颜亮嫡母徒单氏在劝其不要伐宋时说:“今又兴兵涉江、淮伐宋,疲敝中国”[41],是以金朝为中国。另一方面,辽金同时也承认宋为中国,如,“辽人敕其边吏曰:‘中国相司马矣,切无生事开边隙’”[42],中国显然指宋。在同为中国的前提下,辽金将自身与宋归为中国这一共同体的两部分。辽自称为北朝,称宋为南朝,如1052年辽遣使如宋,“其国书始去国号,而称南、北朝”[43],“辽人无论是沿袭当时南北方位互称南北并立政权为‘南北朝’的习惯,还是意欲提高自己以取得和北宋对等地位以及后来意欲凌驾于北宋之上而自称‘北朝’,都具有强调‘南朝’、‘北朝’是一家的用意”[44]。金人更为明确地提出:“念两朝通和,实同一家”[45]。辽金统治者明确将自身与宋都纳入“一家”这一民族共同体中,北方民族共同体意识得到进一步体现与发展。
二、北方民族在政治上积极参与建设民族共同体。唐王朝在北方建立多个羁縻府州用以管理少数民族,将原本的部落首领册封为都督、刺史,北方民族通过这一特殊制度被纳入一体统治,并参与建设这一民族共同体。另外,北方民族也为唐王朝的稳定繁荣输出大量人才,如突厥处罗可汗之子阿史那社尔奉命征讨龟兹,获得胜利,西域诸国纷纷内属,唐朝边境得以西拓。另一方面,北方民族积极维护民族共同体的稳定。安史之乱爆发以后,“回纥遣其太子叶护领其将帝德等兵马四千余众,助国讨逆”[46],在平叛中发挥了重大作用。辽金则采用“因俗而治”的民族管理政策以及同化政策,使得辽金控制下的各民族成为一个实际意义上的民族共同体。同时,辽金政权所控制的各民族,也积极参与该民族共同体的构建。如辽征服渤海国以后,一批渤海国士人选择入仕辽,尤其是在圣宗朝以“渤海旧族有勋劳材力者叙用”为原则[47],采取一系列用人政策后,进一步吸纳渤海士人加入辽代官僚集团,为辽的发展做出重大贡献。在金对宋的战争中,也出现了耶律怀义、耶律涂山、耶律马五等一批契丹族出身的将领担任重要职位。
三、北方民族统治者通过与其他民族统治者构建亲属关系以维护民族共同体。“和亲”一直以来被视为民族交往的重要方式,通过构建姻亲关系,使双方统治者成为实质上的“一家”,同时也使得两个民族共存于一个共同体之中。隋唐时期,北方民族早已具有“天下一体”的意识,并通过求亲的方式使自身更好融入民族共同体。隋文帝时,突厥沙钵略可汗之妻,即北周千金公主,“自请改姓,乞为帝女”[48],隋文帝赐公主杨姓,并封为大义公主,沙钵略可汗与隋文帝形成翁婿关系,在沙钵略可汗致隋文帝的国书中提到:“皇帝是妇父,即是翁,此是女夫,即是儿例。两境虽殊,情义是一。今重叠亲旧,子子孙孙,乃至万世不断,上天为证,终不违负。此国所有羊马,都是皇帝畜生,彼有缯?,都是此物,彼此有何异也!”[49]突厥沙钵略可汗希望通过构建姻亲关系,使得隋与突厥形成彼此无异的一体。唐朝时,后突厥、薛延陀、回纥等北方民族也都曾主动向唐朝求亲,与唐王室构建亲属关系,进而使民族共同体更为紧密。
辽金统治者与其他民族统治者构建亲属关系的形式主要分为真实与虚拟两种。真实亲属关系构建主要是通过和亲构成姻亲关系,如辽曾三次与西夏和亲,将辽朝公主嫁给西夏统治者,而金也曾将岐国公主嫁给成吉思汗。另一种则是构建虚拟的亲属关系,如辽金与宋约为兄弟之国、叔侄之国、伯侄之国,进而构建不存在血缘关系与姻亲关系的虚拟亲属关系。隋唐至辽金时期,北方民族统治者积极与其他民族统治者构建或真实或虚拟的亲属关系,既表明北方民族对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认可,也推动了北方民族更好地融入这一民族共同体。
四、多民族一体:元与清
元朝疆域辽阔,统一了北方草原地区与南方农耕地区,使身为游牧地区与农耕地区共主的元朝皇帝有着不同于以往君主的边疆治理政策。元朝“在很大程度上突破了夷夏有别、内实外虚的传统,采取了直接的更加积极的统治方式,将所谓羁縻关系实质化”[50]。一方面,在少数民族地区设立同内地一样的行政制度,以宣政院、行省、宣慰司等机构对边疆民族地区实行直接管理,当地户籍需要上报中央,边疆地区编户也需要承担赋税徭役。在边疆地区广设驿站,使元朝中央对于边疆民族地区的控制加强,同时为边疆各民族之间往来提供了便利。另一方面,儒学成为各民族共同的思想基础。以忽必烈为代表的一批元朝统治集团成员对于儒学大力推崇,重用儒士、发展儒学教育、翻译儒学经典、恢复科举考试,使得儒学在元朝统治下的各族中广泛传播,儒学不再只被汉族掌握,在这一时期,出现了一批少数民族儒学大家,如畏兀儿人阿鲁浑萨里、汪古人马祖常等,儒学成为多民族的儒学。共同的政治制度以及共同的思想基础使元朝得以构建出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共同体,辽金时期的“一家两国”被统一为“一家一国”。
清朝强调“满汉一家”“满蒙一家”,进一步巩固元朝所开创的统一中华民族。满人入关之前,已经注意到建立多民族共同体的重要性,皇太极认为“满汉之人,均属一体,凡审拟罪犯、差徭、公务,毋致异同”[51]。满人入关以后,满汉民族矛盾尖锐,为解决更为复杂的民族问题,清朝统治者进一步宣扬“满汉一体”观念。顺治皇帝明确说:“今欲联满汉为一体,使之同心合力,欢然无间”[52]。康熙继承了“满汉一体”思想,认为“朕于旗下汉人,视同一体,善则用之,不善则惩之”[53],“满汉俱系朕之臣子,朕视同一体,并不分别”[54]。同时,康熙提出“中外一体”思想,认为“朕统御寰区,一切生民,皆朕赤子,中外并无异视”[55],并在康熙三十年宣布不再修理代表内外分界线的长城,进一步消除中外之别,巩固了多民族共同体。
雍正朝上承康熙时期的繁荣景象,下启乾隆时期的盛世,其大一统思想有着重要意义。雍正皇帝于《大义觉迷录》中批判曾静的“夷狄禽兽论”,认为“盖识尊亲之大义,明上下之定分,则谓之人;若沦丧天常,绝灭人纪,则谓之禽兽。此理之显然者也”[56],强调应该以是否遵守伦理纲常来区分人禽,而不是以狭隘的民族观念将夷狄视为禽兽。并以天命说反驳曾静,提出:“皇天无亲,惟德是辅”[57],强调德行才是能否为皇帝的唯一标准。并提出“天下一家,万物一源,如何又有中华夷狄之分?”[58]打破夷夏之别。雍正十一年,雍正皇帝进一步对“中外一家”思想进行详细阐释:“中外者,地所画之境也;上下者,天所定之分也。我朝肇基东海之滨,统一诸国,君临天下,所承之统,尧舜以来,中外一家之统也;所用之人,大小文武,中外一家之人也;所行之政,礼乐征伐,中外一家之政也”[59]。雍正皇帝以一位少数民族统治者希望建立多民族共同体的角度出发,生动解释“中外一家”观念,提出了具有进步意义的民族观念,这是千百年来众多北方民族政权不断努力的结果,是千百年来众多北方民族政权共同体意识演变发展而来的思想结晶。
清朝统治者有着更为进步的民族观念,并在施政中将“一体”观念贯彻实施,“从思想文化上以‘儒化’促进‘一体’,用人制度上以‘共治’促进‘一体’,经济生活上以‘互补’促进‘一体’,民族关系上以‘通婚’促进一体”,宗教信仰上以‘包容’促进‘一体’等方面入手,全方位地建构多民族‘一体化’体系”[60]。至清末,中华民族已然基本形成。
元与清建立了以北方民族为统治民族的全国范围的大一统政权,这一时期的共同体意识更为成熟与包容,夷夏与内外彻底被打破,并且共同体意识得到了最为普遍且深入的认可,同时,这一时期共同体意识的实践范围包括了更为广阔的疆域以及更多的民族,使得元与清所构建的“多民族一体”在思想上与实践上超越了前期的“一体多元”与“天下一家”,为中华民族的最终形成奠定基础。
结语
纵观北方民族政权共同体意识演变发展过程,可以看出,北方民族共同体意识由模糊体现到明确自我表述,同时在将该意识付诸实践方面,也由汉族主导、北方民族参与转变为北方民族主导并主动构建民族共同体,这些转变与北方民族历史地位的变化及其文明程度的提高有着密切联系。
透过我国古代北方民族政权共同体意识演变发展过程,可以看到我国古代北方政权积极参与及巩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构建,并在此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北方民族始终积极主动参与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北方民族通过多种途径与多种方式与中原汉族交融,为中华民族的形成不断注入新鲜血液。其二,北方民族破除了“内华夏而外夷狄”的狭隘民族思想,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奠定了思想基础。其三,北方民族政权从多方面促进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首先,北方民族政权积极开发边疆地区,同时在学习中原先进技术的基础之上改进生产工具,使得边疆地区生产力水平有了较大进步,极大地加强了边疆地区与中原地区在政治经济上的联系。再者,北方民族文化极具本民族特色,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北方民族将本民族文化与中原汉族文化相结合,为中华文化增添活力。最后,北方民族在中外交流过程中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讲话提出,我们辽阔的疆域是各民族共同开拓的,我们悠久的历史是各民族共同书写的,我们灿烂的文化是各民族共同创造的,我们伟大的精神是各民族共同培育的[61]。而对于我国古代北方民族政权共同体意识演变发展过程的探讨,则更有助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使得各民族亲如一家,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共同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