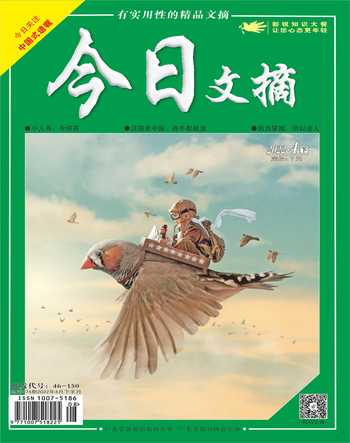中国人的遗嘱里有什么?

遗嘱,是一个人一辈子人际关系的体现。中国几千年的人情社会,法定继承始终占据绝对主导地位。2013年至今,中华遗嘱库登记保管着20余万份普通中国人的遗嘱,它们被封存于档案袋里,直到某一天,遗嘱执行人将其取出,它们才会从封存中被唤醒。
中国式遗嘱
在中国人订立遗嘱的过程中,遗嘱咨询师见过各种各样的中国家庭中的暗流。
80后遗嘱咨询师马小平曾接待过一对夫妻,填写申请表时,夫妻俩都表示将所有遗产留给唯一的女儿。签字的时候,马小平再三与他们确认,她注意到男士轻咳了几声,眼神游离。隔天,男方单独找过来,小声说他还想把其中的一部分留给外面的儿子。
马小平见怪不怪,告诉他,在正式签署、录像环节,密室里只留公证人员和立遗嘱的人,子女统统都得出去等着,就算是老伴,也不能待在屋子里。
立遗嘱是人们生前面对死亡的准备。人们对身后财产的安排,对家人、这个世界最后的话语,浓缩为几张纸,编上编号,封存于柜子深处,身后事如何安排秘密,只有当事人知道。
在中国,你能从遗嘱背后看到家庭,看到中国传统血亲家族制度。通常,人们会在继承人一栏写自己的伴侣、儿女的名字,有的还会写上外孙子、外孙女。
问过眼前这对老年夫妻的年龄、婚史、生育史等常规问题之后,马小平递给老人一张纸,要求他们把主要财产写下来,但最关键的就两行字:房产和存款留给谁,谁当遗嘱的执行人。
这对老年夫妻,异口同声地回答,财产留给儿子。这仅是一个开始,为了实现立遗嘱人的利益最大化,帮助他们规避可能出现的风险,马小平还会多问一句:“您二位要不要考虑先把继承权留给对方,等二老都离开后,再给孩子?”说完,她阐述理由,一方过世一方在世的情况下,过早将遗产留给孩子,导致自身晚年凄凉的例子,也有不少。
问题抛出去,男人和女人态度迥异。多数时候,男方欣然接受,表示愿意将自己财产先留给爱人,至于爱人怎么分尊重她的意见。女方的顾虑往往更多,比如眼前这位妻子,她问马小平:“如果我先走,对方再找一个,是不是遗产也有那女人一份?”得到肯定的回答后,女方马上跳起来:“肯定不行,我不接受,我们俩的份额都要百分百留给孩子。”
在中华遗嘱库工作久了,马小平见惯了这类事。她梳着干净利落的短发,说话理性、直接,擅长用缜密的法律和滴水不漏的逻辑回答登记人各种问题。想让遗嘱具有法律效力,就需要用严肃的“法言法语”。她告诉女方:每个人都只能处理属于自己的那一份合法财产,同睡一张床的夫妻,也干涉不了对方最后的决定。
“我太了解他了,他们家有长寿基因,活到90岁没问题,我肯定比他走得早。”女人意味深长地望向她的老伴,她表示他们还要再商量一下。
订立遗嘱是件专业性很强的事,流程也很严格。遗嘱人先要提交申请表,按照预约时间前往遗嘱库办理遗嘱咨询和起草,之后接受精神鉴定。待遗嘱内容确认无误后,交由老人一页页签字,按手印。最后,遗嘱人还必须走进密室,在两位工作人员的见证下,对着镜头把自己所写的遗嘱清清楚楚读一遍。之后,遗嘱封印,遗嘱证交到老人手中,整个流程才算完成。
面临生死关口的时候,人们记挂、叮嘱的往往就是此生最在意、最放不下的人和事。有时,这份牵挂牵扯到了利益,立遗嘱者的执念也会体现在遗嘱之中。
立遗嘱的人各有各的考虑,只要不违背公序良俗,都是遗嘱咨询师无权干预的私事。
遗产争夺现象的种种
遗嘱咨询师见识过因为遗产分配亲人反目的各种情境。小女儿为抢房产,与兄长闹上法庭;老人将遗产留给保姆;儿媳妇不满没有自己的一份,逼着老人更改遗嘱。这类情节因为发生太多,甚至无法被称为奇遇。
一位66岁的大爷一早就来北京登记处门口排队,他从包里取出各项证件,急迫地说自己要来撤销遗嘱。他无儿无女,老伴去世得早,家中有兄弟五人。2019年他立遗嘱,将自己的一套房子给到三哥的女儿,又把存款留给五弟。
回去后他急火火地把安排告诉家人,得到他遗产的侄女几乎天天打电话,问候:“吃饭了没?身体好不好?”
变故发生在2021年年初,三哥去世,居住的老宅原为老一辈的祖产,父母没有留遗嘱,房子的产权成为家族争夺的核心。它爆发得突然,直指人性中不堪的一面,三哥的女儿、老人的侄女坚持走法律诉讼,与家人撕破脸。老人无法理解,他觉得侄女这么做不讲情分,“她明明已经得到了我的财产,还争什么呢”,这让他很伤心。
“我看透了,把房子卖了,谁也不给,吃光花光。”撤销完遗嘱,他扬长而去。
这类遗产争夺的极端事件,崔文姬见过很多——在中华遗嘱库,她负责操作实施具体的法律事务,帮助遗嘱人起草遗嘱内容,为他们做精神鉴定,录制影像,也包括后期提取遗嘱。
当一个人过世,银行账户冻结,财产也冻结了。不管遗产继承人之间有没有纠纷,都需要先去公证处公证——拿上死亡证明、遗嘱证等材料一起呈交,审核过后,全体继承者认同,签字,这之后才能将父辈的财产过户到自己名下。一旦得不到遗产的后辈提出异议,遗产认证就变成了诉讼,亲人之间免不了一场官司。
2017年崔文姬刚入行时,还是个涉世未深的小姑娘,她以前从没意识到,为了争夺遗产,家人能反目成什么样。“不要在利益面前考验亲情”,如今这句话成为人生警句,总被遗嘱咨询师拿出来给遗嘱人讲。
情感的天平
在与众多遗嘱人聊过之后,杨颖仪发现,遗嘱定立这一行为给不同人带来的牵绊影响,远比想象的还要复杂。她是中华遗嘱库广州区的大家长,也是90后,她认为订立遗嘱是人在走向死亡前最后的自由。
亲人之间谁对你好或者是不好,都能体现在遗嘱里。但最终的抉择并非那么容易,尤其是老人,他们总是“牵扯”很多,有时会考虑哪个孩子更孝顺,有时又会牵扯哪个孩子情况差点。
杨颖仪曾接待咨询一位老人,在遗产分配时她左右为难。她有一儿一女,女儿40岁离了婚没有孩子,这些年母女俩相依为命,自己全赖女儿的照顾。老人想把自己所有的财产留给女儿,以保障女儿的后半生。但同时她预感到她的儿子大概率不会满意这样的结果,儿子是个强势且自私的人。
立遗嘱的时候,老人还是将财产的一定份额分给了儿子,大部分留给了女儿,她写下书信说明这样分配的原因。“妈妈希望你能理解,别留下兄妹之间将来的不愉快。”她写道,想了想又补充:“如果你想通了,我希望你能把自己的份额留给妹妹,你自己做决定吧。”她把最后的选择权留给了儿子。
即使立完了遗嘱,也可以随时自行更改,并不是一次性买卖。但对于老年人来说时间不多了,他们在继承人的选择和财产分配上,慎而又慎。年轻人不会。在决定立遗嘱之前,他们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继承人也往往只包括“最重要的那个人”。
一位18岁的女大学生找到杨颖仪来立遗嘱。交流中她发现女孩很有想法,她靠拍购物网站的平面模特攒了一笔钱,她决定将这笔财产全部留给自己的母亲。女孩说她的父亲瞧不起她,说她是出卖色相赚的钱,她因此恨透了父亲。“他老了我也不养他。”女孩愤愤地说。
继承者写谁的名字,谁先继承谁后继承,谁分得多谁分得少,人们心里都有一杆情感天平,以此对所爱之人做一次排序。
一个现象是,来立遗嘱的人,女性比男性多,比例接近6:4。重组家庭的女人来立遗嘱的情况很多,她们用遗嘱前置婚姻风险,逃离人财两空的窘境。
一位准备再婚的中年女性,第一时间找到杨颖仪问如何立遗嘱。她与前夫有一个孩子,现在这位也带着一个孩子。她把自己名下的房子和存款都留给了自己的孩子,她担心自己万一出现意外,现在的丈夫会偏袒亲生的,自己的孩子会成为备受欺负的“灰姑娘”。
“我不相信爱情了。”女人说,只有把钱攥在自己手里,才能带给她足够的安全感。
爱的表达
旁观每个家庭错综复杂的故事,遗嘱咨询师会对来订立遗嘱的人产生共情,这种共情推动着遗嘱咨询师站在不同人物的角度,去理解人们立遗嘱的初衷。
看多了人性的复杂,马小平对待感情也变得很理性。“就算是亲哥哥找我借钱,我也会让他写借条。”她说。
2019年马小平也立下了遗嘱,继承人写了母亲。
但中国人的遗嘱里,有时也写满了爱。
马小平接待过一对70岁的夫妻,他们唯一的女儿当时47岁,是个坚定的不婚族,老太太想把自己的遗产留给女儿。因为女儿的婚事,母女关系一直拧巴着。“相亲不知道安排了多少,她都看不上,就是不结婚。”话题开启,老太太语气里满是焦急。
“你女儿是不是从小到大都自己拿主意?”马小平询问道。“你说得太对了。”老太太回答,有一天她无意中看到女儿房间里的骨髓捐献书,吓坏了,差点昏过去。
马小平劝老太太放宽心,和老太太说起自己的情况:她36岁了,也单身,过得很自由,她说这一代年轻人有自己的想法,婚姻不是必需。一番相劝,老太太点点头,说自己想开了。老太太是有文化的人,留有一些字画和收藏品。她曾跟女儿聊起身后事,女儿对钱财、生死看得淡,表示不愿意继承。她没有办法,只好到处去联系博物馆,忍痛将自己最珍视的宝贝都捐献出去。做这个决定,花了她四五年时间。现在只剩房子和存款了,她把这些留给女儿。遗嘱订立之后,老太太说,自己的人生没有遗憾了。
马小平很能体会老太太的良苦用心。生死无常,在遗嘱咨询办公室,马小平看过许多普通人通过立遗嘱的方式表达爱。
在立遗嘱的过程中,人们除了分配财产,还会交待自己的身后事。他们通过录像或写家书,表达自己的情感,留与后人。
九十多岁的老人,一生漂泊,定居异乡,他在书信里表达,要落叶归根,把自己带回老家,葬在母亲的旁边。一位老父亲在录影像时泪流满面,他对儿子表达歉意:过去对你严格,有太多的约束,希望你原谅这个不称职的爸爸。还有一个女人在书信里写道:“妈妈走了,当我永远地闭上眼睛的那一刻,你不要哭泣,为我欢喜吧。”
2020年,中华遗嘱库上线“微信遗嘱”,可以通过线上留言的方式,为家人留下想说的话。崔文姬也为父母寄出一份信,送达时间定在写信的一年后,2021年3月21日。她记得这一天,父母打来电话,说信收到了,他们不善言辞,语气淡淡的,就像往常那样,但他们彼此的心都暖暖的。
(张进荐自《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