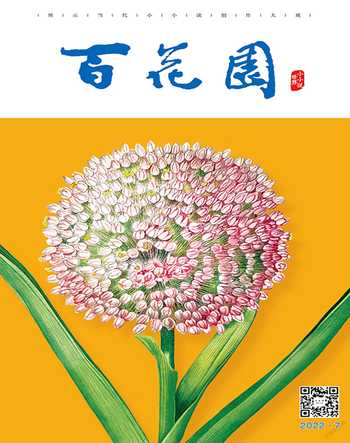考 古
闫兆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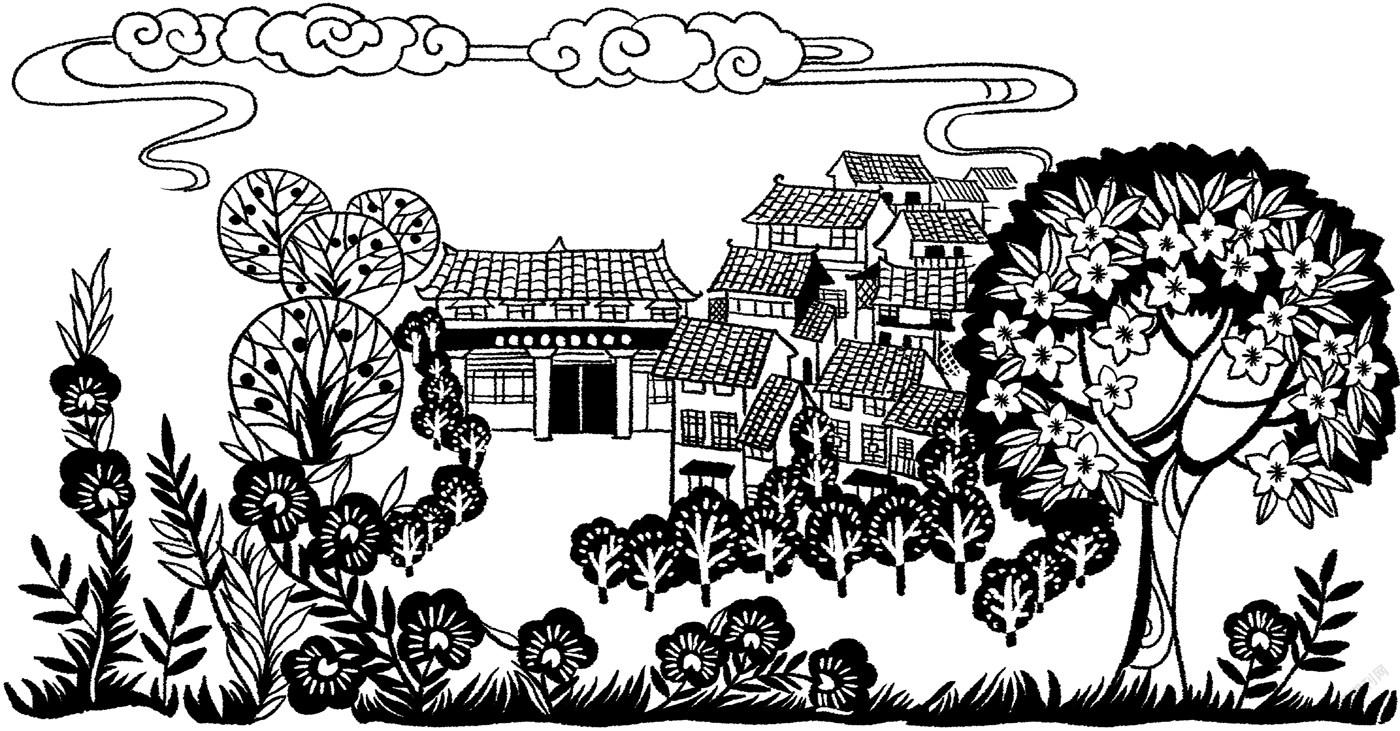
“今胜要回来挖古墓了!”这个消息成了李家村那年春天的头条新闻。七爷站在村西头的壕沟边,看着三三两两的人在西地指指画画,那是得知消息的村民,按捺不住激动,在重新打量这片即将被唤醒的土地。七爷心里说了句:“今胜这孩子,说话顶用。”
当年,李今胜考上北京大学,轰动一方,让整个李家村都沸腾了。周边村里的人、镇上的人甚至有县上的人来到李家村,说:“访访李今胜,沾沾喜气。这在古代可算是状元呢!”这是贫困的李家村走出的第一个大学生,村里人都觉得荣光。他们打来两大桶井拔凉水,放在村头的老柳树下,柳树下的长条青石板上摆了一溜儿粗瓷碗。来了客人,村人就捧上一碗井水,给客人解渴。今胜被人们簇拥着在老柳树下坐。今胜的父母,按村里老辈儿传下的习俗,遇到大喜事,在宅屋里静坐,并不出来张罗。今胜要学的是考古专业,就总有人问他:“考古是干啥的?”他每次都很认真地说:“考古,就是考究古物,通过老物件,看看古代的人是怎么生活的。”
“小小的娃儿,你咋就喜欢这个呢?”
今胜看看坐在一把小竹椅上的七爷,说:“七爷在这树下给我们讲古今儿,我从小就听得入迷。他讲春秋列国、战国、三国……我都喜欢。想象中我们的古人戴着高高的帽子挥着宽大的袖子,美得很。就咱们这片土地下,古今儿也丰富着呢,等我学成了,就把这古今儿打开给大家看。”
人们因为惊讶都笑了起来。有人把笑脸转向七爷:“一个庄子里,有个懂古今儿的人就是好。”七爷谦和地摇摇头,扬起嘴角笑笑,脸上就泛出光彩来。
勘探试掘后,联合考古队来了,名为“李家村车马坑考古队”。李今胜是队长。李今胜北大毕业后在一家考古研究所工作,已出版了三部考古专著。每出版一部,他都会送给七爷。七爷给村人说:“今胜娃儿的古今儿,讲得好!你们闲了都拿去看看。”人们接在手里,翻看插图,都说这图好看,看完图就还给七爷。七爷有点儿急切地说:“读读文,文也好呢。”村民们多忙,憨憨地笑笑,没人读。
考古队员散住在李家村,和村民们相处得很好。村民很喜欢和考古队员们聊天,为了找谈资,就想起李今胜送给七爷的书。有人双手从七爷手里接过书,翻看着,向今胜和他的同事问东问西。人们在一旁听着,不时发出惊叹声和笑声。当时正是芳菲四月天,树叶鲜绿,杂花盛开。村子里整天喜庆得很,过节一样。
中午,考古队员们在小食堂的院子里吃饭,饭桌上摆着村里家家户户都有的六物酒。六物酒是李家村的特产,酒料有苞谷、地瓜、大米、小麦、高粱,另外加了绿豆。据说加了绿豆,对酿酒工艺的要求就高,这也是少见的酿法,李家村人以此为豪。农家自酿的酒,清冽,辣嗓子。七爷的重孙子毛头,很依恋今胜。考古队员们收工,毛头总在村西头等着,看见今胜,就把小手递过去,让今胜拉着他。今胜吃午饭时,总爱抱着毛头一起吃。毛头好奇杯中物,也要喝。今胜用筷子的顶头蘸一下送到他嘴里,他立马闭了眼,好一会儿才睁开眼睛:“伯,这么难喝,你喝它干啥?”
今胜应答道:“去去阴气。”
“啥叫阴气?”
“就是……這墓里的物件呀,睡的时间太久了,阴气就是这些物件的梦吧。”
“啥叫梦?”
大家都笑,疲乏在笑声中消散。
李今胜想了想,问毛头:“那你知道小汽车吧?”
“嗯。”
“这墓里也有车,可比我们的小汽车美多了。车轮比我都高,车身的颜色好看极了,就像傍晚时候的天一样,灰蓝色的。车里有瑞兽,见了那瑞兽,你就不喜欢小怪兽了。”
毛头很急切地要去墓地看。今胜说:“你现在不能去,等伯伯们把大车都摆放好了,再修出漂亮的大房子,那时候,毛头再去看,好不好?”
“伯,你们是为我摆的吗?”
“是呀。”
占地97亩的“李家村车马坑博物馆”建好时,毛头已经是小学一年级的学生了。
在博物馆落成典礼上,李今胜说到了“艺术乡建”,说到了“拭亮乡村艺术因子”“乡野文化脉络的重现”等等,当然也说到了元宇宙。七爷最喜欢听的是“艺术乡建会让乡村实现横跨,由农业社会跨过工业社会,直接进入现代乃至后现代社会”,今胜在他面前展开了一部乡村古今儿的大书。毛头感兴趣的是“元宇宙”,他觉得这个词很厉害。
李家村车马坑博物馆建立了自己的元宇宙系列旅游项目后,线下游客激增。李家村人纷纷开起了民宿。李家村各家的民宿有一个相同的名字,叫“嘤嘤嗡嗡”。不同的是序号,现在排到16号了。游客们喜欢这个名字,都说:“这名字太春天了,你们咋想出来的?”村民说:“今胜带着考古队来村里时,正是春天,花开着,蜜蜂嗡嗡着。美得很!”
(作者系郑州外国语学校2023届5班学生)
[责任编辑 小 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