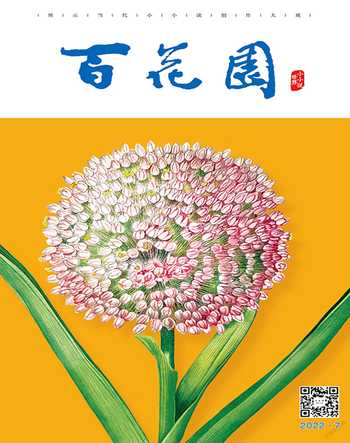董 工
齐川红
董工到我们这儿的时候,已经是我们请的第四个技术员了。
由于疫情的影响,公司承建的工程启动得很晚。劳务聘请的第一个技术员刚拿到图纸,还没细看,就告假说外省的丈人刚刚去世,得奔丧;他介绍的一个来了小半天就说几年没干生疏了,也走了;又来了一个,没几天就回了一个离家近的工地。工程还没开始就换了几个技术员,老板很不爽。当董工来的时候,老板有些疑惑——一则能否胜任,二则能否长久。董工来自淅川,口音自然不太一样,说着土语式的普通话。他身材略高,胖瘦适中,紫铜色皮肤,像秋天田野里的红高粱一样朴实;文质彬彬,没有多余的话,一来就研究图纸,做笔录。老板对他第一眼的印象就很好。因为他姓董,大家都叫他“董工”,感觉叫着有点儿怪怪的。叫他的时候,他不应答,只是抬头看着你,有啥吩咐就照做,有问题就解答。熟悉了,有人开玩笑,喊他“东宫娘娘”。他讪讪一笑。原来他担心的就是被这样的称谓引出绰号,终究还是被喊了出来。虽然不怎么愿意,他也没表示过不悅。
他住在工地的办公室里,一个人应该是舒适安静的。
闲聊时我问:“你知道我们这个地方不?”
他说:“不知道,第一次听说。”
我说:“《三国演义》中‘火烧新野应该知道吧?汉桑城,世界上最小的城。”
他摇摇头,说不喜欢文学,也不喜欢文学作品。不过得知我时常写文章,他倒产生了一丝兴趣。看到我的一篇有关齐大人齐慎的传说,他觉得特有意思,一连几天重复着文章中的几句顺口溜:“风吹棋子落,摸住娘娘脚。犯下欺君罪,我命难逃脱。”“金头银头,不如我爹的肉头。”
董工是八○后,才三十来岁,媳妇在家照看两个孩子。晚上他一个人难免寂寞,也不出去散心,唯一陪伴他的只有手机。有人问:“想老婆不?”他坦诚地说:“肯定想了。”有人开玩笑说:“远水解不了近渴,不如找一个情人,到外面风流风流。”他认真地说:“我要背着她找,她也背着我找,怎么办?”
一天早上我到工地,门卫神秘地说董工昨晚出去,刚刚回来。我愣了愣,这么说董工夜里不是在工地住,莫非晚上真在外面……那就真应了一句话:“白天像教授,晚上是禽兽。”可是世上有多少正人君子、柳下惠,又有多少苦行僧、传教士?不过,如果真是这样,也不算十恶不赦。食色,性也,也能理解,谁也不能站着说话不腰疼,站在道德的制高点评说他人。我冲门卫点点头,意思说知道了。董工像没有什么事一样,不过精神很好,竟然哼了几句刀郎的《西海情歌》:“自你离开以后,从此就丢了温柔……”一连几天,董工都是晚上出去,第二天早早回来。我也装作不知道似的。
一天深夜,我正在梦中,忽然被手机铃声惊醒,模糊中摸过手机,手指一划,问:“谁呀?”听到一个熟悉的外地口音,吞吞吐吐:“齐哥,是我……董工……”我心想,深更半夜,有什么事?那边说:“你能不能来一下?我……我……我在派出所……”我说:“怎么啦?”他说:“一句两句说不清楚。”
我暗自觉得好笑,他真是年少气盛,血气方刚,耐不住寂寞。吃腥一次就可以了,或者十天半月一次,哪能一连几天留恋风尘?在派出所看到了紫着脸羞愧的董工,旁边真有一个女的,垂着头,披头散发,更是羞愧难当的样子。她穿着半旧的衣服,用袖子边遮掩边擦泪,看起来也不像风尘女子。一边有两个警察,似笑非笑,嘲讽的语气中含着鄙夷,有着不易觉察的幸灾乐祸。
董工不住地辩解:“我们真的是夫妻。”
警察问:“结婚证呢?”
“没带,她来看我,我们住在宾馆……”
“那怎么能证明不是卖淫嫖娼?”
“我们有身份证。”
“身份证上的住址怎么是两个地方?”
“她的身份证是出嫁前在娘家办的。”
“就算是一个村的,也不能证明你们是两口子,偷情私奔出来快活的也不算少。我们见得多了。”
警察们“扫黄打非”也真不容易,不能正常作息,好容易逮到两个,如获至宝。我解释说董工是我们劳务聘请的技术员,一直勤勤恳恳;至于他们的夫妻关系,就是没有带结婚证,也可通过别的方式证明,比如手机里存的照片、与子女的合影、聊天记录等等都可以;要理解在外务工人员的艰辛,不是一般人能体会的。果然从董工的微信语音中听到这样的对话:

“媳妇,我好孤独,好寂寞,我想你。”
“我也想你。”
“那你来几天。”
…………
当我们从派出所出来时已是黎明时分。董工垂头丧气,他媳妇一言不发,落后面很远。我安慰他们:“都过去了,不算啥。也许他们也看出你们是两口子了,只是因为你们是外地的,想罚一笔钱而已。好了,天快亮了,你们休息一下,吃点儿早餐,还要上班呢。”
可是董工没来上班,他辞工了。后来他跟我联系说回老家了,以后再也不出去了,一辈子就和老婆孩子守在一起。
[责任编辑 冬 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