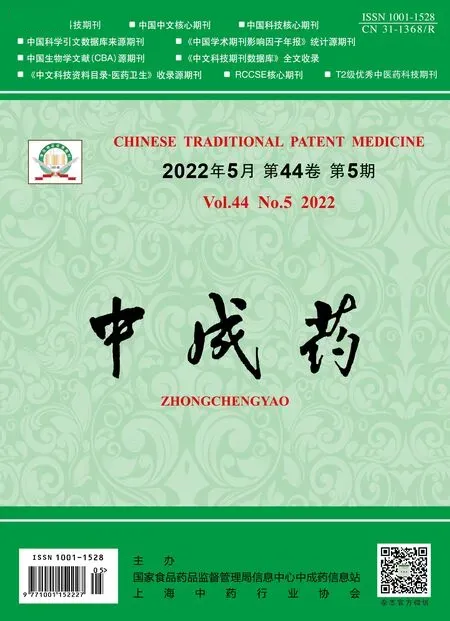温胆汤组方主治研究进展
金 珏, 陈 晓
(上海中医药大学基础医学院,上海 201203)
温胆汤为《古代经典名方目录》(第一批)公布的方剂之一,目前主要应用于神志病证,亦可见于心血管、消化系统病证等,其历代流传之广、运用时间跨度之长、化裁类方之多、临床治疗病证之众,实属方中少见。《古代经典名方中药复方制剂简化注册审批管理规定》[1]指出,经典名方提出的目的是,制剂申请上市提供非临床安全性研究资料可免报药效研究及临床试验资料,表明相关文献研究是帮助其申请上市的首要条件。
经典名方年代久远、流传过程曲折,其内涵、用药、主治等均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对其文献梳理需清晰明确。因此,本文从近20年的温胆汤文献入手,主要涉及方名内涵[2]、源头考证[3]、历代演变探索[4]、主要病机分析[5]、方剂药物探讨[6]等方面,归纳热点、重点及目前存在的困境,并提出解决问题的建议,可对丰富该方理法方药内涵,指导其临床应用起到积极的作用。
1 “一方三源”之论
《外台秘要·病后不得眠方》[7]载温胆汤源于《集验方》云:“病源大病之后,腑脏尚虚,荣卫未和,故生冷热。阴气虚,卫气独行于阳,不入于阴,故不得眠。若心烦而不得睡者,心热也。若但虚烦而不得卧者,胆冷也。(出第三卷中)集验温胆汤。疗大病后虚烦不得眠,此胆寒故也,宜服此汤方。生姜(四两)、半夏(二两洗)、橘皮(三两)、竹茹(二两)、枳实(二枚炙)、甘草(一两炙),上六味切,以水八升,煮取二升,去滓,分三服。忌羊肉海藻菘菜饧。(出第五卷中)”。
《备急千金要方·胆腑方》(简称《千金》)[8]云:“温胆汤。治大病后虚烦不得眠,此胆寒故也,宜服之方。半夏、竹茹、枳实(各二两)、橘皮(三两)、甘草(一两)、生姜(四两)上六味咀,以水八升煮取二升,分三服。(一本有茯苓二两、红枣十二枚)”。
《三因极一病证方论》(简称《三因》)中的“虚烦证治”[9]云:“温胆汤。治大病后虚烦不得眠,此胆寒故也,此药主之。又治惊悸。半夏(汤洗七次)、竹茹、枳实(麸炒,去瓤,各二两)、陈皮(三两)、草(一两,炙)、茯苓(一两半)。上为锉散。每服四大钱,水一盏半,姜五片,枣一枚,煎七分,去滓,食前服。”;“惊悸证治”[9]云:“温胆汤。治心胆虚怯,触事易惊,或梦寐不祥,或异象惑,遂致心惊胆慑,气郁生涎,涎与气搏,变生诸证,或短气悸乏,或复自汗,四肢浮肿,饮食无味,心虚烦闷,坐卧不安”。
以上3种古籍中记载的温胆汤药物组成基本相同,唯个别主要药物剂量、主治内容、煎服法不同,可谓“一方三源”,引发学者热议。
普遍认为,温胆汤最早来自《集验方》,已载入《中医方剂大辞典》[10]等权威方剂书籍,其方源于《集验方》,但其已散佚,仅从《外台秘要》得以窥见其貌。马伯艳等[3]考证史书,明确姚僧垣、《集验方》及《外台秘要》之间的关系,可确认《外台秘要》记载的《集验方》当为姚僧垣所作。但如今临床广泛运用的温胆汤出自《三因》一书,在《方剂学》《中医内科学》教材中可以明确[11-12]。目前,学者共识是温胆汤源于《集验方》,但现存文献最早见于《千金》引而述之,《三因》用而化之。
当然,古代经典方剂并非凭空产生,如温胆汤疗“不得眠”之证就可能受到前人经验的影响,如舒莹[13]跳出“温胆汤”之名,从方药、主治切入,推测《三因》温胆汤以半夏疗不寐当源于《内经》半夏秫米汤。但单从方药组成来看,该方与《金匮要略》中的“小半夏汤”“半夏加茯苓汤”及《深师方》中的“生姜汤”也存在源流关系,可能也是其主治范围在现代临床能得到扩大化的理论基础。笔者曾通过半夏秫米汤源流考证,认为温胆汤与半夏秫米汤亦有着源流关系[14]。
2 组方与主治
现代学者对温胆汤的争议主要集中在该方“寒热”之别、病位脏腑之惑。前者是以功效命名而论,其用似在于“温胆”,而现代的一般认识是该方疗痰热内扰,当为清热化痰、清胆和胃之剂[11],命名与实际应用之间看似对立矛盾的现象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讨论;后者则是由于该方治原为“胆寒”一证,但方中药物与胆腑并无直接关系,如今多视作化痰之用,主治脏腑病证与方药看似难以符合。以上2种争议的根本,是在于组方功效与主治两方面,试分述之。
2.1 组方功效 方剂最根本的效能体现在其药物配置上,性质由药物所决定,而功效由其配伍显昭,药物种类、剂量增减、炮制改变均会影响整首方剂的功效主治。
2.1.1 从药物性味药量配比考察温胆汤寒热升降偏重 渠玉梅等[15]认为,《千金》温胆汤以生姜、半夏为君药,辛温药味最多,微寒药味较少,全方寒温并用,但以辛温为主,提出该方为温养胆气之方。边玉麟[16]亦从《千金》温胆汤药味剂量分析,认为辛温占10两,寒凉占4两,以辛温为重。周叔平[17]发现《三因》温胆汤中热性药物药味、剂量均超过寒凉药物,认为本方非清热化痰之方,而是“温和”胆腑之方。冯学武等[18]以药味升降占比而论,因以降药为多,温胆汤当有气逆于上的病机存在,重在调气,而以降气为主。
一般而言,一首方剂药物性味在某一方面数量和剂量占的比重较大者,能主导该方的主治和功效,当然也并非绝对。
2.1.2 从组方配伍解析温胆汤实际功效 方剂功效由不同药物按君臣佐使配伍组合作用决定,可通过分析药物配伍组合初步掌握其主要功效。
2.1.2.1 疏肝调气,胆气温和 丁元庆[19]以《千金》温胆汤诸药皆有理气行气之功,是调畅气机之方,认为全方辛温善通,与疏肝调气之法同工,气机条达,故胆气“温和”,肝胆表里,实为同调肝胆气机之方。
2.1.2.2 调畅脾胃,痰邪自化 杨鹏等[20]认为,温胆汤半夏、陈皮有“二陈”之意,燥湿化痰不言自明,并且半夏辛温善散,陈皮理气,枳实苦降,竹茹下气,全方以调畅脾胃气机、化痰见长,气机调畅,则痰邪自化,而痰邪一除,则经络疏通,气机顺畅自通,二者互为因果。
2.1.3 比生姜之用,辨温清之别 观《集验方》《千金》温胆汤与《三因》温胆汤,仅生姜一味就用药有异。姜永斌等[21]提出,生姜温和少阳,祛痰下气,为温胆汤组方最妙。郑佳新等[22]认为,《集验方》温胆汤以生姜为君药,配伍半夏而成“小半夏汤”“半夏生姜汤”温散寒饮,配伍陈皮而成“橘皮汤”温阳理气散寒;《三因》温胆汤去生姜一味加茯苓,以竹茹为君,取“橘皮竹茹汤”清热化痰之意,易为“清胆”之方。程岩[23]认为,《千金》与《三因》温胆汤各有侧重,前者生姜、半夏配伍,辛温为主,温补胆腑;后者半夏、竹茹为主,理气化痰,清胆和胃。韩生银等[24]关注《千金》温胆汤重用生姜,在于温化寒痰;《三因》温胆汤少生姜,制半夏缓和药性,增强补益脾胃作用。
不难发现,《集验方》《千金》温胆汤与《三因》在生姜一味上的变化直接改变了竹茹在方中的地位,由前方的甘寒之性以防温燥太过之佐药跃升为君药,甘寒清热,从而使温胆汤之温散胆腑易为“清胆”之清胆和胃。当然也有学者持不同观点,通过分析药物配比、剂型差异认为《千金》温胆汤为汤剂[25],《三因》温胆汤为散剂,生姜在其中的占比并无明显变化,但未进一步研究或补充说明。
通过对温胆汤方药的运用可知,(1)判断一首方剂的寒温属性可通过药物药味数、剂量、占比作为参考,但非绝对指标,仍需要根据方药之间的配伍关系综合判断;(2)温药之温,不仅在于温补、温养,更重要的在于辛温发散、温通气机、温化痰饮,正如《素问·举痛论》所言“百病生于气”,气机逆乱、异常可谓众多疾病的总病机,而胆腑本身为少阳之枢,与气机关系密切,少阳枢机不利,气之运行不畅,病之始生,因此治胆重在治气、治痰,气机一通,而痰饮自除,痰饮一除,而气机自通。温胆汤调畅气机配伍之妙也当为现代学者重视借用[26];(3)一味药物之差,亦可改变方剂的根本属性。
2.2 温胆汤主治之证 温胆汤在原书中用于治疗胆寒证,而组方与主治相应又是中医辨证最根本的临床思维,故若要明确该方“理”“法”内涵,则需了解胆寒证意义。
2.2.1 胆寒证,本在胆虚 《备急千金要方》[8]之温胆汤“治大病后虚烦不得眠,此胆寒故也”。何为“胆寒”?“左手关上脉阳虚者,足少阳经也。病苦眩厥痿,足趾不能摇,躄不能起,僵仆目黄,失精,名曰胆虚寒也”。提出温胆汤主治的病证“胆寒证”,即“胆虚寒”,又明确了其主症,奠定了后世“胆虚则生寒”的理论基础。
而胆寒或胆虚寒,何以有“烦”“不得眠”此类情志病变?从胆本身脏腑的生理功能言,《素问·灵兰秘典论》就有“胆者,中正之官,决断出焉”,《素问·奇病论》云:“夫肝者,中之将也,取决于胆,咽为之使。此人者,数谋虑不决,故胆虚,气上溢,而口为之苦”。肝之谋虑取决于胆,谋、虑本就代表人的思维心理活动,说明肝、胆与人一系列的精神思维心理活动密切相关。从胆病理状态而言,《灵枢·邪气藏府病形》提及“善太息……心下澹澹,恐人将捕之”,胆病可有太息、胆怯恐惧之感。因此,胆虚可引起“烦”“不得眠”等精神心理异常变化。
现代学者普遍认为,此胆寒根本在于胆虚,同经典一脉相承。侯志明等[27]认为,胆寒证包括了古代文献中所称的“胆气虚”“胆虚寒”“胆虚”“胆寒”,此证应具备胆怯、心慌等神志症状及眩晕、呕吐等躯体表现。石相臣等[28]结合当时的社会背景及此方主治对“胆虚寒”进行解读,认为其本质是胆怯之意,仍属精神情志病变。张春晓[5]、冯学武等[18]认为,胆寒证的本质是胆阳不足,与脾胃阳虚、气机逆乱密切相关,伴有持续性惊恐不安的主症表现。
2.2.2 胆郁证,郁而化热生痰 钟泽明等[29]以肝胆为表里脏腑,功能相因,气机升降之枢,调控气血运行及情志,肝气不舒,胆气郁滞,胆气不通,则肝气不畅。杨庆等[30]从阴火角度论述胆寒证,属广义阴火范畴,胆阳虚,阳郁伏于阴中,合阴邪成郁火,最终阴阳失调、寒温失宜、气机失常。陈旭等[31]分述《千金》温胆汤与《三因》温胆汤之胆寒不同,前者大病后,胆胃虚寒,湿郁气滞;后者在前者病机基础上,湿郁化火,痰热内扰。张春晓等[5]明确胆寒证的核心病机为胆阳不足,但其基础在于脾胃虚寒湿郁,郁滞兼虚必生浮火,可谓内有虚寒外有浮火。
2.2.3 “脏寒腑热”,病在脏腑有别 基于南北朝时期“脏热腑寒”的辨治规律及《三因》温胆汤补充“惊悸”一证,王洪图[32]、李明[33]认为《集验方》温胆汤所治为胆寒证,病机为虚,其意在温补胆腑,病在胆、脑、髓。而《三因》温胆汤疗“心虚胆怯”之证,主治病机在“气郁”,病在心胆。
总之,温胆汤一证虽病在胆腑,但病机本质在于气机不利、湿郁痰阻,与肝、脾胃关系最为密切。现代学者通过理论探讨、回归古籍,拓展了其脏腑病机内容,也为温胆汤现代临证治疗多系统疾病提供了理论支持。
3 后世沿革追踪
温胆汤由原来的胆寒证方发展至今日临床常用的痰热内扰不寐方,这中间经历了怎样的发展沿革、历史变迁正成为追踪热点。现代学者主要以方药组成变化和证治演变为切入点,讨论其后世流传情况。
学者以温胆汤同名同方(类方)以及异名类方为线索追踪,进行其历代发展梳理,其中同名同方(类方)较为容易判断。马伯艳等[3]以“温胆汤”同名同方进行后世梳理,发现多从《三因》温胆汤衍化而来,主治也由气郁痰阻逐步扩大为痰、火、气病证变化。高军宁[34]、石历闻等[35]对温胆汤类方作源流追踪,大多在《三因》温胆汤上加减而成,如《世医得效方》的十味温胆汤、《伤寒全生集》的加味温胆汤等,主治也由原来的不寐扩大至明清后期的伤寒、温病甚至狂证等病证。
对于异名类方的确认,现代学者主要是依据方药组成相类似,主治则以痰病为主要线索[36-37]。《济生方》的导痰汤、《奇效良方》的涤痰汤、《局方》二陈汤均被认为由温胆汤化裁而来,是现代临证疗痰病、怪病的常用方[38]。只有王婧等[39]独辟蹊径,注意到温胆汤方药在历代的度量衡问题,使得药材剂量、加水量、服用量方面存在较大差异。同时,历代炮制方法也产生了变化,认为古今温胆汤并不完全相同。
综上所述,现代学者通过温胆汤后世沿革的追踪在一定程度上理清了其发展脉络,揭示了其方药、主证的变化特点,认识到痰在温胆汤衍化方主治病证当中的关键作用,为当今临床提供了丰富的理论基础。随着研究的深入,该方剂量、炮制问题也渐渐引起了学者的关注。
4 启示与思考
总体而言,针对温胆汤源流及方证相关理论的文献研究丰富详实,方剂源头考证理据较为充分。组方与主治病证阐释,是现代研究的热点及重点内容。特别是其方药的配伍运用与病证基本病机的相应性,结合方药的药味、药性、加减变化及配伍作用,主治病证的病机特点,辨识“温清”之治、脏腑之位。后世发展演绎,加减变化,一定程度上关注到了方药变化与主证相应的辨证特点,可为温胆汤的理论发展与应用创新提供借鉴。
目前,已经达成共识的有以下3点,①温胆汤的方源当为南北朝时期姚僧垣的《集验方》,载于《外台秘要》,同方亦见于孙思邈的《备急千金要方》,宋代陈无择的《三因极一病证方论》所载温胆汤与前两方药味基本相同,但药量、炮制及煎服法不同,当为化裁之方;②温胆汤的作用为和胃利胆、调畅气机,主治病证为胆寒证,病机胆虚为本,与精神情志变化关系密切,同时可见肝胆气郁,郁而化热,气机失常;③温胆汤在后世发展演绎过程中,由原来的“胆寒证”方逐步变化为“痰证”方,病证范围由内伤逐步扩大为伤寒、温病、狂证等诸多病证,其衍生方之多、所涉病证之广泛,使其成为当今临床重要经典方剂之一。
但对于温胆汤的文献研究仍有待完善,空白有待补充,内涵有待深入。
第一,方剂源流考证判断标准有待明确。诚然,以“方名”作为线索是十分有效的判断方法之一,但亦会出现同名异方的情况,如何做选择?而异名同方或类方的界定,是采取何种方式,是以药物组成?主要药物剂量?还是主治病证?如何确定两方有源流关系?这是在未来方剂源流研究当中应当明确的。
第二,温胆汤的沿革有待进一步梳理,从组方与主治角度深入探索。目前,已经在一定程度上梳理了温胆汤后世流传的类方、衍化方与主治内涵的变化,但组方与病证内容论述不详,不同年代之间方证变化的内在逻辑关系梳理尚有欠缺。另外,除《三因》温胆汤外,《千金》温胆汤是否有可能以其他方剂形式流传下来?为什么《千金》温胆汤未得到广泛应用?是由于文献获取的便利性有差别?是方药本身的运用合理性?还是主治病证的存在与变化……以及这一系列方剂演变发展背后深层次的原因都是应当考虑的问题。
第三,温胆汤药味炮制、煎服法及其历代发展研究亟待补充。有学者已经意识到个别药味的变化、炮制、煎服法对方剂的影响,但未能进一步开展研究,无法明确其药味及炮制变化的深意及对后世临床运用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