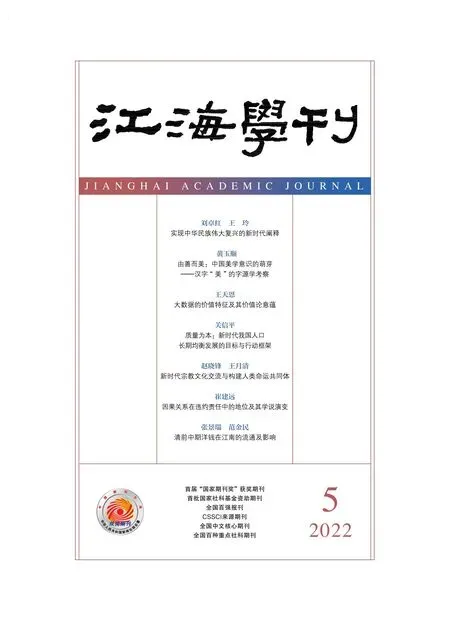兰克与德国统一
——以书信为中心的考察
景德祥
对德国统一的肯定与支持
19世纪是德意志民族统一运动高涨的世纪。18与19世纪之交,德意志民族受到了来自法国的双重冲击。法国大革命给德意志民族送来了自由平等博爱的政治思想,而拿破仑战争则摧毁了古老的“德意志民族神圣罗马帝国”,严重伤害了德意志人的民族感情。在此双重冲击下,德意志进步人士萌生了建立一个自由平等的民族国家的梦想。但在1814—1815年的维也纳会议上,德意志封建君主建立了一个松散而反动的“德意志邦联”,德意志进步人士大失所望,由此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民族统一运动。1848年,德国爆发了试图建立自由平等的民族国家的资产阶级革命,但终因封建势力的强大、革命任务的复杂、革命阵营的分裂等原因而失败。自1864年起,在俾斯麦的领导下,普鲁士通过三次王朝战争(1864年德丹战争、1866年普奥战争、1870—1871年的普法或德法战争),于1871年1月建立了以普鲁士为核心的德意志民族国家,即“德意志帝国”。
兰克出生于1795年,卒于1886年,其一生经历了19世纪德意志民族运动从兴起到德国统一的全过程。他是如何看待德意志民族统一运动的?对此问题,史学界一般认为,兰克不是很热心于德国统一运动,他注重的是欧洲多个民族国家的体系。如格奥格·G.伊格尔斯就曾赞赏兰克在历史编纂中民族情感不断上升的时代里没有放弃他对欧洲共同体的信仰。(1)[美]格奥格·G.伊格尔斯:《德国的历史观》,彭刚、顾杭译,译林出版社2006年版,第108页。胡昌智认为,兰克对德意志帝国的建立没有感到欢欣。(2)李孝迁、胡昌智:《史学旅行——兰克遗产与中国近代史学》,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131页。应该说,此类观点确实有其史料依据。例如,1854年秋兰克曾给巴伐利亚国王马克西米利安二世讲授历史,在课程的最后对话中,国王问及19世纪的主要趋势,并问民族性(Ausprägung der Nationalitäten)是否也是这个时代的一个特征。兰克回答,一个民族可以团结起来抵御外来侵略,例如,法国人作为民族抵抗过外族统治,俄国人与德国人也曾抵抗过法国的统治,“一个完全不同的问题则是将民族组织成国家,这也属于这个时代的最为瞩目的目标,但是德国人没有建国,却能够像一个人那样奋起抵抗法国,所以这两个概念,民族性与民族建国,并不必然相关,民族之间的相互隔绝现在已经无法实现,所有民族都属于一个宏大的欧洲乐团”。(3)Leopold von Ranke, Epochen der neueren Geschichte, als Aus Werk und Nachlass, Band II, hg.von Walther Peter Fuchs und Theodor Schieder, München und Wien, 1971, S.444.兰克的意思是,在1813—1815年的反法“解放战争”中,德意志民族虽然没有建立一个民族国家,但还是能够万众一心地抵抗并击败拿破仑军队,因此建立民族国家是不必要的,而且欧洲各个民族已经高度融合,难以按民族属性割裂开来,它们应该在一个“欧洲乐团”里生存与合作。
这可以说是兰克对民族国家,包括德意志民族国家最为清晰的否定态度。不过笔者认为,兰克与德国统一的关系不能就此盖棺定论。兰克是19世纪德意志统一运动全过程的见证者,而晚年的兰克属于社会名流,应该与德国统一这一重大历史事件有所交集,并留下一些相关历史记录。通过对以兰克书信为中心的史料考察,我们可以看到,兰克与德国统一的关系要比史学界至今所认识的复杂得多。(4)笔者在拙文《从书信看兰克第一本书及附本的诞生》(《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6期)中简述了兰克书信的收集与出版情况,这里不再赘述。本文所依据的兰克书信集主要是以下几种:Leopold von Ranke, Sämmtliche Werke, Band 53-54, hg.von Alfred Wilhelm Dove und Theodor Wiedemann, Leipzig, 1890; Leopold von Ranke, Das Briefwerk, hg.von Walther Peter Fuchs, Hamburg, 1949; Leopold von Ranke, Neue Briefe, gesammelt und bearbeitet von Bernhard Hoeft, hg.von Hans Herzfeld, München, 1949; Gesamtausgabe des Briefwechsels von Leopold von Ranke, Band 1: 1810-1825, bearbeitet von Dietmar Grypa, Berlin/Bosten, 2016。这首先表现在兰克对德国统一的肯定与支持上。
在瓦尔特·彼特·福克斯(Walther Peter Fuchs)1949年编辑出版的兰克《书信集》中,我们可以看到一次珍贵的相关书信来往。1885年4月1日是“铁血宰相”俾斯麦70华诞,德国报刊《汉堡通讯员》(HamburgerKorrespondent)与《股市交易厅》(Börsenhalle)驻柏林记者赫尔曼·海贝格(Hermann Heiberg)约请兰克写一篇评价俾斯麦生平功绩的文章。兰克以“正忙于研究9世纪的纠葛、危险、趋势”为由婉拒了这一约稿,但他还是写了一篇篇幅较长的对俾斯麦统一德国过程的回顾与评论。(5)Leopold von Ranke, Das Briefwerk, S.589-592.我们可以从中看到,兰克对俾斯麦用三次王朝战争建立德意志民族国家的政策做了几乎毫无保留的理解、支持与辩护。
兰克在开篇就十分犀利地指出,德国统一的实质是普鲁士的扩张过程。在文中,兰克几乎把两者视为同一事物。他认为,俾斯麦针对丹麦、奥地利与法国的三次王朝战争(兰克称之为“政治运动”)都有一个共同的出发点:解除普鲁士的外来压力。丹麦因王朝关系对德国北部的影响必须解除,如果德意志民族要统一的话。如果普鲁士想获得完整的独立性,普奥之间长期存在的、因德丹战争更加激化的矛盾,也必须有个了结。德意志纠纷的“戈尔迪之结”不可能被解开,只能被斩断。而普鲁士对奥地利的胜利,削弱了法国对德国事务的影响,法国出于持续不断的嫉妒心理向普鲁士宣战。在德法战争中,“弗里德里希王朝战胜了拿破仑军队”,由此保障了普鲁士完整的独立性。兰克对德国的胜利极为兴奋,认为它是上帝的意志,“几十年来政治与军事领袖们的梦想完全实现了。一个民族自我感觉的最大满足在于知道,在地球上,在它之上有一个更高的存在”。“几乎自动地,普鲁士王朝扩大为德意志帝国”,所有参战的德意志力量都参与了新国家的建立。(6)Leopold von Ranke, Das Briefwerk, S.590.兰克高度评价了俾斯麦在其中的作用,因为“三次战争行动,其真实的原因是内在力量的发展,但其开始与过程,不能没有领导外交事务的部长而完成,他的内心有着思想的整体性,并能在有分歧时机智地维持这一整体性。最强大的思想能力与普世性关切相认同”。(7)Leopold von Ranke, Das Briefwerk, S.591.兰克也基本认可德意志帝国的政治制度,认为它符合欧洲国家的主流思想,试图尽可能地团结广大民众。虽然帝国遇到了反对力量的挑战(暗指俾斯麦针对天主教会的“文化斗争”与针对社民党人的“反社会主义者法”),但他还是深信,那些“造反的被误导者”能够通过普遍包容的思想与所有力量的发展而被击退。兰克还特别指出,德国的科学研究在当代获得空前的发展,这也是俾斯麦的功劳,因为科学研究依赖于长期的和平,而俾斯麦在德国统一后一直致力于维护欧洲的和平。
兰克不仅在1885年的回顾中肯定了俾斯麦统一德国的过程与功绩,而且在1870年德法战争期间为普鲁士政府与军方提供了重要的情报与建议。这是兰克与德国统一关系中最具戏剧性的一幕。1870年7月,法国向普鲁士宣战,9月初,普鲁士军队在色当战役取得了对法军的决定性胜利,并俘获了拿破仑三世。巴黎爆发革命,帝国被推翻,共和国成立,但继续抵抗德军。德军兵临城下,与法国新政府谈判。德方要求法国割让阿尔萨斯-洛林,遭到拒绝,谈判陷入僵局,巴黎面临一场恶战。就在此期间,兰克前往维也纳档案馆查阅档案资料,在其下榻的酒店,偶遇了多年的老朋友、法国著名政治家与历史学家路易·阿道夫·梯也尔(Louis Adolphe Thiers)。梯也尔刚从俄罗斯圣彼得堡来到维也纳,并行将前往意大利佛罗伦茨。兰克估计,梯也尔正受法国政府委托寻找外援。两位历史学家各自代表本国的利益,进行了一场交锋。就战局,兰克认为巴黎守不住,而梯也尔则认为可以守住,不过两人都认为战争结局不容乐观。德法谈判的难题,德国是否有理由要求法国割让阿尔萨斯——洛林,成为他们谈话的焦点。兰克认为,出于历史的原因,德国必须坚持割让法国东部省份的要求,作为未来德国的安全保障。而梯也尔则认为,曾经威胁普鲁士的拿破仑三世已经倒台,法国的帝国主义党派影响有限,德国面对的是一个不想打仗只想要和平的法国,因此不需要什么保障。兰克辩解道,德国要求保障,不是为了防范法国,而是为了预防法国可能发生的革命。近几十年来法国发生了多次革命,未来也可能发生,并且会有一个好战的领导人上台,随之攻击德国。梯也尔认为这不可能,不管哪个法国政府都不可能签订一个割让大片领土的和约。他警告这种和约的后果:随之而来的只能是一场持续的战争,它将持续激怒法兰西民族,深深地侮辱法国。兰克继而认为,普鲁士不想把法国降低为二等国家,割让阿尔萨斯——洛林只是把一个历史上的德意志省份收回德国,因此不会使法国人十分愤怒。普鲁士国王不是在针对拿破仑三世,也不是针对法国,他是在回击路易十四的政策,后者在德国分裂与软弱的时候夺取了斯特拉斯堡与阿尔萨斯。实际上1814—1815年战胜拿破仑一世时,德国人就想这么做,这是全德意志民族的要求。
我们得以了解兰克与梯也尔在德法战争时期的这次交谈,是因为兰克在事后将交谈的内容以信件的方式转告了时在法国战场上的好友埃德云·冯·曼托伊费尔(Edwin von Manteuffel)将军以及普鲁士驻奥地利大使汉斯·罗塔·冯·施崴尼茨(Hans Lothar von Schweinitz)。(8)Leopold von Ranke, Das Briefwerk, S.502-505, S.506-508.兰克给他们的谈判建议是,可以向法国要求割让说德语的法国省份,作为未来的安全保障,同时要求一笔大额的战争赔款。(9)Leopold von Ranke, Neue Briefe, S.722-723.而梯也尔则在1871年2月当选法国新政府首脑,并负责与德国谈判。法德于5月达成《法兰克福和约》,其内容与兰克的建议基本相符,确定法国割让阿尔萨斯与洛林并赔款50亿法郎。应该说,兰克关于与梯也尔交谈的报告与建议对和约的达成起到了重要作用。从兰克与梯也尔交谈的内容可以看出,兰克完全站在当时德国政府与军方的立场上,强烈要求法国割地赔款。而其历史学家的特色,仅在于强调夺取阿尔萨斯与洛林的历史理由。正如梯也尔所警告的那样,苛刻的和约条件加深了法德之间的民族仇恨,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埋下了伏笔,而兰克却未能预见到这一未来。
德国兼并阿尔萨斯——洛林之后,曼托伊费尔于1879年被任命为该州的首任总督。为了扩大德意志文化在阿尔萨斯——洛林的影响,德国在该州重建了斯特拉斯堡大学,兰克也对德国的文化侵略政策做出了支持的表态。1884年10月19日,在斯特拉斯堡大学新楼启用举行仪式之际,兰克给曼托伊费尔写信祝贺,他在信中毫不回避德国的政治意图:“我怀着非常愉快的心情期盼着在您的参与下大学新楼启用的那一天,因为大学的建成是兼并的一个重大步骤。和约是基础,真正的征服只有从逐渐增长的内在的共同体中成长起来。没有比图书与教学能够做出更大的贡献。对于两者来说,大学在德国都是最高级的工作坊。”(10)Leopold von Ranke, Das Briefwerk, S.722-723.福克斯指出,兰克这两句话被曼托伊费尔在其在大学新楼启用仪式的致辞里完全照搬了,可见他说出了后者的心声。
以帝国为依托的民族史学蓝图
兰克不仅肯定与支持了德意志帝国的建立,而且还在帝国建立的1871年向俾斯麦提出了成立国家级史学研究机构——德意志历史与语言科学院的建议。(11)Leopold von Ranke, Sämmtliche Werke, Band 53-54, S.696-705.兰克与俾斯麦的关系不是很亲密,但也不是极其冷淡。据笔者统计,兰克给俾斯麦共写了10封信件,除了1871年建议成立“德意志历史与语言科学院”这一次,其他信件的由头分别是数次赠书与感谢后者给自己获得博士学位60周年(1877年)和90大寿(1885年)的贺信以及颁发“真正枢密大臣”荣誉(1882年)。在其中两封信中,兰克与俾斯麦“攀谈”了政治家与历史学家的区别与关系。总的来说,兰克很在意俾斯麦对自己的史学成就的认可,也对后者做出了友好乃至过度的恭维。例如,在1878年10月18日给俾斯麦赠送《哈登堡回忆录》的附信中,兰克除了感谢俾斯麦提供的支持外,还特地向俾斯麦指出,在该书中有一条资料,说明在1805年11月,时任奥地利驻普鲁士大使的梅特涅曾经在一个报告中提到,如果普鲁士兼并汉诺威王国,奥地利与英国都会接受这一行为,参见Leopold von Ranke, Neue Briefe,S.667-668。1866年普奥战争期间,汉诺威王国站在了奥地利的一边,奥地利战败后,汉诺威王国被普鲁士兼并。这对于保守主义的国家理念来说,无疑是一种理应谴责的行为。兰克为俾斯麦提供这条史料,是为后者减轻因兼并行为可能产生的心理负担,也可谓无微不至的关怀了。
从兰克给俾斯麦的建议中,我们可以看到,兰克建立一个全德意志的历史研究机构的想法,实际上由来已久。1859年,在巴伐利亚国王马克西米利安二世支持下,兰克在巴伐利亚科学院成立了一个历史委员会。当时兰克就设想把历史委员会转变为一个德意志历史科学院,并得到了巴伐利亚国王的支持,此后国王又有了增建一个德意志语言科学院的想法。兰克与国王都认为,这样的科学院不应局限于巴伐利亚王国的范围,而应该成为所有德意志邦国与地区的共同学术机构。兰克在1861年与1862年起草了相关计划,计划也得到普鲁士国王的支持。不过,因当时的德意志邦联缺乏一个政治中心,院址应该设在何处成为棘手的问题。巴伐利亚国王建议在慕尼黑、柏林与维也纳都设立一个秘书处,科学院可以在三个首都轮流举行年会活动。在这一问题解决之前,巴伐利亚国王于1864年意外去世。兰克不仅失去了德意志历史与语言科学院计划的坚定支持者,连设在巴伐利亚科学院的历史委员会也遇到了生存问题,因为新国王路德维希二世对历史学不感兴趣。虽然新国王最终还是答应继续拨付历史委员会的正常开支,但只承诺保障未来的15年,以完成已经开始的研究项目,并特别告知不要开启新的研究项目。兰克必须为自己的计划寻找新的支持者。就在普鲁士打败奥地利,成立“北德意志联邦”的1867年,兰克争取到了萨克森—魏玛—爱森纳赫大公国的支持,并决定将院址设在文化古城魏玛。在继续争取萨克森与普鲁士的支持时,兰克却又遇到了阻碍。萨克森认为兰克的计划不合时宜,而普鲁士则反对将院址设在魏玛,兰克的计划再次搁浅。
1871年德国的统一,给了兰克实现建立德意志历史与语言科学院计划一个新的机会。在其申请中,兰克向俾斯麦解释道,以前是从局部向全国努力,而现在德国统一了,此事可以从大局着手解决,不用有其他顾虑,“您不要见怪,现在民族共同体通过去年的事变意外成形了,旧的愿望又苏醒了。而您被视为那个可以促成此事的人”。兰克不忘向俾斯麦突出成立德意志历史与语言科学院的现实与历史意义,并希望能够尽快实现或至少宣布这一计划,“如果您同意以上的建议,它们当然还需要更具体的确定,那么我深信:它们的实施将赋予我们这个伟大时代一种新的光彩,实现高度的满足与长久的伟大利益。将权力与进步中的文化建设直接地相联系,是勃兰登堡家族的独有特点。新的基金可以继承以前的伟大基金的光荣传统。或许,目前的庆祝活动可以提供一个机会,即使不让它诞生,但可以将其主要内容作为已经决定的事情而公布于众”。(12)Leopold von Ranke, Sämmtliche Werke, Band 53-54, S.705.
上述论述足以说明,兰克虽然视欧洲民族共同体为理想状态,有过明确否定民族国家重要性的言论,但是对俾斯麦统一德国的政策还是做出了肯定的评价与支持,并且试图借用统一的德国作为平台实现自己的民族史学蓝图。如何解释这一矛盾?或许我们应该这么看:兰克在1854年与巴伐利亚国王的交谈中,首先把君主制与民主制原则的较量视为19世纪的主导趋势,而否定民族国家为主导趋势,这或与当时刚刚平息的1848年资产阶级革命有关。革命虽然被镇压了,但属于保守派的兰克仍然惊魂未定,继续视革命为洪水猛兽,并把革命的另一目标——建立统一的民族国家也一并否定了。而当普鲁士王国在俾斯麦的领导下不惜通过三次王朝战争统一德国时,依附于普鲁士国家的兰克自然也不可能举起反对的大旗。再说,兰克自19世纪50年代起也有建立一个统一的德意志民族史学研究机构的梦想,只是囿于德国的分裂而一直未能实现。而1871年德国的统一,则是实现这一梦想的完美平台。
出于尚不明确的原因,兰克成立德意志历史与语言科学院的计划未能实现。但兰克的具体规划却具有重要的史学史价值。我们可以从中看到兰克远远超越其已有史学成就的史学抱负与视野。“关于成立德意志历史与语言科学院的建议”的研究项目包括历史科学与语言科学两大领域。历史科学领域又分三部分:(1)继续与完成巴伐利亚科学院历史委员会已经开始的项目,如旧帝国(1806年前)议会档案的收集与编辑、旧帝国的年鉴、城市编年史、德意志名人传记;(2)《德意志历史资料集成》;(3)其他,包括关于中世纪日耳曼行政区(Gau)的历史地理学的阐述、中世纪军事制度、普遍的德意志著名家族的谱系学(包括诸侯、贵族、大城市著名市民)、德意志教会史、民族教育机构史(包括修道院,但主要是大学)、德意志民族的科学史(包括工业史、技术发明史、物质文明史)、艺术与诗歌史。可见,兰克的史学视野已经包括了社会史、文化史等领域,远远超越了国家政治的范围。在中世纪日耳曼行政区的历史研究方面,他主张地理学家与历史学家的跨学科合作。在教育机构史与大学史领域,兰克主张不局限于新帝国范围内的德意志大学,而要包括对德意志科学文化发展有着重要影响的布拉格大学以及鲁汶大学,这当然属于跨民族国家视野。在涉及该科学院的名称时,兰克解释说,虽然名称是“德意志历史与语言科学院”,但并不是要将现有地方性科学院全部集中起来,而是可以与它们并存。同时,兰克认为,科学院的成员不应该局限于新帝国的范围内,还应该包括瑞士的德语区和利沃尼亚以及荷兰与比利时的一些地区。实际上,兰克这里指的是历史上的德意志文化区,是“大德意志”概念。或许,这也是俾斯麦没有采纳其建议的原因之一,因为他建立的德意志帝国就是要实现与大德意志的历史德国一刀两断。
我们从兰克的民族史学蓝图可以看出,兰克的史学视野是宽阔与多元的,远远超过了以往史学界关于兰克史学的刻板印象。兰克关注的远不止民族国家的政治与军事斗争。其实,史学界长期以来关于兰克没有着重研究19世纪现代化与工业化历史的批评不是很公正。兰克的研究重点是欧洲近代史,我们不能苛求所有历史学家都来研究当代史。关键是,作为生活在19世纪的历史学家,兰克是否对该世纪翻天覆地的历史性变革完全视而不见?答案是否定的。如前所述,1854年秋兰克曾给巴伐利亚国王马克西米利安二世讲授历史。在课程的最后对话中,国王问及19世纪的主要趋势。兰克认为,19世纪的主要趋势是君主制原则与民主原则的斗争、人类力量的无限发展和自然科学的多方面的发展。除了与国家有关的争斗以外,精神的趋势也凸显出来。(13)Leopold von Ranke, Epochen der neueren Geschichte, S.441ff.可见,兰克并不是两耳不闻窗外事的象牙塔里人。对19世纪工业化、现代化、全球化进程,兰克都有仔细观察与深刻思考。再如,在其于1874年11月给大弟海因里希的76岁生日贺信中,兰克深深感叹19世纪发生的巨变,其观察与思考已经深入世界史乃至全球史领域。兰克写道:“你也与我一样,都是上世纪生人,而我们现在已经远远地进入19世纪了。我们自那以来所经历的,是世界历史的重要部分;形势刚刚在最近发生的转折,完全出乎意料。”(14)指的是1871年德国统一。“按我们的信念与本性我们似乎必须否定它,但我绝没有这样的想法。不久前,邮政局总管寄给我其部门的一份成绩报告。它囊括了整个世界。与我们的早年相比,是多么大的不同!那时人们没有身份证件连10里路程都走不出。到处都是阻碍交通的边境界碑。每个再小的地区都与另一个地区相隔绝。而现在没有人问我们是谁了。所有帝国与国家都通过火车与电报最紧密与最快地联系在一起,似乎地球上的所有民族是一个民族。这一结果之外还有上千个类似的结果。在广大的地球上再没有绝对的隔绝了。谁还在讨论生活应该符合人道的主张呢?这样的要求已经是理所当然了。”(15)Leopold von Ranke, Das Briefwerk, S.527-528.
德国统一与世界史书写
兰克曾明确表述,普鲁士德国在德法战争中的胜利是其晚年撰写多卷本《世界史》的重要推动力。在兰克1885年自述的最后一段,他说,“然后是两大改变了世界命运的战争,即普奥战争与普法战争,它们最主要的结果是,政治形势在一个统一的平坦的基础上发展。德国与世界的普世性前景鼓励我将我最后的精力致力于一部我正在撰写的世界史著作”。(16)Leopold von Ranke, Sämmtliche Werke, Band 53-54, S.76.在其同年年底的90岁生日庆典上的致辞中,兰克进一步地阐述,普鲁士及德国对法国的“革命的凯撒主义”的胜利,为“世界历史循序渐进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机会,“我要在此哭泣:这是上帝意志的伟大壮举,我们都成为了其见证人”。“两大世界力量经过长期的斗争”以“革命力量的失败”而告终,他因此受到鼓励,“对以往的多个世纪作一客观的回顾”。(17)Dominik Juhnke, Leopold Ranke, Biografie eines Geschichtsbesessenen, Berlin, 2015, S.199.兰克把普鲁士及德国在普法战争中的胜利视为世界历史发展的大转折或大结局、上帝意志的壮举,并视为自己在晚年动笔书写世界历史的主要推动力,无疑赋予了德意志统一战争及德国胜利极其深远的世界历史意义与宗教意义。
如何理解兰克的上述表态?为此,我们有必要回顾兰克投身历史研究的心理过程。兰克在莱比锡大学学习的是神学与古代语言专业,历史研究是他自己开拓的新领域。他怀着浓重的宗教情结投入历史研究,期待在历史中找到上帝。在他与弟弟海因里希的通信中,我们可以看到兰克从神学向历史学的转变过程。例如,他于1821年11月在奥德河畔法兰克福中学任教时曾向海因里希倾诉:“我希望认识上帝与人类即民族与历史,不,不是上帝(本人),而是对他的一种感觉。”(18)Gesamtausgabe des Briefwechsels von Leopold von Ranke, Band 1: 1810-1825, S.208.在对历史的深入研究中,兰克开始远离正统的神学观点,他在1822年11月就向弟弟透露了自己对《圣经》的不屑:“《圣经》还不是一本理想的书。”(19)Gesamtausgabe des Briefwechsels von Leopold von Ranke, Band 1: 1810-1825, S.341.而在1823年4月给朋友里希特(Carl Anton Richter)的信中,兰克表现出了更强的自我意识,认为“上帝不仅存在于认识对象,也存在于认识者的眼睛里”,(20)Gesamtausgabe des Briefwechsels von Leopold von Ranke, Band 1: 1810-1825, S.391.俨然以上帝自居。海因里希前往纽伦堡慈善机构工作后,陷入了虔信教派的圈子,着迷于《圣经》与福音作者的著作,兰克很不以为然,兄弟之间发生了严重的神学分歧。海因里希表示愿意妥协:“你在历史中寻找上帝,我在福音作者那里找……对于你来说,耶稣也是世界历史的中心。”(21)Gesamtausgabe des Briefwechsels von Leopold von Ranke, Band 1: 1810-1825, S.412.而兰克则坚持认为将《圣经》以及福音作者的著作绝对化是盲目崇拜:“上帝存在于所有材料中,而把某一物认定为上帝,是盲目崇拜(Götzendienst),而语言(Wort)呢?”(22)Gesamtausgabe des Briefwechsels von Leopold von Ranke, Band 1: 1810-1825, S.513.1824年年底,兰克出版了《罗曼与日尔曼诸民族史1494—1535》第一册及其附本《近代史家批判》,(23)Leopold Ranke, Geschichten der romanischen und germanischen Völker von 1494 bis 1535, Erster Band; Zur Kritik neuerer Geschichtschreiber, Eine Beylage zu dessen romanischen und germanischen Geschichten, Leipzig und Berlin, bey G.Reimer 1824.也给海因里希寄去赠书,并特地指出《罗曼与日耳曼诸民族史1494—1535》有两处冒犯基督教信仰的地方,其中自认为“太大胆的”一处文字是:“是什么使各民族兴盛与衰落?是它们的本质的发展、生长与凋零,如一种机缘巧合导致了成功?那生活中就不存在意义,我们就像被夜霜冻死的花朵。是否是那个不仅是造物主的,而且是摧残者的,对人既爱又恨的上帝?”(24)Gesamtausgabe des Briefwechsels von Leopold von Ranke, Band 1: 1810-1825, S.748-753, S.748, Anmerkung 9.
1825年4月,兰克被普鲁士政府聘为柏林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到柏林大学工作后,兰克便开始讲普遍历史或世界历史,并持续几十年。1826年11月,他在给海因里希的信中写道:“你知道我的老想法,即去寻找世界历史的传奇,我们这个物种的事件与发展的轨迹(Gang),作为它实质性的内容、核心与本质。这一野蛮的、剧烈、玷污的、善良高尚安静的、被玷污而又纯洁的创造物,这是我们本身,在其形成与形态中进行理解与记录它。我又在讲世界史的课。在我观察人们的事情时,经常心跳加快。但在表述上我还不大成功,可能我还没有完全理解。”(25)Leopold von Ranke, Das Briefwerk, S.102-103.而海因里希在此前就去信兰克,希望他能够怀着敬畏上帝的心情书写历史,以坚定人们的宗教信仰:“我感到世界历史的研究对于基督教越来越重要了。我深信就此需要上帝特别的保佑,我要与你,亲爱的利奥波德,一起就此向上帝呼吁。否则,科学的每一个方面都在为上帝不存在的观点作贡献。我不知道,还有什么能够比怀着敬畏上帝的心情来书写历史更能给人们动摇的脚步提供一个指向基督教的更坚定的方向。”(26)Gesamtausgabe des Briefwechsels von Leopold von Ranke, Band 1: 1810-1825, S.788.事实上,海因里希担心兰克正朝着“为上帝不存在的观点作贡献”的方向发展。
兰克兄弟提及的“世界历史”,首先是出于宗教视角的概念。研究“历史”的目的,是要在历史中寻找上帝的踪迹,论证上帝的存在。而研究“历史”一开始就是研究“世界历史”,因为与“上帝”相对应的概念当然是“世界”。后来“世界历史”的概念被逐渐学术化,被理解为相对于局部史、民族史的全部史与普遍历史,并从学术角度得到进一步的论证。例如,兰克于1835年2月就对海因里希写道:“从根本上来说一种观点在我心中扎根,即最终只能写普遍历史。所有我们的研究都在向着推出它的方向努力。只有在其普遍的关系中来理解,才能使个体完全显现出来。你也在做这方面的工作,这样我们在研究中与生活中都联系在一起。”(27)Leopold von Ranke, Das Briefwerk, S.265.在同年11月给海因里希的信中,兰克又提到我们后来在其学术著述中经常看到的一些概念或表述,如“世界精神”“趋势”“内在变化”“从一个时代到另一个时代”:“在此期间,我在世界历史(Welthistorie)的广阔天地里到处游历。……我尝试着书写一种不能期待得到广泛关注的历史,但它是从我的感观方式中自然出现的。如果上帝愿意,我会实现我心中的理想。世界的精神与世俗的趋势的内在变化,它们是如何从一个时代到另一个时代显现出来,相互斗争、战胜并一直扩展的。其中存在着一种发展的前后一致性(Konsequenz)、生活的丰富(Lebensfülle)与伟大(Erhabenheit),以至于每个微小的观察都让我们感到幸福。”(28)Leopold von Ranke, Das Briefwerk, S.270-271,S.270.而在1865年5月31日给曼托伊费尔的去信中,兰克又说道:“您知道,我不是将所有这些作为法国史或英国史,而是作为普遍的欧洲史、作为世界史(Weltgeschichte)来研究,在其中,一个时代连接着另一个时代(in welcher eine Epoche an die andere schliesst)。”(29)Leopold von Ranke, Neue Briefe, S.443.
在兰克1854年与巴伐利亚国王交谈中,我们可以看到其偏向于基督教与罗曼—日耳曼思想的世界历史观。他认为,“欧洲的基督教精神,特别是日耳曼思想对世界上所有其他元素的征服,完全是史无前例的”,“罗曼—日耳曼精神的传播是非常广大的,甚至更广大,因它不再受宗教形式的限制。罗曼—日耳曼精神超越了宗教的形式,作为文化在全世界自由而不受限制地扩展开来”。(30)Leopold von Ranke, Epochen der neueren Geschichte, S.443.兰克虽然注重欧洲民族共同体历史的研究,但并没有丧失对德意志历史与文化的偏爱。这一点也可以在其通信中得到证实。1867年2月,是兰克获得博士学位50周年,德国与欧洲众多大学与学术机构纷纷来函祝贺,其中包括“德意志自然研究者科学院”。该科学院的贺信可能写了一些拉近历史学与自然科学之间距离而强调科学的跨民族性的话,不过兰克的回复却特别突出了史学的民族性:“我同意您关于科学在各民族都有效的观点,但史学与文学一样,还有一个民族的血脉(eine nationale Ader)。”(31)Leopold von Ranke, Neue Briefe, S.479.对属于瑞士德语区的苏黎世大学的校长及校董事会的贺信,兰克则回复道,“我完全同意您的说法,我的研究虽然总的来说是关注欧洲民族的,但尤其是关于德意志精神的”。(32)Leopold von Ranke, Neue Briefe, S.480-481.兰克这种表态,可能与当时的政治形势有关。此时,普鲁士已经在普奥战争战胜了奥地利,成立了“北德意志联邦”,下一步只需统一德国南部。而如上所述,1871年德国统一后,兰克则将普鲁士与德国的胜利视为世界历史的结论与上帝意志的显现,并因此要撰写世界史。兰克传记作者容克(Dominic Juhnke)认为,兰克这么说,是在向当时汹涌的民族主义史学潮流靠拢。(33)Dominik Juhnke, Leopold Ranke, Biografie eines Geschichtsbesessenen, S.199.
总结起来,我们可以看到两点:在自我理解上,青年兰克怀着浓重的宗教情结开始研究历史,以求在世界历史中寻找上帝的踪迹。1825年,他以中学教师的身份凭借《罗曼与日耳曼诸民族史1494—1535》第一册及其附本《近代史家批判》进入德国大学史学界。到他告别大学讲台的1871年,兰克不仅可以回望成就辉煌的史学人生,而且可以将其终身寻求的上帝的意志“锁定”在普鲁士及德国对法国的胜利之上。经过一生的探索研究,兰克可以告慰自己,终于在晚年“找到了”上帝,看到了世界历史的结局,而且是一个由德意志民族主导人类未来发展的结局。他怎能不喜极而泣?但客观地看,我们可以观察到,早年兰克虽然宗教情结浓重,但批判意识较强,不轻易接受正统神学提供的答案,颇有反叛心理。同时,兰克的德意志民族情结也不是很突出。但是,至迟在19世纪50年代以后,兰克的批判意识似乎开始退化,关于德意志民族的积极论述有所增加,最后发展到顶点,把1870—1871年普鲁士及德国对法国的胜利作为世界历史发展的结论及上帝意志的体现。这种变化,首先要归结于兰克个人处境的改善。通过几十年的奋斗,他从一个卑微的中学老师上升为普鲁士国家的历史学家,成为受人尊敬的史学泰斗,功成名就的他失去了青年时代的批判锋芒。其次是文化环境与政治形势的影响。在兰克与他人的书信交流中,我们可以看到对“上帝”概念的过度使用,这既是出于对周边社会宗教压力的屈服,也是对这种难以抵抗的压力的一种敷衍与利用。只要提及“上帝”,显示自己的“信仰正确”,就可以方便而有效地与对方达成某种思想上的一致与情感上的和睦。(34)例如,兰克在1873年1月在给好友曼托伊费尔的信中认为,1871年普鲁士通过武力统一的德国与1850年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在1850年未能实现的“联盟”(Union)计划其实是同一种联邦制国家,而联盟计划在20年后还是实现了,就是天意:“我们承认吧:这是命中注定;上帝就是统治着世界,不管人们相信或不相信他的存在。”兰克不可能不知道,普鲁士最终实现自己的统一计划,依靠的是其军事与经济实力,参见Leopold von Ranke, Neue Briefe, S.593。同样,关于兰克在德国统一后提出的民族国家史学蓝图的叙述表明,兰克对于与自我愿望与信念不同而又不可抗拒的政治形势,也进行了敷衍与利用。面对汹涌而来的时代潮流以及根深蒂固的文化传统,老年兰克即便有自己的想法,也已经完全无力进行抵抗,只能希望与之保持和谐关系,能在新形势下继续推进自己的史学事业,并以此继续获得社会的关注与尊重。他的公开说法,在普鲁士及德意志精神的胜利中终于看到了世界历史发展的结局与上帝的意志,因此要把最后的精力投入到以德意志精神的胜利为终结点的世界史的书写中去,对于他个人、德国政界、学术界与公众来说,这都是一种皆大欢喜的说法,但不能说没有自欺欺人的成分。他所做的,是对政治形势与宗教信仰的一种敷衍,目的是在宗教与政治的夹缝中推进自己的史学事业,维护自己的社会地位。
兰克曾于1873年给在德国军队里担任牧师的儿子奥托写信,在信中他将历史学家与牧师的职业相提并论。他写道:“历史科学与书写是一种只可以与牧师的职业相比较的职业,尽管它研究的对象是如此的世俗。因为当代的潮流(die laufende Strömung)试图掌控往事,只做出符合其意义的解释。历史学家的职责是,理解并教会他人理解每个时代本身的意义。他只须客观地关注研究对象本身。在所有事务之上存在着上帝安排的万物的秩序,这一秩序虽然不可被证实,但可以被感悟(ahnen)到。在这一上帝的秩序里,它是与时代的承上启下相同的,重要的个人有其相应的位置:历史学家必须如此理解他们。历史的方法,它只寻找真实,并如此与人类的最高问题直接相关。”(35)Leopold von Ranke, Das Briefwerk, S.518.可以看到,兰克对于时代潮流对历史学的影响有着很清晰的认识,而且他主张历史学家要坚持学术立场,只“关注研究对象本身”。而他对宗教观念对历史学的影响的认识,则不是那么清晰,或许他也不愿弄清晰,因而再次提供了一种敷衍性说法。不管怎样,兰克在史学实践上,未能完全坚持自己的原则。
总而言之,与史学界以往的印象不同,兰克支持与肯定俾斯麦统一德国,并且试图以统一德国为平台实现自己宏大而丰富多彩的民族史学蓝图。他还赋予德国统一战争以世界历史结论与上帝意志的至高意义,并以此为公开的理由推进自己的世界史书写。兰克对德国统一战争的具体支持与肯定,或许主要是出于情景的压力。而以统一德国为平台实现自己的民族史学蓝图,赋予德国统一战争以世界历史结论与上帝意志的至高意义,以此为理由推进自己的世界史书写,则是对形势与环境的有意识的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