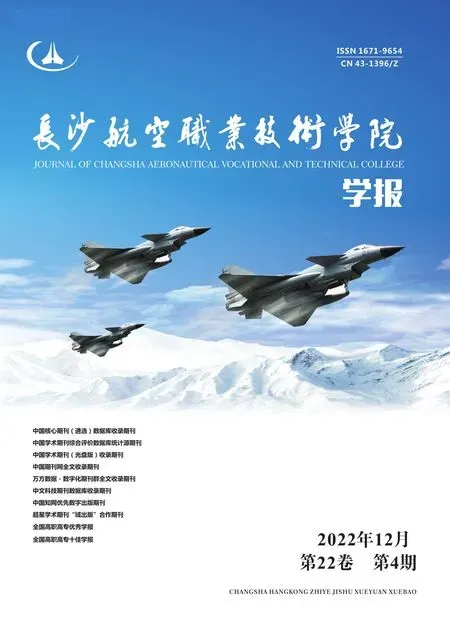政府信息公开中过程性信息的司法认定
葛自丹,肖素馨
(广州大学法学院,广东 广州 510006)
在法治政府建设不断深化和大数据时代不断推进的背景下,信息作为现代社会的重要资源,包含的价值功能不言而喻。在2019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以下简称新《条例》)的第十六条第二款首次以行政法规的形式肯定了过程性信息是政府信息存在的形态之一,但是新《条例》也未给予过程性信息一个明确的定义和界定标准,仅用讨论记录、过程稿、磋商信函、请示报告等四种表现形式形容过程性信息,那么新《条例》的上述规定可能在以下两个方面存在不同理解:一是“等”属于等内等还是等外等不够明确;二是讨论记录、过程稿、磋商信函、请示报告的界定标准未予明确。这导致法院在认定原告申请的政府信息是否属于过程性信息时经常出现认定标准不统一、同类不同判的矛盾情形,而对过程性信息的认定是下一步判断是否公开的前提条件。
为了使研究更具针对性,增加研究结论的信度和效度,本文通过中国裁判文书网、北大法宝等案例数据收集平台进行相关案例检索,将检索条件限定在2019年5月15日新《条例》颁布后的时间,根据法不溯及既往的原则,即将范围锁定在被诉行政行为作出后的时间为2019年5月15日之后的案件,大致锁定在审结日期为2020年1月14日以后的案件,并对这近两年的案例进行筛选和分析,找寻新《条例》颁布后法院对过程性信息的司法认定标准,并尝试分析可能存在的问题,在此基础上界定过程性信息的概念、明确过程性信息的认定标准。
一、法院对过程性信息的认定标准
纵观新《条例》颁布后的相关案例,法院认定政府信息是否属于过程性信息的标准主要有两个:一是信息的时间节点;二是信息的特征属性。对于以时间节点为标准的争议在于是以当事人申请信息时为标准还是以信息形成时为标准;根据过程性信息特征属性来认定分别是以不确定性和外部行政性为标准。
(一)以申请信息时为认定标准
该标准是以当事人申请信息时为时间节点来判断是否属于过程性信息,依据为2010年《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做好政府信息依申请公开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第二条规定的过程性信息属于尚处于审查、研究中的政府信息,若申请公开时信息已经不处于审查、研究等过程中,则不认定是过程性信息。
在张元贵诉重庆市永川区人民政府政府信息公开一案〔(2020)渝05行初14号〕中,原告要求公开永川府文【2012】32号请示文件(以下简称请示文件),认为征地批复已经作出,此前处于调查、讨论、研究中的征地报批文件不再属于过程性信息,具有可公开性。而法院的说理也与原告一致,认为最终的批复文件已经根据该请示文件作出,因此申请公开的请示文件已经不属于正在进行讨论、研究或者审查中的过程性信息,而是被告在履行行政管理职能过程中制作、以一定形式记录保存的信息,应予公开。同样在罗晓红诉广州市人民政府政府信息公开纠纷一案〔(2020)粤7101行初778号〕中,原告要求公开现场勘察结论和本单元同意加建电梯的业主户数和比例,法院认为当决策、决定完成后,此前处于调查、讨论、处理中的信息即不再是过程性信息。
因此,部分法院对过程性信息的司法认定是以当事人申请信息公开时是否属于过程性信息为标准的,只要申请信息时行政决定或决策已经实施,在此之前形成的信息不再认定是过程性信息。
(二)以信息形成时为认定标准
而同属于要求公开的请示文件,吴玉国诉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政府大沽街道办事处政府信息公开一案〔(2021)津03行终11号〕,却与上文张元贵一案存在截然不同的认定标准。原告认为请示文件的形成时间与被申请公开的时间相差五年,行政程序已经终结,不再属于过程性信息。但法院对原告过程已成既往的观点不予采信,认为文件的形成时间并不会改变其“过程性”的属性。持该观点的还有谢金花诉南京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政府政府信息公开一案〔(2021)苏01行终20号〕,一审法院认为认定是否属于过程性信息的着眼点是信息本身是否具备“过程性”,并不会因非行政管理活动的结束而改变其原来作为过程性信息的性质。
司法实践中,大部分法院均采用此种标准审理过程性信息的案件,依据在于新《条例》第十六条第二款的规定,只要申请的信息形成于行政机关履行行政管理职能过程中的空间范围,就均属于过程性信息。
因此,部分法院对过程性信息的司法认定是以信息形成时为认定标准,即只要信息曾经形成于行政过程中,无论行政决定或决策是否已经实施,都不会改变其“过程性”的性质和属性。
(三)以信息内容是否具有不确定性为认定标准
行政程序尚未终结前,行政过程需经一系列的讨论、研究、请示、审议或批示,具有复杂性、多阶段和多环节等特点。不确定性指的是在此过程中不同阶段或环节产生的过程性信息可能随时会发生变动的情况,可能会与最终结果呈现相同、相近或完全相左的情形,所以,信息内容存在不确定性的,应当认定为过程性信息;反之,只要信息内容确定,不论其处于什么阶段,都不属于过程性信息。
该标准强调申请信息的内容是否具有确定性、是否已经成熟,在2019 年4月新《条例》正式实施前,司法部就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修订的问题在记者会中进行回答时提出,过程性信息因不具有确定性从而可以不公开。这可以看出不确定性是衡量是否属于过程性信息的重要因素,并且在新《条例》实施后的司法案例中仍存在该标准[1]。
例如黄皓琪诉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政府及深圳市人民政府政府信息公开一案〔(2020)粤03行初39号〕,原告申请公开76号会议纪要中所称“罗湖区所形成的解决方案”(以下简称该解决方案),经法院查明,该解决方案系推进解决房改问题的方向性、原则性的思路,具体如何分工和计划还需要进一步明确和落实,故该解决方案还未完全确定,属于行政机关讨论、研究有关事项的过程性信息。
综上,法院以不确定性为认定标准的审理思路为:若最终的结果信息未形成,此时信息的内容还处于未确定、未成熟的状态,则该信息为过程性信息。
(四)以是否具有外部行政性为认定标准
过程性信息是行政机关以作出行政行为为目的,在行使行政权力职能过程中产生的信息[2],因此具有外部行政性的特征。关于其外部性的特征,在张新诉郑州市人民政府政府信息公开一案〔(2020)豫行终1289号〕中法院有所阐述,该案当事人申请公开会议纪要未果向法院起诉,法院认为就过程性信息的外部特征而言,其效果仅局限于行政机关内部或者相关单位之间,若要对行政相对人的权利义务产生直接的外部影响,关键还得借助或依赖于后续的行政行为。本案原告申请的会议纪要属于内部会议记录,并不能直接对外产生权利义务影响,属于过程性信息。
根据该特征判断是否属于过程性信息,法院之间也存在不同认定,例如陈鹭琦诉厦门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行政监察一案〔(2020)闽02行终236号〕中,原告申请公开关于某公司实施经济性裁员情况的两份报告,一审法院认为这两份报告是人社部门向上级部门呈报的报告,具有过程性的特点。而二审法院经审理后查明两份报告实质是行政机关上下级之间的情况通报,目的在于让上级部门了解、知晓企业经济性裁员的情况,后续无需对此进行审查或作出行为,因此一审法院认定为“过程性信息”实属不当,应当是内部管理信息。
综上,法院以外部行政性为认定标准的审理思路为:若行政机关是以作出行政行为为目的履行职能,在此过程中产生的信息不会直接对外产生权利义务影响的,则认定为过程性信息。
二、过程性信息认定标准存在的问题
(一)与结果性信息分辨不清
无论是以申请信息时为认定标准还是以信息是否具有不确定性为标准,都需要判断产生最终对外效力的行政行为是否已作出,是否具有不确定未完成的状态,据此部分案件存在与结果性信息分辨不清的情形。
例如在刘某诉南通市人社局政府信息公开一案〔(2022)苏06行终37号〕中,行政机关与法院之间就申请的信息是属于过程性信息还是结果性信息产生分歧。刘某因向人社局请求公开责令某集团为职工补缴保险的《劳动保障监察期限改正指令书》(以下简称《指令书》)和《行政处罚决定书》未果,提起行政诉讼。一审法院认为单位已后期整改,未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书》,因此《指令书》属于具有确定性的最终行为,不予公开不成立。人社局上诉称,《指令书》属于行政程序处理前的命令行为,是处于准备阶段的过程性信息。而二审法院驳回上诉,认为本案人社局向该单位作出《指令书》后,在执法期限内未再作出行政处罚决定或撤销立案决定,《指令书》呈现出具有权利义务影响的最终性的特点,不符合非正式性、未完成性的过程性信息的特点。
此外在司法实践中对会议纪要的判断也存在较大争议,其在形式上具有内部讨论协商形成意见信息的过程性特点,但有时会议纪要也会产生对外效力的结果信息,需要拨开云雾见其本质。例如韩永亮诉郑州市人民政府政府信息公开案〔(2019)豫行终3868号〕中,一、二审法院就对会议纪要作出不同的司法认定。该案一审法院认为会议纪要属于行政机关通过内部集体讨论研究的方式就特定事项形成的内部意见或者工作安排,不直接对外产生法律效力,具有过程性和决策性的特点,因此属于过程性信息。而二审法院认为一审法院仅注意到了会议纪要的过程性特点,忽略了其决策性的本质属性,会议纪要既有内部讨论的过程记录,也有对外产生影响的结论意见,二审法院认为本案中该会议纪要通过一定方式外化产生了结论信息,已经不属于过程性信息,因此撤销了一审法院的判决。
由此可见,过程性信息具有非终局性,不对外发生权利义务影响的特点,这是与结果性信息区分的关键。
(二)与内部管理信息易混淆
若以信息形成时为认定标准,过程性信息则是形成于内部行政过程中,是行政机关在对外作出行政行为的过程中产生的信息,虽不直接对外产生权利义务的影响,但与最终形成的结果信息具有一定的因果关系;而内部事务信息无涉于行政机关外部,强调的是“事务上的内部性”[3],几乎涵盖人事、财务、行政内部事务安排、会议纪要、内部办案流程、各机关和人员之间的意见交流信息或内部文件等关于行政运转方方面面的信息[4],并不会产生对外的效力。这可以看出内部管理信息与过程性信息虽有对内和对外的区别,但都具有内部性和不对外产生效力的特点,多数情况下属于“意思形成”的信息,并且涉及的领域范围也存在交叉和重合(见表1),因而两者的内涵和外延容易混淆。

表1 过程性信息和内部管理信息在司法实践中的具体类型比较
但从法律规范层面,两者于2010年的《意见》第二条规定在同一款中,到新《条例》颁布后分别规定在第十六条第一款和第二款中,说明立法者有意对两者进行区分,然而部分法院在司法实践中却将两者的概念混淆。除了上文提到的陈鹭琦诉厦门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行政监察一案中,一、二审法院对于过程性信息和内部管理信息的认定不统一,此外部分法院还存在将两者不区分的情形,如直接表述为“内部信息”,抑或直接创设“内部过程性信息”的概念。
这些表述直接回避了两者的区分,如果在内部管理信息和过程性信息涉及领域类型存在交叉重合的情况下对两者的表述不够规范,对其内涵、特征理解不到位,极有可能导致法院对相同案件作出不同裁判。
三、法院认定过程性信息的完善建议
(一)对过程性信息进行概念界定
导致上述“内”与“外”、“过程”与“结果”的概念区分不清的原因是对过程性信息的概念不明确,新《条例》也未给予过程性信息一个明确的定义和认定标准,仅用讨论记录、过程稿、磋商信函、请示报告等四种表现形式形容过程性信息。而学术界也存在不同的认定,这就导致法院在认定时出现标准各异、同类不同判的矛盾情形。因此笔者结合过程性信息的特征和法律规范的规定,总结出过程性信息应具备的主体标准、空间标准、目的标准和效力标准,并以此对过程性信息进行概念界定。
第一,过程性信息应符合主体标准,即形成于行政机关履行职能过程中。过程性信息首先是政府信息,应属于《条例》调整的范畴,根据新《条例》第二条的规定,政府信息是行政机关在履行行政管理职能过程中制作或获取的信息。而其他主体制作或获取的信息不属于《条例》调整的范畴,例如刘军诉聊城市人民政府政府信息公开一案〔(2021)鲁行终670号〕,原告申请公开“最高院在某案庭审过程中要求聊城市人民政府作出房屋征收补偿决定书的有关材料”,法院认为该材料系人民法院在审理案件过程中形成的材料,属于司法信息,依法不属于政府信息。该案材料制作的主体是司法审判机关,非国家行政机关,不符合过程性信息的主体标准。
第二,过程性信息应符合空间标准,即处于未成形的内部交流环节。行政过程具有复杂性、多阶段和多环节等特点,需经一系列讨论、研究、请示、审议或批示等内部交流环节,涉及各行政机关之间或行政机关内部人员之间的信息交流,在行政程序尚未终结前这些信息都未成熟,具有不确定性。且在内部交流环节中产生的过程信息,并不只包含带有主观讨论性的意见性信息,还包括纯粹的事实性信息,以及既体现意见性又体现事实性的混合性信息[5]。
第三,过程性信息应符合目的标准,即为作出行政行为而实施。过程性信息指向一个明显的目的,即为作出行政行为而实施,从此产生了一批服务于行政行为的信息,如果没有作出行为的目的,就不具有外部行政性,也就谈不上过程性信息了。可以看出内部事务信息与过程性信息最大的区别也即外部行政性,内部事务信息不需要对外作出行政行为,具有“事务上的内部性”,例如人员编制安排、员工奖惩规定等不会对外产生权利义务影响的信息。
第四,过程性信息应符合效力标准,即对外尚未产生实质影响。行政行为终结产生结果信息才会产生对外的实质影响,为作出行政行为而实施的一系列过程产生的信息并不具有事实上的处分效果,因此判断是否属于过程性信息可以借助行政过程或者行为内容是否形成、变更或者消灭行政法律关系,这是与结果性信息区分的关键。例如上文提到的刘某诉南通市人社局政府信息公开一案,南通市人社局没有按照法律规定对某集团作出撤销立案决定,即没有对外作出具有终结行政程序功能、消灭行政法上权利义务关系的行政行为,《指令书》在行政程序中表现出的是外部性和最终性,是具有权利义务影响性和成熟性的行政行为,不符合未完成、不确定性等过程性信息特点。
综上,过程性信息是指形成于行政机关履行职能过程中,处于未成形的内部交流环节,为作出行政行为而实施,对外尚未产生实质影响的政府信息。
(二)统一和明确过程性信息的认定标准
对于以时间阶段为标准的认定,是以当事人申请信息时为标准还是以信息形成时为标准,笔者赞同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在孙加香诉邹城市人民政府政府信息公开一案〔(2021)鲁行终97号〕中的认定标准,山东高院认为认定政府信息是否属于过程性信息的标准是信息形成的时间节点,而非当事人申请信息公开的时间节点。
新《条例》修订前对于过程性信息具有参考性价值的主要有两处:一是2010年《意见》第二条规定,以“处于……中”来定义过程性信息,该定义侧重于过程性信息的暂时性状态,一旦行政行为完成或实施,过程性的暂时性状态即消失;二是最高院于2013年发布的政府信息公开十大典型案例中的第五个案例,姚新金、刘天水诉福建省永泰县国土资源局信息公开一案,该案二审法院认为“一书四方案”已经过批准并予以实施,不再属于过程性信息[6],即认为行政程序终结前的信息不再是过程性信息,该案以指导案例的形式为当时处于模糊界限的过程性信息的司法认定开辟了一条可操作性的路径。根据上述两个规定可以看出,在新《条例》修订前过程性信息是以时间阶段中当事人申请信息时为认定标准的,只要申请信息时行政决定或决策已经实施,在此过程中形成的信息就变成了非过程性信息。
而对比2019年5月新《条例》对过程性信息的定义,将“处于……中”变更为“在……过程中形成的”,两者对比不难发现,“在……过程中形成的”比“处于……中”更能否定过程性信息的暂时性阶段而注重过程性的空间状态,说明新《条例》已经抛弃了以时间阶段中的申请信息时为认定标准下定义,而改为以信息形成时政府信息的性质属性为认定标准,过程性信息的性质是绝对的,不会因其相对的行政行为完成而改变过程性的状态。而以申请信息时为认定标准的过程性信息的范围显然过于狭窄,其割裂了行政决定或决策与过程性信息之间具有的因果关系,将结果性信息等同于过程性信息。并且无论是从法律位阶还是制定时间,新《条例》都比规范性文件《意见》更具有优先效力,因此应当统一以信息形成时为认定标准。
对于以过程性信息的特性为标准的认定不存在相关争议,在司法审判中可以根据不确定性和外部行政性的特征属性为标准对过程性信息与内部管理信息以及结果性信息进行辨析。过程性信息和结果性信息是“过程”与“结果”的分辨,应以信息内容是否具有不确定性为认定标准,若申请的信息不存在对外作出具有终结行政程序功能、消灭行政法上权利义务关系的行政行为,则是属于过程性信息。过程性信息与内部管理信息是“外”与“内”的辨析,应以是否具有外部行政性为认定标准,若申请的信息是为作出行政行为而实施的,具有明显的目的性,则是属于过程性信息。
四、结束语
政府信息公开是预防“密室政治”、权力暗中运行的重要举措,更是保障公民知情知政,加快推进法治政府、阳光政府建设的有效途径,而过程性信息于2019年首次以行政法规的形式出现在新《条例》中,关于过程性信息的判断结论,是能够直接影响政府信息是否公开的决定性因素,是政府信息公开的重要一环,而且过程性信息的类型多样,行为过程也具有复杂性、多阶段和多环节等特点,在司法实践中,其认定存在较大困难,所以笔者结合司法实践,提出上述认定标准,期待能够为司法实践提供比较完备的过程性信息认定标准,同时也期待未来在涉过程性信息认定的案件中,能以信息形成时为认定标准,并以信息内容是否具有不确定性和外部行政性为认定标准区分与之易混淆的内部管理信息和结果性信息,统一过程性信息的司法认定标准,消解同案不同判的尴尬境况,为建设法治政府、阳光行政扫清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