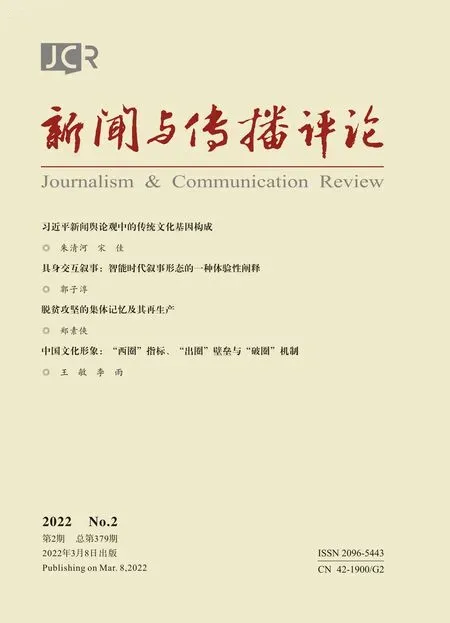习近平新闻舆论观中的传统文化基因构成
朱清河 宋 佳
“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中国五千年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与魂,是中国人民特有的精神基因与血脉。铸牢中国文化,弘扬中国文明,无疑是实现国强民富、国泰民安、促使中国这个社会主义国家永远巍然屹立在世界东方须臾不可或缺的条件。习近平始终重视文化价值,强调文化自信,无论从“修身”“弘道”还是“治国”层面,习近平都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当之无愧的承续者、弘扬者和创新者,其丰厚的史书典籍积淀给予了自身“博观而约取,厚积而博发”的文化底气,其坚定的马克思主义立场为其“执古之道,以御今之有”的战略谋划贡献了思想遵循。正是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明的互构互融互诠中,创立且发展了极具中国风骨与时代韵味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习近平新闻舆论观作为其中的一个重要分支和有机组成部分,同样深受中国精神与文化价值的指引与哺育,这一点从习近平在新闻领域一系列重要讲话、文章、批示及谈话内容中旁征博引的中国典籍和诗词歌赋即可窥见。目前学界的研究论域主要集中在对习近平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观和其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以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结合的探索上,且多侧重简单的学习、概括和解读,而对于习近平在指导新闻工作中大量借鉴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并赋予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以新的时代意义的现象,却鲜有文献关涉,更鲜有文献基于习近平新闻舆论观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点进行更深入的论述与提炼。
由于习近平新闻舆论观是一个科学完整、立意深邃、内涵丰富的思想体系,是习近平关于新闻宣传、新闻舆论、网络治理、国际传播、新闻业态、新闻媒体等诸多与“新闻”具有内在联系的重大命题的理论观点与意见指导,故而不难理解本文所要阐述的习近平新闻舆论观是在广义新闻基础上的广义新闻观。从“‘观’层面的观念,原则上包括主体关于对象之‘所是’‘所应’的观念,还包括主体针对该对象展开相关实践活动时应该如何对待对象、改造对象的观念”[1]来看,习近平新闻舆论观则可以理解为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关于“新闻(广义)所是”“新闻(广义)所应”以及“如何对待改造新闻(广义)”的全面观念,是习近平在马克思主义新闻认识论、马克思主义新闻价值论、马克思主义新闻方法论相统一意义上形成的关于新闻(广义)的系统性、根本性观点和看法。笔者即借用“观”哲学的这三个维度,以新闻认识论、价值论与方法论的分析框架,钩稽爬梳习近平新闻舆论观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创新与运用。
一、认识论:习近平马克思主义新闻认识论内蕴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以物为法”“由其法象,推其神化”等文化基因
任何缺少事物实然知识的价值判断都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任何不基于事物规律的实践行动也如无根的浮萍,极具盲目性与偶然性。对新闻的理性认识无疑是新闻价值论与方法论的前提,而“新闻价值如何”与“如何改造对待新闻”也必然关联对新闻内在逻辑与规律的追问。故而,习近平关于新闻舆论工作规律、性质的深刻认识,无疑是其对新闻整体观念中的基础性、根本性观念,决定了其他理论观点与指导原则转换为新闻实践的具体成效。
自1989年习近平在《把握好新闻工作的基点》一文中第一次将新闻规律上升到与政治性并行的高度,认为“既要强调新闻工作的党性,又不可忽视新闻工作自身的规律性”[2]起,此后讲话又多次强调了新闻工作必须尊重新闻规律。“尊重”本身包含了习近平认为唯有承认“新闻规律”作为客体的客观存在并给予其科学的认识,才能做到尊重规律的认识逻辑。
其实,早在我国古代,就已经有许多著名思想家、哲学家从不同角度对认识问题进行了理论求索,形成了丰富且深刻的中国古代认识论思想。首先,在认识如何发生的问题上,譬如管子率先提出“其所知,彼也;其所以知,此也”(《管子·心术上》),对构成认识系统的两个基本元素进行了区分,认为认识活动的发生正是认识主体作用于客体的过程。而孔子通过“为己”与“成人”将人从统一的物质世界中分离出来,明确了人相对于客观世界的主体性以及认识客观世界的主体是人。人之所以能作为认识主体进行认知活动,在于“知,材也”(《墨子·经上》),即人具备认识的能力。王夫之则进一步从唯物主义立场提出能所关系:“体俟用,则因‘所’以发‘能’,用乎体,则‘能’必副其‘所’。”(《尚书引义(卷五)》),表达了人的“能知”特性或认知能力只有在与客体对象相接相交的过程中才能实现。尽管整体而言,王夫之的哲学观终究没有摆脱心性哲学框架的束缚,其能所思想与其“心性论”难以形成逻辑自洽,但其关于名副其实、名实相称的“以物为法”思想成为古代传统知行观与认识论的高峰,哺育了一代又一代的现代学者。
习近平作为当代中国共产党党中央的领导核心与新时代的领路人,同样受到中国古代认识发生论思想尤其是王夫之存在论哲学的影响。譬如其曾在十八届五中全会上引用王夫之在《张子正蒙》注解中的“理者,物之固然,事之所以然也”(《张子正蒙注·至当》)来说明只有深刻认识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并转化成理念,才能避免盲目性,为发展行动提供正确的行动指南,就是其借中国典籍承认事物自身规律性的生动表现。此外,习近平还使用“事不凝滞,理贵变通”等(《宋史·列传第十五点赵普》)进一步指明规律也非一成不变,要以发展的、实际的眼光对待其自身的变动。可以说,习近平这种熟练运用古籍阐释事物规律的独特方式,使得其无论在论及自然规律还是社会历史规律时,无疑都携带着中国古代存在论哲学的影子。也正是基于此,习近平多次强调新闻(广义)规律,指出“党的新闻舆论工作是一门科学,必须按照规律办事”[3],并随着互联网给新闻工作带来的重大挑战与颠覆性变革,又与时俱进地提出要把“遵循新闻传播规律”向“遵循网络传播规律”“遵循互联网规律”“遵循新兴媒体发展规律”的方向拓展,实际上也形成于其马克思主义思维方式与中国文化思想资源相互融合、共同作用的过程中。
事物“理”之存在自然衍生了认识“理”之过程、层次与方式的问题。习近平在此方面亦受到我国诸子百家思想的浸淫与濡染,分别在不同场合引用荀子的“善学者尽其理”、朱熹的“穷理者,欲知事物之所以然,与其所当然者而已”以及王夫之的“名非天造,必从其实”等说明要透过皮相穷及本质的认识思想。由于新闻舆论具有极强的意识形态属性,在正确的政治立场与价值观的引导下探索新闻(广义)规律则显得尤为重要,习近平相关的论述则主要从以下两个维度体现:一是大局与微观的维度,习近平在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指出,“先立乎其大者,则其小者不能夺也”(《孟子·告子上》),强调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是所有新闻舆论工作的定盘星与导航仪,是所有新闻工作者的思想前提与精神脊梁,必须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毫不动摇;同时又说“太山之高,背而弗见;秋毫之末,视之可察”(《淮南子·说林训》),要求具体的新闻报道必须落于细、落于小,落于实,要通过对基层、对实际环境细节的捕捉与观察实现思想与内容的统一。二是从对新闻工作由表及里、由浅入深的认识维度。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先是引用《二程遗书·伊川先生语》中的“为学之道,必本于思”“不深思则不能造于道”讲述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深度问题,又引用恩格斯的相关话语进行补充说明,无不体现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在认识层次论方面的共通性与契合性,正如习近平所说,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资源“是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包括新闻学)发展十分宝贵、不可多得的资源”[4]。如果说这还只是习近平针对整个哲学社会科学的总体性论述,那么在“2·19”讲话中,习近平直接面对广大新闻编辑工作者,将其工作的深度与王冲在《论衡·别通》中提出的三个涉水层次相比对,认为浮于表面的“浅水者”所见不过鱼虾之属,能够继续深入的“颇深者”才有可能“发现”更多的新闻宝藏,在进一步融事物内在机理与个人情感、思维以及知识结构的过程中最终到达“尤甚”,从而挖掘出真正有价值的新闻,睹“蛟龙”之大观。譬如习近平提出的“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不仅是其对国际舆论格局、对外传播的理性认识与仁义、理性等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元素有机融合的结果,而且其宣传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本身就是在诉说一个个精彩的中国故事。
然而这也不意味习近平要引导新闻工作者忽略表层的“鱼虾之属”。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来看,感性认识是理性认识的基础和来源,是获得事物规律的必由之路;从中国传统哲学认识论来看,在《习近平用典(第二辑)》中习近平共引用4部王夫之的论著,其中《张子正蒙注》是特点异常鲜明的一部哲学著作,总体反映了王夫之在认识论问题上继承张载对知识包含“见闻之知”和“德性所知”的划分,并进一步致力于二者统一的尝试,认为见闻之知虽具有局限性,无法触及事物的规律和本质,但却在某个侧面、某种程度蕴含了真理的颗粒,这一认识发生论观点与其认识存在论观点是一脉相承的,于是才有了“由其法象,推其神化”“即象可以穷神、于形色而见天性”的思想。习近平在引用其“事物之理”客观存在的观点时自然蕴含了其认识发生论的核心思想。了解这一点,才能正确把握习近平关于新闻现象与新闻规律辩证关系的总体思想及其中的中华文化思想资源。
从现象到规律的认识升华,需要一系列“思”的过程,而“思”又主要源于对“学”知与“亲”知的扬弃与深化。习近平首先非常重视学习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譬如曾多次引用典籍包括荀子的“学者非必为仕,而仕者必为学”、庄子的“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等来强调领导干部必须不断学习以解决本领恐慌、本领落后的问题。面对新闻舆论工作者时,习近平则主要强调要通过读经典学新知而拓视野看大势,不仅要从书本、广大人民群众以及学者专家中汲取养料,也要取国外经验而学之;不仅要向前看学新用新,亦要立足当下向后看学习一切异时的、古今旦暮之经验。正如其所说,“在长期实践中,我们党的宣传思想工作积累了十分丰富的经验。这些经验……是做好今后工作的重要遵循……并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5],尽管这里是从一般意义上讲党的整体宣传思想工作的经验借鉴,但由于新闻工作属于宣传思想工作的范畴,自然同样适用。其次,习近平也非常重视亲身行动下获得的知识,即相较于“学”之间接的直接之知,这从其引用《说苑·政理》《荀子·儒效》的经典名句以说明闻、见、知、行等认知方式中“行”高于一切的观点即可看出。其认为新闻工作者只有深入基层,深入实际和人民,在询实话、察实情中坚持做全面扎实的调查研究,才能获得真知,寻得规律,收到时效,并在技术、理念、内容、机制体制等全方位创新实践中锚定媒介融合的方向,进而推动现代化传播体系的建构。实际上,这种基于“学”与“亲”而“思”的过程正所谓体现了“学所以益才也,砺所以致刃也”(习近平在《之江新语·要善于学典型》等文中运用)所表达的道理,然而习近平在引用时只用了前一句,若结合原典中后一句对其的解释说明:“吾常幽处而深思,不若学之速;吾常跂而望,不若登高之博见”以及习近平的相关讲话、论著等,则更容易体悟习近平的只有“学”与“亲”与“思”并行不悖才能正确认识并把握新闻舆论规律的重要思想。
习近平马克思主义新闻认识论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主要特点有二:一是引用诗词歌赋、诸子百家起补充说明的作用,增强文本的说服力和亲和力。譬如引用“凡贵通者,贵其能用之也”说明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引用《随园诗话补遗》中对鱼虾、菱笋经过一段时间会变味变质的描述说明新闻时效性,生动形象易于理解。二是赋予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以时代意义与新的理论内涵,譬如习近平在阐述新闻真实性时援引王符《潜夫论·务本》中的“忠信谨慎,此德义之基也;虚无谲诡,此乱道之根也”,但其并未止步于泛泛之谈,而在多次讲话中利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立场逐渐丰富所谓的“忠信谨慎”的内涵:一方面是从新闻本体出发,要求“根据事实来描述事实”[6],做到文本真实与本质真实、个体真实与全局真实相统一;另一方面,则从整个新闻舆论工作出发,要求新闻工作者坚持揭露假恶丑与鼓励真善美并行,做到舆论监督与正面宣传的统一,从而赋予了“忠信谨慎”在新时代新闻领域新的意义与内涵。
2014年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上,习近平首次以“运用规律”代替“尊重规律”[5]的说法,指出做好网上舆论工作必须“创新改进网上宣传,运用网络传播规律”[5],从而更加直接、更加鲜明地表示出认识的最终目的和落脚点不在认识本身而在于实践,即如何更好地运用新闻规律,如何按照规律办事。关于实践的具体方式是属于“方法论”的范畴,将在下文详细论述,此处谨以此从认识论层面上阐明。虽然习近平擅于引用诗歌词赋、古代名典、俗言俚语等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成果,其新闻观也常闪烁着中国优秀传统认识论思想与理论的光芒,但绝非纯粹的挪用和套用,而是基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对中华文化的取舍与扬弃,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对强调认识本身而缺乏实践意义的中国传统认识论成果的创新性发展与创造性转化。
二、价值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是习近平人民中心新闻观的思想渊源
新闻观的灵魂与核心是新闻价值观,需要回答新闻应该为谁服务的问题。习近平有关“人民至上”“以人民为中心”等新闻观话语代表了习近平新时代新闻舆论观的根本价值旨归,是习近平以马克思主义人民立场为基本原则,融合中华文化进而回应时代关切、构建基本价值取向的当代理论创新,内蕴中国传统民本思想的理论滋养。
中国民本思想大抵朝着“以人为本”和“以民为本”两个向度发展:“以人为本”是指在神与人、天与人的关系中置“人”于本的位置,主张远鬼神,重人事,肯定“人”的主体价值;而“以民为本”则是在君与民的关系中置“民”于本的位置,肯定群众的主体价值,习近平正是在对二者之精髓的汲取与运用中,形成了饱蘸中华风骨的习近平新时代“以人民为中心”的新闻舆论观。
首先,习近平继承了“以人为本”思想中冲破对天神盲目的信仰与崇拜,从而高度肯定人的价值与力量的文化精神,强调人类发展的价值关切点应该回归人类本身,世界“各国应该有以天下为己任的担当精神,积极做行动派、不做观望者,共同努力把人类前途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7]。“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习近平遵循马克思主义主体性理论,依托中华文化中“天人一家”“天下格局”“人文情怀”等凸显对世界与人本真关注的“人本”思想,而形成的具有中国风格的世界性概念,其所提出的全球治理观、新发展理念、新安全观、“一带一路”建设以及包括和平、民主等在内的人类共同价值理念等对外传播话语体系;其以全球视野,提出的既要把中国故事、中国文化推向世界,又要擅于以中国眼光、中国方案回应国际议题从而满足国内国际对中国新闻需要的“内外并重”国际传播格局;其强调国内外媒体开展深度合作,不仅要站稳中国立场,发扬中国精神,而且要充分考虑外国受众的根本需求与话语习惯,以提升我国媒体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等等,无不体现着中华文明发挥人类主体地位、强调人类生命价值、关照人类整体命运、解决人类共同难题的“天下”观以及“美人之美”“美美与共”的人文关怀与人类情怀。
其次,习近平创新发展了“以民为本”的思想,形成了一系列凸显“人民至上”的新闻理论话语。重“民”与重“人”的传统不同,其脱离了人本思想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哲学范畴,而更多地被用于经济、政治等领域,具有特定的含义与一定的现实意义。在我国,关于“民”的表述最早出现在夏禹时期“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尚书·夏书·五子之歌》)中,管仲于此基础上确定了“民”之士、农、工、商的身份。而孔子的“仁者爱人”、孟子的“君轻民贵”、老子的“以百姓之心为心”、荀子的舟水之喻等又进一步将民本思想推向理论化、系统化。之后随着君主专制主义的不断强化,民本思想也越来越朝着工具化的方向发展,譬如:董仲舒提出的通过“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的策略得民心、得民心进而得天下的思想;程颐提出的顺民、厚民、安民、不扰民的为政之道等等都将“民”作为治国之基础。直到明清以后,黄宗羲、顾炎武等人在批判君权、反对专制的基础上,促使民本思想的现代化转型开始萌蘖。由此不难看出,尽管中国传统民本思想历经几千年文明的洗礼表现出鲜明的理性色彩,但其本质上并没有摆脱封建制度的窠臼,是在封建专制主义之下的集“重民、敬民、惠民、得民、安民、爱民”与“畏民、治民、驭民、愚民”为一体的思想体系,习近平对这一思想体系的扬弃与发展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方面,取民本思想中闪烁“德”性精神的内容要义,去其“庸”的糟粕,回答了“为了谁”的问题。在我国,人民是一切工作的重心和出发点,习近平曾多次引用郑板桥的诗表达了“一枝一叶总关情”的为民情怀。所谓“为民”,就是从萧萧竹联想到民间疾苦、就是为官之人如竹子般清雅高尚的节操与对人民执着诚挚的关切之情;所谓“为民”,就是群众面前无小事,时刻把百姓的冷暖安危挂在心头,就是站稳群众立场,与人民同心同德。在新闻领域,就是及时反映群众愿望,表达群众要求,把维护、回应、满足人民根本诉求作为新闻活动与实践工作的价值皈依,在积极教育、服务、引导人民群众的过程中也尽可能提升人民的德行素养,“多宣传报道人民群众的伟大奋斗和火热生活,多宣传报道人民群众中涌现出来的先进典型和感人事迹”[5]。而早在习近平于宁德地区抓文化建设时就提出讲宣传既要有思想的内容也要重视形式的适用性,而好的形式至少应该为群众所喜闻乐见、有群众性、少花钱、多办事并合乎大家的口味;[2]在福州任职期间将媒体视为解决群众现实问题与实际困难的重要渠道,为更进一步便利福州人民还组织指导编写了《福州市民办事指南》等新闻工作方面的探索与实践,也无不凸显着习近平浓厚的“为民”情怀。
此外,中国传统民本思想中还有利民、爱民、惠民等文化精神也为新时代“以人民为中心”的中国特色新闻业贡献了深沉的价值旨归。在利民中,习近平引用“利民之事,丝发必兴;厉民之事,毫末必去”(《周官辨非·天官》)强调走群众路线的本质与意义,并根据互联网及社交媒体带来的党群互动方式的变迁,进一步提出网络群众路线的命题,从而翻开了“利民”思想向网络领域开拓和创新的新篇章,为信息化条件下开展群众工作提供了新理论、新方法与新模式,更为如何利用互联网给群众办实事指明了方向。在爱民中,习近平基于《晏子春秋·内篇问下》中意高于爱民、意下于刻民,厚行于乐民、贱行于害民的思想,进一步突破“爱民”为了“用民”的局限,将“爱民”从“意愿”的私域上升至公德层面,提出“德莫高于爱民”,进而要求新闻媒体必须具备深入群众日常,展现群众生活,把党性和人民性统一起来,把反映党的意志与诉说人民心曲统一起来的职业素养与道德品性,架好党和人民连接彼此、交流互通的桥梁。在惠民中,习近平则借用“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管子·牧民·四顺》)表达人心的顺逆与向背是政权政党命运前途的关键,新闻媒体作为党和国家的喉舌,就必须在工作中把应该抓住、推进和聚焦的重点与群众最急、最盼、最忧的事情联系起来,为厚植党的人民群众基础、满足管子提出的人民“四欲”(即:佚乐、存安、富贵、生育)提供充分的信息资源、思想引导乃至良好的社会氛围。
另一方面,创新继承“人心向背”思想,回答“依靠谁”的问题。习近平指出,新闻舆论工作者要回答好“依靠谁”问题,关键在于从思想上是否澄清了人民的主体地位,在工作中是否坚持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根本方法。儒家思想指导下的“民为贵”“立天王以为民”理论以及诸如“轻刑薄税”“省徭役”“劝农事,不夺民时”等具体方略已有了通过得民心而巩固政权的影子,而管子则明确指出政权的成败关键在于人心的向背与顺逆,即顺应民意则政令可推行,违逆民心则政令废弛,从而道出了民心与执政之间相辅相成的关系。但囿于历史局限性,其终究没有跳出封建等级制的框框,依然是一种“固君位”“强社稷”的统治术、是打着德治的旗号行唯权力唯君主马首是瞻的现实却不可否认。习近平常说,人心向背是最大的政治,关系党的生死存亡,但其对“人心向背”的使用是在对“君民二元对立”等封建思想沉渣蠲涤的基础上使用的,是将“人心向背”这一政治话语创造性地发展到“人民中心”思想的优秀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创新者。这里的“人民”概念不仅代表从“四民”(《管子·小匡》提出的士、农、工、商四民)到一切对社会发展发挥推动作用的社会成员的范畴升华,而且从根本上澄清了官与民不是差等有序、亲疏有别、各安其分的关系,而是在同一阶级内部分属不同社会分工的统一体,具有相同平等的地位,正如习近平多次强调的“我们是从人民中来的”,[8]自然也要回到群众中去。基于这一思想前提,习近平指出,新闻工作者依靠人民就要把话筒、声筒、笔尖、镜头面向群众,坚持把人民作为报道对象,把人民伟大生活作为报道题材,把人民经验成果作为宣传典型,依靠人民的生活提供新闻素材;就要愿做小学生,诚心正意地向群众请教、向人民学习,依靠人民的知识提高工作效率;就要尊重人民群众的创造热情与创新精神,汇聚民智,凝聚民心,将群众的智慧、经验总结升华后再返回到群众中进行宣传学习,扩大试点范围,依靠人民的智慧扩大报道范围。这不仅是对新闻工作在新时代面对新形势处理新事务化解新矛盾的内在要求,更是习近平时刻把人民放在首位的生动写照。最后,正如习近平所说:“让群众满意是我们党做好一切工作的价值取向和根本标准,群众满不满意是一把最好的尺子。”[9]对新闻工作成效的检验也必须重新交回人民手中,从而把“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真正落到实处。
三、方法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辩证法”与辩证唯物主义方法的交融与贯通为习近平新时代新闻舆论观提供方法论指导
新闻观主体在新闻方法论意义上的观念,就是对新闻工作者在展开新闻实践活动时应该如何对待新闻、如何改造新闻的观念,具有鲜明的实践指向性。习近平一直以来都非常重视马克思主义科学方法论的运用,将其视作共产党人的看家本领,治国理政的无价之宝,曾多次强调“要学习掌握唯物辩证法的根本方法”[10]。同时,其在学习运用马克思主义方法论时又不忘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与贯通,习近平新时代新闻舆论观中所包括的思想方法、思维方法与具体工作方法等即是在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与中国传统辩证法的融合下所形成的极具中国风骨和中国气派的理论产物。
中国传统辩证法是在中国沃土上,由中国人民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中集聚而成的理论智慧与思维方式,内含实践辩证法和唯物辩证法。实践辩证法在发展中逐渐形成了知行合一、统分有度、“同异相宜,和而不同”等形式多样、内涵丰富的话语体系;而唯物辩证法也包括多个面相。譬如:在世界普遍联系与整体性方面,《尚书·洪范》首先提出五行说,初步分析了金木水火土五行间的普遍联系与相互关系,思孟学派将其从自然界延伸至人类社会,进一步提出父子之仁、君臣之义、宾主之礼、贤者之智、圣人之道的道德五行说,以表现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依赖关系。而庄子“万物与我为一”的齐物论更进一步把自然界与人类社会联系起来,提出了天地人共生共存、世界万物和谐统一的“天人合一”思想,至此中国传统哲学对“客观世界是一个相互联系的世界”的认识与唯物辩证主义中事物普遍联系的原理已经有了相当的一致性。在事物发展变化方面,譬如“变化者,乃天地之自然”(《抱朴子·内篇·黄白》)、“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孙子兵法·虚实篇》)、“变动不居,周流六虚,上下无常,刚柔相易,不可为典要,难变所适”(《易传》)等均表达了世界无时无刻不在变动之中的观点,并在此基础上发展出“动静互涵,变常不二”的运动变化规律、“积土成山、积水成渊、积善成德”的量变质变规律以及调和量质转化关系的“中庸”之道。在对立统一方面,中国思想家不仅看到了矛盾统一于事物内部的辟翕关系,提出“负阴抱阳”(老子)、“一物两体”(张载)、“一分为二”(朱熹)、“合二为一”(方以智)等一系列命题,亦认识到矛盾的摩荡与消长是促使事物变动发展的根蒂,譬如古籍中的“阴阳合德,化生万物者也”(《梦溪笔谈》)、“刚柔相推而生变化”(《易经》)等均是对这一思想的表现。可以说,中国传统辩证法即是在上述唯物辩证法和实践辩证法的纵向深化与横向交融过程中不断补充完善,螺旋上升。
尽管其在发展中仍以直观、朴素为主,且不成体系,需要人们主观体悟与想象的进一步辅助才能完成逻辑自洽,从而与科学的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方法存在本质上的区别,但在“人类经验共有一个世界”[11]这一信仰上,中国古代先哲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却从“殊途”走向“同归”,为中国传统辩证法与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的汇通提供了契机与客观基础,并在中国土地上实现了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民族化与中国化改造。而习近平则站在新的起点上援古证今、借古喻今,依据新时代新闻界的实际对中国传统辩证法进行接纳、改造和运用,形成了许多适用于新闻舆论工作的真知灼见,把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方法论思想又推向了新的高度:
以系统的思维方法解决舆论引导的问题。习近平提出的做好舆论引导就要统筹好舆论监督和正面宣传两个方面是其将辩证法在新闻传播领域的灵活运用。一方面,从行为主体、报道方式、报道题材上来讲,舆论监督和正面宣传是两个相互对立的矛盾势力,即“两不立,则一不可见”;但从报道立场、根本目的以及客观效果的角度,二者又是统一的,是新闻舆论导向的一体两面,即“一不可见,则两之用息”。习近平经常引用“独阴不生,独阳不生”(《春秋谷梁传》)解释世界之变局,经济之发展,但在其舆论引导的论述中也无不蕴含着这一思想精华。另一方面,在舆论监督内部,澄清谬误、明辨是非与激浊扬清、针砭时弊也是辩证统一的,如习近平所说:“舆论监督的出发点应该是积极的、建设性的。”[2]应该在揭露批评社会丑恶现象的同时提出解决意见和改进措施。这其中所蕴含的通过正面的价值观、真善美的落脚点揭露抨击社会上倒行逆施或违背社会公平公正的行为,以促进社会矛盾的化解、道德秩序的规范,乃至尽可能使接受人民监督的反面教材朝着正面典型方向发展转化的深层意义,无疑也是对“福之为祸,祸之为福”“变而通之,反而合之”的深刻体现。而在应该如何统筹好舆论监督与正面宣传、如何把握二者间平衡点的问题上,习近平不仅提出了具有系统性特征的“时、度、效方法论”[12],而且主张两点论与重点论相结合,既要求成绩问题一起抓,从主流中发现问题,在问题中寻求突破,形成舆论引导凝心聚力的合力,又不是平均发力,要求报道侧重点必须符合社会发展积极向好的真实情况,即“坚持团结稳定鼓劲,以正面宣传为主”。
以理论联系实际的思维方法解释“新闻规律”认识与实践的问题,是对中国古代知行合一思维方法的继承与运用。习近平始终强调实干精神、务实精神,曾引用“为者常成,行者常至”(《晏子春秋·内篇·杂下》)等许多中国传统智慧表达实践的重要性与必要性,在新闻领域对新闻规律从“发现”“认识”到“适应”再到“尊重”“运用”的论述中,便是该实践思想的生动写照,并体现出习近平对新闻工作者能力的极高要求与认识规律是为了运用规律改造新闻(广义)的马克思主义观点。关于新时代背景下具体该如何运用新闻规律、如何按照规律办事的问题,习近平提出“因势而谋,应势而动,顺势而为”的指导原则,并以此为基础,结合媒介生态革新、新闻主体关系转换等现状,进一步提出了传统媒体与新媒体融合发展、走网络群众路线、用事实讲话等破局之径,蕴含强烈的信息观念和大势观念。所谓的信息观念就是变合目的性的传播为合目的与合规律相统一的传播,着实反映社会变革与时代风貌,积极展现真实立体全面多样的中国形象;所谓的大势观念,就是“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刘勰),既从宏观上把握国际国内大势,也遵循技术所带来的传播规律变化的大势,做到“读者在哪里,受众在哪里,宣传报道的触角就要伸到哪里”[13],改变以往传者本位、傲然睥睨的传播模式,进而适应互联网实时传播、平等开放的特点,重视用户的多元需要和传播体验,充分吸纳网络民意,广泛集中民智,从根本上实现平等对话的双主体模式。同时,习近平亦是“知行合一”的践行者,不仅曾先后在正定、宁德、浙江工作期间亲身参加到新闻传播活动中,2002年至2007年仅仅五年就于《浙江日报》的“之江新语”专栏中发表了短评时评作品多达200多篇,基本等于保持着每周一篇的高频次;并且其还撰写了许多意义重大、影响深远的新闻作品,譬如《中青年干部要“尊老”》《把握好新闻工作的基点》《用权讲官德交往有原则》等等,其中《中青年干部要“尊老”》中引用中国古籍八处,亦彰显出习近平极高的文学修养和文化底蕴。正是这些“行”,为习近平指导当前新闻工作的“知”夯实了坚实的基础。由此,习近平吸取中国古代辩证法中以知促行,以行促知,知行合一的养分,在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指导下的认识新闻规律是运用的基础、而运用是认识的目的与最终归宿、二者在相互作用与磨合中共同推动着新闻活动多样多彩、新闻规律理论丰富发展的实践思想已昭昭自明。
以创新的思维方法破解新闻舆论工作之困局,内蕴中华民族最深沉的民族禀赋和中国人民创新观念的精神基因。创新思维是基于对世界普遍联系、一切事物总是在不断发展变化的认识的前提下提出来的,既存在于中国辩证法思想体系之中,也是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理论内涵。当下,随着传媒格局、舆论生态的重新洗牌与深度调整,“特别是互联网正在媒体领域催发一场前所未有的变革”[14],促使新闻领域的创新命题成为时代之需、时代必须。因为树立创新意识从事创新实践的主体是人,做好新闻舆论工作的关键也在人,故而树立强烈的人才意识,择天下英才而用之,建设一支创新型新闻舆论人才队伍成为创新之根本,创新之核心。习近平吸收了韩非子“宰相必出自州部官员、猛将必源于士兵”的思想,要求新闻工作者也必须俯下身,沉下心,真下去,融进去,只有深入到群众内部和基层实际工作中“墩墩苗”,以实实在在的脚力、眼力、脑力和笔力锤炼过硬的内功,才能笔酣墨饱、笔下生花;其也曾引用孟子的“先立乎其大者,则其小者不能夺也”,希冀新闻工作者系统学习马克思主义和党的方针政策,不断强化理论武装,只有牢牢把握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这个“大”,才能在具体工作的“小”中坚定立场、不迷失方向;其亦通过汲取中国古代“公心”的哲学意义而鞭策新闻工作者必须时刻牢记社会责任与使命,弘扬主旋律,撒播正能量,积极传播、培育并主动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同时,习近平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创新思维也往往与其系统思维、辩证思维交相辉映,相映成趣,共同作用于新闻舆论的指导工作当中。譬如其曾提出的推进新闻舆论工作理念、内容、形式、体裁、方法、手段、体制、业态、机制等全方位创新,“理论创新是先导,内容创新是根本”等论述,无不彰显着其创新思想中对整体推进与重点突破相结合、总体布局与战略布局相统一等辩证法的综合运用。
四、结语
综上,在逻辑结构上,笔者从认识论、价值论以及方法论三个独立的维度分别对习近平“以古人之规矩,开自己之生面”的中国化民族化新闻舆论观给予了探讨,但从学理价值的角度,又无不观照三个维度之间认识论内蕴对价值论方法论的追问、价值论又以认识论为基础并始终渗透着对方法论指导的融合性与交叉性。同时,习近平新闻舆论观本身也是在方法论、价值论、方法论共在、共同、共时的作用下,既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融入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用传统理念、方法的合理内核诠释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实现了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也立足马克思主义,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元素运用在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中,形成了饱蘸中国本土文化意蕴与“习语”特质的习近平新时代新闻舆论观及其话语表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