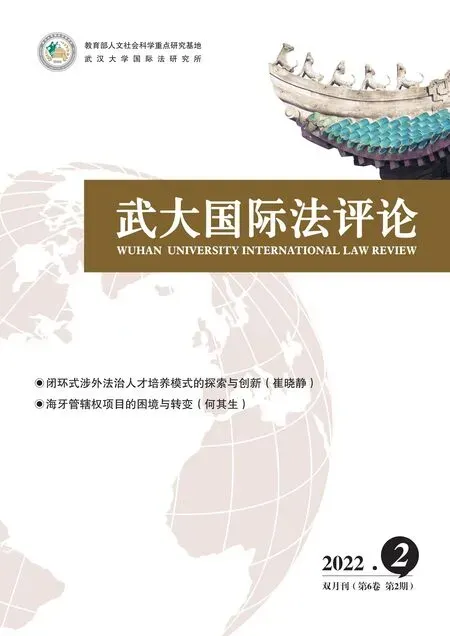非地理因素在国际海洋划界实践中的能动作用论析
孙传香
晚近国际海洋划界实践表明,无论海岸相向抑或海岸相邻国家间的海洋划界(含专属经济区划界和大陆架划界)中,影响划界结果最重要的因素是相关国家的海岸关系与海岸地理地貌。一般来说,海岸地理地貌是指沿海国在水面和陆地接触处,经波浪、潮汐、海流等作用下形成的滨水地带,除此以外的经济、人口等则纳入非地理因素。从公平原则、中间线或称等距离线方法、自然延伸原则到国际法院于2009年在黑海划界案中正式适用的三阶段划界规则,海岸关系与海岸地理地貌在海洋划界中无不发挥重要作用。然而,在海岸关系与海岸地理地貌等地理因素以外,诸如经济、安全与防卫、航行及能源安全等非地理因素在海洋划界中的地位如何?非地理因素在划界中能发挥何种作用?在国际社会面临海洋划界争端尚待解决的当下,厘清非地理因素在国际海洋划界中的地位与作用,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
一、单一非地理因素在国际海洋划界中的实然作用
非地理因素能否对海洋划界产生影响,不能一概而论,要区分不同案件及非地理因素的多寡及重要性。一般来说,单个非地理因素很少能在海洋划界中发挥作用。
(一)经济因素
经济因素涵盖碳烃化合物、渔业及社会经济等领域,是大陆架和专属经济区等法律概念形成的基础。国际法院在北海大陆架案中指出:“(获取)大陆架的海床底土所蕴含的自然资源正是继《杜鲁门公告》之后建立相关法律制度的目的。”①North Sea Continental Shelf Cases(Federal Republic of Germany v.Denmark;Federal Republic of Germany v.Netherlands),Judgment,ICJ Reports 1969,pp.33-34,para.47.在突尼斯诉利比亚案中,国际法院同样指出,大陆架的概念可追溯至《杜鲁门公告》,在大陆架开发自然资源具有经济方面的重要性,已成为众所周知的概念之一。②See Case Concerning the Continental Shelf(Tunisia v.Libyan Arab Jamahiriya),Judgment,ICJ Reports 1982,pp.78-79,para.109.
有学者指出,既然创设专属经济区与大陆架的目的是满足沿海国对近海自然资源的利用,经济因素影响海洋划界自然是合情合理的。③See Youshifumi Tanaka, Predictability and Flexibility in the Law of Maritime Delimitation 393 (Hart Publishing 2019).持相同观点的还有:1969 年北海大陆架案判决书第48 段;1969 年北海大陆架案杰赛普(Jessup)法官的独立意见第66、72 段;1982 年突尼斯诉利比亚案小田滋(Oda)法官的不同意见第119 段;1985 年利比亚诉马耳他案判决书第50 段;2012 年孟加拉湾划界案纳基(Lucky)法官的不同意见第236页等。国际司法机构和仲裁机构的判例自始就将自然资源看做划界应当考虑相关情况。④参见高健军:《国际海洋划界论——有关等距离/特殊情况规则的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54页。实际上,诸多国家在其提交至国际法院或法庭的诉求中均强调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法律制度产生的经济背景,以及经济因素与划界之间的联系。⑤譬如,1969 年北海大陆架案中,丹麦与荷兰的反驳意见第486 页;卡塔尔诉巴林案中卡塔尔的诉状第44-45、218-220、251 页;2002 年喀麦隆诉尼日利亚(赤道几内亚参加)案中喀麦隆的诉状第23、133、499-500、519 页;2012 年孟加拉湾划界案中缅甸的反驳意见第210、214-215 页;加纳诉科特迪瓦案中科特迪瓦的答辩意见第13、47页。但遗憾的是,对于单一的经济因素,尽管国际(准)司法机构并未完全否定,但远没有给予其充分考虑。⑥See M. D. Evans, Maritime Boundary Delimitation, in Donald R. Rothwell,et al. (eds.), The Oxford Handbook of the Law of the Sea 269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Stephen Fietta & Robin Cleverly,A Practioner’s Guide to Maritime Boundary Delimitation 88(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6).诚如威尔所言,“经济因素是一个没有人敢(或者说能)提及的相关情况”,但它们“不止一次地出现在法官的脑海中”。①Prosper Weil, The Law of Maritime Delimitation: Reflections 263-264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9).
如上所述,对于海洋划界是否应该考虑经济因素一直存在争议。国际法院认为,“已知的或很容易确定的”自然资源可以被视为“相关情况”。②See North Sea Continental Shelf Cases (Federal Republic of Germany v. Denmark; Federal Republic of Germany v.Netherlands),Judgment,ICJ Reports 1969,p.55,para.101(D)(2).在尼加拉瓜诉哥伦比亚案中,法院在处理有关获取自然资源的问题时,虽然承认自然资源的获取是影响该案海洋划界的“相关情况”,同时设定了“获取自然资源的特殊问题(exceptional issues of access)”的较高门槛,并且认为该案并不符合其设定的门槛要求。③See Territorial and Maritime Dispute (Nicaragua v. Colombia), Judgment, ICJ Reports 2012, p.706,para.223.与印度尼西亚诉马来西亚案④See Case Concerning Sovereignty over Pulau Ligitan and Pulau Sipadan (Indonesia v. Malaysia),Judgment,ICJ Reports 2002,p.664,para.79.、喀麦隆诉尼日利亚案⑤See Land and Maritime Boundary between Cameroon and Nigeria(Cameroon v. Nigeria:Equatorial Guinea intervening),Judgment,ICJ Reports 2002,pp.447-448,para.304.、尼加拉瓜诉洪都拉斯案⑥See Territorial and Maritime Dispute between Nicaragua and Honduras in the Caribbean Sea(Nicaragua v.Honduras),Judgment,ICJ Reports 2007,p.659,para.258.和圭亚那诉苏里南案⑦See Arbitral Tribunal Constituted Pursuant to Article 287,and in Accordance with Annex Ⅶ,of the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 in the Matter of an Arbitration between Guyana and Suriname,2007,30,RIAA 1,pp.125-126,para.390.不同,突尼斯诉利比亚案⑧See Case Concerning the Continental Shelf(Tunisia v.Libyan Arab Jamahiriya),Judgment,ICJ Reports 1982,pp.83-85,paras.117-119.是国际法院唯一明确考虑油井对划界影响的案件。对此有学者指出,油气资源因素对海洋划界主流方法的影响,体现在该因素是否构成三阶段划界方法之调整阶段的“相关情况”。⑨参见朱利江:《在原则与例外之间:油气因素对海洋划界的影响》,《政法论坛》2019 年第2 期,第133页。
在纽芬兰和拉布拉多诉新斯科舍省仲裁案中,仲裁庭强调,获取海洋自然资源的问题与划界程序不是无关紧要的。⑩See Arbitration between Newfoundland and Labrador and Nova Scotia Concerning Portions of the Limits of Their Offshore Areas,Award of 26 March 2002,128 International Law Reports 46,para.3.21.在国际海洋法法庭特别分庭就加纳诉科特迪瓦案所作出的判决中,科特迪瓦主张根据石油特许权以习惯等距离线划界,法院最终确定的等距离线却对加纳更有利,其原因是特别分庭不认可石油特许权构成默示划界协议。⑪See Dispute Concerning Delimitation of the Maritime Boundary between Ghana and Côte d’lvoire in the Atlanic Ocean,Judgment,ITLOS Reports 2017,pp.46-48,p.147.尽管科特迪瓦声称碳氢化合物的分配构成“相关情况”,但法庭认为“海洋划界不是重塑自然,也不是分配正义的手段”①Dispute Concerning Delimitation of the Maritime Boundary between Ghana and Côte d’lvoire in the Atlanic Ocean,Judgment,ITLOS Reports 2017,pp.125-126,p.128.。为了证明法庭倾向于地理因素而不是与资源有关的标准,特别分庭援引了“灾难性影响”(catastrophic repercussions)这一检验标准,并指出该案没有达到“灾难性影响”最低要求的证据标准。②See Dispute Concerning Delimitation of the Maritime Boundary between Ghana and Côte d’lvoire in the Atlanic Ocean,Judgment,ITLOS Reports 2017,pp.128-129,paras.452-453.总之,从已有司法实践来看,无论个案的特点如何,国际(准)司法机构均没有认可单一经济因素对划界的影响。
“灾难性影响”的概念最初产生于渔业案件。国际(准)司法机构在缅因湾案等案件中认为,欲将渔业资源视为“相关情况”,则需要证明,如果海洋划界无视既有渔业实践,将对相关人群“维持生计造成灾难性影响”。③Case Concerning Delimitation of the Maritime Boundary in the Gulf of Maine Area (Canada v.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Judgment, ICJ Reports 1984, p.246, para.237; Delimitation of the Maritime Areas between Canada and France,Award of 10 June 1992,31 International Legal Materials 1149,para.84;Arbitral Tribunal Constituted Pursuant to Article 287, and in Accordance with Annex Ⅶ, of the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 in the Matter of an Arbitration between Barbados and the Republic of Trinidad and Tobago, 2006, 27, RIAA 147, p.100, para.328; Award in the Matter of the Bay of Bengal Maritime Boundary Arbitration betwee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Bangladesh and the Republic of India, 2014, p.124,para.423.一般来说,如当事国能提供足够证据证明划界对其渔业资源产生影响,国际法院和法庭会在海洋划界案件中审查渔业问题。④See Arbitral Tribunal Constituted Pursuant to Article 287,and in Accordance with Annex Ⅶ,of the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 in the Matter of an Arbitration between Barbados and the Republic of Trinidad and Tobago, 2006, 27, RIAA 147, p.73, para.241; Stephen Fietta & Robin Cleverly,A Practioner’s Guide to Maritime Boundary Delimitation 85(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6).譬如,国际法院在扬马延案中将获得渔业准入视为“相关情况”;⑤See Maritime Delimitation in the Area between Greenland and Jan Mayen (Denmark v. Norway),Judgment,ICJ Reports 1993,p.72,para.76.在秘鲁诉智利案中,国际法院通过考察双方的渔业实践来确定双方以默契方式达成的边界范围。⑥See Maritime Dispute(Peru v.Chile),Judgment,ICJ Reports 2014,p.59,para.151.在突尼斯诉利比亚案中,法院最后考察了其最终确定的界线对渔业是否会产生不利影响。⑦See P. Birnie, Delimitation of Maritime Boundaries: Emergent Legal Principles and Problems, in Gerald Blake(ed.),Maritime Boundaries and Ocean Resources 24(Croom Helm Publishers 1987).在缅因湾案中,双方向法庭提交的划界方案均反映了各自的渔业利益,尽管国际法院特别分庭最终拒绝将渔业资源视为“相关情况”,但仍将渔业作为审查界线是否公平的因素之一,可见,非地理因素在划界中间接发挥了作用。此外,在1974 年英国诉冰岛及德国诉冰岛的渔业管辖权案中,国际法院认可英国和德国有获得渔业资源的权利,①See Fisheries Jurisdiction (United Kingdom v. Iceland), Merits, Judgment, ICJ Reports 1974, p.3;Fisheries Jurisdiction(Federal Republic of Germany v.Iceland),Merits,Judgment,ICJ Reports 1974,p.175.并承认两国在该案中存在一种涉及经济和历史的“重大利益”。但是,纵观所有与渔业有关的案例,渔业准入并没有一律被视为影响海洋划界的“相关情况”。譬如,在加拿大诉法国案②See Delimitation of the Maritime Areas between Canada and France,Award of 10 June 1992,31 International Legal Materials 1149,para.87.、厄立特里亚诉也门案③See Award of the Arbitration Tribunal in the Second Stage of the Proceedings (Maritime Delimitation) in the Matter of an Arbitration Pursuant to an Agreement to Arbitrate Dated 3 October 1996 between the Government of the State of Eritrea and the Government of the Republic of Yemen, 1999, 22, RIAA 335,para.72.以及巴巴多斯诉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案④See Arbitral Tribunal Constituted Pursuant to Article 287,and in Accordance with Annex Ⅶ,of the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 in the Matter of an Arbitration between Barbados and the Republic of Trinidad and Tobago,2006,27,RIAA 147,p.83,para.267.等案件中,国际(准)司法机构均认为不满足“灾难性影响”的评价标准。
需要强调的是,承认经济因素作为海洋划界的“相关情况”,并不等于要求海洋划界必须为一国的经济发展服务或者将不同当事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作对比,国际法院在利比亚诉马耳他案⑤See Continental Shelf (Libyan Arab Jamahiriyia v. Malta), Judgment, ICJ Reports 1985, p.41, para.50.和扬马延案⑥See Maritime Delimitation in the Area between Greenland and Jan Mayen (Denmark v. Norway),Judgment,ICJ Reports 1993,pp.73-74,paras.79-80.等案件中多次表达了这一观点。相反,国际法院和法庭在海洋划界中主要考虑的是,沿海国是否具备在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有效行使包括勘探和开采自然资源在内的主权权利的能力,并借此保障其充足的能源供应并确保其国家安全。尤其是,随着社会、经济和科技的不断发展,除碳氢化合物和渔业资源等传统意义上的自然资源以外,各国逐渐转向诸如发展海洋风力发电场、提高海洋生物碳储存能力等气候友好型发展模式。因此,国际(准)司法机构同样需要在审理海洋划界案件时对沿海国前述活动作出回应,以考察相关活动对行为国是否具有“重大利益”并最终在划界中发挥其作用。
质言之,自然资源、石油开采等经济因素能否构成海洋划界的“相关情况”,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⑦参见张华:《国际司法裁决中的海洋划界方法论解析》,《外交评论》2012年第6期,第150页。在海洋划界中考虑经济因素并不要求将经济因素置于与地理因素等量齐观的地位,而是确保沿海国充分行使其固有的主权权利。为此,国际法院或法庭至少可将各种不同经济因素作为一个整体,以评估主要由地理因素决定的划界结果的公平性。⑧See Stephen Fietta & Robin Cleverly,A Practioner’s Guide to Maritime Boundary Delimitation 89(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6).然而,尽管资源等经济因素是导致海洋划界争端的直接原因,但并非产生海洋权利的法律权源。①参见张华:《争议海域油气资源开发活动对国际海洋划界的影响——基于“加纳与科特迪瓦大西洋划界案”的思考》,《法商研究》2018年第3期,第165页。既有司法实践表明,国际(准)司法机构只有在禁止沿海国使用自然资源将对其造成灾难性影响时,才考虑自然资源对海洋划界的影响,而“灾难性影响”与一国的“重大利益”密切相关。
(二)安全与防卫因素
众所周知,有关大陆架的法律制度起源于《杜鲁门公告》,该公告明确规定,“自我保护使得沿海国需要密切关注其海岸以外的活动,这些活动是利用其自然资源所必需的”。显然,《杜鲁门公告》将大陆架纳入沿海国的管辖范围,正是沿海国对其“海岸以外”安全关切的反映,而安全问题不限于军事活动,还可能涉及环境、捕鱼及其他作业的安全。②See Thomas Cottier, Equitable Principles of Maritime Boundary Delimitation: The Quest for Distributive Justice in International Law 537(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5).遗憾的是,国家安全与防卫虽然在多个案例中被提起,但其未能发挥对海洋划界的作用。事实上,各国在提交至国际法院或法庭的诉状中频频援引安全与防卫因素,③据统计,共有利比亚等24 个国家在其参与的海洋划界案中提到海洋划界对其安全与防卫的影响。学界及实务界也呼吁将安全与防卫纳入海洋划界的“相关情况”。④See Malcolm Shaw, International Law 451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7); Youshifumi Tanaka, Predictability and Flexibility in the Law of Maritime Delimitation 425 (Hart Publishing 2019); Maritime Delimitation in the Area between Greenland and Jan Mayen(Denmark v.Norway),ICJ Reports,p.211,Separate Opinion of Judge Weeramantry,para.228.
国际法院在利比亚诉马耳他案中承认大陆架与一国的安全和防卫事务有关,尽管法院最终没有将安全与防卫作为该案划界的“相关情况”,但认真考虑了安全与防卫事务对划界的影响。国际法院在该案中指出,最终划定的边界不会产生安全问题,因为它并非“十分靠近任何一方的海岸”。⑤See Case Concerning the Continental Shelf (Libyan Arab Jamahiriyia v. Malta), Judgment, ICJ Reports 1985, p.42,para.51.仲裁庭在加拿大诉法国(纽芬兰和拉布拉多诉新斯科舍省)仲裁案中也认为,要特别确保界线不要离任何一个国家“太近”。⑥See Arbitration between Newfoundland and Labrador and Nova Scotia Concerning Portions of the Limits Their Offshore Areas,Award of 26 March 2002,128 International Law Reports 91,para.5.15.在缅因湾案中,与国防相关的活动之所以未被视为划界的“相关情况”,是因为未能达到“灾难性影响”这一标准。⑦See Case Concerning Delimitation of the Maritime Boundary in the Gulf of Maine Area(Canada v.United States of America),Judgment,ICJ Reports 1984,p.342,para.237.在1985 年几内亚诉几内亚比绍划界案中,仲裁庭认为安全是海洋划界的一个相关因素,并强调法庭的主要任务之一是避免一国在另一国海岸附近行使管辖权,以免损害后者的安全利益,最后,仲裁庭在不损害任何一方安全的前提下划定了界线。①See Guinea/Guinea-Bissau Maritime Delimitation Case, Decision of 14 February 1985, 25 International Legal Materials 251.同样,国际法院在扬马延案中也指出,“虽然法院不愿意看到这种安全考虑侵蚀根据地理标准确定分界线的基本任务,但安全依然可作为避免造成不公平结果的考虑因素”。②Maritime Delimitation in the Area between Greenland and Jan Mayen (Denmark v. Norway), Judgment,ICJ Reports 1993,p.38,para.81.在厄立特里亚诉也门案(第二阶段)中,仲裁庭亦采取了同样的办法,为了不损害安全利益,法庭拒绝将厄立特里亚位于红海的部分岛屿视为飞地。③See Award of the Arbitration Tribunal in the Second Stage of the Proceedings (Maritime Delimitation) in the Matter of an Arbitration Pursuant to an Agreement to Arbitrate Dated 3 October 1996 between the Government of the State of Eritrea and the Government of the Republic of Yemen, 1999, 22, RIAA 335,para.157.
在黑海划界案中,国际法院虽然没有以安全为理由调整临时界线,但肯定其在利比亚诉马耳他案中阐述的理由,再次承认安全与海洋划界存在相关性。法院在该案中认为,临时等距离线没有损害任何一方的安全利益,④See Maritime Delimitation in the Black Sea (Romania v. Ukraine), Judgment, ICJ Reports 2009,p.61,para.204.这一结论明确表明,法院在该案中已然考虑了安全因素。在卡塔尔诉巴林案中,法院认为,界线太过接近卡塔尔海岸应该作为一个考虑因素,由此表明界线接近海岸可能对安全产生影响。⑤See Maritime Delimitation and Territorial Questions between Qatar and Bahrain(Qatar v.Bahrain),Judgment,ICJ Reports 2001,p.104,para.218.同样,在尼加拉瓜诉哥伦比亚案中,国际法院指出,如果界线靠近一国海岸,安全问题可能与划界有关,因而需要作出适当改变。特别是,法院在该案中还提到有必要维持海洋的公共秩序,⑥See Territorial and Maritime Dispute (Nicaragua v. Colombia), Judgment, ICJ Reports 2012, p.706,p.708.由此彰显安全对海洋划界的重要影响。仲裁庭在斯洛文尼亚诉克罗地亚案中也指出,既往相似案件承认安全在划界中可能发挥的作用,本案亦应将安全作为划界的可能考虑因素,为斯洛文尼亚能够通过克罗地亚的海洋进入公海而建立“连接区域”。⑦See Final Award in the Maritime of an Arbitration under the Arbitration Agreement between the Government of the Republic of Croatia and the Government of the Republic of Slovenia, Signed on 4 November 2009,2017,pp.305-306,paras.985-986.
综上所述,尽管《杜鲁门公告》的合理性与公正性涵盖了安全、保护等方面,⑧参见吴少杰、董大亮:《1945年美国〈杜鲁门公告〉探析》,《太平洋学报》2015年第9期,第103页。安全与防卫在既有海洋划界案例中亦偶有提及,部分案例甚至对其进行了较为详尽的分析,但整体上看,其发挥的作用十分有限。
(三)航行及能源安全因素
航行一般是国际法院或法庭在解决领海划界争端时考虑的因素。在专属经济区划界或大陆架划界时,一般不像领海划界那样重视航行对划界的影响,但并没有完全忽视这一因素。在英法大陆架案中,仲裁庭认为,航行是表明法国在英吉利海峡具有“重大利益”的因素之一。①See United Kingdom of Great Britain and Northern Ireland/French Case,1977,18 RIAA 3,para.188.仲裁庭在加拿大诉法国案划定界线后同样强调,其确定的分界线不会对航行产生“不利影响”。②See Delimitation of the Maritime Areas between Canada and France,Award of 10 June 1992,31 International Legal Materials 1149,para.88.显然,在前述两个案例中,仲裁庭均考虑了航行对划界的影响,设若仲裁庭在划界时忽略航行问题,就没有必要在确定界线后阐述界线与航行之间的关系。除仲裁庭在审理过程中关注航行问题以外,各国在将大陆架划界或专属经济区划界争端提交司法程序时亦十分重视并阐述其对航行问题的关切。③See Case Concerning Delimitation of the Maritime Boundary in the Gulf of Maine Area(Canada v.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Counter-Memorial of Canada, para.162; Land and Maritime Boundary between Cameroon and Nigeria (Cameroon v. Nigeria: Equatorial Guinea Intervening), Counter-Memorial of the Federal Republic of Nigeria,para.20.19.
概而论之,各国加紧海洋划界争端的解决,其主要目的之一是获取海洋生物或非生物资源,保障其能源安全。然而,由于历史等多方面的原因,全球主要能源供应地大多政局不稳,直接影响能源的可持续供应。因此,各主权国家必须确保其能源供应多样化,以减少供应链中断带来的影响。④See Daniel Yergin,Ensuring Energy Security,85 Foreign Affairs 69-70,76(2006).丹尼尔·尤金(Daniel Yergin)对此指出,能源的相互依存需要所有利益攸关方通力合作,以维护海底管道占据突出地位的供应链。⑤See Daniel Yergin,Ensuring Energy Security,85 Foreign Affairs 69-70,76(2006).可见,各国一方面有权勘探并开发本国的国内能源资源,以减少对其他国家的能源依赖;另一方面,确保能源外部补给通道的畅通也是各国保障能源安全的重要方式。有学者因此指出,能源的充分供应可保护一国的经济利益,构成该国的重要利益和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⑥N. Llein, et al. (eds.), Maritime Security: International Law and Policy Perspective from Australia and New Zealand 27(Routledge 2010).可见,能源的充足、稳定和及时的供给亦应成为海洋划界的影响因素。
总之,海洋划界对一国的航行与能源安全有重要影响。在划界过程中,欲确保沿海国获得其“重大利益”,亦不能忽视航行与能源安全问题,须将其纳入影响海洋划界的因素范畴。
二、非地理因素纳入国际海洋划界考量因素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无论海洋划界采取何种具体方法,皆以取得公平划界结果为其终极目的。由于《公约》等现行法律制度规定海洋划界主要基于地理地貌等地理因素,未能对所有影响因素作全面考察,海洋划界的公平性因此屡遭质疑。
(一)制度缺失:非地理因素纳入国际海洋划界的必要性
国际海洋划界的国家实践表明,各国缔结海洋划界协议的主要目的是获取海床洋底及水体中的自然资源。为此,海洋划界从表面上看是海岸相向或相邻国家对海洋的划分,其实质则是对海洋资源的分割。①参见孙传香:《中日东海大陆架划界国际法问题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13页。随着陆地资源的持续紧张与日趋枯竭,各国竞相将获取资源的目光投向广袤的海洋并为此加快海洋划界进程,相伴而来的是不断涌现的海洋划界争端。由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以下称《公约》)第74、83条对专属经济区划界以及大陆架划界的具体方法规定不详,海洋划界方法论领域亦未形成习惯国际法规则,致使海洋划界的具体方法至今付之阙如,其选择与适用均由国际司法机构根据个案的具体情况确定。
有关海洋划界方法的适用,国际司法机构或准司法机构的实践一波三折。1958年《大陆架公约》第6 条规定海岸相向或相邻国家间的大陆架采用等距离线方法划界,但由于参加国较少,该公约对国家实践与国际司法实践产生的影响十分有限。此后,在1969 年北海大陆架案中,国际法院摒弃了1958 年《大陆架公约》规定的等距离线方法,适用“公平原则”划界以实现海洋划界的公平结果。1977 年,仲裁庭在英法大陆架案中作了新的尝试,将等距离线方法融入公平原则,使等距离线方法成为实现公平结果的手段。而在随后的突尼斯诉利比亚案(1982 年)、缅因湾案(1984年)以及利比亚诉马耳他案(1985 年)中,国际法院复又削弱了等距离线方法在划界中的作用。直至1993 年扬马延案,国际法院再次表明,等距离线方法也能实现公平结果。晚近,特别是从2009 年黑海划界案起,国际司法机构与仲裁机构在海洋划界司法实践中开始适用三阶段划界规则,②参见孙传香:《国际海洋划界三阶段理论:形成、实践与检视》,《法学评论》2016年第6期,第113页。并在其后的案件审理中重新重视等距离线方法的运用。
由于具体划界方法的缺失,国际司法机构无法确定其在海洋划界司法实践中应考虑的影响因素,导致个案之间存在较大差异。无论效力范围较小的《大陆架公约》还是更具普适性的《公约》,其规定影响海洋划界的基本因素是相关国家的海岸关系及其地理地貌。③《大陆架公约》第6 条规定的大陆架划界影响因素包括第1、2 款的“领海基线”以及第3 款的“海图及地理特征”,《公约》第74条与第84条则规定了“海岸相向或相邻”字样。与《公约》第74、83 条仅通过“海岸相向或相邻”的措辞暗含地理地貌信息而无其他更明确的规定相比,《大陆架公约》在规定地理地貌因素的同时允许“因情形特殊另定界线”,给包括非地理因素在内的其他因素对海洋划界产生影响留下了空间。尽管《大陆架公约》不具普适性,但国际(准)司法机构在其实践中频频予以援引与阐释,其对海洋划界司法实践的影响显然不可小觑。国家实践与国际司法实践亦表明,影响海洋最终界线的因素众多,不仅包括能发挥关键作用的海岸关系与海岸地理地貌,其他诸如经济、航行等非地理因素亦能对海洋划界结果产生一定影响。可见,不能完全忽视非地理因素在海洋划界中的地位,有必要将其纳入海洋划界的考虑范围,否则会有损海洋划界公平结果的实现。
有学者认为,非地理因素,特别是自然资源应该纳入海洋划界的考虑范围。①See Thomas Cottier, Equitable Principles of Maritime Boundary Delimitation: The Quest for Distributive Justice in International Law 99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5); M. D. Evans, Maritime Boundary Delimitation, in Donald R. Rothwell, et al. (eds.), The Oxford Handbook of the Law of the Sea 274-276(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Stephen Fietta & Robin Cleverly,A Practioner’s Guide of Maritime Boundary Delimitation 84(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6).尽管国际(准)司法机构最终将非地理因素纳入其考虑范围的既判案例实属不多,但亦有不少参与相关案件的法官呼吁将非地理因素纳入划界的考虑范围。曾任国际法院院长的史久镛法官指出,尽管国际法院认为与海岸地理相关的情况是最相关的,但自然资源的分配等非地理因素也可能被考虑。②参见史久镛、高健军:《国际法院判例中的海洋划界》,《法治研究》2011年第12期,第11页。布斯塔曼特·伊·里韦罗(Bustamante Y. Rivero)则明确强调,“法院不能忽视的是,在大陆架概念产生之时,其初衷是为沿海国提供开采大陆架中自然资源的可能,即满足沿海国的社会与经济需求”。③1969 年北海大陆架案布斯塔曼特·伊·里韦罗法官的独立意见第5 段。此外,同案田中(Tanaka)法官的不同意见第172 段以及1982 年突尼斯诉利比亚案阿雷查加(Arechaga)法官的独立意见第70段表达了相同观点。威尔也在加拿大诉法国案中极力赞同经济因素在海洋划界中发挥重要作用。威尔认为,不能从公平划界中完全消除社会和经济因素,否则将违背大陆架、渔业区以及专属经济区等概念的起源是勘探和开发自然资源,仅囿于事后检测划界结果有无“灾难性影响”是远远不够的。④See Delimitation of the Maritime Areas between Canada and France,Award of 10 June 1992,31 International Legal Materials,Dissenting Opinion of Judge Weil,para.34.威尔法官在其不同意见中还引用了缅因湾案裁决书的第83、84段。此外,阿吉波拉(Ajibola)法官亦强调,“除地理构造以外,‘相关情况’还包括人口、社会经济结构、安全、当事方行为等”。⑤See Maritime Delimitation in the Area between Greenland and Jan Mayen (Denmark v. Norway),ICJ Reports 1993,p.280,Separate Opinion of Judge Ajibola,p.301.在2012 年孟加拉湾划界案中,国际海洋法法庭法官纳尔逊(Nelson)、拉奥(Rao)和科特(Cot)均明确支持将某些非地理因素纳入“相关情况”的考量范围,称“其他相关情况包括……与经济资源、渔业、安全问题和航海有关的考虑”,①Bangladesh v. Myanmar Case, Judgment, ITLOS Reports 2012, p.134, Joint Declaration of Judges Nelson,Chandrasekhara Rao and Cot,p.135.伯尼(Birnie)也提出要在比例检测阶段考虑经济和安全因素。②See P. Birnie, Delimitation of Maritime Boundaries: Emergent Legal Principles and Problems, in Gerald Blake(ed.),Maritime Boundaries and Ocean Resources 33-34(Croom Helm Publishers 1987).
(二)司法能动:非地理因素纳入国际海洋划界的可行性
如前所述,有关海洋划界的国际司法判决或裁决主要基于当事国的海岸地理地貌作出,非地理因素一般不发生划界效力。但是,如果当事国能够证明其在争议海域存在基于非地理因素的重大利益,不排除国际(准)司法机构以“重大利益”为由予以考虑。质言之,尽管单个非地理因素一般不被国际(准)司法机构视为海洋划界的“特殊情况”或“相关情况”,但多个非地理因素可能累积或叠加成“重大利益”,从而成为影响海洋划界的重要因素。
尽管《公约》第15 条明确规定领海划界适用“等距离/特殊情况”规则,而专属经济区划界与大陆架划界既无实体方法,亦无习惯国际法可供适用,自然成为“重大利益”发挥海洋划界效力的“用武之地”。尽管国际法院等司法机构或其他准司法机构在实践中不太重视非地理因素对划界的影响,但并没有完全忽视非地理因素对海洋划界的作用。实践表明,国际(准)司法机构最终未将非地理因素认定为影响海洋划界的“相关情况”,主要是因为国际(准)司法机构要求的证据门槛过高或当事方提供的证据材料不足,而不是国际(准)司法机构一概否定非地理因素在海洋划界中的地位和作用。实际上,国际(准)司法机构在审理海洋划界争端案件时已经含蓄地考虑了非地理因素,尽管它们没有公开承认。③See Thomas Cottier, Equitable Principles of Maritime Boundary Delimitation: The Quest for Distributive Justice in International Law 58(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5).
一般来说,一国往往在其主权范围内的岛屿主张其“重大利益”。尽管国际法院多次明确将《公约》第121 条“岛屿制度”定性为习惯国际法,但岛屿在海洋划界中的法律效力却不够明确。譬如,一方的大陆海岸线较长,另一方岛屿的划界效力显然应该受到限制。实际上,在三阶段划界规则中,岛屿不仅能影响第一阶段作出的临时等距离线的位置,而且在第二阶段亦可作为调整临时等距离线的考虑因素。④See Massimo Lando, Maritime Delimitation as a Judicial Process 155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9).国际(准)司法机构在确定岛屿在海洋划界中的地位与作用时,似乎需要考虑一系列相关情况,而不是孤立地分析某一因素的影响。⑤See Massimo Lando, Maritime Delimitation as a Judicial Process 185-186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9).譬如,国际海洋法法庭在2012 年孟加拉湾划界案中指出,在划分专属经济区或大陆架界线时,岛屿对划界的影响不仅取决于地理现实,而且与每一案件的具体情况有关。该领域尚未形成一般规则,每一独特的案例需要具体分析。①See Dispute Concerning Delimitation of the Maritime Boundary between Bangladesh and Myanmar in the Bay of Bengal (Bangladesh v. Myanmar), Judgment, ITLOS Reports 2012, p.46, para.147; p.86,para.317.由此可知,地理因素以外的其他因素亦可成为国际(准)司法实践考量的重要因素。
就三阶段划界规则而言,如果在第二阶段仅基于地理因素考虑是否调整临时等距离线而完全忽视其他非地理因素的存在,可能对海洋划界的公平结果造成影响。同时,即便忽略单个非地理因素不会导致不公平的划界结果,但多个非地理因素叠加后对公平结果的影响则不容小觑。换言之,“重大利益”在海洋划界中可发挥双重功能:其一,维持第一阶段确定的临时等距离线不被调整;其二,在必须调整的情况下,避免将临时等距离线向援引“重大利益”的国家海岸调整。实际上,除2002 年喀麦隆诉尼日利亚案、2007 年圭亚那诉苏里南案以及2017 年加纳诉科特迪瓦案以外,其他运用三阶段划界规则的案件均在第二阶段对其第一阶段确定的临时等距离线进行了调整。
可见,由于国家将其海洋划界争端诉诸国际司法机构的目的是解决自然资源的分配问题,②1977 年英法大陆架案裁决书第96 段、1984 年缅因湾案裁决书第59 段、1992 年加拿大诉法国案裁决书第24段均有相关阐述。地理因素在海洋划界中自然占据主要地位,但是,司法机构并未完全排除海洋划界中的非地理因素,非地理因素在一定程度上亦能发挥其作用。特别是,在确定岛屿的划界效力时,国际法院和法庭不仅应考虑其地理因素,同时也应考虑其他诸多非地理因素,以查明该岛屿对当事国是否具有“重大利益”。因此,在现有基础上,进一步发挥非地理因素在海洋划界中的影响与作用不仅十分必要,而且完全可行。
三、非地理因素累积后在国际海洋划界中的初步实践与应然作用
如前所述,单个非地理因素在海洋划界中难以发挥其划界效力。但是,当存在多个非地理因素且叠加后对某一当事方产生“重大利益”时,如果仍将其视为单一非地理因素并忽视其划界效力,显然会影响海洋的公平划界。
(一)非地理因素累积后产生的“重大利益”之概念溯源
“重大利益”(major interests)的概念可溯源至1977 年英法大陆架案,此后,美国在缅因湾案的诉状中使用了这一概念,乌克兰在黑海划界案中以及尼加拉瓜在尼加拉瓜诉哥伦比亚案中也援引“重大利益”来主张其海洋权利。
在英法大陆架案中,英国和法国都主张在英吉利海峡享有航行、安全和国防事务等方面的特殊利益。仲裁庭认为,由于英吉利海峡是服务于包括本案当事国在内的诸多国家的主要国际海上航线,英法两国主张的航行、安全和国防事务的重要性因此减弱。仲裁庭在该案中指出,前述各项事务对本案最终边界线的确定不具有决定性作用,它们只能支持或加强本庭依据地理、政治和法律等方面的考虑而作出的所有结论,而不是予以否定。①See United Kingdom of Great Britain and Northern Ireland/French Case, 1977, 18 RIAA 3, para.188.显然,就与该案大陆架划界相关的因素而言,仲裁庭得出的结论已经充分反映了英国与法国在英吉利海峡的“重大利益”,肯定法国作为英吉利海峡南岸沿海国的独特地位。
可见,正因为“英吉利海峡作为国际海上航行的主要路线这一特殊性质”,使得仲裁庭认为航行、安全等单一因素不足以否认地理现实,也不能对海洋划界产生实质性影响。但仲裁庭同时承认,跳出单个因素从整体上看,这些因素综合叠加起来能表明法国在该地区存在“重大利益”。②See Thomas Cottier, Equitable Principles of Maritime Boundary Delimitation: The Quest for Distributive Justice in International Law 382-383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5); Youshifumi Tanaka, Predictability and Flexibility in the Law of Maritime Delimitation 391(Hart Publishing 2019).正如大卫·阿塔德(David Attard)所言,“仲裁庭准备将航行和安全利益纳入大陆架划界的‘可能’考虑范畴,但之所以在本案中没有考虑,是因为英吉利海峡是重要的国际航行通道。”③David Attard, The Exclusive Economic Zone in International Law 269-270 (Clarendon Press 1987).即便如此,仲裁庭仍然考虑了法国的重大利益,并将隶属于英国的海峡群岛作为“飞地”处理,目的是不损害法国在英吉利海峡南部地区的重大利益。如果仲裁庭在该案中给予海峡群岛全效力,将会使英国在离法国海岸非常近的海域行使管辖权,进而损害法国在英吉利海峡的重大利益。④See United Kingdom of Great Britain and Northern Ireland/French Case, 1977, 18 RIAA 3, paras.198,202.
实际上,国际法院在其司法实践中为适用“重大利益”而扩大了可援引的“相关情况”的范围。譬如,国际法院在北海大陆架案中认为,为实现海洋划界公平结果所要考虑的因素没有限制。⑤See North Sea Continental Shelf Cases(Federal Republic of Germany v.Denmark;Federal Republic of Germany v.Netherlands),Judgment,ICJ Reports 1969,p.51,para.93.在突尼斯诉利比亚案中,法院亦指出,“相关情况”并不限于地理或地貌的事实,公平原则需要考虑所有的“相关情况”。⑥See Case Concerning the Continental Shelf (Tunisia v. Libyan Arab Jamahiriya), Judgment, ICJ Reports 1982,pp.64-65,para.81.正如有学者所言,实现公平结果的任务为国际法院和法庭在选择“相关情况”方面提供了较大的可塑空间与回旋余地。⑦See P. Birnie, Delimitation of Maritime Boundaries: Emergent Legal Principles and Problems, in Gerald Blake(ed.),Maritime Boundaries and Ocean Resources 33(Croom Helm Publishers 1987).在缅因湾案中,美国认为,捕鱼、研究、开发以及为该区域提供导航辅助设备和搜索救援的责任表明其在该区域存在“重大利益”。①See Case Concerning Delimitation of the Maritime Boundary in the Gulf of Maine Area (Canada v.United States of America),Counter-Memorial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paras.7,104,329,411.此外,美国还根据形成“重大利益”所需的累积叠加标准认为,即便在绘制临时界线时不考虑这些情况,也应在稍后阶段加以考虑,以获得公平结果。②See Case Concerning Delimitation of the Maritime Boundary in the Gulf of Maine Area (Canada v.United States of America),Counter-Memorial of the Canada,para.540.尽管国际法院特别分庭认可美国在划界区域渔业中确立了某种程度的主导地位,但最终仍没有支持美国的划界主张。③See Case Concerning Delimitation of the Maritime Boundary in the Gulf of Maine Area (Canada v.United States of America),Judgment,ICJ Reports 1984,p.246,paras.233-235.换言之,法庭承认美国在缅因湾的部分地区存在“重大利益”,但由于这种利益没有覆盖整个区域,由此,美国的主张最终未能得到法庭支持。
在黑海划界案中,乌克兰声称其在相关区域具有“重大利益”,这种利益使其在防卫事务、航行安全和海洋环境保护等方面具有“某种优势”。④See Maritime Delimitation in the Black Sea (Romania v. Ukraine), Oral Hearings, 12 September 2008,para.81.但是,由于乌克兰前述观点均以地理地貌为基础,而地理地貌不是“重大利益”概念的组成要素,因此也未能获得国际法院的支持。此外,尼加拉瓜在尼加拉瓜诉哥伦比亚案中也援引了“重大利益”这一概念,但由于尼加拉瓜的主张基于其延伸的海岸这一地理因素而未获得法院支持。⑤See Territorial and Maritime Dispute(Nicaragua v.Colombia),Memorial of Nicaragua(Volume I),p.169,para.2.240.尽管前述两个案例的“重大利益”最终未能影响划界,但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重大利益”这一概念的继续发展。在斯洛文尼亚诉克罗地亚案中,仲裁庭考虑了包括安全和航行利益在内的所有“相关情况”,甚至还考虑了斯洛文尼亚对海洋经济的依赖,借此为其建立“接合区”(junction area),⑥See Final Award in the Maritime of an Arbitration under the Arbitration Agreement between the Government of the Republic of Croatia and the Government of the Republic of Slovenia, Signed on 4 November 2009,2017,pp.305-306,paras.985-986;p.345,para.1080.较好地反映了斯洛文尼亚的“重大利益”。
上述案例表明,单一非地理因素经过叠加后可能产生一种累积效应,从而形成影响海洋划界的“重大利益”。一般来说,“重大利益”概念的本质在于,单个非地理因素不足以影响海洋界线的确定,但多个非地理因素经“抱团”后能产生更大的利益分量,继而使法院或法庭在划界过程中重视这些非地理因素对划界产生的影响与效力。费希尔(Fischer)法官在扬马延案中指出,“不单独评估单个非地理因素是否与海洋划界相关是没有问题的,问题在于是否应该整体性评估和权衡这些因素。”⑦Maritime Delimitation in the Area between Greenland and Jan Mayen (Denmark v. Norway), Judgment,ICJ Reports 1993,p.304,para.14.实际上,在扬马延案中,挪威使用了“累加”观点,以此加强其对扬马延周边海域的权利主张,认为“挪威在扬马延周边海域存在的利益”,“倾向于形成一个自然团体”。①Maritime Delimitation in the Area between Greenland and Jan Mayen (Denmark v. Norway),Counter-Memorial of Norway,para.673.
由此可见,由于不具有地理地貌性质,部分因素在传统司法实践中被排除在海洋划界的考虑范畴之外。然而,如果这些非地理因素能组成“因素矩阵”,②M. D. Evans, Maritime Delimitation and Expanding Categories of Relevant Circumstances, 40 International and Comparative Law Quarterly(1991).国际司法机构将其作为整体考虑,则有可能证明沿海国存在“重大利益”,③See M. D. Evans, Maritime Boundary Delimitation, in Donald R. Rothwell, et al. (eds), The Oxford Handbook of the Law of the Sea 275-276(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5).继而对海洋划界产生影响。不过,一般来说,只有主权国才能援引“重大利益”这一概念,而且只能在解决海洋划界争端时援引。换言之,国际社会不能因为防止沿海国损害国际海底区域这一“人类共同遗产”,以此援引“重大利益”来阻止主权国家依《公约》主张200 海里以外的大陆架管辖权。埃文斯(Evans)认为,“‘重大利益’的价值来自‘证据的叠加’,旨在证明争议一方在某一特定海域比另一方拥有更大的利益”。④M.D.Evans,Relevant Circumstances and Maritime Delimitation 208(Clarendon Press 1989).亦有学者指出,“重大利益”是由其他称之为因素或要素组成的集合体,其总和大于各组成部分的价值。特别是,一国在中间线/等距离线以内善意开展的一系列活动,亦可说明该国在争议海域可能拥有特殊利益,⑤See Nicholas A.Ioannides,The Legal Framework Governing Hydrocarbon Activities in Undelimited Maritime Areas,68 International&Comparative Law Quarterly 23(2019).这些利益经过叠加后进一步证明其在特定海域存在“重大利益”,继而在海洋划界中发挥作用。
从法理层面来看,将达不到特定门槛的单个活动予以累积或叠加,在国际法领域并不鲜见,国际法院和其他司法机构以及仲裁机构在其审理的案件中多次探讨过“事件累积原则”。首先,《国家对国际不法行为的责任条款草案》第15 条第1 款规定:“一国通过被一并定义为不法行为的一系列作为和不作为违背国际义务的情事,发生于一作为和不作为发生的时刻,该作为和不作为连同其他的作为和不作为看待,足以构成不法行为。”⑥刘颖、吕国民主编:《国际法资料选编》,中信出版社2004年版,第73页。可见,国家承担违反国际义务的责任并不一定由某单一行为引起,亦可能起因于一系列作为或不作为。换言之,欲确认成立诸如种族灭绝、种族隔离或危害人类罪等侵权行为,则必须审查组成复合行为的若干单个作为或不作为是否发生。此外,国际法委员会也强调,委员会应该为各方利用国际习惯法的依据提供便利,例如,搜集和出版有关国家惯例。系列实践一俟累积,即可作为证明习惯国际法规则的存在依据。⑦参见《国际法委员会章程》第24 条,https://legal.un.org/ilc/texts/instruments/english/statute/statute.pdf,2022年3月9日访问。
在司法实践中,适用“累积原则”的案例并不鲜见。譬如,在对尼加拉瓜进行军事和准军事行动案中,国际法院在审查尼加拉瓜自1982 年至1984 年进入洪都拉斯和哥斯达黎加的一系列行为后认为,尼加拉瓜的行为并不构成武装袭击,洪都拉斯和哥斯达黎加因此无权实施自卫。①See Military and Paramilitary Activities in and against Nicaragua (Nicaragua v.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Merits,Judgment,ICJ Reports 1986,pp.119-120,paras.231-233.在伊朗诉美国石油平台案中,国际法院指出,美国行使自卫权的前提是伊朗的行为构成袭击,但法院认为,从伊朗的单个行为来看并不是袭击行为,需要对这些“接连发生的”事件从整体上分析。②See Oil Platforms (Islamic Republic of Iran v.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Judgment, ICJ Reports 2003,pp.191-192,para.64.另外,在2005 年关于在刚果境内的军事行动案中,国际法院讨论了将“解放刚果民主力量联盟”对乌干达发动的攻击归于刚果民主共和国的可能性。法院最后裁定,“即使这一系列令人遗憾的攻击可以被视为累积性(cumulative)攻击,但它们仍然不能归于刚果民主共和国。”③Armed Activities on the Territory of the Congo (Democratic Republic of the Congo v. Uganda),Judgment,ICJ Reports 2005,pp.222-223,para.146.在杜兹吉特诚信仲裁案(马耳他诉圣多美和普林西比)中,根据《公约》附件七组成的仲裁庭也适用了“事件积累”原则,仲裁庭综合审查了圣多美对悬挂马耳他国旗的船只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认为这些措施与“依据《公约》第49 条主权国家行使主权的规定”不符。④See Duzgit Integrity Arbitration (Malta v. São Tomé and Príncipe), 2016, paras.256-261, https://pcacases.com/web/sendAttach/1915,visited on 10 March 2022.
由此可见,将非地理因素“累积”或“叠加”成“重大利益”并发挥其在海洋划界中的效力,不仅有坚实的法理基础,而且有较丰富的国际司法判例。
(二)非地理因素累积产生的“重大利益”作为对公平结果的检验要素
毋庸置疑,海洋划界的主要目的是获得公平的划界结果。因此,不管采取何种划界方法,国际法院或法庭最终需要验证其提出的解决方案能否实现公平结果,沙哈布丁(Shahabuddeen)法官在缅因湾案中指出,“不接受法律验证其正确性的决定绝不能算是司法行为”。⑤See Maritime Delimitation in the Area between Greenland and Jan Mayen (Denmark v. Norway),Judgment,ICJ Reports 1993,p.130,Separate Opinion of Judge Shahabuddeen,p.193.在结果验证阶段,为避免出现不公正的划界结果,国际(准)司法机构可能倾向于评估地理因素以外的其他因素。⑥See Prosper Weil, The Law of Maritime Delimitation: Reflections 260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9).
在缅因湾案中,国际法院特别分庭尽管最先拒绝考虑诸如捕鱼、石油和天然气开采、科学研究以及安全或防卫等与划界无关的一系列非地理因素,但同时承认,前述非地理因素可能在稍后阶段发挥作用。①See Delimitation of the Maritime Boundary in the Gulf of Maine Area (Canada v.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Judgment,ICJ Reports,p.278,para.59.因此,在初步确定界线后,特别分庭决定重新考虑其此前排除的非地理因素,以评估其初步确定的界线能否实现公平结果。对此,特别分庭指出,在评估由界线产生的划界结果是否符合公平要求时,似乎应该适当考虑其他情况,这些“其他情况”无疑包括双方提供的有关人文地理和经济地理等数据。特别分庭因此认为,虽然前述“其他情况”本身不能作为划界所适用的标准加以审议,但可以用来评估最初根据自然和政治地理标准确定的划界的公平性。②See Delimitation of the Maritime Boundary in the Gulf of Maine Area (Canada v.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Judgment,ICJ Reports,p.340,para.232.需要特别说明的是,特别分庭在该案中强调,只有在得出不会产生“灾难性影响”的结论后界线才是确定的。③See Delimitation of the Maritime Boundary in the Gulf of Maine Area (Canada v.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Judgment,ICJ Reports,pp.342-344,paras.237-241.可见,特别分庭实际上已经考虑了部分非地理因素。
无独有偶,仲裁庭在加拿大诉法国案中更是明确强调,由于双方均提出证据并辩称,划界会对其捕鱼权利与捕鱼习惯产生影响,继而影响民众的经济福祉,仲裁庭不能对此置若罔闻。在根据地理因素初步确定界线后,仲裁庭仍有义务确保自己作出的解决方案不是“根本不公平的”。④See Delimitation of the Maritime Areas between Canada and France,Award of 10 June 1992, 31 International Legal Materials 1149,para.84.在利比亚诉马耳他案中,国际法院同样指出,法院需要使用一些标准,以备调整临时界线之需。⑤See Case Concerning the Continental Shelf(Libyan Arab Jamahiriyia v.Malta),Judgment,ICJ Reports 1985, p.46,para.60.威尔对此认为:“对安全、政治以及其他非地理因素的考虑,主要是从法律上评估界线是否具有公平性,这说明对非地理因素的考虑与不侵犯空间原则之间是密切相关的。”⑥See Prosper Weil, The Law of Maritime Delimitation: Reflections 265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9).在扬马延案中,国际法院也注意到非地理因素对海洋划界的影响,国际法院指出,按照200 海里的距离标准在格陵兰东部海域划定界线,从数学角度看可能比根据中间线划定的界线更为公平,因为前者考虑了双方海岸线长度的差异。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由此确定的界线绝对公平,是否公平还须基于法律的考量作出,如仅将给予格陵兰东海岸全效力后的剩余面积划归挪威,将严重损害扬马延岛的权利,亦违背了公平的基本要求。⑦See Maritime Delimitation in the Area between Greenland and Jan Mayen (Denmark v. Norway),Judgment,ICJ Reports 1993,p.38,para.70.
上述案例说明,非地理因素即便在划界的第一阶段不被视为“相关情况”,也可能在第二个(验证)阶段予以考虑,作为国际法院或法庭判断其确定的界线是否公平的辅助因素。①See Case Concerning the Continental Shelf(Libyan Arab Jamahiriyia v.Malta),Judgment,ICJ Reports 1985, p.47,para.62.诚如学者所言,在评估划界方案是否公平时还应考虑(地理地貌因素以外的)其他方面。②See M. D. Evans, Maritime Boundary Delimitation,in Donald R. Rothwell,et al. (eds.), The Oxford Handbook of the Law of the Sea 270(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5).韦拉曼特里(Weeramantry)法官也认为,在法律没有明确规定何种因素对划界无关紧要的情况下,就需要评估所有因素对划界的影响。③See Maritime Delimitation in the Area between Greenland and Jan Mayen (Denmark v. Norway),Judgment,ICJ Reports 1993,p.211,Separate Opinion of Judge Weeramantry,para.26.特别是,如果将全部非地理因素累积起来并证明该国存在“重大利益”,其在海洋划界中将发挥更大的作用。
总之,既有国际司法实践表明,所有“相关情况”都应在海洋划界中予以审查并加以权衡,以确保公平。④阐述这一观点的主要案例及法官的不同意见主要有:北海大陆架案判决书第93、94 段;突尼斯诉利比亚案判决书第71 段;缅因湾案裁决书第108~125 段;尼加拉瓜诉哥伦比亚案判决书第242 段;突尼斯诉利比亚案阿雷查加法官的独立意见第24 段与第35 段;利比亚诉马耳他案莫斯勒(Mosler)法官的反对意见第119 页;丹麦诉挪威案韦拉曼特里法官的独立意见第26 段;缅因湾案加拿大的诉状第311段。在海洋划界中,需要考虑的因素十分广泛,远远超出地理地貌的范围,对相关国家具有重要意义的各种因素都应该被考虑到。⑤See Thomas Cottier, Equitable Principles of Maritime Boundary Delimitation: The Quest for Distributive Justice in International Law 381(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5).鉴于单一非地理因素对海洋划界的影响非常有限,应考虑将非地理因素予以累积并“抱团”作为影响海洋划界的新因素,以提高划界结果的公平性。
(三)非地理因素累积产生的“重大利益”在海洋划界灵活性与确定性之间的平衡作用
一直以来,公平原则集团与等距离线集团在海洋划界的灵活性与确定性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前者诟病等距离线方法的僵硬死板及其对公平划界可能造成的危害,后者则非议公平原则的随意性与不确定性。无论两大集团之间的观点如何迥异,国际(准)司法机构应该以追求公平划界为己任,而公平结果需要在适用规则的明确性和不同案件的特殊性之间寻求平衡。“重大利益”概念在海洋划界中的引入,在某种程度上有利于平衡海洋划界的灵活性与确定性,为公平原则集团与等距离线集团所乐见。
在北海大陆架案中,国际法院在审理之初即决定适用公平原则,而不是仅将其视为评判划界结果是否公平的矫正工具。随后,国际法院在其后续审理的海洋划界案件中更加重视公平结果的实现,并在突尼斯诉利比亚案以及缅因湾案中将其视为一项规范性规则。然而,在利比亚诉马耳他案中,国际法院摒弃了一开始即适用公平原则的观点,转而发展出通过调整临时等距离线来实现公平结果的新型公平原则。法院意欲通过这种方式,在不忽视海洋公平划界这一目的的同时,力求提高海洋划界的规范性。①See Robert Kolb, Case Law on Equitable Maritime Delimitation: Digest and Commentaries 391(Martinus Nijhoff 2003).实践表明,自扬马延案以来,国际(准)司法机构在大多数案件中均将中间线或等距离线作为划界出发点,随后逐渐演进为三阶段划界规划并得到广泛应用。然而,新近案例表明,划界第一阶段再次出现向公平原则而不是等距离线方法的转变,有学者因此指出,晚近海洋划界司法实践“在划界过程中引入了高度的不可预测性”。②M. D. Evans, Maritime Boundary Delimitation, in Donald R. Rothwell, et al. (eds.), The Oxford Handbook of the Law of the Sea 664-665(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尽管如此,托马斯·科蒂埃(Thomas Cottier)认为,不应直接比较公平原则和中间线/等距离线方法。他进一步阐释道,公平原则比中间线/等距离线方法的外延更宽,公平原则可以但并不必然通过中间线/等距离线来实现,两者不能相提并论,他还特别指出“公平原则远未成熟。”③Thomas Cottier, Equitable Principles of Maritime Boundary Delimitation: The Quest for Distributive Justice in International Law 381,386(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5).科尔布对公平原则只提供一个总体框架颇有微词,认为公平原则的规范性较弱,需要具体规则与之配套。④See Robert Kolb, Case Law on Equitable Maritime Delimitation: Digest and Commentaries 443(Martinus Nijhoff 2003).可见,要想克服纯粹依据自然地理地貌特征划界可能造成的不公平结果,矫正公平必不可少,但亦不能“矫枉过正”,不能改变地理地貌的现实状况。“重大利益”致力于寻求划界的公平结果,可发挥“平衡测试”的功能,对界线是否公平作出最终评估。⑤See Thomas Cottier, Equitable Principles of Maritime Boundary Delimitation: The Quest for Distributive Justice in International Law 617(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5).
尽管在司法实践中,国际法院或法庭使用“比例检测”来判断海洋划界结果的公平与否,或将“比例原则”认定为划界的“相关情况”,或者将其作为评估最后界线是否公平的检测工具。⑥See Thomas Cottier, Equitable Principles of Maritime Boundary Delimitation: The Quest for Distributive Justice in International Law 554-555(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5).据统计,运用“比例原则”的案例主要有:北海大陆架案判决第98、101(D)(3)段;英法大陆架案裁决书第99~101 段;突尼斯诉利比亚案判决书第131 段;缅因湾案判决书第185 段;利比亚诉马耳他案判决书第55、75 段;加拿大诉法国案裁决书第63 段;1993 年丹麦诉挪威案判决书第66 段;1999 年厄立特里亚诉也门案(第二阶段)裁决书第165 段;2018 年哥斯达黎加诉尼加拉瓜案判决书第159~162 段;利比亚诉马耳他案鲁达(Ruda)等法官的独立意见第20 段;突尼斯诉利比亚案利比亚的答辩意见第514 段;卡塔尔诉巴林案卡塔尔诉状第279~283、301~302段。但是,由于三阶段划界规则在第三阶段所采用的“不成比例检验”仅囿于将相关国家海岸线长度之比与各方所分配的海域面积之比进行比较,⑦See Maritime Delimitation in the Black Sea (Romania v. Ukraine), Judgment, ICJ Reports 2009,p.103,para.122;pp.129-130,paras.210-216.强调对以地理为基础的不成比例进行检验而忽视了由非地理因素组成的“重大利益”对海洋划界可能产生的影响,最终可能影响划界的公平性。因此,可考虑在第二阶段审查相关国家“重大利益”的有无以及其对划界的影响。
(四)“重大利益”概念下非地理因素划界效力的自我克制
在英法大陆架案中,仲裁庭认为,“重大利益”这一概念的目的不在于“重塑地理”,而是促成公平结果的实现。“在某种程度上,这是一个补救因特定地理地貌所造成的不成比例和不公平结果的问题。”①United Kingdom of Great Britain and Northern Ireland/French Case,1977,18 RIAA 3,para.101.可见,与地理因素相比,由非地理因素组成的“重大利益”所能发挥的作用具有消极性与防御性。换言之,在考虑“重大利益”在海洋划界中的适当作用之同时,不能无限放大“重大利益”在海洋划界中的划界效力,否则会有碍公平结果的实现。譬如,即便一国在国防和安全方面存在“重大利益”,亦不应利用该“重大利益”来支持其过分的划界主张。
有学者认为,争议海域离某沿海国的海岸越近,临近争议海域的国家利益就愈占主导地位。②See Thomas Cottier, Equitable Principles of Maritime Boundary Delimitation: The Quest for Distributive Justice in International Law 530(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5);Nicholas A.Ioannides,The Legal Framework Governing Hydrocarbon Activities in Undelimited Maritime Areas, 68 International & Comparative Law Quarterly 8-9(2019).尽管传统观点认为一国安全关切仅与领海有关,③See Donald R. Rothewell & Tim Stephens, The International Law of the Sea 60 (Hart Publishing 2016).但随着科技的飞速发展以及人类可利用的自然资源日益枯竭,沿海国在专属经济区内有全面行使管辖权的趋势,④See Thomas Cottier, Equitable Principles of Maritime Boundary Delimitation: The Quest for Distributive Justice in International Law 591(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5).即使是发生在远离海岸的行为也可能对沿海国的安全构成威胁。因此,为了尽量减少前述风险,沿海国倾向于依中间线/等距离线分割海洋,或者尽可能减小将中间线/等距离线向其海岸方向调整的幅度。
然而,前述观点值得商榷,尽管非地理因素在海洋划界中可能发挥某种程度的作用,但不能将“临近一国海岸”泛化为该国的“重大利益”,以此主张严格适用等距离线更是削弱了地理地貌因素在划界中的主导地位,不利于公平结果的实现。实际上,依据《公约》之规定,划界当事国以外的其他国家在当事国的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亦享有若干权利,只须其他国家行使相关权利时“适当顾及”当事国的主权权利和管辖权。⑤参见《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58条第3款。既然《公约》在“临近一国海岸”的专属经济区及大陆架赋予其他国家“铺设海底电缆和管道”等权利,足见一国对其近海大陆架的管辖权是相对的,其安全亦并非完全依赖界线予以保障。
一言以蔽之,无论传统海洋法还是现代国际海洋法,均以追求公平划界为己任,公平划界无疑要充分考虑沿海国非地理因素所产生的“重大利益”。国际(准)司法机构只是将“重大利益”作为整体纳入“相关情况”的范畴,而“重大利益”的单个组成部分并不能独立发挥“相关情况”的作用。海洋公平划界并不是一一满足沿海国依非地理因素提出的所有利益诉求,而是在“重大利益”这一概念的综合权衡下使其各项利益在一定程度上得以实现。“重大利益”创设了一个内涵更广的概念,最大限度地全面考虑沿海国因非地理因素产生的国家利益,以此发挥“重大利益”对不公平结果的矫正功能。
四、结论
从整体来看,在海洋划界中发挥主要作用的是国家的海岸地理与地貌。与地理地貌相比,国际(准)司法机构一般不明确地将单个非地理因素纳入海洋划界的“相关情况”。但是,从本质上说,海洋公平划界要求海洋划界必须考虑所有“相关情况”。在实践中,尽管单个非地理因素不足以在海洋划界中产生影响,但多个非地理因素“抱团”后却能在海洋划界中发挥重要作用。因此,如果国际(准)司法机构在海洋划界中完全忽略非地理因素对海洋划界的影响,可能会导致错把本该赋予甲国重大利益的海域划分给了乙国,最终使甲国的海洋利益受到损害,从而无法实现海洋公平划界的目的。
“重大利益”这一概念的引入,使得国际(准)司法机构在基于相关国家地理地貌作出基本判断的同时,兼顾非地理因素对海洋划界的影响,最大限度地实现海洋划界的公平解决。鉴于非地理因素普遍存在于海洋划界的不同个案中,在适用三阶段划界规则过程中,可考虑在第二阶段发挥非地理因素对界线的调整作用,以确保主张“重大利益”国家的利益不受损害。与此同时,“重大利益”只能作为在海洋划界中维护海洋权利的防御性工具,不能无限放大非地理因素在海洋划界中的地位与作用,非地理因素不能颠覆地理因素对海洋划界的主导作用,否则会破坏划界结果的公平性。
总之,尽管在国际海洋划界中起主要作用的是当事国的地理地貌,但非地理因素,特别是将诸多非地理因素作为整体考虑而对一国产生“重大利益”时,国际司法实践亦给予其一定的划界效力。诚如学者所言,通过司法手段解决国际争端已经成为当今国际关系一个明显特征和突出现象,①参见朱利江:《国际法院判例中的争端之界定——从“马绍尔群岛案”谈起》,《法商研究》2017年第5期,第159页。在这种大背景、大趋势下,我们需要参与国际争端的司法解决程序。②参见何志鹏:《国际司法的中国立场》,《法商研究》2016年第2期,第53页。为了在海洋划界中更好地维护我国权利,我国不仅要重视东海、南海对我国有利的地理地貌的论证,同时也要发现对海洋划界可能产生影响的非地理因素,适度调整“自我克制”的传统油气开发政策,加强对争议海域的地震勘探,①参见张华:《争议海域油气资源开发活动对国际海洋划界的影响——基于“加纳与科特迪瓦大西洋划界案”的思考》,《法商研究》2018年第3期,第162页。巩固并进一步扩大我国在钓鱼岛群岛海域的捕鱼等活动、加大对南海的管理力度,以增强非地理因素在将来划界中的影响效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