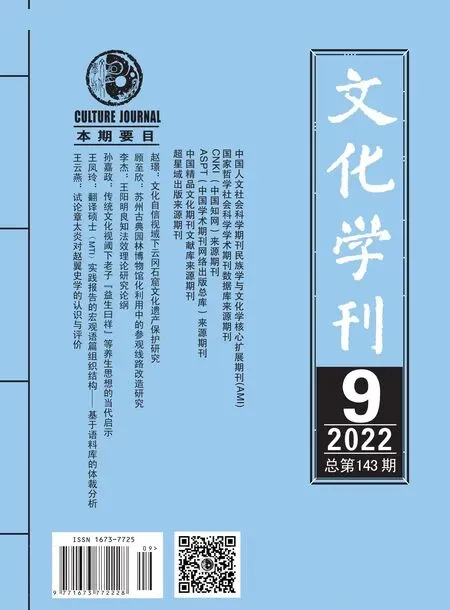网络旧体诗词中的城市书写
韩文昕
改革开放之后,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的步伐加快,现代城市体系越来越完善,已然代替农村成为现代人主要的生活场所。然而根植于农耕文化的土壤,长于书写田园牧歌情调和古典情怀的传统诗词,在面对现代城市经验的感觉化、片段化和复杂化时,不可避免地出现了表达危机,甚至有学者认为“传统诗歌的语言、节奏,及其意象符号系统,已然无法处理纷繁的现代都会感觉,诗人的内在文化心理也与现代城市出现巨大的断层”[1],并由此断言古典诗词与“现代性”无缘。这种断言虽不至于一无是处,但绝对是以偏概全。20世纪90年代以来,网络渐渐普及并且逐渐超过纸媒,成为诗词爱好者们发表和探讨旧体诗词的平台,网络的自由、开放、包容与多元,使旧体诗词呈现出不同以往的新面貌,诗人们致力于突破传统的认知方式和思维方式的局限,摸索着与现代城市经验相契合的新型表达方式,对现代城市景观、城市众生复杂的心灵状态及生活面貌进行了全面而深入地摹写和呈现,体现出全新的人文精神与现代性取向。
一、光陆怪离的城市景观
现代城市是一个景观化的社会,作为城市景观的高楼、车站、街道、广场等往往被看作是有别于乡村的重要标志。景观作为被展示出来的可视的景色、景象成为都市最重要的本质特征,对景观表象的感觉体验成为把握都市生活的重要方式[2]239。网络诗词的创作者们对城市的感知和观照,直接表现为对周遭城市景观的摹写与复现,他们笔下有作为城市发展与繁华标志的高楼大厦,“广厦摩天深峡险”“危楼万幢号新天”;有作为城市重要聚合节点的车站和机场,“客中送客更南游,一站华光入夜浮”“机场亭午虹桥路,景物漫移车”;有隐喻着城市消费欲望的广告牌和酒吧,“广告牌中笑靥,被玻璃、折射千回”“玄栅朱棂,铜牌门号,依约欧陆风情”;有代表城市速度的汽车与地铁,“河床以下,城市绽开银骨架”“彩色电车叮当响,闪过轻眉靓痣”;也有上演着市民日常的街道与民居,“楼下街摊争叫卖,人如赛,小锅潽了鲜牛奶”……网络旧体诗人们对都市景观包罗万象式地呈现,涵盖了城市文化的主要特点,使旧体诗词呈现出鲜明的现代性和时代性,和柳永等传统文人笔下充满古典情调的都市景观大相径庭,现代城市景观是工业化和机械化的直接产物,呈现出纷纭复杂和光陆怪离的特点。栖身于高楼大厦钢筋水泥间,面对声、色、光、电等都市景观的庞大堆积和挤压,很容易产生不真实感和错乱感。现代城市诗词的力倡者曾峥在《渔家傲·城市黑洞/昨夜星辰》一词中,就写出了现代都市景观在给人带来便利和震撼的同时,也造成了紧张和压抑:
广厦摩天深峡险。死生时速天天演。黑白人涂斑马线。加或减。楼中楼外翻双面。城市错车休眨眼。反光镜里曾惊艳。昨夜恒星都塌陷。时空卷。立交桥上银河旋。
这首词通过对城市纵横交错的交通路线,以及日日穿梭不息的车辆洪流的解构,折射出现代都市景观给人带来感官的新奇和刺激的同时,也像物理现象中的“黑洞”一般淹没了人的个性和选择,造就无力与迷失。现代通讯和运输革命给都市空间带来“运动、速度、光和声音的新变化,这些变化又导致了人们在空间感和时间感方面的错乱”[2]230。
与乡村景观及社会结构相对稳定不同,现代城市充满着矛盾、偶然、短暂和裂变,随着现代化和商业化的不断发展,旧的景观会迅速被新的景观所替代,随之逝去的不仅是都市景观,还有城市的记忆。曾峥的组词《我们的城市记忆——江城后现代竹枝词十首》中的武汉关、汉口水塔、武汉长江大桥、大智门火车站等老武汉的地标性建筑,武汉1路电车、黄鹤楼开往晴川的轮渡等交通工具以及竹床阵这种风俗民情等人文景观,极富地域特色。诗人怀念那些见证了他成长的城市景观,却又无力抵挡它们在日新月异的城市化浪潮中退出历史舞台乃至走向消亡。林彬的《选冠子·待拆迁老弄堂》则聚焦于弄堂这一富有生活气息的城市景观:“斑驳缭墙。纵横电线。缚住几家门巷。扶梯浅浅。天井深深。……竞逐繁华。忍看塔吊频来。工棚开敞。料明年重到。唯有东风无恙。”住宅区的弄堂和老街是城市居民日常生活的重要场所,上演着城市人的喜怒哀乐和矛盾冲突,充满了市井气息和人文色彩。诗人曾经生活过的弄堂和街道,承载着他成长过程中许多记忆和情感,然而随着城市化的发展,弄堂或被改造成商业区,或被拆墙重建,随之消失的不仅是一条巷弄或街道,还有饱含文化记忆和故事的市井景观。
二、异化困守的城市心灵
对城市景观的呈现更多地指向物质层面的城市,然而城市并不只是一种物质机制,它和居住在其中的人群紧密联系在一起。城市并不仅仅以它的街道、交通、建筑物来表达自己,而且也通过居住于其中的人群的生活、娱乐、心态等方式来表现自己[3]。留取残荷在《城市诗词三百首》编后志中说到:“城市是万相众生之镜,一切忧愁、不安、隔膜、疏离、愤怒无不映照其中。[4]”现代城市带来新的机械文明,带来新的享乐和受苦,也带来了人的异化,造就了新的心灵困境。现代都市中人普遍面临的心灵困境之一就是孤独。孤独是人类的本质属性,自古以来古今中外的文学家和哲学家对“孤独”这一母题的阐释层出不穷,中国传统诗文中有关孤独心绪的吟咏亦是不绝于耳,然而古代文人的孤独感多是源于离别、羁旅漂泊和怀才不遇,而现代城市中人的孤独更倾向于一种“人群中的孤独”,如殊同在《桃花》一诗中所呈现:“我本山里人,尝把繁华慕。拥入城市来,攘攘顿成误。楼宇相平行,街道相交互。简单之人情,纷繁之事务。喜亦无人饮,悲亦无人诉。城中多故友,不知在何处。”同乡村的熟人社会大不相同,现代城市的庞大、高速、紧张、压力以及畸形的欲念竟逐造成人与人之间的冷漠、生疏和隔膜,“自古远亲难比邻,今兴老死不相闻。房前摆手应招手,楼里钢门对铁门(汪孔臣 《邻居》)”。在以工业化和机械化为特征的城市经验面前,人不仅被强行取消了和自然经验交流的可能性,更重要的是被剥夺了人群中的精神归属感,“人的整个存在连同他对世界的全部关系都从根本上成为可疑的了,人失去了一切支撑点,一切理性的知识和信仰都崩溃了,所熟悉的亲近之物也移向缥缈的远方,留下的只是处于绝对的孤独之中的自我”[5]。曾峥以诗人的敏锐触角深入都市人的心灵甬道,书写出挣扎在现代城市“黑洞”中个人的漂泊感、孤独感和迷失感:
大黑肇万象,胡为乎返往。车灯有狼性,尖锐撕夜网。
真空弥微尘,无序而振荡。我亦等粒子,加入彼合唱。
一尘既一狱,我眼亦我障。起视同车人,沉泥失眉样。
大块呼吸匀,林峦涌微浪。霜星有芒角,驰道系其上。
城市若跳炬,灼灼欲何向。银河多暗流,永夜靡恒亮。
古月旋金橙,时闻发条响。(《发条橙在路上——冬夜自鄂州返汉》)
诗中“发条橙”这一意象本是来自于英国当代著名作家安东尼·伯吉斯的小说,后来经美国导演斯坦利·库布里克改编,成为电影史上最重要的电影之一。一种说法是马来语中Orange包含“人”的意识,所以“发条橙”是指上了发条的人,隐喻着人的异化和迷失,“人的异化”最直接导致的便是主体精神的丧失和因虚无而造成的生命漂泊感和幻灭感。从标题“冬夜自鄂州返汉”可知此诗基于诗人冬夜乘车的一次经历,但作者并没有沿用传统的纪实手法,而是采用了超现实主义和后现代的手法来呈现自己在车上的所见所闻所思,实境与幻境交织,意象缤纷,光怪陆离,表现出都市漂泊人迷失混沌的状态。人处在机械化的城市当中,有如一个上了发条的橙子,丧失了自主性,成为了异化的、无根的、漂泊的都市陌生人。
现代城市所带来的人生虚无感和孤独感进而导致了欲望的泛滥与放纵,“城市本身就是一个巨型的假面舞会,在这里,一切的游戏规则被重新规定,你必须学会假笑、哭泣、热爱短暂的事物、追赶时髦”[6]。曾峥在诗歌《我是平民》中刻画了一个“生活从来寓表层”的城市平民形象,面对着城市中转瞬即逝的一切,城市平民随波逐流,追求浮浅的快乐,“若有所诗终不在,实惟解构及无形”代表着理性和深刻的丧失,“空吧微醉点歌罢,午夜狂飙又闯灯”喻示着在城市欲望的洪流中迷失了自我和道德。“酒吧”是网络诗词中频繁出现的一个城市意象和景观,“酒吧近零点,坐客犹喧喧(嘘堂《饮酒第五》)”“浅歌深醉葡萄盏,吧台畔、君且沈沦(李子《风入松》)”,酒吧作为城市中供人消费和享乐的场所,不只是停留在物质消费的层面,这里没有时间和道德的规束,始终困扰着都市人的孤独和虚无得以获得暂时性的解脱和释放,酒吧作为一个经典场景指向欲望化的叙事,沉沦在物欲中的人也难逃被物化的命运,丧失了自主性,只能被城市支配,囿于善与恶、节制与放纵的双重困境。
三、形形色色的城市众生相
城市是万相众生之所,不同地域、阶级、民族、职业的人聚集在城市之中,上演着一幕幕悲欢离合人生百态。诗人一旦进入城市,也就成为城市人群的一部分,他们代表着人群中一种较为清醒和独立的审美意识,他们从城市的角度对自我进行定位和阐释,不同的成长和生活经历导致他们在自我认同方面存在较大的差异,进而又会影响他们观照、书写城市的角度以及对城市人群的刻画。
“书生霸王”赵缺站在普通劳动者的角度书写底层人民的生活,他笔下的人物各行各业都有,老挑夫、送水工、乞丐、卖花女、地铁卖报人、搬运工、推销员、卖报纸的、擦皮鞋的、城管人员、门卫等等,构成了一幅壮阔的民间生活画卷。赵缺当过推销员,卖过报纸香烟,他自称和民工、保安、开电梯的属于同流,对于这些中下层人民的生活,他以一个亲历者而非旁观者的身份来呈现,正是因为有着感同身受的亲身体验,才能将底层人民的生活写得如此细腻生动感人。有学者认为这种记录新时代底层人民生活的诗,还不曾在以往哪个诗人的笔下如此大量的出现过[7]。
曾峥作为土生土长的城市人,则以冷峻审视的笔触刻画出一个城市游离者的形象,从《发条橙在路上》《我是平民》等诗歌中,可以看到曾峥对高度发达的城市文明持一种审慎的态度。如果将现代城市比喻成一座围城,曾峥笔下的城市平民是欲出围城而不得,故而随波逐流的“城里人”,李子诗词中的城市平民就是欲进围城而不得的“城外人”。李子在赣南山区出生和长大,19岁去武汉读大学,25岁来到北京读研究生,然后在北京过着漂浮不定的生活。他以自己的亲身经历为基石,写出了外来打工族在城市的夹缝中求生存的艰难,如下面这两首诗:
高吊一灯名日光,河山普照十平方。伐蚊征鼠斗争忙。
大禹精神通厕水,小平理论有厨粮。长安居易不思乡。(《浣溪沙》)
方便面,泡软夜班人。一网消磨黄永胜,三餐俯仰白求恩。槐梦案头春。(《望江南》)
诗歌充满了反讽意味,古典语汇和现代语汇无缝衔接,形成一种荒谬的美感,将租屋狭窄、环境恶劣、生活艰辛的北漂生活以一种调侃和解构的方式呈现出来,让人忍俊不禁的同时却又莫名心酸。虽然外来打工者在城市中求生存十分艰难,但李子和他笔下的城市平民其实在十分努力认真地对待生活,比起曾峥笔下都市游离者的冷漠和疏离,这些漂泊于城市的打工者更加鲜活生动。都市游离者在留下与逃离之间摇曳迷失,而以李子为代表的外来打工者有着比较明确的生活目标,他们考虑柴米油盐,忧心居住环境,想要在城市站稳脚跟,他们有理想有追求,虽然这理想可能成为“槐梦案头春”,但他们依然拥抱真实的生活,并未迷失在都市的混乱无序中。
城市只是一个时代背景,一个外在的生活场域,旧体诗词作为一种文学样式,与其他文学并没有本质的区别,都必须深入生活的细部,描写人情揭示人性[8]。现代城市诗词的创作者们以网络为平台,以自己的亲身经历为创作基石,立足于当下语境,对城市进行多角度的书写,真实复现了现代城市居民的生活状态和心灵感受,既彰显了诗人的个性,也突破了古典诗词的审美规范,体现出鲜明的时代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