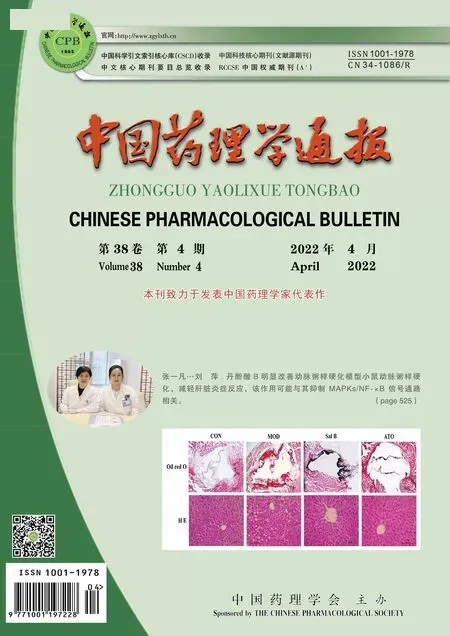钙调神经磷酸酶抑制剂体内处置的临床决定因素及机制研究进展
张 璐,李晶洁,闫佳佳,王长希,黄 民,陈 孝,陈 攀
(中山大学1. 附属第一医院药学部,广东 广州 510080;2. 附属第六医院生殖医学中心,广东 广州 510655;3. 附属第一医院器官移植中心,广东 广州 510080;4. 临床药理研究所,广东 广州 510080)
钙调神经磷酸酶抑制剂(calcineurin inhibitor,CNI)他克莫司和环孢素是实体器官移植中大多数免疫抑制方案的基石,但其使用因为具有较高的药代动力学(pharmacokinetic,PK)和药效学变异性而变得复杂。因此,临床医生常规基于治疗药物监测(therapeutic drug monitoring,TDM)来调整CNI的剂量,以使其血药浓度保持在治疗窗内。但是TDM有局限性,例如治疗窗作为相对合理浓度范畴不能保证有效性及安全性,TDM不能预测剂量需求及与药物的相互作用程度。此外,常规CNI的TDM是基于全血浓度,但是全血浓度与游离浓度(药理活性形式)的比例在随时变化。鉴于此,必须在了解特定临床环境下决定个体患者体内CNI处置因素的基础上,个性化使用CNI。本文综述了有关CNI的PK变异机制相关的研究,涵盖吸收、血液分布、组织分布、代谢、排泄以及与药物的相互作用环节。
1 影响CNI处置的机制—CYP3A和P-gp
影响CNI处置的因素通常是通过对CYP3A和(或)P-gp的影响来实现。他克莫司和环孢素都是CYP3A4和P-gp的底物和抑制剂,他克莫司的抑制作用低于环孢素[1],其解释可能是他克莫司的剂量比环孢素低20~50倍,在人体内没有达到体外抑制所需的浓度。基于生理学的PK模型估计肠细胞中的CNI浓度比血液和大多数其他组织中的游离浓度高出10倍[2]。因此,CYP3A4抑制的相关程度更可能发生在肠细胞而不是肝脏。
当CYP3A底物转化为代谢中间体与CYP3A不可逆地结合,导致酶的快速降解时,就会发生基于机制的抑制。许多药物和草药成分都是基于机制的CYP3A抑制剂,它们能强烈抑制肠道CYP3A活性[3]。肠道中的绝对酶含量低于肝脏,肠细胞的周转率高于肝细胞。因此,肠道CYP3A可能更容易被耗尽。
CYP3A4和P-gp的诱导是一个缓慢的过程,涉及转录激活,需要几天的时间才能起效。孕烷X受体(pregnane x receptor,PXR)和组成型雄烷受体(constitutive androstane receptor,CAR)是一类代谢相关核受体,能调节多种药物代谢酶和转运体的表达,包括CYP3A和P-gp。由于这些非特异的诱导途径,外源性物质通常会同时上调多个酶和/或转运体的表达,如利福平可以同时上调CYP3A、CYP2C8、CYP2C9、P-gp等的表达。
2 CYP3A和P-gp在肠道的分布
肠道对他克莫司首过代谢起关键作用,CNI的PK变异性与吸收过程中的肠道代谢有关,而不是仅与肝脏代谢有关。在肠壁中有表达许多I和II相代谢酶以及转运体。CNI是高度亲脂性的,很容易扩散到肠细胞,在那里它们可以被 CYP3A代谢,被P-gp泵回肠腔或者通过基底膜扩散到门静脉循环。由于CNI通过P-gp反复的再循环到肠腔中,每次通过肠细胞都为CYP3A介导的代谢提供了新的机会。这种连续的流出也使细胞内CNI的浓度保持较低,并防止了酶代谢能力的饱和。产生的代谢产物也是P-gp的潜在底物,并且亲水性更高,更可能保留在管腔一侧。
CYP3A和P-gp在整个肠道具有相反的表达梯度。肠上皮细胞中CYP3A4的表达量从近端到远端逐渐降低。人肠上皮细胞中P-gp的表达量在不同研究之间差异很大,但总体趋势与CYP3A4相反,即从胃到结肠逐渐升高[4]。远端小肠中的CYP3A4含量低,因此,尽管P-gp含量很高,他克莫司从远端肠道的吸收可能比近端肠道更有效。
2.1 腹泻/肠道炎症对CNI处置的影响感染性和非感染性腹泻可显著增加他克莫司的生物利用度,腹泻导致他克莫司谷浓度升高的可能机制是肠道运输时间的减少,导致他克莫司向远端小肠和结肠的递送增加,这些小肠和结肠能够吸收更多的他克莫司。在一项对6名健康志愿者使用定点放射标记胶囊的研究中,比较了他克莫司在小肠远端和近端结肠中的定时释放量。与近端结肠相比,小肠远端具有较高的AUC[5]。使用红霉素呼气试验(erythromycin breath test,EBT)对20名肾移植受者的P-gp活性进行的功能分析,与对照组相比,腹泻患者的肠道P-gp活性降低了50%,腹泻对肠道或肝脏的CYP3A活性没有显著影响[6]。
肠道损伤和炎症也会通过改变P-gp和CYP3A的表达和活性来影响CNI的处置。体外和动物实验均表明,在内毒素等炎性刺激下,CYP3A4在肝细胞和肠道细胞中的表达下调,机制涉及炎症反应抑制CYP3A4上游调控核受体PXR和CAR的激活。同样,发炎的肠粘膜的活检样本显示CYP3A4的表达低于未发炎的粘膜。多数人体内研究表明,肠道损伤和炎症会降低P-gp的表达。
2.2 肠道微生物对CNI处置的影响一项关于肾移植患者肠道菌群变化的研究发现,与健康人群比较,肾移植患者体内普拉俊菌(Faecalibacterium prausnitzii)减少具有统计学差异[7]。而在19名肾移植受者中进行的一项研究表明,移植后3个月,粪便中普拉俊菌的含量与他克莫司的较高剂量需求存在关联,这可能是因为该细菌产生的丁酸盐是肠细胞的能量来源,并可能刺激上调CYP3A4和P-gp活性[8]。另一项在24名心脏移植早期(<3个月)患者中的研究发现,他克莫司高剂量需求患者有更高的肠道菌群多样性[9]。
3 CNI的血液分布
因为CNI的亲脂性和红细胞中存在免疫亲和素,CNI与红细胞高度结合。他克莫司在全血与血浆中的含量比为13-114 ∶1。血浆中的他克莫司与白蛋白、α1-酸性糖蛋白和球蛋白高度结合,而与脂蛋白的结合程度较小,游离的他克莫司占比低于1%。环孢素在全血与血浆中的含量比为2-3 ∶1,血浆中的环孢素与脂蛋白结合,游离的环孢素占比在1%~5%。淋巴细胞中含有0.5%~5%的循环CNI。在较高的CNI浓度下,全血与血浆的比率较低。测定CNI的全血浓度是临床实践中定量的首选方法。对于他克莫司,未结合的浓度非常低,以至于难以检测到[10]。
血液中游离的他克莫司与组织区室保持动态平衡,并决定了生物学效应和肝脏提取率。即使游离的他克莫司肝清除率中等较高,但大部分他克莫司被截留在红细胞中,仅缓慢(超过几分钟)与血浆达到平衡,因此避免了过高的肝脏提取,导致肝脏全血清除率较低(占肝脏血流量的±3%)。红细胞压积和白蛋白的变化增加了CNI的清除率和剂量需求,但对游离部分没有显著影响。当红细胞压积降低时,游离部分会短暂增加,但会被肝脏迅速提取。最终结果是相同的游离浓度(和治疗效果),但由于清除率较高,全血浓度降低,每日剂量需求增加。白蛋白的变化也是如此,预计不会影响游离浓度。在一些临床情况下,全血浓度的改变仅是血液分布改变的结果,而游离血药浓度不变。例如,妊娠期患者的血容量增加,而血红蛋白、白蛋白和a1-酸性糖蛋白下降。Zheng等[11]报道由于血容量增加,10名孕妇需要增加45%的平均剂量才能维持他克莫司的谷浓度水平,但是剂量增加,而血红蛋白、白蛋白和a1-酸性糖蛋白下降,导致游离的他克莫司AUC增加173%,这可能与观察到的妊娠肾移植受者较高的感染率、高血压和先兆子痫有关。因此,在贫血和(或)严重低白蛋白血症的患者中,他克莫司的全血浓度会低估游离的浓度,维持相同的全血水平可能会增加中毒的风险。
许多临床PK研究证实,红细胞压积与他克莫司血药浓度呈正相关。红细胞压积增高,他克莫司的清除率下降,测定他克莫司全血浓度来评估疗效可能导致他克莫司的疗效水平低估0%~20%[12];相反,随着血细胞压积降低,他克莫司的清除率增加,测定他克莫司全血浓度来评估疗效,可能导致他克莫司疗效水平高估10%~40%。儿童肾移植患者红细胞压积低于成人参考值,可根据红细胞压积校正他克莫司剂量和浓度。更高的白蛋白水平为增强他克莫司清除率的协变量[13]。由于环孢素与血浆脂蛋白高度结合,因此脂蛋白水平的变化对血液分布和剂量需求也有类似影响,但不如贫血对他克莫司的影响明显。
4 CNI的组织分布
虽然CYP3A主要决定CNI的“进出”,即限制进入人体的药物数量,然后将其清除,但不同组织之间CNI浓度的差异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组织或细胞特异性的P-gp活性、脂肪含量和免疫亲和素浓度。
4.1 脑P-gp作为主要的转运体,在限制CNI的脑渗透中发挥重要作用。ABCB1C3435T多态性的存在与P-gp功能下降有关,导致几种P-gp底物(如苯巴比妥)具有较高的脑渗透性[14]。无论是由于基因多态性或伴随使用P-gp抑制药(如维拉帕米),血脑屏障的P-gp功能降低都可能导致更高的CNI脑浓度和更高的神经毒性。ABCB1多态性对P-gp功能的体内作用尚有争议。在63位骨髓移植受者中进行的一项研究报告发现,环孢素相关神经毒性的预测因素之一是ABCB1C1236T和G2677T/A基因型。然而,对103名接受他克莫司治疗的肾移植受者研究发现了相反的关联:ABCB1野生型等位基因2677GG和1236CC与神经毒性的最高风险相关[15]。
4.2 外周血单核细胞外周血单核细胞(peripheral blood mononuclear cells,PBMCs)内的CNI浓度直接决定免疫抑制效应。P-gp功能和基因型是PBMCs内浓度的重要决定因素。ABCB1 mRNA的表达与细胞内CsA浓度呈显著负相关[16],而P-gp抑制剂如维拉帕米以剂量依赖性方式增加PBMCs内环孢素的浓度。关于ABCB1基因多态性对他克莫司药效学的研究发现,ABCB1 3435C>T 单核苷酸多态性对肾移植患者T细胞P-gp活性有影响,相比于3435CC基因型患者,ABCB1 3435TT患者T细胞内CNI浓度更高[17]。另有研究表明,ABCB1 1199AA患者P-gp活性降低降低,PBMCs内他克莫司浓度增加[18]。同样,在一项对96名肾移植受者的研究中,多因素分析显示,ABCB1 3435T、1199A和2677T/A等位基因携带者的P-gp活性降低,PBMCs内他克莫司浓度增加[19]。此外,性别也可能影响CNI的细胞分布。在研究非裔美国人和高加索肾移植受者环孢素PK特征和PBMCsABCB1表达的性别差异时,发现女性肾移植患者PBMCs环孢素清除较慢,ABCB1基因表达较低,提示外排活性降低,细胞内药物暴露较多[20]。
Yoon等[21]研究发现CYP3A5基因型可以影响单核细胞内他克莫司的代谢,与CYP3A5*1/*1或CYP3A5*1/*3患者相比,CYP3A5*3/*3患者的他克莫司及其代谢物的AUC0-12和剂量调整后的C0更高。另一项研究结果表明,与年轻患者相比,老年患者的环孢素清除率降低了34%,但淋巴细胞内环孢素与全血环孢素的比率高出44%,该变化与ABCB1基因型和CYP3A5或ABCB1 mRNA水平无关[22]。同等谷浓度水平下,较高的淋巴细胞内CNI浓度可以解释老年患者不易发生急性排斥反应,同时更容易出现免疫过度抑制。
4.3 肝脏一旦从胃肠道吸收,CNI就会经肝代谢和胆汁排泄。环孢素是一种中低肝摄取率药物,而他克莫司是一种低肝摄取率药物,因此,预期肝功能障碍对首过代谢和口服生物利用度的影响是中度的[23]。肝硬化患者的内在肝清除率较低,但由于他们经常伴有贫血和低白蛋白血症,因此可用于肝清除的游离部分会增加。多数研究证实,中至重度的肝功能障碍才会显著影响CNI的处置。在122名骨髓移植受者的队列研究中,与胆红素<20 mg·L-1的患者相比,胆红素为20~99.9 mg·L-1的患者他克莫司清除率降低了20%,而当胆红素>100 mg·L-1时,他克莫司清除率降低49.9%[24]。与对照组相比,轻度肝功能不全(Child-Pugh评分6-7)对他克莫司清除率没有影响。
在肝移植中,移植的肝脏大小也是剂量需求的决定因素。在成人右叶活体肝移植患者中,在术后前两个月,与非小体积移植物受体相比,小体积移植物受体的他克莫司剂量需求明显降低[25]。而环孢素分布体积和清除率高于他克莫司,其血浆浓度与肝脏体积无关。小体积肝移植儿童的他克莫司浓度升高可能与其肝代谢较低相关。这很可能是因为肝脏较低的他克莫司代谢相关。
患有丙型肝炎的肝肾受者的CNI剂量需求较低,这种影响在病毒复制活跃的PCR阳性患者中最为明显,可能的机制是肝细胞中的病毒复制、炎症和轻度肝损伤会干扰药物代谢。
4.4 肾脏肾脏对CNI代谢清除的影响很低。但是,严重的慢性肾脏疾病会至少部分通过尿毒症毒素,炎性细胞因子和甲状旁腺激素的作用影响非肾脏消除药物的处置,这些作用可以抑制或诱导多种肠道和肝酶和转运体[26]。尽管如此,慢性肾脏疾病对CNI处置的净效应似乎有限。在绝大多数移植受者的CNI群体药代动力学研究中,肾功能不是剂量需求的预测因素之一[27]。
肾小管上皮细胞表达P-gp和CYP3A5,但很少表达CYP3A4。CYP3A5和P-gp基因型影响CNI的肾脏代谢[28],从而导致潜在的CNI代谢物在肾内蓄积的毒性。Zheng等[11]研究显示,表达CYP3A5的肾脏对环孢素和他克莫司的尿表观清除率较高,与肾内代谢增加相关联。
5 药物相互作用
通过抑制CYP3A和/或P-gp导致CNI暴露显着增加的药物主要为唑类抗真菌药、钙通道阻滞剂(主要为维拉帕米和地尔硫卓)、HIV蛋白酶抑制剂(尤其是利托那韦)、大环内酯类药物(阿奇霉素除外)等。其中许多药物同时抑制CYP3A和P-gp。唑类抗真菌药是CNI代谢的最强抑制剂之一,但不是基于机制的抑制剂;阿奇霉素是基于机制的抑制剂,但临床经验表明,它对CNI代谢的影响很低。CYP3A和P-gp的主要诱导药物是利福平、抗惊厥药和皮质类固醇。
某些药物相互作用具有潜在的药物经济学或治疗效益。在中国,五酯片或五酯胶囊可以提升他克莫司谷浓度,减少他克莫司剂量,明显降低药物费用。当CNI达到中毒浓度且透析不能有效去除时,苯巴比妥和苯妥英钠可被尝试用于加速CNI的肝清除,尽管此方法的有效性可能会受到诱导肝酶所需较长天数的限制。
CNI的DDI通常在肠屏障水平比在肝水平更为明显。抑制剂和诱导剂对口服生物利用度的影响大于对肝清除率的影响。其原因可能是,与肝细胞相比,口服药物在肠细胞中的浓度要高得多,而肠道中CYP3A的绝对含量低于肝脏,因此基于机制的抑制剂更容易耗尽CYP3A4。该理论的临床意义在于,与静脉联合给药相比,口服联合给药往往对CNI体内暴露产生更大的影响。
与他克莫司相比,环孢素对DDI的敏感性明显降低。研究表明,伊曲康唑的口服联合给药对环孢素谷浓度的影响显著低于他克莫司[29]。CNI和HCV蛋白酶抑制剂波普瑞韦和特拉匹韦[30]的口服联合给药也发现类似的结果[30]。特拉匹韦使他克莫司剂量校正后AUC增加70倍,但环孢素的AUC仅增加了4.3倍。可能的解释是环孢素本身对CYP3A4和P-gp的持续抑制会减弱抑制剂的额外作用。如前所述,抑制剂的最重要作用是增加CNI的生物利用度。如果患者的生物利用度为10%,则在完全抑制CYP3A4和P-gp的情况下,理论上患者生物利用度可以增加10倍至约100%。如果生物利用度为50%(例如由于之前使用了抑制剂),则只能增加2倍。CNI的基线生物利用度与CYP3A4和P-gp活性有关,因此,它是患者对抑制和诱导的易感性的关键因素。
6 结论和展望
随着对CYP3A和P-gp动力学的了解不断加深,逐渐揭开对CNI体内处置的影响因素(例如腹泻、移植术后时间)的机制。CNI全血谷浓度和剂量需求的变化与红细胞压积和血浆蛋白相关的CNI的血液分布的改变关系显著。优化CNI使用的PK模型应该涵盖药物遗传学信息、临床变量,以及可能使用药物探针对CYP3A和P-gp活性进行功能评估。鉴于CNI的治疗窗窄,需要使用PK模型来预测其DDI的影响程度。CYP3A5基因型和CYP3A4基线活性影响个体对DDI的易感性,但目前这些因素尚未纳入CNI相互作用的预测性PK模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