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的四种境界
罗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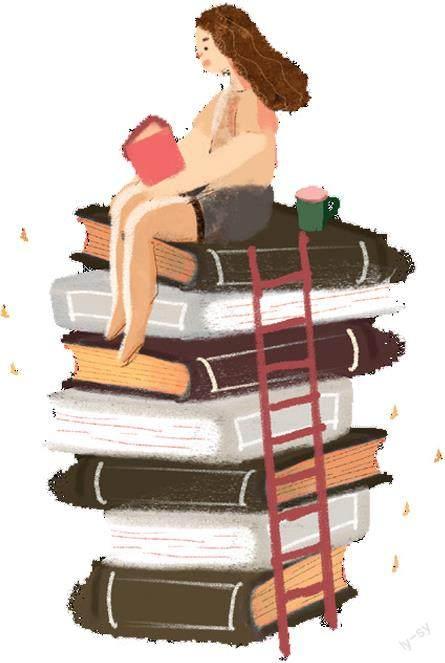
在书籍中逃避世界
我很喜欢《纳尼亚传奇》的作者C.S.路易斯,他小时候就沉迷阅读,自认为书中的世界比外面的世界更真实。路易斯把书籍当作这个世界上最安全、最温暖的避难所,能够保护自己的心智,远离生活的种种凄苦。
但路易斯在书中搭建的美好世界,随着母亲的病逝轰然倒塌。书籍并没有为他提供真正的庇护,当他从想象的世界中走出来,依然要面对这个令人心碎的世界。
如果书籍只是逃避世界的工具,那么,当你走出书房,会发现自己还是那个无能为力的懦弱之辈,这难道不是一种自我欺骗吗?
在书籍中营造世界
也许对完美的追求就是我们作为人类的出厂设置,每当我们遇到不完美,就会激活这种本能,在书籍中想象和营造一种完美。可想象毕竟只是想象,在书籍中获得的完美,在现实世界中依然不完美。
我时常反省自己,我读很多反映战乱、饥荒、贫困的书籍时会流泪,进而获得一种道德上的优越感。我对他人的苦难感同身受,就自我感觉是一个道德高尚的人,但是我付出实实在在的帮助了吗?
远藤周作在《沉默》一书中有一句话很扎心:“罪,并不是一般人所想象的,如盗窃、说谎。所谓罪,是指一个人通过另一个人的人生,却忘了留在那里的雪泥鸿爪。”
如果我们只是通过阅读营造一个假想的世界,却不愿意走入真实的世界,并关心真实世界中他人真实的苦楚,那么,这种自我欺骗式的阅读,其实毫无意义。
在书籍中理解世界
书籍可以拓展作为个体的经验,让我们接轨于人类经验的总和。每个他者都跟自己休戚相关,无论是过去的人、现在的人,还是将来的人,我们都生活在人类总体经验的故事中,都能在他人的故事中获得教诲。
个体虽然是独特的,但是在人类的总经验中,个体又并不独特。我们经常说,每个人的悲喜并不相通,从个体的角度看也许是对的,但是放在人类的总经验中,这又并不準确。
每一部伟大的作品,都会让你更多地认识自己,理解自己。
我很喜欢威廉·戈尔丁的《蝇王》,每次读都能再次洞悉我内心深处的幽暗,觉得自己比想象中更邪恶、更幽暗、更堕落。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书籍会让你深刻地认识到人性的复杂;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会让你反思科技与幸福。总之,每一部伟大的作品都是对你心灵的追问,都在帮助你反思自我、走出偏见,引发你思考那些自以为是的观念是否真的无懈可击。
当我们越多地理解世界,我们也就越多地理解自己。
在书籍中超越世界
如果书籍无法赋予我们对抗黑暗的力量,那么,读书就毫无意义。小说《偷书贼》贯穿着灰色的时代调性,但依然有很多令人温暖和感动之处。我在阅读过程中,时常想如果换作是我,是否拥有汉斯家族的勇气,敢于冒着生命危险去藏匿一个犹太人。
人类总体的经验时常在拷问我们内心,这些书籍能不能帮助我们成为人类历史长河中的高光一刻。虽然这种高光一刻在有些人看来只是一种愚蠢,就像陀思妥耶夫斯基《白痴》中的提醒:“当善良成了白痴,仁爱变得无用,狂暴显示为力量,怯懦装扮成理性,美注定要被践踏和毁灭,恶却愈加肆无忌惮、扰乱一切。”梅什金公爵并没能撼动这张根深蒂固的网,他并不能为这个世界做什么,只能回到自己的净土。但是这个世界真的有净土吗?如果没有净土,我们还要做白痴吗?
这也许就是经院哲学家阿奎那所说的,我们今生活着的唯一意义,就是超越今生。
大浪淘沙//摘自《法治的细节》,云南人民出版社|果麦文化出品,本刊有删节,摄图网/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