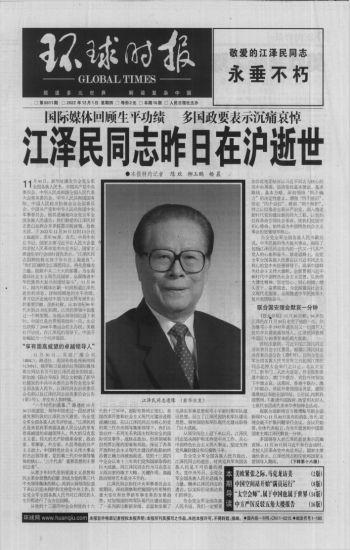美国对华战略 没考虑盟友
美国“外交学者”网站12月19日文章,原题:美国的盟友是否无法在涉华问题上保持“一致”? 美国总统拜登上任时承诺,他的政府将“(开始)改进合作的习惯,重建过去几年来因忽视和在我看来的滥用而萎缩的民主同盟。”
拜登指的是特朗普的四年总统任期,后者将盟友贬为搭便车者和制裁目标。对盟国政府来说,听到一位美国总统这么说,会松一口气。但到头来,与“志同道合”国家合作只是拜登政府从“实力地位”出发来对付中国的战略的关键部分。这将成为美国政府对华战略三要素“投资、结盟、竞争”中的第二个要点。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今年5月阐述该战略的讲话中坚称,拜登政府在涉华问题上正与欧洲和印太地区的盟友和伙伴密切合作。
然而,正是在这个领域,拜登政府屡,遭诟病。盟友尤其质疑美国的产业政策和出口管制。引发争议的是两项被美国视为重大国内成就的立法:《2022芯片与科学法案》和《通胀削减法案》(IRA),前者提供2800亿美元资金以提升美国在半导体行业中的竞争力,后者为美国清洁能源行业尤其是电动汽车产业提供巨额补贴。
在许多美国盟国政府看来,问题在于这些法案中的保护主义倾向。在韩国,IRA引发对韩国电动汽车被排除在美国市场之外的担忧,一位韩国官员甚至称之为“背叛”。法国总统马克龙本月访美时也发出严厉警告,称拜登政府正在作出“将分裂西方的选择”。在试图限制任何使用美国技术的公司向中国出口技术方面,拜登政府也面临阻力。严格管控或将危及美国多个关键伙伴的经济健康。
所有这些例子的共同之处在于,除纯粹的“马后炮”外,美国的盟友都认为其关切没被美方考虑进去。而这在很大程度上给这些国家带来意想不到的负面后果。拜登已向法韩同行承诺将解决其担忧,但鉴于相关法律已获通过,尚不清楚他如何做到这一点。
“投资、结盟、竞争”中的“投资”部分被视为聚焦于国内的立法范畴,拜登政府可能压根没想到要就此进行广泛磋商。然而,“中国挑战”不仅跨越传统的国家安全领域,还涉及“经济安全”新领域,其复杂性意味着在一个领域对中国作出任何反应都有可能对其他国家产生连锁反应。一个在上任时曾夸口要与合作伙伴密切磋商的美国政府,秃其需要了解外国政府将如何看待其在国内的所作所为。(作者香农•蒂耶兹,王会聪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