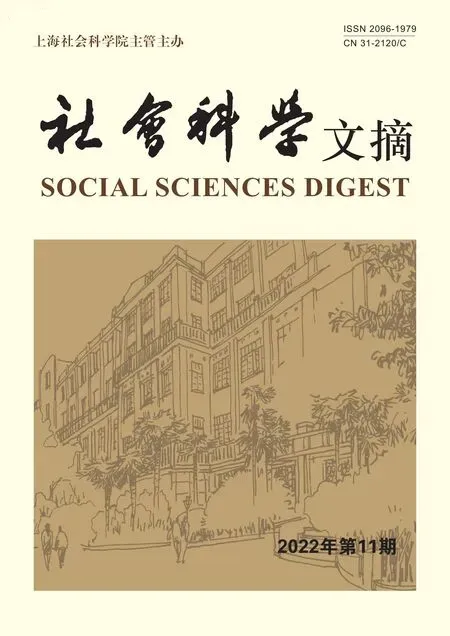效度与路径:重审中国电影理论的民族化问题
文/谢建华
知识穿越历史的纵深和地理的藩篱,所发生的“变异”现象,在各个学科领域比比皆是。需要追问的是:两个相近的概念究竟应该被视为哪个民族的精神遗产?这既涉及我们对理论生产“革命”还是“修正”的界定,也关乎民族化可否作为理论创新正确方向的判断。
民族化作为方法论选项
每个学科都有自己的方法论,其理论谱系的形成常常经历漫长的模仿、借鉴和矫正过程,涵盖概念的创制、方法的演绎和框架的建构诸要素,是一个关于话语、思维和体系演变的非线性叙事。电影理论研究以本体论为核心,宗旨是引导、扩展我们对电影本性的理解,但这种理解受制于电影的媒介技术状况和地缘政治语境,是“媒介特异性”和“文化特异性”两种核心冲动综合推动的结果。
“媒介特异性”是电影理论研究的起点。电影史无可避免地涉及电影与其他艺术(媒介)的竞争性定位,通过保存优势、淘汰劣势的自然演化机制,在历史进化中顺时应势,逐渐形成自己的质性特征。文化特异性致力于解释电影的多样性和特殊性问题,是艺术创作对地缘政治和民族思维差异的自然反应。虽然电影产业是全球性的,但不同种族具有不同的思维,不同的政治又规定了不同的艺术性质,电影与特定文化和民族的相遇会形成不同的“艺术症状”,电影理论的生产因而必须同时质疑艺术和工业。电影在知识和政治层面存在持续张力,媒介特性总是和各种各样的文化政治问题掺杂在一起。电影进化是两条线竞争演绎的结果,电影理论生产就是本体论与语境论的双重变奏。
我们据此可以将电影理论生产的路径区分为两种:一是典范的转移,二是文化的旅行。典范是一个时期内某一知识社群解答问题的模型,它提供了一个“可被重复套用的范例”,“而此一范例原则上能用同一类型中的任何个例充任”。作为“前典范”阶段,早期电影理论诸说竞陈,用以描绘和解释电影的概念各不相同,反映了人们认识电影的不同方式和满足工具期待的不同思路。因为研究者在媒介特异性上套用了新架构,对电影的认识就会焕然一新。这意味着,任何新理论并不改变研究对象本身,仅涉及典范与对象、典范与典范的持续比较、转移过程。电影理论的创新是重构性的,任何新理论都是破坏传统、转移焦点的结果。
旅行是理论的宿命,也是知识生产的驱动力。思想跨越时间、空间和语言的障碍,通过流通、置换和杂交产生变量,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W.Said)称之为“理论的旅行”:“就像人和批评流派一样,思想和理论也会发生从一个人到另一个人,从一种情况到另一种情况,从一个时期到另一个时期的旅行。”思想的全球旅行现象,本质是人在游牧过程中,因应异质性的政治、社会、历史、价值观和人类经验压力,对相同问题的创造性诠释。这意味着:流放是理论的通常状态,译介是知识生产的基本方式。在一个政治、经济、文化关系依赖加剧的世界中,跨文化置换和转移已成为知识再生产的重要机制。没有任何原始的概念,只有“政治和文化重新语境化后的连续重述过程”,“意义的传递获得了一种政治和文化形式”。
这意味着:不存在独属于一个民族的原创知识,重组和类比充当了新理论的“助产士”,理论创新仅是对既有知识的重新组合,或在新领域中进行类比关联的结果。重组意味着选择了新的向量,确立了新的典范,生成了新的系统。
因此,跨学科流动与全球疆域的旅行在电影理论研究中不可避免,这个过程也是理论拓展论域边界、再民族化的历程。因此,在中国电影理论中发现安德烈·巴赞、吉尔·德勒兹、吉奥乔·阿甘本、雅克·朗西埃,如同在中国电影文本中找到好莱坞、长镜头和现实主义,这并不令人意外。面对新的技术条件、观众期望和政治经济规则施加的修改压力,旧理论通过调适阈值、重新工具化,得以催化出可匹配条件的新理论。这就如同在文学理论研究领域,中国人“用先秦名学说符号学,用陆王心学阐发现象学,用禅宗解释精神分析,用毛宗岗金圣叹小说点评支持叙述学”,可以说是对西方文论进行了卓有成效的“中国化改造”。
民族化理论的风险与挑战
确立民族化为电影理论研究的方向,必须明确这一选择面临的风险与挑战。无视创作实践和理论生产面对的复杂媒体、社会、政治语境,一味将民族主义作单向度的简化和提纯,不仅会使民族化沦为理想主义的空洞辞藻,也会误导创作实践的未来方向。
首先,艺术的本性会稀释民族化的纯度。虽然艺术的界定仍无定论,但对模式、共性、平庸的抵抗和对一切具有辨识性的元素的消解,肯定是所有艺术品的普遍特征。一方面,艺术家不断“向内心寻求创造力”,经常被描绘为各种各样的离经叛道者,这否定了其“所属国家的文化象征性”;另一方面,为了不威胁其与赞助商、批评家、观众和特定市场的关系,多数艺术家时常宣称自己的灵感源于任何国家、任何时期的艺术家,而非仅仅来自本国传统,“这进一步稀释了他们对特定国家的认同感”。散见于各种访谈、传记和文本中的“证据”表明:中国电影的“民族化历程”,可能同时是一张全球电影交流、互动的“路线图”。
其次,跨国主义会抵消民族化的效力。无论作为媒介还是艺术,电影的创作、传播都与全球社会进程、地缘政治变动息息相关。当流动的旅程穿越固化的疆域,移民、离散、全球普世、游牧主义、文化互联概念日渐凸显,解域和再疆域化进程相互交织,全球化挑战民族国家范式,“民族主义的阐释模式会面临贬值的危险”。是否还存在一个稳定的本土文化体系?今天比比皆是的各种“文化混血”现象和“元素杂糅”产品,一再提示我们:同化(Assimilation)和异化(Differentiation)、均质化(Homogenization)和混杂化(Hybridization)彼此难分,有多少对形式统一的追求,就有多少对元素混合的迷恋。
跨国主义造成艺术创作上的两重后果。一是趋同逻辑。万物互联、瞬息千里,媒体全球化和技术具身化缩短了人类的时空距离,进而缩小了不同国家的文化差异。二是混合逻辑。资本为了通过流动获得最大利润,艺术家为了通过合作获得最多受众,开始尝试与更广泛的地缘政治力量合作。民族国家致力实施各种形式的“电影走出去”战略,包括:导演的跨国移动,合拍合制生产中的国际化阵容,全球大同主义的主题框架,高度消费主义的视觉地理,对跨国翻拍和跨文化挪用的无节制开发,这些策略强化了单体叙事融合民族国家和全球跨境的能力,但也冲击了民族电影的美好愿景。民族主义的行销和商业主义的民族化互为表里,很难界定一部电影在哪些方面提供了“民族性”特征,很难断言离散族群的创作是否会抹杀民族色彩,也很难说跨国电影的出品策略能否令民族主义流离失所。
最后,理论的衰败阻碍了民族化的努力。理论的目的在于寻求对现象的本质阐释和世界的多元理解,理论建构不是为了达成共识,而是将我们从具象和经验中解放出来。但近年来历史主义的兴起和经验主义的转向,加上出版的商业化,致使理论的交换价值下降,理论的面世举步维艰。越来越趋向具体化的理论研究,不管是强调可靠数据,热衷实用、实证主义路线,还是以描述、运用代替思想原创,逐渐成为一种专业化、技术性的知识生产。在这样的语境下,以方法论的民族主义为中心的理论建构可能会引发更多争议。
理论民族化的可能路径
在直面上述挑战的基础上,承认民族性仍然在中国电影创作中发挥巨大影响,民族化仍然是中国电影理论建构的重要动力,我们的论述才能方法正义。因为严格来说,所有的研究方法都是不可靠的,一切结论都隐含反结论。就像关于侯孝贤电影“民族性”的争议,其纷争根源在于,把民族性看作一种静止、单一的现实,还是要考虑其生成的复杂语境?
我们有必要回到概念本身,首先考察民族主义作为思想源头,究竟为民族化提供了何种方法范式。作为一种建构认同、争取独立、建立国家的思想运动,民族主义通过两个领域的努力,使其成为能够动员社会、凝聚思想的策略和意识形态:从历史来说,民族主义之所以依赖历史叙事,是因为任何民族国家的存在都需要“一个可被描述的过去”。历史不是对中性信息的“无菌叙述”,其对事实的选择首先基于本质/非本质的甄选判断。民族主义要想提供民族国家的图像、追寻身份认同的基因,必须在历史重述中建立“民族身份的文化目标”,从满足民族主义的未来想象出发,解释历史发展的动因和内在逻辑。因此,“民族主义在神话的创造和身份认同的追寻中离不开考古学”。从理论来说,民族性是一元的、稳定的、排他性的,还是多元的、发展的、融合性的?文化、语言、种族、政治如何参与民族主义的建构?跨文化、全球化如何影响民族心理共性?电影如何处理民族和国家议题,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探索和建构了民族的概念?民族性可否解读为一种“文本间的症状”?总之,民族主义不是一个静态的概念,它涵盖了不同的历史经验和政治愿景,是在文本集群中建立的统一机制、结构力场和连贯话语。当民族化被视为电影理论的方法论时,意味着我们不仅要对历史和文本做选择和重述,还要建立典范,提炼出一种共通的修辞、模型与方法。
这决定了知识考古和文本发掘是民族化理论建构的必经之路。我们要么重返历史、重读经典,要么重新挖掘、考释文本,唤醒其中埋藏的民族话语和理论议题。知识考古是民族化理论建构的根基。唯有将理论历史化,建立起理论的时间维度,才能使民族化论述具有一个可回溯的源流。这个工作可以从两个方面展开:一是对古典(经典)理论的批判性、选择性重释,在民族主义的“力场”中重新安置它们,以便理出一条民族化的理论谱系。二是着眼于理论的“旅行”性,在不泛化民族性的前提下,进行电影理论与其他文艺理论、中国电影理论和外国电影理论的对话比较,将古典理论的“同化”与外国理论的“调和”结合起来。如果我们将视野扩展至中国古典文论、诗论、画论、曲论、剧论、乐论、舞论、书论等,就会发现:它们和电影领域同声相应,在民族化论述上多有精彩的互动共鸣。这种平行关联思维,有助于从整体性把握中国电影理论的观念。民族电影的可识别性,不仅体现在其与另一种电影的差异性比较,更体现在其与本民族文化艺术传统的联系。与此同时,与外国电影理论的横向联结也是必要的,兼具跨界(学科)与跨区(文化)的追问,有助于理解民族性与国际性之间的合理张力,进而明确:中国电影理论有何“中国性”?如何定位“中国性”?民族性又是如何在“以旧化新”中完成的?
发掘文本是民族化理论建构的另一项重要工作。民族是通过各式各样的故事得以镌刻和流布的,换句话说,每一个电影文本可能都有一个隐性的民族性假设,这体现在特定的主题导向、类型定式和形式系统的民族化呈现上。与笼统归纳中国电影民族性特质相比,勘查单个影人如何继承传统,或特定文本如何体现中国性,这种小处着眼的做法更具包容性,也更理性。例如:埃克托尔·罗德里格斯(Héctor Rodriguez)从京剧乐谱和京剧演员的使用,动作场面的重排,关汉卿、李白等古典诗词曲赋的吟诵,古典书法、卷轴形式的利用,传统绘画构图的模仿,以及静物、山水空镜中的抒情味道和佛味禅意,推导出胡金铨电影与中国传统错综复杂的关系网络,既关注文化、经济、时局和个人因素对导演中国观念的中介作用,又注意到其对电影特性的挪用。在此基础上,论文的立场显得更谦逊,结论也没那么武断。
多年来,研究者有意识地将文本、历史和理论结合起来,在重返影史、重释文本方面产出甚丰。在进行中国电影“民族化理论”建构中,如何避免“概念掠夺”和“工具投机”,这些成果提供了某些重要参考。
放眼全球,以民族化为方向的国家电影理论鲜有成功的范例。立足于历史和现实,我们仍有必要认识到民族化理论存在的两个误区:首先,预设一致性的研究思维,这包括稳定的制度安排、静态的社会流动和简化的民族国家概念,而没有将创作者的多样性、观众意图的多元性以及政策、创作、市场在民族化进程中的复杂互动置于研究的中心,使得一些研究结论呈现出明显的预设立场、论证苍白的问题。其次,不能克服本质主义和群体主义的取向,研究方法相对窄化为宏大的定性路线,摒弃了实证、比较、量化等方法后,无法建立有效的自我反思程序,结论难免僵化。在这种情况下,电影理论最终不是用民族化取代跨国化,就是用商业替代国家。
结语
在一个全球网络和民族话语交互施力的今天,传统既不会骤然消失,大同也不会即刻到来,民族主义夹杂于各种过程中间的现况决定了“去民族化”和“唯民族化”都是不可能的,同化和融合也非绝对一律的方法选项。中国电影理论的民族化建构应该以总结中国电影多层次的“民族心理地图”为中心,充分考虑民族化的异质性和多元性,民族、国家和艺术生产之间的复杂张力,因为它们都是影响研究结论的重要变量。我们既要同化先典,持续对历史理论化;也要调和外来,开展与其他学科、其他国家的学术对话,在一个更广的视野内理解中国电影的话语逻辑:当民族主义在定义文化身份、输出国家战略的时候,如何面对全球资本和本土价值的角力,如何配置世界语言和地方叙事,如何生产既满足民族主义期待,又符合当下审美趣味的国家形象?这些问题唯有随着民族化理论的持续深入,才可能有更清晰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