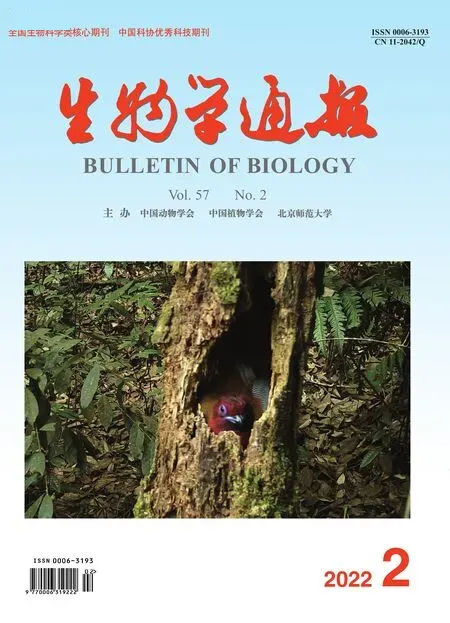肠道菌群影响因素的研究进展∗
桓宗锦 陈红卫 赵 波 刘选珍 毛 杰
[成都动物园(成都市野生动物研究所) 四川成都 610000]
肠道菌群是动物体内最复杂、最庞大的微生态系统。肠道菌群与宿主、菌群群落之间形成了相互制约、相互依存的动态平衡关系[1]。肠道菌群在宿主营养代谢、免疫、环境适应及行为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2]。由于肠道菌群与宿主机体健康的关系密切,近年来生物医学领域中肠道菌群的研究发展迅速。肠道菌群在宿主慢性病的早期诊断、干预和治疗方面也存在巨大潜力[3]。肠道菌群反映了消化生理、食物、宿主遗传等因素的综合影响[4]。随着研究的深入,发现越来越多的因素可影响肠道菌群。一些研究已估测了宿主系统发育和遗传、食物及环境等因素对哺乳动物种间和种内肠道菌群多样性的影响。
1 宿主遗传因素对肠道菌群的影响
宿主物种是决定肠道菌群组成最重要的因素。哺乳动物宿主的系统发育影响肠道菌群的组成,在新近分化的哺乳动物中表现更为强烈[5]。宿主肠道中的微生物是动物消化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与宿主之间的相互作用有着悠久的进化史。宿主通过促进有益菌群向子代的迁移和利用肠上皮黏液屏障识别菌群的表面分子将菌群进行隔离,并限制菌群的出入调控菌群[6]。宿主亲缘关系可指示肠道菌群结构的相似性,宿主遗传距离是肠道微生物组成的一个强有力的预测因子。在对共享同一个栖息地的田鼠属(Microtus)、姬鼠属(Apodemus)和鼩鼠青属(Sorex)的研究显示,宿主遗传差异对肠道微生物的影响占主导地位,宿主物种是决定肠道微生物区系组成的最重要因素[7]。分析黑白疣猴(Colubusguereza)、红疣猴(Piliocolobus tephrosceles)和红长尾猴(Cercopithecus ascanius)的粪便样本,发现同一物种的肠道菌群具有更高的相似性[8]。在对马达加斯加6种哺乳动物的肠道菌群研究中,同时考虑食物、基因和生态因素,发现肠道菌群组成受到亲缘关系的强烈影响[4]。Amato等[9]对18种非人灵长类动物的肠道菌群进行了研究,发现虽然食性(食叶和非食叶)可影响微生物群落结构,但宿主的进化关系才是决定性因素。同时,宏基因组测序结果也表明,菌群的功能也受到宿主系统发育关系的影响。
宿主基因影响肠道微生物群落的组成。在人和小鼠模型的研究中都清晰表明,特定种类的肠道微生物丰度,一定程度上受宿主基因型的调控[10]。在野生家鼠研究中也发现了20个与肠道菌群相关的基因[11]。在分析英国双胞胎的肠道菌群中发现可遗传的细菌类群,这些类群与宿主的代谢和嗅觉相关基因有关[12]。宿主基因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肠道微生物群落的组成,Christensenel‐laceae科、Methanobrevibacter属和Faecalibacterium属等几种常见肠道微生物是可遗传的[13]。这些研究证明宿主遗传背景是决定肠道微生物组成的重要因素。
2 食物因素对肠道菌群的影响
食物是影响动物肠道菌群多样性最直接的因素[14]。食物是微生物发酵的底物,驱动微生物群落的组成和代谢[15],是肠道菌群的直接影响因素,也是动物及其肠道菌群协同进化的关键因素[16-17]。因为物种在适应一个特定的食性过程中,肠道菌群通过为宿主提供关键的代谢通路而发挥重要的作用,宿主也为肠道菌群提供了进化的机会,即宿主肠道环境与食性的相互适应,促进宿主主导的双方多样化和协同进化。研究发现,普氏菌属(Prevotella)和毛螺菌属(Lachnospira)与植食性呈正相关,而链球菌属(Streptococcus)与肉食性呈正相关,且与植食性呈负相关。长期摄食蛋白质和动物脂肪的人群肠道菌群以拟杆菌科(Bacteroidaceae)为主。人体肠道中优势菌群与食物中的蛋白质、糖类和脂肪的比例有关[18]。
2.1 碳水化合物与肠道菌群 人每天摄入的碳水化合物中,约有40 g逃脱了宿主酶的消化而到达结肠[19],主要有抗性淀粉、非淀粉多糖和寡糖,以及一些双糖和单糖。微生物可在盲肠和结肠内发酵碳水化合物产生短链脂肪酸,包括乙酸、丙酸和丁酸等,这些发酵产物的产生也往往会降低结肠的pH。这些弱酸会影响微生物的组成,从而直接影响宿主的健康。有研究表明,在长达4周的时间内,改变碳水化合物的种类或数量,对成人志愿者肠道微生物及其代谢产物的组成具有深刻而迅速的影响[20]。比较生活在非洲农村和意大利城市儿童肠道菌群,发现2组儿童的菌群分别聚类。非洲儿童肠道拟杆菌门(Bacteroidetes)中的优势菌是Prevotella属和Xylanibactern属,这些细菌擅长发酵木聚糖和植物纤维[21]。
2.2 蛋白质与肠道菌群 小肠中未完全消化的蛋白质和肽被大肠内的细菌充分发酵利用,同时产生吲哚类、胺类和硫化氢等代谢物[22]。共生细菌可通过食物和内源性蛋白质为宿主提供氨基酸。肽和氨基酸也可被糖化细菌和非糖化细菌作为碳、氮和能量的来源[21]。从人类粪便中,已鉴定出降解蛋白质的细菌,主要包括产气荚膜杆菌(Clostridium perfringens)、拟杆菌属(尤其是Bactevoides fragilis)、丙酸杆菌属(Propionibacterium)、芽孢杆菌属(Bacillus)、链球菌属(Streptococcus)和葡萄球菌属(Staphylococcus)[23]。肠道菌群会显著地受到摄入蛋白质的组成和含量的影响。摄入高蛋白质食物会增加肠道中代谢蛋白质的微生物和致病菌的数量。而且动物蛋白和植物蛋白对肠道菌群的影响也不同。研究发现,大豆产品促进双歧杆菌(Bifidobacterium)和乳杆菌(Lactobacillus)的增加[24],但摄入糖化牛血清白蛋白却显著降低了肠道中双歧杆菌的含量[25]。
2.3 脂肪与肠道菌群 肠道菌群以多种途径参与能量和脂质代谢。摄入过多的富含饱和脂肪酸的脂肪会增加肠道中变形菌门(Proteobacteria)、厚壁菌门(Firmicutes)和梭菌属(Clostridium)等,从而改变代谢过程中胆汁酸等信号分子,增加了宿主肠道的通透性和炎症的发生[26]。研究表明,高脂肪低碳水化合物食物的摄入会显著降低肠道中双歧杆菌和短链脂肪酸(例如,丁酸)的含量[20]。Guo等[27]研究也发现高脂肪的摄入会改变肠道菌群结构,引起肠道炎症。高脂肪摄食可诱导肠道内产内毒素的微生物丰度增加,减少保护肠黏膜屏障的双歧杆菌的丰度,从而促进了氧化应激,使肠道通透性增加。长期摄入单不饱和脂肪酸能降低肠道菌群数量,其中,双歧杆菌含量明显降低。ω-3多不饱和脂肪酸能增加上皮细胞的抵抗力、改善上皮细胞的完整性[28]。Simoes等[29]研究发现,长时间摄入ω-3多不饱和脂肪酸,能提高肠道中乳酸菌的含量。
2.4 食物烹饪方式的影响 高温会改变食物的理化性质,从而影响肠道菌群。烹饪通过淀粉糊化提高碳水化合物在小肠的消化率,减少到达结肠的数量,而结肠是微生物较多的地方,从而影响结肠发酵碳水化合物的肠道细菌数量。之前已有研究显示,摄入生的和熟的植物性食物,对肠道菌群的塑造作用存在显著差异[30]。食用含淀粉的块茎类食物(例如,土豆)时,与生食相比,熟食的肠道菌群α多样性降低,厚壁菌门的比例减少,而拟杆菌门的比例增加。研究发现,烹饪或不烹饪植物性食物对人类肠道微生物区系有显著差异[30]。
3 高海拔环境对肠道菌群的影响
最近的研究显示,肠道菌群的多样性组成对宿主的环境适应起到了积极的作用[31]。环境因素中,高海拔地区是一种极端的环境,热能和氧气可用性的降低对生物体构成极大挑战。最近,高海拔环境对哺乳动物肠道菌群的影响受到关注,研究表明,哺乳动物的肠道微生物随着海拔高度而变化,例如,啮齿动物、反刍动物和人类[11]。对生活在高海拔地区和低海拔地区的反刍动物进行对比研究发现,生活在高海拔地区的反刍动物肠道菌群结构与在低海拔相比存在显著差异[31]。在高海拔环境中的哺乳动物含有多种可产生短链脂肪酸的微生物类群。这种生产短链脂肪酸的微生物数量的增加与食物无关,可促进高海拔群体更有效地摄入能量,从而有利于宿主应对高海拔的低温环境。最近已证明,微生物来源的短链脂肪酸可影响宿主血压调节系统[32],因此,短链脂肪酸生产者的增加可能有助于高海拔环境的血压调节。由此推测,肠道微生物可帮助哺乳动物应对高海拔的极端条件。
4 总结
肠道菌群受多种因素,包括宿主遗传、食物、环境等因素的综合影响。随着研究的深入,越来越多的因素被证明可影响肠道菌群。但还需更进一步的研究,以精确地揭示动物肠道菌群多样性变化的驱动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