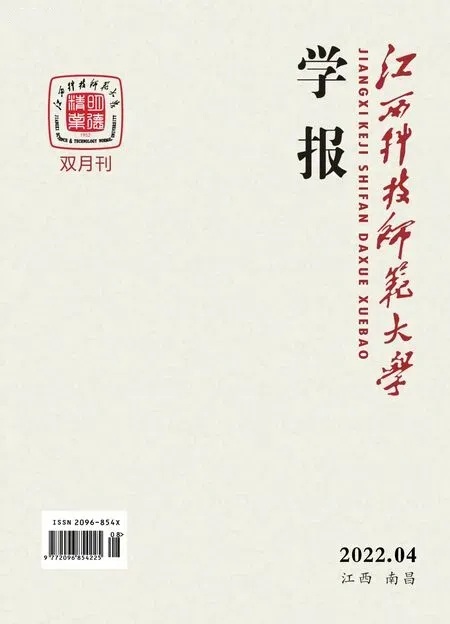重大革命史叙事与记忆建构研究视域的拓展
——以《布尔塞维克》《申报》《上海民国日报》对南昌起义的报道为例
阙伟康,叶 桉
(江西科技师范大学,江西南昌 330038)
革命史是20 世纪中国社会的重要内容,革命史研究亦是我们理解近代中国社会变迁的重要场域。随着新社会史、新文化史等史学新动向的出现,新革命史应运而生,成为革命史研究的新范式,在探索革命史的产生发展的复杂历程进行了许多有益的探索。学者们倡导革命史研究应该回顾史学属性,回顾常识、常情和常理加强对史料分析,探讨符合革命实际的历史问题[1],同时强调应该打破学科区隔,不断推动中国史学走向未来[2]。由此可以看出,为了进一步推动革命史研究,应该走向开放、多元融合,善于借鉴多学科的研究方法,在史料中深耕细作,重回历史现场,注重概念史、记忆史学和新文化史的研究。
报刊是通过利用纸张把文字资料传播于大众的一种工具,起到宣传、教育、阐释等作用,近代以来,作为刊载新闻和时事评论的定期向公众发行的出版物,对关注近代社会文化发展的特殊性,注重考察历史中的文化因素,广泛借鉴人类学、社会学、政治学等多学科的研究方法,继而不断构建革命史研究的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和学科体系,促进重大革命史事件的叙事与记忆建构。南昌起义作为事关国共两党和中华民族前途命运的重大事件,《布尔塞维克》《申报》《上海民国日报》各自从不同立场、观点和方法对南昌起义作了报道,对其进行比较研究,以利阐明不同立场的媒体在报道中有何不同,又是基于什么立场进行叙事和总结,试图更加深入认识南昌起义的历史地位与影响,不断丰富南昌起义的研究,进而从新的论域中认识中共重大革命史叙事和记忆的建构。
《布尔塞维克》:中国共产党党刊视野下的南昌起义
1927 年10 月,大革命失败后,中共中央决定创办新的机关刊物取代已经停刊的《向导》,《布尔塞维克》应运而生,成为中国共产党宣传的重要“喉舌”,主要内容包括中国共产党的政策理论和革命事件,也包括中共对革命的探索,见证了中国共产党从幼稚走向成熟的历史过程,为我们揭示中共早期的革命道路、历史书写和理论探索提供了重要的窗口[3]。周刊《布尔塞维克》由瞿秋白任编委会主任,罗亦农、邓中夏、尹超麟、王若飞等人为编委会委员[4]。1927 年10 月24 日至1932 年7 月间,《布尔塞维克》发表了大量的中共中央机关理论文章,比较深刻地总结和反思中国共产党关于国民革命的经验与教训,在探索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向何处去等重大问题上肯定了中共“八七会议”后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
《布尔塞维克》“发刊词”中强调中国革命已经到了“激烈万分”的时期,中国革命斗争的营垒分为买办军阀豪绅资产阶级的反革命营垒和工农贫民的革命营垒,国民党已经变成了“反革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解放中国,要坚持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才能彻底完成中国革命的任务[5]。《布尔塞维克》在第一期就发表了毛达的文章《八一革命之意义与叶贺军队之失败》,强调南昌起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其意义是“历史上伟大的革命事件,是中国革命史上最光荣的一页”,武装暴动是革命的阶级斗争最高的形式;分析了南昌暴动的主客观条件,“八一革命是适合于客观情形和暴动时机的”;强调了南昌起义的转变意义,就是要实行彻底革命的无产阶级的布尔塞维克的政策,“八一革命的南昌暴动是中国革命发展中一个极大的转变关键,尤其是中国共产党政治行动上的一个极大的转变关键”,“这是中国第一次有大规模劳动民众武装暴动意义的大事件,这一暴动不但反对军阀和地主,并且反对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南昌暴动是中国工农革命的第一声,开启了布尔塞维克道路的新纪元。”[6]这与时隔90 年之后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 周年大会上对南昌起义的评价一脉相承、同条共贯:“南昌城头一声枪响,拉开了我们党武装反抗国民党发动派的大幕。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伟大事件,是中国革命史上的一个伟大事件,也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的一个伟大事件”[7]。
中国共产党是由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底蕴的先进政党,无论是党的历史决议,还是党发表的宣言、通告、新闻等,都证明中共极其善于总结自己的历史和得出经验与教训,为促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注入崭新的生机与活力。《布尔塞维克》确定的南昌起义的历史基调代表着中共早期对重大革命史叙事与记忆建构的重大突破,即以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不吝笔墨地赞扬南昌起义是适于“客观情形的”革命壮举,“在革命史上,从没有劳动民众的暴动是预先便绝有胜利保证的事”[6],强调革命的政党不会因暴动失败而不采取符合客观条件的暴动,表明中共在大革命失败后面临的“要不要继续革命”问题的抉择时,以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和进行土地革命作为正确的回答:是“中国革命史上最光荣的一页”——武装暴动是革命的阶级斗争的最高形式,“工人阶级的政党便有组织这种暴动领导这种暴动的天职。……答复这种反革命的白色恐怖,就只有并且应当是工农民众的武装暴动。中国共产党就尽了自己的革命责任,担负起组织这种武装暴动的任务”[6];是开启“布尔塞维克道路的新纪元”,强调“南昌暴动及南征广东始终是我们党政治行动中最光荣最英勇的历史,反动的新旧军阀能够偶然在军事上战胜叶贺的军队,但是他们决不能战胜这几千万的农民”[6]此外,《布尔塞维克》除了关注南昌起义本身的发生发展过程外,还尤其关注南昌起义对革命形势发展的意义,报道了南昌起义之后江西工农红军的发展过程。如瞿秋白在《布尔塞维克》第十期有《南昌暴动后的江西农民运动》,指出虽然南昌起义最后失败了,但是南昌起义极大地激发了民众,对于广大江西农民来说是一帖“兴奋剂”[8]。除了关注南昌起义对工农武装暴动的意义之外,《布尔塞维克》还关注起义后革命的发展形势,指出国民大革命失败之后要推翻一切反动的国民党政权及一切军阀,进一步发动工农贫民暴动,建立苏维埃[9]。在第二期中,《布尔塞维克》专门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中国共产党反对军阀战争宣言》,要反对一切军阀的战争,“中国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是一切劳动民众的领袖。”[10]瞿秋白在《军阀混战的中国与工人阶级》中强调中国的出路只能是通过激烈的工人斗争,开展武装暴动,推翻新旧军阀的统治,建立真正的苏维埃的中国,叶贺的南昌暴动虽然失败,但是轰轰烈烈的农民暴动、工人运动在如火如荼地进行中,要继续战斗到底,反对军阀混战[11]。在第三期中,强调“没有革命的理论,便不能有革命的运动”,要复活中国的革命运动,推翻国民党反动派,就得有革命的理论,揭露国民党的反动统治,阐述中国革命与共产党的任务。在后面的几期中,《布尔塞维克》反复强调要反对一切军阀战争,积极探索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任务,不断推动革命运动的前进[12]。在第六期中刊登的《中国现状与共产党的任务决议案》特别强调,南昌起义及南征广东的军队虽然失败于潮汕,但是轰轰烈烈的农民暴动说明了中国共产党革命策略的正确[13]。
综上所述,《布尔塞维克》对南昌起义的报道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在主动建构自己的革命史时,通过话语、文本、叙事等逐渐以正确的历史观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方法强调南昌起义的伟大历史意义,关注南昌起义对党的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土地革命政策以及工农红军建设等事关革命成败的重要问题,从四个方面为中国共产党解决了敢不敢继续革命的问题之后,如何继续革命作出了有益的探索,即一是重振革命信心,宣传马克思主义,强调要用革命的理论指导革命运动,推动中国革命继续向前走;二是积极宣传南昌起义之后的工农运动,强调中国共产党对工农运动的正确领导是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坚强保证;三是进一步揭露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强调要反对一切军阀战争,建立工农苏维埃政府,既要继续反对旧军阀,也要反对国民党新军阀;四是进一步强调武装暴动的重要性,要求用武装暴动争取革命的胜利,不断推动革命运动的胜利发展。
上海《申报》:社会公共舆论视域下的南昌起义
上海《申报》是十九世纪晚期至二十世纪中期极具影响力的中文日报,创办于1872 年4 月30 日,历经了清朝晚期同治、光绪、宣统三朝,以及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北伐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等历史阶段和近代以来重大历史事件,是中国现代报纸开端的标志,见证和记录封建社会至半殖民半封建社会曲折复杂的发展历程,被誉为中国近现代史的“百科全书”。作为中国近代民族资产阶级创办的报纸,一方面,欲“将天下可传之事,通播天下”,以发表政论文章、重视新闻的真实性和擅长副刊聚集读者,成为当时体现新闻自由的典范;另一方面拘于阶级和时代的局限,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乃至官僚资产阶级属性与特点,亦如影随形。特别是史量才接任总经理之后,对报纸进行了大量的革新,以“言论自由,不偏不倚,为民喉舌”为标榜,使其影响力大增[14]。有舆论认为,《申报》有时好像是变成中国报纸的“公名”了[15],足可见《申报》的影响力和知名度,这里既与《申报》自身经营有关,也与当时民众对报刊的认识有很大关系。
《申报》在民众和社会舆论中的地位极高的原因,是缘于所谓的无党派关系、经济独立、企业化经营,尤其是关注社会热点,关心时局。因而也对南昌起义的发生发展过程,作为一个影响国共两党局势和中国社会的重要历史事件进行报道。《申报》关于南昌起义的第一篇报道是“各社电讯:南浔铁路发生战事”,转述中央社、东方社和国闻社的电讯,说明南浔铁路附近发生战事[16]。在同日,还有两篇报道值得注意,“南浔铁路变乱之内幕”引述中央社的电讯,“浔赣间纷扰之现状”引述《文汇报》的信息,说明还很难知道实际情况。在8 月7日,“各社电讯:迷离惝恍之赣局”引述了东方社、电通社、国闻社、路透社的信息说明国民党各派系“围剿”南昌起义的情况,南昌起义的共产党军队显出孤立无援之势[17]。8 月8 日,《申报》又以“赣局大紊乱”引述南京、汉口两地的电讯,说明南浔铁路战事激烈,商业萧条,张发奎部进剿叶贺[18]。此外,还报道了武汉的政治和军事情况[19]。8 月9 日,《申报》又积极关注江西省及南昌起义之后各方势力的反应,“赣省战云弥漫”强调九江战事激烈,“汪唐表示反共”、“闽粤军政要讯”报道各方势力对南昌起义的态度与立场,“各社电讯:贺叶宣言共产”引述电通社的信息报道南昌起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起义[20]。8 月10 日,报道了广东军队的情况,广东军阀对南昌起义军进行了“围剿”,“粤方军队陆续入赣”引用香港、广州等地的信息强调“李济琛荐黄绍雄为‘讨共’军第八路总指挥”[21]。随后,“驻韶各军全数开赣”[22]、“本馆要电:粤桂军分道入湘赣”[23]说明两广军阀已经开始对南昌起义军进行围剿,成立了第八路总指挥部负责进剿事宜,南昌起义军面临更加复杂的革命形势,反映了南昌起义的复杂性及其进程的曲折性。而“武汉驱共益形峻厉”[24]、“武汉方面——对反共的通电”[25]、“武汉共产党破坏阴谋大暴露”[26]关注了武汉方面的局势,强调武汉政府已经蜕变为“反共”的政府,这就导致武汉政府与南京国民政府开始慢慢走向合流。到1927 年9、10 月之后,《申报》对南昌起义的报道有“叶贺军败退闽境”[27]、“叶贺残部窜扰南雄”[28]、“叶贺残部窜入湘境”[29],重点在说明南昌起义军进入潮汕之后,起义军进入闽西、湘南、粤东北继续开展斗争。
由此可以看出,《申报》对南昌起义的报道呈现出更广阔的视野,有着三个鲜明特点。一是认为南昌起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一次武装起义,既关注南昌起义的发生发展过程,更加关注南昌起义期间各方势力的反应,尤其是关注武汉、南京、广东等地的军阀势力是如何对南昌起义军进行“围剿”的情况,通过“赣局迷离惝恍”、“赣局大紊乱”、“赣省战云弥漫”、“贺叶宣言共产”、“粤方军陆续入赣”、“南浔路交通” 等视角和语言报道南昌起义期间的双方军队的激战和社会民众利益等情形,这就把南昌起义作为影响中国国共两党政治和军阀政治的重大事件进行报道。二是不同于《上海民国日报》出于国民党立场将南昌起义作为攻击武汉国民政府的由头和靶子,将“反武汉”与“反共”等混为一谈,保持着一定的独立性和政治立场,不试图卷入国民党内部的纷争。《申报》的信息来源比较广泛,及时关注电通社、中央社、东方社、文汇报等媒体的电讯,也广泛征引来自武汉、南京、广州、香港各地的电报,令我们看到南昌起义的产生发展各方关注的伟大事件,更是影响近代政治军事发展的重大历史事件。三是基于资产阶级的本质与特点和国民党的打压与管控,《申报》在对南昌起义的报道时的立场是变化的,即从一个介于国民党与民众之间的立场,后期由于国民党对新闻宣传的管控加强,《申报》也转变为国民党新闻媒体宣传的重要部分,如通过发布蒋介石“下野”和原配离婚等启事以及报道宁汉合流后成立的国民政府在南京成为“新都”等,表明《申报》与国民党的政治关系越来越紧密。
《申报》对南昌起义的叙事结构与《布尔塞维克》具有显著差异,其立场与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也有所不同,在其报道叙事中重点是阐述各方立场及观点,在转述观察各方的过程中体现自身对于共产党革命的态度。这样的叙事特点对于理解中国共产党领导武装起义的复杂艰巨性具有重要的认识,从一个侧面反映,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担负起领导中国革命的重任,才能改变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命运,才能在四面白色恐怖中奋起,开启独立领导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的征程。
《上海民国日报》:国民党党派政治视野下的南昌起义
《上海民国日报》是国民党上海市党部机关报,创刊于1916 年1 月22 日。初以高举反袁护法大旗反对北洋军阀统治为宗旨,有着强烈的政党意识。在新文化运动中,其副刊《觉悟》宣扬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相关理论知识,配合《新青年》展开反对无政府主义的斗争。1924 年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后成为国民党中央机关报,1925 年末被西山会议派所把持,转为国民党右派的报纸,被广州国民党中央执委宣布为“该报为反动分子所盘踞,议论荒谬,大悖党义。”上海“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此报为蒋介石所控制,主要编辑者有叶楚伧、陈德徵等人,主要从事国民党政策宣传“反共”方面的报道。
南昌起义前,《上海民国日报》就以一篇“赣事特载:共党铁蹄之江西”借此“反共”,说明了中国共产党在江西的政治、军事、言论与行动、教育等方面的情况,认为江西党权为共产党所“窃据”,江西的政治无异于“军阀时代的政治”,江西的经济状况混乱,教育已经破产等等。其中的事例大都没有经过证实,是基于党派利益和党派纷争的偏颇性报道,意在假托民意,渲染紧张局面,同时全面强化自身的意志。但其政治嗅觉已感江西“黑云压城”[30]。8 月4 日发表了第一篇关于南昌起义的报道“共产党起内讧”[31],将南昌起义看成共产党内部纷争,认为张发奎是共产党的一部分,可见其并未看到本质,并且是以“反共”的立场报道南昌起义的产生发展过程。“共产党内讧 南浔线战事激烈”[32]说明南浔战事的紧张,再次以“反共”的立场说明南昌起义的性质。而所谓的揭示南昌起义内幕的文章则将南昌起义作为攻击武汉和汪精卫的靶子,认为这是汪精卫借机攻打南京的事件[33]。而“汉口陷于恐怖状态”[34]、“武汉伪政府大恐慌”[35]、“混乱中之武汉现状”[36]则是一味地借南昌起义攻击武汉政府,同时发布“汪精卫、唐生智、朱培德等先后电中央悔罪,并请出兵讨共,中央认汪等无诚意未复。”这类消息,意在强调南京国民政府的正统性。所谓的“武汉状况之解剖”[37]更加强调其“反共”立场,也在不断嘲讽武汉政府,这说明其将南昌起义作为“反武汉”的一部分,反映了宁汉对峙的时代特征。而“武汉决定驱共办法 谭平山等褫职拿办”则是在强调南昌起义发生后,武汉政府也已经开始“反共”,意味着宁汉双方开始在“反共”中变得同流合污,国民党内部由分裂开始走向表面上的统一局面。“十一军集合余江”[38]说明国民党反动派已经在“反共”的立场上趋于一致,南京国民政府开始参与到“进剿”南昌起义军的部署之中,这对共产党革命形势的胜利发展极为不利。“赣人呈请国府讨共”[39]转载的是南京通信的信息,意在强调其“反共”与南京方面是一致的。10 月后,《上海民国日报》将共产党领导的武装部队称呼为“盗匪”、“共匪”说明其试图塑造自身正统立场对南昌起义军及共产党进行“剿杀”,充分显示了其反动立场。“叶贺共军全部歼灭经过”[40]引用汕头通讯认为叶部向黄绍雄投降,贺部被陈济棠缴械,汕头的商店照常营业。“叶贺崩溃的经过”[41]采用书信的形式报告了南昌起义军在潮汕地区经历的挫折。
由此可见,在南昌起义期间,《上海民国日报》将“反共”、“反武汉”与宣传国民党政策结合在一起的,把南昌起义作为国民党内部争权夺利的一个靶子,将南昌起义的叙事作为其“反武汉”的一部分。从其对南昌起义的报道广度来看,不仅关注到了南昌起义本身的发展过程,也关注到了国共两党局势、国民党内部斗争的情况,将南昌起义放在更大的时空中去认识,不断挖掘其与自身政治利益的关系。再次,《上海民国日报》充斥着“反共”的气氛,等武汉国民政府也在“驱共”、“反共”方面走出实质性的一步之后,国民党内部两大政治派系(武汉和南京)渐渐趋于合流,该报对南昌起义的报道集中于“反共”这一点。
与《布尔塞维克》《申报》不一样的是,《上海民国日报》以国民党党派纷争的角度认识南昌起义的产生、发展过程,将南昌起义作为其实现自身政治利益的一部分去认识,这就让我们观察到它是以一个党派的立场认识南昌起义。当国民党内部党派利益趋于一致之后,其对南昌起义的报道和叙事就变成了只剩下“反共”这一块。但也应看到,国民党内部仍然不是铁板一块,只是达成了表面上的统一,内部之间的争权夺利、派系纷争仍然是国民党无法解决的实际问题,其“反共”深受自身权势影响,也受到自身四分五裂的制约,可见在半殖民半封建国家的反帝反封建民主革命中,统一战线至关重要,中国共产党打着“国民革命军”的旗号打响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第一枪,既是基于当时历史条件所制约,又是汲取大革命失败教训的进步。
结语:重大革命史叙事与记忆建构研究重塑与拓展
南昌起义发生后,中国共产党的党刊《布尔塞维克》、民族资产阶级创办的社会公共报纸《申报》和国民党方面的报纸《上海民国日报》都进行了报道和评论,三个不同报刊的阶级属性决定了对南昌起义的报道角度、立场、观点和方法存在着显著的差异。《布尔塞维克》重在揭示南昌起义的意义,认为南昌起义是“历史上伟大的革命事件,是中国革命史上最光荣的一页”,是“中国工农革命的第一声”,给南昌起义奠定了历史的基调,也为我们后面认识和纪念南昌起义提供了重要的参考,才有“南昌起义连同秋收起义、广州起义以及其他许多地区的武装起义,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的开端,开启了中国革命新纪元。”[7]《申报》将南昌起义作为一个关系国共双方、影响近代史进程的事件进行报道,在报道的广度和深度上进行了重要的探索,反映现代新闻报刊以新闻、评论、广告为内容,具有一定程度的客观性。但是也应注意到其阶级立场,尤其是在国民党对其管控日益加强的情况下,其报道的客观性将会大打折扣。《上海民国日报》作为上海地区国民党的机关报,其不仅将南昌起义作为“反共”的一部分来报道,也在报道的初期将其作为影响宁汉关系,进而作为“反武汉”的一部分进行报道,当国民党宁汉双方趋于合流之时,南昌起义军成为了国民党上下共同“围剿”的对象,南京国民政府表面统一完成之后,其“反共”的立场暴露无遗,不仅反对南昌起义等武装起义,而且大肆制造“白色恐怖”,但也应注意到国民党内部的纷争依然严重,国共双方的斗争也是潜藏在国民党内部纷争的重要内容。
作为历史研究者,既要将革命放回到20 世纪中国的历史情境中去“设身处地”地理解,又要使自己与这场革命保持一定的距离以“冷眼旁观”;既要客观平实地解读“过去”,又不可能完全摆脱现实关怀的干扰[42]。因此比较《布尔塞维克》《申报》和《上海民国日报》等报刊对南昌起义报道的异同,对三种报刊的叙事结构和记忆结构的建构问题研究,可发现在重大革命史叙事和记忆建构研究中,要更加重视对史料的挖掘与利用。具体从南昌起义来看,报刊对南昌起义的叙事与记忆结构建构,不是一开始就形成的。就中国共产党而言,对南昌起义的认识也不是一成不变的,除了《布尔塞维克》外,《红色中华》《新华日报》等中共报刊也对南昌起义进行了革命史叙事。除了关注党报党刊对南昌起义的革命史叙事和记忆建构之外,还应着重关注革命事件发生时候报刊的现场报道,如《申报》和《上海民国日报》对南昌起义的报道。这缘于:一是报刊史料可以拓展南昌起义研究的广度,报刊立体化探究重大革命历史事件的产生发展过程,可以通过舆论、民情和社会反应,将南昌起义置于纷繁复杂的近代史场域中,以期展现南昌起义发生发展面临复杂多元的历史世界,从而体会到南昌起义是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和中华民族发展史上的一个伟大事件;二是党报民刊史料还可以拓宽南昌起义研究的深度,从当前的史学研究趋势来看,记忆史学、概念史、书籍史、物质文化史等新趋向的出现不仅可以开拓更多的研究新领域,更为重要的是令研究者可以观察到更具有深度的历史,比如说从记忆史学的角度认识革命史的产生发展,进而探究革命史书写的近代化及其演变过程,从物质文化史的角度认识革命,不仅可以让研究者注意到革命产生发展的必备条件,也可以从日常生活的角度研究革命史叙事,从而理解“革命的日常”和“日常的革命”;三是民国其他非中共报纸报刊展现了南昌起义斗争的复杂艰巨性,在纷繁复杂的民国社会中,除了中共革命力量外,还有很多其他的革命力量在不断产生发展演变之中,透过民国时期非中共报刊及其他史料,就能发现革命史叙事的多元复杂性,既可以看到革命史多主体演进,也可以看到革命史本身过程的曲折,为展现更加立体化的革命史提供平台和可能。
结合以上的研究,笔者试图强调以下几点:一是革命史研究应该尽可能多地挖掘史料。史料是史学的根本,中共革命史的百年历程诞生了许多报纸报刊,中共与其他政党的一个显著区别是中共善于总结自身历史经验,善于主动建构自身历史,善于向外传播自身革命理念,这也就意味着革命本身也是一个不断生产革命叙事的过程,围绕革命和革命叙事,理应在充分占有革命史史料的基础上取得突破。二是革命史研究应该尽可能多地借鉴多学科的研究方法。近年来,心灵史、情感史、物质史的出现解决了革命叙事中的日常问题,也揭示了革命的产生发展演变诸多面向,革命史研究的重点任务不仅是揭示历史事实,也应在推动史学发展中有自己独特的地位。革命史研究只有借鉴更多样化的研究方法,才能不断在史学研究中有更多话语权和主动权,进而在解释中共革命的过程中构建自身历史地位。三是革命史研究应该融通内外,学会从全球史的眼光看待革命史。近来,全球史的深入发展不仅可以看到整体史的演变思路,也可以展现革命史在解释微观中的诸多可能。在全球史视野下,不断理解传统与现代、革命与未来、全局与微观在革命史研究中的意义。
———纪念八一建军节95周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