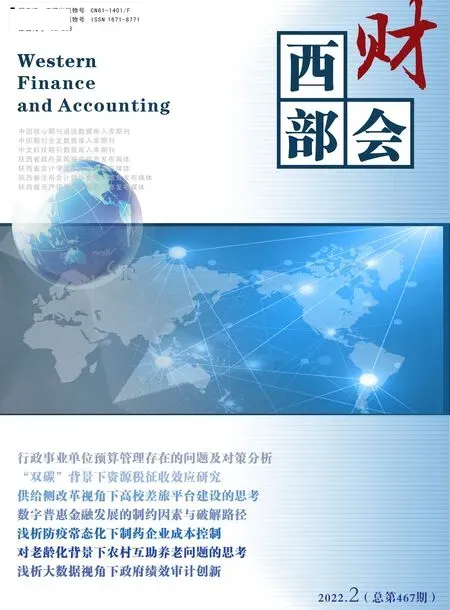对老龄化背景下农村互助养老问题的思考
钟丽红
(福建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福建 福州 350117)
一、农村老年人互助养老的现状与内涵
我国人口老龄化呈现出城乡倒置和未备先老等特点,农村将面临着巨大的养老挑战。第七次人口普查的数据显示,2020年,农村60岁及以上、65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的占比分别为23.81%和17.72%,比城镇分别高出7.99和6.61个百分点。与城镇相比,农村老龄化程度深,高龄、独居、空巢现象严重。为此,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提升农村养老服务能力”,国家则倡导通过发展“农村互助式养老”来解决农村老年人口的养老问题。基于此,农村互助养老作为一种新型的社会养老模式也成为了学界关注的重要议题。
农村互助养老是指在一定的地域范围内,在政府、社会机构、志愿者等多个主体共同参与下,农村老年人通过互助的方式解决养老难题,提升老年生活质量的养老方式。根据群体动力理论的观点,人的行为是个体需要和外在环境的作用,故将老年人互助养老的需求量作为个体需要,政府投入作为外在环境因素,纳入框架中,分为四种农村互助养老类型。一是村庄内生型。该类型政府投入小,老年人互助养老的需求量也较小,常见于小型的精英互助养老,或小型的协会互助院。二是政府外生型。该类型是主要靠政府的支持,部分老年人参与的养老模式。三是村庄推动型。该类型内生动力足,主要依靠当地的资源实现自我管理,政府投入小。四是政府推动型。该类型不仅老年人互助养老的需求量大,且政府支持力度也较大,能够较好的实现农村养老问题。
二、农村互助养老产生的原因
(一)制度推动论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指出,“十四五”时期是我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做好养老服务的关键“窗口期”,要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国家战略,推动养老事业高质量发展。互助养老作为一种低投入、易推广、可复制的模式,逐渐进入大众的视野。中央和地方政府也十分重视发展农村互助养老,早在2011年,国务院就在《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规划(2011-2015年)》中提出要探索农村互助养老模式。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强调要大力培育互助性农村社会组织。同年,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表示要发展互助式养老。《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也对推进互助型养老服务发展做出了要求。一直到2021年,中央一号文件仍强调了发展农村互助性养老。由此可见,政府一直致力于推动农村互助养老的发展。
(二)现实需要论
现实需要论认为,农村互助养老之所以会产生,是因为老年人的切身需要。一方面,随着年龄的增大,老年人的社会角色逐渐丢失,社交范围逐渐变小,老年人需要防止社会关系弱化的渠道;另一方面,老年人对于机构化的养老服务给付能力有限,导致其对低成本的养老服务有较大的需求。农村互助养老不仅让老年人以较低的成本重新嵌入社会网络中,还使其获得了生活照料、精神慰藉等养老资源。
(三)文化影响论
文化影响论认为,农村互助养老可以推行的原因与道义观念、合作精神相联系。道义观念是农村互助养老观念的重要思想基础,自古以来,中国就传递扶危济困、行善施德等道义观念,且强调对弱者进行义不容辞的保护,道义观念是人们实行助人行为的重要思想力量。农村互助养老是农村老年人依靠自身力量,采用“自助+互助”的方式解决自身养老困境的一种务实选择。为保证互助养老模式的持续发展,仅靠道义互助传统是远远不够的,还依赖于福利合作模式的构建,参与互助的老年人一方面是养老服务的接受者,另一方面是养老服务的供给者,也就是说,合作精神是农村互助养老发展的关键。
(四)环境诱导论
环境诱导论认为,农村互助养老的出现是现行农村特殊的社会环境导致的。首先,在独生子女政策的背景下,农村年轻人城市单向流动的比例大,同时,在个体化的趋势中,“为自己而活”的现象越来越普遍,家庭养老功能逐渐弱化。其次,农村的养老服务基础薄弱,养老服务设施陈旧落后,养老服务质量较低,例如,许多农村仍然延用建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的敬老院,设施不仅老旧,还存有安全隐患,对于照料护理、医疗康复等服务需求也难以满足。最后,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对老年人的定位和年龄污名也急需改变,老年人不再只是单纯的“被照顾者”和“无能者”,年龄对于老年群体的约束面逐渐缩小,老年人可看作是具备自我发展能力和自我创造能力的生产主体。
三、农村老年人互助养老存在的问题
(一)农村互助养老受到传统思想羁绊
农村互助养老是为解决农村养老问题而创设的新型养老模式,作为一种新的尝试,我国既无经验可用,也没有规章可循。首先,农村地区作为传统氛围较浓厚的地方,对于新事物的尝试常常带有怀疑、排斥的心理。其次,传统孝文化强调养儿防老或者以血缘为纽带的宗族赡养,而农村互助养老并不以血缘关系为基础展开,这与老年人传统的养老认知是相违背的。最后,老年人及其子女会将参与互助养老看作是一种折损“面子”的行为。因此,农村互助养老在开展阶段会受到传统思想的阻碍,实施存在一定的困难。
(二)农村互助养老资源碎片化
农村互助养老能否持续运转,其关键在于各种养老资源是否能够持续支持。但实际上,农村互助养老却存在内部资源零碎化、外部资源零星化、资源递送临时化等问题。一是内部资源零碎化。内部资源是指农村及参加互助的老年人自身所掌握的资源,由于老年人存在个体差异,其自身掌握的资源也不尽相同,参与互助的老年人提供的资源,多以生存型等基础性资源为主,缺少技术型等方面的资源。同时,未参与互助的老年人拥有的资源又较丰富,这就使得互助养老的内部资源呈现出零碎化特征。二是外部资源零星化。互助养老的资源大部分是以“自助+互助”的形式获得,而急需的养老资源却往往无法通过互助形式获得。例如,医疗、教育等资源,除政府外的其他外部主体资源供给程度低,大多数是以一次性供给为主。三是资源递送临时化。为保证农村互助养老模式能够更好的运转,政府的民政、老年委等部门均设置了供给互助养老资源的职能,由于缺乏长期性的规划,其养老资源的的递送也呈现为临时化状态。
(三)互助养老供给目标和需求偏好发生偏离
农村互助养老的本质是满足农村老年人的养老需求,提升老年人晚年生活质量。因此,在尊重老年人需求偏好的前提下,设置合理的供给目标是保障农村互助养老有效性的重要基础,但最终呈现的结果却显示,互助养老的供给目标和需求偏好发生了偏离,究其根本在于政府、市场以及社会组织均以不同的视角去看待农村互助养老问题。上级政府着眼于中长期目标,基层政府追求短期效应,市场关注利益,寻求利益最大化,而社会组织则看重社会价值,注重其带来的社会效应。在各方主体的目标导向中,农村老年人的养老需求逐渐被忽视,最终导致供给目标和需求偏好两者之间的偏离。
四、解决农村互助养老问题的建议
(一)加强舆论引导,提升农村互助养老的认知
加强宣传力度,提高农村居民的互助意识,转变老年人的养老理念。一方面,村委会和基层党组织,要以喜闻乐见的方式讲解有关互助养老的理念和政策,传递患难相恤、守望相助等积极思想,分享相关的案例和经验,让养老需求溢出家庭范围,让互助养老实践延伸到宗族范围之外的关系中。当互助理念成为一种盛行的乡村文化时,老年人互助养老组织起来就会显得轻松许多。另一方面,组织专业团队下乡传授相关技能,通过有针对性的辅导,提高老年人的生产能力,激发老年人自我发展的信心,破除“老人无用论”等消极思想。
(二)加大对社会资本的吸引,拓宽资源筹集渠道
农村养老互助模式的发展思路在于:构建互助组织,配备互助服务队伍,持续的资源保障。为更好的发展农村互助养老,一是要发挥农村老年人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在老年群体间构建合作互助组织,可以发挥现有老年群体组织的力量,例如老年歌剧团等,动员更多的老年人参与到互助养老的建设中来,通过老年群体自主组织筑起养老互助共同体。二是配备互助服务队伍。在鼓励老年人参与的基础上,引导更多的社会主体参与互助养老,例如志愿者团队、专业机构、医院等,构建多主体参与的互助服务队伍。通过多主体的参与,提高互助养老的专业化、规范化,如通过与专业养老机构的交流,提高养老服务的水平。加强与城市医院的合作,满足老年人的医疗需求,可以通过构建“互联网+医疗”的模式,实现农村老年患者与城市医院专家在线面诊,利用互联网技术监控老年人的身体健康状况,及时给予医疗救助等服务,为老年人提供智能化、系统化、全面化的养老服务。三是持续的资源保障。一方面,要加强外部资源的供给能力,通过出台相关政策,例如提高相关贷款的优惠制度,吸引社会资本的流入。另一方面,则是要提高内部资源持续供给的能力,可以结合当地的实际情况,组织老年人从事小规模的种植、加工和养殖,获取的收入不仅可以满足互助老年人的生活开销,还可以用于解决互助养老机构的资金困境。
(三)完善农村互助养老的制度设计,建立中央地方协同治理策略
农村互助养老应该明确供应主体的责任。农村互助养老行为可以看作是一种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以及地方协同治理之下,以集体主义为原则,通过多个主体参与的组织。因此,在中央地方协同治理的思路下,中央不仅要优化农村互助养老的制度设计,完善相应的法规政策,还应该平衡好各种政策工具的方向,提高服务供给的精准性。而地方政府则需要转变供给思路,在“需求—资源—供给”的路径下,分层分级动态供给,在明确农村老年人养老需求的前提下,进行资源整合,最终才能形成有效供给。为使农村互助自治组织能够得到更好的发展,可以将部分权利下放给村委会,并将监督权也部分让渡给村民,这样才能真正实现上下协同治理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