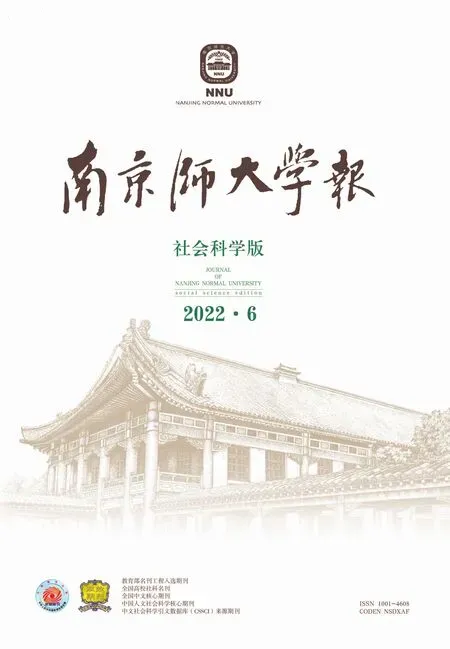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的双重差异与政策启示
雷万鹏 向 蓉
一、 问题缘起
家庭是影响儿童成长的重要环境之一,家庭教育是影响儿童发展的关键因素。在2018年召开的全国教育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家庭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要给孩子讲好‘人生第一课’,帮助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1)习近平:《共同担负起青少年成长成年的责任》,《人民日报》2018年9月14日,第2版。家庭教育作为现代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共同构成塑造人的教育体系,家庭教育质量的提升对人与社会的发展有重要影响。
从现实来看,我国家庭教育发展与家长教育素养的提升依然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家长教育意识与教育行为脱节、家长教育观念功利化、家长教育素养不高等问题还普遍存在。长期以来,家庭教育被视为家庭的“私事”。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及家庭教育深层次问题的显现,人们逐渐认识到家庭教育不仅仅是私人问题,还关乎社会和谐稳定与国家长远发展,家庭教育逐渐从“家事”变成“国事”。近年来,为全面强化和提高家长的家庭教育主体责任与教育水平,教育部等部门相继颁布《关于加强家庭教育工作的指导意见》《关于指导推进家庭教育的五年规划(2021—2025年)》;明确提出建立健全适应城乡发展、满足家长和儿童需求的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体系,促进家庭教育工作均衡深入发展,为营造有利于儿童健康成长的家庭和社会环境创造条件。特别是在“双减”背景下,党、国家和人民对家庭教育提出了更高要求,建立健全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体系,提升家长的教育素养,显得尤为重要。
阿马蒂亚·森提出要对个体及其家庭的“可行能力”进行社会投资,以此促进家庭监护能力与教育能力的提升(2)胡湛、彭希哲:《家庭变迁背景下的中国家庭政策》,《人口研究》2012年第2期。。Heckman(2007)构建的“能力形成模型”指出,外部投资和社会干预是提升个体能力的重要途径之一(3)J.J.Heckman,“The economics,technology,and neuroscience of human capability formation”,PNAS,Vol.104,No.33,2007,pp.13250-13255.。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主要有五方面的功能:一是挖掘家长的教育潜力,二是提高家长的教育意识,三是帮助家长树立正确的教育理念,四是帮助家长获得教育技能,五是预测父母行为的后果(4)R.Ailincai & A.Weil-Barais,“Parenting education:Which intervention model to use?”,Procedia-Social and Behavioral Sciences,Vol.106,2013,pp.2008-2021.。家长的教育能力是影响儿童发展的重要因素,对家长的指导可以有效帮助家长形成正确的教养理念和养育子女的知识技能,抑制错误的教养行为,从而减少儿童的问题行为并促进儿童健康发展(5)A.R.Piquero,D.P.Farrington & B.C.Welsh,et al.,“Effects of early family/parent training programs on antisocial behavior and delinquency”,Journal of Experimental Criminology,Vol.5,No.2,2009,pp.83-120.。实证研究表明,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的投资回报率介于2%至17%之间,具有较高的投资回报率(6)S.Aos,P.A.Phipps,R.Barnoski & R.Lieb,The Comparative Costs and Benefits of Programs to Reduce Crime,Olympia,WA:Washington State Institute for Public Policy,2001,pp.234-238.。
《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明确指出“教育行政部门、妇女联合会统筹协调社会资源,协同推进覆盖城乡的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体系建设”。这对家庭教育指导服务提出机会普惠性和指导差异性两方面的要求:一是家庭教育指导服务具有普惠性,必须惠及每一个家庭、每一个儿童,尤其要关注学困生、贫困生、农村留守儿童、城市随迁子女、离异家庭等处境不利儿童和家庭,应以公平为基本价值取向,优先满足处境不利群体的基础性需求,为这部分弱势群体提供公共性、公益性的“兜底式”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二是家庭教育指导服务应满足人民群众多层次、多样化需求,坚持因材施教原则,为不同家庭提供精准化指导。富有个性的家庭系统决定了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的特殊性和复杂性,应变革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的供给方式,提供丰富、多元、优质的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产品,以回应不同家庭的需求和偏好,提高家庭教育指导服务效果。
国际社会对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的重要性已达成共识,美国的“早期开端计划”、澳大利亚的“积极教养计划”、法国的“明智育儿项目”、英国的“确保开端计划”等均属于家庭教育指导服务项目。整体来看,我国的家庭教育指导服务还处于萌芽阶段,以家长会、专家讲座等集体指导形式为主,“家长学校”的功能发挥极为有限(7)许璐颖、周念丽:《学前儿童家长亲职教育现状与需求》,《学前教育研究》2016年第3期。。此外,家庭教育指导服务内容零散,无法满足家庭需求(8)边玉芳、张馨宇:《新时代我国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体系:内涵、特征与构建策略》,《中国电化教育》2021年第1期。,家庭教育指导服务途径不灵活,指导对象缺乏针对性(9)吴艳、吴颖婷:《上海市小学家庭教育指导的现状调查》,《教育学术月刊》2021年第1期。。究其原因,一方面,家长对自身教育素养和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的重要性认识不足,投资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的积极性不高。另一方面,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作为一项社会支持政策,仍停留在倡导层面,一直被视为是一个“软任务”,而不是“硬制度”(10)钱洁、陈汉民:《家庭教育指导:急需个性化和科学化》,《教育科学研究》2018年第5期。。如何拓展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的覆盖面,不断提升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的质量与效果,是构建覆盖城乡的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体系的关键。
在家庭教育日益得到各界高度关注的当下,家庭教育指导服务对提升家长教育素养产生了怎样的影响?不同家长的获益机会与效果是否存在差异?本文基于湖北省8市18县(区)1850个家庭的调查数据,利用普通最小二乘法、准实验的倾向得分匹配法及异质性的分位数回归等方法,实证分析了家庭教育指导服务对家长教育素养的影响及其差异性,以期为相关政策制定提供有益启示。
二、 研究设计
(一) 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来自2019年6月至8月华中师范大学课题组对湖北省8市18县(区)进行的调研。湖北省地处中部地区,是教育大省,从产业结构、地理差异、教育发展形态和人口特征看,能够较好地反映中西部地区特征。近年来,湖北省相继出台了《家庭教育指导与服务“十三五”规划》《湖北省家庭教育促进条例》等家庭教育政策,在构建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体系方面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比如,通过打造“家爱学院”网上家长学校,持续推进“家庭教育楚天行”;通过“湖北省家风家教实践基地”和示范家长学校开展“家庭教育公益大讲堂”“荆楚好父母”“家教万里行”等丰富多彩的家庭教育指导服务活动,有效提升了家长的教育素养。因此,基于湖北省的调研具有相当的典型性和代表性。
本次抽样分四个步骤:首先,按照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地理位置等因素选取湖北省8个样本市;其次,在每个市内根据经济发展水平选取经济较为发达、经济发展水平中等及相对贫困县各一个;再次,在样本县分别选取城关镇、经济发展水平中等及经济欠发达乡镇各一个;最后,采用非概率抽样中的偶遇抽样方法,即研究者在乡镇中选择30至50个容易找到的或者偶然遇到的家庭进行入户调查。调研分别设计了家长问卷和学生问卷,并将两者一一匹配,形成“家长-学生”数据库。
(二) 变量界定
1. 被解释变量
本文被解释变量为家长教育素养,其量表参考育儿胜任力模型中的家长教育素养分量表(11)B.D.Johnson,L.D.Berdahl & M.Horne,et al.,“A Parenting Competency Model”,Parenting:Science and Practice,Vol.14,No.2,2014,pp.92-120.,采用“翻译-回译”的方式,在保持与原量表内容一致的前提下,对其进行本土化表达形成五点计分量表。数据结果显示,量表的Cronbach α系数为0.932,KMO值为0.948,表明量表具有较高的信效度。量表共24个题项,分为家庭教育观念、家庭教育知识、家庭教育能力三个子维度。家长教育素养及其子维度得分均值(1—5)代表家长教育素养状况,均值越大,代表家长教育素养越高。
2. 核心解释变量
本文核心解释变量是家庭教育指导服务。问卷中询问了家长“您有没有接受过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答案为二分变量(有=1,没有=0)。在倾向值匹配分析中,没有接受过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为控制组,接受过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为处理组。其中接受过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的家长比例为40%。
样本信息显示,从指导服务形式看,参加家长会占32.19%,家庭教育讲座占20.84%,开展亲子活动占13.88%,QQ或微信群的资源共享占13.76%,家长学校占6.91%,家庭访问占5.56%,电话指导占3.82%,个别指导占3.03%。从指导服务内容看,有关家庭教育方法的占28.73%,有关家长教育观念的占24.09%,有关家庭教育知识、家庭教育策略、家庭教育能力的分别占23.10%、12.94%、11.14%。从家庭教育指导服务存在的问题看,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即指导内容服务太理论化(33.53%)、指导服务活动形式单一(27.97%)、指导者专业化水平不高(20.66%)。这表明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体系的可及性和覆盖面不够,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的质量有待进一步提升。
3. 协变量
基于已有研究及课题组田野调查,本文选择了可能会同时影响家长家庭教育指导服务机会获得和家长教育素养的因素作为协变量。(1)家长年龄。有研究显示,母亲年龄越大,心理越成熟、经验越丰富、生活越富裕,她们教育子女的能力可能会越强(12)J.Hardy,N.M.Astone & J.Brooks-Gunn,et al.,“Like mother,like child:Intergenerational patterns of age at first birth and associations with childhood and adolescent characteristics and adult outcome in the second generation”,Developmental Psychology,Vol.34,No.6,1998,pp.1220-1232.。(2)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相对而言,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家长有更多时间和经济资本去提升自己,其教育素养也更高(13)A.V.McGillicuddy-DeLisi,“Parental beliefs about developmental processes”,Human Development,Vol.25,No.3,1982,pp.192-200.。本文选择父母双方教育水平较高一方的受教育年限、父母双方职业水平较高一方的职业得分、家庭经济状况得分、家庭文化资源得分四个变量计算得出的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作为协变量(14)计算公式为:家庭社会经济地位=(β1*edu+β2*ocup+β3*eco+β4cul)/γ,β1-β4分别代表受教育水平、职业得分、家庭经济状况得分、家庭文化资源得分四个指标的因子载荷系数,γ为主因子特征值。其中,父母的职业参照中国社科院在《中国社会分层研究报告》的职业划分标准,从低到高分别赋值为“1分(无业、待业)-10分(党政干部)”,取父母双方职业得分较高一方纳入计算。家庭经济状况用“一张供学习使用的书桌”“一个孩子单独的房间”“一台可使用的电脑”作为测量指标,“有”赋值1,“没有”赋值0,加总分数为经济状况得分。家庭文化资源得分用经典文学作品(如《西游记》)、古诗词(如《唐诗三百首》)、艺术品(如画作、雕塑)、教辅读物(如课外书、参考书)、字典词典作为测量指标,“有”赋值1,“没有”赋值0,加总分数为家庭文化资源得分。。(3)家庭结构。实证研究表明,单亲家庭由于家庭结构不完整,家庭教育功能出现缺损,由此也影响亲子互动、父母监督、学业辅导(15)P.R.Amato,“The consequences of divorce for adults and children”,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Vol.62,No.4,2000,pp.1269-1287.。根据王跃生(2013)和吴愈晓、王鹏、杜思佳(2018)对家庭结构的划分,本文将家庭结构分为双亲缺席家庭、单亲家庭、双亲家庭三类(16)参考吴愈晓等对家庭结构的划分,父母双方均不和孩子同住的为双亲缺席家庭、孩子仅与母亲一起居住或者孩子仅与父亲一起居住的为单亲家庭、孩子与父母双方共同居住的为双亲家庭。,以双亲家庭为参照组。(4)城乡分布。养育行为存在明显的城乡差异,城市家长的教育知识水平普遍较高,这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保证养育行为的“质量”可能会好于农村地区(17)李英、贾米琪、郑文廷、汤蕾、白钰:《中国农村贫困地区儿童早期认知发展现状及影响因素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9年第3期。。城乡为二分变量,以户口所在地为划分依据,城市为设立市的市区和县政府所在的建制镇(城关镇),村为非县政府所在的建制镇和乡村,以农村为参照组。(5)父母外出务工。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及城镇化进程的快速推进,农村剩余劳动力不断向城市地区和经济发达地区流动,由此形成了大量外出务工人员,他们整体呈现出教育素养不高和接受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的情况不佳等问题(18)李杨、任金涛:《中国流动、留守儿童的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现状与建议》,《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5期。。具体操作中,父母外出务工为二分变量,以父母未外出务工为参照。(6)参与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的意愿。参与意愿不仅会影响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的选择,还会影响家庭教育指导服务效果,应加以考量。(7)家长工作之余的自我发展。家长在工作之余的学习,是家长对自身人力资本投资的途径,也是其不断积累文化资本的重要过程(19)雷万鹏、向蓉:《学生科学素养提升之家庭归因——基于中国PISA 2015数据的分析》,《全球教育展望》2020年第9期。。具体操作中,本文将该变量设定为二分变量,工作之余有自我发展活动为1,没有自我发展活动为0。
(三) 研究方法
首先,我们要分析接受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与未接受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的家长在个体特征和家庭背景方面是否存在差异,以此了解两类群体的基本特征是否匹配。在此基础上,采用Logit估计方法考察家长接受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的影响因素。
其次,为了精确地评估家庭教育指导服务对家长教育素养的影响,我们同时采用了OLS估计方法和倾向得分匹配法(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以下简称PSM)。家长接受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的决策并非随机,受到个体因素、家庭因素等可观测特征的影响。为探索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与家长教育素养之间的因果关系,本文采用Rosenbaum和Rubin(1985)提供的倾向得分匹配法(20)P.R.Rosenbaum & D.B.Rubin,“Constructing a control group using multivariate matched sampling models that incorporate the propensity score”,American Statistician,Vol.39,No.1,1985,pp.33-38.,以处理选择性偏误问题。倾向得分匹配法的基本原理是:为接受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的家长i找到一个在可观测特征上近似但未接受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的家长,将该个体作为家长i的反事实样本,同时基于对结果均值的比较,实现平均处理效应的估计。我们将接受家庭教育指导服务对家长教育素养的平均处理效应记为处理组的平均处理效应(Average Treatment Effect Treated,简记为ATT),模型如下:
ATT=E{E[Guide1i-Guide0i|Di=1,p(Xi)]}
其中,Guide1i和Guide0i分别表示家长个体i接受家庭教育指导服务和未接受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两种情况下家长教育素养得分,Di为处理变量,表示家长是否接受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的虚拟变量,如果家长i接受了家庭教育指导服务,则Di=1,反之Di=0。p(Xi)为倾向得分值,表示在控制样本特征协变量X的情况下,家长i接受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的条件概率。本文主要采用k近邻匹配方法,并运用半径匹配以及非参数核匹配方法对估计结果进行稳健性检验。
最后,为检验家庭教育指导服务对家长教育素养影响的异质性,本文采用Koenker和Bassett(21)R.Koenker & J.G.Bassett,“Regression quantiles”,Econometrica,Vol.46,No.1,1978,pp.33-50.提出的分位数回归估计方法,模型如下:
β1表示家庭教育指导服务Guideit的边际变化对家长在Qτ分位点上教育素养的边际影响。Qτ表示分位数,一般取值在0.1—0.9之间,取值越高表明家长教育素养分位越高(如0.9表示教育素养排前10%的家长)。
三、 实证结果
(一) 样本的描述性特征
表1显示,接受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的家长与未接受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的家长在家长个体特征和家庭特征方面存在明显差异。相较于未接受过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的家长,接受过家庭教育指导的家庭社会经济地位更高,城市家长占比更大,参与意愿更强烈,且均在0.1%的水平上显著。数据显示,接受过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的家长,其教育素养总体水平显著高于未接受过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的家长。从家长教育素养的三个子维度来看,接受过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的家长在家庭教育观念、家庭教育知识、家庭教育能力上的得分分别高0.12分、0.21分、0.17分。
(二) 影响家长接受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的因素:基于Logit模型的估计
表2中,Logit回归结果显示,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城乡分布、家长参与意愿对其接受家庭教育指导服务有显著影响。家庭社会经济地位每提高一个单位,家长接受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的概率增加11%,即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越高,家长接受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的概率越高。城市家长接受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的概率比农村家长显著高33.7%。家长参与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的意愿每增加一个单位,家长接受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的概率增加43.2%,这表明家长参与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的意愿越强烈,越有可能接受家庭教育指导服务。此外,家长年龄、家庭结构、父母是否外出务工、工作之余是否有自我发展活动对家长是否接受家庭教育指导服务没有显著影响。

表1 变量描述

表2 接受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的影响因素
(三) 家庭教育指导服务对家长教育素养的影响:基于PSM模型估计
1. 协变量的平衡性检验
协变量的平衡性检验关注的是具有相同倾向得分的家长在接受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上是否遵循随机分配,即接受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与未接受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的家长应该具有相似的个体特征,从而保证平均处理效应估计的准确性。从表3提供的k近邻匹配的平衡性检验结果可知,数据平衡后各协变量的标准化平均值差异均小于5%,各协变量的偏误均实现了不同程度的削减。其中,单亲家庭实现了最大幅度的偏误削减,降幅达到了201.8%,而父母是否外出务工的偏误削减幅度最小,降幅为2.8%。从t检验来看,匹配后协变量的p值增大且均大于0.05,说明数据匹配结果接受处理组与控制组之间不存在显著差异的原假设,数据匹配消除了接受家庭教育指导和未接受家庭教育指导在可观测特征上的显著差异,这表明本研究满足了平衡性假设。家长教育素养匹配前后核密度函数估计图显示(22)家长教育素养匹配前后核密度函数估计图备索。,数据匹配后,处理组与控制组变得相对拟合与聚拢,重叠区域也变得宽泛,处理组与控制组倾向得分的部分形态已经非常接近。因此,通过数据匹配能够消除家长在可观测特征上的组间差异,匹配过程明显修正了两组样本倾向得分的分布偏差,匹配效果理想,满足了共同支撑假设。

表3 协变量的平衡性检验
2. PSM估计结果
本文采用k近邻匹配法(k=4)估计家庭教育指导服务对家长教育素养的影响,并采用半径(卡尺)匹配和核匹配检验结果稳健性,结果如表4所示。第一,对比匹配前后各维度的平均处理效应,我们可以发现家长教育素养、家庭教育观念、家庭教育知识、家庭教育能力的平均处理效应均有所减小,这意味着选择性偏差高估了家庭教育指导服务对家长教育素养及其子维度的效应;第二,总体来看,接受过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的家长,其在教育素养相应维度上的得分在匹配后均高于未接受过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的家长,这表明接受过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的家长在教育素养优于未接受过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的家长;第三,从接受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的平均处理效应来看,接受家庭教育指导服务对家长教育素养的影响在不同维度上存在差异,其中,接受家庭教育指导服务对家长的家庭教育知识的正向影响最明显,平均处理效应达到0.113,对家庭教育观念的影响次之,对家庭教育能力的影响最小;第四,从稳健性检验结果来看,半径匹配和核匹配在估计结果上与k近邻匹配估计结果较为一致,这表明本研究所使用模型及研究结果具有稳健性。

表4 家庭教育指导服务对家长教育素养的影响
(四) 家庭教育指导服务对家长教育素养影响的异质性分析
表5报告了家庭教育指导服务对家长教育素养影响的均值效应和异质性效应。分位数回归中,我们分别选取了10、25、50、75以及90家长教育素养分位点,依次表示家长在低、中低、中位数、中高以及高教育素养上的水平,采用自举法反复抽样500次进行回归。OLS回归结果显示,家庭教育指导服务对家长教育素养及子维度均有显著正向作用,接受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的家长在家庭教育素养得分上比未接受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的家长高出0.105个标准分。分位数回归结果显示,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的影响效应随着家长教育素养分位的提高,呈现先上升后小幅波动的态势。值得关注的是,家庭教育指导服务对教育素养低(10分位)的家长效应不显著,对教育素养中高(75分位)的家长受益较大。就家庭教育观念看,家庭教育指导服务对家庭教育观念呈“倒V”型关系:随着家庭教育观念分位点的上升,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的影响效应先上升再下降,“倒V”型曲线的拐点出现在75分位上,且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仅对家庭教育观念75分位上的家长有显著正向作用,影响效应为0.145。就家庭教育知识来看,家庭教育指导服务对不同家庭教育知识水平的家长均有显著积极影响,且效应值较大(0.09以上)。此外,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的效应随家庭教育知识水平的提高不断增强。就家庭教育能力而言,家庭教育指导服务对家庭教育能力呈“倒V”型关系,随着家庭教育观念分位点的上升,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的影响效应先上升再下降,其中家庭教育能力在75分位点的家长接受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的收益达到了0.151,且家庭教育指导服务对家庭教育能力中低及以下(25分位及以下)的家长没有显著影响。

表5 家庭教育指导服务对家长教育素养影响的分位数回归估计结果
四、 结论与建议
构建覆盖城乡的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体系,提升家长教育素养是促进我国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基于湖北省8市18县(区)1850个家庭的调查数据,利用普通倾向得分匹配法及分位数回归等方法,本文实证检验了家庭教育指导服务对家长教育素养的影响,结果如下:
第一,家庭教育指导服务有助于提升家长教育素养。OLS和PSM估计结果显示,接受过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的家长在家庭教育素养、家庭教育观念、家庭教育知识、家庭教育能力上均优于未接受过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的家长。家庭教育指导服务对家长教育素养的影响效益为0.105,在处理了个体因素、家庭因素等因素带来的选择性偏误问题后,家庭教育指导服务对家长教育素养的影响效益为0.072。这一结论不仅用实证数据验证了有关家庭教育指导服务能提升家长教育素养的观点,也进一步说明了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的重要性,为构建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体系提供了重要参考。
第二,家庭教育指导服务机会的获得存在不均衡性。Logit模型估计结果显示,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城乡分布、参与意愿对家长接受家庭教育指导服务有着重要影响。与农村家长相比,城市家长接受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的概率要显著高33.7%,且随着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提升,家长接受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的概率不断增加。家长迫切需要权威性的专业指导,但是城乡家庭教育指导服务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的现实境况,制约了农村家长对于高质量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的获得。为此,构建覆盖城乡的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体系就成了新时代家庭教育事业发展的核心任务之一。
第三,家庭教育指导服务对家长教育素养的影响效应存在异质性,家庭教育指导服务对教育素养低(10分位)的家长不具有显著影响,对教育素养处于中高水平(75分位)的家长均有显著正向影响,且影响效应较大,均在0.14以上。具体而言,家庭教育指导服务对家庭教育知识的影响效应呈直线上升的趋势,对家庭教育观念和家庭教育能力的影响呈“倒V”型曲线,“倒V”型曲线的拐点出现在75分位上,并且投入更多时间精力接受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不会拉开家长在低-高家庭教育观念和家庭教育能力上的组内差距。总体而言,教育素养低的家长缺乏主动学习家庭教育知识的意愿和能力,往往以被动心态接受公益性指导,加之他们既有知识储备少,对新知识的接受能力较弱,家庭教育素养难以快速出现增值,形成家庭教育指导效果的“地板效应”。对于教育素养中高水平的家长而言,他们本身对家庭教育的重要性有深刻认识,往往主动增能,能快速吸收、消化、内化指导内容,因此对这部分具备一定家庭教育知识但仍存在进步空间的群体来说,只需略加指导即可取得较高收益。相反,对教育素养处于高水平的家长而言,家庭教育指导服务提供的知识可能因触及发展“天花板”而改善空间较小。这表明,应该提供差异化家庭教育指导服务,尤其关注教育素养处于低水平的家长。
从实践意义上看,本研究具有重要的政策意涵。一是为弱势群体提供补偿性指导,保证所有家庭都能公平地获得家庭教育指导服务机会。本文发现农村家长、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家长接受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的概率显著较低,家庭教育指导服务应向农村、经济困难、教育素养低的弱势家长倾斜,保障处境不利家长接受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的机会。罗尔斯提出通过差别原则和弱势补偿原则来改善“最不利者”的处境,实行对弱势群体的“优先扶持”,缩小他们与其他人之间的差距(23)[美]约翰·罗尔斯:《正义论》,何怀宏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第8页。。作为社会治理体系中的重要一环,需以公平为基本价值取向,优先满足弱势群体的基础性需求,为弱势群体提供更充足、更有质量的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二是创新家庭教育指导服务形式,回应家长的多样化需求。调查显示,湖北省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以家长会、家庭教育讲座等集体形式为主,指导活动形式单一也是目前家庭教育指导服务存在的主要问题之一。提供多样化家庭教育指导服务是回应家庭需求和偏好的重要路径,也是提高家庭教育指导服务接受率的重要策略。首先,充分利用已有的家庭教育指导服务模式,通过家长会、讲座、沙龙、阅读、观摩、分享、角色扮演、亲子活动等集体指导服务方式,扩大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的覆盖面。其次,增加家访、电话指导、个人咨询等个别指导服务方式,提升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再次,伴随着互联网、手机网络、多媒体通信、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发展,通过信息化开发家庭教育资源、优化家庭教育指导服务过程,把传统家庭教育指导服务升级为移动指导、远程指导,打破时空限制,满足家长不断增加的多样化指导服务需求。三是“因类型施教”,提升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的精准性和有效性。第一,根据不同儿童和家庭的特征,对家庭教育指导服务对象进行细化和分类,分析不同类型儿童和家庭的共性和个性,实施分类指导、分层服务、分步推进,建立和健全兼顾全面、重点突出、分层分类的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体系。第二,精准定位家庭教育重点问题,分专题进行指导服务。要科学调研家庭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和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从解决问题的角度有针对性地设计指导服务内容,使每次指导服务都能突出重点,如此既能将有限的教育资源发挥最大的效用,又能解决家庭教育问题以提高指导服务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