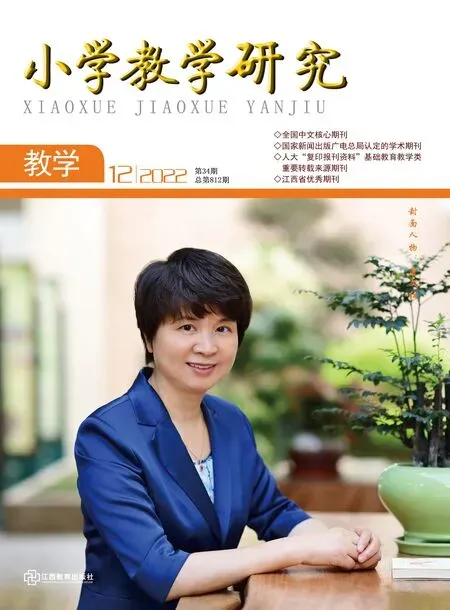由言入意,求有始终
——儿童古诗词“意会”学习微探
江苏省泰州市凤凰小学 闾 琳
古典诗词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承载了丰富的内涵。然而,诗歌瑰丽的言语形式对事物描摹所带来的感官冲击,要比诗歌本身竭力展现的精神世界更容易把握。所以,不少学者、教师认为,儿童的诗词学习应从其心智接受的角度出发,侧重于较好地把握的“言”,并以期以此实现“意”的感悟。此种做法实际是将“意”的体会“甩锅”给儿童“自行开悟”,有太多不确定因素,路径模糊。因此,儿童古典诗词学习,要么是“不求甚解”地反复诵读,要么是对诗词“意”的层层分析,此为古典诗词学习的难解之题。
一、始:古典诗词的言意之初
一切事物的生发都有其原初本意,这是事物发展的原点和归宿,要弄清问题本质,也只有回到初始,以此出发进行审视。
所有语言现象发生之初在于表情达意,诗歌更是如此。于此,中国很早就有“言意”之说。论“言意”绕不开庄子,郭沫若对他有如下评价:“秦汉以来的每一部中国文学史,差不多大半是在他的影响之下发展的。”庄子的“言意观”直接影响着中国古典诗词的创作和鉴赏,成为几千年来中国文人普遍接受的美学追求。
庄子的“言意观”秉承老子对于“道”之认识的“言不尽意”,又超越 “得意忘言”。老子和庄子认为,“大道无形”,“道”不可言,可言非“道”。他们认为,“道”是世界的本源真理,只能靠个人体悟触摸。世间万物复杂多变,以至于不能用确定的言辞对“道”进行精确定义与描述。但无论怎样,万物运行都是在“道”的笼盖之下的。所以,庄子说:“大道不称,大辩不言。”从表达的角度出发,语言能够精确把握的是“物”,它的形、声、色、相一一与实名对应,这些粗浅的表象可观、可感,容易把握。而作为思维工具的语言,对于事物精密的内在,如人的情感与思维,却显得苍白无力。
“得意忘言”是庄子对老子“言不尽意”的继承与超越。语言是表情达意的工具,心领神会之时,任何语言都显得多余。因此,“意”的境界是任何言辞都无法达到的境界,是人之心灵自由所在的最高精神境界,这才有了陶渊明的“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这种精神境界,构成中国古典诗词的精华所在,它是诗歌表达的初始期许和终极目的,对人的影响无比重要与深远。
二、觅:从言到意的思维路径
几千年来,中国诗词创作与鉴赏达成一个共识,即言意交融、密不可分。“意”是“言”的属性与价值,“言”是“意”的工具与途径。但从当代文学评论理论出发,从“言”到“意”并非这样简单。学者蒋寅在其《语象·物象·意象·意境》一文中提出,从“言”到“意”的思维路径层次:语象、意象、意境。
“语象”是构成诗歌的基本素材,与外界事物、内在感受相对应。“语象”侧重于诗句的品味,包括音韵节奏在内的修辞分析。如张继《枫桥夜泊》中的落月、啼乌、寒霜、江枫、渔火,我们习惯称其为“意象”。教学时,教师常设计如此提问:看到什么,听到什么。但这些“象”脱离了诗歌,仅是一个个自然物的呈现,教师只能算是“语象”。教师只有把这些“语象”合在一起,放到诗歌中,才能使其成为一幅有张力的图画,并以此衬托出诗人的孤寂与悲苦。因此,被理解为“意中之象”的“意象”实际上融入了作者的主观情感,“语象”组成的画面才能被称为“意象”。厘清了“语象”与“意象”,我们就发现一些诗词教学由所谓的“意象”入手,因层层分析造成了支离破碎,这于诗歌学习而言毫无意义。
从“言”到“意”的第三个层次是“意境”。叶朗先生认为,意境是“超越具体的、有限的物象、事件、场景,进入无限的时间和空间,即所谓‘胸罗宇宙,思接千古’,从而对整个人生、历史、宇宙获得一种哲理性的感受和领悟”。
中国古典诗词,使用凝练、优美的语言展现复杂丰富的精神世界。从创作角度来讲,诗人用“语象”组合成“意象”,再通过凝练的“意象”展现自己丰富的精神世界,此为“意境”。如辛弃疾的《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意象”画面呈现出诗人对历史英雄人物的缅怀和崇敬,但作者的原初本意,是表达自己郁郁不得的家国大志。从读者的角度来看,是通过对“意象”的解读感受,逐步领会诗歌“境界”的表达,甚至以此为点,生发出与之有关的联想体验。无论从创作角度还是从鉴赏角度,“意境”都是超越表面的“言”而存在的精神层面的美学追求,也是当下儿童学习古典诗词的重要意义。这种追求与意义,使偏执地追求语感与积累而“不求甚解”的诵读课堂显得苍白而单薄。儿童对于“意境”的理解并非一窍不通,只是与大人相比,所显示的问题层次较浅。
从“言”到“意”的思维路径,反映了构成诗歌本身的结构层次,弄清楚它们,会使儿童诗歌教学更具条理,目标也更明确。
三、终:由言入意的价值回归
很多人认为,精神世界所属的“意境”是无法言说的意会,对于儿童来说更困难,但事实并非如此。所谓的“意会”,只是不好言说充分、难以言说清晰的内容。庄子就此难题想了好多办法,如“寓言”。古典诗词从“言”到“意”则更多地寄托于“语象”,以及由其组成的“意象”。这与庄子的“寓言”不谋而合,都是言此说彼,通过可言说的“象”,领会精神世界的“意”。
这些意象化的言语方式,恰巧与儿童学习活动的本质相吻合。最有效、有意义的学习,就是在对学习内容的体验感悟中发生的。儿童用身心感知诗歌的情感意蕴,感知世界万物,在感同身受的同时,将其转化为生活和学习经验积累。所以,循着从“语象”到“意象”再到“意境”的思维路径,教师可以带着儿童找到古典诗词的魅力之源。
(一)在“语象”的审视中“整体感知”
语言是阅读的起点,子曰:“圣人立象以尽意。”说明对“意”的领会必须从“言”开始。通过“语象”组合而成的“意象”,对诗词进行整体感知,有助于把握“言”所表达的“意”,直击诗词表达的重点,这也是训练阅读素养的有效途径之一。
古典诗词表达含蓄、意义深远,不如白话文浅显直白。儿童拿到一首古诗,首先会对诗歌语言所表达的意义进行初步理解与猜测。这种活动产生于文字表情达意的基本功能,是阅读的必然活动,也是儿童的自觉。但这种猜测式的理解是建立在儿童尚未成熟的知识积累之上的,因此,这种感知非常浅显,也有偏差。
所幸的是,古典诗词语言凝练的另一特点是短小精悍,特别是儿童学习的内容,篇幅短小,有利于其进行整体感知。所以,教师可以引导儿童从“语象”建立起来的“意象”中找到蛛丝马迹,由此推断诗歌的整体基调:愉快、悲伤、有趣、优美……如张继的《枫桥夜泊》:“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一个“愁”字就能让儿童推测出此诗的基调是悲伤。再如孟浩然的《春晓》,前两句中“不觉晓”与“闻啼鸟”让儿童知道早起的愉悦,后两句中“花落”让儿童知道诗人的心情有点小失落,由此推断此诗的情感走向。
诗词教学之初,让儿童通过“语象”先行整体把握,有效避免了逐个分析理解导致的支离破碎,让诗歌以完整的面貌出现在儿童面前,保持了诗歌“意”之表达的荡气回肠。于此,儿童才能进一步以“言”作踏板,跳出“言”的束缚,感受“意”的自由,从而真正抓住诗词的学习重点。
(二)在“意象”的观照中“感同身受”
“意象”是作者的心灵观照。人的阅读活动,离不开心灵参与。只有全身心思考与体验,才能让阅读向纵深推进,从而发挥出最大价值,这是阅读追求的最高目标。“言”的表层感知是意义把握的浅层活动,体验式的“感同身受”,才是心之“意象”的深层观照。
对于一首诗歌,阅读者根据语言描述,通过想象对其进行勾勒:画面、场景、动态……将语言联想观照产生的情感共鸣留存心中,形成“意象”。儿童根据诗歌意象,在心中勾勒出相应画面,产生相应的情感体验,从而达成对“意”的领会。那么,如何达成对“意”的领会?
首先,要有联想的意识和习惯。联想是阅读要培养的能力之一。有的诗歌浅显,儿童很容易就能理解诗歌的浅层意义,此时对“意”的领悟只需更进一步。如高鼎写儿童的《村居》,很是浅显易懂,但如果联想到自己放学后,与伙伴在小区里玩耍的情景,定会有不同的感受。在诗词教学中,教师要引导儿童多加联想:读到这个,你想到了什么?在反复有意的训练中,儿童会逐步拥有“联想”的自觉和习惯,对“意”的领悟也会自然而生。
其次,要营造诗歌“意象”体验的“场”。儿童“意”的领悟并非都要在教师语言引导之下,可以是一种更为巧妙的自由生发。如张志和的《渔歌子》,整首词描摹了一幅悠然自得的山水画卷,“意象”众多、古朴质雅。如果对“意象”逐层推断,学生没有体验感悟的回答最多是教师想要的答案,并非身心投入的“感同身受”。因此,教师可在学习之初用一段意境深远的音乐或者水墨动画营造“意境”的场,让儿童在这“场”中诵读、品味,引导儿童在脑海里将诗歌所描写的情景描摹出来,感受各种“意象”错落有致、相映成趣,同时从整体意境出发,体验斜风细雨中渔翁垂钓的闲情悠然。此时,儿童作为学习主体进行“意会”,由此而得的体验与表达源于自身的“感同身受”,教师的大多数语言反而显得苍白多余。
(三)在“意境”的领悟中“更进一层”
“意境”是诗歌的最高追求,“诗以言志”的观点为历代文人所赞同。古典诗词,乃至古典文学,都在庄子的“言意”论影响下,形成了独特的美学追求,意在言外、含蓄隽永的表达方式成为古典诗词的“言意”特色,“志”藏诗中,“意”在言外。
比较典型的是辛弃疾的《清平乐·村居》。此首词描摹的是一幅闲情淡雅的田园生活,词中的人、景、物组成的意象画面有声有色,富有生活情趣。学生初看,整首词基调平和悠然,再对照辛弃疾的生平,就会有不同的发现。南宋偏安一隅,大片故土犹在金人铁蹄之下,作者心有壮志却难酬,苦闷不言而喻。这样有远大抱负的人,如何能安心惬意地过着田园生活?由此,学生的理解更进一层:由“醉里吴音相媚好”推断,此时辛弃疾想起自己郁郁不得志,或许也在饮酒,但只为消愁。醉眼朦胧中,诗人看着其乐融融的生活画卷,复杂的情感使其想要报国却不得的苦闷精神世界到达崩溃的边缘,眼中不知是笑是泪。学生由“言”入“意”,走进作者内心,体会到隐藏在文中的“笑着哭”的悲凉与无奈。至此,整首词的意境由普通生活画卷升华到家国抱负层次,学生理解由表面“语象”更进一层,深入诗词背后包含的“意”,领悟更为广阔与深刻。
诗歌的诞生,即为表情达意。古典诗词已经融入每个中国人的血脉之中。优秀的古典诗词,寄托了诗人的一生抱负与满腔情谊。我们只有走进诗歌意境之“场”,走进诗人的内心世界,才能有“感同身受”的情感体验。优秀古典诗词,还是古代文人浪漫情怀与精神追求的集中体现,它给予我们的,既有言语意境的优雅审美,又有其中所体现的整个民族的精神与气质。儿童学习古典诗词的最终目的,不正是吸收这些向上的力量,从而塑造自身的精神气质、指明人生的正确走向吗?将这些言与意传递给儿童,才是诗词学习、文化传承的终极目的与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