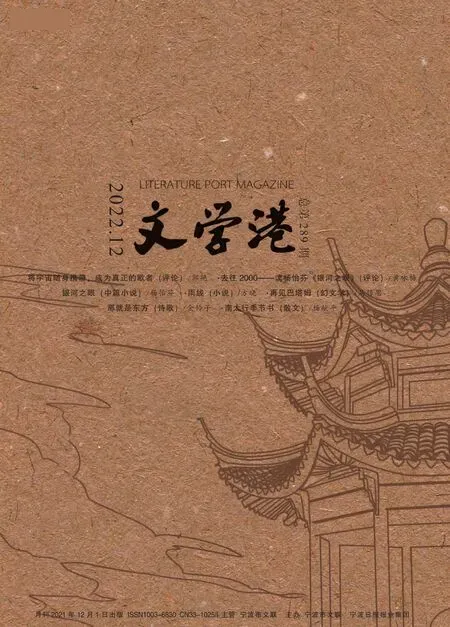寻找阿格隆
□王征雁
刚放寒假的第二天,小强收拾好自己的随身物品,火急火燎地赶往爷爷家。爸爸工作调动搬到城里后,他只有寒暑假才能到爷爷家住上一阵子。
客车在铺满积雪的山路上缓慢行驶着。窗玻璃上,结了一层厚厚的冰霜,小强看不到车外的景物,更不知道车已行至哪里。他将嘴巴努向车窗,哈上两口气,把脸贴过去,细细地看着。他看到了起伏的山峦,但又好像什么也没看到,脑海里一直浮现着,一只只狍子,在奔跑着;一长队野猪正横穿冰河;一头罕达犴,正昂举着华美的犴角,凝望着远方……这破车,咋就这么慢呢?
到了爷爷家,天色已晚,爷爷正弓着身子,在院子里卸雪橇,一看就是刚刚出围回来。黑豹、花子和其他两条猎狗正围着狗槽吃食,唯不见他最宠爱的阿格隆,便问: “爷爷,阿格隆哪去了?”爷爷叹口气,摆摆手: “先进屋吧!”这时候,奶奶隔着窗子看到了孙子的身影,乐颠颠地跑出来: “哎哟,小强回来了,快过来让奶奶看看。”她拉起小强的手,乐得满脸皱纹堆了起来: “哟,又长高了,都成大人了!”说着,就拉着小强往屋里走:“咱进屋去,奶奶给你炖野猪肉,正新鲜着呢!”
吃饭时,爷爷才告诉小强: “阿格隆失踪了,是为追赶一头孤猪失踪的。你知道,阿格隆就是条犟狗,比驴还犟,十头牛也拉不住呀!昨天傍晚,正在回家的途中,偏偏遇到了一头孤猪,平时也就罢了,可咱着急回家呀!你那阿格隆却像中邪了,根本不听指令,箭一般射出去了,几遍口哨都唤不回来。没办法,我只好跟着足印追了过去。后来,天渐渐黑了,只好借着月光,猫着身子,察看着蹄印往前追。到了下半夜,林子里的风越刮越大,雪面上的蹄印就再也看不见了。”爷爷叹了口气,接着说: “到了早晨,又转了好几个时辰,到底也没找到,唉——”
小强知道,爷爷也格外喜欢阿格隆,但凡有一线希望,他是不会放弃的。饭后,小强说: “活要见狗,死要见尸。爷爷,我明天再去找找。”
爷爷没吱声,两只脚在热水盆里上下揉搓着,好像在权衡和掂量。小强清楚地看到,爷爷的脚脖子肿了。半天,爷爷才盯着小强说: “那就早点睡吧。”
小强躺在隔壁的热炕头上,清楚听到奶奶和爷爷的对话: “你就这么放心呀!万一有个闪失,看你咋向儿子儿媳交代!”静了一会儿,又听奶奶说道: “别看个头不小,毕竟还是个16岁的孩子呀!”爷爷显然不耐烦了:“你个老婆子叨叨啥,孙子啥样我知道!”爷爷可能意识到了自己的蛮横,接着,又把语气平缓下来: “老婆子,你就把心好好放在肚子里,安安稳稳地睡觉吧……嘿嘿,我有数着呢。”之后,便沉静下来,只有窗外的星星眨着冰晶似的眼睛。其实,爷爷是对的。小强自小跟着爷爷长大,无论枪法,还是意志力,爷爷看得一清二楚。
在爷爷火车轰鸣般的鼾声里,小强失眠了。阿格隆从小就是他喂大的,它跟小强最亲,平时也最听小强的话。可有时候,它又有一股子犟劲儿:面对野兽,分外眼红,心中根本没有生死概念,贸然出击,屡屡犯错,正像阿尔巴尼亚电影《地下游击队》里的那句台词: “阿格隆不是第一次犯这样的错误了!”因此,小强才给它起了个外国名字——“阿格隆”。它对主人的忠诚,对野兽的凶悍,以及在战斗中的机警,较之于黑豹和花子,却有过之而无不及。
前年冬天,他趁爷爷外出不在家,带着五条猎狗进山了。在朝阳的一个山坡上,跑在前面的群狗汪汪地狂吠起来,他快步赶过去,只见一头孤猪被狗群圈了起来。他将手指伸进嘴里, “啾、啾——”打了两声口哨,狗群迅速向两侧闪开,他瞄准孤猪,扣动了扳机,“砰”的一声,孤猪只是身子一晃,紧接着就向他冲来,群狗重又围了上去,却见那孤猪獠牙左右开挑,让猎狗阻挡不得,像一辆所向披靡的坦克,披荆斩棘,隆隆开来,雪地上卷起一团白色雪雾,后面则是一道长长的血痕。小强稍一惊诧,又射出了第二发子弹,可这一枪却打在了孤猪的前腿上。它身子一歪,差一点跪下,但接着,还是挥着两把一尺多长的獠牙刀,冲到了眼前!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阿格隆就像一支利箭,从猪身上飞跃过来,挡在了孤猪面前。孤猪将一柄闪亮的獠牙向阿格隆挑去,却见阿格隆身子一歪,獠牙挑在它的耳根子上,将它一下子撩出三四米开外。黑豹则死死咬住了孤猪的尾巴根子不松口,孤猪猛一甩臀,整条尾巴就留在了黑豹嘴里。就在孤猪摆脱了猎狗的那一刻,小强的枪口已对准了孤猪的头颅,他立刻扣动扳机,可他心里一颤:坏了,哑火!他根本来不及退膛,就地打滚儿,躲到了一棵粗大的白桦树下。孤猪见攻击不成,自己又有伤痛在身,便不再恋战,一瘸一拐地向密林深处逃去,但速度仍然很快。狗群撒腿追赶,小强赶紧吹响了口哨,把它们收拢了回来。心想,穷寇莫追。若再次对阵,孤猪必定穷凶极恶。到那时,自己非但没有完胜把握,也错过了这全身而退的时机。从此,阿格隆的右耳朵,就分成了两半儿……
明天,不管阿格隆是死是活,必须进山去找,哪怕找到的是具狗尸,也绝不能让它葬身于冰雪之下,更不能让它被野兽分尸果腹。
一大早,爷爷便忙碌起来。他把米袋、干粮、犴肉干、酱野猪肉、军用水壶、猎刀猎斧、熊皮睡袋,还有那口被烟火熏烤得黢黑、到处坑坑洼洼的小铝锅,凡打猎和宿营用到的,一样不少地全装到了雪橇上。其实,放小强一个人进山,他既担心,又高兴:孩子不能总放在手心里捧着,该让他见见世面,这样才能成材。山里有名的猎手,哪个没有一身过硬的本领?哪个没有一个山谷一样的胸怀?这可都是经过痛苦的摔打和出生入死的搏斗练出来的。如果小强此次能够战胜可能出现的所有困苦和艰险,他不仅可以成为一个真正的猎手,更重要的是,在今后的人生道路上,他就不会有吃不了的困苦,不再有克服不了的艰难。这样想着,越是觉得自己的决定无比正确。
小强刚刚撂下碗筷,就去换上了牛皮靰鞡,披上狍皮大衣,戴上狐皮帽子,很快武装齐备,雄赳赳、气昂昂的样子,俨然闯荡山林的老猎手。爷爷先把四条猎狗套在雪橇上,又回屋从墙上摘下那支半自动步枪,再把军刺安上,这才递给了小强: “你不是最喜欢这支半自动吗?今天就交给你了。爷爷答应了你独自进山,你也要答应爷爷一个要求:进山的目的是寻找阿格隆,最好不跟野兽纠缠,尤其是那些恶兽,安全最重要。”小强高兴地答应着:“爷爷放心,我知道怎么保护自己,保证安全归来!”爷爷笑了,向大山方向努了努下巴,小强便驾着雪橇出发了。爷爷看了看天,皱了皱眉,今晚十有八九会有一场暴风雪。
四条猎狗,又高又大,简直就像四头小牛犊。它们一定是嗅到了山林里飘来的诱人气味,十分卖力地拉着雪橇在积雪的山路上奔驰着。飞扬的四蹄,刨起团团雪雾。山是白的,树是白的,路也是白的,就像白色的梦境一般。
树林越来越密,山路已到了尽头,狗拉雪橇也越发吃力了。小强知道,前面有一面陡峭的山崖,崖底有一座很小的木刻楞小屋,在那里扎营,该是最佳选择。于是,又前行一段距离,便在木屋前停下来。小小木屋,玲珑得就像一个玩具,更像是童话里小熊小兔的家。爷爷说,它是从前一个孤独的老猎人搭建的,采用的全是红松木料。老猎人虽然早已作古,但小木屋却依然坚固,一根根松木,可能饱含着太多松脂,以至风雨不侵,虫蚁不蠹,如同老猎人的骨头,始终不朽不烂。爷爷说过,就是山崖坍塌把它埋入地下,它也只会成为化石变得更加坚硬。也许这里窝风的缘故,木屋后侧堆满了厚厚的积雪,一直堆向半面崖壁,整座屋子,竟有小半掩埋其中,如同深嵌在冰山里。山风真的是个神奇的家伙呀,竟把这么多的雪堆砌到了这里。也好,屋子里不再透风,会更暖和些。他卸下雪橇,将所有东西搬进了木屋里。
爷爷指了指,阿格隆就是在附近出发的。
这小兴安岭北麓的方圆几百里内,每一道山梁,每一道沟沟壑壑,对爷爷来说,就像了解自己的掌纹;他熟悉野猪、狍子、黑熊等各种野兽的习性,就像熟悉自己怀里的孩子。当然,经常跟随爷爷一起出围,他也学到了很多,了解了很多。比如现在,他知道,山坳里有条小溪,各种动物经常在此出没。尤其是鹿群,更喜欢这里的环境,它们常常结队翻过山梁,走下山坡,去溪边饮水。但这里早年设有多处鹿窖,必须格外小心。
他十一岁那年的秋天,爷爷骑马来打猎,他死乞白赖地跟着来了。一进山林,他就像笼子里飞出来的小鸟,活蹦乱跳地跟着猎狗往密林里钻。爷爷在后面只喊: “慢点呀,小心鹿窖!”他以为爷爷在唬他,还是一阵风似地跑着。忽然,脚底一下踩空,整个人就哗啦一下子掉进了三米多深的鹿窖里。他定神一看,窖里还有一头野猪, “嚯、嚯”地叫着,两只黑亮的眼睛瞪着它,身子一躬,正准备向他扑来……之后,他就什么也不知道了,脑袋里一片空白。等醒过神来,已经坐在鹿窖上面的边缘上,低头一看,那猪还在仰着头, “嚯、嚯”地看着他叫唤。他不知是后怕还是委屈,放声大哭起来。这时爷爷已来到跟前,知道他掉入窖里后,便疑惑地问他是怎么上来的,他却什么都不知道。或许,人在特别危急时刻,往往会爆发出深埋在机体中的潜能,在直觉和本能的指令下,他竟扒着直上直下的窖壁,像壁虎一样爬上来了,他两手沾满的泥沙,足可作为这种判断的依据;也许,是那野猪帮助了他,本想出于自卫,向他拱来,长嘴一撅,却恰好把他挑飞到窖外。爷爷摸着他的头顶: “摸摸毛,不吓着。”见他还在抽泣,又笑着说:“好了好了,别哭了。这不没啥事嘛。幸亏是头小猪,还没长獠牙,要是一头大猪或孤猪,你这条小命儿就很难说喽!”
如果说鹿窖脱险是小强的侥幸,那么,再次躲过野猪的攻击,完全就是凭借他自己的机灵劲儿了。
前年冬天,他随爷爷出围,走在大雪覆盖的山坡上。爷爷端着半自动,靠近山顶些;小强则端着双筒猎枪,走在山二肋上。黑豹带着阿格隆、花子等五条猎狗走在最前面。忽然,狗群越过山脊,跑向了山背坡。不一会儿,就传来了猎狗的狂吠,爷爷本就靠近山脊,很快就追了过去。等小强就要跑到山顶时,却见一头半大野猪翻过山脊,与他面对面猛冲下来。猪群显然被猎狗冲散了,惊慌中,这头野猪选择了爬坡翻山逃脱的路径。小强还没来得及举枪,野猪已风驰电掣般冲到了他眼前儿!就在这十分危急的时刻,他两腿原地一跳、一劈,那猪竟从他胯下冲过去了。也许是惯性,也许那猪只是逃命,根本就没有攻击他的意思,接着就继续冲向坡下。小强掉过枪口,砰的一枪,那猪即刻倒下了。这时候,爷爷用绳子拖着一头野猪,翻过山脊,走过来了。听小强说起刚才的险情,爷爷哈哈大笑: “好样的!不然,我孙子两个小蛋蛋可就被野猪拱爆了,以后咋娶媳妇嘛!”
小强和四条猎狗在山坡上搜寻半天,没发现一丝踪迹。他向山上攀去。翻过山顶,进入山谷,又上了一个山坡,再进入一道草炭沟,还是毫无收获。他在一棵风倒木上坐下来,这才感到身上黏黏的,摘下皮帽子,头顶立刻升起了一团子白雾。这时,树梢摇动起来,幅度越来越大,很快就吹起了口哨,像怪兽的嘶鸣。抬头看天,天空变得有些苍茫,太阳就像正在溶解的冰片,越来越薄,正向着西山顶滑落。山里的冬夜可是说来就来的。小强站起身,决定马上返回营地,明天再继续寻找。
刚回走不远,就要攀上山梁时,只见一只狍子刚好翻过山梁,好像受到了惊扰,向这边坡下狂奔而来。这时,狍子也看到了他和猎狗,扭头就向另一侧跑。猎狗早已疯了一般围了过去,前后左右将狍子包围起来,汪汪汪地狂吠着。小强吹了一声尖啸的口哨,四条狗闻声迅速散开,只听砰的一声,狍子晃了晃,倒下了。狗群立刻猛扑上去,见其并没断气,便个个咬向它的要害。小强抽出猎刀,笨拙地将狍子胸膛剖开,掏出下水,奖赏给了四条猎狗。直等到它们饱餐结束,他才扛起狍子,继续赶路。就在翻过山梁走到半坡时,小强发现了一行脚印,心里顿生狐疑:这脚印与狍印重合,显然是追踪狍子留下的,却为何没看到人影?而且只追到半山坡,便突然拐向另一个方向,向着大山更远处走去了。

一定是他发现了我,不是听到了狗吠,便是听到了枪声,知道物有所属,便悻悻离去了。这真的是来得早不如来得巧啊!不过,他也真是个独来独往、影只行单的家伙,天都这个时候了,还要去哪里?不然,我俩完全可以共进晚餐,饱餐一顿狍子肉的,之后,再挤到小木屋的床上唠嗑,说不定还能进入同一个神奇的猎梦呢!
返回小木屋,风刮得更大了,并夹带着零星雪粒,打在脸上,生疼。远处,好像有千万匹马在奔腾,轰轰的声音跨过左右山梁,汇聚在山谷里,朝这边滚滚而来。小强心里一阵打颤——暴风雪就要来了!
趁天还没有完全黑下来,他要去下面不远处的小溪里打水。那里有个“青眼”,再冷的冬天都没有冻住过。爷爷说,无论大江大河,还是这小溪,都会有这样的“青眼”,就像下围棋一样,总要作两个“眼”、留两口“气”,不然,这棋子很可能就成了死棋。小强听不懂:难道水流也会喘气?没有这“青眼”,它们就会在冰层的封闭中憋死?不明白。
木屋里没有灶台,小强找来几块石头,架起铝锅,一个锅灶便形成了。铝锅里冒出腾腾热气,一股子肉香和烟火味弥漫了整个木屋。屋外,传来一阵阵磅礴的风声。雪,绝不是在落、在飘,而像无数疯狂盲目的飞蛾,在黑暗中急切地寻觅着哪怕星点儿火光,漫天里飞扬跋扈,恣意妄为,直搅得没天没地,没山没树,把这雪夜,塞进了一个狂躁、混沌的世界。可这一切,都关在屋外,屋里狭小的空间,在烛光里反倒显得格外宁静。
小强一边嚼着狍子肉,一边在思考:阿格隆追击孤猪,到底跑向了哪里?他知道,这并不取决于阿格隆,而是取决于孤猪。他努力回忆着从前看到的野猪逃窜的场景,回忆着爷爷经常说起的,有关野猪的生活习性,为自己的判断寻找依据和线索。直到钻进熊皮睡袋里,他还在琢磨,明天到底选择哪一条寻找路线呢?就这样翻来覆去地想着,朦胧中,他已站在一个晶莹剔透的水晶宫里,阿格隆摇着尾巴跑过来,带他去寻找可以出去的地方。他和阿格隆在水晶宫里转来转去,就是找不到出口……
大概半夜时分,他听到轰隆一声,几条猎狗也不知其然,跟着叫了几声。小强睁开眼,见屋子里一片漆黑,猎狗也不再作声,自己就在熊皮睡袋里翻了个身,接着睡着了。
一觉醒来,屋子里仍然漆黑一团,怎么回事,天还没亮吗?他伸手摸过火柴,点燃蜡烛,往窗口一看,贴在玻璃上的竟是一堵雪墙。他赶紧披上狍皮大衣,穿上牛皮靰鞡,下地拉开板门,却见从上到下整个门口也被一座雪墙堵住了。他想,暴风雪再大,也不至于大到这种程度,昨晚那一声轰隆,定是岩壁上的积雪坍塌下来,把小木屋整体掩埋了。不行,必须赶紧冲出去,时间一久,小屋里必然缺氧。他用脚使劲踹向雪墙,却只留下一个雪窝;又侧着身子用肩膀撞去,还是只留下一个肩形的雪坑。这雪经过沉积,已经压实压硬,以他的身体,无论如何也是无法撞开的。他开始用猎刀挖雪,身后很快就堆起一个雪堆。挖累了,想休息一会儿,没想到黑豹冲上去了,两只前爪迅速扒挠着,就像一个正在打洞的土拨鼠。之后,花子和其他两条猎狗也轮番挖洞,屋地上的雪堆越来越高。
雪洞终于挖通了,四条狗一字儿钻了出去,小强趴在地上顺着雪洞往外一看,洞口像蒙了一层薄膜,天已经大亮,大风在洞口吹出呜呜的叫声。他爬出来站起身,回头一看,整个小木屋完全埋没了。但正对窗口的位置,却有一道深沟,尤其是在接近房檐的窗玻璃处,已经挖开了一个缺口。他爬上去用手轻轻扒拉几下,便露出了玻璃,贴在上面,就可看见屋里。这层软雪显然是后来覆盖上的,可这雪沟又是谁留下的呢?他扒开窗口,究竟偷窥什么?周边一个脚印也没有,即使有,也早被风雪掩埋了。
风雪丝毫没有停歇的意思。山峰、山谷、树木、天空,浑然一色,茫茫苍苍。都说“风三儿”,一刮就是三天呢。小强搓了搓手,不能等,也等不起,要继续去找阿格隆。他背着枪,带着猎狗,走进了暴风雪里。
这是一片平缓的山坡,坡上多是些柞树,偶尔也有些灌木。枯红的柞树叶子不时地被风刀剪掉,在林子里伴着雪片横飞;仍死死咬定枝头的,就在风雪中狂舞着,发出哗哗的奏鸣。
猎狗突然狂叫起来,小强透过雪雾,只见十几只群狼正守在前面。在这样的天气,能见度不过二三十米,而且,狗和狼的嗅觉都已大打折扣,一旦遭遇,血战必定已在眼前。小强紧闭双唇,吹出 “噗、噗”的声音,指令猎狗,安静下来、勿急勿躁。群狼一个个蹲在前面,并不上前攻击。尽管雪雾弥漫,却遮挡不住它们那橙黄的眼睛所发射出的凶光,比这狂风还锋利,比这天气还阴冷。
这是一群饿狼。狼皮包裹着狼骨,棱角分明,就要支棱出来一般。一杆枪,四条狗,要对付十几只饿狼,其危险性不言而喻,尤其对狩猎经验并不丰富的小强来说。他听爷爷说过,饿狼最狠、最凶。可一旦有了食物,它又轻易不去招惹人。还说,在极端境况下,狼群里一旦有只同伴受伤或死去,这群狼会毫不犹豫地上去将其肢解、吃掉。这时,坐立狼群中间的那只狼,左右环顾一下,仰起头,对着茫茫天空,发出一声长嚎,阴森而凄厉,摄人心魄。它一定就是头狼了。它这声嚎叫,发出的是什么指令呢?稍顷,只见饿狼纷纷站了起来。不好,它们就要发起攻击了!小强不再犹豫,瞄准头狼,立刻扣动了扳机, “砰!”头狼就像一只空瘪的口袋,一下子倒了下去。这时,奇异的场景出现了,也正应了爷爷所讲的,一群饿狼毫不犹豫地围上去,争抢着将它们的首领肢解了!不一会儿,雪地上只剩下了一堆骨头。饿狼们向小强这边看了看,扭头向暴风雪深处走去。都说动物不食同类,那要看到了哪一步境地,尤其对狼来说,骨子里的凶残与狠毒,可是与生俱来的。
危险解除了。
小强继续寻找阿格隆。他行进得很吃力,每走一步,须把腿抬得很高,不然,就会蹚雪,徒增阻碍,耗费更多能量和体力。猎狗的肚皮已经贴在了雪面上,行进中必须一蹿一蹿的,向山顶跋涉着。
昨晚,小强模拟了多条路线,一再权衡,最终还是优选了这一条。尽管如此,他心里明白,这也无异于大海捞针。大雪覆盖,肉眼怎能看到雪层下面?寻找阿格隆的神器,本来是猎狗的鼻子,可这么大的风雪,无疑削弱了它们的嗅觉灵敏度。可想归想,他的信心并没有动摇,他相信,奇迹往往就在艰苦卓绝的坚持中出现。他不由地加快了步子。登上山顶,已是中午时分。他清理开脚下的积雪,露出一小片空地,找来一抱干树枝点燃,在怀里掏出几个馒头,穿在树枝上,伸进火中烤了起来。这就是午餐了,他吃,狗也吃。
山的背面,坡陡涧深,不会是野猪逃跑的去向。他指挥猎狗沿着山梁前寻。山梁上风急,落雪大多被卷走了,雪层相对薄了许多。眨眼工夫,四条猎狗就跑没了影儿。他只好加快步伐。黑豹忽然跑了回来,一边跑着,还一边汪汪地叫着,一副兴奋的样子。来到跟前儿,叼着他的袖子向前扯了扯。他也顿然兴奋起来:黑豹是回来报信的,不敢说已经找到了阿格隆,最起码也是发现了重大线索。黑豹带他来到一棵白桦树旁,停下了。他这才看到,树干根部,已被鲜血染红,就像一条白皙的长腿,脚上穿了一只高靿红靴子。这里面一定有阿格隆的血,以黑豹的嗅觉,一定不会辨别有误。这一定是在阿格隆与孤猪生死对决中,轮番以这棵白桦为掩体,展开了一场惨烈的厮杀。
花子汪汪叫着,又在更远处跑回来了,见小强和黑豹迎着跑过去,它又掉头往回跑,还不时地回头看看。跑了一会儿,只见不远处,另两条狗正一左一右蹲守在那里。小强到了跟前一看,两具尸体,一前一后,半埋雪中;一个是阿格隆,另一个,是没有尾巴的孤猪。阿格隆脖子被挑开了一道口子,胸侧也被挑开了,身子下面,结了一层血冰,红红的; “秃尾巴”肚子上也有一道口子,肠子淌在雪地上有一米多长,冻成了一根冰棍儿。狗和猪,一字儿摆开,早就冻成了冰坨,凝固成了一个破折号。只是,阿格隆仍咬着“秃尾巴”的一条后腿,两个冤家,至死也紧紧拴在一起。
小强抚摸着阿格隆光滑的皮毛,眼泪汹涌而出。他缓缓站起来,从肩上摘下枪,走到“秃尾巴”跟前,用枪刺狠狠扎了两下,硬邦邦的却没扎动,便举枪对向天空, “砰、砰”放了两枪。好半天,他的情绪才平复下来。他抽出别在腰间的猎斧,砍断阿格隆嘴里咬着的猪腿,把阿格隆抱起来扛在肩上,往回走。
四条猎狗跑得很欢实。小强却很吃力,本就顶风冒雪,脚下又蹚着一尺多厚的积雪,肩上还扛着阿格隆,早已气喘吁吁,汗水淋漓,狐皮帽子的一圈,挂满霜雪,就连他的眼睫,也成了白的。在一根粗大的朽木跟前儿,他停下了脚步,把阿格隆放下来,用脚将木头上的雪刮去,一屁股坐了上去。这是一个山边子,地势较为平缓,四处为混交林,多为柞树、杨树、桦树和水曲柳等,树下没有更多的幼树及灌木,显得空旷许多。风雪也突然变小了,树梢虽然还在摇动,却没了呼啸声,林子里难得安静下来。小强捧起一把雪塞进嘴里,还没化净便咽了下去,胸口顿觉凉凉的。他盘算着,以这个速度,赶到小木屋,怕是要天黑了,要回家,只好等到明天。不管怎样,找到了阿格隆,对自己、对爷爷,总算有了个交代,尽管只是一具尸体。
其实,这个结果,前天晚上吃饭时,他和爷爷都已料到,只是谁也没有说破而已。
前方传来猎狗急促的叫声,这是发现野兽的讯号。他赶紧扛起阿格隆,跑了过去。
原来,猎狗发现了一个鹿窖,窖里掉下去一头黑熊,四条猎狗围着鹿窖直转圈,急得呜呜直叫。这家伙真的倒霉,大冬天的不好好趴在洞里蹲仓,跑到这里干什么?也好,这可是送上门来的礼物,四只熊掌正好给爷爷补补身子。这头黑熊足有七八百斤,在三米多深的鹿窖里急得团团转,尤其是见猎狗探头探脑,更是火冒三丈。它一会儿直立起来扒着窖壁乱抓一气,一会儿又坐下来仰着头向着窖口咆哮,以森林之王的神威,给猎狗以恐吓。可它再威猛彪悍,毕竟是一头困兽,他完全可以将其一枪毙命。可是,这么一头巨熊,他无论如何是弄不上来的,就连自己,一旦下到窖底,再想上来也是很麻烦的事情。
“有办法了!”他摘下步枪,立在一棵小树边,想了想,又拿起来,关上保险后重又立在那里。他拔出腰里的猎斧,走到一棵又高又直的黑桦下面,正要砍,又考虑到黑桦发软,不利于黑熊攀爬;旁边是一棵挺拔的山杨,树干够粗够长,可杨树的躯干发脆,韧性较差,易折;他又向另一棵大树看去,那是一颗水曲柳,碗口般粗细,正合适。他挥斧砍伐起来,歇了两气儿,才将其砍倒。去其枝杈,截成四米多件子,扛到窖边,小心翼翼地把它出溜下去,一头戳在窖底的壁根,另一头斜搭在窖沿上,之后,端起枪迅速跑出三十多米外,赶紧把枪架在了树杈上。通过准星,向窖口上侧瞄过去,位置正好。
不一会儿,黑熊便露出了脑袋,接着,两只前掌和前半身已搭到窖沿上。他还在等,并不开枪,必须等到黑熊四掌落地,否则,它会重新掉进窖里。这时,无意间,眼睛的余光看到右前山坡上好像有个人影,但又更像是个黑树桩,树桩上还横出一截子干树枝。但他没去细瞅,他必须全神贯注地盯向窖口。黑熊完全出来了。四条猎狗立刻围了过去,狂叫着。他打了个口哨,猎狗向两侧散开了,他对着黑熊的头颅扣动扳机,指下却硬硬的,没有扣动。坏了,是冻住了吧?再用力扣了一下,还是没有扣动!他慌了,赶紧把枪侧过来,一看,原来保险还关着。多么低级的错误啊!他赶忙打开保险, “砰——”匆忙中,他再次扣动了扳机。或许,心理受到刚才过错的影响,使他的击发状态发生了微妙变化,直觉告诉他,这一枪没有打中要害。可是,令他意外的是,黑熊摇晃了几下身子,接着,就慢慢地瘫倒了。猎狗立刻围上去,有的掐脖子,有的掏肚子。可黑熊一点反应也没有,他这才确认,黑熊一定被打死了,便放心地走了过去。
突然,黑熊又爬了起来,前掌顺势在雪底抠起一把干树叶,塞住了肚子上的伤口,朝着他狂奔过来。慌乱中,他急忙又开一枪,却根本没有打中,黑熊只是一怔,接着又向他扑来。
这时,黑豹箭一般飞过来,拦在了黑熊前面,黑熊抬起熊掌只是一拨,黑豹便滚出六七米开外。情急中,他正要躲到一棵老柞树后面避险,可脚下一绊,身子仰在了雪地上。所幸枪还在手里,赶紧把枪立了起来,手指搭在了扳机上。此刻,黑熊已站立在他脚边,只要扑下来,他必被碾压成一张肉饼。就在这千钧一发、命悬一线之际, “砰!” “砰!”两枪几乎在同一时刻扣响了!第一枪从侧面射进了熊颅,第二枪从下方射进了黑熊的月牙白。黑熊凝固了足足有好几秒钟,之后,才对着枪口趴下来,枪刺深深扎进了它的胸膛;然后,就像一座黑山,向一侧坍塌下去。他爬起来,摸摸脑袋,四处张望,刚才山坡上的那根黑树桩不见了。奇怪,那第一枪是谁打的呢?真的是神来之枪啊!
他正迷惑着,却见爷爷在右边林子里走过来了。他这才恍然大悟,两天来所有疑惑,顿时消释殆尽,向着爷爷奔跑过去。他紧紧抱住爷爷,不知是感激还是嗔怪,撒娇般说道:“爷爷,您一直在跟踪我!”爷爷呵呵笑道:“没有,没有,我这不是刚刚来接应你嘛!”小强又说道: “爷爷,谢谢您救了我!”爷爷摸着他的头说: “傻孩子,怎么是我救了你,是你自己救了自己。你看,你那一枪不正打进了熊的心脏吗?就算不是心脏,你的刺刀也把它捅死了。”
爷爷从身上掰开小强,细细端详着他的脸,又心疼,又欣慰,眼角闪烁出晶莹的光亮,像是嵌着两颗融化了的冰晶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