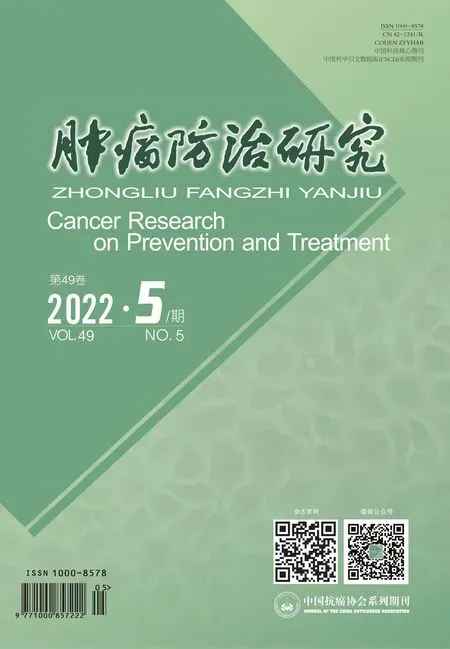免疫检查点抑制剂疗效相关生物标志物的研究进展
杨雯雯,田宏伟,雷彩宁,黄显斌,景武堂,靳川伟,宋绍明,龚世怡,郭天康
0 引言
肿瘤免疫治疗是当前肿瘤治疗领域中有价值的研究方向之一,它主要通过改变机体的免疫系统,增强抗肿瘤免疫力,从而抑制和杀伤肿瘤细胞。免疫检查点抑制剂(immune checkpoint inhibitors,ICIs)是肿瘤免疫治疗中最具代表性的治疗方法。免疫检查点是在主动免疫反应中诱导的一组抑制性分子,作为一种负反馈机制来限制侧枝组织损伤。细胞毒性T淋巴细胞抗原-4(cytotoxic T lymphocyte-associated antigen 4,CTLA-4)和程序性细胞死亡受体1(programmed cell death protein 1,PD-1)是最早确定的免疫检查点,肿瘤细胞利用CTLA-4和PD-1信号逃避免疫监视[1]。因此,用抗体——免疫检查点抑制剂阻断CTLA-4和PD-1可以显著增强肿瘤特异性T细胞激活作用,从而间接达到杀伤肿瘤的作用[2]。然而有研究[3]发现,ICIs对实体瘤的抑制率仅为10%~40%,这表明有很大一部分患者并不能从免疫疗法中获益。此外,ICIs在一些患者中诱发了严重的免疫相关不良事件(immune-related adverse events,irAEs),涉及皮肤、心脏、胃肠道、肝等多个器官,根据肿瘤类别、ICIs的种类和易感性而存在个体差异。因此,寻找决定ICIs临床疗效的预测生物标志物,并设计合理的ICIs与其他治疗药物的联合治疗方案,是增强ICIs整体疗效的关键所在。现就ICIs的作用机制和疗效生物标志物两方面的研究进展进行综述。
1 ICIs的种类和机制
传统的治疗方法通常只针对肿瘤细胞中的特定分子,而ICIs治疗通过抑制免疫检查点的活性,释放肿瘤微环境中的“免疫刹车”,重新激活T细胞对肿瘤的免疫应答,从而达到抗肿瘤的作用。迄今为止,依据肿瘤作用靶点的不同,由FDA批准并用于临床试验的ICIs药物主要分为两大类:靶向细胞毒性T淋巴细胞抗原-4的抗体(CTLA-4i)、靶向程序性细胞死亡受体1(PD-1)及其配体程序性死亡受体配体-1(programmed cell death ligand 1,PD-L1)的抗体(PD-1i和PD-L1i)。目前国内已获批上市的CTLA-4i,包括ipilimumab及tremelimumab,分别应用于晚期黑色素瘤、恶性间皮细胞瘤的治疗。另一组临床广泛应用的PD-1i/PD-L1i主要分为:针对PD-1的单克隆抗体,如nivolumab、pembrolizumab、camrelizumab、cemiplimab、sintilimab、toripalimab、tislelizumab;另一种是针对PD-L1的单克隆抗体,例如atezolizumab、avelumab、durvalumab。PD-1i/PD-L1i治疗已应用于多种恶性肿瘤,包括黑色素瘤、非小细胞肺癌、默克尔细胞癌等。
PD-1i/PD-L1i带来的PD-1信号通路阻断机制,实际上属于免疫正常化治疗。当细胞发生癌变时,抗原呈递细胞将处理癌细胞的抗原并将其传递给T细胞以引起免疫应答。随着抗原不断地刺激,PD-L1可选择性地在癌细胞表面进行高表达,通过与活化的T细胞表面PD-1特异性结合,激活PD-1/PD-L1下游通路,传递负性调节信号,进而导致激活T细胞的凋亡和免疫活性丧失[4-5]。ICIs能针对性地阻断PD-1/PD-L1信号通路,从而解除肿瘤细胞对T细胞的抑制,加强免疫系统对外来肿瘤细胞的识别杀伤作用,达到肿瘤治疗的目的。
与PD-1i/PD-L1i免疫抑制机制不同,CTLA-4i往往带来的是免疫增强作用。CTLA-4是表达在T细胞表面的细胞毒性T淋巴细胞相关蛋白,当其和抗原提呈细胞表面的B7-1(CD80)和B7-2(CD86)结合时,可以竞争性抑制B7与T细胞表面的CD28结合,进而抑制T细胞的激活。CTLA-4i通过抑制CTLA-4分子,使T细胞大量增殖、攻击肿瘤细胞,提高机体免疫细胞杀伤作用[6]。
2 预测ICIs疗效的生物标志物
2.1 肿瘤突变负荷
肿瘤突变负荷(tumor mutation burden,TMB)定义为靶基因编码区每兆碱基替换(包括同义突变)的总数量,即肿瘤基因组去除胚系突变后的体细胞突变总数量。CheckMate 026研究表明,在高TMB(≥243个错义突变)的患者中,与传统化疗药物相比,使用PD-1i nivolumab治疗的无进展生存期(progression-free survival,PFS)和总生存期(overall survival,OS)均显著改善[7]。TMB同时也可以预测PD-L1i的疗效。POPLAR研究分析了血液TMB(bTMB)与临床获益之间的关系。在bTMB≥10、≥16和≥20的患者中,PD-L1i atezolizumab治疗的患者PFS和OS获益增加,其中bTMB≥16的获益最大[8]。CheckMate 227研究[9]结果表明,在TMB≥10的晚期NSCLC患者中,与铂类双联化疗相比,PD-1i nivolumab加低剂量CTLA-4i ipilimumab治疗明显延长了患者1年无进展生存率(42.6%vs.13.2%),PFS也显著延长(7.2月vs.5.4月)。尽管TMB被认为是免疫治疗的一个很好的预测因子,其预测作用可能是条件性的,存在高TMB的患者发生免疫不应答,低TMB的患者反而产生良好免疫效果的情况,明确TMB发挥预测作用的条件至关重要。PD-L1表达水平、HLA基因型、肿瘤基因组中其他结构变异等均值得进一步探索。
2.2 PD-L1表达水平
在目前的临床实践中,PD-L1的检测主要靠免疫组织化学(immunohistochemistry,IHC)。KEYNOTE 024的研究结果表明[10],与传统化疗药物相比,PD-L1高表达(≥50%)的晚期NSCLC患者使用PD-1i pembrolizumab治疗的OS、PFS更好,而当PD-L1表达<50%时,免疫治疗的疗效与传统药物化疗相当。这表明,PD-L1的表达水平越高,NSCLC的免疫治疗效果越好。CheckMate 057研究报道,PD-L1<10%的患者中,PD-1i nivolumab治疗组的OS得到显著改善。在CheckMate 012研究[11]中,PD-1i nivolumab联合CTLA-4i ipilimumab用于治疗晚期NSCLC,PD-L1≥50%的患者有效率高达90%以上。另外,在CheckMate 227研究中,对肿瘤细胞PD-L1表达量<1%的患者随机接受PD-1i nivolumab加CTLA-4i ipilimumab、PD-1i nivolumab加铂类双药化疗或铂类双药化疗单独治疗,结果显示接受PD-1i nivolumab加CTLA-4i ipilimumab的患者中位OS和3年OS分别为17.1月和33%,而接受化疗的患者中位OS和3年OS分别为14.9月和22%,并且ICIs联合方案显著延缓了疾病进展[12]。CheckMate 017和OAK报道,肿瘤细胞中PD-L1的表达水平可能不是预测免疫治疗疗效的合适生物标志物[13-14]。这可能是因为某些信号通路促进了癌细胞的恶性行为,如EGFR、丝裂原活化蛋白激酶(MAPK)和磷脂酰肌醇3激酶蛋白激酶(PI3K AKT)。目前PD-L1检测平台有DAKO和Ventana,推荐检测抗体22C3和28-8采用DAKO检测平台,SP142和SP263采用Ventana检测平台。不同检测平台和评价体系均具有不同的阳性临界值,PD-L1在肿瘤细胞中的表达也没有统一的标准[15]。因此,对于PD-L1表达能力低或缺失及具有高PD-L1表达能力的患者,为使临床获益达到更高,我们更青睐含有ICIs的组合方案以及组织学选择的铂类双药化疗[16]。
2.3 循环肿瘤细胞
近年来,循环肿瘤细胞(circulating tumor cell,CTC)已经被用来预测ICIs治疗NSCLC、结直肠癌、前列腺癌患者的疗效[17]。ICIs通过阻断CTC上的免疫检查点(PD-1和PD-L1),激活免疫系统,消除血液循环中的CTC,为减少恶性肿瘤的复发和转移提供新的途径。为了评估肿瘤中的PD-L1表达,组织PD-L1活检是一种常见方法,但是这种方法会给患者带来一定的痛苦和并发症风险,且有限的样本可能不足以代表整体肿瘤异质性。因此基于CTC的液体活检可以作为PD-L1表达分析的补充诊断工具,弥补了PD-L1检测的技术问题[18]。基于CTC上的PD-L1表达,NSCLC患者在接受了6个月的PD-1i nivolumab治疗后,PD-L1(-)CTC组取得了临床获益,而PD-L1(+)CTC组经历了进展性疾病,这表明,PD-L1(+)CTC组的持续存在可能反映了一种治疗逃逸机制[19]。有研究发现[20],除了NSCLC之外,CTC也是头颈部恶性肿瘤复发转移的预测因素,使用PD-1i nivolumab治疗头颈部肿瘤后,CTC阳性患者的PFS较短,而PD-L1(+)CTC患者的预后更差。尽管CTC具有较高的预测潜力,但CTC的表征仍然受限,因为它们的发生率极低且生命力短[17]。因此,关于CTC作为预测标志物的研究仍有待完善。
2.4 肿瘤浸润淋巴细胞
肿瘤浸润淋巴细胞(tumor-infiltrating lymphocytes,TILs)是分布在肿瘤细胞簇和间质中的单核免疫细胞,通常用苏木精-伊红(HE)染色并在光学显微镜下进行半定量评价[21]。由于ICIs的作用需要肿瘤细胞临近的淋巴细胞参与,因此TILs浸润程度也可以作为预测疗效的生物标志物。在癌组织中,TILs主要由CD8+和CD4+T细胞组成,其次是调节性T细胞(Treg)和B细胞[22]。TILs,尤其是CD8+T细胞浸润,往往表明免疫治疗反应和预后均良好[23]。在三阴性乳腺癌患者中,高CD8+TILs的浸润与ICIs的高反应率相关[24]。既往研究表明[25],与传统的细胞毒性化疗相比,肿瘤组织和肿瘤边缘中高CD8+TILs浸润的转移性黑色素瘤患者对免疫治疗反应更明显。另外,经ICIs有效治疗后,肿瘤组织中CD8+T细胞的增殖与影像学上的肿瘤缩小直接相关[26]。研究发现[27],接受PD-1i pembrolizumab有效治疗的NSCLC患者,其基线活检标本的CD8+和切缘浸润数量远远高于疾病进展患者。相信随着研究的深入,将TILs与PD-L1或TMB表达状态相结合而建立的综合预测模型终将成为肿瘤免疫治疗最精准的生物标志物。
2.5 其他肿瘤微环境因素
肿瘤微环境(tumor microenvironment,TME)中的许多细胞因子和肿瘤细胞的外泌体可以诱导PD-L1的表达,促进肿瘤免疫逃逸。TME主要由血管系统、细胞外基质、肿瘤周围的非恶性细胞以及维持微环境内联系的复杂信号分子网络组成。这种成分促进了恶性细胞的生长、增殖、侵袭和转移。携带非编码RNA的细胞外泌体是TME中的另外一种成分,可促进肿瘤细胞增殖与演化[28]。IL-12与IL-6能够在T细胞受体活化后,通过改变PD-1基因组的染色质结构以及通过活化STAT3/STAT4增强PD-1的转录,促进PD-1表达[29]。有研究表明[30],由于CTLA-4在Treg上的构成性表达,CTLA-4i的效果依赖于治疗期间Treg的消耗程度。肿瘤细胞外泌体能够促进单核细胞极化为M2巨噬细胞,并通过STAT3磷酸化促进PD-L1在M2巨噬细胞中的表达,进一步增强免疫抑制作用[31]。TME中炎症因子的高表达可能是导致免疫治疗效果不佳的一个重要因素,未来抗炎药物和ICIs的联合使用也必将会给癌症患者带来更好的治疗效果。
2.6 肠道微生物群
近期在小鼠异种移植实验中,Routy等[32]观察到广谱抗生素或特定无菌环境明显影响PD-1i或CTLA-4i治疗的疗效,在NSCLC患者中也观察到了类似的现象,在37例接受nivolumab治疗的晚期NSCLC患者中,具有良好肠道微生物群的患者(如具有高多样性的患者)表现出记忆T细胞和自然杀伤细胞增强的特征,推测使用抗生素引起肠道微生物失调可能会影响小鼠肿瘤模型和癌症患者行ICIs治疗的疗效。Matson等[33]研究了转移性黑色素瘤患者的肠道微生物组对其免疫治疗反应的影响,并对应答组和无应答组患者进行了隔离。对免疫治疗前的粪便样品进行基因组测序发现,应答者中8种微生物的丰度增加,包括长双歧杆菌(Bifidobacterium longum)、柯林斯菌(Collinsella aerofaciens)和粪肠球菌(Enterococcus faecium)。另有两种微生物也与无应答组密切相关(Ruminococcus obeum和Roseburia intestinalis)。用应答组患者的粪便对无菌的荷瘤小鼠进行微生物群移植,显示出良好的肿瘤控制和对PD-L1i治疗应答,表明肠道微生物群多样性和组成的动态变化特征可能对ICIs疗效和疾病预后有影响。Li等[34]研究同样表明,在对ICIs治疗有反应的肝癌患者中,肠道微生物群的多样性明显增加,柔嫩梭菌属(Faecalibacterium)菌量高的患者的PFS明显延长,拟杆菌属(Bacteroidales)菌量高的患者的PFS则缩短。综上所述,肠道微生物菌群组成可能是肿瘤免疫治疗的疗效预测标志物之一,通过菌群移植等方式调节肠道微生物群有望成为一种肿瘤免疫治疗的辅助疗法。目前对肠道微生物菌群与宿主对肿瘤患者免疫治疗的反应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仍不清楚。
2.7 DNA损伤修复
当人体DNA出现损伤的时候,DNA损伤修复(DNA damage repair,DDR)基因会立即对DNA损伤进行修复,这类基因包括ERCC2、BRCA1、BRCA2、ATM、CDK12。既往研究报道,在接受PD-1i/PD-L1i治疗的转移性尿路上皮癌患者中,DDR基因的突变可以预测疗效[35]。该研究对接受PD-1i/PD-L1i治疗的患者进行了基因组测序,结果显示,DDR突变患者(包括ATM)的客观缓解率(objective response rate,ORR)显著升高(41%vs.21%)。DDR突变(不包括ATM)患者的OS没有明显延长,可能是因为样本量小(n=6)。ATM突变患者(n=53)的ORR显著增高(40%vs.29%),OS显著延长(HR=5.7,95%CI:1.65-19.74,P=0.006)。另外,CDK12中的突变可导致DNA累积损伤及免疫原性新抗原的形成。Wu等[36]研究评估了360例晚期前列腺癌男性患者的肿瘤DNA,其中,在11例CDK12基因突变患者中,共有4例去势抵抗性前列腺癌患者接受了ICIs治疗,有2例患者前列腺特异性抗原(prostate-specific antigen,PSA)含量明显下降。这一结果暗示,对转移性去势抵抗性前列腺癌患者而言,CDK12基因的失活可能增加其对免疫疗法的响应性,值得进一步研究。
2.8 错配修复缺陷和高度微卫星不稳定性
错配修复缺陷(mismatch repair,MMR)是一种重要的避免基因复制错误的机制,它可以防止突变、修复复制过程中的聚合酶错误,对遗传基因的稳定至关重要。多项临床研究表明高度微卫星不稳定性(microsatellite instability-high,MSI-H)/错配修复缺陷(deficient mismatch repair,dMMR)患者更有可能从免疫治疗中获益[37]。另外,FDA已批准PD-1i pembrolizumab用于治疗MSI-H/dMMR表达阳性实体瘤[38],这项批准是基于5项多中心临床试验,涉及结直肠癌、子宫内膜癌、乳腺癌和其他消化道肿瘤在内的15种肿瘤类型,来验证PD-1i pembrolizumab治疗携带MSI-H或者dMMR实体瘤患者的有效性和安全性,结果显示,39.6%的患者达到了完全或部分缓解,78%的患者药物反应持续时间为6个月以上。CheckMate142研究证实,与PD-1i nivolumab单药治疗相比,经PD-1i nivolumab和PD-1i pembrolizumab联合治疗具有MSI-H/dMMR的转移性结直肠癌具有更强的免疫应答[39]。近期一项临床试验更是支持了这个观点,在KEYNOTE-177试验[40]中,总共307例转移性MSI-H/dMMR结直肠癌患者被随机分为两组并接受PD-1i pembrolizumab或化疗两周直到病情进展,主要终点是PFS和OS。在中位随访时间为32.34月时,PD-1i pembrolizumab组PFS和OS分别达到16.5月和43.8%,显著高于化疗组的8.2月和33.1%,另外PD-1i pembrolizumab组发生3~4级irAEs的风险也显著低于化疗组(22%vs.66%)。
2.9 POLE基因突变
POLE基因突变的肿瘤组织可以迅速积累大量的体细胞突变,进而促使肿瘤特异性新抗原的产生,这种现象显示了肿瘤发展的一种新机制。POLE突变被认为是预测结直肠癌、子宫内膜癌患者ICIs疗效最具前景的生物标志物之一。Stasenko等报道了23例微卫星状态稳定且携带POLE EDM突变晚期子宫内膜癌患者,在接受ICIs治疗后,临床症状得到显著改善,持续缓解时间达到14月[41]。Chen等[42]报道一例携带POLE F367S突变晚期结直肠癌患者,在接受PD-1i pembrolizumab单药治疗后,其中位PFS达到49月,CEA趋于正常和肿瘤负荷减少,并且该患者的微卫星状态处于稳定。以上均提示在结直肠癌和子宫内膜癌治疗领域,POLE突变是独立于微卫星不稳定状态的免疫治疗预测标志物。因此,在临床实践中,联合检测POLE突变与微卫星不稳定状态可以更加全面地指导这部分患者接受免疫治疗。
2.10 免疫细胞
2.10.1 淋巴细胞与单核细胞的比值 2020年,一项回顾性分析研究了使用PD-1i的晚期肿瘤患者淋巴细胞与单核细胞的比值(lymphocyte and monocyte ratio,LMR)的预后价值,以确定患者可能对PD-1i有更好的反应[43]。利用受试者的工作特征曲线划定LMR的最佳截止值,将患者分为高表达LMR组和低表达LMR组。研究结果表明,高、低LMR组6周的ORR分别为32.7%和7.6%。LMR-6周与PD-1i治疗效果显著相关。另一项研究将接受PD-1i pembrolizumab的NSCLC患者按照血液学特征分为两组,27例低表达组(LMR<0.54)和24例高表达组(LMR≥0.54),LMR低表达组中位PFS为7.81月,而LMR高表达组为1.41月。LMR低表达组中位OS为14.06月,而LMR高表达组为1.97月。在12和24月时,低LMR组的OS率分别为64.6%和24.2%,高MLR组12月的OS率为29.20%,24月后该组没有幸存者[44]。
2.10.2 中性粒细胞与淋巴细胞比例 Afzal等[45]将黑色素瘤患者接受ICIs治疗后6周内的NLR设为基线值,发现低中性粒细胞与淋巴细胞比例(neutrophil and lymphocyte ratio,NLR)基线值与ICIs疗效预测密切相关。分析结果表明,低NLR组中位PFS为8.3月,而高NLR组中位PFS为2.6月。NLR高表达组中位OS为23.5月,而低NLR组中位OS未达到。近期一项研究分析了NSCLC患者接受PD-1i pembrolizumab治疗后的血液学特征,33例为低表达组(NLR<5.6),18例为高表达组(NLR≥5.6),研究结果显示,NLR低表达组中位PFS为8.51月,而NLR高表达组中位PFS为0.70月。NLR低表达组中位OS为20.30月,而NLR高表达组中位OS为1.21月。低NLR组患者的12月和24月OS率分别为73.9%和30.8%,而在高NLR组,无患者存活12月[44]。
3 总结与展望
由于免疫调节机制的复杂性和恶性肿瘤的异质性,联合治疗代表了临床治疗的下一波浪潮,能够克服单药治疗的局限性。PD-1通路阻断在部分患者中引发了持久的临床反应,这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有效的T细胞浸润和效应T细胞在TME中的功能。到目前为止,联合治疗建议针对癌细胞与正常细胞分化的多种异常,主要包括降低TMB和提高肿瘤免疫原性(如与化疗、放疗和靶向治疗相结合);使用表观遗传重编程药物(GSK126和5-AZA-dC)加强效应T细胞转运;阻断其他抑制受体,如LAG3、TIM3;为共刺激分子提供激动剂以及通过免疫增强T细胞应答。
除了专注于刺激适应性T细胞介导的肿瘤消除,靶向先天免疫系统可能是一个有前途的策略。先天免疫细胞,如巨噬细胞、NK细胞、中性粒细胞和其他髓系细胞在补充T细胞的效应活动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可以从循环或TME中大量招募来支持持续的适应性反应。目前正在研究各种联合治疗方法。例如,结合靶向CD47/信号调节蛋白α(SIRPα)的免疫疗法,肿瘤细胞和巨噬细胞之间固有的抗吞噬轴被证明在血液恶性肿瘤和实体肿瘤中激发协同抗癌活性。简而言之,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先天免疫效应剂对抗肿瘤免疫的潜在贡献,并将多种靶向自适应免疫系统的手段整合到免疫检查点封锁治疗中,这可能是未来免疫治疗中更有效的方法。
目前,ICIs治疗已被写入各种晚期肿瘤的临床应用指南中,但由于免疫系统错综复杂,单一治疗很难达到预期效果。在未来,随着基因组学、转录组学和免疫检测技术的进步,采用多种免疫检查点抑制剂联合治疗的方法是一种新的发展趋势,通过计算生物学、生物信息学等新的方法建立综合的生物标志物评价体系可以更加全面地预测免疫检查点抑制剂疗效,从而推动肿瘤精准医学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