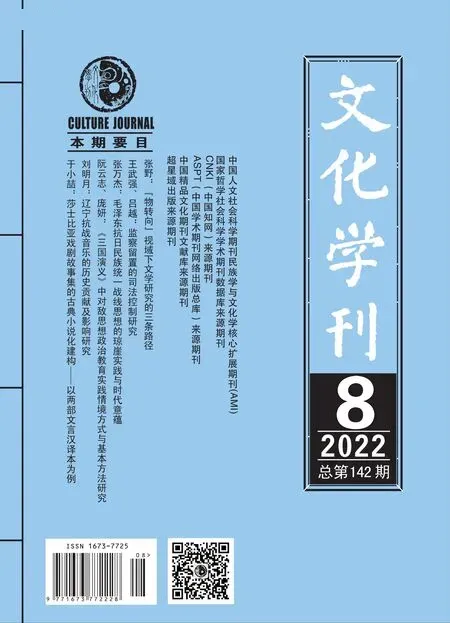司马迁与司马光史学思想比较
——以李广形象塑造为例
肖亚楠
“文学与历史”孰是孰非?这是历代学者感兴趣的话题。在最能体现这两种论题的《史记》与《资治通鉴》这两部巨作中,“李广难封”历来都是文人墨客感兴趣的历史与文学现象。《史记》是纪传体,《资治通鉴》是编年体,体例的不同客观映射了作者面对相同现象时的不同表现。本文从司马迁与司马光对李广这一形象的塑造入手,在解读文本的基础上比较、分析造成司马迁与司马光不同史学思想的原因。
一、《史记》与《资治通鉴》对李广形象塑造的不同表现
(一)叙述方式不同:司马迁以人为主,司马光以事为主
《史记》的纪传体体例使得司马迁在塑造人物时以“人”为中心,时间与事件是丰富人物的手段与素材。《资治通鉴》的编年体体例却让司马光把人作为时间与事件的“要素”,人是事件的“填充物”,是时间数轴的坐标点。
以李广为例,《史记》以“李将军广者,陇西成纪人也。其先曰李信,秦时为将,逐得燕太子丹者也。”[1]1462开头,从李广的先祖开始讲起,说他家世代为射,家族传统优良。接下来用大篇幅分别介绍了李广在文帝与景帝时的辉煌过去,以典属国公孙昆邪的原话强调“李广才气,天下无双”。[1]1462接下来从汉武帝即位开始,详细地讲述了李广与程不识治军的优劣,用程不识来衬托李广的治军的高超。“是时汉边郡李广、程不识皆为名将,然匈奴畏李广之略,士卒亦多乐从李广而苦程不识。”[1]1464李广因“马邑之谋”事件如何被贬也记叙得非常清楚。司马迁甚至用了大量的笔墨叙述被贬谪后的“李广射虎”事件来加强李广形象的立体性。直到后来李广如何被起用,如何在对匈奴的战役中受尽不公的待遇,最后含恨而亡,作者都倾注了大量的情感。为了表达对李广的同情,司马迁甚至在此传中加入了李广儿子甚至孙子李陵的描写,一定程度上强化了李广作为“飞将军”的人物形象。司马迁用“及死之日,天下知与不知,皆为尽哀。彼其忠实心诚信于士大夫也!”[1]1467结束全文,字里行间毫不隐晦地表达了自己对李广的肯定与深厚感情。
相反,《资治通鉴》对李广的塑造只是将这一人物置于“世宗孝武皇帝上之下元朔元年(前128)”“世宗孝武皇帝上之下元朔元年(前128)秋”“世宗孝武皇帝中之上元狩四年(前119)”三个时间段里,简单地介绍了李广在这三个时间段里出现的情况。分别是李广在行军途中遭遇匈奴袭击机智脱险的故事、李广拜为右北平太守击退匈奴的故事、李广随卫青抗击匈奴受到不公平待遇的故事。司马光叙述客观、冷静,止于叙事。他在塑造李广形象的时候并没有引入例如“李广射虎”“程不识”等事件,目的也是摈弃一些带有浓重主观情感的塑造技法。对于李广之死,司马光也只是冷静地叙述了一句“遂引刀自刭”。虽然后面也发表了一些如“广为人廉,得赏赐辄分其麾下,饮食与士共之,为二千石四十余年,家无余财。猿臂,善射,度不中不发。将兵,乏绝之处见水,士卒不尽饮,广不近水,士卒不尽食,广不尝食。士以此爱乐为用。”[2]649的感慨,但总体上情感不如司马迁浓烈。
(二)叙述态度不同:个人情感支配司马迁,客观事实支配司马光
在对文本的分析中很容易看出,司马迁对人物的描述是带有强烈的个人感情的。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说“夫人情莫不贪生恶死,念父母,顾妻子;且勇者不必死节”[3]这句话的感情真实而具有人情味,丝毫没有官方口气。对比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对李广的塑造,这种主观感情甚至一度“夸张与过分”。《史记》对李广的塑造中,司马迁多次引用旁人语言来证明自己对李广的赞赏并不过分。例如他引用了汉文帝的原话“惜乎,子不遇时!如令子当高帝时,万户侯岂足道哉!”[1]1462来证明李广的价值。另外,典属国公孙昆邪的为“李广才气,天下无双,自负其能,数与虏敌战,恐亡之。”[1]1462连匈奴单于也素闻李广贤名“得李广必生致之。”[1]1464都充分证明了李广的英雄形象。司马迁利用他惯用的“春秋笔法”通过直接叙事、间接叙事以及设计其他众多人物形象来衬托李广的方法。比如文帝、景帝对李广才能的赞赏、单于对李广的称赞、程不识事件的记载、卫青故事的穿插其中、李广数次遇险而机智摆脱等等都充分显示了司马迁对李广的“情感深厚”。
相反,司马光《资治通鉴》中关于李广的四段叙述中没有引用任何一个外人对李广的评价。作者就如一个写记叙文的小学生一样,只是客观地叙述了人物、时间、事件、地点,故事的前因后果等等。读《资治通鉴》里的李广,就如读众多人物中的一个,读者根本不能从作者的叙述中体会到作者想要表达的浓烈情谊。司马光把李广看成是汉武帝时期一个普通的将军,他的经历、他的曲折以及在司马迁那里所描述的“委屈”都没有在司马光的笔下呈现。作者将李广和其他汉武帝时期的将领一样放置在武帝统治时期的大背景下,用第三人称的叙事方法介绍了他的一生,李广的一生仅仅是穿插在众多的政治叙事之中、战争叙事之下、统治者思想变化的一个侧影。司马光用始终如一的客观态度与笔调,止于叙事而已。
二、司马迁与司马光不同的史学观
从对李广这一人物的文本分析之中可以看出,司马迁与司马光的史学观是不同的。司马迁综合了先秦时期各种历史概述的表达形式,在写历史中写人物,写人物中讲历史进程。他完全是在写人物中实现“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学理想。正如班固在《汉书》中所论述的“是非颇缪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力而羞贫贱”(《汉书》卷六二《司马迁传》)。金圣叹在《读第五才子书法》中也说“大凡读书,先要晓得作书之人是何心胸。如《史记》须是太史公一肚皮宿怨发挥出来,所以他于游侠、货殖传特地着精神,乃至其余诸记传中,凡遇挥金杀人之事,他便啧啧赏叹不置。一部《史记》只是‘缓急人所时有’六个字,是他一生著书旨意”。司马迁写史记,除了是为继承父亲之遗嘱,更重要的是“成一家之言”。他注重的是人,他认为人是历史的创造者,人是历史的推动者,人的精神是文化中最具有价值的一部分。
相对于司马迁以“人”为主的史学观来说,司马光的史学观中更重要的是政治责任感。司马光认为史著的目的是“穷究治乱之源,上助圣明之鉴”,他的目的与出发点就是为了在历史事件与人物的记叙中总结经验教训,给统治者提供资料与经验辅助君上治理国家。与司马迁不同,司马光在挑选历史事件与人物时格外重视与政治相关的资料,比如司马迁爱的文化名人、文坛雅事、剑客侠士、商人贩旅等等都不受司马光的喜爱。即使是著名的文人雅士也只是与政治有关他才会费笔墨加以记叙。对于皇帝这类特殊人群,司马光或赞扬或抨击。遇到好的帝王,他不吝啬溢美之词大加赞扬,详细记载丰功伟绩、硕果累累;遇到暴政者,他也从各个方面帮助读者分析造成不良后果的原因;这些喜恶如此分明的取舍目的就是政治的需求。司马光在《资治通鉴》卷一中就强调“何为礼?纪纲是也。何为分?君、臣是也。何为名?公、候、卿、大夫是也。夫以四海之广,兆民之众,受制于一人,虽有绝伦之力,高世之智,莫不奔走而服役者,岂非以礼为之纪纲哉!是故天子统三公,三公率诸侯,诸侯制卿大夫,卿大夫治士庶人。贵以临贱,贱以承贵。上之使下犹心腹之运手足,根本之制支叶,下之事上犹手足之卫心腹,支叶之庇本根,然后能上下相保而国家治安。”[2]2司马光的“资治”意识不仅体现在“臣光曰”上,而且在“正统之争”“礼乐教化”“宦官问题”“君臣之际”等多个问题上论述严密客观。
三、司马迁与司马光史学思想不同的原因
(一)历史文化背景不同
司马迁生活在汉武帝时期,汉朝经历了高祖、文景之后进入了经济相对稳定的时期。但由于边境少数民族的滋扰不断,国家在连年征战中虚耗过度。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思想的影响,中央集权意识的强烈需求让统治者从巩固中央集权的方面考虑将儒家思想变作护身符。汉朝也从一开始的无为变作有为。个人英雄主义的文化鼓吹也使汉武帝时期的战争变得必要而激烈。司马迁深受家族史学传统的影响,他在《太史公自序》中详细地介绍了他父亲对他的影响,乃至整个司马家族在“史官”这条道路上的文化传统。特别是司马迁父亲死前嘱咐一段尤为感人,太史公执迁手而泣曰“余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尝显功名于虞夏,典天官事。后世中衰,绝于予乎?汝复为太史,则续吾祖矣”[4]1770司马迁就是在这样的家族传统和历代的文化背景下开始创作《史记》。因此,他的史学思想是在多维度的关照“人”“人的历史”而不是为统治者寻找治国方法的背景下形成的。
相反,司马光生活宋真宗晚年到宋哲宗即位初期,这个时期是“社会经济、制度建设、科技文化领先于世界的时期;同时也是周边被挤压、内政因循求稳、面临严峻挑战的时期,战略格局与政策应对有诸多问题的时期”。[5]文化上,经过隋唐科举制度的发展,国家政治体系再也不是由世族大家垄断,由于统治者自身的特殊经历,“重文轻武”的思想指导使得宋初期的文化氛围十分宽松,数量众多的士子通过科举考试脱颖而出。传统儒家思想中“学而优则仕”的文化动力使得知识分子在“天下”“家国”“先天下之忧而忧”的忧患意识下产生的责任感得到了极大的满足,士大夫的“资治”意识逐渐加强,参与国家政治建设的责任感得到了空前的提高。在经济和军事上,与宋朝廷同时发展起来的契丹、党项、女真、蒙古各个民族,他们分别建立了辽、西夏、金、元,北方民族的强劲给宋带来了压力,在这样的压力之下,又加上唐五代的惨痛记忆还没有从民族记忆里散去,宋朝的内政在这个时候就显得特别谨慎,统治者决定建立一套纲纪制度来保证对治国理念的实现。面对朝廷的“内忧外患”,宋朝初期士子对治国理念的确立与改革格外热心,无论是“庆历新政”,还是后来的“熙宁新法”都是这个大国治国实践的真实反映。面对如何治国这一封建中央集权时期的永恒话题,《资治通鉴》是司马光实现治国真理的实践尝试。“资治”是一种治国的理念与意识,准确地说就是“戒惕忧患、期待治世”,在这种理念的指引下,司马光将一种严肃的考辩思想引入他的史学思想之中。
(二)个人史学审美追求不同
李长之先生认为司马迁属于“浪漫的自然主义”。虽然司马迁的父亲希望儿子做第二个孔子,司马迁也在儒家思想的浸润中获益匪浅,但是司马迁性格上却受到道家的深刻影响,可以说自然主义的无为精神是他哲学和审美的根底。特别是评论一个人的成败,他基本用的都是道家的观点。例如在谈及项羽、韩信、周亚夫等人时,司马迁极力阐述这些人不懂得老子“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的道理。自然主义的哲学审美追求使得司马迁的情感爆发常处于不控的地步。他因李陵之事而受到宫刑,因而对李广的塑造难免有同情之嫌。特别是在《李将军列传》与《报任安书》中过分夸张其战功,大篇幅地为李广家族纪事,并为李陵的投降变节辩护等等,这些都可以看作是司马迁自由情感的外露,而不是一本正经地说教。例如《太史公自序》中面对壶遂的突然追问“孔子之时,上无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断礼义,当一王之法。今夫子上遇明天子,下得守职,万事既具,咸各序其宜,夫子所论,予以何明?”太史公曰“唯唯,否否,不然”[4]1772几字形象地写出了司马迁不敢正面回答,害怕触及时代禁忌,陷入狼狈的样子。这里完全看不出作为政府官员的形象,反而是一个自由写作人的样子。另一方面,自由浪漫的审美取向让司马迁始终秉持“变”这一史学理论,在《史记》中随处可见他对变化的理解“为天数者,必通三五,终始古今,深观时变,察其精粗,则天官备矣”(《史记·天官书》)“是以物盛则衰,时极而转,一质一文,终始之变也”(《史记·平淮书》)“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史记史记·报任安书》)等等。
司马光在“资治”意识的影响下,在传统儒家思想的熏陶下,在对“理想秩序”建立的期望下,结合自己本身是一位注重纪纲、处事笃实的政治人物,他的史学观决定了他的审美是客观、求是、尽可能剔除个人好恶而尽力为君主与国家服务的。例如他与王安石讨论“变法”问题时提出的观点。王安石主张“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三不足精神”,司马光却认为“治天下譬如居室,弊则修之,非大坏不更造也,大坏而更造,非得良匠美材不成”的稳进改良主张。他论事论人客观通达,特别是对君主的得失毫不隐晦,在礼乐教化的目标下,给当政者提供“何为君道”的途径。他提倡儒家“为政先礼,礼其政之本与”的思想。特别是对唐末五代十国时期的政治进行大篇幅的介绍,力图给当政者以警惕。总体来说司马光《资治通鉴》编制目的就是为统治者寻求治国理政的方法,对秩序的建立起到推动作用。
四、结语
综上,从对同一历史人物李广的描述中可以看出,司马迁与司马光由于受到不同史观的影响呈现给读者的李广形象是不同的。分析历史背景、文化渊源以及个人审美的不同对司马迁与司马光的史观形成的影响有助于我们从各个角度深入地研究《史记》与《资治通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