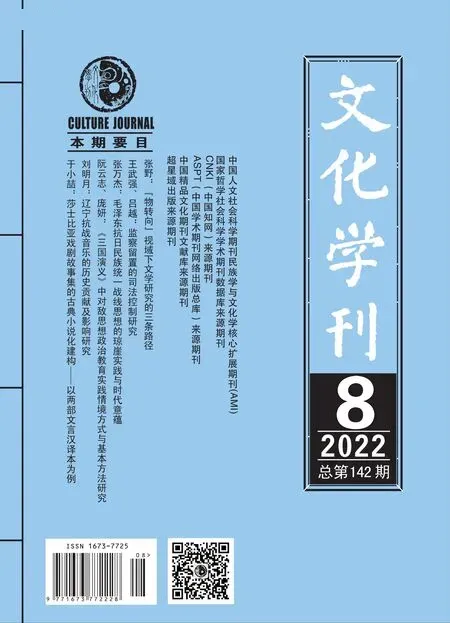殉国话语的古今之辩
初翠菊
如果我们以死亡——这个一切宿命之中最终极的宿命——作为起点来考察民族主义的文化起源,也许会有所助益。[1]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
“死亡”话题在中国一直以来都讳莫如深,子曰:“未知生,焉知死”,(1)语出《论语·先进》:“季路问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曰:‘敢问死。’曰:‘未知生,焉知死?’”这段对话体现出孔子以及儒家文化强调人活在世上,应该重人事,不应将精力用于思考死亡和死后的事情上。主动选择死亡不被认可,因为“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2)语出《孝经·开宗明义》:“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唯一例外是在生与死、大义与屈从的权衡中,为了国家利益选择牺牲生命。这是唯一被认可的赴死行为,是被纪念和歌颂的“殉国”行为。
到了近代民族危亡之际,“殉国”话语更经常出现在日常叙事中。大家都谈殉国和殉国精神。然而什么是殉国?这个看似不证自明的问题,实则包含了传统与现代的二重性。如果将殉国定义为中国自古以来的民族传统,在当下看来,岳飞、文天祥更确切地说,应该是忠臣、殉道者。他们所尊崇的信念与近代以来为了民族国家而死的“殉国”有根本的区别。如果将殉国话语定义为近代民族国家观念产生之后的民族认同,那么与世界上其他民族国家横向对比会发现,各个国家对民族英雄的追忆都不尽相同,对“殉国”概念的定义也并不一致。而且吊诡的是,同一个历史事件,不同国家有着不同的解读。中国讴歌的是革命英烈保家卫国、舍身忘死的自卫行为。有的国家却走得太远了,会祭奠发动战争的主将,会利用始祖传说去其他民族国家寻根,等等。不难发现,怀念自己国家民族英雄的行为已经在全球范围内形成一种普遍性共识,然而却是具有自圆性和强烈排他性的共识,民族国家观念的普遍认同不能代替民族国家英雄观念的普遍性认同。因此,了解中国“殉国”观念形成的文化传统和现代语境,有助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更好地审视当下民族、国家间话语冲突和不同文化身份认同之间的冲突问题。
一、“殉国”内涵之演变
“殉国”现在通行的含义是为了国家利益献出生命。“殉国”一词最早出现在扬雄《太玄经》中。《太玄经·勤》:“次八:劳踖踖,心爽,蒙柴不却。测曰,劳踖踖、躬殉国也。”[2]指的是对国事勤恳辛劳,以至献出了生命。到晋代,殷仲文《解尚书表》:“进不能见危授命,忘身殉国;退不能辞粟首阳,拂衣高谢。”[3]“殉国”的意义转变为在国家危难之际,将生死置之度外的行为、精神。到了宋代,对中原正统文化的强调以及与周边少数民族不间断的战争,于危亡中维护正统已经不再是一种个体行为,而是一种普遍认同的精神。“殉国”专指为了维护国家正统在对外战争中献出生命的做法,并且被赋予了比生更高的价值,殉国开始成为最光荣的死法。《太平御览·兵部四十三·决战中》“我为大臣,以身殉国,不亦乐乎。”[4]至此,殉国的含义基本固定下来,为历代沿用。对殉国行为的高度赞扬在战时起到了凝聚人心,同仇敌忾的作用,而当国难解除后,“殉国”话语就悄然退场,直到统治危机再次出现。19世纪中叶以来,中国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变局,面对外侮,激发出植根于文化传统中的殉国精神。林则徐道:“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殉国话语再次发挥其鼓舞作用,即便在应对帝国主义军事进攻中屡战屡败,也未能动摇人民保卫清朝的决心。
庚子事变之后,清政府被认为无法带领全国人民摆脱帝国主义的剥削走向“现代”,因而在全国上下出现了统治危机,革命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汪晖认为“20世纪是一个激烈地反对旧世界也激烈地反对自身的世纪。”[5]71一直以来被信奉的三纲五常,中国人不恤为之奉献生命的“君”和“朝”,成为了中国摆脱民族危机的障碍。这时的“殉国”的定义仍是为了国家的利益不惜牺牲生命的精神,殉国主体还是有识之士和爱国人士。不同的是,在民族生死存亡之际,古代中国为之殉国的“君”和“朝”,现在变成是哪怕殒身殉国也要攻击的靶子之一。“殉国”行为的目的在于建立一个民主共和的“中国”,一个现代民族国家,“殉国”话语拥有了现代内涵。这个愿望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而变得越来越迫切,影响范围从知识分子和革命阶层逐步扩展到工人、商人、城市平民,以至共产党领导革命后的农民、小生产者。“殉国”话语的影响也深入人心。
概言之,当下“殉国”的通行含义是在北宋时期形成的。宋代在之前的基础上,沿用“殉国”这个语言符号的能指作用,转变了所指范围,对内的牺牲是奉献,对外的牺牲是殉国。在近代民族危机之际,“正统”观念的内与外被现代民主政权与封建政权,被“民族国家”观念的中国与外国所取代。至此,“殉国”的所指为民族国家中的“国”,并被固定下来。
二、近代民族国家观念的兴起与爱国内涵的重置
19世纪时期,中国在西方人眼中是半开化的国家,世界上流行着一套以西方为中心的“文明等级论”,文明等级论最核心的观点在于建构一个以西方人为榜样的“文明世界”,而一切不符合所谓“文明”标准的行为则被认为是半文明人,甚至是野蛮人。并将此作为一种价值观念,对内传递西方中心价值,对外通过军事、物质产品以及文化等方式传播推介,使殖民地地区以及受剥削地区人民逐渐将此内化为一种民族的心理状态。在处理国际事务中,非“文明”人呈现出自卑情绪,以及无意识的自我否定的行为。在西方普遍主义话语之下,中国面临两个迫切的问题,一是解除民族危机,二是求得更好的发展。向西方学习,似乎是唯一的出路。要融入西方所构建的民族国家话语体系之中,否则就有亡国的危险。汪晖认为,20世纪的中国,“在经历一系列‘文化革命’之后,人们开始以一种普遍主义的方式将历史中的不同共同体称为古代国家、中世纪国家或近代国家,并将中国或其他非西方历史中的政治共同体贬低为帝国、王朝、部落、酋邦。”[5]50
在建构文化共同体和现代民族国家过程中,有意将中国古代文化传统与现实勾连,通过文化认同构建中国式民族认同。在文化广度上,比如在清末新政时期,在为教科书命名时,“中国”已经开始被用作国名,而不是用大清。比如在《奏定学堂章程》将学科科目命名为“中国历史”“中国地理”。在文化历史纵深问题上。反复强调祖先传说、历史传承以及几千年来的“中国”传统,强调绵延的文化影响力在发挥民族凝聚力方面的重要作用。将历史上在“中央之国”大地上的“中国”历史高度抽象化。在引入“国家”的概念之际,清末将“中国”译为民族国家(nation state),这种翻译方式虽然是在nation和state的基础上翻译过来的,但却与欧洲以民族为国家并不相同。中国不强调以民族为国家,也不强调民族的同质化意义,而是反复追溯文化渊源,反复强调中国文化在国家危亡之际的现实意义。
民族国家成为了线性发展规律中更优越的、更先进的人民组织形式。无论是否愿意,中国被裹挟到了世界民族国家体系之中。从民族国家角度来看,古代殉国为的是一家一姓的朝廷,或者是汉族政权。他们不惧生死的精神,在维系中原正统的儒家观念,强调其文化的先进性和统治正当性上起到了向心力的作用。三纲五常虽已被认定为限制个体生命发展,封建王朝也早已随风逝去,但古代殉国精神却能和民族国家认同重新结合,发挥其呼吁民众,保卫国家的重要作用。
三、民族独立诉求与爱国精神的升华
经历了国家观念的变革及信念的变更,为国不畏死的精神成为具有时代特征的崇高品格和讴歌范畴。
1904年,陈独秀在《安徽风俗报》上发表《说国家》一文来辨析国家与国民之间的关系。“我生长二十多岁,才知道有个国家,才知道国家乃全国人的大家。”(3)《安徽俗话报》第5号,1904.在民族国家建立之后,“国”的观念被单独提炼出来,与个体的小家分离,与传统的大家庭分离,强调“国”对于“家”的重要性。“救国”作为从晚清以来到民国时期一贯主题,由“国”之概念植根于心到为国捐躯,经历了“五四”运动等一系列爱国救亡运动,到了抗日战争时期人们对“国”的认同达到顶峰,国家成为了新的共同信仰。2020年上映的电影《八佰》 成为一部现象级的电影,它如投石入水,引来片片涟漪,一部讲述抗日时期爱国救亡的故事收获了众多的鲜花与眼泪,其中最感人的情节莫过于烈士殉国的壮烈场面。慷慨赴死行为具有了震撼人心的气魄和强烈的鼓动作用。为国不畏死的精神是特殊时期的必要选择,也是和平时代共同追怀的民族楷模。“讲述一个关于英雄的故事, 是对一个民族历史、现在、未来进行积极判断与响亮召唤的过程;聆听一个关于英雄的故事, 则是民族成员确认自身对于民族共同体的归属感, 增强民族自豪感, 并将民族精神内化为自身生存准则的重要途径。”[6]
因而,对民族共同体的认同,实际上是在现代民族国家独立和解放的要求基础上,将个体无限的爱国精神,转化为具体的爱国实践,最后通过艺术化升华的场景,实现了追思和教育的意义。
四、好生恶死传统与为国牺牲行为之间的强烈张力
自古以来,伤害自己生命的行为是不被赞同的,珍惜生命则被视为美好的品质。《吕氏春秋·贵生》篇中说到“圣人深虑天下,莫贵于生……若王子搜者,可谓不以国伤其生矣。此固越人之所欲得而为君也。”圣人认为天下的事,没有什么比生命更重要的了,王子搜害怕做国君而引来杀身之祸,越人反而认为王子搜如此爱惜生命,而想让他当国君。哪怕是在受辱之后,忍辱负重仍被视为勇士之举。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以文王等“发愤”的事例为榜样,认为“且勇者不必死节,怯夫慕义,何处不勉焉!仆虽怯懦,欲苟活,亦颇识去就之分矣,何至自沉溺缧绁之辱哉……恨私心有所不尽,鄙陋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在“去就之分”,也就是死生的界限中不一定要追求节义,而是要活在世间,才能有功业传世。子期去世之后,伯牙不再抚琴(而不是就死),二者的友谊被视为绝唱。民歌《孔雀东南飞》创作于建安时期,后始终不登大雅,这与作品主人公轻生的行为不无关系,而在近代以后,一下子成为普遍歌颂的爱情故事。“好生”传统在古时占据的主流地位。
到了宋代以后,当汉文化传统受到威胁之时,在保全生命与忠君爱国之间需要做出选择,无论在世的是明君、庸君还是昏君,都要忠义,忠君,不能效忠异族统治,从千年以来对岳飞行为的歌颂,民间有关杨家将的传奇都能看出忠君话语的普遍认同。文天祥更将这种行为艺术化升华为“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好生恶死的传统在与死节的权衡中,英勇就义被认为是懦弱,“忠义”与“好生”之间的强大张力,使得就义行为显示出极其强烈的悲剧意味。到了20世纪,在现代民族国家危亡的背景下,忠君谱系已被英雄谱系所取代,尤其是现代的媒介发达,报纸杂志扩大了殉国事件的传播范围,使更多的读者了解到殉国英雄的故事(或者说被加工过的英雄故事)。人本身具有生的渴慕和死的恐惧,而为了保卫国家甘愿赴死,殉国的意义冲淡了死亡行为本身带来的恐惧。好生与恶死之间的矛盾冲突被崇高的意义所消解。
古代的殉国,实际上是殉朝。近代“殉国”话语上接忠君传统,下启近代爱国主义精神,继承了古代的“仁义”观,否定了其具体内容。这个转变实际上是现代民族国家观念建构时代之必然。近代中国受到西方普遍主义话语影响,亟需确立崭新的民族认同,重新定义“国家”的现代内涵是构建民族文化认同的重要方式。梁启超戊戌一代、孙中山辛亥革命一代、陈独秀五四一代都在关注国家认同的首要作用。(4)参见李泽厚.《略论鲁迅思想的发展》,《中国近代思想史论》,第470-47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l979年。可以参照的是,许纪霖也将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划分为六代,以1949年为界,可分为前三代和后三代,即晚清一代、五四一代和后五四一代,“十七年”一代、“文革”一代和后“文革”一代。参见许纪霖:《20世纪中国六代知识分子》,《中国知识分子十论》,第82页,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民族认同是至上之认同,也是全球化世界中维持国家独立地位的根本所在。全球化发展到了今天,国家安全仍然是最重要的主题,在此基础上,爱国精神则上升为至上之精神,为国牺牲的“殉国”精神也升华为一种爱国信念,爱国方向。